
话说这世上万事皆缘起,因缘生万物;万物又有灵,就此诞山川精怪,飞禽鸟兽。
大清尚书纪晓岚先生有云,事出无常必有妖。这林林总总的东西多了,便会起争端,扰世间清闲。
只是非人的东西要是搅乱伦常纲纪,也不好叫人判断,因此诸国就此暗地里建立了各自的组织。
说到这里,便要提一提那中国的六扇门——此地搜人类中的能人异士,又招神佛妖怪,为的是清查异常、解决事件。
正是因其存在,世界齿轮啮合如常。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世界半架空企划,并不会涉及南京的严肃历史事件。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并无法完美还原南京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陈知安做了个梦。她恍惚间看到有个黑色长发的女人坐在她面前,手里捧着一本硬皮书。
“嘘……外面下雪了,不用去上课。”她说,“助教总是有点特权的,我帮你请过假了。”
“学姐……”陈知安觉得应该这么叫她,“我想吃火锅。”
那个女人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优雅得像是个坐在舒适躺椅里的魔女,虽然她坐着的只是个没有靠背的硬板凳:“闭上眼睛亲爱的。睡一会。”
这场梦是暖洋洋的。陈知安不是很想醒过来。
然而有人不这么想。
她听见自己耳边冒出了咕嘟咕嘟的声音,像是煮沸的水正要逃出锅来。她怕自己父亲又一次忘了在蒸笼上的花卷,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她仿佛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动弹不得。
“小姐?小姐醒一醒,您点的鱼丸来了,要帮您下进去吗?”
陈知安猛然惊醒。
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白头发的……科长?
茶茶依旧是那副有些严肃又有些无可奈何的表情看着她,似乎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很奇怪。
她仿若被雷劈中,茫然四顾,举目皆是辣锅。对面还坐着一个头戴高帽的男人,手里拿着杯酸梅汤,那脸色活像是被扔进辣锅涮了一回又撩出来扔进辣油碟子来回拖拉三十次的面色。
再低头,雪白弹嫩的鱼丸竟然一颗颗自己跳进了覆满一层花椒的锅里,上下浮沉好似她的心率那般忐忑不安。
“您的菜上齐了。”科长……女仆说,裙边似乎有点短,但是陈知安不敢看,她捂着眼睛留出一条缝去看那人的脸色和手里的黄瓜,“要帮你切成丝吗?”
陈知安听着像是在说‘我把你切成丝吧’于是她连连摆手恐怕自己说慢一步就要被凌迟了下油锅煎炸烹煮,裹上花椒粉馋哭隔壁的辣锅。
大约是她的表情太过惊悚诡异,那人把黄瓜放下了,一瞬间陈知安觉得自己听见了黄瓜在呼唤自己的声音:“今天你直球了吗?今天你直球了吗?”
陈知安努而甩手把黄瓜拍进了墙里指着骂道:“你知道社恐有几种写法吗!”
这时陈知安余光瞥见了锅里的鱼丸,它表面似乎并不光滑,像是画在奇怪四格里的小球,不仅嘲讽的表情生动,还有眼睛和嘴巴,陈知安只觉面熟,久别重逢非少年,落花时节又逢君但如何也想不起是谁,她觉得自己大约是掉进洞里的爱丽丝,摔到了头。而对面的柴郡猫掉线了。
陈知安着急忙慌拿来漏勺一把撩起鱼丸喊道:“新乐!!你糊了!!”
鱼丸的怒号像是小狐狸吹哨子又细又响:“你才糊了!!”
霎时辣油四溅,陈知安仿若看见了黑夜中的流星,铁树银花般的光芒在眼前炸开。她抓住桌沿大喊:“麦艾斯!!”
她好不容易睁开眼,碗里的酱料却看上去有个整齐的平刘海和眼罩。正朝她微笑致以:“知安啊,鱼丸要配苦瓜拌香菜加番茄酱才好吃啊,你记住了吗?”
陈知安晕头转向拍下呼唤铃,转眼面带微笑的帅气青年就站在了她的面前,一手拿着柔软细腻白皙如萨摩耶的虾滑,一手拿白底黑字的红头文件,上书‘六扇门辞退通知’几个大字。
“您丢的是这份通知书,还是这份虾滑呢?”
一瞬间陈知安觉得看到了他背后的圣光,憧憬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涌出心头,化作嘴角一地鲜红辣油缓缓落下,她五体投地跪拜臣服大喊道:“我没丢东西!!!”
“很好,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这就把通知书和虾滑一同送给你。这是账单,请记得在前台付款。”
陈知安再抬头只能看到男人胸前闪闪发亮的红领巾,上别着的徽章,上的店长二字了。
她顾不得去听虾滑发出的神奇海螺般的喘息,虽然那像极了萨摩耶要抱抱的声音。
她拿着账单冲向前台又猛然被绊了一跤,回头望去,一条不怎么熟悉的尾巴甩在眼前。
热辣的前台小妹手里牵着红线和结账小哥一边接吻一边用尾巴把POS机递了过来。
“一共250元,谢谢惠顾!”
仿佛有一只手捏住了陈知安的四肢,她梦呓般念叨‘随一箱,随一箱’抬手扫出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当她缓过神来的时候工资卡已经空了。陈知安骇然大惊,换不择路风驰电掣跑出店门,口中只能大喊:“我不吃辣!我不吃辣!”
身后六扇门时尚火锅店的招牌依旧在黑夜中静静闪耀。
我把能找到的都找来了,真的找不齐啊!我不认识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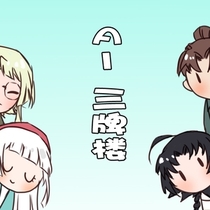
(共2287字)
春天雨后的潮湿是左筠所中意的天气,湿度与空气的比例堪称完美,他半打发时间地坐在桌子上从后面双手捏着宋和的耳朵轻搓着。理由是自己还需要学习人类的社会习惯,包括打发时间的时候用狗的耳朵和尾巴发呆,宋和有没有被说服这件事还带考量,但最终还是变成这样的局面。左筠凑过去看对方的耳朵,尖端的绒毛上会沾染着空气中的细小水珠吗?也许因为距离太近,呼吸落在小狗的耳后让他不太习惯,宋和抖抖耳朵,将手上的几份最近自己部门的资料给放在膝上,仰头看本来比他矮的左筠。
“什么事情?”
“情有独钟。”
“嗯?”
“钟鼓之色。”
“诶?在成语接龙吗?”
“色胆迷天。”
“那个是你从谁那里听到的评价学来的吗?”
友好,真诚,不带任何恶意。宋和觉得左筠的下巴压在他的脑袋上,随后少年模样的妖怪便伸出双腿在人身侧晃搭晃搭,宋和知道狗摇尾巴表示友好,兔子跺地表示愤怒,但是海豚晃腿这件事确实难以思考行为逻辑——海豚好像确实也没有腿。“天经地义。”
“意味深长。”有人的声音从远到近,什么人推开休息室的房间门,很自然而然地接上这个成语接龙的节奏。宋和脑袋上的重量一下子减轻,身边的两条腿晃着就像自己的同类在向主人示好,他压下其中一只腿,从转椅上起身离开那三面被桌面包裹的独立区域。左筠跟着跳下来,拍拍自己的衣摆接下去:“长命百岁!舆宝!”
周舆笑着——可能他在进来的时候本来就笑着,男性不留痕迹地侧身后退半步将冲过来的粉红色少年体妖怪躲过,道了句借你吉言。他伸个懒腰,露出腰腹处一点皮肤,又自然地躲过左筠的手指,接过宋和递过来的纸杯。“想要休息一下,这里还有地方睡吗?”
“昨天没有休息好吗?要注意身体才行呢,人类做不到同时休息和工作呀。”左筠揩油无果,换上一副比较严肃的口吻说着,给周舆指向旁边的休息位。人类的青年拉开休息位处的折叠床,嗯嗯着回应医者,从旁边翻出点布料折叠后盖在眼上,躺平。
“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没有休息好吧,昨天是有什么工作吗?”工作犬理解这种行为。
“嗯……该说运气好还是不好呢,不过既然现在我好好在这里的话也是运气好吧?”周舆轻笑出声音,他伸手将眼部的遮盖物向上推,同时睁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宋和。宋和脸色一沉,蹲下与躺着的人处于同一水平,压低声音:“遇到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遇到,啊,虽然有损失一些东西。不过不是阳寿这种。运气好的话,能好好活到今天不就蛮好吗?”周舆很顺手地轻拍狗头,他偶尔会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似乎对于这些事情都过于紧张。“最近附近学生自杀的事件不是闹得很大吗?本来以为夜班能有什么收获,没遇到啊。”他又收回手将遮盖物下拉挡住光线,周舆懒洋洋地打个哈欠。
“没发生什么是代表平安,我认为确实是好事哦。”他听见左筠的声音在自己的身侧响起,随后凑近。或许是海洋妖怪特有的皮肤温度,左筠的手指带着一些湿度的凉意,要是在夏天会感觉更舒适吧。随着对方扣住自己手腕,周舆能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倦意在体内流动后褪去。左筠没吭声,松手后伸手戳戳周舆的脸颊。“舆宝好好休息哦。”
“不过这样工作会没有进展吧,如果事件已经出现的情况,什么没发生也会丧气。”宋和在旁边以另一种方面评价,随后鼓励。“打起精神……舆、宝。”
“不用专门用那个称呼也可以。”人类青年诚恳,又笑。“你们这在轮流临终关怀吗?”
“睡会儿吧。”左筠笑眯眯地拉起被子打断这个称呼的问题。“今天是休息日,要珍惜才是。”周舆还没说什么,宋和就在旁边补充一句:没事我会看住他的。
“诶?在提防我吗?”
气温似乎干燥些许,外面的太阳从窗外爬入后在地面上打滚,伴随着鸟儿清脆的啼叫与更远处的吆喝声音。宋和拿着文件,周舆正在打盹,这两件事在同一个场景里出现给左筠也带来一股春困,少年体的妖怪换个姿势用手撑着脑袋,看着窗户外面。
人类如果不借住外力的话好像很难做到自己死亡,这种求生本能在左筠看来是一种很美好的能力,但是正因为有这种力量,所以要克服着迈向死亡一定更加困难吧。他想自己的族群在本能托起水中虚弱生物的时候心中所拥有着的那份延续的心,确确实实地写在每一个人类的心里。左筠一边呼吸着,一边想,换只手支撑脸颊。他开始停止呼吸,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很简单——不如说呼吸本身倒是他的刻意去做的事,换句话说,他可以随时原地把自己窒息而死。在视线模糊之际,左筠突然站起身也伸了个懒腰,恢复肺部活动。宋和被对方吓了一跳,和左筠的视线对上后,粉色的妖怪冲他一笑。“和宝,小狗,狗狗。”
左筠蹭过去,宋和不由自主地后仰,靠在椅背上被拦住退路。
眯着眼睛带笑的妖怪伸手去微微拉扯宋和的脸颊,又收起笑容询问人:“你觉得那件事是为什么呢。”“嗯……这次的事件吗?”“自杀对于人类来说很困难吧,克服这些困难还要去做的话,肯定更加痛苦和难过吧。”左筠干脆跨坐在宋和腿上,一边询问着又再一次捏捏人脸颊。
“但是死亡是离人类很近的事情。”宋和说。左筠倒吸口气,有些震撼地后仰。“……哇,你这个回答听上去就像是最糟糕的答案里的最糟糕的一个。不应该问你,狗男人。”
少年体的妖怪起身。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那边正在睡觉的周舆:“学生的事情应该还是有其他原因吧……嗯,不过果然人类的话还是过得再快乐一点比较好。”他眨着眼。“对哦!”
“嗯?你有这次事件相关的线索吗?”
“快乐的话果然还是要找个配偶才行!”
“诶?”
“你看,因为你没有配偶,所以你不快乐。”
“我觉得我也没有很不快乐。”
“等周舆醒了我们去鸡鸣寺吧。求一个姻缘,让娘娘保佑一下!”左筠没有理会宋和的话,他愉快地原地转了一个圈——就像是在游动一样,对着宋和眨眨眼。“反正今天是休息日嘛。”
此时的周舆还不知道,自己醒来后的假日已经被别人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