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这世上万事皆缘起,因缘生万物;万物又有灵,就此诞山川精怪,飞禽鸟兽。
大清尚书纪晓岚先生有云,事出无常必有妖。这林林总总的东西多了,便会起争端,扰世间清闲。
只是非人的东西要是搅乱伦常纲纪,也不好叫人判断,因此诸国就此暗地里建立了各自的组织。
说到这里,便要提一提那中国的六扇门——此地搜人类中的能人异士,又招神佛妖怪,为的是清查异常、解决事件。
正是因其存在,世界齿轮啮合如常。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世界半架空企划,并不会涉及南京的严肃历史事件。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并无法完美还原南京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进行一个乱写
年关将至,我和邓云青开车去采购。我头一次知道鞭炮和烟花真的能用来驱赶年兽,不过近年来为了环保,六扇门也改用电子烟花。这可真是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电子烟花都有了,什么时候来点赛博年兽。我把赛博年兽跟邓云青说了,他在副驾驶上哈哈大笑:“想象一种年兽病毒,在每个人的桌面上像瑞星小狮子一样咆哮,到时候过年加班的就不是我们了,是程序员。”
邓云青不开车,虽然他有驾照,但是那玩意毫无疑问地已经吊销了,开车的重任落在我肩上。我上路经验太少,一趟下来开得慢悠悠,每次倒车进车位,手心里都捏一把冷汗。邓云青当指挥,在我旁边喊“倒倒倒”,把我搞得心烦意乱。
我不是后勤部的,这趟采购本来没我什么事,不过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办,就干脆来当邓云青的司机。在车上我给邓云青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何推断出最近X岛上一个灵异串的事发地就在我们要去的商场,他听得津津有味,又问我,那会不会很危险。
“白天大概没问题,我只是去踩个点,不行就打电话叫人。”我说。
“电话打不通我就极速飘回去叫人。”邓云青给出后备方案。
我嘴角动了动,没说话。邓云青对自己的新身份很适应,似乎还有点乐在其中,这让我觉得不太高兴,又说不出为什么。
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先下车,给邓云青开车门,然后撑伞,仿佛他是个少爷。从商场门口到门里,就两步路,他也要打伞,而且偏要我给他打。我有点搞不明白,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贵了?以前他打篮球扭到脚,都一声不吭地打完下半场。但我决定不跟他计较,毕竟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
进了商场,收了伞,我们先去采购。商场里到处都装饰着大红色,播放着喜气洋洋的过年音乐。我们被华仔的恭喜发财围绕着,走进悬挂着大红春联的区域,选好烟花鞭炮还有春联,邓云青就开始跟老板讲价,看他张口就把价格砍到一半,我就知道这项工作我永远都干不来。
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板竟然还乐呵呵地帮我们把东西都抬上车,有时候我怀疑邓云青也会法术,他的法器就是他的嘴。
后勤部的事做完了,接下来是情报部的时间。
这个商场的4号电梯只到7-9层,但是如果按下6层的按钮,电梯仍然会上升。X岛的肥肥说他是晚上来的,结果打开电梯之后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怎么也走不到头,还感觉一直有人在跟着自己,他吓坏了赶紧回头,最后倒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我们情报部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妖异,打算确认过之后就让执行科的人来处理。
我和邓云青来到4号电梯,这里位置很偏,少有人来。我按下6层按钮,对着电梯门摆了一个照相机,设置好了定时连拍之后走出电梯。邓云青很有兴趣地在旁边观看,我则是有点不安地看着电梯的楼层。小小的显示屏上数字从1逐个数到6,在6层停下了脚步。我默默在心里读秒,十秒钟之后按下按钮,电梯开始向下。
6,5,3,2,1,电梯门打开,我长出一口气,至少相机还在。我和邓云青迫不及待地打开相册,一张张翻过去,照片里电梯门在6层缓缓打开,但那里并没有什么走廊,只有大片不祥的,如同电视信号不佳时的灰色雪花。
“可以确定了,就是妖异所为。”我说着,掏出手机开始发消息。
“要不我上去看看?如果对方是鬼,我们还能沟通两句呢。”邓云青说。
“你上去干什么?太危险了!”我立刻反对。
“没事,相机还在,对方攻击性看起来不强,”邓云青笑了笑,“再说了,我又不会死。”
他的表情刺痛了我。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但能猜出来必然是非常之难看。
“邓云青,”我咬牙切齿,感觉自己的浑身都在发抖,“你要是真想去,我也要跟你一起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邓云青好像被我的表情吓到了,赶紧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开玩笑呢。我又不会打怪,这种事肯定还是要让专业的来嘛!”
可我的发抖还没停止,甚至嘴唇都在抖。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说完这句话我就扭头往外走,一直走出商场正门,邓云青打着伞出来追我,这个时候他倒是知道自己打伞了。
我无言地上了车,等邓云青在副驾上系好安全带再发车,一脚油门踩得又猛又狠。
“你慢点开,限速的!”邓云青赶紧劝我。我还能不知道限速?但也许是我表情太过阴沉,四十迈被我开得活像八十迈。
“我错了,以后不会了。”邓云青道歉。
“……我没怪你。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一不小心又开始哭。丢人啊!丢人啊!但在邓云青面前也不算丢多大的人,所以我任由鼻涕眼泪一起流。邓云青又不是自己想死的,他有什么错?还不是我太脆弱了,直到现在也无法接受。
“哎呀,你看我这嘴,瞎说啥实话。”邓云青说,用某个赵姓小品演员的语气。我噗嗤一声乐了出来,邓云青看这招有用,开始深情朗诵改革春风吹满地。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协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
想想那个时候的小品也没少歌功颂德,怎么就觉得那么好看。想到这里我问邓云青:“今年还看春晚吗?”
“不加班就看,不然也没事干。”
“我也是。”
春晚越来越难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我能把语言类节目骂上几个小时,然后没完没了地回忆起以前那些精彩的节目。可以说大部分的经典台词都刻在我dna里了,树上骑猴,下蛋公鸡,蓝色骷髅,绿色尸体,队长别开枪是我,TV吧你说先踢哪儿,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行走的春晚台词储存器。
我们开始玩台词接龙,邓云青在这方面不如我,很快变成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有说有笑,好像刚才的不愉快没发生过一样。
我本来想好好和邓云青谈谈,但转念一想,快过年了,不要讲太沉重的话题,等过完年再说吧。
不过就连我自己都知道,这只是我的借口罢了。
其实我是故意的。我希望天明知道我已经死了,别在一个死人身上浪费时间。现在想想,可能从一开始我就该装失忆,不过我的演技不怎么样,如果被看穿就会很麻烦。
不过我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强烈,看来以后得换种方式,我也不想老是看他流眼泪。
我俩在车上闲聊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扩音器的叫卖声:“……批发灵兽,欢迎选购……”
许天明急忙踩下刹车,我俩探头一看,上面有块牌子写着“烟花鞭炮,批发零售”。
场面可以说是十分尴尬。
“我差点就要打电话了。”许天明说。
谁不是呢?不过车都停了,我转头看到不远处正好有家一点点,干脆下车去买奶茶。
我给许天明讲笑话:“一个人去看病,医生说要忌口,他问医生,能喝奶茶吗?医生说,只能喝一点点。他又问,coco行吗?”
许天明没笑:“太冷了。”他有轻微的乳糖不耐症,不太喝奶茶。
他又问我:“怎么买这么多杯?”
“给同事带的。”我晃晃手机,上面是玄亥给我发的消息。玄亥是我们这儿的奶茶发起人,经常组织大家点奶茶。我对店员念了一长串咒语一样的东西,什么少糖去冰半糖少冰芋圆珍珠燕麦红豆椰果寒天,末了问许天明他喝什么,他说要柠檬汁,很好,很简单。
然后许天明扫码付款。我的支付宝都被注销了。
我们开始等奶茶,期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到六扇门,还有六扇门第一女捕头。
“你要是白展堂,展红绫和佟湘玉你选哪个?”
许天明毫不犹豫:“展红绫。”
“那祝无双和郭芙蓉?”
“郭芙蓉。”
我心想,好家伙,这不是跟我选的全都反过来了。又想,上辈子他当秀才的时候,和他谈情说爱的那个确实挺郭芙蓉的。
不过不管他选什么都无所谓,反正选项里永远不会出现邓云青。
之后我们又聊到一起案子,许天明参与处理的第一个案件。他很擅长寻找事件里的联系,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找到事件相关的拼图,虽然是第一次参与情报科的工作,但他也算是帮了大忙。许天明说起案件的时候没有了平日的那点木讷,反而是手舞足蹈,神采飞扬,整个人好像在发亮。他这副样子我没少见,从小时候一起玩推箱子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他两眼发光地从地上跳起来,夺过我的手柄,兴奋地从第一步开始推演。说实话,我很难不对这个动心。
每当这时我的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些类似的念头:“如果……就好了……”,如果我那天没有出门,如果我能再小心一点,如果我能早点和他说,可惜没如果。人应当向前看,我也希望许天明向前看,可他却总看着我。
我到底是真的拿他没办法,还是我也喜欢这样,希望这样?
我拎着一堆奶茶回到车上,许天明给我撑伞。坐上副驾驶的时候我问他:“对了,为什么是展红绫?”
许天明想了想,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毕竟是初恋吧。我比较喜欢先来的。”
我听完了有点高兴。还有人比我来得早吗?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看,我这就是太不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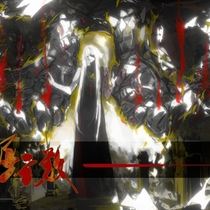


还是请当番外看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哐哐磕头
“……”
“…………”
诡异地寂静在几人之间蔓延开。
废弃水泥楼内已然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干枯烧焦的枝叶,更有甚者还似碳一样燃着红色的星点光芒。
“那个。”陈知安自知理亏不得不最先开口,“辛苦后勤科的大家。”
“我本来在床上打塞-达玩得好好的。科长一个电话我把游戏机摔了。”
出云红躺在另一边装死,好像肩膀上的那点伤口能要了她半条命,一米七几的个子就那样直挺挺地睡在那里,好似一根刚被砍下来的甘蔗。
“我——”
“我好不容易赶过来,差点撞上墙,还被人看见,还好那是我多年老伙伴。”邓云青揉着太阳穴深吸一口气,“结果还没在科长办公室站定就被一股脑塞进车里一路奔驰来到这里看到这等惨状简直如同惨绝人寰天崩地裂山石塌陷日月无光天河倒灌四里八荒皆为焦土——”
陈知安猛地打断他,深吸一口气——又一口气,在众人众目睽睽的盯视里,最后又一次吸气,半晌才说:“你让我喘喘。”
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地上那根红甘蔗正在细密抖动。
邓云清“……”
陈知安终于觉得不那么胸闷了,环顾一圈用几乎毫无差异的口气问道:“惨绝人寰天崩地裂山石塌陷日月无光天河倒灌四里八荒皆为焦土?”
邓云青一指地上的出云红和倒在四处正在被救治的受害者“这不惨绝人寰?”又一转身指向被钉出凹陷有些残缺的墙壁窗沿,“这不天崩地裂?”随即抬头指着三楼簌簌落下的灰尘,“这不叫山石塌陷?”而后转首侧目看向天边,“日月无光。”视线下移看向地面散落一地的爬山虎汁液,“天河倒灌。”最终缓释周遭,枯死的爬山虎落得到处都是,灰白色的墙壁上几乎都被染成了枯黄的焦黑,邓云青冰冷的目光落在陈知安身上,上下一打量,那两块镜片上透出一点怜悯的光,“四里八荒皆为焦土。”
陈知安觉得自己被烟雾憋住了。甘蔗抖得像开了震动模式。
最终在周遭所有后勤科同事的瞪视以及赞同的目光中,在邓云清那怜悯又笃定的眼神里,陈知安败下阵来,双手一举开始背法条。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邓云青“……”他猛地从背后拿出那个裂了一半的掌机,扣掉了保护壳,亮出里面贴着的一张通讯用的符纸。又朝陈知安亮出了被加持过后,信号满格的屏幕——只见那屏幕上赫然两个几个叫人瞪掉双眼的大字‘执行科办事处’
陈知安两眼一翻,和出云红双双倒地不动成了一高一段两根待宰的甘蔗。
执行科办公室内
白茶坐在办公桌后面,尾巴晃着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
陈知安面色凝重,姿势标准,双手五指交叠紧贴后背,双脚打开脚尖与肩膀齐宽,脚跟微微内靠形成无可挑剔的四十五度夹角,目视前方收紧下颌。
赫然一个标准军姿。
白茶猛然想起这位姑娘的出生,母亲是特种部队退役功勋军人现任武术教练,父亲省市高级法院堪称青天大老爷的高级法官,本人出身军校优秀毕业生。
一时间更头疼了,以上三点齐聚一堂汇成四个大字——惊世刺头。
“陈知安——”
安字话音还未落下就听响亮一声“到!!”响彻整个办公室,震得门外路过的员工差点摔了手里的头。
这一嗓子差点把白茶昨天的懒觉都喊醒了,执行科科长呆愣半刻,终于意识到今天不能善了,从抽屉里掏出一沓两指厚的报告纸,一盒黑水笔推了过去。
“先口述吧。”
陈知安微微垂下眼,还没来得及戴回隐形眼镜,现在眼前一半清晰一半模糊,显得她表情更加愧疚了。
“我和红姐两人大约是凌晨两点到的事发现场,诱饵勾引不成决定潜入作战,在途中我被绑走想索性釜底抽薪遂未反抗,红姐应该是遇到了欲要拖走成年男性的变异爬山虎,鏖战多时不敌,在追击途中与我相遇。”她吞了口唾沫没敢去看白茶的表情,“我被拖走后听见了水声,大约是爬山虎在饲养人类或者动物,以便更长久地在活物身上获取热量,随后我与大量爬山虎缠斗,为了脱困才用的烟雾符,最终致使整栋楼的爬山虎燃烧殆尽。”
白茶从中听出不对,又细问道:“伤亡呢?”
“死了些小动物,无法计数,昏迷一人在医院观察,轻伤一人。”陈知安军姿站多了倒也不觉得累,此时只觉得心里憋得有些发慌,口干舌燥。
“我是问……算了。”白茶知道陈知安嘴里说的昏迷一人和轻伤一人的概念,两人一个是三天未进食只有水喝有点虚脱,还有一个只是在被爬山虎拖动的过程里有点擦伤,现在已经被安顿好消除了记忆重新回工地上班去了。
但是按照把人带回来的后勤科说出云红肩膀上的伤口贯穿前后肩胛骨,其实有一点点难办,三个月最好不好大幅度动作更不要说举起她那把枪,已经被医生明令禁止没收了,刚才似乎还想要偷偷拿回来。
陈知安伤的不重,为了脱困自己把手腕当了回可拆卸部件,有点软组织挫伤,阴阳眼倒是有些用眼过度的趋势,医生也已经开了药每天点点缓解疲劳就没事了。
白茶敲着桌面看向陈知安手上的烧伤和焦痕给她开了张单子:“回去停职半个月,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出来,扣你半年奖金。”
陈知安又一声响亮的“是!”脱口而出。
转身一出门又看见邓云青站在不远处推了推眼镜。
“去吃火锅吗?”
“可我要去罚禁闭。”陈知安有些蔫,连自己掉了的那个假发片都没想起来。
“什么时候要罚禁闭了?”邓云青不记得还有这项规定,“你是不是听错了?”
“可是科长说要停职半个月。”
邓云青更不解了:“他给你文件明令禁止你出门了吗?”
陈知安摇摇头。
邓云青又说:“那他给你批条子说你要在家里禁闭吗?”
陈知安看了看手里的条子又摇了摇头。
邓云青逐渐开始无语:“那么他开口说过闭门思过四个字吗?”
这是一个成语,一般不用在口头,陈知安没反驳,还是摇了摇头。
邓云青斩钉截铁道:“那就是可以在火锅店禁闭的意思,快走!”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