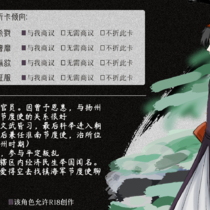
不写完序章浑身难受、序章挑战不一样的文风浑身难受、写完了发现折卡死线近在咫尺浑身难受(尖叫)
总之,前传和构史,全文2046字
————————————————————————————————————————————————————————
十五岁那年,我哥死了。
那是个涝年,稍微往南一点的,十里八乡都被水淹过一遍。水灾之后便是疫,我那想脚踏实地,做中州司马的兄长,很快累倒了。好巧不巧,他暂住的地方又闹起了鼠患,虚弱之中的兄长又得了疫病,抬回家的时候,人就剩口气了。
天下又哪有那么巧的事呢?
丧事办得匆忙,兄长又是因疫病而死。家中避讳,最后只有远远的灵堂,厚重的纱幕,还有呛人的艾烟。
兄长留下的孩子不过总角之年,披麻戴孝站在前头,像个小草人,和他爹一模一样的倔强。我去叩拜敬香的时候,那孩子只是看着我,他眼睛哭得红肿,我看不清他的想法。
不过,那大概是恨吧,恨死的人为什么不是他体弱的小叔,而是他年轻力强的父亲。旁支侧室应该也吹了不少风,总不过是那些以后我会继承家产,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臆测,我那早慧的小侄子一听便懂。
兄长的头七刚过,小侄子就跑来找我。他问,小叔,我爹怎么死的。
我屏退了丫鬟小厮,又让人在外面守着。人都陆陆续续退了出去,房间里就剩下我和他。我安静地看着他,我听见自己冷着声反问,“小小年纪,问这些做什么?”
我听见他说:娘每日抱着我哭,我问她,她也不说,表叔、表姑总围着说些钱财家产,却不说我爹,更不像真的。还有,爹死前说,让我听你的......小孩子几乎要哭出来,我拉着他进了我的书房,问他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相,知道之后也死守秘密,谁也不说。
他用力点了点头。
那还要答应小叔,你要好好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也要去学骑射,去游历,但不能去科举。我说。
他疑惑,但应下了。
我拍拍他,尽量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了一切,倔小孩听完又红了眼。唉,明明最不擅长哄小孩了。
“我要让那群家伙血债血偿!”他哭着喊。
我搂着那愤怒而哭泣、发抖的小身躯,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有小叔在,小叔给你爹报仇,也是要给小叔的哥哥报仇。”
“但是啊,你要在家里保护你的母亲,让她不要被欺负,你会有很好的老师,你要去多看看人间。”
“等你明白了今天我说的一切,你就可以离开家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恨的人是我。
我差人送我那小侄子回去,葬礼结束之后,府中的流言也逐渐平息。父母长辈旁敲侧击,推着我去科举。族中传承术数的人本不应入世,可是啊,这天下要乱,没有个人撑起柯氏的门面,那是真的要被大浪淘尽了。
我掂着手里的铜钱想了一夜,它们还是丁零当啷地落在了桌上。卦象摇指京城那位陛下,还有一位看不清的......
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啊。
十六岁,我大病一场,几乎去了半条命。家里似乎以为我是为了参加科举操劳过度,补品流水似的送进我屋里,总算是保住了这个家族唯一的出路。
十九岁,我入京城。
朝堂混乱,世家都在安插自己人,清流也不得不紧随其后。很幸运,我找到了伯父的同乡至交,年过六旬、时任礼部尚书的林大人。他给我安排了六品的员外郎,一个合适的位置,不会风头过盛,又能看清京城的形式。
他大概想把我作为接班人培养。
可惜天不遂人愿,烨帝在修道路上剑走偏锋,不问政事,这如何让一个两朝老臣忍得下去?
“林大人......”
“莫要在说些什么,我心意已决。”
我劝不住。
回去的路上,我见着一小摊,挂着算命占卜的招牌。那人自称李半仙,见着我就开始招呼:“哎呀,老爷您也是修道中人啊,有缘,有缘!”
我猜他看到我刚刚收进袖子里的铜钱了。
不过也好,这摊子上该有的都有,我也不必对着六枚铜钱劳心劳力。我微笑着走过去,“有缘,那就帮我占一个解忧卦吧。”
李半仙递出一个签筒,我随意摇了两下,便蹦出一根竹签。
“哎呀大人,接下来您是平步青云,逢凶化吉啊!”他捏着那根竹签,还要说下去,我抬了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既已逢凶,又如何能成吉?”
他愣了一下,怕不是又在肚里诌些说辞。看天吃饭尚且不易,看人脸色吃饭又能好到哪儿去。
我摸了摸荷包,掏了几块碎银塞他手里。
“多谢前辈解惑,这些碎银就当是晚辈请您喝茶了。”
李半仙大概没见过一下子给这么多的,趁他愣神的间隙,我快步离开了。
逢凶化吉?不,只是有人得敲碎了牙,把苦果咽进肚子里。
年末的祭祀总是肃穆隆重的,肃杀的寒风几乎要渗到骨头里。林大人还是越过了御史台的职权谏言,年迈的身躯匍匐在地上,抱着必死的决心。
烨帝的眼神冷得要结冰。
我从百官队伍中站了出来。
提前备好的说辞、伪造的卦象、几卷青词,我把老师在殿前贬低得老眼昏聩一文不值,我扯出身上的骨头把它们砸碎、磨成粉、捻成线,把它们交到这个昏庸的皇帝手里。
烨帝大笑,他看上去挺开心,便丢给林大人一句轻飘飘的归老,然后把我放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上。
“谢主隆恩。”
你看,做不了忠臣、奸臣、权臣——
做个弄臣,也能成为一颗不错的棋子。
是夜,我暗中拜访林大人,他似乎想通了,有似乎没想通。事已至此,我劝他快些离开京城,不要让烨帝起疑心。
“烦请大人回乡之后,指点一下我那不成器的侄子......”我深深作揖。
林大人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好吧,老夫答应你。”他深深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你要走的是个什么路吗,你......”
我只是把身体压得更低。
“难走的路,晚辈替您走。”
像我这种没骨气的,死了也罢,就当是平一平这崎岖的乱世路,你们也好走得顺利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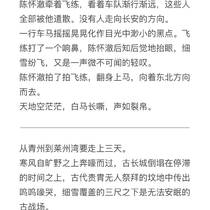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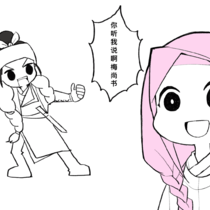




持卡人:王焕荼。
省流版:折卡是用的太玄子的赏赐,用法是路费和给狱卒的贿赂。
烨灵帝化身太玄子重登皇位,是谁也不曾想过的事情。闻人俟在那日混乱中因为耳朵过于灵敏,被有心避人的烨灵帝放了个假,等她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所剩的只有一片残垣断壁和开得极繁极艳的桃花了。
太玄子化身的桃花并不比冥虚子所化更有安全感,但好在,作为造反势力的赤仙会一向小心,有几处暗哨潜伏在多个路口关隘,时刻等待着接应的命令。而她这样的“异人”,对于已经超凡入圣的太玄子来说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太玄子轻而易举地同意了她请辞的说法,甚至以诸多金银珠宝相赠,看起来实在是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他甚至记得关心女孩一个人携重宝出京会被贼人盯上,叫来如今繁忙的王都尉作陪。
闻人俟不敢假定太玄子心存善意这样的天方夜谭,只能想是否自己身上有什么可疑之处,然而实在找不到答案。这件事一直到她与王焕荼见面才得到了解答,王都尉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同时对于长相漂亮的人都多有几分爱护之意,很是细心地为她解说了一番。原来是有一位同为花鸟使纯秋进献的侍女银杏刺杀了皇帝,虽然闻人俟没有什么嫌疑,但是显然坐在皇帝这种位置多年的人必然不可能没有疑心病,所以她也在猜忌当中。王焕荼将她送到了场外寄住的农人家中,这家的农人正是赤仙会的信徒,王焕荼将手中的玄铭灵牌塞给闻人,笑到,“这灵牌虽然有万般不好,但唯独用来威慑是为妙机,你如今身负重金,恐怕还是要早日脱手为好,免得被贼人盯上,落得人财两空。”
闻人谢过对方后走进屋里,手上细细摸索,才发现这竟是一张「铜奢靡」,自己此次得到的赏赐倒是差不多能折断……那么太玄子叫王都尉来为自己送行的做法看非常可疑了,他是期待自己的臣子监守自盗吗,还是希望自己能顺理成章地难逃一死呢?
闻人并没有过多思虑,而是叫众人商议南渡的事情,不论是将情报带回荆州,还是去撕那符咒或是除妖法会来灭杀两位伪神,都不是在长安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恰有一位信徒在会上提到,往南的关隘见到了那与刺客银杏极为相像的侠客,闻人心中一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位侠客刺杀皇帝,那自然也是赤仙会的朋友了,何况二人一起坑了那位倒霉的花鸟使,也算是有一段渊源了,何不干脆请那位侠士共谋大业呢?
赤仙会毕竟经营多年,为了此次圣女的安危更是小心谨慎早做准备。于是虽然闻人出发得更晚,却还是在银杏渡江之前赶上了对方。
皇帝发布的通缉令还没到达,但是这样锋芒在背的感觉不做他想,银杏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有任何代价,只是觉得长安那边的反应实在太快,不符合她对大烨腐败的认知,而司徒京也太过没用了,竟没能多拖上几日……还是说,他也是追缉的一环呢?毕竟那「护送」的侍卫大概已经回去通风报信了,恐怕司徒公公也很是不满吧?
银杏注意到马蹄声音越发急了,遂转身藏入道路一旁的竹林当中,身形如燕一般踏竹而上,正打算伺机而动。未曾想追在身后的追兵也跟着停下脚步,银杏有些不屑,所以说这些官兵都是一样的路数,还是怕死。不过这样也好,人在林中比骑马赶路更轻快,她一样可以摆脱追兵。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道声音准确报出了她的名讳与方位,“银杏,林中左侧的第十三棵竹子上面的便是你吧?”
“不必惊慌,我并非任何人派来的追兵,而是来祝你脱困的人。”一个身着白衣身披红帛的女子孤身进入林中,她眼睛闭着,但走起路来却毫无迟疑,在靠近银杏之时停了下来,给二人进退留足了空间。“我是闻人俟,我在纯秋大人那里听说过你的名字,或许你也曾听过我的?”
确实,闻人俟这个名字银杏并不陌生,毕竟这位目盲的女子曾经也是烨灵帝眼前的红人,虽然这样的红人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不妨碍她知晓这个人的存在。只是,烨灵帝或者纯秋,都不是她所在乎的人,何况他们也不可能叫这样一个小姑娘来带领追兵吧?虽然她的耳朵看起来很好用,但是银杏毫不怀疑,自己只要一招就能轻松杀死她。
“你的刺杀很成功,烨灵帝已经死了……但是有妖桃从其身中复生,如今自称太玄子,他记得烨灵帝的所有事情,也包括刺杀的情况,如今长安上下已是被通缉令贴满,想来他是不会放过这次刺杀的参与者的。”闻人俟见她没有动作,料想银杏或许并不介意多听她说一些话,于是继续说道,“如今通缉令一散开,多个驿道关口恐怕都要紧张起来,哪怕银杏侠士想要走水路,情况也是不容乐观,但是我赤仙会已在此耕耘多年,在漕帮势力里亦是说得上话的,不知我可否邀请侠士,一同乘船南下?”
银杏才知道情况如此严峻,难怪朝廷的反应如此迅速,原来那狗皇帝竟然没死!她脸色阴沉了一瞬,从树上一跃而下,靠近闻人,压低声音质询,“看来我还应该感谢你们雪中送炭了,但是帮我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怎知你不会转手把我卖给那狗皇帝。”
闻人笑道,“我知晓你心有疑虑,但这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自古便有荆轲刺秦的美谈,虽然我贫弱不比侠士,却也愿助这般有胆魄的侠士一臂之力。何况我家乡多是因为朝廷暴敛暴征而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大家拜入赤仙会便是结为兄弟姊妹,自当互帮互助。阁下杀了那狗皇帝,也算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纵然萍水相逢,也是异父异母的亲姊妹了。我等自然是没有坏心思的,只看银杏侠士是否愿随我等入荆州,以期来日共讨这非君非人之辈?”
银杏并没有完全相信她说的话,毕竟如果有人刚刚被做棋子利用,恐怕也很难马上相信其他人。但是借赤仙会的势力摆脱追查,对他来说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所以她审慎地答应了借道的事,却并不肯承诺会为做赤仙会做什么事情。
闻人并不在意这件事,毕竟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在此,难道赤仙会真打上长安了,银杏会不想再取太玄子性命吗?只是在临上船之时,银杏并没有踏上那只用芦草掩盖的小舟,而是语气莫名地询问,“你知道,汝阳公主如何了吗?”
闻人沉默不语,汝阳公主当日便以身故,这是长安如今人人皆知的事情了,只是她的死法众说纷纭,无人能下一个定论,不过银杏走得早,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她摇了摇头,空茫的眼睛看向远处,“我于宫中没有什么势力,因此也不得听闻。”
“你的人不一起走吗?”银杏又问。一起乘船的只有闻人和几位摇桨的船工,当时追击的熟面孔,如今都还在岸上呢。闻人摇了摇头,“长安的情报需要有人去整理……何况还他们还有旁的事情要做。”
看着小舟顺着夜色飘荡远去,岸上一骑才出声发问,“我们真的要帮那个劳什子花鸟使越狱么?要打通狱卒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零头的信众横了他一眼,“圣女大人已经留下了用来打通狱卒的钱,又不是从你兜里掏银子,你有什么意见?”
那人讪笑道,“这事不是叫大哥你也头疼好久吗……这钱若是花在我们兄弟姊妹身上不好吗,那个什么花鸟使,虽然确实是个倒霉鬼吧,但那不是他自己倒霉嘛。”
几人不着边际地闲话几句,又策马返回长安。此刻的长安城一片混乱,因着桃花暴动的缘故,满城百姓都是灰头土脸的,有些贼人便趁乱作祟。赤仙会的几人趁机挤入城中,头人厌恶地将一个企图趁机猥亵妇女的地痞流氓摔在地上,“就他了,这种人也是死不足惜,先把他舌头扒了,省得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几人通力合作,这个恶人生生痛昏了过去,在几日后他们终于花重金收买了狱卒,假借当初纯秋硬是带走了他们妹子进献皇帝的说法,叫人放他们进去多多「照顾」那位花鸟使,实际上暗中狸猫换太子,将人偷渡了出来。
而纯秋本人一直到登船才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这艘船已经行舟过江心,唯见碧云落江涛与两侧深红映浅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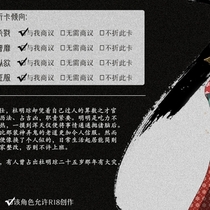
谢谢陈怀澈大人借的银征服。
周郎妙计安天下(大概)
-------
草原的天暗得比中原晚些,夕阳的光烧得草场红彤彤的连成一片,带着暑气的风吹过,金红色的海便波光粼粼地鼓动起来。
夏季的草场尚且青着。一个牵着马的身影劈开了草浪。人烟、马粪与牛羊的腥膻顺着晚风飘来: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几近看不出的道路向前走去,此路向前不远便是一处大集,羊毛织成的大帐层层叠叠地将中心的牙帐围住,旅人紧了紧马背上的行囊,事到如今,在离大集不到半座山头的地方,旅人长叹一口气:自己在这草原上见了十次日出日落,终于将这条长路走到了尽头。
从大集处远远的有几个人影见着了旅人,聚集了六七人近来。为首之人牵着马,披挂着半身皮袄,正一副霜原好汉的模样。那人隔着老远便叽里咕噜地喊起话来,指着青衣旅人,身后六人散开至半圆,隐隐地包围了来人。旅人辨着顺着风传来的词,似是霜原语中的“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于是远远地向着那霜原好汉作揖,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霜原语高喊:“我是周拂桢,乃是大烨来的使者!”
果然,那几人听了这话,互相交头接耳了几句,犹豫着散开了包围圈。为首那人点了队伍中的两人,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两人便行了个礼,策马朝着大集中央的牙帐飞驰而去。旅人——周拂桢心下了然,那二人定是向帐中的头人报信去了。才歇了口气,却听到那领头人对着自己高呼:“贵客不如将马放一放,与我一同往帐中歇歇腿脚,喝口茶水!”话音落定,又有一人前来牵马,周拂桢也不推辞,只拍了拍陪着自己走了十个日夜的劣马脖颈,将缰绳交予了来人。
“不知这位好汉如何称呼?”
“你叫我别日得便是。”
周拂桢借着暗淡的天光打量着别日得,一身半旧的袄子,磨得看不出颜色,身后背着的弓箭却是光滑漆黑。是个用弓的好手。周拂桢当下便有了定论。待到别日得领着周拂桢进了带着膻味的帐篷,两人在帐中坐定,饮了一碗劣茶,这才使着半生不熟的霜原话聊了起来。
“周兄弟来这里倒是颇废了几分力气。”
“别提了,这日头晒了一路,草原的路实在不便……”
又敷衍了几句,周拂桢饮下一口茶水,引着话题往时节上走。
“真不愿这时间走这些路,正是农忙的时候呢。”
“怎么不是呢,这时节该是羊儿吃草的时候……”
夏日的牧草鲜嫩饱满,正是牧人放牧的好时节。牧人最恨冬日,冷风与枯草如刀子一般将羊群的肥膘刮下。捱过一个冬天,羊群、马群饿得瘦骨嶙峋,春日的新草只是堪堪给牧群续上了命,只有到了夏日,牧草鲜嫩饱满,这才是牧群上膘的时候。平常的牧人自然是不会在这样的夏日驱使着牛羊马匹远赴千里地奔驰的,但话又说回来了,霜原也并非寻常牧人:受可汗驱使的族群,在宝贵的夏日抛弃了各部族的草场,前来为可汗取得下一场胜利。然而胜利是可汗的,那些耗尽了肥膘的马群却是各部族的,没有了积攒着的宝贵脂肪,这一个冬天对各家来说定是格外难熬。
别日得抿了口茶水,摇了摇头:“若不是为分些草谷,谁家愿意将马儿赶出草场,奔上这许多路程呢?”
“别日得兄弟也真是为部族考虑。”
“在夏日里征发这样多人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若是这次带不回够多的粮食铁器,这才是真亏呢。”
“草原的英雄倒会被粮食铁器难住么?”
“英雄也得起锅做饭哪。”草原的勇士用衣袖抹一抹嘴,“春里的局势也不好,部族还没赶得及去南边交易……”
粗劣的茶水在陶碗里打着旋——泡茶的茶梗用的是应当被择下的老枝,茶碗也未上过釉,挟裹着茶水泛起土腥味来。自然如此。周拂桢想。哪怕在中原,也不是所有军爷都能吃香喝辣的,再好的良家子,谁没有挨过两次饿呢?更不用说资源匮乏的草原了。天赐的大雨在关中转身离去,留下草原这片贫瘠的土地,这些甚至无法看天吃饭的人必然比中原人更饿、比中原人更渴,必然比谁都更渴望一碗浸着咸汤的饱饭。
“春日的集市没有赶上么?”
“是,去年买的盐都快吃完了,挨饿也就罢了,谁家没有饿过几顿呢?但是省着这些盐,族里的娃娃都没得力气了……”
周拂桢心中一动,却不说话,将茶碗放回桌案。披挂敲击的声响从帐外靠近,帐门一掀,一人大马金刀地叉手立在门外:“谁人是大烨的使者?”且看此人衣着规整,披挂甲片,衣摆上绣着缝边,腰间还挂着一柄大刀,想来就是头领的信使,于是立起,不急不慢地行了个礼:
“正是在下。不知有何吩咐?”
“随我来。头领想要见你。”
-
牙帐比起其他帐篷高了不止一倍。除去那些经过鞣制、缝在一起的皮子外,还缠着不少来自大烨的丝绸作装饰。十数个身穿皮甲、披挂金银饰品的部将吵吵嚷嚷地围坐着,即使是语言不通的大烨人也能从他们的神色中看出此时的愤怒。而在铺着羊毛毡地毯的牙帐中心,一座胡桃木色、饰着皮草的胡床上正坐着一位不怒自威的老者,此人不仅披挂齐全,甚至外袍还缠着丝绸光泽的布料——在大可汗南巡之时,这样的头人自然是这一整个大集的话事人。
而负手立在头人面前的青衣使者,尚未擦去面上积攒的尘灰,不卑不亢地与头人对峙着。
“人都说中原人好那劳什子礼节,可我未曾从使者你的身上看出礼节呀。”
沉闷的霜原语从大帐中央传来,四周也随之涌起哄笑和嘘声。霜原的将士尚未学会礼节,狼群正以明晃晃的恶意对着使者龇牙。
“你带来的……是钱粮?还是城池?”头人摇了摇头,“既无钱粮,又无城池,竟敢发话让我们退兵?实在是不知礼数呀。”
“头人好大的口气,这几万人马在这谷地白耗军粮,怕不是撑不过下月便要退兵,却要大烨给你送上钱粮城池,可打的好算盘。”
“既如你所说,我等下月便要退兵,使者又何来求我?不如抛了这天子命令,在边关等着退兵便是。”
周拂桢摇了摇头:“我非是天子使者——”
嘈杂的怒火又一次自四周响起,霜原的将士们似乎再也掩饰不住怒意,愤怒地咒骂着来人。
“哼,哼哼。”头人对着四周挥了挥手,只对着周拂桢冷笑道:“既非天子使者,那更拿不出什么东西了。送客吧!”
一时间,牙帐里混乱得好似一锅沸腾的粥,早已按捺不住的草原人从座位中跳了出来,更有动作快的甚至伸手够到了使者的衣领,试图把人扔出去。“慢——!”周拂桢眼疾手快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高举起来对着众人大喊:“我非是天子使者,乃是可汗使者!若要逐我出去,先看了此物再说!”
帐中的声音霎时一静。头人勾了勾手,抓着使者衣领的年轻将领便骂骂咧咧地将人一推,从堪堪站稳的周拂桢手里抢过那个小盒子,恭敬地递给头人。轻薄的木盒三两下便被拆了个干净,盒子中的事物如此便落入了头人的手里:一束缠着发绳的断发,发茬处坚硬凝固,呈现出血迹干涸的状态。——可汗落在他们手里?什么时候?是否出兵?要不要杀了使者?其余部族会不会散去?一连串的问题在头人脑海里打着转,不到两个呼吸间便下意识地做出了回应。
“呵哈哈哈哈,我道哪里来的野崽子也敢喊我们退兵,原来是可汗派来的使者呀!”头人将手中的断发随手一抛,咧嘴大笑起来。“不必这样紧张!既是我霜原的贵客,我们当设宴招待你才是啊。”
周拂桢只觉双腿打着颤,如此一来,对方在拿到信物之后便会意识到可汗在南方不得脱身,更不会有什么动兵的命令可以传来;因可汗之命在错误的时节聚集的众多部族,在得知无法动兵劫掠后,原本便有怨气的部族们会各自为政四散而去;然而放任部族四散,对可汗的君威与草原上的信誉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便是使出手段扣押住自己这个报信的使者,软禁或是暗地里灭口——最后等待可汗的军令从南方传来,纵兵劫掠。如此一来,自己最重要的目的,留在霜原大集内便可以成了。只是将性命交予异族人实在是胆战心惊,但与科举的难度相比,拿一条命换一个官身倒也算便宜简单……
头人的神情换得轻巧,帐内的气氛也随之一变。又有人搬来新的胡床与矮桌请使者落座,头人哈哈一笑:“贵客可敢与我族勇士一同饮酒吃肉?”
“有何不敢?”周拂桢坐在胡床上,拾起桌上的短匕,学着周围人的模样,刀口向内,从盘中切下一块烤肉送进嘴里——咸,太咸了!然而这咸味反倒是霜原待客之道的体现了。内陆不比沿海地区,无法煮海作盐,但人又不能不吃盐——缺了盐,人不说劳作,连站起都有困难。中原靠一套盐铁专卖的制度将海边盐场的盐源源不断运往内陆,其中催生了多少私盐贩子暂且不提。然而草原上却不同,没有直抵海边的盐场,没有连接国都的道路,没有漕运,没有盐税官,也没有——盐。
草原缺盐。人要吃盐,牛羊马也要舔盐。然而盐在这片草原上的唯一来源便是与中原的贸易,凭着几张薄薄的盐引,中原王朝通过少数几个关隘便将草原上的劲敌锁死在这片土地上。盐的稀缺又造就了草原的礼仪:贵客的食物里自然是要放盐的。不仅要放,而且越咸越体现对客人的尊重。更何况开春的局势紧张,与大烨的贸易几近停止,今年直到现在,草原的部族都没有一粒盐的进项。
周拂桢努力咽下这块过咸的烤肉,对头人露出了一个微笑:按自己被看重的程度,对方怕是根本没打算放自己走。
-
五天后。
“那使者。”头人倚靠在胡床上,握着匕首,用丝绸细细地擦拭着。他向着周围的侍卫微微仰头,慢条斯理地说着:“没见他耍什么花招吧?”
“这可是我们的地盘,谅他也不敢……”
“唉!”头人提高音量打断了侍从的话,依然不紧不慢地擦着手中的银匕。牙帐是这一整个大集中最高的,十几柱高耸的木柱将它的穹顶撑起。在那木柱上,霜原人用羊毛制成的毛毡缠绕它,于是那夏日里毒辣的阳光被阻拦在了外边,唯独在接近穹顶处留出了几个通风的窗口,昏暗的天光就这样从那口子中朦胧地落进来。光洁的匕首表面将昏光影影幢幢地反射至头人花白的胡须上。老头人也不言语,只是半阖着眼打量着手中的匕首,过了良久才开口:“……你已二十多岁了,不错吧?你是从几时开始捕猎的?”
“我从五岁便上了马、拉了弓。”
“你与那使者,谁人更善猎?”
侍从并不言语,双唇抿得死紧。将自己与那孱弱的中原使者放在一起比较狩猎?这简直是对草原儿郎的侮辱。他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你与那使者,又是谁人更善搬弄文字、搅弄是非?”帐中尚未点起篝火,天光只一个劲地暗了下去,头人几乎无法从残存的光亮中看得见匕首上的污垢了。“你从五岁就开始骑马捕猎……我们在马上摔下来的次数比那使者见过的马还多。但是那群中原的官人,从五岁就学了文字,若是他用言语欺你,你认得出么?”
侍从低下了头。
“你还是不服气。”头人最后一次擦过匕首。“罢了,是谁在盯着他?”
“一个小部族里,名唤别日得的。”
“你差人送半斤青盐给他,让他把人盯紧了。”
“是,这就去办。”
“让他们把火升起来吧。”
大帐中的篝火尚未被点燃,却又有侍卫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喊:“不好了!外面……外面乱起来了!”
-
“贵客,今日可要赴头人的宴?”别日得挂着笑,大大咧咧地入了帐,坐在周拂桢对面的毯子上。
“再不想赴了,那宴会吃得我食不知味的……”
“怎会这样!”别日得义愤填膺,怒得一拍大腿:“他们竟不给使者的肉食放盐么?这实在不尊重……”
“不是!”周拂桢连忙解释,“盐,自然是给我放的。只是头人及几位将军实在威风过甚,某与其同宴,实在不敢下口呀。”
这话乐得别日得一笑:“哪那么多想这想那的,你们中原人真是规矩多得很……哪里需要这样担忧呢?”
“别日得兄弟是霜原的勇士,这些场面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呵!使者有所不知,两年前我也经几个头人赏识,赴过一次宴……”
别日得饮过一碗马奶酒,又说了几件那时赴宴的趣事,似是显得分外开心。这几日周拂桢有意通过这位霜原的小头目结交其余部族,屡次佯作好奇询问对方经历,几碗马奶酒下肚,以别日得为首的几个小部族头领也聚到了一起,几人吹水闲聊,而那闲聊中不经意吐露的消息就是周拂桢这几日的目的。
只是今日,别日得显得格外开心。周拂桢知道自己在这大集中被盯得紧,只装作对好兄弟的境遇感到好奇:“兄弟,你说与头领一同饮酒是你最开心的日子,不过我看你今日也不遑多让哪。”
别日得乐得摇头晃脑:“也托了使者你的福……”
“我?”周拂桢也乐于做出一副茫然的样子。自己这几天认的这位便宜兄弟是个多嘴的性子,自己只需在对方说话时捧上一捧便能知晓不少新消息。
“看看这个——”别日得撑着地毯挪到了周拂桢身侧,一股子膻味冲得周拂桢做出的疑惑笑意险些破了功,好在他从皮袄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对着周拂桢晃了晃,吸引了使者的注意力。“若不是照看使者有功,我是断然拿不到这五两粗盐的。”
“盐也能做赏赐么?”周拂桢大吃一惊——或者是看起来大吃一惊。
别日得瞪大了眼睛,似是思考了少许时候,又作恍然大悟状点了点头:“你是大烨人,尚不知这里的情形。难怪了。”
“还请兄弟指教。”
“也说不得指教。”别日得将那包粗盐收入怀中,“兄弟你也知道,我们草原不曾产盐,若要买盐,非得从关口与大烨买来才行。只是与中原人买盐需得盐引,往日里只有头人有这样大宗的生意往来,得以收入盐引。我们这些小部族,只好买些粗散盐两,若是要大量购入的话,只得从头人处转一次手才行。”
“这样岂不是有不少耗费?”
“耗费虽有,总是看在同族的份上减免些的。只是路途遥远,又多加转手,草原的盐总是要贵上一些,往日里也是不够敞开来用的……只是今年又是别的事了。”
“是关贸……”
“不错,正因关贸未开。”别日得的脸上泛起苦笑,“往年用一车皮货能换的盐,今年是拿三车皮货也换不着了。若说往年,粗盐虽然紧俏,若是省着吃,也堪堪够一年的,年景好的时候几车皮货还能换一斤青盐尝尝。然而今年不提青盐,连粗盐都得争破了头去抢……”
“居然成了这样!”
粗盐是苦的。海水煮成了盐,百姓吃到的却不尽是盐。海水里的杂质煮不干净,那种带着涩味的白色晶体随着盐一同被装上车,跋涉了这样远的距离,经过了层层加码,从草原人的手中换成了皮货。粗盐苦涩,却便宜。像别日得这样的部族,能有粗盐吃已经是足以欢喜的事了,然而头人与可汗吃的却是青盐:一种咸得精纯、没有涩味、粉如白雪的好盐。这种盐出自青池山的盐矿,他们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井盐。蜀郡的盐工在山上打下直上直下、碗口粗细的井,从井里提出溶解着纯正盐矿的盐水,那盐水煮出的盐最终上了王公贵族的餐桌,也以极高的价格打入了草原,成为头人与可汗桌上的盐。
“唉,若是我也能赴头人的宴便好了。想必可汗的桌上,煮肉时撒了盐,切完还能蘸一圈盐,连马奶酒都是咸的……”
“我竟不知兄弟你的日子过得这样辛苦,只是……”周拂桢慢慢俯下身,一种紧张的喜悦传遍了他的全身。若他是个钓鱼佬,他便知道这是“鱼咬钩了”的感觉,可惜他不是。“只是兄弟莫要怪我愚钝,为何不往宣威渡的集市上去买盐呢?”
“宣威渡?”别日得露出茫然的神色来。周拂桢见着他这副模样,故意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来:“别日得兄弟,你竟不知么?——也是,近来兄弟被困住此处,也无从知晓别处消息……”
“局势这样紧张,竟还有集市敢开么?”别日得急切地问道。
“据说是朝中有人向天子上策,以怀柔拉拢霜原人,只是我非是官场中人,对此事不甚了解……”
别日得的神色显出焦躁,起身在帐中乱踱着步子,思考了一会,复又转身对着周拂桢道:“我当给族里传个信……我带族中子弟应召,将族里的好马带出来不少,得让她们往那什么宣威渡去看看……”
“别日得兄弟,可是有困难?”
别日得心神不宁地坐下,“若是她们能将今年积攒下来的皮子卖了……盐、粮食……唉,我还有十几位其他部族的兄弟,得和他们说一声……”
“兄弟!”周拂桢猛地拉住了别日得的手,凑近了低声说道:“扰乱军心可是大忌!”
“可我族里的孩子快要被饿煞了!”别日得似是反应过来,虽压低了声音,却隐隐透出愤怒来:“你怎得不早几日告诉我?我也好让族里早些去买盐……”
“兄弟,兄弟!”周拂桢的脸上浮现出一副后悔的神色来:“我不该说的,此时你也万万不该告诉别人……那些盐引是我用来收买头人用的,事成便可去宣威渡提货,你千万不可——”
“你还带了盐引!”别日得的声音越发压抑,他扯住周拂桢的衣领,神色变幻了几下,又狠狠将他扔在了地上。别日得从腰间抽出刀来指着他,喘了几口气平复了一番,小心翼翼地退出去,招来在一旁发呆的部族年轻人:“快收拾东西——帐篷不要了,我们带着马和财货走……让他们不要惊动别人,出去之后在山谷集合,我自有安排!”
他想走了!别日得想偷偷溜出大集,带着财货换走盐带回部族。周拂桢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叠盐引。
别日得又把视线转回周拂桢。周拂桢害怕得发起抖来,哆哆嗦嗦地将手中的盐引递到别日得手里,又是恳求又是作揖:“兄弟,看在我们这几天兄弟的份上,我不告诉任何人,求求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让其他兄弟也来抢我的盐引……”
别日得心中一动。自己自然可以偷偷摸摸地一走了之,只要混过去,过了这个冬天没有人能记得自己的失职,自己如今犯下的过错自然一笔勾销,然而那些兄弟们呢?他们也与自己一样缺少盐,他们部族里的娃娃也因为缺盐四肢无力地躺着,可这狡猾的中原人,手里的盐引还有很多,难道就不能分润一些给自己的兄弟,让他们也救救族里的孩子们吗?
“妈的,抢的就是你!”别日得恨恨地暗想,胡乱将周拂桢手里的盐引一把夺过,那盐引花纹细腻,哪怕这大集的消息是假的,盐引也该是真的。别日得的心中更加怨恨,将颤抖的手塞进袖管里,佯装无事发生一般离开了分给大烨使者的帐篷。
不多时,几人带着骏马号称巡视离开了大集,又过一会,几辆马车号称联系其他营地,驶出了大集,安静得犹如水壶里冒出几个气泡一般无人注意。
不到半炷香后,几位年轻的族长聚集在使者的帐篷前,周拂桢仿佛早有预料,恳求着递出盐引请几位兄弟饶自己一命。得了盐引的几位推推攘攘地吵了起来,几人各自回了营地,大集就好像水微沸一般鼓噪起来。
太阳尚未落下,两则消息便如风一般传透了营地:
大烨使者的手里有盐引!
宣威渡正在卖盐!
大集喧扰起来,往常与别日得及几位年轻头领陪同着四处走动的大烨使者已不见人影,只是他的帐篷里散落着一地盐引。盐!有了这盐引,就可以在宣威渡买到盐!众人躁动着从地毯上捡起盐引,揣进怀里,驾着骏马或马车往外奔去。草原上的众多部族间,他们是被压迫的最底层。他们平日里放牧劳作,战时便是大部族的马前卒,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没有多余的金钱买盐。
可是盐多么重要呀!在这草原上,连含着盐分的泪水都是宝贵的。缺了盐的孩子迅速虚弱下来,他们无法劳作,无法站立,使原本就挣扎在贫苦生活中的牧人家庭受了一记重击。然而此刻散落的盐引可以救下他们。可以让孩子健康。可以救下许多生命。
必须得换到盐。
散落的盐引飘散在大集中,昭示着使者逃亡的方向。一架又一架马车驶出大集,往宣威渡的方向飞驰。头人从牙帐中钻出,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局面。头人暴跳如雷,喝令军士维持秩序,然而那些最底层的军士早已揣着盐引离开,无人可用,无人可挡,整个霜原大集就好像一头嗅着盐水气味的老牛,被盐引了过去。
篝火仍未升起。篝火不会被点燃了。
-
大烨使者周拂桢,以盐引一千二百斤收买霜原将士,霜原之围已解。这次不合时宜的出兵使得霜原离心离德——一年。或许明年的秋后,霜原会再一次举兵南下,但是这与今年的霜原再没有关系了。荒废了一整个夏日的牧民需要休整,恐怕在下一年之前,霜原再也无法聚集起足够的兵力了。
当然,事后回到大烨的周拂桢因此受到嘉奖,甚至蒙恩主连衡的上书得了个官身,甚至乐得差点得失心疯的事就与此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