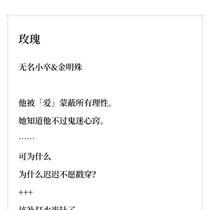这次终于写了主线φ(゜▽゜*)♪
字数:3200
+++
一足鸟站在厕所外,心不在焉地听着里头的人交流刚看见的事儿。他胳膊上搭着周一的外套。除开兜帽里有满满一兜的彩虹糖而不是爆米花以外,一切就像任何一次电影散场后那样。
而如果要给在那个冰冷、阴暗的停尸房里发生的一切打分级,那无疑是pg-17——毫无疑问是恐怖片,但混有少量喜剧(或者说地狱笑话)元素。
首先,主角们理应是具备职业素养的、来自中国的、会功夫的道士。可他们一开场就被困在停尸房的冷柜里,生死不知,变成了没那么多戏份的特邀嘉宾。那些冷柜,在残肢断体拼凑的肉山怪物面前就像是一台台的冰箱。他逐个打开变形的柜门,像是穿山甲在找蚂蚁,不费吹灰之力。有时他会从柜中拽出什么,也有时会因柜内空空如也而敲瘪更多柜门。
而其他人呢?
手无寸铁、围在停尸房外的长廊,拿着可笑的武器和防具,像一帮发现主演罢工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上的群演。包括他,也包括周一。
通常这种情况下该有一位世外高人伸出援手,可他们能指望的“帮手”只有时在时不在的Ymir。安排这样的混乱中立外挂,导演大概是铁了心要拍全灭结局。不甘认命的群演在公共频道拼命刷屏,寻找带了符、能掐会算的道士和看起来三拳能打死老虎的功夫人。可那两个账号像是掉线了,始终没发言。
到了这种局面仍算“pg”而非“x”,是因为在任何一部,呃,更古典的邪典片里都不会有人在想呕吐时呕出大量彩虹糖。它们铺满地面,像盛满巧克力豆的容器被打破,遮掩了满地的黑红血迹。当一足鸟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倒是想过如果发生这种事该有多酷多快乐。可他现在已经25岁了,只觉得这部游戏里的设计实在是混乱得够可以。
公屏叮叮当当的提示声和停尸房里的声音混在一起,古怪得要命。这里的隔音有时特别好,有时又像完全没有衰减——至少咀嚼的声音毫无掩饰地钻过铁门到了一足鸟耳朵里。他被迫在骨骼被清脆地咬碎、骨髓被珍惜地吸出、并且从关节被用力扯断的声响里分辨出气息奄奄的求救和哀嚎。
这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他不得不绝望地反复确认口罩是否戴好了、甚至紧紧用手指按着它,尽管理论上那是一片不会掉落的贴图。
门开着一道缝,他站得不近,但或许还不够远,也许他的视力在万灵所得到了加强,否则怎么能清晰窥见怪物捏在手里的断臂断腿呢?理论上它们不会喊疼……但那就更糟糕了。人体的断肢面滴着血,人们喷涌的呕吐物却是彩虹糖。彩虹糖是真的,那么感官生出的食欲或许也是。一足鸟必须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这是vr游戏,你看到的只是没有实际气味和口感的贴图”……老实说,收效甚微。
在看见腐坏的露骨肢体时,他也看见焦红如被高温炙烤过的断面边缘;他嗅到腐臭的气味,也闻到滴落的肉汁;他看见怪物发黄的犬齿撕扯人体,也看见去除皮肤后的饱满脂肪与肌理。他的血管里似乎正生出羽毛,喙和爪也似乎又要回到身上。而他的咽喉和口腔在万灵所就已被腐肉征服,固定成了一只游隼或秃鹫,听见进食、看见“类人之物”被吞吃的场面,尽管属于人类的胃部隐隐痉挛、将胃液上逼,但冷汗似乎都向口腔汇聚,叫他口舌生津。
幸好被恐怖与美味同时拉扯神经致使两厢矛盾的大脑最后指挥身体——你大吐特吐吧!
做得还不错。喉头被颗粒物撑开时,一足鸟拉过周一的兜帽,在对方的抗议里把肝胆和食欲都吐了个一干二净。很神秘——没有血迹,没有唾液,只有 光洁的糖——他看着这些东西竟没有生出多少抵触心理,甚至神差鬼使地捻了一颗放在舌尖。东京湾已经这么做过了,但吃不知谁的代码构成的糖果,就好像吃掉了对方意识或身体的一部分。这是需要额外警醒的事情。
甜的。
咀嚼,咀嚼。和平时一样没很喜欢,真不知道谦人哥为什么会吃到得蛀牙的程度。
血肉也好彩虹糖也罢都是由代码构成,为什么其中之一变得明显更有吸引力?一足鸟试着回忆在万灵所发生的:人类,动物,几乎所有在场的生命都收到抽屉中血肉的吸引。可那样的东西难道不是圣餐吗,怎么反而带来无可救药的欲望?
……不,动物们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食,积蓄足够的能量而繁衍。只有“人”会为“无可抑制的食欲忧心。
大师们还是毫无动静。
一些人决定逃跑,另一些决定声东击西创造救援机会。理所当然周一是后一派,他往怪物的方向丢杂物想吸引它的注意力,而一足鸟把他拉扯到房门边的走道,用CD机的一角猛敲墙面制造更多噪音。
怪物要冲到他们面前也就是20秒的事,一足鸟平时不会掺和进这种混乱局面——就算在逃生游戏里,他也是更倾向于独自逃跑的一派。周一会说“等等兄弟我来捞你”,而他说得更多的是“See You”——他的道德只到看见““英雄”被“暴徒”暴揍不会笑着录像发到社交平台。柯蒂说“你们是英雄”,一定是有哪里搞错了。
只有一小撮人真的不假思索在做勇者。年龄越小的越这样,中二病和勇者只有一线之隔。也有些人不那么小了但天生有颗侠义心肠,遇事不决搭把手。
中国似乎特别流行这个。
一足鸟望向周一。后者向他投来一个“好兄弟够义气!”的眼神,砸得更卖力了。
……有点抱歉。
一足鸟转而去看其它地方。
很难和周一解释他只是由于已经处于被兽性入侵的状态,唯恐再不多做点“人性所致”的壮举恐怕会被同化得更快,故而为不沦落到四足爬行而在努力。
看看那个以人的形体扯了肉吃的程序维修员吧!他的眼睛根本要黏在怪物身上了!
有人冒险关上了停尸间的门。过了片刻,恬静微笑着的“前台管理员”从里头走了出来,朝躲躲藏藏的群演们浅浅鞠躬。公屏消息慢下来几秒,随即刷得更快了:
【她不是在简的背包里吗?】
【在的,ZIP格式】
【现在出来的是什么?】
【她就是刚才那个怪物吗??】
没人敢拦着她问是发生了什么事,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像抱换洗被褥一样抱着一堆血肉进入了卫生间,又两手空空回到“工作岗位”。再过了会儿,停尸间里又伸出四只手,齐齐把两扇大铁门掰得更开——黑白中国人一左一右闪亮登场。
“摆摊!宵拐!你俩没事啊!”欢呼的人们迎上前去,而公屏消息中突然刷出好些发送时间为数分钟前的图像。
——肉山怪物翻找停尸柜胡吃海喝。
——肉山怪物从自己身上撕下多余的手脚。
——嶙峋的怪物吞吃从自身扯下的部分。
——它剔除几乎所有的多余,变成“她”。
——前台小姐抱着多余的血肉离开停尸间。
一足鸟猜想这可能是某种自洁型杀毒程序,只是它的呈现形式过于直接……不过玩家曾用过的载体居然也是病毒的一部分吗?幸好分开送的第二具尸体并不在这里。它在他和周一的房间安睡,不日便要被他们送进奇观所的集体墓地——只要他们没有因其它原因死于非命。
群演们也很快接受了这件事。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带领下,人们浩浩荡荡地挤进厕所型谜象的内部开始探险,人们的惊呼声和谜象的赞颂声此起彼伏。同样不容忽视地还有快要从厕所最末的隔间喷薄而出的血肉。女高中生们在和谜象谦虚,周一在和谜象互夸,白川奈奈的哽咽夹杂在大笑间。还有人在气急败坏地喊““别说啦!”。
明明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声音,一足鸟却痛苦地发现占据自身最多注意力的是卫生间里飘出的香味。他只看了一眼就缩回脑袋——有些人正捧着血肉往隔间内塞——像个拒绝陪孩子登上儿童小火车的家长。
他往嘴里又丢了几颗彩虹糖,飞快地 机械地咀嚼。
甜的。甜的。酸的。甜的。
有个人弓着背走出厕所。一足鸟注意到,那是同样在万灵所吃了肉的维修工。他的喉结在频繁地上下挪移,像正被使用的粘毛滚筒。
“想抽烟……”他因一足鸟投去的视线含糊地解释了半句,又在看到他的黑色口罩后戛然而止,转而身体贴着墙往下滑,叹息着像只大狗一样蹲坐在地。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不住搓动,像那儿夹着根看不见的烟。
一足鸟垂着眼看他:”你怎么样了?“
”我吃了一块分开送。“维修员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很香,口感像生牛肉。那台料理机真的不错……你那天是不是没留下?很可惜啊。”
一足鸟闭紧嘴。
或许他该规劝对方别做这些出格事。但这是“游戏”而非“现实”。
“我好饿啊~你也是吧,不想填饱肚子吗?”维修员是个大个子,无论何时喊饿都合情合理。一足鸟看见他健康的牙龈和牙齿,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似乎是在笑。并不泛黄反而森白的牙齿嵌在粉色的肉里,让他看起来像只追猎失败的野兽。他的肚皮还是空瘪,但野性得以释放。
他们都知道这种饥饿要如何缓解,但一足鸟只是掏了把糖,分给他。
他往自己嘴里也又顺手丢了一颗。
……是绿色的,好酸。

是主线正剧!但顺序没有在连着看
已修正内容,有请计分和观看
字数:4300
+++
2024.04.07 22:40
305B
温度24度
“肯定金的银的都要啊!”周一盘腿坐在床上揉着发酸的胳膊,“三把斧头一起上,你一柄我一柄还、哎不对我可以拿两把,李逵好像就是俩...肯定能把农神砍得落花流水!刚那会儿就只找着个板凳不顶事儿!哎、鸟哥,你呢?你怎么说?”
一足鸟没搭腔,于是周一探头往浴室望。后者也已将自己收拾干净,似乎正对着镜子擦头发。
今天回来时对方不言不语、只是频频低头看衣服上的血污,叫周一多少有些不安心,但人气主播MondAy是多聪明的小伙儿啊,才不会明知故问“你没事吧是不是异食癖又发作了”——他直接把一足鸟的外套扒了往浴室里一丢,又表演了个一秒入浴,主打一个眼不见为净。
晚上发生了太多事,又是和顶天立地的巨人搏斗(单方面)、又是在裁判所拍桌子勒脖子地阻拦同伴斗殴并出庭作证,他像刚参加完极限运动似的满身青紫,浴袍一掀也有瘀伤。他自己倒不怎么介意这些(反正也不疼),相反因做成了两桩大事神清气爽,但一足鸟瞥见了立刻眉毛皱得死紧,所以还是快点消掉得好。
可即使洗刷干净、处理完伤口,他的好搭子今天安静得要命。
一足鸟不提自己实属正常,他在游戏外也这样。但无论是在连线游戏还是干碎农神时,他总会来望周一有没有事,像这样从庭审回来一句都没不问,这就不对劲了。
——那么,在一足鸟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2024.04.07 22:22
一足鸟洗去灿若星河的毒药。拂过银河水的手掌并未截留美丽的星空。清水洗过后留下的只有艳红的肌肉和焦黑的皮肤边缘。疼痛感几近于无,大约一觉醒来就不再会有这些像素噪点。但一足鸟还记得手掌被贯穿时的知觉,无法对它置之不理。他一遍遍用冷水冲洗它,就像在现实世界中处理化学灼伤。
……但也有人一直处于肢体欠损的状态中。无口,无舌,无声。
一足鸟望向镜子。
与他贫瘠的游戏常识不相吻合的是,这个局域网游戏中的世界几近真实。镜面映射出的一切都是实时的(尽管不一定忠实),如果处于潮湿又高热的环境中,水汽一样会模糊镜面。
并不清晰的镜中人与他相互注视着,像一道幽灵,它同他一样疲惫又冷淡,不会像55555那样讨喜地鼓励说,“你今天做得漂亮”、“你几乎付出了生命、你是个高尚的人”,而这沉默正合他心意。
“勇气”称号带来的效果持续了一整晚。它先是帮助他在外神的肠腹中攀爬,冒着被胃液溶解的风险、克服将神食用的欲望,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般完成弑神壮举。又帮助他在异常之物遍地的法庭中与非人的审判者们对峙,让他得以冷静地协助其他人、从荒诞的厉法中救出并不熟识的同伴。
英雄之举!毫无疑问。
【……可我不想做 这种 英雄】
说不清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一足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当被激发的肾上腺素消耗殆尽、总算从英雄做回凡人,比起失落,他更多是感到脚踏实地的安心。
窃窃私语着的念头越扎越深,一遍遍在他心中回响,像株渴望阳光的植物。
我不想逞英雄。
我不想做那个所有人站在原地时上前一步的人。
我不想做那个所有人后退时站在原地的人。
——我不想做会被记载传唱的英雄。
如果有人因此无法得救?不,这根本不是有价值的砝码。
一足鸟清楚自己非要躬行善举的人,不会把救护他人的责任揽在自身。哪怕在“勇者成名录”中积极地交涉、积极地挥舞武器,在那以外也积极地解锁迷雾地图,甚至带着剧毒潜入了食人之神腹中……但那并不是因为想“帮助谁“。他只是在想——
【快让这一切结束吧】
所有的、所有的。
如果自然所要得到祭品,他可以给出自己身上不影响生存的部分。如果有冒险精神的人需要援助,他可以为对方奉上提高生还率的物资。如果谁的形态影响他的思维,他可以试图帮助对方摆脱。
英雄脱胎于凡人。
Jimbeam会为救助朋友在所长转让申请书签下自己的名字,哪怕已看清前方无路;昇会为不知回报几何的险境剜出自己的心脏;白和周一冲入能溶解人的雨幕;瑞士花生舍弃自己的手臂保护了其他人。
……而一足鸟。
他会为即将崩溃的琳娜呼唤柯蒂——但不会拉住那只血肉模糊的手将自己置于险地;
会为分开送的遗体寻找埋骨地——但不会从此看顾弱小者以免她丢掉第三条性命;
支持和默许身手敏捷的周一去帮助更多人——但不会为提升集体胜率自己也去冒险;
他不排斥成为一个无责的辩护者——可辩护律师这一具责任的职责,他从未想担当。
他期待“游戏结束”,却又忧怯要为此支付无法清偿的代价。
他所为非是英雄之举,只是凡人援手。
恐惧逼着他奔跑,却又使他斤斤计较,未知在他耳畔呓语,他因而瞻前顾后。
……不过,即使处于这种境地,即使自认是凡人,一足鸟也认可总有些事不是为【结束】而是为【保有未来】做。
自身的,他人的未来。
一足鸟用指尖摩挲镜面,冷水在潮气覆盖的镜中融为文字。他以这种方式向某个不在此处的人书写,就像对方常做的那样。
——你称我们为英雄。
——你如何理解英雄?
镜子当然不会自动拼出文字回应。就像人们被呼唤时并不一定会破窗而入。
可一足鸟还是继续写。
——琳娜是一段程序。
——你能帮助她,你是她的同类。
——你们是处于局域网中的智能生命。
他前倾身体从左到右写满镜子,又将手指下移去书写另一行。浅红的字句落到镜中,又被凝滞的水珠抹去,像是被撤回的字符。
——如果我们通关离去,你们会去向何方?
——如果一开始的爆炸已真实发生,你们是否将和这里一起消失?
——你说过,我们是高级的信息载体。
——那么、如果、
想书写的位置有水流淌下,不再能留下痕迹。
一足鸟没有再哈一口气继续写。他收回手,镜子里的世界变得更清晰了些,叫他得以看清自己现在的神情——没什么特别的,没在笑,也没有哭。硬要说的话眼睛睁得比平时大点儿——他将食指放在自己的右眼眼角,压着睫毛根本向左滑动,而后径直向上。他制服了下睫毛,将指腹竖在眼前往内压,可眼球刚接触到温热的指腹,上睫毛就指挥眼皮合拢驱逐异物了。
他又试了两次,还是这样。
他开始在滴落的水珠中拼写那个名字。
C_
Cu_
Curtie
一足鸟在镜子前站了大约有十分钟,耐心地听着水声冲刷砖石,直到它被周一的喊声盖过。
镜子上的水迹未作回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自由的武器商人。”一足鸟轻声说着,在镜面画了个笑脸。
2024.04.07 22:42
——在镜子上书写过的都已被水痕抹去。
手上的血水已经不再往外渗了,但看起来“很疼”。一足鸟戴上防割手套,慢慢用吹风机将头发烘干。当然,为了发质考虑,发尾还是得用毛巾擦。有些事还未想出结论,也许放片刻再思考更好。
周一没等到回答,蹦下床三两步跑到浴室边:“……而且金银做的斧头还很值钱!我可以年节多奉河神香感谢他老人家,然后把斧头融了分给需要的人嘛。你呢鸟哥?你肯定也不会说谎,也能拿三把斧头对吧?”
一足鸟调小吹风机的档位,他的喉咙还在因过量的糖分不适,音量很小:“恐怕我会把金斧头和银斧头丢回河里。”
“这是为什么?”周一探出半个脑袋,把脸颊搁在门边贴着,问。
“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一足鸟回答。头发半干不干,他从镜子里看了一眼周一,补充,“但我会要祂把铁斧磨厉。”
“这又是为什么?”周一换了个姿势,双手抱臂,肩膀靠着门口。好像给不出他满意的答案就不让走了似的。
“因为那是我的东西。”一足鸟说。
我的东西。我所持有的,我所期望的,我所依赖的。
……依赖?期望?
沉在溪流的尸体松开手,涂着红色甲油的手从墙内伸出。
一足鸟浮上水面,少女在棺中安睡。
一足鸟撞入墙内,蜷缩在角落的金发女郎抬头微笑。
【如果她是有成长能力的AI】——她向他递出的不是签字笔,而是胶带。
【她会继续生长,拥有未来】——他叮嘱她遇到危险躲起来,她逃离了坍塌的会议室。
【她还活着,她是 活着 的】——她从致命的画作前拉开他,死死地遮住他的视线。
智能生命?谜象?人?动物?植物?语言相同?这些分型……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She is alive.
一足鸟关掉吹风机看向周一。
他的朋友是个经典英雄式的人物,会不计得失地帮助任何人、有勇敢的品格和成为“英雄”的潜质,看重亲友甚过外物——他们患难与共,对对方的品格和行事准则心知肚明。
他哑着嗓子问:“周一,如果有人因你的请求帮了另一个人,你会用自己所有的几成感谢他?”
“当然百分之百咯,我自己的诉求有人肯帮我做,肯定要百分百感谢啦?”周一理所当然地说。
“什么样的百分之百?”一足鸟又问。
“诚意啦、诚意。你看,愿意帮我的人,对我好的人,我就不应该辜负他们,应该全力以赴去回报……不应该是这样吗?”
不,就应该是这样。
【理】就该是这样简单得让人惊叹,明澈得无从质疑的东西。
“有人救我一命,我希望他们都能活下来。”一足鸟看着镜子,“我们也会尽力活下去。”
“没问题的啦,我们设定就是勇者和英雄嘛。你选法师的话,我做战士就好了。”周一和他并肩而立,用双手将嘴角向上拉,“来吧!微笑面对生活。”
一足鸟模仿着周一。
就好像……拥有人形的柯蒂模仿着他面前的玩家们,尝试用人类所能做到的方式与人交谈——即使他在这片数据空间中无所不能。
你呼唤他,他响应。你解开他的眼罩,他默许。你捉住他的手,他任你引领。但这可不是什么有约束力的上下级关系。只是他【选择】更靠近人类
2024.04.07 19:42
法则所
前往法则所之时,在一足鸟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段关于幼小的ai的,无声无痕的交谈而已。
将琳娜和U盘托付给柯蒂不到一日,一足鸟已经开始烦恼它的保存问题——他完全没怀疑过“柯蒂无法帮被错误数据侵蚀的琳娜修正代码“——如果他们现在是处于意识的局域网或二维与三维的夹缝之中,之后要怎么把琳娜带离这个已经不安全的地方?柯蒂又能去哪?
他始终没忘记宣告游戏开始的那次爆炸——柯蒂未能感知它。
他有心找到少年模样的人工智能以梳理那些影影绰绰的想法,但与农神的斗争让他疲累不堪(先不提如何攀爬曲折的肠道有多费力,过量的糖分让他快被黏住嗓子),又兼想为昇等人的脱罪出一份力(既然已经获得了自然所的工牌,不使用它将是可耻的),没法思考太多其它问题。比如”如果柯蒂也有核心代码,需要多少储存容量“。
当和柯蒂在法则所的庭前相遇,他的精神只容许他以口型和气音发声。
“Lynna?”就像之前的每一次交谈,一足鸟未做寒暄。
眼睛如同羊羔的人工智能不在乎这些。他将手指架在空气中,横平竖直地比划:“24”
一足鸟的视线追着他的指尖,追问: “Day?Hour?Min?”
“Hour”柯蒂眨眨眼,依旧用书写回应。
这比对口型舒服多了。一足鸟莫名感到雀跃。他环顾四周,有的人正围着抽屉看,有的人在地上爬,有的人在摸0069……总之没人在注意这两个默默无声的家伙。
……而就在这里,这个无人注意的角落,有人应他的请求截留了另一条生命。
”Anything else?“柯蒂画出一个问号。一足鸟点一点他的手指尖,就像小时候常对胞兄做的那样。柯蒂不做询问,只是抬起手交给他。
【像是要去过马路】
他莫名地想。遗憾的是他们并非要去春日出行,而是要去裁判庭争取留下同伴的性命。他低下头在柯蒂的掌心书写。浅浅的压痕仅留存一瞬,但他就是觉得柯蒂可以看见。
U re her hero
U re one of the heros
——而就在这一瞬间
——像夜昙绽放,蝴蝶起飞,顿悟收敛羽翼不期而至。
【这也许也是我唯一愿意成为的英雄】一足鸟意识到。
一个属于个体的、微小的、平凡人的……就像柯蒂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