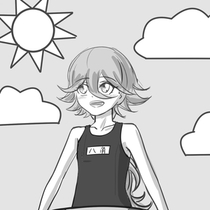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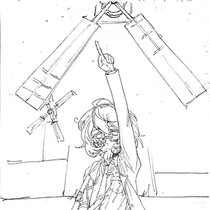


烈火。
浓烈而炽热的火焰席卷了他所能看到的所有一切。橙色的、橘色的,热烈而炫目的,他们如同有生命般的吞噬、占有着眼前的一切,仅仅留下一丝焦黑的残渣,而之后他们就会熄灭,如从未存在般渺无人烟。
这正是无相降雾有记忆以来,能够触动自己、给自己感受最深的场景,没有之一。
这场事故大约发生在他六岁,是他的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异常、感到绝望之时。是他的才能——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尚未发现之时。说来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或多或少有些可笑,但当时的他,当真是觉得生命如此无趣,决定消灭自己的存在。他甚至准备好了凶器、一把从厨房偷来,被大人们随手放在低矮橱柜中的水果刀。若不是他的感官并无异常,第一次试探性的下手就痛的喊出声来,他本人或许早已不存在与这个世界上了。
理所当然的,他被家里人询问了,他也理所应当似的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倾诉了出来。这份想法没能被理解,颇有些惊慌失措的家人将他关了禁闭,同时禁止他跟一切危险物品的接触。
而事故正由此时发生。事故的起源已经不可考,大约是忘记关闭的炉火又或是翻倒的油灯。这场大火与其他同类事故一样发生在深夜,他在睡梦中被燃烧的焦烟呛醒,黑色的烟雾与高温的空气扭曲了,而他在痛苦和朦胧中转醒,他张开眼睛。
那是火。
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火,他们像是一幅画一样,在墙上扭曲攀爬着,比血的颜色更明亮,比红叶的颜色更炙热,那是无相第一次在他的世界中、获取感受到那么多明快的颜色。
他自然是痛苦的。但他却一动也不动。这份炫目的颜色与热沾满他的整个世界与所有感官,这对他而言是从未有过的冲击。
(我也。)
(我也能够,变成这样吗……?)
而那之后房间的门是如何被打破?他自己是如何被救出?这些事情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的人生他的记忆之中,只有那燃烧着的明快的,如红色蝴蝶一般的,炽热的火焰留在他的印象里。
(我的人生,也能变成这个颜色吗?)
这是尚且年幼的孩子,失去最后的意识之前,内心中留下的小小愿望。
这之后他就没有再进行过任何的自杀行为。或许是那份炽热的火焰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苗,又或者说得不那么浪漫些,那火,或者说那个濒死的体验如同小石子般落入他内心中的死水,泛起了些许的名为希望的波澜。
与之相对的是他变得积极起来,相较于以前来说。他开始努力的尝试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事物、努力的体验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事情。这些尝试有许许多多,从备受好评的虚拟故事到真实而充满危险的活动。再一次的'刺激'是一次跳伞的尝试,以从未想象过的角度俯瞰大地,那份波澜壮阔,就算是他也感受到了一丝欣喜。
——以及,一丝恐惧。
站在舱门边缘时,俯瞰这云与月时。身体比情感更加诚实,他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些微的发着抖。
(……原来我……还是会害怕吗?)
于是这份快乐压倒了恐惧。他第一次这么清晰的感受到了自己的感情、又或者说,感受到了自己身为人类的证明。是对生命本身抱有渴望,被称为人的本质的感情。于是之后他就爱上了极限运动,虽然一般来说并不会带来真实的疼痛,却能让他体验到对死的恐怖,或者说在死亡边缘游走的感觉,正是这份感觉,确实让他体会到——他还活着。
但是这份快乐,或者说是刺激总是有尽头的。再大的刺激也总有习惯的一天,每次的平安无事都是在告诉他下次结果的信号,他逐渐变得习惯起来。
于是他又把视线投向其他地方。这时候他已经不是小孩子的年纪了,也逐渐的可以从自己那枯竭的感受中跳出来思考。他发现自己的思考仅仅围绕着现象本身,而不是这份现象的原因。于是他转换了思路,把思路扩展到更为长远的,更为久远的人类的整体上去,为此考古学的技能可说是必然而然。
一定要说的话,他成为考古学家还有另一份原因。那就是这些人——他的同行之中——有很多都是对人类有着相当的兴趣与热爱。他们如饥似渴地探索着人类的一切,像是沙漠中求水的旅人,也像是他,渴求着存在与意义的他。
为什么他们会对人类本身如此的感兴趣呢?
为什么他们会对说到底无意义的人生充满执念并为之奋斗呢?
他思考着好奇着,就这么投入了兴趣与毅力,而这之后,就是身为超高校级的考古学家无相降雾的故事了。
他偶尔会想起那火。那壮烈燃烧而绚烂的样子,不正像是有些人的一生么?
*
他从梦中转醒,他又梦见了那场大火,纵使时隔多年,那壮丽的颜色仍然栩栩如生。
他睁开眼睛,眼前是熟悉的星斗,托br把他们带到无人小岛上的福,这里没有晦暗的阴沉的劣质空气以及城市的光污染,星与月是那么的清晰与明朗,月色静静的流淌下来,像是一副静悄悄的画儿。
(如果没有br的话……说不定倒是不错的休学旅行呢。)
他这么感慨着,又慢慢躺回自己的睡袋里面去。四周都静悄悄的,夜色比现在的环境添上一份诡异,仿佛在哪儿都躲藏着时刻想要吞噬掉他性命的人。他转头凝视着黑暗,黑暗也转头凝视着他。
(……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我也变得这么疑神疑鬼了啊。)
他重新闭上眼睛,却没有了睡意,就只是静静的躺着看着那星光。他本人对br法案了解不多,仅仅只是'超高校级被选中的概率明显更高'这一点而已。人类在稀有的惨剧降临前总是不认为那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又或者——他仅仅是因为害怕而不去想这份可能性了吗?
无相降雾没有杀过人。
严格来说是,没有夺取过任何能够让人看出痛苦的、有人类能够理解的智力的生物的生命。
不过,他曾经想要试试看夺取一个生命。
或者杀掉一个人,这恐怕是比他想象中要更加容易的事情。勒紧颈脖上的绳索,将锐器捅入一个人的体内,甚至是在不经意时候轻轻的一推,一个生命就会如此简单的走向死亡。
他很早就发现了,他个人的同理心非常的淡薄…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在别人痛苦难过哭泣的时候,很少也很难能够在他心里激起什么波澜。就算夺取什么生物的生命,就算真正的杀掉一个人,他的内心想必也不会有什么波澜吧。又或许能够像感受到恐怖一样,能够有些些微的、人类存在的证明吧。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呢?恐惧?法律的约束?如果是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在这里。
这个充满着鲜血与杀戮的地方,亦或是说他不得不,去伤害一个生命的地方。
(……如果真的杀了人的话,我……)
他看着已经逐渐泛白的天,一缕朝阳正在地平线上与薄雾中升起来,是他的不同的、这里格格不入的,阳光。
*
早上有些许的薄雾,让整个世界朦胧不清。无相在林中穿行,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什么森林中的秘境。薄雾在她身上凝成细细的水珠,多少让他的外套有些湿漉漉。远处的村庄若隐若现,正像是虚无缥缈的桃园。
是已经荒废的村落。
(……这里在变成br的根据地之前,曾经有人生活过吗?)
房屋已经是残破不堪,墙面上也都是斑驳的污迹。东西全都是散落着的,偶然间出现不知道是什么的腐败的物品。
(……但是日常的物品都很齐全。)
日用品之类,小型家电之类的东西还有不少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发出吱呀声的桌子和椅子也还能够勉强的站立,看上去这些屋子更像是匆忙撤退的、曾是谁生活过的家。
(这些人都去哪了呢……不,现在想这个也没有意义。还是找到武器比较重要。)
能够致人死亡的东西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之多。刀具、洗洁剂、锤子、扳手、甚至是绳索,太多了反而会碍事,最后他也仅仅是拿了两把较细的菜刀,总比之前好——他到当真没想到配发的武器里面会有火柴这种正常来说完全没法当成武器的东西。
(既然这里有这么多能够当成凶器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不能已初始武器来考虑其他人的攻击方式……吗)
一遍漫无目的的走着,一边搜索着目之所及的房屋。午饭被匆匆的解决,是并没有什么滋味的压缩饼干和矿泉水。期间也不是全无收获,多少拿到了还能够勉强运行的平板和笔记本电脑。
(……好吧,多少有可以做记录的工具了。)
于是他再往前走,却在下一刻顿下了脚步。他听见有什么声音在前面的屋子里、是翻找的,东西散落的声音,是动物所做不到的、持续很久的声音。换句话说,那里有人。
毫无疑问是他的同学。
项圈尖利的声音提醒他这也毫无疑问是他的对手……或者说,是他要杀死的人。
他紧手中的刀。
*
“你好啊,无相同学。”
“……”
他的同学——超高校级的枪械研究者 渡边翼笑眯眯的看着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立刻攻击的打算。无相没有进门,只是默默的盯着这个人的脸——或者说是脸上的笑容,这么看着,一股轻微的烦躁感情自他心中升起。
“……这种时候,就不需要伪装了吧?”
他冷冰冰的开口,换来对方一个稍微有点愣神的表情。而后是笑容的碎裂,像是被打破的镜子,又像是被打破的冰一样,他看起来和善而谦逊的笑容瞬间变得冷漠,换做有些不快而无所谓的面容。
“……你发现了啊。”
他当然是发现了。不过,这多少是因为对方和自己同类的原因,是在和普通人不同方面的同类,只是他不想伪装,虚假而虚幻的东西总是让他烦躁,像是水中的倒影,像是面前的他。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观察着对手,而渡边没有去找掩体,或者拉远距离的意思,看起来起码并不是远距离攻击的武器——这多少让他松了一口气,如果对手的手上真的存在枪械类的武器,那么这场战斗几乎就已经没有再打的必要了。
不过若对方手上也是近战武器,那么他无论是体格还是身高都更加占优——以杀死对手为目的来说。
而渡边则一声不吭的拿出了自己的武器——看起来是撬棍。他的眼睛是没有色彩的,脸上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他仅仅是机械似的抡紧了手上的武器,然后向前挥去,仅仅如此而已。
——这样真的好吗?
无相这才发现自己其实比对手更早一步开始了攻击,刀光像是被划破的水,带着冷然的杀气劈砍在对方的武器上,金属清脆的碰撞声在空中回荡,像是清脆的银铃。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看着对方眼睛里的自己,那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冰冷的、带着杀意的自己。
但他心中却有火在烧。
不是那种明亮而鲜艳的火焰,不是那种绚烂的自我献身,他更像是炉灶上的,阴影中的,蓝色而静谧,与黑暗中、以影为燃料的火焰。
那份火正在吞噬他的知觉。
但他从未如此集中。
这对他而已是与之前所不同的感觉。世界消失了、那份缠绕与其周身的迷茫也消失了,他的眼前只有这个人,他的眼前只有他的敌人。
刀的锋刃被挥开,刀的进攻被挡住,舞动的铁像是彼此杀意的具象,似有火花四溅。
刀具擦过对方的发丝,黑色青丝散落,险些就夺取了对方的一只眼睛,而无相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认真。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而敌手像是能够听见他内心一般的如此询问。他对上对方同样冷冰冰的眼睛,想必自己的也是如此的毫无温度。一瞬间的迷茫把他从那份内心中的火焰所拉回,他手中的刀也就此停了一瞬。
(……是啊,我为什么要杀人呢?明明我并没有那么强活下去的执念吧。)
撬棍从左边打来,无相用右臂用防御的姿态勉强挡下了这一击,庆幸的是对方并非是多么孔武有力的人类,这一击并未给他造成什么难以行动的伤害。
“……那么你呢?”
他如此反问,手上的攻击也没停。他或者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本身?他自己其实清楚这一点。
而攻击是不会停歇的。渡边手上的撬棍打中了墙上的柜子,玻璃破碎声像是清脆的三角铁般与刀剑声合鸣,而他的刀具擦着撬棍而过,这一次成功的划破了对方的面颊。
有鲜血流出,有铁锈的腥味,他从未知道鲜血的颜色是如此鲜红,如此的明亮。这份血液滴下,就像是代替对方留下的泪水,在地面上留下小小的一摊。
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是否真的要要对方的命吗?
他并没有手下留情,他感受到,他自己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杀意。他想要杀掉对方,他想要破坏对方,是的,他想亲手斩断对方所有生的希望。
这也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那么对方呢?
是的,为什么要杀人这个理由,仅仅在这一点上对方和他一样的无助。他们并没有,或者说之前并没有那么强的要活下去的执念。只是不想死罢了、或者说是,仅仅没有死亡的勇气罢了。
——他再度刺出一刀,目标是对方的脆弱的脖颈。
仅仅是没有死亡的勇气这件事,真的会让人产生无论如何也要杀掉对手的信念吗?
——刀划破对方的衣服,而撬棍擦着他的脸而过。
那么他们在此刻究竟是为什么如此认真的想要杀掉对方,如此认真的想要活下去呢?
“因为是,生物的本能吧。”
恍惚间,对方回答的声音夹杂着武器的破空声而来,那声音带着自嘲的笑意,又像是一声叹息。
(……生物,吗?)
野兽尚且拼劲全力而活,为了留存下自己的基因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那么他们呢?
(但是,我……)
“唔——”
些许是渡边生疏的动作让无相有所大意。他没有留心到,对方从侧边所踢来的,看起来是武术动作的踢击,他的膝盖一弯,几乎就要摔倒。
“我觉得……你是'人类'。”
因为是同类。因为是同类,所以无相立刻就意识到了,他所说的'生物'的意义,那是感受不到身为人类的家伙们,才会去下意识使用的用词。
他被从高位压制欺身而上,他看见对方的眼睛,依旧是晦暗而暗淡,像是蒙了尘土,但那里面似乎也有什么,有什么静静的正在燃烧。
“——只是,和许多人有些许'不同'罢了。”
渡边的双手高举着,他的手紧紧握着那个撬棍,白皙的手上沾满了肮脏的铁锈。就在下一秒,就在下一秒那个撬棍就要挥舞而下了。而那一秒似乎很长,他的视野里只有双紧握着的手,和那双或许在静静燃烧的眼睛。
——以及,对方暴露出来的,白皙的脖颈。
*
天旋地转。
他试图站起身,他完全无法站起身。他的身上全都是冰冷粘稠的液体,他们曾经那么的炽热,那么的鲜红,现在已经逐渐凝结转化成了冰冰冷冷的黑色。他的心跳过速,身体和手都在发抖。
“……渡边……同学。”
轻轻的喊着对方的名字,就像默念着什么的咒语。但是死者是不会回答他的,渡边或者说是曾经的渡边倒在他身上,他的喉咙被划破了,鲜血就像泉水一般涌出,沾满了他自己洁白的脸和曾经雪白的衬衣。
(……我。)
这里突然安静下来,仿佛刚才的刀枪齐鸣都是虚假一般。而他自己是停止不断的颤抖,他任由渡边的尸体趴在他身上,精疲力竭,都不愿再挪动一丝一毫。
混乱与恐惧。
红色与扭曲的现况。
他的大脑是混乱与麻木的,像是在刚刚高度紧张的对决中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而他心中的火焰却还是燃烧着的,像是把渡边的生命,当做了自己内心的燃料。但这份感情却并不是喜悦,也与恐惧并不相同。血液混杂着污泥,展现出令人作呕的颜色,这颜色沾满他的身体,也沾满了他的心灵。
(……杀人了呢,我)
他像是反复确认一般捂着自己的胸口,感受到自己心跳与脉搏的鼓动,感受到自己还活着的这份现实。稍微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站起身,他犹豫着将手探向对方的胸口,连自己也知道这是毫无用途又毫无意义的事情,但他就是忍不住,忍不住就确定对方真正已经死亡,忍不住去确定自己切实的成功。
(渡边同学……对不起。)
最后他稍微收整了下对方的仪容,起码让他的尸身,看起来不那么恐怖。他去那窗外,他去那草地,他小心的摘下了几朵明黄色与白色的小花,像是祭祀,像是祭典,将它们轻轻地放置在对方的尸体上。像是一个柔软而没有名字的墓碑。也不知曾经葬于br中所有无辜的人们,他们最后的归宿又会是哪里呢?
.
"果然,我……"
他的双手胡乱抹上自己的脸颊,他的手脏的一塌糊涂。那污渍是血、是铁、是褐色的泥土,是——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会留下的眼泪。
.
那份火焰正在燃烧。
那份火焰已经熄灭。
.
而他正在远去,与他从未知道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