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43字
前面还凑合,后面太水了。
-------------------------
“祈亲,快醒醒……!”
她面对靠着墙角的她跪坐在地上,身体微微前倾按着她的肩膀不断摇晃,无果。她半扶半搂地把她挪过来让她靠在自己怀里,抱紧了怀里的人。
“祈亲……祈……醒过来啊……”
她的声音发颤得厉害。
白光静静地照耀着她们,每一束光线都是一根泛着寒光的银针,亿兆根打在地上,静谧又嘈杂:医务室的灯光此时显得有些过分了。
“啊……呃……”
她怀里的她挣扎了一下。
“祈亲?!”她立即拉开她们之间的距离,仔仔细细的看着她的脸,又紧紧抱住,“你终于醒了……你终于醒了!”
“理绪、理……啊!槽……”
苏我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硬木地板上抱着头打滚打了很久了。不仅眼前的理绪被摔得灰飞烟灭,连她自己也被磕得眼冒金星——酒吧阁楼这木地板实在是太硬了!
她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非要照顾室友的想法从大学宿舍搬出来住在酒吧阁楼,也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把钱全都寄给失去生活来源的妈妈,没给自己留一点点钱买个软地毯,更不知道阁楼这床为什么小的可怕,让她打个滚就能滚到地上——
总之现在考虑这些早就没用了,她的头着实砸在了地板上,像砸核桃那样。
咚咚。
有人敲门。
“你终于醒了?”
一个梳着背头的男人也不等里面人应门,大大方方推门而入,一副有要事相告的样子。他俨然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却没在床上发现发出那声砰响的主人。他推了一下眼镜,在小阁楼里仔细的找了一会,终于在床边地板上发现了捂着脑袋抱成一团的苏我。
“快起来,你该销假了。”他看见赖在地上的苏我,忍不住皱眉,“你一个月前的事假到今晚到期,况且根据你的说法,你大学的考试应该在前天就结束了,所以实质上你早在两天前就该来上班,现在已经上午八点四十一分,距离你到岗的时间还有……苏我?”
“黑崎,”苏我听到他的报时突然神色一凛,她在地上挣扎着爬了好一会才起来,揉着磕痛的额角说,“我申请再歇一个月,这得算工伤。”
“假如你活到七十岁,你可以再跟我申请四十八年,为了你磕坏的脑子。”
“不用了谢谢您我今晚就来上班!”
苏我噌地站起来,顺手抄了放在床头的钱包,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黑崎看了一眼一并掉到地上的抱枕,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难得诚恳地体贴员工:
“你是不是需要找个恋人?”
“我不需要!”她一脸不快的转过头,“反正我这幅样子就是找不到男人而且很不巧我对女人又没有什么兴趣!”
“找一个伴侣有助于缓解你在经济上的窘境。”
“那我去砸一个ATM不是更容易吗。”
“那你去监狱里吃牢饭也更容易了。”
“……你到底想干嘛啊,”她皱起眉来,“我不就起的晚了一点,和你没关系吧?”
“不,是紫发的小姑娘来找你了,有一撮黄色头发,看起来像安琪儿。她在酒吧后门站了很久。”
黑崎这才说出他过来叨扰的真正原因。
他早上七点多钟从后门进来时看见一个紫发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他原以为是迷路的旅游者,却又感到有些面熟,于是上前问候,这才得知是来找他的员工的。
“天守?”
“恩。”
“知道了,我这就下去。”
“还有,”黑崎叫住转身就要走的苏我,“这个。”
她瞥了一眼黑崎手上拿着的粉红色的传单,没有接,似乎在等待对方说明意图。
“一个朋友给我的,不过我现在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黑崎思索片刻,怕苏我又不懂他的意思,补了一句,“你马上就要面对真正的人生了,是吧。”
“多管闲事。”她不客气的夺过黑崎手里的单子,折了几折放进口袋,一挥手,“姑且谢了。”
“……”
黑崎忍不住摇头:“好好的一个人。”
从地上捡起了印着颜文字图案的抱枕。他不得不承认苏我在工作上态度不错,也很有销售和调酒天赋。她请假的一个月里,从销量数据上表现为业绩下降,从现实上则是表现为一个接一个问候她的女孩子们不断光顾酒吧,可这家伙却好像一点自觉都没有的样子。
他叉腰盯着门外层层的楼梯,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又让他摇了摇头。
“可惜脑子有问题。”
其实也并不是苏我想这么粗鲁的下楼的,她实在是赶时间。
她好巧不巧忘了带手机下楼,本来起的就晚,再被黑崎耽误了些时候,要想买到限时的“那个”恐怕很困难了……哦对天守!还有神前天守在后门等着她,按天守的性格恐怕又是从开店等到她醒,就不能不那么温柔直接上来喊醒她嘛!这样她也不必赶着下楼吸引一串灼人的目光了,她差点被那眼神盯到烤熟诶!
她这么想着的时候,自然是忘了自己起床时的样子是有多凶暴。就连练过拳击的黑崎也不乐意上来喊她,何况一个小姑娘。不说打不打,被恶狠狠的瞪一下就够无辜的,谁乐意自己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啊。
“呼……呼……天守?”
她终于穿过重重激光似的视线,跑到后门。她急匆匆赶来,甚至忘了自己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
“苏、苏我哥哥!”天守惊喜的转过身来,看见一头乱发的苏我,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
“诶、诶?很乱吗?”苏我看了看自己的头发,发绳半梳半挂地缠在马尾上,鬓角的头发全部散下来了;好像是被她在地上摔的,头右侧方的头发有点扁……她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跑过来的时候,周围人都用看病人的眼神看她。她挠挠头,眨了眨眼睛把目光转向别处,“抱歉啊,那个,有点事在忙,所以……等久了吧?”
“没有很久啦,我刚到。恩……”天守的笑容消失了,她嗫嚅了片刻,还是开口道,“前些天苏我哥哥要告诉我的事有准备好吗”
“啊?我要告诉你?”
“是一个月前你说要告诉我的那件事啦……”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一个月前?”
苏我在一个月前采用狂背狂忘的方法,忘掉其他所有事务,把自己的脑子全部塞满英文单词才勉强通过考试。为此她连着睡了一天半来庆祝,别说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就是前天刚刚背完的单词也被她忘个一干二净。
她悄悄观察着,天守的表情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妙,如果说错了什么,友谊的小船好像就要翻了。瞎编一个答案吗?不行,万一被识破,场面就太尴尬了。不过,天守问出的问题,想必也不会太复杂,干脆坦然一点,这样也好弄清楚。
“这……我不……”
“不记得?”
“抱歉……”
“没关系的,我说说看,或许你就想起来了。还记得我在神社许的愿吗?”
“啊!那是……!”
“我当时问你,你的愿望是什么,来着。”
“恩。”
“你说,和我的一样,对吧。”
“!”苏我这才恍然大悟,“后来我说等到一个月之后再告诉你……原来是这件事。那不是一起来保佑我通过考试的吗?”
“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一小部分。”天守低下头,不愿再看苏我茫然的眼睛,她自顾自地摇摇头,想要驱散掉内心的迷茫,“我真正想说的是……是……”
“什么?”
“……还是算了吧。”她抿嘴摆出一个很难堪的笑容,“说出来的话,你我都不会开心的。”
“有话就直说啊,我又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苏我很早之前就觉得天守有哪里不对劲。在街上偶尔碰到天守的时候,她会开心的打个招呼,然后忽然转移开目光,装作不太在意的样子;来酒吧找她的时候也是,如果她不在,天守也不会向其他侍者提她的名字,只是站在那里一直等下去,等遇见了具体问她什么事,她又含含糊糊不肯说,实在让人着急。
天守还是紧闭嘴巴,拼命地摇头。
“啧……哎,你又来了,总把话说一半,很急人啊。”苏我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头,况且现在她还有急事要做,“小孩子到底有什么事要讲啊。”
“不是的……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天守立即反驳,眼睛里好像带着泪花。
“那你就把话说出来啊?”
“我……”
看,追问一句马上就退缩了。
“啊,真是,你该不会是想对我告白吧?”苏我实在很想打发她走,于是干脆说了最想说的话,“拜托——那一定是你的错觉啦,现在社会上说喜欢简直和睡觉一样容易,要么是错觉要么是玩笑,有几个是真心的啊。小孩子还是赶紧去学习,你也马上就要考试了吧?”
“才……”
“哈?”
“才不是那样啊!”
几乎在天守喊出那句话的同时,她用全身的力量朝她扑过来。
就算是苏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个少女用尽全力扑倒也免不了中招。拜天守所赐,她刚刚才痊愈的头又开始痛了。她有点烦躁的看向天守,责备的话语还没来得及出口,几颗冰凉的泪珠就落在了她的脸上。
她哭了?
“喂,你……?!”
天守按着她的肩膀,眼泪扑簌簌地落在她的肩上。看那表情,她大概已经下定决心了吧——那双银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她按着苏我的肩膀,沉默着,没有言语作为回应。
她只是俯下身去,双手按在苏我的胸膛,低下那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头、藏起那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爱,凑上去,对她本以为永远也无法触碰的人深施一礼——
她轻轻的吻了她的嘴唇,随即仓皇离开,眼泪止不住的落。
“祈,我喜欢你啊……这样的话,能相信了吗?”天守站起来,用她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苏我。现在的话,大概已经能够直视了——她注视着的那个人永远也不会看着她,她还有什么必要转移视线。
“本来我是……我不想说出来的。说出来的话,我恐怕连幻想也保留不住,连朋友也没法做了吧。祈。我已经十七岁,不是小孩子了呀……害怕也好、不安也好,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
“……”
“对不起。喜欢你什么的,是我自说自话了吧。”
天空中,雪花纷纷落下。冰凉的雪花落在脸上,显然和她温热的皮肤并不相容。白色的晶体一片接着一片,被她的体温融化成上帝的泪痕。
——啊……糟透了。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她怔怔的躺在原地,耳畔传来的,附近商店街的嘈杂早已远去了。看一看表,现在想买到上午九点之前才有可能买到的限定闪电泡芙大概已经不可能了。况且,脸还没洗、头发还没梳好、穿了几天的黑衬衫外套也要换了。
“真狼狈……”
她翻了个身,从口袋里连同手机一起掏出了先前黑崎给她的传单,再看一遍,还是觉得很好笑。
“什么啊,印的花花绿绿的,一看就是骗人的东西,白痴才会打电话过去。”
于是她将传单背面的一串数字输进手机拨号窗,按下了通话按钮,认命一般地在地上躺平,闭上眼睛。
……
“您好!这里是爱川补习社,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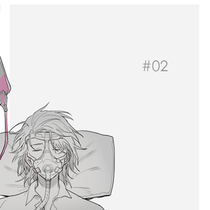





某人的日记
全文梗概:在另一个世界的八月一日爱与知见寺弥生之间,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春晚小短文,为了不破坏弥生的春晚就只响应了一下爱酱……是爱酱那篇漫画的衍生脑洞!没有商量就擅自写了,ooc就打我吧!
*
即使早已经在第一页声明过了,但我仍然要无数次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再重复:我究竟是谁?这无关紧要,仅仅是热衷于在日记本中写下那些平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再从其中淘金般寻求乐趣与幻想的普通的女高中生而已,有着属于十五六岁年龄该有的飘飘然的幻想和属于“我”这个人独特的成分。说到底无所谓希望与绝望,羁绊和未来,最终我们所期盼的、所渴望的也只不过是触手可及的生活吧?正因如此才要加倍地珍惜,把每一件在眼前一闪而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然后寻根究底,去体验和想象其他人的人生,这也是我在学业间寻觅到的乐趣。
言归正传,关于八月一日爱。
在切入正题前容我多说几句吧,是我在此之前印象中的八月一日。梳着长长的跳动着的发辫,执著地将大一号显得松松垮垮的开衫套在最外面,脸上偶尔(或是常常)带着明显的因彻夜不眠形成的暗沉色彩,在上课时会与以严厉著称的国语老师矛盾不断——因为迟到而被迫站在教室外面,还不断困倦地打着哈欠的女孩子,是这个班级时常可见的风景。尽管我们中间只隔了两个座位的距离,但那仿佛成为了所有平凡与否的分界线。于是我一厢情愿地断言道,八月一日爱是普通高中生中的不普通的高中生,就像是鸡蛋中的猕猴桃。
除此之外我与她没有更多的交集了,我相信这种淡淡的、可有可无的印象每个人都时常经历:就像是是班里关系不远不近的普通同学,目光相会时可以点头问候,毕业分别后短短一周就能够忘记对方的名字。而我们关系单方面的转变则是从那同样普通得无可挑剔的一日开始的。
*
转学生的名字叫做知见寺弥生——这是我后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的,至于为什么是后来而不是当时,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了。
“连学生都管不住,可能是老师你的的问题吧?”
当他笑着回击了班主任的那一刻我就如同其他的同班同学一样并没有感受到异样,只是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别开生面的一幕,权当做日常生活以外的插曲而已,但是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却感到了确有其事的惊讶,接踵而来的则是手足无措——八月一日在哭,眼泪默然地一滴接着一滴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但却是无声的、近乎被淹没在欢声笑语中令人察觉不到的哭泣,她和我一样显得茫然而又惊慌,诧异地不知道看向哪儿才好,那表情还带着未褪去的笑意,突兀得像是在疑惑为什么忽然间下起了雨。
我触电般地移开了视线,一种愧疚的、偷窥了别人秘密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但是当我环顾四周时却发现人们仍然在谈笑,在交头接耳,恍惚间我以为刚才的事情都是我以为太过无论而产生的幻想。
直到我发现转学生出神地看着八月一日爱的方向,不自觉地说了句什么,而那个发音也顷刻间被喧哗淹没,再也无从辨认了。
*
于是此时此刻我摊开笔记本,企图把这一切通过我的记忆再现,零碎得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那么、那么,让我就这个似乎热闹异常、却只有我完整目击的一幕恣意发挥一下想象力好了。
你相信前世吗?或是平行世界、或是梦境成为了现实?我一厢情愿地相信着,整个世界都要染上浪漫的颜色了。
在别的地方,八月一日还是北十字星的学生吗?也许她如自己所愿成为了电竞选手,也许她曾经像是只有在游戏中才能看到的那样拔枪射击,也许她曾经与知见寺弥生并肩作战。那个世界也许有我,也许又没有,但这无关紧要。
另一个八月一日爱和知见寺弥生又是什么关系?是青梅竹马吗?是恋人吗?是亲密无间的伙伴们?这我已经不得而知了。我清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越过八月一日的意识而涌出的眼泪,或许其中融化着的不是悲伤而是因为奇迹降临而产生的喜悦吧。
那么关于知见寺弥生究竟说了什么——请容我冒昧地猜一猜。
“好久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