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预言:嗡。絀利。卡拉魯帕。吽堪。梭哈。
他们说预言的源头来自于古印度。一开始,佛也只是凡界中的一人,但与已经被名字所玷污的世界不同,初始的天地中,他们都没有名姓。年轻的佛曾走过地上八万四千的湖泊,从太阳的倒影里看过所有将要发生的事。读罢,他的心被攥紧,像中了一副毒,跌坐在地,身体向内缩小,于是化作一颗种子,钻入土中。佛在黑暗中等待着,直到他感到燥热,火从星球的内部喷涌而出,将他顶出红土壤。于是他张开双臂,举至头顶时,双腿已经落在了地上,就这样变成了一株菩提。因佛已看过众生万象,不论谁来到树下,他都觉得恍若隔世,曾在镜子般的湖面上见过一生。
阿提作为村里的代表来到树下,双手合十,菩提叶摩擦的声音传到他耳中,像喃喃低语。他忽然回头,对躲在山坡后的村人说:「你们出来罢,你们将要说的话,我已都听到了。」村人走出后纷纷跪在地上,另有四人将阿提一同抬起,称他为先知,而先知不可落地,否则就将失去所有的神秘。
开悟后的阿提瞎了眼睛,只靠一对耳朵生活。他手上的指甲逐渐增厚长长,每天要花上五个小时扣出甲缝中的污泥。清除出来的污物被置于一盏金瓶中,金瓶由九只十足蜥蜴守护,为的是防止污物流入世间带来苦难。剩下的时间里,阿提总是手执转经鼓,不厌其烦地拨弄着,长年累月,他指腹中藏匿的蝉被唤醒,在皮肤上吐出一个个饱满的茧球。转经鼓中被放入了一颗虫铃,是将晚秋时最后一只蟋蟀掏空身体,嵌入铃铛所制成。每当阿提摇晃转经鼓,虫铃便在其中发出一种同时包含清脆和浑厚的复合声,听了能治百病。人们因此称阿提为多赫拉耳神(Dholaker),前来求其庇佑的人占满了村外的山谷,常堵住村人外出的小道。
山外的宫殿里,王也听说了这件事。
王本是一位无名英雄,某夜,梦中的他亦梦见一汪湖水,一如佛曾见过那样,英雄用同时代的眼睛窥见了未来。倒影中,他看到自己手执长矛,胯着骏马走进一座白垩色的城堡。英雄隐约觉察到一种命运,第二天他便离家远走,找一切能够凑齐长矛和骏马的地方。跨过山谷时,英雄在低洼的水潭边见到一群野马正在小口啜水,他悄悄靠近马儿,却仍是被发现了踪迹。马群嘶叫着四散,其中一只红棕色的马迷了方向,径直向他冲来。英雄打了个滚,堪堪避开马足,转身间,他伸出手拽住马蹄,红棕马在空中发出一声长啸,预知了自己的命运那般,顺从地落地,停在全身是泥的英雄面前。
骑着红棕马的英雄进了城,四处打听哪里有战争。但城镇很和平,打铁铺中只有农具,继承铺子的年轻师傅告诉英雄,打制武器的方子早在他父亲的时代就遗失了。英雄很是失望,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城镇,去到下一个地方。沿路,他看到山野间奔跑着绵软巨大的白兔,饥饿感很快吞噬了他,于是英雄从树上摘下了毒果。那是一种鲜红色的果子,撕开表皮后,会炸出一片剧毒的黄色泡沫,若是好好收集,放在月光下晒上三天三夜,便能去除黄沫中的毒素,留下一块析出的盐块。将盐块磨碎加入食物中一同吃下,人便充满精力,一日能翻越三座大山。英雄将果子喂给白兔,黄色泡沫很快腐蚀兔子腹部,将兔子从中截断。英雄扯下泡沫还未侵染的部分,将兔肉喂进嘴里,甜丝丝的兔肉润了他的喉,填补他胃中的空缺。风吹过田野,带着头的兔尸横卧在土中,血水混着毒渗入土中。带了毒的土壤失去营养,无法培育庄稼,需要用人的汗水才能解毒,天地间自此充斥着苦劳农人光亮亮的额头。
英雄来到一条大河前,他不会凫水,无法渡水,只好骑着红棕马在对岸慢慢行着。汤汤之河,没有一处是细窄的,英雄为此感到烦恼,他本想锯断岸边的巨树,搭成木桥,却苦于没有工具。夜渐深,他只好安顿在树下,卧着土睡着了。夜间,风雨大作,一道闪雷将英雄惊醒,他睁开眼睛时,发现面前原本通天高的巨树此时已被雷电劈做两半,摇晃间,向对岸的方向倾倒下。他看着面前的一起,在风雨中不禁挥手大叫起来,忘掉了自己已经成人,退化出猿猴的本性。这样的幸运让他感到一股自古老时代传来的神秘,狂喜之下他短暂地遗失了语言,只能用叫喊、嘶吼、抽笑和眼泪来表达自己。不等天亮,他便牵着马,踩着巨树过了河。
另一座城镇赫然出现在岸边。英雄还未进城,马上发现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城被火舌舔过,已将天空染成黑焦色,石制的墙面被打穿,心脏无防备地露了出来。他走进城内,发现这里俨然是一副地狱景象。人的碎骨和尸片遍地都是,土地全都染成了深红色,散发出浓烈的腥气。英雄继续向前走,发现沿路散落着各式武器,长剑、弯刀、弩弓、铁鞭、手戟、巨斧、飞锤粘着血,被丢弃在路边,唯独找不到他梦中的矛。
英雄知道他非找到矛不可,于是他继续向城中心走去,此时一片寂静,两侧的矮房门户大开,死去的尸体倒在家中,他们的手全都环握成圈,而本该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却不翼而飞。英雄对此视而不见,他的心中只有那柄出现在梦中的长矛。他继续向前走,一直到城中最高的那座楼前。那是城主的居所,数千把长矛从城楼的窗子、墙壁、梁顶刺出,每一把长矛上都系着一截红色布块,那是这柄长矛曾经杀过人的证明。
英雄躲过长矛们的刺刃,小心地踩着长柄向上爬去,每爬过一把长矛,他便闭上眼睛重回一次梦境,将眼前的长矛与梦中的长矛细细比对。一直到英雄爬上城楼顶,他才终于在飞檐上找到那支长矛。他十分兴奋地拔出了长矛,握在手中时,他觉察到矛身阵阵发烫,像有千百只火蚂蚁啃咬那般,刺痒从指头传染到他的心脏,很快他便感到一阵麻痹,等不及他感觉疼,英雄倒地而亡。
他的灵魂落入冥河,英雄顺势漂流到亡界。一路上,他见到众多人间死去的亡灵,他们化作一盏孤灯,或明或暗地照亮了他的前路。英雄低头看向身旁的河水,当他的眼睛接触到水面的那一刻,曾经藏在河底的白骨纷纷上浮,将冥河挤成一条尸骸路。
英雄伸出手,随意地拾起一根白骨把玩,那是根人腿骨,粗长的白色骨骼在边角沾染血肉的红,膝盖处本应光滑的股骨破碎了,流了一地白色的残渣。英雄忽而认出这只腿骨的主人来了,这是他曾经的挚友之骨,但英雄知道那位朋友的灵魂早已离去,徒留一尊老人的皮囊仍存于世,现在看来,他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将腿骨放下,又拾起旁的一根肋骨,他摩挲骨上的纹路,用手指读出这是他妻子骨头。英雄看着这本应从自身生出的骨,生出一种恐惧,仿佛脱离了他躯体的一切都不再受他控制那般,他感觉肋骨自发地生长着,在他的掌控外孵化出一具完整的胴体,一副他陌生的皮囊。那陌生的身体正是妻子的身体,她正飞速成长着,啃噬了一切能够啃噬的,最终长成了臃肿颓败的模样,看到这里的英雄颤抖着将那条肋骨丢掉了。
他在尸骸中航行,一直到英雄已经看腻周遭的白骨,他继而发现,一枚头骨立于众骨间,仿佛等待他般一路漂流到他掌下。英雄捧起那颗头颅,虽面目已不在,他仍认出那是他儿子的头骨。他捧起那端正的骷髅面,鼻骨和眼眶露出三个黑黢黢的洞,让他想起儿子早年时亮晶晶的眼睛,那时他们都很快乐。儿子的头顶有两处大裂,是从高处跌落所致,他用嘴唇吻了吻那两处裂,感觉到一阵疼痛,像被蝎子蜇了般。他害怕毒将倾入体内,于是忙把那颗头颅放了下来。
他继续行进,一直滑入最深的幽冥,英雄在终点见到了自己的命运。命运里仍矗立着那栋白垩城堡,英雄于是领悟不论生死他终将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不识水性的他从河中站起,来到属于他的王城前。城堡中静悄悄的,唯有在那城堡前,那柄送他至此的长矛挂着红缨正随着风轻轻飘动。
英雄重新拔出那柄矛,再睁开眼睛时,他已回到了地上。而寄宿在长矛中的战争之果在这一拔中松动,战火因此在地面绵延,人们聚集在一起,却仍旧是无法抵抗。最终时刻英雄站在了人民面前,他的长矛突出,锋芒向外,捅破了果核的外壳,将战争钉死在土地上。
人们于是围绕着这柄长矛建立起了宫殿和城市,英雄也靠着这柄矛成为了王,在他的王国里,不再有纷争,人们只有富足的生活可过。在这个国度中,王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视梦的作用,因他觉得这座城市正是诞生于他年轻时的一个梦境。自然而然,释梦者被重用,王每天醒来,第一眼见到的不是侍女的面容而是释梦师的脸。王国里组建起了三百人的释梦会,每天经手分析王的梦境。当王度过了一个无梦的夜晚,他们便在王宫外点起明黄色的火焰,向全境的人宣告王的安眠。
因此,当王听闻阿提的故事后,他便决定前去拜访这位先知。
王于正午时分到达了村落,此刻正是一切因缘汇集的时候,人间所有可寻的关系都被缝于村口的一根粗壮的柱子上,它的周长足有十个成年男人手牵手围起来那般长。王抚摸那根神木,对村中人说,若是阿提能够解开他所带来的难题,那么这根巨木就可保留,阿提也可以继续做他们的神。若是阿提失败,那么这棵木头就要被世间最锋利的锯子打磨,成为他们村落今后会客所用的木餐桌。
阿提出来迎接王,王于是派人呈上五把金锁。他对阿提说:
「我听说你是已经开悟的圣人,那么现在请你打开这五把金锁,它们分别锁住了世间的康健、欢乐、学识、吉运和忠贞,才搅得世间如此疾苦。若你能将它们一一还给世人,想必能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阿提接过那五把锁,他将瞎眼对准孔洞,听到洞眼中,无数只金蟾驮着金珠正绕着锁心爬动,他不忍伤害这些小生灵,于是将锁放下,对王说:
「我无法打开这五把金锁,或许打开它之后,孔眼中能放出你所提到的那些美的品质,但这样一来,锁孔中的金蟾就会尽数死去。哪怕为了众人的快乐,我也不能做这件事。」
王听完了这段话,觉得面前被村民高高抬起的阿提不过是乡野中的一个骗子,他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人能够悟道成神,因此他虽表面微笑,却打心底瞧不起这位不肯接纳残忍的年轻人。
王于是说:「你很仁慈,我可以应允你不伤害神木,但你们必须每年都送来与那棵巨木等量的木料,我才能让你们继续在王国中存在。」
村民和阿提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当即有人跪倒在地,伸出手指扣出自己的心脏丢在地上,想以死逃避这一切。阿提阻止了更多人的效仿,他从身后拿出那封存着他的甲垢的金瓶,将它当作应允的信物赠予了王。
阿提告诫王:「金瓶傍身能够让你永葆青春,长生不老,但千万不要打开瓶口,这样一来,一切就无以挽回了。」
王于是颇为高兴,命人在衣袖中缝制了一个特殊的口袋,用于存放金瓶。每当他抚摸瓶身,都觉得时间正被自己打败,一种征服的快感掠过他的心头。
王离开村落后,阿提唤来了剩余的村人,要他们收拾行囊离开家乡。众人明白自己无法实现王的要求,只得背起包袱,走向山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走向了相同的方向,他们将用双腿丈量整个世界,将阿提教给他们的佛法传遍每一个角落。
众人离开后,阿提一个人坐在他的椅子上,拨弄着手中的转经鼓,他就这样祈福了整整一年,直到王再次降临村落,向他讨要木料。
阿提说:「我失信于你,因此必将走上覆灭之路。而你心无善念,你的儿子将死于战场,你的妻子将溺于宦海,而你故去的老友将成为唯一得道的人,受万人敬仰。」
王不信阿提的预言,命人将他捉住,随后鄙夷地表示,他所讲的不过是一些陈年往事,他已在冥河中见过他们三位,这点话语无法伤他分毫。
而阿提只是摇摇头,说:「你怎知那是前世之事、现世之事还是来世之事?王啊,你正站在神最不起眼的一匹战马的车轮上,你无法逃开这样的命运,只因我知晓了,原来你就是那个毁灭佛法的人。」
王因此暴怒,命人取来他的长矛,一枪捅穿了阿提的喉咙。青色的血液自阿提的喉管中渗出,在声带完全停止震颤前,他说出了最后一个预言:
王啊,你已堕落,因此我将赐予你一个诅咒,你永生无法脱离它的束缚。从此往后,人们再次提起王,就不再单指向于你,你注定要与旁人分享你的荣光。
于是,王从那一刻起拥有了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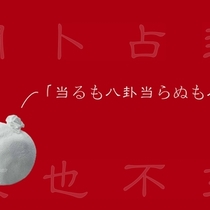






日記空了好幾天,我沒有寫些什麼。我剛從外邊回來,身上還是一層薄雨。降溫了,霍格沃茨真冷。貓咪窩著的地方溫度意外地高,除此之外整個被窩都是冷的,還帶著潮氣,這大概就是住在湖底的壞處。哎,霍格沃茨真的好冷。
愛蜜莉,近來我想了很多⋯⋯關於我,關於愛情,關於你⋯⋯
愛情於我而言也是一種宏大敘事,因此不能有任何差錯,必須純粹,極端的純粹——然後倒映在現實,就變成了極端的自利。但難道不是嗎?愛情也是一場權利鬥爭,在其他地方我輸得夠多了,所以這一次我絕不想輸。只有攥得夠緊夠痛才是我要的愛情,宏大的開場與悲劇的落幕⋯⋯啊,我好像從來不期待圓滿的愛情,我想要的是偉大的愛情,而偉大的愛情的別名也是失敗、痛苦、破碎的愛情。丟了的東西才最珍貴,通過愛你,我可以更好地愛我自己。我渴望的終極,那種包容一切的愛,最終指向的人並不是你,愛蜜莉,我愛你,但我更愛我自己。終有一天,我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更愛我自己。
我要徹底地放縱,徹底地拋棄過去,我要成為我自己,不論是理想中、幻想中、他人口中、書本中或是任何一個夢中的我自己。我要更愛更愛更愛我自己,因為除此之外我收穫不到更多了。就算我再訴說自己的可憐和無助,我也無法得到更多,我終究還是只能和我相伴。
孤獨時我會想起你,我會假裝你還在我身邊,對我喃喃細語,擁抱我,和我說你愛我。但愛蜜莉,你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幻影,當我的想象停滯,當我的大腦被堵塞,當我被困於混亂,你就會消失。你無法真的永遠陪伴我。
夜裡無法停止哭泣的時候,我會拿起刀,儀式化地安慰自己很快就可以解脫。與兒時喜愛撕開傷口的癖好相對,我開始依賴從創造傷痕中獲得安慰。物理上的受難可以搪塞很多無解難題,包括我無緣由的哭泣。我在向我自己證明,哪怕我無力也尚且保存了摧毀自己的力量。
我們可以最後接一個吻嗎?滿足我的願望吧,愛蜜莉,我想要得到最後的確認,你愛過我的證明⋯⋯或許明天,我就能在枕上發現你的髮絲。
晚上的時候,我去過格蘭芬多塔樓,雨打在窗玻璃上,伴著暖爐的火光,讓人感到治癒。我很難和G談愛情的話題,因為我太了解她了,我所追尋的東西在她眼裡都是奢侈的煩惱,在愛中尋找「家」的人和在愛中獲得實現的「勇氣」的人⋯⋯算了。她能做的最多就是坐在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讓一切都過去吧。
乾脆給我一瓶遺忘藥水吧。我忍不住說。
真的嗎?
真的,當然是真的。我不僅要忘掉我失敗而偉大的愛情,我還要忘記我的過去,忘記魔法,忘記霍格沃茨,忘記伊法魔尼,忘記保密法,忘記我到底是誰,然後站在時代廣場上向每一個過路人大喊Tarantallegra。
但一刻鐘後我又回到湖底地牢裡。
壞貓咪吞了太多毛球,也可能是吃飯吃得太過著急,大團大團的嘔吐物留在地毯上。我拿出魔杖用清潔咒把這堆東西都收拾乾淨。愛蜜莉已經離開了,或許她之後還會出現,但我很確定,她今夜不會再來了。
我抱著貓咪倒在床上,潮溼感很快將我包圍。那一刻我意識到,愛蜜莉離開了我的生活,而這隻呼嚕呼嚕的暖和貓咪才是我可以觸碰到的現實。
好想有人能帶我逃離現實。但如果沒有的話,我就要自己帶著小貓咪逃離現實,進入永遠的幻想空間,在那裡,我可以是一隻沒有大腦的宇宙水母,逝世前還可以隨機蜇死一個手賤的人類。但總之,晚安⋯⋯晚安,霍格沃茨⋯⋯晚安,小貓咪⋯⋯晚安,不會再見的愛蜜莉⋯⋯晚安,妙妙,晚安,妙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