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1:http://elfartworld.com/works/74337/
前文2:http://elfartworld.com/works/74733/
借用映柳轩!http://elfartworld.com/works/72778/
有人在下,我欲辅之。
魂魄离散,汝筮予之。
- - -
“啧啧啧啧……疼得慌吧?都这样了,还不说,倒是真的硬气。也不枉我同你相识一场,把你当个朋友。”
临安府,西湖岸,栖霞山。游人只道这栖霞山每入深秋,红枫满山,美不胜收,却都不知在这山底地下,也是别有洞天。
也不知是何人在何时,于这地下修了那么处地方。顺着一条狭窄的石阶,越往下走地方就越是宽敞,通道四周都是整块的花岗岩,切割整齐,显然是人工开凿后精修而成,再往深处进,可见多处岔道,而这些岔道则都分别通往不同石室。
本该是个阴冷幽暗的地方,却有一间石室里隐隐透出火光。
只见一男子背靠着一堵石墙瘫坐在地上,四肢关节均被卸下,一条拇指粗的铁链一端深深嵌在墙里,另一端则是一个带钩的铁环,牢牢扣住了他的琵琶骨。这男子蓬头垢面,满身血污,看不太清他的长相,只能依稀分辨他大约三十出头。油灯里微微摇曳的火苗实在太小,无法给那人失血过多的苍白脸庞带去多少暖意。男子身上的衣物早已变得残破不堪,有几处都已成了烂布条,跟血肉模糊的伤口粘连在一起。
更可怕的是这人的一只手臂,从上臂中间开始便不见血肉,森森白骨直至指尖!
他被关在这里已经是第三天了,这三天里他滴水未沾,嘴唇早已干裂出几道深深的血口,喉咙也干得好似火烧。他虽不能行动,却不是没有知觉。他不吭声也不是他有多能忍,只是这过度的疼痛早已让他连出汗的力气都没了而已。
“这半个多月你可让我好找啊…商兄?你害我的「人」丢了条手臂,我找你要一条回来,也不过分吧?”关才把那不足三寸的薄铁片拿在手里不住把玩着,轻声说道,“…本来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既答应了你,事情要没办好该我跟你赔不是才对。可你呀,偏偏是有意隐瞒情报,犯的正是大忌。”他眉眼含笑,语调也是温吞软糯。右手却是突然忽地一闪,那手里的铁片上就多了一条肉片!眼前的男子片刻后才闷哼一声音,身躯一阵颤动,才发现本就惨不忍睹的上臂上又缺了一块。
他的动作快得仿佛根本没有出手,他的表情也淡然得仿佛根本没有出手。
“…不过我这人脾气好得很。这本来啊,也可以不是什么大事的。”他抬起眼,望着那男子,“只可惜你运气不好,就偏偏是「那家」的人,又偏偏找上我。”
七月十七,临安城内。
已过卯时,在一会儿就该到雄鸡司晨的时辰了,关才却一直睡不着。从那具骨偶里取出的暗器被整齐地摆在桌上,他已经盯着它们看了很久了。
错不了。
几天前他正在映柳轩打发时日,跟陈掌柜聊着今年中秋赏月宴的事。
他关才在临安是开棺材铺的。虽说这算不上什么特别体面的行当,但也绝不落魄。生老病死人人都有,临安有钱人又多,生意就定然不会少,有需求的人自然会找上门来。要是运气好接个大生意,干一票能顶大半年。他在这临安待了十多年了,口碑积攒的多,手艺又好,也没什么竞争对手,就连临安外都有人特地慕名而来找他订棺材。只是他脾气古怪,上门的生意也不是样样都接,高兴起来了给街坊邻居修个桌椅搭个床分文不收,不高兴了就算是白银百两摆在他面前,他也是连白皮棺材都不卖的。这样一来他一年到头做事的时候其实并不太不多,自由得很,就干脆经常把铺子丢给店里打杂的管着,自个儿成天混迹在各家酒馆茶楼。
这映柳轩的饮食称口称心,价格可都不便宜。因此来的也大多都是体面人,下午的时候人尤其少。他想求热闹的时候会去些更为市井的地方,想图个清静就会到这映柳轩来,要些小酒小菜闲坐一个下午。
那陈掌柜在他头一次来映柳轩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之前也说这映柳轩收费不低,但关才也是出手阔绰,每次来都放上好些银子,很多时候明明只有他一人,也能跟设宴似的点上满满一桌。几遭下来店里的人可就都认得他,也渐渐熟络了起来。但他自己对这些定价知道的其实并不太仔细,从没细问过,大约只晓得个「不便宜」。关才把那些银子交给店家,便让他们算着扣,他也不知道每次花了多少、剩了多少,只是隔三差五再来时又添上一些。陈掌柜也从没找他补过钱,想必是还有多吧。
这样的客人到哪儿都不会被店家讨厌的。
“这告示还得过一段时日才会张贴出来,关二爷若是需要,我也能给您提前安排个雅间。”
“不用不用,我孑然一身,要雅间来做什么?那日子热闹,定是会有其他人要的,陈掌柜弗要担心的。”关才笑吟吟地说道,“陈掌柜忙去吧,不用特地招呼我。”
陈掌柜自是知趣得很,当下便也回报一笑转身走开,还不忘补一句“若有何需要,关二爷尽管招呼”。
关才听了点点头,捏起杯子抿了口酒,又忍不住轻笑起来。
「关二爷」是他自己给起的名号,至于原因可就说来话长了。
临安这棺材铺也不是他开的,是带他来临安的人开的。那人是个老头,大概五十来岁,姓刘,叫什么名字连关才都不知道。只听说这刘老头以前在家里排行老大,所以大伙儿也就都喊他刘大。他做棺材的手艺也都是刘大教给他的。关才本就聪明手巧,刘大教他些门道,他自个儿琢磨琢磨不用多久就研究了个透,青出于蓝还胜与蓝,棺材铺的名气也是在有了关才以后才响起来的。刘大膝下全无子女,也没见他提过其他亲戚家人,为人又沉默寡言,极少与人来往,关才倒是能言善辩还不怕生,帮着刘大打理着这铺子,生意也就越来越好。这时间久了,他就照着别人喊刘大的样子,给自己起了「关二」这外号,外人笑敬他一声爷他也不推辞。做这行难免得常跟些秽气打交道,这关二爷就是关公,本就有个镇宅辟邪招财的说法,用在他身上也是吉利得很。只可惜他这关二爷当上还没几年,刘大就撒手人寰了,现在铺子里只剩他跟一个年轻伙计。
这一眨眼,就十几年了…他是做棺材的,自然也认识不少其他做白事生意的人,间接也好直接也罢,由他送走的人也是不少。刘大是他送走的不说,街坊之间他送过的更多,就连这映柳轩的老太爷当年也是他送走的。
就不知道自己走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来送。
“关二爷?那么巧,您今天在这儿歇着呐?”
关才正想着些有的没的,听到声音就转头看去。
“哦哟,商兄啊!可是好久不见了,来来,坐坐坐。”
这来人姓商名恺,跟关才认识也有四五年了,似乎是个做生意的,但也不过给人打打下手跑跑腿。具体做的什么生意关才没问过,也并不感兴趣。一见来人是商恺,关才也是立刻就眉开眼笑,称兄道弟,显然是有几分交情。
他同人交朋友,一向只看聊不聊得来,并不太讲究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哎哎,好好,……唉。”商恺应声点头,但才一坐下就是一声长叹,“这阵子,生意难做啊,上面也是三天两头找我麻烦。”
“难怪那么久不见你人。”厅里跑堂的很快又送来一副碗筷酒杯,关才忙不迭地结果,亲手给商恺把酒给满了上。
“我也甚是怀念以前的清闲日子啊,…唉…”
“安权不可两得,钱闲不能皆取。商兄这几年忙活得也挺够了吧,何不学我这般轻松点过活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唉…”
他一连三声长叹,听得关才不由眯起了眼。
“商兄可是有什么难处?不妨说来听听,关某要有能效劳的地方,搭把手不算什么。”
商恺听了,沉默片刻,又倒了杯酒仰头一饮而尽。
“不瞒二爷,我确实是有事求您!最近遇到个难缠的大疙瘩,给咱们惹了不少事,我就想求您帮帮忙,能不能找人帮我给他…”
“诶~何必多礼?”关才开口打断,又瞥了瞥四周。那商恺立刻明白过来,点了点头低下头去。关才不紧不慢地又给他满了杯酒,“这事好说。就是这点子…扎手不?”
“不扎手不扎手!唉!这也就我们这些生意人觉着麻烦,您那些行家哪儿会…二爷啊,我也不是第一次求您办事了,什么时候给您惹过麻烦?”
他这话倒是不假。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江湖上总有亡命徒会靠一些不太好见光的方式过活。关才不缺钱,他只是闲得慌。除了这棺材铺外,他手底下还做着些其他生意,除了那些跟白事有关的外,传闻他手底下有不少拿人钱收人命的「小鬼」,只是知道这事的人并不太多,商恺也是与他相熟以后才无意得知的,以往也求过他几次,确实没出过岔子。
“二爷、您可千万得帮帮我,这事要是成了,我一定……”
“这么见外,我什么时候跟商兄讨过报酬?”关才又笑着打断他道,“朋友一场,这点小事算什么?商兄只要将这分寸好好交待给我就行。这多大的庙,请多大的佛,可万万出不得错。”
关才手底下从来就没有「小鬼」,命都是他亲自去收的。
商恺请他处理的人他并不认识。七月十六日晚,他顺着商恺给他的消息一路远远地跟着那个人,就等适当的时机好出手。
但突然地、来了这云栖坞,见了这龙井茶园,脑子里好像闪过些什么东西。
「那个人」看起来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江湖小辈,他自认为没有亲自出手的必要。而自己这具骨偶尽管不是最得意的那具,对付一个默默无闻的毛头小子,想来也是绰绰有余了。
这二十多年来他并未真的过过多少清闲日子,武学修为也好,机巧毒药也罢,他什么都没放下。只是如今的条件不如当年,许多事做起来并不便利,比如制毒配药,要鼓捣出些名堂来,可少不了些稀罕药材,他却没那么多时间去寻,也就只好搁置了。但这机巧可不一样,本是他的拿手绝技,又恰好各种机缘巧合撞在一起,还真让他造出这些「骨偶」来。这骨偶是他的得意之作,每一具都以真人骨为基础,经过层层强化后再用独门秘法连接组装,竟真可做到与活人行动几乎无异。不过光是这样,也不过是一具精巧的傀儡,并无特别。
傀儡终究是傀儡,而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傀儡;傀儡也不会害人,会害人的从来都只有人。
可怕的正是操控傀儡的人。
操控傀儡的人越强,傀儡就越强。傀儡能做到多少动作、会多少「武功」,都是由操控的人决定的人。
而关才恰好懂得很多。
但懂得多也还不够。
他这傀儡不仅能操控得好,而且就算人离得远远的,也依然能操控的好。
没人知道这当中的奥妙是什么。
关才静静地看着「那个人」,他有信心在一招之内就结束这件事。这傀儡虽没有活人那般的内力,但力道、速度上却也不输大多江湖中人,加上本就不是活物,所以不惧生死、不畏刀枪,出手便全由他说了算,不会有半分犹豫!这些年来江湖上死在他这骨偶手里的人不下二十,其中也不乏几个小有名气的。由他操控的骨偶百丈外即可取人性命,并且转瞬间便可来去无踪,而谁又能想的到这是傀儡所为?当真是「千里不留痕」!
那些死在骨偶手里的人往往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一命呜呼了;而江湖上活着的人更是没有听过这门功夫,怕是连想都不敢想!这正是他的绝技,也是让他活着的动力之一。
只是这次他并不想那么轻易的杀了「那个人」。
所以他刻意地让对方发现骨偶的存在,交锋之际也是处处留手。只因为他想看看清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所猜想的那样。
他确实没猜错。
终于他将桌上的那些暗器都小心地收到一个木匣里,又仔细地将那木匣放好,动作之间满是珍惜。
只是…
他转身看向那具站在一边的骨偶,它一侧的斗篷下空荡荡的,原本该在那儿的右臂已然被人卸下,骨骼断口暴露在外,看得他好一阵心疼。
虽然留了手,但能做到这一步,这小子也是不错了。他这样想着,又觉得心里头竟然有些欣慰和暗喜,不禁苦笑起来。
但既然他没猜错,就说明商恺给他的「分寸」错得可就厉害了。他愧疚地看着那具骨偶,在那断骨处不住细细抚摸。
这笔帐还是得讨回来。
“商兄啊…你要是早早同我讲了,这点子究竟是谁要你除的?我也就灌你一碗「孟婆汤」,你我就都当没发生过这事,也就算了。”关才一手掰过商恺的脸,柔声道,“只是你偏偏那么忠义,我就不得不跟你讨这债了。你看看你这胳膊啊,要不是有这「阎王愁」吊着你的命,你能活到现在?几天了,我也累了,这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肯说,虽然这胳膊是没救了,可命还能留下。”
商恺的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发出几声闷响。关才凑过脸去。
“嗯?你说什么?”
“…说…了…也、…也是……死……”
勉强分辨出这几个模糊不清的字,关才脸色一沉,原本的笑容瞬间从脸上退下,眼神也变得刺骨般冰冷。他摇摇头,从腰侧掏出一个小瓶。
“遗憾,遗憾…”他轻声叹着气,眼里的寒意却又不见了,好像根本没出现过一样,剩下的只是浅浅的哀伤,“这「观音泪」我向来是不屑用的,只因为它太没意思了…让你死得凄惨痛苦的办法我也有的是,但念在几年交情,我也确实把你当过朋友,……唉,我就做一次这没意思的事吧…”说罢,他打开那小瓶,捏住商恺下巴就给倒了进去,“不疼的。”他站起身来笑笑,把那小瓶重新收好,又抽出一块帕子将那片薄刃细细擦过包上。
商恺还来不及把那「观音泪」咽下,突然身子一紧,便软软垂下了头。他的眼帘也在这时缓缓阖上,平静得仿佛睡着一般。
“「点滴观音泪,可解万般苦」…想不到我还会再用这东西。”关才自嘲似的笑笑,最后看了一眼那商恺的尸体,便转身对一直站在一侧的一人说道,“他的骨头不行,用不了。一会儿干脆都化了吧,记得收拾干净,石头。接下来啊,可有的忙了……”
-END
========
牙膏终于挤完了(擦汗)总算上线了我也是O-<-<
太久不装逼了大概装得不太好……………阅读上有困难的话欢迎提出||以及这个挂也是开的没谁了,算了就这样吧(。
大概解释一下:
*开头来源为《楚辞·招魂》by屈原,死人出墓的意味(。
*栖霞山位置参考企划公告·Q&A;第一答最后的临安地图,我搞不太懂地理,如果有问题就当是原创吧总之在城、城外(擦汗)地下室是他的暗室,不好找,也不好进,不要好奇,我也懒得多想(。)
*关才看出来了唐珏的来路,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但他不对唐门的人出手。相对的,对唐门有威胁的人他要是方便,也会顺手解决掉。
*「阎王愁」和「孟婆汤」都不是毒,而是药,来源于岭南老字号温家,百家不准备写了但将来还会用到!所以这里提一下!
*石头是谁?下次再说吧…
差不多就这样吧!以上,阅读感谢TUT!
五儿叫嚷着滚进账房时,柳云岸正在算账。饶是他功力精深,听到那吼声也是忍不住一皱眉,这下笔下那一撇虽也是可圈可点,却比其他字差远了。他叹了一声,放下笔,带点可惜地拂了拂桌上账本,心中暗自庆幸。这幸亏是自己,要是换了别人,听了五儿这声狮子吼,怕是要毁了这页,又得重新算过。
柳云岸抬起头,一双深潭似的眼睛投向五儿。柳条一样的少年连滚带爬跑到他桌边,扯了扯他的袖子,道:“先生,先生!”
“这又是怎么了?”柳云岸道,伸手擦了擦对方脸颊上的脏污,皱起了眉。“我是怎么说你的?”
那五儿如梦初醒,笑嘻嘻地站好,但是手还是扯着他的衣袖——这小混账幼失怙恃,从小让镖局养大,对他早就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只当柳云岸是个会讲好玩故事的父辈,十分粘人。
“咱们镖局换了送肉的——“五儿眨眨眼,略去柳云岸的责问,说:“你让我镖局有什么异动就马上来跟你说。”
说罢,他又眨了眨眼,脸上闪着骄傲又得意的光芒,像是办成了什么的大事。柳云岸好气又好笑,只得说:“换了就换了,用得着你这样吼着进来吗?想来是罚得不够,说吧,想要扎马步还是顶水桶?”
五儿听了马上就扁了嘴角,再说话时声音就已经带上了委屈,道:“可这个人不是本地人。”
柳云岸当下一抬眉,接到:“你又知道了?”
五儿还没回答,在这一息间柳云岸的心思已是转了百转千回。他本就心眼多,多年前横行江湖,除了一身武功确是难有人敌以外,靠的也是他这玲珑七窍,事事多虑的心思。此时镖局正在丢了镖不久的当口,少东家又遭逢巨变,不同以往,在节骨眼上忽而来了个外地人,自是怪不得他多想了几分。
正在他沉吟之时,只见五儿也是点了点头,继续说:“之前二虎哥带我出去玩——办事,到最后我们去了前街的德庆楼,要给赵叔打四两桂花酿回来,但是我们给挡住了。”
他伸直了手,直指天空比划几下,继续道:“门前有好大的一尊佛站在那儿,把门口都挡得死死的。二虎哥那时候就说了!”他又停了下来,模仿义兄处于变声期难听的鸭子声,说:“乖乖,从来没见过那么高大的人,怕是比总镖头和那些红衣官爷都要高!”
“然后呢,然后呢,”五儿皱了皱鼻子,说:“我们就让他听见了,那大佛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就走了——那脸,说是佛还不如说他是金刚,铁青铁青的,横眉怒目,把我们吓了一跳。”
“但是他没说话,也没有动手,只是回到门前单手把另外半扇猪甩到背上,回头就跟着德庆楼的伙计奔后堂去了,那力气,说不定来咱们镖局也是特别少见。”他本想说在镖局里也是数一数二,但是承认几个刀头舔血的镖师不如一个杀猪匠实在让他心有不甘,只好不情不愿地换了特别少见。
说着,五儿侧头看了柳云岸一眼,看见他脸上虽未有不耐之色,但是左手已经伸向桌上捧起茶杯,还用一双幽黑凤眼斜睇着过来。五儿马上知道自己旁枝末节说得太多,吐了吐舌,继续说:“后来听酒肆的人说他是最近才到附近住的,带着爹和一个儿子,没有当娘的。顶了原本三秃的场子和店,继续干杀猪卖猪的勾当。我们本来也没放在心上,可你看,没两天,他就连镖局的单子就也接过去做了。”
柳云岸听完他长篇大论的一通,没有说话,只是把纤长有力的手指搭在下巴上,摩挲了一阵,似是在推算什么。过了一阵,柳云岸才开口,道:“今天来了?”
“嗳,二虎婶让他帮忙把肉斩开,现下怕是还在厨房忙活。”五儿点了点头,道。
柳云岸站了起身,一振衣袖,说:“好,待我去看看这金刚怒目。”
说罢,他拿起折扇,往手心一敲,抬脚走到门外去。
XXX
上元镖行着实不大,厨房就在两进院子的中间,离房间不愿,走不了几步就到了。柳云岸背着手,信步走到厨房门前,探头查看。只见屋子里被清出半片空地,中心半跪着个灰衣男人。即使是这样屈折着也能看出身材高大,猿臂蜂腰,站起来的确能当上五儿所讲“金刚似的”描述。
那男子背对着柳云岸,手中举着把寻常的猪肉刀,哈出一口气,举起的右手就像是顺着刀本身的重量落下,在半道轻轻侧了侧,切豆腐似的把刀片滑进猪肉的肌理间,轻松起出一片猪肉,露出底下森森的白骨。柳云岸袖手站在门边,对二虎他掌管厨房的娘亲摆了摆手,示意她不用打招呼,就饶有兴致地看着屠夫继续工作,把一整扇猪处理成不同的肉块。
他半瞇起眼睛,只觉对方舞蹈似的动作似曾相识,能看出扎实功底,但是举手略有滞涩,应是受伤未愈,以至于出手时动作走样了五分,与当年那天下第一人的独门武艺又不尽相同了。
就在他思考的当下,屠夫已经把猪处理完毕,站了起来,用身上围裙擦了擦手,道:“大娘子,要把这肉搬到哪儿去不?”
这倒是北国口音,柳云岸心下暗忖,开口接道:“不用了,回头让五儿几个来搬就好。不用辛苦——?”
屠夫闻言转过身来,对柳云岸欠身行了个礼:“管事先生,鄙姓林。”
说罢一抬脸,两道冷电似的目光霍地在柳云岸脸上转了两转,又迅速敛了回去。柳云岸心下一动,这姓林的屠夫约莫三十上下年纪,顾盼之间颇有军人气度,只是脸色浮白,略有病态,平添了几分风霜之意。
柳云岸看着对方,心下不由得好笑。这冒牌屠夫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懵,完全没有掩饰的心思,先不说屠夫何如有武艺在身,就算当朝重文轻武,天下百姓不少念过几年书以求得一官半职,寻常杀猪匠又怎么会张口就是“鄙姓”抬手就是标准拱手礼?他心思一转,嘴边就噙着微笑,还了一礼。孤身一人,身上带伤,即使有异,不难擒下。只是听五儿说这林屠似是还带着父母亲人,不知牵连多少,现下不得不先放虎归山,探清虚实再做决定。柳云岸暗自思量,开口对对方说:“林屠,鄙人柳云岸,是此间门客,以后上元还请林屠多多关照了。”
那屠夫有几分意外。时值中秋前后,正是多事之秋,这几日他用林水成的名字顶替了老相识的养猪场,到处送货少不免总被管事的讯问几句,最少也会被关心老三秃哪去了,像这看着文弱温柔的书生却是半分没问。他皱起了眉,正好对上对方幽幽黑水似的眼睛,不禁一凛,心道:“这人功力好深,怪不得这般托大。”
现在林水成最见不得的除了官府就是江湖人。尤其是武功高强者见多识广,虽说“林水成”就是个寻常百姓,他本人也早早离开江湖投身军旅,但是一身武艺却是脱不了恩师痕迹。当年的武林盟主徐一杭弟子不多,除了独生子不过三数人,若有心如明镜者,他的身份不消一阵就能曝光个干净。到时逃兵斩立决倒不是大事,就怕害那老医师和他孙儿一个窝藏逃兵的罪名。林水成心中骂了让他接下上元镖局生意的老朋友一通,当下不再纠缠,只是按惯例对柳云岸谢了谢,把自家的猪肉夸赞几句就告辞。对方也没有阻拦,只是含笑道别,把林水成送到门边。
二人相对无言走到后门,林水成听着对方脚步沉稳,几乎有如猫爪着地,不动声色,心下又是提防了几分。
等到他们走到门边,林水成脸上虽是神色如常,腹中愁肠怕是已经打了十个结。反观柳云岸却是胸有成竹,笑得如春花拂脸,他站在门边朝林水成一拱手,轻声问道:“不知道林屠下次送货又是何时?我上元镖局人口颇多,加上大部分又是青壮男儿,肉食消得比较快,须得时时补充。”
说罢,又补了一句:“今日二十,不如就逢十卯时吧,有劳了。”
林水成眉头一皱,心道这管事的好生强硬,定好日子一方面掌握行踪,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排查出若是林水成别有所图是为了什么。他本想就此拂袖拒绝,可林水成又实在舍不得那酬劳,见对方似是无意揭穿,便咬咬牙答应下来,又朝对方行了一礼,这才脱身离开。
等到林水成走到巷口,冷风一吹,他才惊觉自己竟是屏住了呼吸好一阵。他摇摇头,回头看见已经不见柳云岸人影,才长叹一声,放松了下来。
他捏捏眉心,心中雪亮,自知方才是半分也没有瞒过那镖局的管事先生。原本以为只有几个寻常武夫的镖局,却大隐隐于市的藏了个高人,林水成苦笑一声,摇了摇头,离开了巷口。
XXX
在上元镖局这么一耽搁,日头就已经攀上了中天。林水成走在路上,心里过了一道早上的事,深觉行事须更为谨慎。他一边在心里盘算,若是东窗事发,牵连到林氏祖孙前必须离开临安;一边脚下不停,往前街德庆楼走去,只觉肩头重担如山重。他思虑既深,自然没有注意身边的人物,忽地就感觉下臂被撞了一下。撞上来的女子惊呼一声,退开了几步。她身边一个侍婢模样的少女吓得脸色一白,慌忙伸过手扶了扶,看起来竟是比被撞上的人更为惊惶。
林水成低声致歉,垂眼一看,登时眼前一亮。只见那女子约莫十六七岁年纪,鬓边斜斜插一支金钗,镶着颗指头大的珠子。明珠生晕,衬得她更是明艳若火,眉宇间的英气与寻常江南女子大为不同。少女此时也抬眼看向林水成,琥珀一般的眼珠子目光流转,在他的脸上溜过一圈,竟是没有移开视线,就那般直勾勾地盯着,芙蓉脸上漾开笑意,款款道了个福道:“小女子失礼了。”
此时,少女身旁一个三十上下的男人粗声开口道:“看路,姑娘若是有个好歹可不是你能担得起的。”
没等林水成回答,就见那少女轻蹙起眉,似是十分厌烦,她又对林水成点点头,道:“够了。继续走吧。”
她显然御下甚严,那大汉听到指示后,很快点了点头,快步走了上前,指引方向。主仆虽然只有三人,却走得颇快,不一会就已经混入人群中。看起来和其他人别无二致——
就是有哪儿感觉略有违和。林水成皱了皱眉,说不清所然来。他不经意间转头看向大街,但见街上行人熙来攘往,这繁华升平却是征战十年从未认真看过,也从不敢认真想过的景象。他来临安已有一月有余,浑浑噩噩的却是从未发现,这都城竟是这般繁华,与印象中的凄风惨雨,萧条肃杀断然不同。路边的小摊物资丰盈,瓜果盈车,正是周边道路畅通,交易往来无碍的代表。
林水成一时觉得恍如隔世,想起当日浴血沙场,又想起大半年前的风波亭外,当下百味陈杂,嘴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忍不住摸了摸左手鲜红如血凝成的珊瑚佛珠,摇摇头,不再深想。他还得帮林家老父捎上几壶特制的桂花酒,金秋时节,桂花开得盛,正好是前年酿下的桂花酿好开坛的日子。前几天德庆楼就已经在门前贴出告示,说是这一年的桂花酿过两日就开售,他可得早点去买回来,以免错过。
耳闻德庆楼桂花酿盛名的显然不止林家,方才的少女主仆三人早已到达,站在门前。林水成内功不错,虽然伤重未愈,依然耳力极聪。只听那侍卫道:“我爹本不是临安人士,好几年前为了一位病人才来了临安。” 那侍卫脸上又堆上了几分笑容,继续说:“结果到后来所有来找桑青先生寻医问药的,千方百计也会弄来一坛德庆楼的桂花酿,禁止不绝。”
林水成本来已经走远,听见桑青先生四字,他猛然一扭头,看向那侍卫。
那少女捉狭一笑,道:“你们江南的酒,淡然无味,也就比水好上几分。”
“我林水成敢向小郡主打包票,您不会失望的。”侍卫说。
现在约是未时,这城里城外仍是热闹得很,阿朗抱着那婴孩东张西望,脸上写满了好奇和兴奋。他父亲雷焱本是雷门二公子,而这雷门在江湖上的大名正是江南霹雳堂,总部就设在临安。
对他来说这可确确实实是到了老家。
只是这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涉足中原,一路上虽然也有好几个月了,所经之处却无一能和这临安城相比,难免兴致盎然。
但就他这副奇奇怪怪的样子,路人也难免对其侧目。要刚好遇到目光对上了的,也都对别人友好的笑笑,偶尔有几个人露出嫌弃的表情他也并不在意。
“别看了,要玩以后再玩。先找地方住,再过会儿又得给她找吃的了。”徐飞白说完话不见阿朗回应,便转过身去看,才发现自己已比对方走出了好几丈远。此刻阿朗被两名官差模样的人围着,正低声地说着什么,他听不太清,但心里着急,也就赶紧掉头走了回去,“阿朗?”才刚走到阿朗身边,就见那俩官差打扮的人笑着同少年打了个招呼转身离开了。
“嗯?小哥哥什么事?”阿朗一手抱着婴孩,一手有些吃力地整理着自己腰侧,像是正把什么原本挂着的东西重新摆回去。
“以为你走丢了。刚才是…?”
“噢!来问路的。”
徐飞白一时无言,心里想着看你这个样子,又一嘴外乡口音。这身处皇城也没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假作官差打扮吧,既是本地人怎么会来跟你问路。但也就想想,还是没说出口。
“…没事就好,快些去寻处客栈吧。”
住处安排妥当后的开头几天阿朗还会带着那孩子到处去转悠,后来大约是觉得无趣,也就渐渐不闹着要出门了。这期间徐飞白也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甚至连照料孩子的手势也一点点学了起来,原先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现在也能做个七八分像样。这孩子倒也是真的好养,照阿朗的说法,她现在大约也就半岁左右,这年纪的孩子除吃喝拉撒睡外,剩下最多的时间就该是嚷嚷着哭了,她倒懂事,成天乐呵呵地不谈,也很少叫唤人。阿朗喜欢挨着墙睡,一旦睡着了又睡得极沉,晚上照料孩子的活儿基本就都包给他来做了。偶尔起得晚,那孩子饿得慌也就低声嘤哼几下,并不多闹。只是这天进了八月里,是愈发的热了,孩子虽小也不方便像之前那样摆在盆里。也就好在这是临安,大地方,这客栈看起来派头也不算小,还真弄了张能给小娃儿睡的床铺。入睡的时候徐飞白就把那床铺挪到不远处,好方便照顾。
就是有几次半夜起来,借着那昏黄的油灯,看到那孩子躺着床上仰着脑袋,睁着双乌黑的大眼倒着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瞧,总能把他惊得一激灵,那感觉还真是渗人得慌。
后来他无意间提起这事,惹得阿朗哈哈直笑。
“这周岁前的娃儿可精怪咯,灵台还敞亮着,眸子也干净,小哥哥知道醒,说不准就是她喊得你嘞。”阿朗笑着把那孩子一把抱起托在怀里,捏过自己一缕头发戳戳她肉乎乎的小脸,逗得她咯咯发笑,“不过这娃儿,确实挺特别的,同一般小孩儿不太一样。”
徐飞白有些不解,他是没见过什么小孩儿,但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是说过分乖巧、或是女生男相的话,倒确实跟自己想象里的有几分不一样,但再多怕也说不上了。
“七八月里蚊虫多,这一路上小哥哥可有被叮咬过?”突然间,阿朗没头没脑地甩出那么句话,倒是把徐飞白给问住了,他仔细回想了下,好像真的没有,就摇摇头,“是嘞,我八字硬,有我在呀,这蛇虫鼠蚁、阿猫阿狗,都不敢过来的。本来吧,虽然在村子里带过不少小娃娃,都不用我走近他们就能哭得震天响,连我阿妹在三足岁前看到我都是怕的咯。”说到这里,他望着怀里的孩子,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她倒是跟我挺投缘哩,都不怕我,所以我才说她跟一般小孩儿不太一样。”
徐飞白听罢也没说什么。他也听说过有些人就是天生不讨这些动物小孩喜欢的,阿朗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只是这一类人大多不是身上戾气重,就是长得凶,阿朗虽然在皮肤上有些颜色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应该远不到让人害怕的程度。就如他所说,传闻小孩子在一定年纪以前、和一些动物确实能见着、或者说感受到些一般人察觉不到的东西,这蚊虫一类的可没这本事吧,阿朗不提起他还没注意,说起来了才发现确实如此。这事虽然有些古怪,可也不算什么大事,他点点头随便应了几句也就抛到脑后了。
看样子有阿朗在身边跟着,不仅能照料孩子,分摊食宿,还连驱蚊草都省了,也挺不错的。
这日子过得安稳了,时间仿佛流逝得特别快,一眨眼又过去了好几天的功夫。前阵子徐飞白接到来自同门的传信,这会儿人也终于是来了。
一来就来了四个,原本安逸的氛围突然就热闹了起来。
“…喜得贵子啊?”来人的其中一个似是完全被徐飞白抱着的孩子吸引了注意力,盯着瞧了好一会儿,“不过这…谁生的?”
“啊,不是我。”阿朗倒也不怕生,干脆地接话道。
“那就是徐…哎呦!”话刚出口,他身边一直冷着脸的青年就用手肘狠狠地往他侧肋一顶,“…我说笑的嘛!方师兄你下手可真黑…哎哎不说了不说了!你别!”
徐飞白对着这副吵吵闹闹的熟悉场景轻叹了口气,在给简单给两边都彼此介绍了一下后又几句话把这孩子的来历给说了说。这段时间他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孩子之后的安排,但也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家好提这事,便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往后的事还是得看个缘分了。
“可师兄啊,你带着这孩子去赴宴也不太合适吧?”那叫江雪的青年说道。
徐飞白点点头,往阿朗瞥去,这才一眼,那边就立刻做出了拒绝的手势。
“带孩子可以啊小哥哥,可我也想去看看热闹嘛,让我一人留下看娃儿我可不干的。”
中秋将近,离万贤山庄的英雄宴也就没多少时日了。看他这副决绝的样子,徐飞白想这拖油瓶是甩不掉了。便想着到时还是看看能否找到可以暂时托管的人好照顾一天,应该也不会出多大事。几人随后一起吃了顿饭,把接下来住宿等的问题都给理了理,又接着聊起这段时间各自遇到的事。
阿朗在一边也不插嘴,光是听他们聊也觉得相当开心,不时附和地笑着。手上的酒也是不停,这一桌喊的酒水有一大半都给他一人喝了去。酒不算烈,但那么多酒给他喝下去却似乎跟喝水没什么两样,除了脸色比之前更显红润外,神情却是没一点变化。
但喝了那么多,说是没其他感觉也自然是不可能的,至少肚子是装不下了。他同桌上的人打了个招呼,便出门去行方便。
就在回来的路上,突然背后一阵袭来一道气劲,他眉头一挑,以脚跟为点侧过身,堪堪避了开。
那气劲一道追了过来,并未收手,待他看清楚眼前所来是何人时就也不再闪躲,干脆站定在原地,笑着望过去。
“我想想…是该鸣启哥?你这是做什么呀。”
一柄长剑直指自己喉头。被剑尖抵着的人笑眯眯的,倒是那执剑之人始终冷着脸,盯着自己不发一言。阿朗并不觉得害怕,倒是对方那种警惕的神情让他凭空起了兴奋之情。他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来缓解胸口那种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的感觉。
这感觉他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在那个山寨肆意杀戮之时,这种感觉就一直像一团火似的烧在他身子里。他不动声色地捏了捏拳头——这安逸日子过惯了,三尺三寸他此时并未带在身边,不过他也不担心,刀法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要真动起手来,指不定还是空手来的方便。
只是这来的要是别人,说不定他早已一个箭步向前冲着人命门攻去。但这方鸣启分明是徐飞白的同门师弟,看他们之前的交谈也并无交恶,相反好像还关系甚佳。这会儿到底是为什么来找自己麻烦?
“…唔,我没得罪你吧,鸣启哥?”
“别叫得那么亲。”方鸣启盯了一他一会儿,冷冷开口道。“你有什么目的?”
“……啊?”阿朗闻言一愣,“目的?”
“来路不明,话语不清。你跟着徐师兄到底想做什么?”
“我……”见阿朗说话之间吞吐,方鸣启手上剑锋一抖,更显出他此刻意向——他是确实在怀疑自己来路不正。想想也是,连阿朗自己都觉得跟徐飞白的相遇有些过于巧合了,而徐一杭当年出的事江湖上并不少人知道,突然跑出来一个几十年没出现过的挚交之子,确实让人生疑。可他是真没什么目的,父亲在他出谷前确实交待他要找到徐飞白——但也没告诉他上哪儿找,他还真是碰巧给遇到的。之后虽然也有些事要转告,这段时日来徐飞白也不是没问过他,但总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了过去。这倒也没什么道理,他第一次来中原,人生地不熟的,难得遇到个同辈,又聊得投机,他是真的很想跟人多玩一阵子,就那么跟着了,总比继续去拜访他父亲那些故友来的有趣,“没有目的呀,鸣启哥觉得我能有什么目的?”
方鸣启仍旧是盯着他,稍稍眯起了眼,像是对他这话非常不满。
“我晓得你是他师弟,关心他嘛,可我真的没什么目的呀。小哥哥早就不是当年的身份了,你在担心什么?要现在有人想从他身上谋什么,除了性命以外,没什么好拿的咯吧?”阿朗笑了笑,“要真是那样,我早就动手啦,这一路上小哥哥跟我同吃同睡,你可看他对我有什么防备?我干嘛要等到现在?”
“…你说你是雷大侠之子,那他…”
“——我爹自然是不信那些的。”方鸣启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阿朗便忽然打断他,那神情看起来正经异常,下一刻却又话头一转,换上了平时那副轻松的笑脸,轻叹了口气,“但我爹早就不管中原这些事啦,孰…什么来的,他管不到,也管不了,这次就是让我出来见见世面,顺便去瞧瞧他几个老朋友,传些个口信,看看还有没有谁想带些话给他,就这样咯。”
阿朗所说虽是三言两语,但也并不失道理。如今单就「徐一杭之子」这个身份看来,徐飞白确实没多大让人惦记的价值,即使当年之事已过去数年,但江湖上记得那些风言风语的人仍是不少,以「朋友」的身份同他扯上关系,给自己招惹的麻烦显然是要比好处多不少。方鸣启尽管年轻,但江湖武林上的故事也听过一二,有关那雷焱的传闻除了突然退隐外也没有什么太过负面的内容。这样看来或许是真的是自己多心了,他这样想着,脸上的冰霜也似是融了一两份,手上的剑也缓缓放下。
就在他稍作放松的这一刻,只听到阿朗嘻嘻一声笑,一个俯身跨步到自己眼前。
“照我说呀,鸣启哥该不是吃醋了吧?我老粘着小哥哥,教你没了撒娇的机会?你俩在一起的时间久嘛,我也懂的,分开才那么些时候就想哥哥了呀?”
方鸣启万万没想到这小子会说些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时间也是好看得很。他反手一剑便刺了出去。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一剑显然是他留了手了,同方才背后突袭相比不仅不带半分杀气,连速度和力道也客气上不少。
只是阿朗并不领情。他脚下一移,身形灵活地绕到方鸣启身侧,整个人几乎都要贴了上去,就那么凑在他耳边轻笑着。
“不要羞嘛,我上头也有三个哥哥呢,又不笑你的。”
“……混小子,我看你是欠收拾。”这个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的小鬼在自己眼皮底下说着这种仿佛把自己当成三岁娃娃一般的话,大约是真的有些把方鸣启给惹恼了,他说话的口气比起方才又冷了几分,执剑的手上也加上了力度,又是一剑向着身侧利落地横劈过去。
阿朗也并不慌张,仍是嘻嘻一笑,他反手揽着方鸣启腰侧紧贴着他转了一整个圈,两人这一来一往,竟还保持着先前的站位——阿朗仍然紧紧粘在他侧后方。
方鸣启眉心紧紧蹙起,自知小看了这小鬼的功夫,想他空着双手总会对自己的兵刃有所顾忌,倒没料到他还是个贴身缠斗的好手。他当下就沉了口气,双肩一缩往前踏出半步,距一拉开,借着月色只见一道剑光闪过,眨眼间已是数剑袭出!他并无伤人之意,只想给这人些教训,劈、刺、撩、点几式直指阿朗左右,俨然将其进退闪避之路尽数封死。
“好剑法!”阿朗见势不禁赞叹,他膝下一屈,身形猛地缩起,脚下一用力后像离弦之箭一般竟生生原地跃起近一丈之高!硬是从眼前剑影中突出,腾空一个翻身再次到了方鸣启身后,“鸣启哥,再过几招?”又是一声轻笑,他虚虚握着个空心拳,却偏偏探出拇指关节,往方鸣启手肘筋骨处一顶。
刹时间一阵酸麻沿着筋骨直窜上指尖。他立刻运功压下这股不适,握紧剑柄就地一个转身横劈过去。清冷剑光忽地扫过,阿朗心下一惊赶忙往后疾疾退开,胸前衣料上已是忽然一道刀口,正是被方才那道剑气所破。
“戏弄我?三分颜色你还开起染坊来了。”方鸣启沉着脸,并不打算给对方多少喘息的机会。这小子近身的功夫他也算领教过了,稍有放纵再让他粘过来也不好对付。这几手本事他并不太放在眼里,但那副嬉皮笑脸的得意样看着却是不舒服极了。他心头一把无名火起,剑随心动,片刻之间剑芒四溢,“你若是服软认错,我便放你一马!”
他出剑迅如光电,虚虚实实间变化繁复万千,阿朗只觉周身剑气环绕,逼得他连连后退。
只是对方这千招万招,并无命招。直到他脚下退无可退,也就不再避退!
“不服!”话刚出口,只见他不退反进,身子微微一侧便直向着那剑锋攻出一臂,他手掌上下翻腾,竟如一尾毒蛇般贴上剑刃径直游走。
方鸣启觉眼前剑芒似被片片红光所没,阿朗左右手不断反转交替,硬是把那剑身从茫茫冷光中给困了住。不消片刻他就从这微一愣神中恢复过来,手心一松一旋,使得那剑身也跟着转了起来。他这招本是想逼得阿朗放手,却发现毫无效果!他这剑刃是何其锋芒毕露,现又有气劲加持,此刻在那人手中却并无任何切割穿刺之感,仿佛被困在石缝中一般。
而阿朗攻来的双手满是血色,却像是并不觉疼,还直往他心口袭去!
他心道一声不好,暗自运功提气聚于手中,侧身斜让半分,剑锋一震便将阿朗双手挑开,向他右肩刺去。
自己倒是心慈手软处处留手,这小鬼一时得意竟有取自己性命之意!真是欠教训得紧了!方鸣启怒由心头起,已是决定非得让他吃点苦头不可。当下剑光再次四起,锋芒划空而至。
他这招出手是志在必得。这几式剑法每一招都有数十路变化,加在一起又能组合出百般套路,对手若是有意要解,也得将这些招式出路招招封死再一一破解,他也能在后续再使出新招。虽说无论何种武学,这万事万物都必有破绽,他也是心知肚明,但这剑法的破绽连他本身都尚无信心说得清道得明,此刻就更不怕阿朗这毛头小子更破得了。
不想眼前所发生之事,却真让他始料未及。
对着这式式剑招,阿朗闪避得虽极为狼狈,却每次都堪堪避开要点,几次剑尖刺过都被他用极其诡异的掌法化开。他出掌毫无规律,随着方鸣启剑招变幻,掌法也不断变幻,两人进退之间竟已教手数百式,仍是平分秋色。方鸣启突然发现眼前虽一直有红光闪动,剑身上却不见有血,仔细一看才发现那红光竟是阿朗双手本来的颜色。他原本戴着的羊皮手套似在之前的缠斗中破碎脱落,这才露出一双手的本来面目,这掌法看着古怪,这双手也是一样,他这般利剑的锋芒竟没能伤它半分。
“妖路子,不服也得服!”他转念一想,突然大喝一声,果然震得阿朗心神微滞。这片刻破绽已足以令他从这缠斗中取得优势!他执剑向前,已是胜券在握!
更让他惊讶的事也发生了。剑气刚出,阿朗突然双腿分别往地上一蹬,下半身整个凌空跃起,双腿在空中一阵交替纠缠,整个人往后一个翻腾就突出了重重剑气包围。更令他想不到的事这人在没任何借力的情况下,竟生生在半空强扭过上身,带着整个身体调转了面向,稳稳落到他的身后。
霎时间一阵阴风扫过。
此刻阿朗身躯微偻,双手掌心微微点着地,半伏在地,整个人有如一张拉满的弓,剑拔弩张。
方鸣启自是没有发现他不对劲的地方。阿朗的脸上不知何时已没了先前那副调笑模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怪异,漆黑的双眼在经历这番激烈的较量后竟如一潭死水般沉静。
这一切徐飞白都看在了眼里。
阿朗从饭局上离开后不久方鸣启就跟了出去,还带着剑。他原先也是猜到这个警戒心强的师弟也许是找人问话去了,但毕竟自己在,也不太担心两人闹出什么事。只是这两人一去都久久不回,他难免担心,这时也忍不住出来看看。
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副场景。
不死不休。
这四个字一下子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阿朗之前同他说的那些关于斗蛊、关于比武的话也一股脑的全都涌了上来。
他可千万别来真的啊!
“阿朗!!”
说时迟那时快,原本已然跃出的身躯在他将话喊出的那一刻有了一个明显的停顿,他看到阿朗眨了眨眼,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
“小哥哥?你怎么……呜!”
突然一股凌厉剑气迎面破来,穿过右肩的衣服把他整个人一把往后拽起,钉在墙上。
他回过神,就看到方鸣启居高临下看着自己。
-END
=======
为了赶时间线强行压缩日常到这程度也是没谁了…仍然很不满意的一篇||本来是准备昨天发的,但后半段怎么也续不上,拖到今天终于想出合适的跳跃(。)法才…ToT
打戏写得要呕血,平时积累不多,想找参考都不知从何找起…(倒地)
标题本来是想叫「近中秋」的…但想想好像几篇的标题都挺没文化,这次就强行装逼…舞的当然是方师兄了!(被打死)
仔细想想我大概只是想要调戏他才写得这篇吧…吧…吧……
没有QA!如果有什么地方描写的不清楚,欢、欢迎留言问我…Orz
PS.万贤山庄阿朗会去,但不会跟华山的人一起去,如果有幸哪位PC想用到他,还请稍微留意后续更新TUT…我、我争取三天内…(别信)
以上!再次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多余的话就不说了,每次看到大家的回复和收藏都泪流满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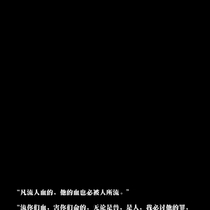
“这下可真得赶点路咯,小孩子饿得快,上一顿不晓得是啥时候,现在睡着还太平,一会儿醒了可麻烦的,得赶紧到镇子上,好给他搞点吃的。”同徐飞白相比,阿朗显得淡定得多,他转身站起,便把那婴孩往徐飞白怀里一塞,对方赶紧接了过来,却也笨手笨脚摆动了好一阵,才在阿朗协助下给抱了住,使点力怕掐疼了,太虚又怕摔了,看起来有趣得很,阿朗也忍不住哈哈笑了几声,“小哥哥你回来就好咯!你先抱会儿,我去把孩子他爹娘给找个地方埋咯先。”
“埋?拿什么埋?”徐飞白看了看这马车里的陈设,想这对夫妇大约是带这行李家当走动的外地人,不想在此地遭了山贼毒手,横死他乡,死后尸首不能入土也是挺可怜的。但他们二人也是步行,不可能带着他俩的尸首上路,要再去别处找人也挺耽误事,在附近寻处空地掩埋算是下策里的上策了。只是当下连把铲子都没有,要弄出能装下俩人的坑来也委实不易。
“……。噢噢!对对!…拿…拿这个啊!”阿朗闻言一愣,脸上似是一阵古怪,但徐飞白还来不及再问什么,对方就拿起腰侧那柄黑刀,“这个嘛!结实得很!比小哥哥的剑好使!”
徐飞白不住汗颜。
那「三尺三寸」当年在江湖上随着雷焱走天下时,也算是响当当的“神兵”了。具体来历他是不太清楚,他爹从前也没跟他细说过这一段,但隐约也记得是有点名堂的宝物。因为生得宽厚就要被前主人的儿子拿来干挖土掘穴的活儿,要这刀本身有意识,肯定也不服这事,他想。但此刻也没更好的办法了,那身在远方的雷大侠要知道了估计也是挺没辙。
“小哥哥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吧!我很快就回来!”阿朗说罢就从车里跳了出去。徐飞白看着那婴孩,先前在阿朗手里时候他睡得似乎还挺安稳,此刻被换了个怀抱,隐约有些要醒来的势头,他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
大约过了一盏茶多的功夫,阿朗就回来了。他半身衣服上都沾了土,脸上也有不少。但手上缠着的那些布带倒是没多脏,大约是影响动作就提前解下放在一边,之后再缠回去的吧。虽然看起来有些没头没脑的,但这些地方倒是细心得很,徐飞白心想。对方回来后跟他打了几声哈哈,就从他怀里把婴孩又接了回去,托着臂弯里掂了掂又拍拍,动作很是熟练。不知这婴孩什么时候会醒来,两人也不敢多做停留,便又启程而去。
就算是加快了脚下的步子,路上也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等抵达镇子时已是接近黄昏,入眼的大多是熙熙攘攘收工回家的人。路上的摊子们收起来时另一些酒楼客栈却是热闹起来,两人跟路人打听了几句就寻了处客栈落脚。
“两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住店。也准备几个小菜。”徐飞白说着掏出些铜钱,“另外劳烦店家,帮忙弄些能给孩子吃的东西。”
那小二接过钱,往他身后看去。孩子此时已经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倒是意外懂事,不哭不闹,反倒在阿朗怀里笑嘻嘻地往两人瞧。小二打量了他俩一会儿,露出些许疑虑的神色。
“店家哥哥就帮帮忙,我阿妹年纪还小,饿不太起嘞。”没等徐飞白解释,阿朗倒先开了口,“我原本跟爹娘住在乡下,但家里头出了点事,现在只好带着妹妹来投靠我家小哥哥。就在这儿住一夜,明个还得赶路咯。店家哥哥晓得往临安去还有多久不?”
“还有些路啊。你说你俩…兄弟?这是你妹妹?”
“是咯。”阿朗脸上露出有些尴尬的笑容,“…我生相不太好,所以一直跟爹娘留在乡下。但现在没法子也只好…”说到这儿仿佛是触及了什么难言之隐,他咬了咬唇,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哀伤的神色,把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了些。那孩子也很是配合,此时也停下了笑,小声抽噎起来。
“难怪难怪。…哎,这世道也不太平。两位放心,这街坊里总能找着有奶的妇人的。大家乡里乡亲的也不会不帮忙,您也是给了好处的嘛,交给我吧。”跟看起来有些古怪的阿朗不同,徐飞白一身干净利落的白衣,配着把一看就价值不菲的好剑,这小二就算再不懂行大约也能看出他是个有点来头的江湖中人。两人言语之间说话口音也有所不同,倒跟阿朗说的话也搭得上。此刻便也不再生疑,把擦桌掸布往肩上一甩,“两位住一间?”
“就一间吧,省点盘缠。”阿朗开口道,“再麻烦给弄个够大的木盆,一些软和点的垫布。”
“好说好说!这边走!”话说完小二便带着两人往客栈楼上走去。
期间阿朗又跟他提了些听起来像是照顾婴孩需要的东西,那小二也一一答应下来。徐飞白听得云里雾里,心中倒不免有些佩服这个少年——几句话之间把自己有些为难的问题全都给化解了去,虽然乍听起来可能觉得勉强,但细想来竟也合情合理。
从意外遇上父亲挚友之子,到因此耽搁行程以至于遇上山贼行凶,最后捡到那么个孩子,这一路上发生的事不知是巧还是命,徐飞白不禁苦笑。不过他尚有些庆幸,要怎么都躲不开这孩子,还是遇到阿朗来得好,自己还真不太会带孩子。
“你说她是个…姑娘?”安顿下行李后阿朗又前前后后跟着小二忙活了一会儿,终于给那孩子喂了些食,自己也总算吃了些东西,这便想阿朗先前的话。
阿朗在店家准备的木盆里垫上了软布,做了个刚好够睡的床,就把孩子放在里头。徐飞白凑过去看了看,这孩子生得浓眉大眼,很是精神漂亮,眼仁也是又黑又大,笑起来时看着尤其显得深邃。他本身也没见过多少婴孩,但乍一看还以为这精神样是个男孩子,一路上也就想当然的没有多问。原先是准备找合适的时候找户人家托付了去,但这会儿才知道是个姑娘家,反而有些犯愁起来,女孩一般不如男孩好送,若是随随便便交了出去自己也是不放心,这样一来就又得多带上她一阵了。
“嗯啊,是啊?”阿朗伸了个懒腰,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按了按肩膀,看起来颇是劳累。仔细想想也是,这小半天来孩子几乎都是由他抱着,吃喝拉撒洗也都由他一手包办了,“抱着的时候就随便看了下咯,还是得晓得一下,有些地方男娃女娃带起来不一样嘛。”
徐飞白一时没忍住,噗一下笑出声来。
“你也没多大年纪,听起来倒很会带孩子?”
“我也说我有个阿妹嘛,老看娘带她咯。村子里有其他孩子我也喜欢,就偶尔去带着玩,几个下来就知道二三了。”
“看起来倒不像只知道二三。”徐飞白笑笑说道,“不过,你吹牛本事也不小啊,说起谎来面不改色的…阿朗?”他话说到一半,再转过头去只见阿朗已面朝着墙蜷起身子安安静静地在床上睡下了,还隐约能听到他发出的安稳轻鼾。就这一句话的功夫,这小子居然就这样直接一头栽倒睡着了。这床铺也就是标准大小,并不特别宽敞,好在阿朗身型不算高大,这会儿睡得又格外老实,除了呼吸带动的身体起伏外没一点动作,剩给徐飞白的位置也不少,“睡着了?”他走过去,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见对方像是毫无感觉般没一点反映,心想这小子可能真的累了,也就没再多做理会。只是这天色才暗不久,自己实在是没打算那么早睡,便只好看着盆里孩子的睡脸发起呆来,等真的有困意袭来才往床上躺了睡去。
他这觉睡得并不踏实。倒也不是被噩梦魇着,而是被身边奇怪的异动给触醒了。
约是儿时一些事故的关系,徐飞白几年来睡得都比较浅,虽不影响什么,但稍有些外力就很容易醒来。此刻便是,他明显感觉到手肘处被什么东西给碰了一下。原本以为是那睡得异常老实的少年有什么翻身的动作,但立刻,一股异样的阴冷气息就顺着被碰到的地方袭上全身,在这初夏时节竟激得他浑身一个冷颤,也让他彻底醒过神来。
他转身看向身侧的阿朗,那人还是如此安稳地背对着自己、面向墙睡着。仍旧是那平稳的呼吸声,一动没动。
那刚才碰到自己的是什么?错觉吗?
念头刚一闪过,只见少年衣衫下的脊骨处突然隆起一个怪异的高度,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衣服下头似的。
难道是老鼠爬上床了?
还来不及消化自己脑袋里出现的这个可笑的念头,先前的那股异样的阴冷此时突然一下从脚底窜上灵台!徐飞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紧张,头皮整个一麻。他睁大了眼睛盯着对方的背脊——刚才那个动静的出现和消逝都实在太快了,几乎是一闪而过,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走了眼。但若真是自己看错,这种奇怪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是夜晚风寒?或兴许他还在什么奇怪的梦里?他不禁屏住了呼吸,紧紧地盯着。他也不是很确定刚才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会再出现一次,大概自己真的看错了也不一定。可不知为何那股阴冷的气息仍环绕在自己身边,让他无法就那么放下。他不自觉地咬紧了牙,甚至感觉自己的内息都开始变得不受控制,像是在跟那股入骨的寒气做着抗争一般。
大概是真的被魇着了——这是他后来想的。
“…干嘛?”
突然之间传来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抬起头发现阿朗不知什么时候歪过头来眯着眼疑惑地看着自己。
“…我…”
天还没亮,关着门窗的房间在这个季节仍显得有一点闷热。徐飞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但却完全感觉不到刚才那阵寒意。再看那少年,只是稍稍偏过头,看起来仍是睡眼惺忪,背上的衣服也因为他蜷缩着的动作而紧贴在背上,哪有什么老鼠能钻的地方,也没有隆起过的痕迹。
“…怪怪的嘞…”阿朗打了个哈欠又背过身去,从脚边拉过先前没盖上的薄被裹到身上又更缩进了身子,“…明早还要赶路…早些睡咯…”
“…啊、啊…嗯…好。”对方迷迷糊糊的关照听起来倒让徐飞白觉得有些安心,随口应了几声他也再次阖上眼试着睡去。
这回倒是直接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阿朗比他醒得还要早些。
用这小子的话说就是村里的日子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不是因为累,只是天黑了又没什么事做的话自然而然地就想睡了,一直如此。
“什么叫没什么事做?”
“噢,就是偶尔啊,会有些人喜欢聚在一起喝个酒,谈个天嘛,就能打发时间咯。”
多了个孩子在手上,原本的计划也就稍有了些变化。婴孩要吃的东西不好携带,如果只是在路上走的话,怕孩子饿得快,也就不好在人少的地方逗留太多时间。两人合计了下就雇了附近的车夫,顺着大路走人多的地方,沿途也好解决这孩子的日常需要。到了有客栈的地方就住上一晚。原先还担心盘缠,好在后来阿朗还是硬着头皮顺路去拜访了几位他父亲的旧友,也讨了些红包。那些前辈若是要挽留,八成都被他「要送朋友和其子去临安」为由给拒了。几天的功夫离临安也是越来越近,这期间闲聊也好,听他跟几个前辈客套也好,徐飞白在边上见识了他不少滑头的地方和嘴皮子上的功夫,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熟络起来,聊得也就越来越多了。
“你们村里人很多?”
“唔…我想想噢…也算不上多,百多个吧。”阿朗仰着头眨巴眨巴眼,“不对不对,我再算算…唔…两百…唔…大概还得再多些,有好多都不爱跟人来往,见不太着,不是很晓得咯。”
“有那么多人?”徐飞白惊讶地问。他原本听阿朗把那村落形容得如此闭塞,还以为是个几十口人的小地方。照他现在那么说,江湖里不少上得了脸的门派其实也就不过这些人而已,甚至还不一定有那么多。而之前他说村子里头有不少中原退隐的武林前辈,如果是这样的基数里「不少」,那到底该有多少?虽说厌倦了江湖事的人每天都有,但那样的人通常最后都走上了闲云野鹤的独行道,很是不合群,就算再怎么不跟人来往,能都在同一个地方待得住倒也稀奇。他不禁对这个「村子」好奇起来,又追问了阿朗几句,那边却狡猾地眨眨眼不再多说。
“小哥哥要是好奇,以后跟我回去瞧瞧嘛?”阿朗低头看了看仍熟睡中的孩子,那小小的手里还紧紧拽着一条他从原本腰带上割下来的绣带。又瞟了一眼徐飞白,懒懒一笑,却也不等对方回答,“不过小哥哥问的,我确实也不晓得太多,他们都不太讲的。”
“他们?”
“村子里头的人咯。特别是我生下来就在的那些人,都不太讲的。我只晓得有好些是苗人。”他想了想,接着说道,“我娘就是咯,她是村子里头原来就在的人,好像最上头几辈就已经在村子里咯。”说到这,他看着徐飞白好奇的表情,又笑了笑,“我也算是半个吧。小哥哥晓得我们苗蛊不?”
“略有耳闻,不甚了了。”徐飞白摇了摇头。
“可神咯,我娘跟我师父都是玩蛊的好手嘞!我阿妹也会一些。”
“你师父?你还有师父?我以为你师父就是雷大侠呢。”
“不是哇,爹只教了我刀法而已,其他都是跟师父学的。”阿朗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眼神也变得有些躲闪。一张小脸上百般纠结,几次张开嘴都又合了上,就那么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吞吞吐吐地说道,“…我小时候身子不好,差点就养不大咯,亏得师父的功夫能医我,我也就跟了他好些年,喊得他师父…”说话间徐飞白注意到他一直瞥向自己那双手。因为照顾孩子的关系,阿朗特地在临走前寻了副软皮手套,说是方便动作不容易散开。一开始徐飞白也是奇怪, 阿朗对于自己的面貌似是并不在意,却特别在意这双手,直到对方解下布条后往他手里摸了一把他才知道,那双手不仅是看起来怪异,连触感都奇怪得很。凡是泛红的部位都硬如牛皮,触手更是有如细磨刀石般粗糙,光着手倒确实是不方便照顾孩子。
“你的手莫非就是因为那病…和你师父的蛊术?”
“嗯。”阿朗点点头,便不再说话。
这样的沉默让徐飞白很是不自在。如果只是两人话题到了适合收尾的时候,稍作歇息倒没什么,但像现在这种时候,原本开朗活泼的人被突然碰了伤处而不得不蛰伏起来却让人有些不忍。要他选的话他宁可听阿朗那些半真半假的胡话,也不想看到他这个样子。
“那你师父会蛊术的话,是教了你吗?”得让他打起精神。他这样想着,就又顺着刚才的话题换了个方向继续下去。
“啊?没有哦,我不会那个的。师父只是救我的命,又教了我些调息心法罢了。不过师父以前也跟我讲过他在进村子前的事,听起来可有意思了!”
“哦?”
“师父在进村前,好像是什么挺有名的寨子…我不太晓得。但好像总有外人会去那儿找他们的人斗蛊。可厉害了,五花八门的咯!”
“嗯…中原也有差不多的事。如果是功夫很好的人,或者什么门派的掌门,三五不时也会有人上门拜访求一切磋机会,也算是一种挑战。若是来者功力相当,那是必须得应战的,也算一种礼数。”
“切磋?我爹好像讲过。但斗蛊又有点儿不一样哩。这斗蛊啊,要是没什么大事,都不会请家里最厉害的人来斗的,连稍微厉害的都不会派得太出去。”阿朗说道,“斗蛊跟比剑不一样,你们这叫什么来的…点…点到鸡止?我听着好像是那么说,有点下流啊…。”
“……是点到即止。”徐飞白叹了口气,抽过阿朗的一只手,在对方没反应过来时便摘下他的手套,在摊开的手心上拿食指比划着,“是‘即’,立刻的意思。连起来就是「到了分寸就立刻停下」的意思。”
“…唔。”阿朗看着对方在自己血红手心写字的样子表情一柔,紧紧抿着嘴也遮不住嘴角泛起的温暖笑意。他看着徐飞白又帮自己把手套戴好,才收回手,“可我师父,我们那儿可没这种事。这斗蛊啊,一旦开始了,就一定是得寻个你死我活的。中原人比剑拼的是武,我们斗蛊啊,拼的是命。所以这等大事,哪能让当家的来搞哦,才不管什么礼不礼的。要有人来找当家的麻烦,下头人没死光前,绝不会让当家的出手的。这家里的小儿输了,死了,也就认了,家还在,也多少晓得了对方的底,将来要报仇什么的还有的算。这当家的要是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徐飞白听了连连点头。中原武林大多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尤其是那些名门正派,他也是见识过的。哪怕是一开始说好交流武学的切磋战,最终因为放不下颜面,或者简单的「输不起」,搞得家破人亡灭门的故事也并不少。像阿朗他们那儿这种把面子看得那么豁达的倒还真不多,一时也觉得新鲜。
“要嘛不斗,要斗哪有人没死就留手的说法?所以输了的也是认命,技不如人嘛。”
“话也不是那么说,如果只是交流…”
“为什么要交流?我听说很多武林高手,一个人闭关好多年,也到了天人之境啊,跟人斗不就是要杀人吗?”
“…也不是那么说…”徐飞白似想到什么,也是一时语塞。阿朗的话处处都让他觉得不对,但却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纠正他,“…要照你那么说,家里的人全都不在了,这当家的就算活下来,当的还算是家吗?最后被留下来的人也不一定是想被留下来的…”
话一出口,阿朗也是一愣,好一会儿没说话,像是在认真琢磨着徐飞白说的话。
“…好像也有点道理…唔,小哥哥说得也是,入乡随俗嘛,我会多学学的。我爹是中原人,但我娘是苗人,我又是师父带大的,很多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跟他们比较亲哩。中原很有意思,但好多事我都还不太懂。那一套一套的道理也好,礼…礼数?礼数也好,都不太懂,太麻烦咯。”阿朗抬头看向徐飞白,“刚才小哥哥是在我手心里头写字吧?痒得很哩。我也不识得几个字,你多教教我罢?”
“嗯?好啊,举手之劳。”徐飞白应道,“会痒?我还以为你手上木得很,若是不适我…”
“不会不会,没不适!”阿朗赶紧解释道,“我手上虽然这样子,但其实还挺能知道事咯。别的地方你拿刀子割我,我都不一定晓得疼的。就只有手上还能觉得点…”说着他作势往自己脖子侧捏起起皮拧了下,白皙的皮肤立刻红了一片,但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一点不疼的。”
“难怪…”徐飞白恍然大悟,心想上次他睡着时自己对他的推搡他没点反应,怕也是因为感知迟钝的关系。对此他倒也没太多好奇,想必也是因为他这怪病导致的吧。这少年现在看起来活泼开朗,原来也是有过一身旧疾,让他不由觉得可怜起来,“所以上次那老板娘捏你的脸,你是故意喊疼的?”
“…呃—”阿朗耳朵一红,脸上表情也是一滞,“这瞧见了就、就装装嘛…”
“挺狡猾的啊小子?”徐飞白说罢难得地大笑起来,把阿朗笑得是怪不好意思,对方低着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又拍了拍怀里的孩子,才让他压低的笑声。
“还笑呢。我说呀小哥哥,我虽然挺难察觉到别人碰,但要谁「盯」我,我可晓得。”阿朗有些得意地仰起下巴,“习武之人不是常说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我对筋骨皮是没什么知觉,但这「气」我可晓得的清楚噢。”说到这儿他眯起眼睛故意阴恻恻地笑了几声,还掩住了怀里孩子的耳朵,“前几天夜里小哥哥盯着我的时候可真是烫人得很啊,都把我给燥醒了哩。”
徐飞白很明显地听到自己脑袋里「轰」地一声,尴尬是次,倒是这小子这幅样子让他好气又好笑,要不是看他还抱着个孩子,一定少不了给他些教训。
“哈哈哈哈,不开你玩笑咯,小哥哥脸都绿了。”阿朗自顾自地乐了一会儿,也不多捉弄他,反倒安静下来看着徐飞白笑道,“…我爹虽然已经离开中原很久了,但他跟中原武林还是有些联系的。他跟我说起徐叔叔的时候,也是一直喊得他盟主。”他顿了顿,“我爹喊小哥哥的爹一声盟主,我又喊你一声小哥哥,你家还是有当家的。”
徐飞白听他那么说,一时间竟是有些恍惚。
此时忽然一声马鸣。
“二位公子,”那车夫停下车,回过头来,“这临安到啦,你们自个儿进城去吧?”
两人才发现已经到了热闹非凡的地方,高耸的城门,来来往往的各色行路人,无一处不显露此地和先前几处落脚镇子完全不同的排场。
都城·临安。
-《往临安·完》
-----
噢拖好久…我真的很不擅长写这种…严格上来讲我也不擅长写长文…
但总算是走、走完这一段了…
后半段要说的跟原先计划的差好多,但我尽力了||表达不周实在是…望多包涵||希望不会让人感觉看得太乱T0T(喷泪)
好像没什么要多说了只希望下一篇能尽快写出来赶进度(哭
仍然感谢看到这里的您们,万分,万分感激,这次真的相当不满意但无奈话已经放出口了说更新就更新为了声誉也只好ry(我也确实做不到更好了越拖反而越没底…)
希望您们还会期待这小子的后续……(躺平
以上!再次感恩!Or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