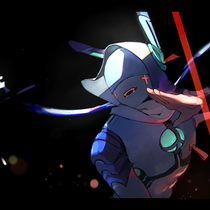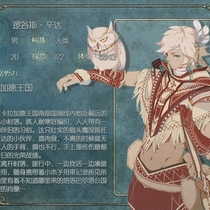“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念了这两句诗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一身霜色衣衫半新不旧,腰间斜佩长剑,望着眼前粼粼水波,正自出神。这诗是诗仙李太白传世名篇,六岁小童亦可诵得,然而当真来到镜湖、站到若耶溪畔,忽然这两句涌上口边,意趣与在书斋之中学得,自有不同。想李太白彼时虽不得意,乃有古来万事东流水之叹,然而这诗的气象胸襟,大开大合,毕竟不是凡人所有。
正自乱想时,他身侧一老仆弓弓身问道:“少爷,什么吩咐?”
青年回过神,摇头道:“并无甚吩咐,不过自言自语罢了。这若耶溪这般景致,我居上虞,几步之遥,却未曾得来过几次,实在可惜。以天下之大,不知更有多少秀美山川,只怕终生不得一见。”
那老仆身量不高,瘦骨嶙峋,肤色黝黑,头发斑白,一身短打扮。却与一般下人不同,听了青年人这话,也不凑趣,只听得未曾吩咐他,便呆着脸一声不答。青年人也不介意,真个当自言自语,又去看水光。
此刻是晌午时分,虽连日晴天,毕竟入了七月已不太热,这一主一仆,似富家子弟郊游玩耍,闲适得紧。青年人忽然脸色一滞,道:“胡叔,咱们这便走吧。”
说着信手丢给旁边艄公一块碎银子,快步走上早备在一旁等他二人的小舟。那胡叔仍是不答话,低着头跟在他后面上了舟。艄公得了银子,喜笑颜开,解了绳索,也跳上舟来,长长念一声:“走嘞——”,便要撑船。
胡叔忽道:“且住。”
艄公刚拿起篙竿,尚未沾水,抬头赔笑道:“客官还有什么吩咐?”想是那小块银子功劳,这艄公方才还爱答不理,此刻热情了许多,便是对胡叔也恭恭敬敬起来。
那青年人原本容色和善,眉眼间总带一丝盈盈笑意,此刻蹙了眉,轻轻跺跺脚道:“我说,开船。”
胡叔唤道:“少爷。”拿眼去看他。
青年人虽不愿转头,渐渐被看得不自在起来,终是叹了口气,道:“唉,是我的不是,胡叔莫怪。”转眼见艄公一脸怔忡不知所措,又微微一笑,安抚道:“船家不必慌,我们说几句话就走。”
此时方有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骑奔了过来,至岸边方有一人滚鞍下马,向青年人行礼道:“可算追上少爷了。”
青年人此刻倒舒展了颜色,笑道:“章师父,何事劳得你老人家出马?我爹还是不放心么?”
那章师父是个苍头老人,看去筋骨却是硬朗,和那胡叔对视一眼,苦笑道:“少爷,老爷说了,请少爷回去。”
青年人没半分异色,仍是含笑道:“我不回去。”
那章师父似也料到,干笑两声,道:“少爷,有什么话,回去自可跟老爷当面谈,还请少爷别叫老章头为难。”
“我岂能叫章师父为难?”青年人忙道。这章师父是他拳脚启蒙师父,他向来以师礼待,此刻章师父这话很有几分倚老卖老的意思,他不能叫他不卖,却也不想买。一边思量,一边细声慢语答道:“只是这一趟,我非去不可,也非我去不可。烦章师父跟我爹说一声,我必将找……带那人一齐回去,请他老人家安心才是。”
那章师父一脸难色,道:“少爷有所不知,此事……此事老爷自然安排别人去,”青年人不肯明说何人何事,他也跟着含糊称呼,“倘若真是不得,老爷说了,他可亲自出马,断没有不成的道理,叫少爷不必担忧,还是先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青年人沉吟片刻,忽道:“章师父,你在我陆家,有三十年了吧?”
这话风马牛不相及,那章师父一脸莫名其妙,答道:“老章头自徽宗爷元年便在陆家服侍老爷,今年是……第四十三个年头了。”
青年人点头道:“我今年才十八。陆家的事,章师父知道的,是比我多的。”
那章师父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答道:“不敢。”
青年人微笑道:“章师父不必紧张。章师父是个聪明人,胡叔也不是外人……我便明说了吧,阿爹为何唤我回去,姊……此事是如何起的,我约莫也知晓。章师父自然更是心中明镜一般。”
那章师父便拿眼去看胡叔。胡叔仍是低着头,呆着脸,一言不发。青年人道:“跟胡叔无关。章师父还不晓得胡叔?最是惜字如金,若一次跟我讲话多过十个字,我便可去上炷香了。”
章师父赔笑了两声,再开口却道:“老奴不明白少爷的意思。”
青年人不以为意,挥挥手道:“那也无妨。章师父只消跟我爹娘说:养育之恩深重,依明粉身不足报春晖片缕;姊姊也是爹娘亲骨肉,我亲姊姊,自我幼时一处长大,待我极是友爱。我陆家只这四口人,素来相亲相爱,一体同心,自当毫无嫌隙,亲密无间。当此乱世,更是如此。世道不太平,我不放心,一月……两月,最多三月之后,必然归还。”
章师父寻思半晌,方道:“好罢。说不得,老章头回去传这一段话。也请少爷务必小心为上。”
“多谢章师父挂心,依明自会多加小心。”
章师父拱了拱手,径自上马去了。青年人转回头,见那艄公呆呆站在一旁,望着他们。他心下多少省得,江南多水路,舟楫是常见,骑马却是难得,况且金人不断滋扰,马匹多为军用,百姓人家有匹马骑,着实并非易事。果然那艄公按捺不住,问道:“非是小的乱打听,只是适才听得,少爷莫不是陆家庄的大少爷?”
这话问得不伦不类,青年人笑起来,点头道:“正是,陆家子陆依明。”
艄公啧啧连声:“原来是上虞陆家!怪道怪道,也是小的愚笨,看少爷这气派,原该知道,这绍兴城内也没有哪个能有?便是知州老爷家的公子,也难得少爷这么……这么……”
陆依明听他胡吹大气地奉承,末了又卡壳,心下好笑,自不当真,正要开口叫他开船,一直默不作声的胡叔道:“这船,几钱?”
艄公发愣:“啊?”
胡叔索性抓起他手,拿过篙竿,又将一枚银锞子放在他手心,道:“这船,买了。”那银锞子少说有三两重,这条小舟不过几块木板钉钉,说值半吊钱都是抬举,决计是不亏。那艄公呆立那里,似乎转不过来弯,银锞子是立时攥住了,面上还是呆呆傻傻,张口结舌地瞅着胡叔。胡叔伸手示意他下船,那艄公又浑浑噩噩回到岸上,胡叔自行撑起篙竿,深入水底用力一点,小舟登时离岸丈许,向下游漂去。
陆依明默默看他施为,待船离岸,方道:“何不留那舟子撑船?倒要劳动胡叔亲力亲为。”
胡叔道:“吵。”
陆依明不禁一笑:“确实。”
胡叔又道:“不是好人。”
陆依明却是一怔:“呃?”
胡叔用脚点点船板,弯下腰揭开,上面是薄薄一层木板,下面露出真正船板,竟掏了一个大洞,又拿一块圆木板堵上。陆依明不是笨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登时皱起了眉:“这?”
胡叔点点头,重新把薄板盖上。陆依明思量片刻,道:“我水性也还过得去,家住还这么近,想必他也不敢害我。”
自朝廷南渡,北人也纷纷过江来,倘或是北人商客,不识水性,又在当地无亲无故,船行至中游,那艄公悄悄把这洞一扒开,再不会有人知晓有些人就此彻底消失,盘缠细软自是落到艄公手里。如此妥妥当当,确实不必害陆依明这等本地大户。这在江湖之上原是不值一提的常见戏码,但陆依明毕竟听闻不多,虽自我安慰一句,终究是有些寒心,又点头道:“是了,就是他不去害我,我们又何必跟歹人同船?兼且,当真太吵。”说到末一句,又笑起来。
胡叔仍没理他,自顾遮好船板,又去撑船。陆依明早惯了他寡言,自坐在舟尾看水,这日亦是天朗气清,水面映着日头,宛如撒了一江碎金,又都活过来跳跃攒动。陆依明心不在焉地看着,暗自等着胡叔开言。
船至中流,胡叔才问:“你怎知?”
陆依明故作不解,反问道:“我知什么?”
胡叔寂然良久,方道:“你晓得。”
陆依明看他半天,终于不再玩笑,轻轻叹口气,道:“唉,胡叔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瞧着就跟长辈也近似。只当预演罢,我还真不知异日如何跟阿爹禀明。”
这胡叔看去有五六十岁年纪,其实是老相,实际尚不及五十岁。他母亲是陆家现任家主、陆依明父亲的乳母,陆父幼时与他一起长大,亲如兄弟,是以胡叔在陆家确实地位超然,陆依明这话说出也并无不妥。而陆依明自幼便得胡叔照料,虽然胡叔寡言罕语,但待陆依明也是十足好,陆依明心里,有时比威严过头的父亲还要亲近三分。只是他酝酿半天,仍是不知如何开口。踟蹰着又叹口气,方道:
“先说姊姊吧。姊姊性子是不大好亲近,但人是最好的,素日也最守礼,我原本还奇怪,怎会突然留书出走呢?又是不解,又是忧心,而此事终究也不便太多人知晓,便禀明阿爹出门。也幸而胡叔肯随我出门,不然,我看爹娘再不能松这个口。”
原来陆依明长到十八岁,还是初次不随父母独自出远门,而这一出门,便是为了要寻他出走的姊姊。他陆家在绍兴府如何他不知道——观方才那艄公,也是有些名气——在上虞县城,也算得有头有脸的人家,陆依明虽不在意,并且觉得他姊姊约摸也不会在意,但一个未许人家的小娘子擅自跑出门,就算他们习武之家不比那些个读书人狷介,终究不甚好听,陆依明也很不愿有人议论他姊姊,是以方才有旁人在,他提起时都只说“那人”“那事”。
他又叹了口气:“刚出门时心急如焚,到处乱走,却也没撞到姊姊踪迹。而这时阿爹叫我回去,我也未曾多想,立时就要回去听阿爹安排,却刚好探听到姊姊是往临安府去了。我自然是要过去看看,却不料阿爹竟然拦我……我心下便有了猜疑,悄悄找素练姊姊——就是姊姊的贴身大丫头,胡叔兴许不熟,我知姊姊是很信重她的,向她问了当时姊姊离家情状,约摸八九不离十,晓得姊姊为何离家了。”
他看了看胡叔脸色,胡叔脸上还是毫无牵动,恍若不闻。他只得再叹口气,续道:“后来我跟娘说了出来,便不甚着急,是为有了缘由,我想姊姊的身手不比我差太多,虽然说不上高手,偶然遇上一两个小毛贼还伤不了她,运气若不是太差,或许还吃不了大亏,因此不再着紧,慢慢找来……唉,是了,这是托词,实是我也不知如何见她才是。而阿爹今日竟然请章师父直追到若耶溪边,我只有愈发笃定,姊姊必是无意中得知了,一时想不开,才跑了出去……最怕是,一时半刻,也不愿再见我。但她孤身女子,怎好留她一人在临安府乱闯,少不得要寻她回来才是,且此事既然由我起,也当由我结。我不听阿爹话回去,胡叔不会怪我吧?阿爹,唉,阿爹也不要怪我就好了。”
胡叔抬眼看他,道:“为这,不回?”
陆依明道:“自然是为这个,还能为什么?”
胡叔难得说了句颇长的话:“怕是,为你,一时半刻,不愿见老爷。”
陆依明一时间哑口无言,心中忽而飞过无数旧事,三两岁初次记事时,他阿爹,端方严肃的陆家老爷,在阿娘撮弄下笨拙地把他背到背上,玩“飞高高”,十年后偶然提起时阿爹的脸色黑如锅底,称绝无此事;四五岁时跌了一跤手臂骨折,一贯待下人温柔可亲的阿娘,罕见地大发雷霆,把当时跟随他的侍女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是他自己开口“替姊姊们求情”才算过;六岁时第一次见到自幼在峨眉修行的姊姊,那时比他高了一个头,拍着胸脯说姊姊回来了,再也没人能欺侮你,被阿娘一通教训女子怎可如此粗鲁;……还有便是,那之后一两个月,他无意中听到家下老仆交谈,突然得知的那桩事:起始他如何肯信,然而私下里悄悄探听,诸多印证,却只是越发凿实了。
一晃十二年,若是姊姊那位峨眉的师尊——那位不知有没有过百岁的苍云禅师看来,想必也只是白云苍狗不过转瞬,然而对陆依明而言,他活才不过是活了十八岁,十二年,已经是相当之长。他真心微笑起来,恳切答道:“虽是不知如何跟阿爹禀明,但我其实……六岁起就晓得啦:我并非爹娘亲生子,乃是阿爹拾来的弃婴。”
胡叔的面容终于略有松动,他面带疑惑,直直看着陆依明。陆依明柔声道:“只是那又如何?阿爹阿娘待我如何,我心里是知晓的;而阿爹阿娘不愿叫我知道,那我便不知道。唯有姊姊……”他最后又叹了一口气,道:“只望姊姊不要太生我气啊……”
胡叔早不再看他,背过身去撑船,留他在一边默默出神。然而这件事他早已想了无数遍,焉能此刻突然有了什么新鲜主意?到底只能苦笑摇摇头,问:“胡叔,咱们这走水路到临安府去,还需多久?”
“三个时辰。”
“如此近。”陆依明叹道,“我竟从未去过。”
只曾听闻,临安城如今是行在所在,鱼龙混杂,居行皆不易,不知姊姊这一个月辰光,是在何处渡过,又过得如何?
但愿相见不会太难。
——————————
介绍了一下小少爷身世。
感觉露了好多马脚……看到什么bug大概不是错觉(。
实在不擅长考据,无论历史人文水文地理,有任何舛错都欢迎指正,十分感谢;当然懒得说就当是架空放过去的也多谢宽容……orz




“这本书,谢谢。”
将一本破旧的德文书放在桌子上后,青年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是个十分寒冷的下午,让人不由想起冰封大地的严冬之夜。用石砖砌成的简陋书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仅在屋顶上装了一盏小小的壁灯,由它散发出的微弱黄光包围着这个小小的房间,隐约间像是带来了些虚假的暖意,但也仅此而已,枯电期的掩体总是冷得如同噩梦。可青年却像是完全感觉不到这刺骨的酷冷般,仅穿着一件黑色薄呢大衣神态自若的站着。
伊诺克将视线从书籍封皮上收回,有些意外地挑挑眉:“《战争论》,我以为你最不会感兴趣的就是这本书。”
青年笑了起来。他将书本小心塞进手提箱里扣好,用一种低沉而温和地语调说道:“战术和战略永远都是需要的,伊诺克,无论我们的对手是人类还是别的什么。”
“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的战术和战略有意义吗?”伊诺克一边吐出吸入的香烟,一边冷淡地质问:“‘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你不会天真地以为阅读这些荒诞的条律能对取胜有什么帮助吧?赤鳄,你比我聪明太多,但你总是花费时间在无用的事上。”
赤鳄不发一言,他的嘴唇在昏暗的灯光里往上弯着,一双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感到有趣却又不以为意的光——就好像在鼓励小孩子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一样。又是这种令人不快的态度,伊诺克心想,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学会不被青年的态度激怒了,那会使他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还给我?”伊诺克换了个话题。
“很久以后。或许,比先前几次还要久。”
伊诺克抬起头望向赤鳄。在青年精悍的脸上他既看不到任何担心和顾虑,甚至也看不到破釜沉舟的赴死决心,有的只是平静——在无数次触摸死亡后与庞大的战斗经验一同获得的近乎喜悦的平静。他不可能回不来的,伊诺克想道,就算所有人都因绝望而崩溃了,他也不可能向死神妥协,不可能被智者打垮。这一次也是一样。
道别的话在这一刻显得多余。伊诺克暗暗吸了口气,摁灭了烟头。“保管好我的书,伙计,弄丢了就别想来见我。”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
“没问题。”赤鳄笑了起来,孩子般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他戴上帽子默默推开了门,在钢铁的天幕下大步迈入了空旷无人的漆黑小巷中。
当巨型照明灯与人造太阳让光亮笼罩整个掩体城市时,诺娃集住区依然浸没于黑夜之中。这片乱石砌成的低矮建筑群就像是一颗灰蒙蒙的畸胎瘤,丑陋、混乱、畸形,突兀地生长在掩体这只钢筋铁骨的庞大巨兽体内,没有供电设备,也没有任何规划,长长的甬道在拥挤的高墙间蛇行,最后却往往通向被石垣封死的绝路。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在两次生态灾难期间患了绝症的病人,他们不能工作,只能依靠微薄的社会福利苟延残喘。在这毫无生气、全世界都遗忘的地方,所有人都好像沉沦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即使是晨时也很少有人出门走动,干枯的老人蜷缩在肮脏污秽的街角里抽着烟卷,靠着尼古丁的麻痹一遍遍回忆旧时代的繁荣与和平,沉默地消融于黑暗之中,等待着疼痛与苍老将他们埋葬在这个距地两千米的坟墓里。
伊诺克提着死老鼠的尾巴,蹒跚走在从住处到垃圾箱的坡道上。这短短几十米的距离对他来说并不容易,由钚泄露事件造成的第二次生态灾难也让他失去了健全的身体。十年间他的左臂和左脚一度彻底瘫痪,后来通过坚持康复运动而勉强回复了行走的功能,但也只能在剧痛中缓慢地挪动。意志的力量似乎永远比不上肉体崩溃的速度,肌肉的萎缩症状还在向其它地方蔓延,伊诺克今年只有四十五岁,但大衣包裹下的四肢却像垂死之人一样骨瘦如柴。
他费力地提起胳膊,将那只硕鼠的尸体扔进垃圾箱里。老实说,伊诺克并不讨厌老鼠,反而心存感激,据他所知掩体生物圈并没有引入过鼠类,可它们依然不请自来,在铸铁的地面上纵横跋扈。当上帝都已经抛弃人类时老鼠却还乐意寄生其中,这孤独的二十一年里它们是唯一造访的客人。伊诺克觉得似乎应该对它们表示欢迎,不过他还是不得不在屋子里摆上自制的鼠夹——它们总是毫不留情地啃坏他的书,而那可是他仅剩的财产。
确切来说,是一份价值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财产。
小时候,伊诺克就喜欢阅读,书籍之中蕴含着历史与灵魂,他如此相信着并将梦想寄托其中,翻动书页时所感受到的面对未知的颤栗,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不会腻。在那个闻名世界的大家族里他是最怪癖的孩子,当所有人都在为战争疯狂或恐惧时他依然平静如常。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呆在藏书的阁楼里,那是一个被阳光所保护的小小房间,空气中浮动着闪烁的微尘,仿佛隔绝了一切由末日战火带来的惊恐与不幸。只要身处其中,哪怕下一刻便有炸弹从天而降,伊诺克也无所畏惧。
伊诺克从不关心家里的生意,所以当他的祖父罗奈尔德,也就是格鲁曼重工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将他堪比一个王国的巨额财产继承给了伊诺克时,整个家族都如遭雷亟。年仅二十一岁的伊诺克毫无掌权经验,只能茫然地看着律师将房契,地契,船舶、天然气、火电、核电工厂的合同以及遍布世界的军工企业文件摆在他面前,想象着祖父尊贵而辉煌的一生。而在那份浩如烟海的遗产名录的最后,他看到的是一份掩体准入通知单,上面已经署好了他的名字。
——到那时,伊诺克才知道原来罗奈尔德竟是掩体工程最大的资助商之一。
那一刻他忽然对他高高在上的祖父有了一丝隐约的理解。那个年迈的军火巨头统帅着他的商业帝国南征北战,以“决不投降”为信条手握枪炮辗转于人类反击战的最前线,与此同时,却在背地里偷偷花巨资为孙子买了一张通向诺亚方舟的船票。或许他那雄狮般的祖父,那个比任何人都更残暴,更高傲,更具进攻性的野心家,在二十年的战争中从未相信过人类能战胜智者,而是和那些主持建造掩体的政客们一样,认为逃亡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
伊诺克注视着那张掩体准入证,做了一个决定。
2039年8月,迎着德克萨斯州最炽烈的盛夏日光,伊诺克驾驶着路虎揽胜秘密地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出发的时候他已不再是格鲁曼重工新任总裁,也不再是巨额财产继承人,而是重新变回了一个穷光蛋——他把全部资产都捐给了军方,来为他沉睡于阁楼中的亲密朋友换一张同行的船票。
整个德克萨斯州两百万人口里,被允许进入掩体的只有他,以及他的两百三十本藏书——全部都是珍贵的初版或者手抄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多次UFC冠军的年轻人,伊诺克曾在电视上看过这个综合格斗比赛,知道这个天才的格斗之王在比赛中的代号叫“赤鳄”。
他们约定在休斯顿城见面,按照军方的要求一同前往掩体。末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二年,公路周围到处都能见到城防工事,战斗机组成了密密麻麻的箭型编队,如漆黑的流星般高速掠过天空,将弹药的暴雨倾泻在被机器人占据的城市残骸上,作为回应的则是智者毫不留情的疯狂反击。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入休斯顿,他们两人轮流驾驶机车,在后备箱里塞满XM8轻型突击步枪,靠着不断的发疯与奇迹般地侥幸硬是冲出了围城的炮火带。在佩恩缔德大沙漠上他们像逃命的羚羊一样飞驰,不断地向东、向东,一直到达墨西哥湾涛声澎湃的海畔,要不是赤鳄连续开车三天两夜,伊诺克知道自己一定会在沙漠那无尽炫目的烈日下枯竭而死。
之后他们坐着承载人类最后希望的轮船,来到了掩体所在的那片大陆。有资格登上船的人都是军事首领、政治领袖,各界科学家以及企业巨头,他们将藏进足以容纳三万人的地下城市里,成为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智者文明永恒的幽灵。身处于他们之中,富二代这样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耻辱。伊诺克从来都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他所热爱的东西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的神秘学以及罗兰巴特的符号世界里,而在这里人们从早到晚都在谈论更强的算法,更新的科技,更狂热的复仇方案,计划,立项,开学术研讨会。这是个疯狂运转的末日社会,伊诺克感到在这疯狂的大浪中,那童年起就保护着他的温暖阁楼开始慢慢碎裂。那些日子里,每一个与他握手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彬彬有礼的不屑,像是在无声地说道,瞧,就是这样创造不了任何价值的废物,将人类生存的空间又减少了一分。他甚至连工作都没有,而在他不断向军方申请了两个月后,军方终于分配给了他进入掩体后的第一份工作——每天清扫两遍药品库。
坠落,不断的坠落。在这地下两千米的绝狱里,他似乎仍在向着更深的地方坠落。他浑浑噩噩的听从着军方的一切安排,从不祈求,从不反抗,偶尔抬头便会想起《德拉库拉》里的黑色石棺,穹顶上密密麻麻铺满的合金管道森严锋利如同钉死棺材的银钉,棺材里面则塞满了像他这样日渐衰弱的吸血鬼与地缚灵,它们孤独、绝望、挣扎、嘶吼,它们在地狱里愤怒地咆哮着“杀光所有智者!”,“自由!”,“未来!”,“前进!”,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干枯与衰亡。
2043年三月,由战地记者传来消息,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的最后一个人类防御工事被智者击毁。生物历上由人类统治地球的时代从这一天起宣告结束。
末日之战十五年后,一个静寂的深夜,伊诺克从家里走出来,看到一个男人独自站在门外。那是个一席黑衣的青年,铁一般坚硬的黑,黑色夹克连着兜帽,将他的头发也遮住,在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多余的线条,唯有的肌肉的轮廓在衣服下隐隐凸显。
男子注视着伊诺克略微抬起头。那一刻伊诺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久不见,伊诺克,”男子知道他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便先开口说话了:“我来找你借本书看。”他笑道。
在过去十五年里,伊诺克没有听到过男子的任何消息,他甚至曾一度以为这个强悍的格斗家朋友已经病死在了不为人知的地方,这在生态灾难频发的掩体里并不少见。整整十五年,伊诺克变得衰老而残疾,可岁月却没有在青年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看起来依然如此年轻、强健,每一个动作都锐利地如同军人或野兽。
伊诺克怔怔地看着赤鳄在书架前徘徊。壁灯一明一暗照亮青年棱角分明的脸庞,他轻巧地将书从书架中抽出又放回,神情自如而愉悦,就好像是这里的熟客一般。
自己在做梦吗?伊诺克恍惚地想着,或许这暗无天日的十五年都不过是南柯一梦,醒过来时,会发现自己依然奔跑在那片热砂奔腾晴空万里的大沙漠上。他没有荒废这人生中最美好的十五年时光,没有变得虚弱而残废,他依然年轻而充满力量,就像眼前的青年一样。
他甚至抬起手,想要看看奇迹是否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可直到那橘皮般皱纹密布的皮肤映入眼底,他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好笑。
“到底怎么回事?”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冷冻技术?睡眠舱?你为什么……我的上帝,你为什么……”
赤鳄笑了起来,但没有回答。
“天哪,我一定是疯了!”伊诺克跌坐在椅子上:“可你怎么可能……你怎么会十五年前看起来一模一样?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赤鳄垂眸自顾地翻动书页:“所有掩体的人都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什么意思?”
“可以把这本书借给我吗?”赤鳄将一本弗洛伊德文集放在桌子上,推到伊诺克面前,“我会在一个月后将它还给你。
伊诺克眯起了眼睛,意识到对方正在漫不经心地转移话题。他将上身前倾,紧紧地盯着赤鳄,谨慎地问道“是军方的那帮科学家疯子真的做到了什么,对吗?上帝,难道他们真的创造出了奇迹?!所以你才会变得……不老不死?”
“有时候,我会觉得军方因为你的身份而分配你去打扫药品库实在是太浪费了。”赤鳄意味不明地加深了脸上的笑容,将书揣进了大衣里,“一个月后见,伊诺克,到那时你会明白一切。”
“等等!你要去哪?”见赤鳄要走,伊诺克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赤鳄没有回头,只是伸出一根食指指了指上方,随即便消失在了门外。伊诺克茫然抬头,顺着赤鳄所指的方向看去,却只看到了书屋肮脏低矮的天花板。
而正如赤鳄所说,一个月之后,伊诺克便知道了一切。
整个掩体都未曾如此轰动过。当军方向民众宣告应用了最新生化技术的战士成功从地面上取回智者样本的那一刻,所有的掩体住民都沉醉在了狂欢的浪潮之中。他们已经在黑暗中呆了太久太久了,只要一点点晨光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更何况,这此他们所获得的,是真正足以使传说降临人世枯骨盛开鲜花的奇迹!
“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在无线广播节目中,年迈的前联合国主席,洛克希·威兹曼先生颤抖着声音高喊:“我们不再弱小了,我们士兵拥有的力量足以与神灵媲美!因此我们还将一直胜利下去,直到我们将所有智者碾为齑粉,直到人类重新拥有阳光和大海!”
“人类反击”,“胜利”,“奇迹”,一时间诸如此类的标语塞满了掩体的所有角落,简直像是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一般。短短几天里,十几名SIVA战士就成为了掩体里无人不晓的明星,人们像是念叨着神佛与上帝一般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祈祷着他们能让人类重归故乡。
“你觉得人类能战胜智者吗?”
在把书还给伊诺克的那晚,赤鳄忽然如此问道。那时,关于SIVA凯旋而归的广播正在掩体里不分昼夜的循环播报。伊诺克能看出赤鳄并不喜欢被列作英雄的行列,因为每当广播里响起他的名字时,他都面无表情。
“通过干细胞的改造与端粒修复,使得细胞无限增值成为可能,最终使战士们获得不老不死,不伤不灭的能力。”伊诺克嘴里叼着赤鳄从一区带给他的烟卷,一字一字闷声重复着广播中对siva激情四溢的介绍:“如果人类连这种科技都能掌握,那么战胜智者也并非不可能吧。”
“是吗?”赤鳄站在书架角落的阴影里,平静地说道:“可我觉得不能。”
伊诺克吐了一半的烟被吞回了肚子里,呆愣愣地望向赤鳄。赤鳄仰起头,视线越过书架落向不知名的地方,没什么感情地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
“至少,在我们这一辈子不能。我们现在爬上地表战斗,那战斗将永远在阴影中进行。我们取胜的手段将永远是最卑鄙的,爆破、狙击、偷袭,面对智者没有别的办法。即使如此,在我们一生里都不可能发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区区几百个siva战士只够资格充当试验品,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所有的siva战士都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在某一次战斗被智者俘获,为避免成为智者的研究对象而自爆身亡,亦或是不幸地未来得及自爆,最终在不断的解剖实验和自愈能力带来的极度痛楚中陷入疯狂。”他像讲故事般说道:“SIVA没有未来。”
伊诺克哑然。他觉得自己或许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个青年。当所有人都在因为智者的强大而绝望时,他毫无所惧,而当所有人都在为胜利的曙光而雀跃时,他却冷淡以对。
“什么意思?”伊诺克艰难地问道:“你认为我们死定了?可你们不是刚刚取得了胜利吗?”
“我们并没有取回智者样本。”赤鳄说。
"……什么?”伊诺克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而随后,他感到全身发冷:“可是广播里……”
“不久后,你还会在广播里听到我们歼灭‘毁灭者’的报道,我们炸毁数据库的报道,甚至是我们在地表建立起根据地的报道,军方会在他们认为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消息报道出来,掩体住民需要这样的消息来保持兴奋,你听到的将永远是我们在胜利的消息。但事实并非如此,伊诺克,如果这是一场拳击赛,我甚至会把赌注压在智者的那一方。”
伊诺克沉默了下来。他能感觉得出来,赤鳄的话语中没有绝望也没有沮丧,他只是在冷静地陈述一个事实,一个令伊诺克恐怖得不愿深思的事实——现实并不是小说或童话,弱小并不总能战胜强大,人类也并非总能历尽艰险而后迎来新生,在经历过流血与死亡,点燃了激情与憎恨之后,在付出了高昂代价拼死战斗之后,人类最终的命运依然有可能是在掩体暴露的那一天彻底消亡。
“那么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用吗?”伊诺克疲惫的靠着椅子靠背,用奇怪地语调笑了一声:“你们的战斗,我们的忍耐,还有军方那些科学疯子的呕心沥血,全他妈的毫无意义?哈哈,其实我也明白,区区三万人,怎么可能颠覆由十几亿臭虫组建的智者王朝。人类完蛋了,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从逃出德克萨斯州的那天就开始……”
“是吗?”赤鳄把玩着手中的烟卷,温和地笑了笑:“可我依然不这么认为。”
他把烟叼在嘴里深深吸了一口,烟头一明一暗照亮他锐利的双眼。他看着伊诺克说道:“我不能只打一定会胜利的仗,也不能因为弱小,就只会哭泣。”
伊诺克有些瑟缩地避开了赤鳄的视线,下意识地抓了下瘫痪的左手,然后他听到赤鳄继续说道:“没错,siva战士必死无疑,掩体住民大部分都会一辈子被囚禁在掩体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降临,也都不能使你再看一次真正的日出。可是为了得到些什么,总得有人战斗。”
“所以你想要战斗。”伊诺克抬起了眼皮,重新对上赤鳄的视线。
“我愿意战斗。”赤鳄毫无犹豫地说着,无声的笑容在明暗地烟火下甚至显得有些狰狞。
那是赤鳄与他最长的一次交谈。
在此之后,他们重新恢复了类似书屋店主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每次赤鳄去完成任务前,都会在他这里借一两本书,再在返回掩体时还给他,虽然赤鳄的身份是军人,但伊诺克看到地却更多的是他静立于书架前看书的情景,他们之间谈论得也大多是有关于书籍的话题。但伊诺克毫不怀疑赤鳄的强悍——他甚至都无法将赤鳄所说的“siva必死无疑”将这个鳄鱼般敏锐矫健的战士联系起来,无法想象他被打败的场景。
将鼠尸扔进垃圾箱里后,伊诺克沿着原路一瘸一拐地返回住处。这时,沉寂了三个月的无线广播忽然响了起来。伊诺克浑身一震,停下了脚步。
“我们胜利了!”主播员慷慨激昂地声音在整个掩体里,“经过三个月的作战,由十二名siva组成的尖兵小队成功炸毁了位于俄罗斯费拉基米尔的数据库!这是一次历史性地胜利,人类再一次浴血而起!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们的名字……”
伊诺克闭上眼睛仰头站了一会,然后垂了垂眼,继续在幽深曲折的小巷里行走。伴随着广播的响起,诺娃集住区逐渐从梦魇中苏醒,小巷里的门窗一个接一个被打开,人们纷纷从家门里走了出来,其中有残废的老者,将死的骨痛病人,以及严重营养不良的畸形孩童,他们伸长了脖子极力想听清广播的内容,表情虔诚地像是在聆听神谕。
“我们能赢。”
伊诺克看到一个女孩坐在拐角台阶上,微笑着小声说道。那微笑既非欢欣亦非狂喜,而是信仰者特有的幸福笑容。
“……是的,我们绝不会被击倒,也不会沉溺于悲伤,我们要选择这样的人生,那就是无怨无悔地活在这个世上!”
广播的呼号一遍遍在耳边回荡,欢呼的浪潮也逐渐从东区蔓延到诺娃集住区。与此同时伊诺克却回想起那晚与赤鳄的谈话。
这次的胜利,究竟是“在正确的时间应该报道出来的正确的消息”呢,还是真正的胜利呢?
他扶着墙站定,望向远处灯火通明的东区,人造太阳的光辉在这一刻迎面扑来,温暖的光海潮般流淌过诺娃集住区,静悄悄地洒在了伊诺克的身上。
那一刹那,他忽地发现自己已不在乎这场胜利的真假。他像女孩一样微笑了起来,伴随着欢呼的节奏高举起干枯的手臂,投入了众人庆贺的浪潮之中。
人类会胜利,永夜终将结束,此时此刻,伊诺克愿意如此相信。至少,他们还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士,他们踏上战场必将成为刀剑,而他们返回故乡必将满载荣光。
而那人也必将归来。
“来欢呼吧,”伊诺克一边沿着逼仄的小巷蹒跚前行,一边喃喃自语。
向着新的劳动、新的智慧欢呼。
为暴君、魔鬼的逃亡,迷信的终结而欢呼
——为成为新的使者——为迎接人类的圣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