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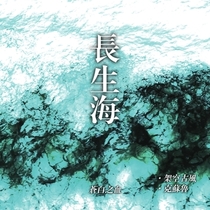
本来只是一个文手的简单角色portrait,交代一下和爸的关系基调,没想到写得太磨蹭了反而意外地搭上了主线?
写不出来了,爽朗地飞快先斩到这里,亲爱的同胞们,等我下章正式的主线再来挨个啵儿嘿~
=======
木棍人今天好像不怎么高兴。她想,趴在她喜欢的那块人工礁石上往外看,金红色的尾鳍浸在水里,慢悠悠地摇晃,像一块随着水波轻柔飘拂的丝绸。
不管怎么说,木棍人平时也没有特别高兴过的样子,所以不如说他一如既往地不怎么高兴。
木棍人是她给那个人类起的外号,他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不过露莎卡不怎么在乎:人类的名字总是发音奇怪而且冗长,况且他也没问过她的名字。事实上,他基本上不怎么跟她说话——倒不是说露莎卡对此有什么意见,反正她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一个安静的人类远好过之前她还住在湖里时那些聒噪的、时不时把她拖到浅水处做这样那样检查的家伙。不过有的时候,她还是会对自己的人类邻居生出一些好奇,比如现在。
露莎卡从礁石边无声地沉入池水。清凉的水流擦过脸侧的鳃,带来舒适而轻微的痒,她灵巧地摆动身躯,滑行到水池边缘,然后把头探出水面。
哗啦的水声没有惊动木棍人,他依旧安稳地坐在他惯常的位置——临近水池边的茶桌旁。帮助他走路的那根木棍靠在桌边,他正在读一封信。
一封漂亮的信。浅绿色的厚实信纸带着隐约的暗纹,像是从水底向上看时粼粼的波光。纸边裁成别致优雅的弧形,四角还印上了装饰的金边,和信封上的烫金花体字一起,在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的阳光底下闪闪发光。
“那是什么?”
她问。听在人类的耳朵里就像是一声啁啾的鸟儿咕哝,不过在安静的温室里也足够引起读信人的注意。
“下午好。”他说,从信纸上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
木棍人有一双沉郁的蓝眼睛,像天气不够晴朗时的冬季天空。但是冬天已经过去好一阵子了,从高高的玻璃穹顶洒落下来的日光逐渐变长,在她居住的池子里,碧绿的荇草疯狂地生长,她几乎听得见它们在她睡梦中拼命伸长的声音。就连水面上的空气里也浸润着一种湿暖的,叫人舒服的水气,这让她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水面之外,去看看她的人类邻居今天给她带来了什么新鲜玩意。
露莎卡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叫做“下午好”的东西。人类有很多亮闪闪的漂亮小东西,她喜欢趁木棍人不备从他的茶碟上偷走银色的茶勺,在她靠着睡觉的巨大假贝壳底下她藏了好几把。木棍人也许没有发现,也许他发现了但并不在意,因为第二天茶碟上总会出现一把新的茶勺,偶尔还有一两块或许是被他遗忘在那里的焦糖小饼干。
她浮得更高一些,把整个上半身都露出水面。溅出来的水泼湿了水池旁边的地面,不过木棍人只是习以为常般地缩了缩脚踝,让皮鞋避开浸泡在水里的命运,把目光又移回到信件上。露莎卡伸长手臂,带蹼的指尖攀上洁白的棉质桌布,留下湿漉漉的斑驳水痕。
“会弄湿的。”在她够着那个绿色的信封之前,木棍人不轻不重地说,稍微把她的目标挪出她手指碰得到的距离。露莎卡不满地冲他龇龇牙,他也没有打算要松手的意思,她生气地甩动尾鳍拍打水面,搅出更多的水花溅到水池外面,可木棍人只是把信纸举得更高,在半空中把信纸折了折,放回信封,塞进外套的口袋里。
真讨厌。露莎卡在池边兜了个小小的圈子,气呼呼地瞪他。她记得上一回她想看看他脖子上的漂亮挂坠盒时,木棍人也不许她碰,小气的人类。
小气的人类和她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轻轻叹口气,移开视线,拿起放在旁边的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露莎卡趴在水池边缘,不满地摇晃尾巴,从喉咙里发出人类听不明白的短促音节。木棍人这回并没有接茬,只是充耳不闻似地继续翻阅他的报纸,不过露莎卡发现他的手肘似乎支得有点太靠外,以至于从报纸底下把那只盛着切片草莓蛋糕的洁白瓷碟顶了出去,不近不远,就刚好在她伸手够得到的位置上。
好机会!
露莎卡俯低身子,警惕地看向木棍人的方向,后者被手里的报纸挡了个结实,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样子。她像只准备狩猎的猫一样绷紧后背,随后闪电般伸出手去,抓起一块草莓蛋糕,迅速回过身,摆动鱼尾,以一种像水獭似的古怪却灵巧的姿势仰面游向水池中央——她已经充分吸取了把偷来的糖罐带到水下时的教训,知道浸湿的蛋糕也不会好吃的。
她在水深足以让她伸直身体的地方停下来,把护在胸前的草莓蛋糕小心举在水面之外,向着木棍人的方向示威般地晃晃,发出像是得意又像是炫耀的声音,然后把蛋糕整块塞进嘴里,像过冬的仓鼠似地把脸颊撑得鼓鼓囊囊,一头扎进水里。重新浮上水面的时候她已经在水池另一头的人工礁石边,手里拿着玛莎上周找出来给她的旧发梳,一边颠来倒去地摆弄,一边忙碌地咀嚼嘴里的蛋糕。
露莎卡只是一条无忧无虑的小人鱼,她不会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木棍人在她游到远处后就放下了报纸,凝视着她的身影,看着她快乐地用除了正确用途以外的各种方式探索发梳的用法,看了很久。她不知道那张被她飞快抛诸脑后的漂亮邀请函上,人类用最优雅、得体、矜持的词汇友善地提醒这封信笺的收件人,他们所租借的人鱼租约即将到期,根据约定,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内,将不再保有与这条特定个体相伴的权利。她不知道作为一件昂贵的商品,她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自己,甚至并不取决于那些友善的、愿意纵容她任性的租客。她不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春天与之前的四个春天会有些怎样的不同。
她尚且还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