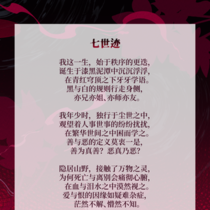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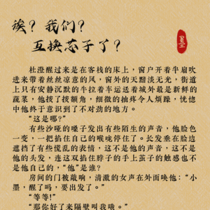
巫山梦企存档
——————
R预警
净衣诀也好,清尘术也罢,都不及一汪清池来的舒服,虞郁瑜褪去衣衫,足尖轻点水面,试了试这冰凉澄澈的水之后一步步走进了池水之中。
寒意没过小腿、没过小腹、最后停在红樱上,藕臂撩起水珠洒在肩头上,那银珠顺着肩头滚落,溅起荡漾涟漪。
幽幽碧波吻着白皙凝脂,虞郁瑜嫌这日头晒,游了游躲进了被树荫遮蔽的巨石后,莲叶丛遮住了她一大半身影,恍恍惚惚见那柔顺粉发在其中像是待放的荷花包。
她靠着被冲刷光滑的石头伸出指尖玩着水,淡翠绿色的灵气控着一颗一颗小水珠浮空然后注入进去像是水种极佳的青白和田玉,绕在手腕上衬得雪肤更加莹白透亮。
哗哗水声响起惊动了虞郁瑜,她眼神一凛抱着肩头钻入水中,只露出眼睛上方看着来人。
那人高大壮硕,黑发披散在肩头,堪堪用红绳扎了个有些凌乱又有些可爱的麻花辫,衣衫大开敞露着雄健的肌肉,手上却温柔托着一只雪白小鸟,待他踏入水中后那大掌像稳健岛屿一样让它饮水嬉戏。
好一会后小鸟从他手心里飞走掠过了虞郁瑜所在的那片莲叶时他才看到水种还有其他人。
虞郁瑜这样委实狼狈,眼睫颤颤抖落几滴水珠,粉的眸子,慌乱中浸水的长发像是水藻一样粘连在脸上,丝丝缕缕如细蛇般爬着,衬得她好似水中女鬼。
她也知道在这秘境里区区金丹算不了什么,更别说新的规则随时都可能会让女修被抓去做了肉鼎稳固修为,尤其是她现在身无寸缕的样子……
即使花妖并无人类的羞耻心,可是她也不想被难看的讨厌的人接触。
眼前的男人不一样,脸庞上几乎横穿的伤疤也只是在男人味上增添了些许凶戾,明明看着让人感觉不好接触,可是送飞小鸟时嘴角含着难以察觉的笑又显得他格外诱人。
虞郁瑜视线从他手臂上游走到胸口,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是心脏在收紧还是小腹在收紧,直到他转过身去慌慌张张说着话才发现那黑发间若隐若现的耳朵都红透了。
“冒犯姑娘了!我乃湘池,路过这里无意撞见……呃……”
湘池站在水中背对着虞郁瑜,先前那一瞥让他仿佛落到了水中的芙蓉花,重瓣层层的粉花浸着水娇弱又惊艳,他闭着眼还能看见方才那粉白浑圆的兔儿在池水里游。
半晌没听见身后的回复,只闻水声荡漾,然后娇柔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池公子……转过来说话吧……”
待他转过去时,虞郁瑜寸缕不着地站在他眼前,只能没过他腿根的水深淹过了她的小腹,饱满的胸部被长发遮了些,绯红茱萸若隐若现,湘池瞳孔震动了几下,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冰凉的手牵住。
纤长的手指勾住了粗壮有力的手,湘池看见虞郁瑜依偎上来,温软的胸脯贴在他胸腹上。
“冷……”
她冷,可他热。
香甜的气息蜿蜒盘旋,不管是怀里娇小的人还是胸腹贴着的玉体都让湘池面红耳赤浑身燥热,只要虞郁瑜不安分地动一动,那熟透软烂的蜜桃在身上滚一滚,他就感觉下腹绷紧,不受控制的感觉一点点侵占全身,他好想落荒而逃,可是又紧张地迈不开腿。
虞郁瑜贴着这燥热身躯,舒服得很,一冷一热绕着身体像是冰火两重天一样,可是丝毫不难受,甚至还能感受到有逐渐狰狞的东西抵着自己小腹。
她吻着湘池的胸膛,感受着快跃出来的心跳,嫣然一笑伸手探进裤腰里,抓住了躁动不安的巨根。
揉捏了几下如意听见忍耐的闷哼之后把湘池轻轻推到石头上,然后压在他双腿之间释放了气势汹汹的那一处。
湘池想拦,可是已经完全勃发的阴茎随着裤子被扯下之后猛地弹了出来,在虞郁瑜眼前晃了两下。
她亲了一口,眼角弯弯说:“都怪瑜儿让池公子这么难受,让我会帮池公子处理好的~”
粉嫩的舌尖顺着虬结的青筋向上舔舐着硬挺的柱身,等到顶端时又用小嘴含住,湿热柔软的包裹感和吮吸的抽空感让湘池抓住了虞郁瑜的肩膀,他是推也不是压也不是。
虞郁瑜挑着眼看他,把那巨物吐出来时还牵着淫靡的银丝,她勾唇笑笑,抬手把散乱的粉发别到耳后又舔了上去。
这一次更慢更刻意,每一次吻上舔上都看一眼满面通红的湘池。
轻吮根部时他视线游走阴茎微颤敲在虞郁瑜鼻尖,张嘴叼住柱身齿尖刮擦时他闭眼咬唇下颚绷出凌厉的线条,含住顶端时带着茧子和刺鳞的手僵硬地想把她往下压。
在腹肌沟壑上打着圈的柔夷感受到紧绷的感觉后换了个姿势伏在了那窄臀两侧,然后……张嘴用舌头垫着把硕大的阴茎吞了下去。
婉转的低吟断了片,只有困难的呜咽轻轻传来。
吞吐、舔舐、揉捏、套弄,再被舌尖抵着冒出汁液的顶端,温热的口腔和滑腻的舌头让他流连忘返意识溃散,随着手指拨弄着精囊,湘池再也忍不住了,高扬起了头压着虞郁瑜一挺腰抵进了喉咙深处。
浓厚的精液喷涌而出,只差一点就她就要吞不下了,趴在湘池身上好半天才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罪魁祸首慌慌张张支支吾吾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只好揽着虞郁瑜逐渐下滑的身子掂了掂放在自己身上。
虞郁瑜终于仰起头看他,嘴角还挂着一点精丝,整个人慵懒又淫靡,仿佛之前落水的芙蓉被碾出汁儿一样荼靡。
她窝在湘池的怀里换了个方向,鞠一捧池水擦了擦嘴角,柔软的臀部压在坚硬的大腿上,沟壑蹭了蹭刚刚才发泄的东西,然后掰着那快比自己腰粗的胳膊环在了腹部上,往后靠着贴在那纹理分明的肌肉上。
“阿池~”
被轻轻柔唤着的湘池低头看着怀里的小花妖,虞郁瑜只披着长发,沾了水贴在玲珑有致的身躯上,胸前的桃儿没有衣物的遮蔽更显得挺翘白软,还有一丝绵软力量压在他的手臂上。
她黏黏糊糊又叫了几声,摇着腰作得身下压着的阴茎又微微勃起,这才侧过头勾着湘池的下巴说:“阿池公子还想不想玩更舒服的呀?”
巫山梦企存档
——————
R预警
虞郁瑜也免不了馋那福地洞天的灵气和秘境中的宝物,她本就贪玩冒进,只盼着有一丝好运能夺得点有助修炼的天材地宝,金丹期的花妖已经算是不错的天赋,可是她控制不了欲,只想着更进一步越过那个稍稍有些阻塞的坎。
结果这方手上还握着千年莲,妖却被传送到不知何处了,手腕翻转那妖莲被她收进镯子里,端的是娉娉袅袅媚眼如丝,一妖在这宽阔场地里找了棵大树背着阴观察着眼前的宏伟宗门也观察着其他的修士。
人声沸沸,她们从那俊秀女子的口中倒是得知,这已不是鸿渊秘境了,什么天材地宝奇遇险境都不复存,只有她们这些被压制的修士们魔尊的养分。
“周公之礼?呵……有意思……”她吐出丁香小舌舔了舔指尖,摘取千年莲的时候掐断那莲茎时沾上了一些汁液,那汁液涩中带甜,吞噬之后身上微微发热,令人痴迷。
明眸掠过场中一位又一位,她方才听得很清楚,若是不行这周公之礼便是会被吞噬修为,本来已经不如元婴,她可不想跌到炼气最后死在这里,再说那事也不令人烦躁,反而更有乐子了,于是她足尖一点朝着先前看过的背影掠去。
那抹青色身影她在“鸿渊秘境”时路过过,这男子面容俊俏挂着温和笑意,周身平和如暖玉,看不出修为却也不自傲或自谦,本来以为能坐享渔翁之利的虞郁瑜反而看到他笑笑把一株灵草让给了他人,如此好说话的男子必然也会照顾照顾柔弱女修对吧。
莫说一度春风,至少让她尝尝那那人淡然如古木的木灵气也好,真要有什么事跑就得了,这还能缺了植物不成?
她飞到男人前方,装着柔柔弱弱跌在一片开着婆婆纳的草丛里,等掌心的植物摇摆着告诉她那人已来了的时候开始如泣如诉哭起来。
“嘤……这地方……我会死在这儿的吧……”
她给身子扭出好看的曲线摆在男人眼前,抬手接了滴眼泪,那泪水圆滚滚留在鲜红的指甲上映着色像极了红宝石,又被她随手甩开落在男人鞋前。
只听见虞郁瑜用婉转悠扬的声音唤着他:“公子~~”
忏岳笙倒是先前就发现了这绕到自己前面的女人,本以为会做什么张牙舞爪或着半路劫道的事情,没想到倒是一摔摔在自己眼前,这是要讹上他吗?
他不动声色微微挑着眉,笑得云淡风轻,微微弯下腰如了她的意伸出手,“这位仙子是受伤了吗?需要在下帮助吗?”
虞郁瑜搭上那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莹白和深色露出极为刺眼的反差,她借着忏岳笙的力站起来,又哎呦一声崴着脚弱风扶柳似的扑在了男人的胸口上。
“仙子?”
“公子~人家站不稳了……”
作乱的小手轻抚上忏岳笙的胸口,食指勾住一缕绿发打着卷儿,小指刻意又轻柔地一下一下勾着他胸口的流苏。
她仰起头看着忏岳笙,粉色的眼睛刚哭过湿湿润润看着他,眼尾还留着比桃花妆更娇艳的红。
“您这么好的人不会见我灵气枯竭而死的对吧~”
他当然不会,这送上门的小花妖还以为他是什么良善之人,拐着弯勾引他一同双修,她身上甜腻的花香和清新的木灵根实在是个不错的开胃小菜,虽然他也很想事实在秘境里究竟修为会被如何压制吞噬,可是能抑制一会儿让他多些时间探索也不错。
于是那方才还护着人揽着腰的手沿着柔韧的细腰往上滑,撩开满背的粉发摸上了虞郁瑜的脖颈。
弱点被人抚上让虞郁瑜颤栗了一瞬,她装作无知环抱住了忏岳笙的腰,抬头把脆弱的喉咙露在忏岳笙眼前,幼猫般的叮咛声又绵又长却不会让人觉得刻意做作,反而伴着那由内自外散发的幽香更好地撩拨起情欲。
忏岳笙屈指拂过虞郁瑜的后颈,丝绸质地的手套带着丝丝凉意从薄纱外衫盖不住的圆润肩头一路向上,最后勾起了虞郁瑜下巴,半强迫地让她仰着侧过头去。
“仙子就这么想行这事儿?”
她已经发现了这男人和看到的并不一样,故作柔弱地垂下眼帘,鸦羽般的睫毛颤了颤演一出期待又害怕。忏岳笙早识破了她的小心机,配合着虞郁瑜单手掐着她的脸,双指陷入白嫩软肉里,笑意温柔,只是这笑不达眼底,另一只手顺着腰间往下摸去。
这手游走过浑圆挺翘的臀又顺着腿根往下探,等把粉色的襦裙撩起来之后才发现虞郁瑜的脚腕上还挂着个精细的小铃铛,只不过之前她除了站起来就是倚着忏岳笙,没发出一丝声音。
这会儿被撩起裙子,骨节分明的瘦长指节探入双腿之间,丝绸在磨蹭中已经沾染上湿润的温热,每一次深入都会让虞郁瑜被戒指剐蹭地呻吟起来。
风儿每一次吹拂都让二人的粉绿发丝交缠在一起,忏岳笙戏谑地吻上虞郁瑜鲜红的泪痣,每一次动情都让这泪痣被浇灌得更加鲜艳,看起来无比诱人可口。
侵入身体的手指抬向更深的地方,他笑得恶意,抽出手时故意用戒指刮了粉贝中的珍珠,坚硬的东西触碰上去惹得虞郁瑜淫叫连连,花汁顺着双腿低落在草地上。
舌尖舔过眼角滑落的生理泪水舔过嫣红的泪痣,忏岳笙引着虞郁瑜把手搭在自己腰带上让她解开。
衣带被柔夷胡乱拆开,还未层层剥开时就有小手按上那已经勃发的阴茎,手指挑开已经松垮的外袍和里衣,虞郁瑜握上了那灼热的东西。
柔弱无骨的手一松一紧缓慢套弄着,不上不下的感觉让忏岳笙笑出声,他埋进虞郁瑜肩窝嗅着那幽幽花香抱起了她一条腿,脚腕上的铃铛叮铃作响。
失重感让虞郁瑜小声惊呼一下然后松开手紧紧攀上了忏岳笙的肩膀,这一抱让二人下身更为贴近,滚烫的阴茎贴着湿润的穴口,只要轻轻一顶就能长驱直入挤进那发烫的软肉里。
可是忏岳笙故意玩弄她,一次又一次揽着虞郁瑜贴近都只是压着滑腻的小穴蹭着,听着耳边鼻息的闷哼和背后抓着衣衫加重的力气勾起了嘴角。
先是尖端挤进小穴里,站姿让穴道更加紧致拥挤,奋力挤进去后他到不急着动,勾的动情的虞郁瑜轻晃细腰,连被抱起的那条腿都晃荡着,让铃铛淫靡作响。
等虞郁瑜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抱着他吻上下颌的时候忏岳笙微微侧开脸躲过这一吻,虞郁瑜还没来得及生气就被坚硬炽热的阴茎贯穿。
“啊!”
舒爽浪荡的声音先响起,随后是粗重的呼吸和暧昧的水声。
虞郁瑜踮着脚配合着忏岳笙,每一次肉壁被贯穿都好像从尾椎带着电流直冲大脑,她的眼神开始迷离,吞吐也变得更积极,好似要榨干男人似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又变换了几次姿势,最后虞郁瑜是匍匐在花丛中的,襦裙被体液和精斑弄得深一块浅一块,堪堪堆在臀上,露出被蹂躏得鲜红的小穴,随着每次呼吸还会挤出点滴白浊。
她缓了好一会才微微撑起身子,凌乱的粉裙被小手扯了扯盖住交叠的双腿,又撩开因为汗水粘在脸上的发丝,她就这么贴着被碾坏的花,像是开败了的芍药一样糜烂缭乱,眼尾勾着高高在上站着整理衣服的忏岳笙。
“公子……可真是正人君子啊~”
忏岳笙已经系好了腰带,如果不是下摆上一些暧昧的水渍和衣褶倒像是从未发生什么一样风光月霁似的,他抚平衣褶的手一顿,莞尔一笑说:“多谢仙子投怀送抱了。”
3.
高冷系统再也不给我透露岑轩墨有没有对象了,它不理我了。
我,余钰榆,新世纪好青年,团费每次都交,同学之间和睦相处,尊老爱幼,无不良嗜好,名校学子,成绩优异,年级第一,母胎单身的优质女青年为什么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
岑轩墨打完电话心情很好的回来,我马上假装认真看剧本。
“小虞姐有什么搞不懂的地方吗?”
啊啊啊啊啊啊!他主动搭话了!我做错了什么!!
“咳,还好……”
“还没到我的戏,小虞姐演的杨小姐还是个蛮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对手戏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聊聊入戏会更轻松一点。”
岑轩墨把他的折叠椅拖过来,细心整理好自己衣摆坐下。
然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可恶!
这个男人绝对是个魔鬼,怎么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的真面目啊!他搭话绝对不怀好意!
“你说的对!我们熟悉起来了进入状态快就可以给罗导节约很多时间了。”想想任务,万一完成了呢?我举起剧本挡住他的视线,然后问他,“岑老师,我可以这样叫你吧?你那么有经验。”
“嗯,你不介意的话没问题。”
哇语气好冷。
“好!岑老师你看,就是这里,我看原作是雾因为四皇子和宁曦月关系越来越好开始忧虑还去院子里喝闷酒才被杨若若趁虚而入,然后雾又把杨若若抓起来送到四皇子面前。”
岑轩墨低着头认真看我指的地方,看起来像是邻家弟弟一样乖巧。
“然后呢?”
如果他说话温柔点就好了。
“你不觉得这里和他死士的身份有……呃……怎么说呢?”
“违和。”
“对!违和!死士应该一心一意为了主子,这里不管是作者还是编剧都是让雾失控,这也太小看他了!”
“小虞姐是不是还没看到原作后面只看了自己份的剧本?”
“是啊,怎么了?”
“这是殿下的计谋,我做什么事情都听命于殿下的。”岑轩墨说完把我的剧本卷起来轻抛到了我的怀里,“趁着最近还没拍小虞姐你的戏份,早点看完原作吧,狗血但是还挺好看的。”
怎么回事,现在演员拍ip改变剧都认认真真看原作的吗?原作那么狗血他怎么看的下去?原来他岑轩墨是这种女频爱好者?
岑轩墨被工作人员叫走了,接下来要准备他的戏份,四皇子和宁曦月一灯之缘聊完了,该送少女回家了。
噔噔噔噔!道具朋友小马出现了!
真马啊!罗导也太下血本了吧!晚上骑马不怕摔了男女主?
腹黑四皇子一身月白色,在星星点点灯火中温润如玉,柔和地看着宁曦月作势要扶她上马。
死士雾从树后走出来,单膝跪地双手手掌向上叠在一起,做马凳让宁曦月踩上去侧坐在马上。
然后他牵着缰绳让男女主一起并肩,三人两马在河边像是一幅画。
走出画框好一会罗导才喊咔。
还特别表扬了一下女主娇羞的表情演的不错,呵呵,帅哥服侍,怎么不娇羞。
哈!大师兄!还让人踩自己手,岑轩墨一定忍的很辛苦吧,脸臭了不少,喊咔马上鞠躬走了。
我看到了,他助理紧张兮兮的拿着一包湿巾给他擦手,是消毒湿巾哈哈哈哈!
半个晚上加上新人女主的调教根本不够拍几场戏的,大家忙忙碌碌今天就过去了。
接下来几天我只是认真在马扎上学大家怎么演戏,既然不能回去读书学习,那学演戏也行,我爱学习,学习爱我!
终于轮到我的恶毒女配戏份,系统虽然没说话但是感觉它兴奋了不少。
无非就是撒泼捣乱,这种事情难不倒我!
尚书之女杨若若刁蛮任性,大龄未嫁,花痴成性,京城有名的翩翩公子她都馋一嘴,一直到遇见了回京的四皇子。
她心许四皇子,饱读诗书风流倜傥才华过人的四皇子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宴会。
杨若若就借着尚书之女的身份去各种诗词会,文会宴,而且每次都赶着往上贴。
腹黑的四皇子欲拒还休,接受了杨若若的示好和撩拨,让尚书看到了一丝夺嫡中不一样的氛围,但是又对杨若若保持礼遇,让其他人挑不出刺也无法说他和杨若若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觉得有没有杨若若这个角色都无所谓,演的好累,要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男人摆出花痴的样子,还言听计从,真傻啊,反正也只是筹码而已。
所以每次拍戏的时候我都把对面人当成历史书,我最爱的历史书!看着历史书我能吃下三碗饭!
感谢虞郁瑜这张脸,虽然看起来很凶,非常适合赘婿歪嘴笑,但是我用看历史书的眼神看人的时候对方会被电到诶!
找了个有对手戏的配角演员试了下看着他的脸想象我在温柔翻着书,新鲜的油墨香味,柔顺的纸张,刻入人心的历史……
“小虞姐……别……别这样看着我了……”
面前的年轻男配脸红到了耳朵根,捂着半张脸往后退了好几步,支支吾吾不知道想说什么,最后跑开了。
鬼!到时候不会有工作人员爆料虞郁瑜片场欺负年轻人吧!我只想学学演戏!杨若若花痴戏码太多了啊!
此时看着娇羞跑远了的男配还在震惊的我根本没发现,不远处搭起来的室内棚里,岑轩墨正悄悄看着我,手指搭在唇上眯着眼睛若有所思……
“统哥……那个……金手指……有……”
“没有,宿主加油。”
今天也是很想回去的一天!
2.
我想读书,准确的说,我想回家读书,回我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家自己的身体。
但是统哥跟我说不做任务会死,我尝试了,然后我看到那个比虞郁瑜小几岁的男人用看物品的眼神看着我和虞郁瑜,我犹豫了,我觉得与其勾引他不如我去死,去社死,反正是虞郁瑜的脸。
围读剧本的时候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男主是当红演员得奖无数,我去厕所查的,温文尔雅,称得上一句陌上人如玉。
女主是新生代小花,貌美如花,第一次拍戏,资本真厚啊!
男二就是我和统哥的目标——岑轩墨。
我觉得男二选他真没错,罗导眼光杠杠滴,那个叫做雾的死士正适合他,反正他岑轩墨眼神会杀人,我真的有感觉下午开始片场气温挺冷的。
但是实在是不懂怎么死士是男二,死了怎么办?哦,男二也不容易死。
第一天围读就算比较快结束但是压不住人多也整了几个小时,虞郁瑜干净的剧本和其他配角那翻卷了也写满了人物小传的剧本完全比不上,呵呵,活该她信用卡欠债。
现在的问题是,我,普通文科女大学生,怎么演戏?
“统哥……我真的没有演戏金手指吗?”
“宿主,加油。”
“那你有没有什么商城可以让我买个演技教材包?”
“宿主,加油。”
“有没有什么能量控制我……”
“宿主!加油!”
“好嘛……我懂了……”
我彻底懂了,这个穿越就是个坑,我是填坑路上微不足道的一把土,丢进去啥也不是啥也不算啥也不管用。
罗导看起来真的很喜欢那个岑轩墨,不过想了想也是,年轻帅气有演技没架子,对谁都是笑着喊前辈,明明童星出道的他应该才是前辈,不拍他的时候也认真跟导演学习,比起其他几个懒懒散散的男三四五六七八来说这也太好了吧!
要不是他眼神杀我我真的会心动哦!
“那宿主就去勾引他。”
“不要,会死的。”
第一幕拍的戏是男女主对戏,为了让男主带动新人女主罗导废了大半天时间和无数带子才让他俩和睦相处。
是男主和女主和睦相处,我精通22年的人情世故告诉我,女主那个演员想左拥右抱,呵呵。
我没事干,赵姐也不让我回去,说反正没戏没综艺没通告,这部剧还挺重要说打算上星的,要我留这学习,剧组定的酒店更加无聊,所以我就搬了个没人坐的马扎和岑轩墨保持五米的距离开始看罗导拍戏。
夜景布置的超美,工作人员在小河下游拉了网子拦河灯,放满了的灯照得水面波光粼粼的,映得男女主那叫一个俊啊!
哦,简单说一下这幕戏的剧情,镇民放完河灯回家休息了,男主和死士才去放河灯,啧啧啧你说他俩没点别的关系我不信的,我新时代好青年积极向上不腐败的。
男主是不受宠的皇子,今年才回京城,夺嫡这种事情他表面上没打算,可是私底下喊死士干很多活,还挑拨兄弟妥妥两面派。
该挂路灯啊!他这要是当上皇帝了男二是做禁军统领呢还是做太监呢还是做太监呢?
面容和善一点也没生气哦不是,一点也没野心的男主这次放河灯遇到了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大家闺秀女主,然后一番闲聊被女主的天真无邪打动,和死士一起送女主回府。
就这样就看对眼了?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毕竟许白也是一伞之情,一灯之情也没事。
现在还没到岑轩墨呢,他换了古装老老实实坐在边上,衣摆还被他按布料顺序叠着提在手里没落泥地上。
我明白了,他强迫症加洁癖!
原作我还没看完,不知道雾最后是做统领呢还是做太监呢还是做太监呢?正当我悄悄看着他的时候,他转过来了。
岑轩墨看了我一眼,对着我勾勾嘴,然后歪着头说:“小虞姐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
唔!他装的好乖!居然喊虞郁瑜小虞姐!好懂啊这个24岁的狗男人,直接喊28的虞郁瑜做姐肯定会被讨厌的。
岑轩墨脸长得很干净,带点锐利的那种干净,剑眉星目,眼角略微上挑,显得表情潇洒又不羁,下巴上那颗小痣配上他古风的造型真的很适合!
“等等……统哥统哥!救命啊!!”
“宿主莫慌。”
“我慌啊,岑轩墨要走过来了,他会不会片场找茬甩我耳光说我多管闲事啊!”
“……”
岑轩墨站起来往我这边走,该死的,我赶紧捂住了我的嘴,我怕等下口水流出来。
这小子怎么长的?一米八几的身高穿这种纯黑劲装,手腕被护腕勒得紧紧的,显得指骨更突出,脖子也被裹在衣领里,肩头被假发马尾辫扫来扫去,整个人凶厉又禁欲。
然后他越过了我。哦,越过了我。
从我背后出现的助理手上接过了手机,走了几步去远一点的地方接电话。
“……”
“宿主,你不甘心是吗?”
“统哥,是不是朋友,住口吧”
系统没理我了,但是我感觉它看我出糗一定很愉快。
我往岑轩墨那边看过去,他接着电话看着拍戏场地,不知道在和谁打电话说什么,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岑轩墨靠着墙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悠闲轻松地和人聊着天,偶尔看看剧组,偶尔看看自己手腕上的袖剑,脸上是无比温柔的微笑。
温柔的微笑,真好看啊,这样看他一点也不凶了……嗯???等等!!!温柔???
“统哥统哥统哥统哥!!”
“我在。”
“岑轩墨是不是有对象?”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就说明可能会有,他这一脸怀春的表情绝对是有喜欢的人了!
“系统,你让我用虞郁瑜去勾……去吸引有喜欢的对象的人合适吗?”
“我是完美恶毒女配系统,任务还有拆散情侣。”
“别说了,失败的惩罚是怎么社死,我提前做一下准备。”
“宿主先加油吧。”
好家伙,强买强卖起来了!!我!很!生!气!
既然给大鱼上户口了,虽然没给小鱼搞出来但是也存一下几年前写的
——————
我叫虞郁瑜,准确的来说我并不是虞郁瑜,我只是一个穿越到了虞郁瑜身上的普通女大学生,余钰榆。
我这个穿越感觉有点问题,不只给了我女明星一样的外貌身材,还给了我一个叫做完美恶毒女配的系统,但是没有金手指。
到虞郁瑜身上的第一分钟,系统就告诉我说:“宿主,你穿越了,我是你的完美恶毒女配系统,在这个世界你的任务就有三个,1勾引男人。2拆散情侣。3涨粉。”
然后系统就不说话了。
该死的,我只想好好读书,我的全市第一,我的名校,我的美好未来,我只想读书。
1.
第二天我才知道,女明星一样的外貌身材是真的,因为虞郁瑜真的是个女明星,虽然是18线年纪大点的演员。可是也有好几万粉丝呢,居然没有僵尸粉!
好家伙,做明星还这么惨,涨粉那不是去买就好了!
当我打算联系虞郁瑜经纪人去交流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虞郁瑜的手机来了条消息。
赵姐:休息够了吗?剧组那边说找到合适男二了,要提前开拍,十分钟后我来接你。
我根本不会演戏怎么办??
正当我快速换衣服打算去个现场然后假装受伤回家躲开演戏这个事情的时候,高冷系统出来了。
“宿主如果想逃避的话会有惩罚。”
“什么惩罚?”
“社死。”
“啊??”
“……”高冷系统的沉默像是西北风一样凛冽,虽然不知道它应该在哪里,可是感觉好像在叹气一样,“社会性死亡,也就是会让你拍奇怪的视频发上网络让你的粉丝们看见。”
“不会……有那种视频吧?”
“会掉粉。”
“切。”
“粉丝清零,人物失败,宿主死亡。”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去拍!”
经纪人准时到公寓楼下,我换好虞郁瑜衣柜里我觉得挺简单方便的一身衣服钻进了车里。
“小鱼,你怎么想着穿这个?”
“啊?不行吗?那赵姐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换一下?”
牛仔裤和宽松T恤也不可以吗?可是别的衣服真的……怎么说……太……妖艳了吧?虞郁瑜怎么是这种审美?
“哦不是,只是突然觉得你今天想了事情,我们要直接去外景地,高跟鞋旗袍不方便的。”
赵姐指尖敲了敲方向盘,像是再做什么决定一样,然后开口继续说,“你这样挺不错的,看起来是用了点心,罗导应该会满意一点,别气他了,小心又丢工作。”
虞郁瑜不愧是被粉丝喊傻鱼的女人,二十好几了因为性格丢了工作,如果没这张看起来……
唉,现在是我的脸,不骂了,没这张好看明艳的脸那根本拿不到剧本,跪着都拿不到。
我在后座看着赵姐开车的侧脸,心想真是苦了她了,然后拿手机出来去搜虞郁瑜。
好家伙,这女人黑料盖都盖不住!
什么片场和工作人员暧昧,什么打狗仔,什么私联粉丝……哦女粉……嗯?她怎么女粉多啊?
我看了看车窗倒影里模模糊糊都能看得出漂亮、妖艳、销魂、妖娆妩媚的脸,这张脸不是应该讨女人厌吗?那种红颜祸水勾引人的类型,别说还有这个系统的任务……
系统……我想回家。
“宿主完成了任务就能回去。”
还想悄悄问下高冷系统怎么算完成,结果赵姐就停车说到了。
“我们不重要,所以要提前到,等下你老实点,能不找麻烦就不找麻烦,想想你的信用卡。”
“哦。”对,虞郁瑜是半个购物狂,她还要还卡……哈哈,是我替她还……更想回家了,想回去读书。
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收拾场地,罗导演还在休息室,其他主演还没到,小配角倒是到了一片,聚在一起三三两两聊天,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我一过去她们就会停止聊天,反正赵姐说了不要找麻烦那不说话就行了。
不知道是哪个工作人员带的小说,好像是这部剧的原作,反正没事干也没人拿,我随便看看。
古言确实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他爱她她爱他他爱她的故事,翻了几页之后看到我的角色出场,好家伙,怎么也是恶毒女配。
女主和男主产生误会,男主忠心耿耿的下属男二心许女主又不能说,喝闷酒的时候被“我”遇到了,“我”想借男二的身份爬到男主床上踩女主上位,结果还没来得及给男二下药就被男二发现了,直接抓到男主面前。
丢人啊!!!!哪里是恶毒女配,傻子女配吧!
男二是不是也有点毛病,“我”对你下药你抓我去你上司面前对峙干嘛?你难道是假爱女主真爱男主?
还没骂上几句,高冷系统冰冰凉凉说话了:“宿主,目标人物出现,请你在这部剧的拍摄时间内勾引男二的演员。”
“啊?我?勾引那个傻子的演员?”
“没错,岑轩墨,本次男二:雾,的扮演者。童星出道,大火之前回去读书,现在是表演系大四,成绩优秀,为人……”
“为人怎么样啊?喂喂?统哥?”高冷系统难得卡壳,“统哥你说话啊我紧张起来了!”
“为人,非常不和善。阴险腹黑小肚鸡肠特别记仇,而且一般有仇能报马上报,不能会惦记着找到机会报仇。”
“……我会死吗?”
高冷统哥难得露出一丝温柔,它轻轻对我说:“加油,宿主。”
我放弃了,试试就逝世,大不了社死,我可以的!嗯!虞郁瑜你也可以的!谢谢你的脸!
我顺着人群看过去,那个叫岑轩墨的人在和已经出来的罗导说话,人群时不时挡一下,看不太清脸,只看到黑色中分短发的高个子男生好像笑着,笑得还挺开朗。
“这也不像很凶的人啊。”我和统哥悄悄吐槽。
然后岑轩墨不知道在看什么,朝我这边看了过来,看清楚了,还是笑着的样子。
“哦豁,我完了,我看清他的脸了,统哥,我有没有看错?他是在看我吧?”
“宿主,你没有看错。”
岑轩墨笑归笑,但是看着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