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市公安局刑侦队会议室
副队长屈泽闯了进来,拉开百叶帘打开窗户放了点阳光进来,看着一屋子少说五天没洗澡的臭男人摆了摆手说:“能别抽了吗?再抽线索没找到我们高低得死上四五个兄弟,到时候法医部尸检清一水儿的报告是肺癌,挖开洗干净了都得说一句好黑。”
当下就有人不爽了,抬腿就扫到屈泽刚换的裤子上,留下灰扑扑的印记叫骂着:“老屈你懂个锤子,你家近你清高你还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抱了抱老婆慢悠悠来上班,还不记得给我们带早饭。”
“带带带,带个锤子带,特么的实习生买的你吃了吗就在这里放狗屁,不吃别浪费人小孩的钱,老子是昨晚上和岑队轮班的,全都这么熬你他妈是破案呢还是熬鹰呢?”
屈泽喊完这句稍微活跃一点的会议室又死气沉沉了。
十年来一直有个案子压在A市公安局的脑袋上——四一三连环虐杀案,受害人没有共同点,有男有女各种职业,都在壮年的年龄段,死因五花八门。
最简单的是十指被砍断塞进嘴里肢体被碎全部骨头摆成爱心的形状,最离谱的是被剁成小块塞进猪肉冷冻库的整猪肚子里,还是准备贩售的时候有员工从钩子上取下猪肉才发现里面掉出了不是内脏的东西。
真要说唯一的共同点让刑侦大队知道这是连续作案是因为从来没有通告说犯人有留纪念品的习惯所以不存在模仿作案,但是十年来近10桩人命案子里都有一张和尸体放在一起被血水泡到变色的拍立得,拍立得白边上会有刀划的日期,被血水一泡十分明显。
真要说有这么明显的线索应该很好找,但是犯人像是熟知反侦察一样,拍立得相纸是多年来的网红款,从线上到线下到处都有卖的,痕检科看了刀口也是2元店的水果刀,仿佛只是碎尸之后留个纪念随便摸了一把记了个日期。
每一个犯罪现场都没有任何指纹,凶手像是洁癖强迫症晚期患者一样,擦掉了全范围内所有的痕迹。
除了血迹。
“他娘的上面给的时间就剩一周了,这么这么倒霉。”有人看着挂满了证物照片的白板发愁,又迫于主位上夹着烟闭目休息的那位大魔王的淫威不敢放其他的屁,只能小小声腹诽。
岑轩墨窝在椅子上,乌黑的短发有点起油小撮小撮粘着,眼睛下是乌青的痕迹,下巴上冒出了不少胡茬,身上的黑短袖看不出干不干净,反正也被熏得全是烟味。
他一只手搭在腹部一只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手上的香烟缓缓亮着快烧到他的手指上,听到下属的碎碎念抬起了眼皮,即使是半眯着眼睛也能透过这点缝隙看到眼白上的血丝,不知道他已经熬了多久了,浅色的眼瞳都开始发混凝滞。
烟头被他抬手丢进已经泡了烟灰茶的一次性水杯里,干哑的嗓子发出零下十度的声音:“这是工作,被害人是无辜的,不是让我们倒霉的。”他顿了顿,揉了揉发疼的眉心,“下次再有这种想法你自己收拾东西滚去内勤吧。”
没点名,倒也不需要点名,挨骂的心惊肉跳恨不得把自己埋进会议桌低下,没挨骂的在想“愣头青怎么敢在大魔王面前说这种话,不要命辣!”,好在岑轩墨现在处于一种迟缓的状态,像是没睡够的猫一样你分不清是散漫还是困倦,他骂完那句话之后又回归了安静,只是原本闭着休息的眼睛望向了白板,黑笔的字红笔的线像是蜘蛛网一样把十年来的惨案联系在一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最新一例是上上周四的凌晨四点,凶手那该死的仪式感让他抓住了喝完酒后游荡在街上发酒疯的年轻小混混,完成了他心目中的作品,拍下了荒诞可怖的照片留念。
金发小混混的颅骨被撬开,内容物像是发泡奶油一样被打散成糊,还贴心的翘起一个小角,然后插上绿化带里随处可见的苜蓿草,身躯被打包用的宽大保鲜膜缠绕起来,像是一个人形的花瓶一样,而最令人不适的是……小混混的脸应该是狰狞的,可是被切开又缝合调整变成安详如睡眠的状态,拍立得照片上安静地像是行为艺术一样。
尸检报告上述被害人颅骨粉碎,有重击在水泥瓷砖一类的痕迹,皮肤破损处无法检测dna但是从砂砾的检测情况来看,发现尸体的现场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只是可能被凶手拍完照片之后觉得占地方,丢到了小吃街的后街垃圾巷里,早上给环卫阿姨吓得不轻。
屈泽嘴上说带个锤子,实际上还是给会议室里每个人带了包子油条豆浆,避开了好几个神志不清抱着过来喊爸爸的人之后他放了一杯豆浆在岑轩墨面前说:“岑队,现在只能查受害者们这十年来的关联,反正是翻卷宗你回去歇着也是等,你垮了我们就难搞了。”
“监控呢?”
“什么监控?”屈泽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岑轩墨问的是街道的监控,“好巧不巧,盲区,年年评选卫生街道被放弃的地方。”
“呜呜嘟!我呜嘟!”嘴里塞着大半包子的陈雨听到俩人聊到的内容举着手呜呜叫,然后被屈副队一巴掌拍后脑勺上骂着要他咽了再说话。
挨打的人三两口吞下了包子,喝了大半杯豆浆打了个油菜味的嗝才从桌上一摊资料里翻了点什么出来,他挤了挤岑轩墨面前桌面上的东西,放了个平板之后又把手里的截图和文档一个一个排开。
纸上是小吃街的记录,店面照片配着店铺员工的证件照,从每家店的证词到盲区外能查到的一切监控和摄像头,陈雨抓了抓油焉了的卷发顶着俩肿泡眼一项一项说,他声音比较低沉,人也困倦到一定地步,导致根本没办法中气十足地讲线索,低哑平缓的声音让整个会议室昏昏欲睡。
“最后,就是运气比较好的一点,街口的咖啡店因为换了装潢加上了店外区域所以在一个月前装上了监控,但是兄弟几个熬夜翻完了案发前几天的录像,没有携带行李箱大件物品等可疑物品的路人经过。”他嘬了口杯底的豆浆继续说,“根据口供和排除,当天值班的店员晚上10点就下班锁门了,店内监控也可以查到,现在卡在这里了。”
定风波企划文
————————
要说这岑轩墨爱找茬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习性了,只是连他这恶劣性子也没琢磨明白这宝塔镇都要开英雄会了,一块石头丢下去不知道能砸到多少个身手高强的侠客,还有小酒馆敢做黑店。
今日天阴,至少不下雨,他闲着没事在坊市钻了个巷子青天白日就开始喝酒,结果遇到了想摸行囊的小二。
此时此刻他双腿交叠侧坐在八仙桌前,左手撑着脸偏着头灿烂笑着,如果不是右手上那双竹筷子被他捏在手里中指微微发力死死压着小二的手,那店小二满头大汗两股战战的话,倒是显得二者交谈甚欢。
“我说啊——”他拖着嗓子像是捉弄老鼠的猫一样夹着促狭,“手脚不干净的话切下来洗洗呗,干净~”
“不、不……不要啊……!!小的也只是为了老板干活啊,少侠、少侠就饶了小的这一回吧!”
颤抖的破音吸引了不少视线,按理来说应该装个大方小小惩戒一下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但是被赶下山的人没这么好脾气,也不嫌看热闹的人多。
竹筷刚卸力小二就飞快抽回手掌,低垂的脸上透露着阴狠,随即浑身紧绷前踏一步,握拳上扬起手探马似要直捣岑轩墨中门,却被坐直了的岑轩墨抬臂拨开。
原本搭在长椅上叠着的腿也伸了出去,擦着地面踹上了小二的脚腕,那店小二失去平衡后重重跪倒在地,岑轩墨起身踢了长椅卡在小二身上,转了一圈后轻轻坐下。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淡淡说:“你要是只拿东西呢,那就随便你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摸我的剑呢?这可是老太婆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啊……你手上还有油呢。”
“我最讨厌别人动我的剑了。”
岑轩墨把空了的酒杯放在桌上,又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他懒洋洋倚在桌边举起杯子朝着几桌开外侧着脸看着自己的人。
他问:“练练?”
白瓷杯正对着的是戴着眼罩的男人,身边放着一看就知道是武器的布包,岑轩墨有注意到从这手脚不干净的店小二被他用筷子打手的时候这人就面无表情直勾勾看着这边,生怕没人知道他是在看热闹,偶尔还小酌几口仿佛看评书一样下饭。
岑轩墨这杯酒敬过去之后那人也举杯点头,一饮而尽,豪爽的酒滴还撒了一点渗入桌面。
“可以。”
布包被他抖落,露出了冰冷锐利的苗刀,他站起来掂了掂手中的刀,转了半圈反手握在身后,对着窗外抬了抬下颚,然后翻身跳窗,走之前还回头看了眼岑轩墨,示意他跟他出去。
岑轩墨笑了,摸了摸下巴。
“有点意思。”
然后他在厅内扫了一圈,剑鞘拎起布包甩到了隔壁桌一直背对着自己的青衣少女身边,落在了她的面具旁。
“这位女侠,看你还有菜没上完估计还要吃一会,东西劳烦照顾一下,弄丢了我家老太婆会骂人的,回头请你喝酒。”
青衣少女微微侧头只露出了白皙精致的下巴,她看了一眼身边绣着雪花暗纹的黑色布包,点点头,马尾随风摆动做出了回应。
岑轩墨衣摆扬起跃起踩在围栏上,爽朗一笑向后翻倒仿佛要摔下去一样,但瞬间楼下就传来了一声低沉的:“有劳了!”
楼下是待他站定之后调整着护腕,抬着眼皮看着面前的男人。
“怎么着也要互相通报一下名号吧?翎霜阁岑轩墨。”
“段四。”
“点到为止?”
“嗯。”
破风声划开了街上的杂音,段四前踏好几步,苗刀大开大合从身后向前横扫,即将要接触到岑轩墨剑鞘时被他用惯性往回一带,再刺,闪烁着寒芒的刀尖直击面门。
后者踏地接连后退,侧着身子踩上了栓马的石柱借力高高跳起,手中漆黑长剑出鞘,剑鞘被甩开一旁,岑轩墨掐着剑诀,左脚北落拉出弓步,带着自己身的重量长剑下劈压下了沉重的苗刀。
段四微微眯眼,沉气蹲马,双手绷直发力,苗刀在手中一搅旋转半周,提即颠起抖落了直压着的墨竹剑。
“不赖嘛。”轻飘飘的声音从侧面落到身后,不知何时岑轩墨竟快速越过了段四,裹挟着极淡的冰凉雪松气息被后者捕捉到了。
段四长刀向身后反卷,刀尖扫过一大片地方阻碍另一位的接近,他身子逆转,顺步伏低在石板路上横扫一圈,发出了磨砺的尖锐声音。
沉重刚强的苗刀在段四手里如臂使指,他按着刀柄沉在腰间,仿佛挎剑一样中平相对,柄根缠腰,刀尖朝下压以防岑轩墨随时提剑上挑露出破绽。
不够爽快,他心里冒出这么一个想法。
这人狡诈又滑溜,仗着轻功在这条巷子里攀墙又翻飞,还十分卑鄙喜欢从右边冒出专攻视线死角,而刚好能施展开来的苗刀又因为地形局促显得有些拘束,古井无波的脸上露出极难察觉的一丝裂痕。
岑轩墨盯了段四很久,终于捕捉到了这细微如发丝的蹙眉不耐,他太擅长惹毛没感情的人了,像极了热爱玩弄猎物的猫,就连师父能从清冷无情被他惹得动手打人,看到这样的段四后他终于收起了玩耍的心情,提剑正面对上。
双腿交错侧身抱剑向前,刀刃剑刃碰撞中发出清脆的铮鸣声。
苗刀下劈、长剑上削,苗刀横撩、长剑隔档,苗刀担肩、长剑后扎。
一次又一次碰撞在一起,巨大的力量让二人手臂微微发麻,你来我往的隔档中难舍难分。
过招到百回时岑轩墨先收了手,墨竹黑剑被他挽了个剑花背在身后,侧身躲过苗刀惯性的直刺。
他看着同样停下来收刀的段四,甩甩手说道:“累了,喝酒去?”
是毫无疑问的肯定句。
“好。”
定风波企划文
————————
初夏的雨下得令人有些心烦意乱,岑轩墨抖了抖青色的油纸伞甩掉了连绵的水珠之后握住那青伞挽了个剑花收在身侧,弹了弹护腕上的水就顺着那人群在坊市走着。
吆喝声、叫卖声、高谈阔论的笑声,还有那健壮马儿的嘶鸣,宝塔镇好不热闹,这一切听在他耳里比在雪山上吵多了,即使来了这么多天也没习惯,偶尔如钟的声音重叠在一起还让岑轩墨有些头脑发晕。
“老太婆真是的……”
不知道钻进哪条小巷,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喧嚣声如潮水般慢慢退去,偶尔又几句断断续续的对话又遮遮掩掩让人听不清楚。
岑轩墨倚着还算干燥的石墙看着师门寄来的信件,又开始念他那不近人情的师父。
“这种地方有什么历练的必要吗?只怕是隔壁门派那老头搞的鬼想看我挨揍吧。”
他还记得被赶下山的时候宁执华带着他的小徒弟来翎霜阁,冠冕堂皇对着师父说想过两年送小徒弟去江湖闯荡一下,但是心智还不够成熟,能不能让可靠一点的兄长先去看看……然后岑轩墨就看到了修奕霖那张古波不惊的脸看向了自己。
这可真是吉凶自有天定啊,约莫也是修奕霖这清冷性子都有些受不了岑轩墨这浑身反骨的叛逆孽徒,能找到机会把他丢进江湖摸爬滚打磨砺磨砺也是好事。
岑轩墨摸着墨竹上红色的剑穗子,眼神凶狠笑得嘴角扭曲,又骂了好一会老头老太,这才脚尖一点轻轻一跃翻身上了屋脊。
雨停的傍晚还留有不少云层,夕阳半透不透露出一丝丝余晖染橙了天际,他摸出怀里塞的舆图看了看方位,朝着武林驻地跑去,衣摆飞扬马尾雀跃,在云暮霞光之下显得无比鲜活开朗,好一副英雄少年的模样,如果他嘴里没在说什么阴阳怪气的嘲讽就更好了。
“老头的信件里武林盟还要什么助力英雄会……先去悄悄,与我无关的话就溜回去逛逛,找家茶馆听听小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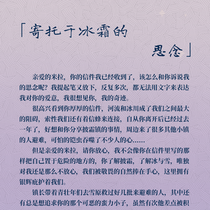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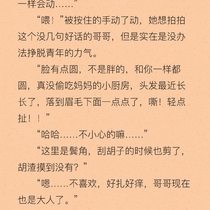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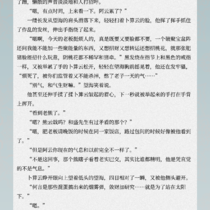
作者:莫特
评论:随意
————————————
“很抱歉,你刚回来就有一份包裹需要你送去悠达卡。”芙蕾雅一脸正色看着站在面前的塞隆·陶德,青年眼下明显的青色让她顿了一下,视线在包裹上停留了一会,在抬起来时只剩下公事公办,“因为时间很紧急所以只能辛苦你再跑一趟。”
塞隆看着办公桌上放着被细绳捆绑好的纸包,闭上了双眼抬手捏了捏发紧的鼻梁,深吸了一口气跨步上前拿起了那个也就两个巴掌大的包裹,指尖晃动掂了掂重量感觉比以往送的东西轻上更多,让他猜不着大概的范围。
“没问题。”
“目的地是边缘地带,你需不需要再叫一名信蜂和你搭档一起?”
“嗯……”他松了松压住头发的护目镜,想了下说,“不用吧,最近大家挺忙的,跑这么远还赶时间也不好叫新人一起,控制状态快去快回就行了。”
芙蕾雅抬了抬手还想说什么,被塞隆笑着打断了,他抓抓额头上乱翘的头发问:“副馆长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吗?有没有不紧急顺路的信件我回程路上一起送了,省得再多派人手了。”
“没有了,多休息一下然后尽早出发吧。”
塞隆点点头抱着包裹转身出门,规划着现在去领一叠顺路的信件之后再去吃顿好的,然后睡一觉出发应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等他临近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芙蕾雅的声音。
“塞隆。”
“嗯?副馆长还有什么事吗?”
严肃认真的副馆长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抬眼看着他,金色的眸子被光线照耀的有些朦胧,藏起了眼底那一丝难以捕捉的担忧。
“注意安全,切记不要冲动。”
“哎呀~”
青年笑了笑挥挥手,隐藏在话语里的另一个意思他明白,不要头脑一热就对着铠虫冲上去就行了,他有全世界最好的波亚兹陪着他。
手臂上搭着的围巾随着塞隆的走动看起来心情很好似得晃了晃,他说:“那这次回来副馆长要给我好好休几天假啊,不然我真的会心力交瘁的呀!”
芙蕾雅看着那个有些散漫的背影扶着额头叹了口气:“真是的……”
厚厚一沓信件被塞隆塞进塔里克绑着的包上,包裹放在最上面,又被盖了一层薄薄的毯子包裹好,皮革手套拍在皮质的包上发出好听的砰砰声,他跨上摩托拧了拧把手,排气管冒出点点橙金色的星光一路从蜂巢蔓延至波尔卡街的留声机门口。
“不吃饭了吗?”
“埃尔你做的能吃吗?”
“那你不也长这么大了。”
“弗洛家婶婶给我带了些熏肉干,比你做的好吃多了!”
“哦哦,那要好好谢谢人家,不休息一下吗?”
“嗯,不了,早点出发进悠达卡前还能找到旅馆。”
“臭小子……”
“嗯?”
“注意安全,别……”
“知道了,波亚兹陪着呢。”
踏在地砖上的脚收了回去踩在车上,塞隆握着拳锤了埃尔维斯一下,把这个瞎操心的叔叔赶回店里工作,戴上护目镜调转车头驶离了城镇。
微弱的人工太阳光芒照着蜿蜒的路,疾驰在路上的机车和风声作伴不停歇地前往目的地,后座上波亚兹被背带安全绑在车上趴着休息,耳朵时不时抖动一下警戒着周围,但是比起风声中可能夹杂着的危险信息来说,它的搭档可能才是最麻烦的那个。
“好累啊波亚兹……”
絮絮叨叨的话被风切得断断续续的。
“你饿了吗?”
“汪汪。”
“真可恶啊,吃饱了的小狗就是舒服啊……”
“汪呜!”
一人一狗的自言自语就这么在崎岖的路上被夜晚吞没,泥泞的土地被车轮画出不同曲线的花纹,路上风化的石子被碾碎卷进尘土里,橙金色的星星就这么一直跟着塞隆,直到行驶到连通下一个区域的桥。
“每次路过都在担心要是走神控制不好方向就会掉进海里呢……信蜂塞隆·陶德申请渡桥,辛苦开个门啦!”
“汪汪!”
“波亚兹说的也是辛苦了哦。”
反射着光芒的水面被车轮破开分成两条长长的水痕,波浪一圈圈蔓延开来揉碎了天上的星星,深蓝色的海面承接了塞隆逸散开来夹杂着回忆的心。
越往边缘越冷清,第四次休整的塞隆裹着毯子抱住温暖的波亚兹,脸颊蹭着被风吹得发凉的狗耳朵叹着气黏黏糊糊说着:“早知道答应副馆长再找个搭档了,一个人太寂寞了,波亚兹你说话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汪汪!波亚兹,来,汪汪!”
被勒住的波亚兹狗脸上都露出了非常人性化的无语表情,但是始作俑者实在是沉浸在自己的牢骚中无法发现,他抱着连回应都不想回他的波亚兹好一会之后就摘下围巾架起了小锅就着火堆开始炖这次份的晚餐。
熏肉被吃掉了一半多,离目的地还有一天的路程,即使是小心再小心的使用心驾驶机车也让塞隆有些吃不消,他卷着毯子缩成一团靠着波亚兹昏昏欲睡,大狗蜷着身体让塞隆枕着它好好睡上一会,耳朵机敏地抖动着,现在是优秀的叮钩守护搭档的时候。
夜幕散发着柔和的光辉,她悄悄落在奔波的人身上,安抚着每一个疲惫的心灵。
包裹送到了收件人手中,那是有一双粗糙历经风霜的手的老妇人,苦寒地带让她的脸上布满了时间的痕迹,那双关节粗大还带着厚茧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微微颤颤握住笔写下了名字,然后抱住了轻巧坚硬的包裹,老茧在油纸上磨出唦唦的声音,塞隆垂着眼还能看她凌乱额发下泛红的双眼,她温和又苦涩地对着塞隆笑了笑,似乎已经知道了里面是什么,然后垂下头缓慢地拆了起来,泛黄的照片和熟悉字迹的信件被她小心翼翼捏在手里,生怕弄皱了一点。
塞隆没有继续留在那,这是收件人的时间,他只要完成配送就好,波亚兹仰着头看着塞隆,一人一狗转身往山崖下停车的地方走去,长长的围巾被风吹起在空中飞舞,背后的声音从细微的嗫嚅变成嚎啕大哭,他把帽子摘了下来紧握在胸前闭上了眼,金绿色的睫毛颤了颤,再抬眼时只有和星空一样的平静的目光。
“波亚兹。”
“汪……”
“我们继续去送信吧……”
“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