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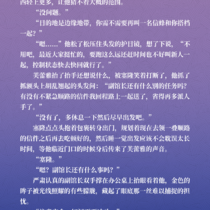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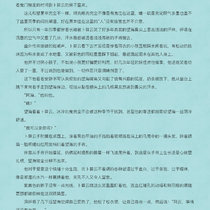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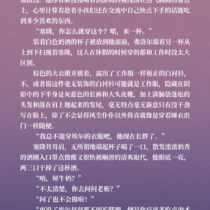
作者:莫特
评论:随意
————————
连绵的雨让整个城市被笼罩在潮湿的蒸汽下,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密集又聒噪。整个城市变得又湿又滑,屋檐下嘀嗒嘀嗒落着连成串的水晶珠子砸在地上,激起一阵阵混合草木和泥土气味的风。
卜算云坐在窗台撑着脸看着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彩色的雨伞笼罩着一个个身影不断碰撞又分开像被风吹乱的花,又像三流画家凌乱的调色盘涂满了各种各样混合的颜色。
他端着一杯奶茶咬着吸管,视线转移过来看着书桌前看资料的望海,男人低着头看着纸上的字,骨节分明的手修长白皙,干净整齐的指尖没规律地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左手转着笔时不时划上几划,垂着眼眸一脸沉思的样子让卜算云咬吸管的力度重了不少,他深吸了好几口,发出很大的咕叽咕叽声来吸引望海的注意力。
“阿云?”被声音吸引的人不出所料抬眼看了过来,满眼都是疑惑,“怎么了?”
卜算云最喜欢看他有些莫名的呆样子,松开已经变形的吸管歪着头笑了笑说:“没事哦~”
咕叽咕叽的吮吸声再一次充斥在二人之间,望海看着卜算云笑弯了的眼睛有些不知所措只好低下头继续计划着他的工作。
要瞒着地府的事情太多了,在望雾亭筹划的话被发现的可能性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偶尔他会借着鬼门稳定的时间到卜算云的房子里来。
这儿和望雾亭完全不一样,明亮敞亮完全不像是有鬼住在这里,唯一就是无论阴气多重也盖不了盛夏雨季的闷热潮湿,好在原本住在这里的“人”没有感觉也并不介意。
所以只有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被卜算云笑了好多年真装的望海鼻尖上冒出浅浅的汗珠,呼吸在沉重的空气中又重了几分,汗水最后被透着浅浅青筋的手背擦去。
窗外传来细微的喧闹声,卜算云看下去才发现是穿着雨衣的小孩互相踩水闹着玩,有松动的砖块因为积水变成了水地雷,又被彩色的雨鞋重重踩下翘起,最后溅起泥水在其他人身上。
他并不讨厌小孩子,不如说小孩更好骗更好利用,好几次年轻的妖怪求他做事,他还能笑着给人耍了一圈,不过说到也能做到,一切作恶只是调味剂罢了。
这下他看着安静书写认真规划的望海嘴角又勾起了饶有兴趣的弧度,奶茶被放下,他从窗台上跳下来背着手走到望海身边,视线从黏在额头上的几根黑发游离到鼻尖的汗水。
“阿海。”他叫他。
“嗯?”
望海看着卜算云,冰冷的鬼完全不会被这种季节干扰到,甚至他的靠近都能带给望海一丝阴冷舒适。
“我可以亲你吗?”
卜算云手肘撑在桌面上,涂着黑色甲油的手指掐着前倾落在肩上的马尾中的一撮头发,眯着眼睛一脸明媚灿烂用发梢扫着望海的手背。
痒意从手背开始蔓延,仿佛延时摄影的藤蔓一样飞速爬升着,到底是从手背上生长还是心底里扎根,望海完全分辨不出来。
他对于爱意这个情绪十分生疏,而卜算云不着调的各种话语过于直白,过于亲密,过于暧昧,像是潮湿的水汽一样裹挟着他,无孔不入又令人窒息。
紫黄色的眸子没有一点光线,卜算云就这么笑盈盈盯着他,连血红瞳孔的动摇和鸦羽般的眼睫震颤都被倒映在这双眼睛里。
深呼吸了几下后望海觉得自己更热了,他松了松衣领,让自己自由一点,然后说:“阿云,事情还没有办完……”
“嗤,真煞风景。”
雨声夹杂着喉咙间溢出的低笑声让望海突然慌张了起来,卜算云好像恼了,又好像在笑,他连怎么和人交际怎么照顾小孩都是从别人身上学来的,又怎么会懂爱情这词,更别说直白热烈但是捉摸不透的话语。
“我、我是想说,我不是……”
平日里云淡风轻的海老板突然大舌头了起来,怎么也无法给自己解释清楚,只好抓着那只按在桌上的手来延缓这一刻的兵荒马乱。
温热的体温触上冰冷的肌肤,像极了雨水打在干涸的土地上,是饮鸩止渴吗?望海开始贪恋起这份凉意,窗外的雨越落越大,隐约响起雷鸣声,到底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卜算云他完全不想管,脑子里只剩下别让他恼别让他气别让他失落。
“轰隆——”
夏日的雷鸣总是那么突然,窗外的天只剩下阴霾,就连敞亮的室内都暗了下来,视线被手掌盖住,嘴唇覆上了冰凉湿润的柔软,在单方面灼热的吐息中安抚掀起波澜的心。
望海在黑暗里眨着眼,听见了含着傲慢得意的声音。
他说:“谁要听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