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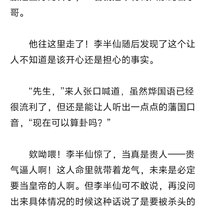


*听着打卡里提到的钢琴曲写完了
*又是一如既往只记得把醋给泼出来就完事了的东西。
*有非常多余的感性描写。
*字数:3252(含小标题及重复的句子)
你知道“唱片”或“磁带”吗?是的,一片中心镂空的圆盘、一个内部由齿轮状的卷盘缠起一卷卷黑色塑料带的长方体盒子。
置于唱针下,在转台上开始旋转。
置于播放器的空槽中,随着咔咔声将带子从一边转向另一边。
——这是A面。
翻转唱片,将另一面置于唱针下。
翻转磁带,将另一面嵌入播放器的空槽中。
——这是B面。
明明在刻录在同一个媒介上,两面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此,你又怎么想呢?
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答案了。
现在,分别听听A面和B面的声音吧。
-A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纤细的指节、交错的指节。
和音、杂音。
一首毫无章法的乐曲,而后是没有敲下指节却兀自弹奏或修正的琴声,杂乱的音符从下压的琴弦里流出来,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这根本算不上是在演奏。
“啊啊啊啊钢琴活了啊!”穿着校服的男性发出了尖叫声。
“哎?”穿着校服的女性反应慢半拍地歪了歪头。
夜晚的学校,两个毕业已久的学生,和仿佛在呼吸、仿佛在吼叫、仿佛在躁动着的钢琴,空气中充斥着不协和音。假设从内部上锁的音乐室是一个密室,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将穿着校服的男性称之为A,女性称之为B,音乐室内,此时此刻,没有除AB以外的第三个人类,不论死活。
然后——
“唧唧!”密室内发出了第三者的声音。
是一只红松鼠,在钢琴的腹腔中穿梭,将琴弦向下压,将螺丝、弦,甚至是木制的外壳都撕咬得松动而摇摇欲坠,使得有着漂亮黑色皮囊的钢琴内里溃烂不堪,发出失真的惨叫声。
“哈哈,哈哈哈。”男性干笑两声,“还以为真的有鬼呢。”
……
1、2、3、4,5。
无论怎么走,向上的台阶总有盈余。
“你知道彭罗斯阶梯吗?”她这么说了,“透过视觉的错位,展现出不可能的…‘无限’的光景。” ……就像是,现在的状况。
“那是什么?”提问的人已经将脚步迈向阶梯的拐角。绵延无尽的长蛇般的楼梯折出一个新的角,稳稳地承托住了他的鞋底……当然,这只是经过主观加工的说法,事实上,他只是在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阶梯上又踩过了一层。
“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假设我们被困在四维……或者更高维的空间里,假设我们所在的世界受到某人的操控的话……罢了。到现在为止,阶梯数到多少节了?”
“我看到尽头了,但是……”男性犹豫着放慢了脚步。
661、662、663、664,665。
“666。”女性接过了他的话,先一步踏上了最后一节阶梯,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看来我们已经来到阶梯的奇点了。”她笑了笑。
-B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无形的指节、不存在的指节。
和音、颤音。
漂亮的韵律随压下的琴弦处发声,一下一下,以《小星星》开始,在琴键上由慢而快地跳跃着,仿佛能看到窗外有流星闪过。实际上,流星从天上撒下来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或许这是两周前的星星的余热吗?杂乱地在琴键上左右跳动的星星仿佛迸发出了灼热的火星子,想伸出手去触碰的时候,星星的温度与音符一同落到了地上,发出了干脆的声音,没有再跃起来。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自己在弹的钢琴吗?”一个看起来还是能穿上校服的年纪的男性敲了敲陷入寂静中的立式钢琴,就像是在确认某个野生动物是否还有呼吸一样,钢琴没有回应,他就顺势把琴盖合上了,黑与白的齿列被关进了木制的嘴唇中,不作一言。
“它应该还在这里才对,但不清楚具体的对象是谁,就算是寻人寻物魔法也需要具体的媒介……”一旁的男性抓着形状奇特的叶子、蜥蜴的断尾一类的东西,沉思片刻后作出结论:“把钢琴拆了吧,用里面的琴弦或者螺丝钉之类的做媒介。”
“故意毁坏财务罪最低的刑罚是……”一旁的第三个男性正要开口,此刻,钢琴却先撬动了唇齿,音符发出轻快的跃动声。几人看向那架钢琴,琴盖仍是合上的状态。音乐室内的四人并不知道,但这一曲是麦克道威尔的《女巫之舞》,琴壳内未知的世界里正以极快的速度弹跳出一个接一个清脆的跳音,像是音符一个个跳进翻涌着绿色浪潮的坩埚中,飞溅出无数无害的水花。心头鹿似乎正不自觉地随着女巫的舞步而撞得头破血流,好不容易才随着乐曲渐渐缓和的节奏而得以找回自己的呼吸。四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最终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开口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不把钢琴砸了?”手上捏着奇怪的巫术道具的男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总是很干脆。钢琴叫嚣着又弹起拉赫的《小丑》,像是正发出轻盈又让人头晕目眩的抗议声。即使琴板盖上了,也能从四处跳跃的音符中明确地感受到像有两只手正快速地在八十八个交错的黑与白的琴键上跑动着,平稳而精准、如节拍器般牵动人的心跳的乐声,就像是面前并非是一个需要他人操纵的乐器,而是一个自行轮转的纸带八音盒,随着不知何人打好孔的长长的带子,吞进去,在既定的孔洞处发出空灵的乐声。
“一千美元以下的罚款、社区服务、缓刑,以及一周的象征性监禁。”似乎对本地法律了解颇深的男性一边说着一边掰出四根手指。
“别的不说,我觉得它弹得挺好的。”唯一称得上是学生的男性发表了中肯的评价。
“那怎么办?钢琴又不会说话,我们怎么知道它想要什么?”捏着蜥蜴尾巴的男性叹了口气。
“或许…它想要的是一场合奏?”女性用指腹摩擦着盖上的琴板,琴壳内发出温和的低鸣声,像是一只正打着呼噜的幼兽。
黑色木质生物轻柔的呼噜声,慢慢地、渐渐地,转为风暴般的嘶吼。当然,一台钢琴自然发不出野兽的怒吼声,只是错落而杂乱、时而低沉时而尖锐的乐声渐渐变得刺耳了。
“好主意!”像是学生的男性身先士卒地拿起贴着墙面放置的吉他,稍微试了下音,“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女性清了清嗓子。
“我不会。”干脆的男性作出了干脆的回复。
“要不试一下那边的尤克里里?它只有四根弦,相对好上手一点。”已经轻车熟路地把吉他挂在腰间的高中生指了指一旁墙边如面试者一般等待被选择的乐器们。
“这个?”
“不对,那个是贝斯。四根弦的那个才是。”
“这个?”
“对,那夏露露呢……?沙锤吗,真是古板又缺乏新意的选项啊,罢了,也很有你的风格。那么——
“开始表演吧!”
……
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临时组建的乐队被愤怒的钢琴赶出音乐室…的十分钟前发生的事。
“它干嘛这么生气?”始作俑者不解地一边在楼梯上奔跑着一边发问。
“大概是因为有人连c和弦都不会弹吧。”女性冷冷地回道。
“话又说回来,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还有……斧头、摩擦地面的声音。”四人中最小的男性一面说着一面频频回头,脚下的影子被阶梯拉得长长的,像是被折成了数叠。
“比起这个……”存在感略低的男性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准确地说,是看着脚下的阶梯:“这条楼梯,我们已经……”
“走了666节阶梯了,对吧。”跑在最前的男性停下脚步,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一个陌生的女性不知正说着些什么,她转过头,朝四人打了个招呼:
“初次见面。”
“请说英文。”气喘吁吁的男性如此回答。
-杂音-
“所以,你们的名字是?
“……
“这是哪国的名字?
“好吧,亚洲人,欢迎你来到奥庇沙……开玩笑的,这里是美国,埃芬市,罗卡里兰高校。
“开场白…或者说结束语已经说完了,那么,你们想怎么样?想回去的话,我这里有认识的小叮当和任意门,又或者…你想组个临时乐队吗?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两个音痴所以那边的钢琴很生气,是的,音痴是在说我自己。
“哼…你们能答应就太好了,希望你们能让它满意……你是说希望渺茫吗?我会期待的。”
-和音-
称不上和谐、称不上优雅、称不上漂亮,甚至略显狼狈的一曲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最后一根颤动的弦、最后一句即兴的歌词落下而画上休止符。三个人弹唱,而另外三个人坐在音乐室的椅子上只负责了鼓掌,据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并不是活着的生物。
穿着校服的男性手中的红松鼠在安静的音乐室内一跃而下,蹦跳着跑向那架有着漂亮骨架与外壳的钢琴,就像寄居蟹找到了全新的壳,它钻了进去。
被沉默所充斥的室内,不知是钢琴或是松鼠送来了一曲《月光》,月亮温柔而沉静,如隔着层纱幕般垂下眼睑,圆而白,投来明朗而慈悲的目光。
某个人轻轻哼唱、某个人弹起和弦、某个人打着拍子、某个人跺着脚,某个人轻叹出声:
“真是…像魔法一样。”
“这种话,现在才说吗?”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变回了它应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