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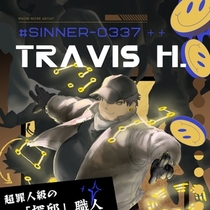
【4191字】
*感谢和我互动的各位老师!!!干巴巴的剧情和ooc属于我,角色属于最好的老师们……
*可能有很多虫但是中人要被小学期结课课题抓走了,哭
*日常没能写到的那位,求你别死啊啊啊非日常会继续的所以求你啦!!!!!(汪汪大哭)
———————————————
■■.
“是,您所言极是,这都是我们考虑不周。您愿意的话,我们会虚心遵从您的指摘——”
就算真正的危险降临,夜逃屋从没察觉到它已经悄然到来。她循声望去,只是看见那具曾横在乘务员和超高校级中间的女性身体应声倒下,只不过……闻到一股浓郁的铁锈味在车厢中弥漫。
“什……喂,我没听说过会这——”
咚!!!这回是女性身后的高大男性倒下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孩脑袋开花前的悲鸣犹如火星迸发的引线,引爆了整座车厢的不安与恐慌。玻璃车窗突然传来砰砰砰砰砰的声响,尔后BANG地炸成碎屑。狂风卷着黄沙扑面而来,一时间哒哒哒、突突突、噗叽、噗通、“呀!!!”、“快找掩体!”、嗡————之类的声音全都一股脑涌入她的脑袋。
爱丽丝只是站在那里。
“可恶,早知道就不来美国了!”
“呀啊啊啊!!!救救我!!!!!”
“喂,你!!快来这边避难!”
不知是谁拽了一把,她踉跄两下摔到座椅后面,数颗子弹划过她方才站着的位置,砰砰砰地撞进车厢墙壁里。
“你没受伤吧,夜逃屋小姐?!”
但爱丽丝没有回答
她只是瘫坐在那里
看风沙与弹雨
听惨叫与呼喊
看鲜血淋漓的肉体倒地
听碎落一地的玻璃残渣
看那逐渐逼近的恶意
【小屁孩,你就和躺在那边的女人一起■■吧!!!】
——看那场,夜逃屋最初的「夜逃」。
“不……不要………!!!”
她抱住头,听自己的心脏跃出胸膛。
————BOOOOOOOM!!!!!
什么东西在她耳边炸开,在灼烧与震动中,刺耳的耳鸣声终于远去了。
05?.
鬼岛爱丽丝醒来时,只见清晨的柔光照亮了这间有些破败的屋子。留有黑渍的墙壁、掉漆的天花板、起了毛球还破了洞的不怎么软的床垫,这一切和列车上的住房相差甚远。莫非是列车抵达目的地了?她坐起身子,身上还套着外出穿的常服,看来是旅途太累了,还没换睡衣就沉入梦乡。枕边的智能手机已没电到自动关机,应该是自己顾不上充电了吧?她系好鞋带,站起身,活动活动手脚,蒙了一层薄灰的地板发出“吱呀”的声响。
她就这么走出108号室,路过走廊,推开木门,走出这栋挂着旅店招牌的三层大木屋。作为旅行的目的地,这里自然不只有旅店。对门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餐厅和酒吧,不小心吃坏肚子还能上隔壁的医院救治。倘若有些厌烦了,还能去北边的小店购入材料做点DIY,或在射击场打上几轮娱乐一下,还怪贴心的。不过位于镇子中央的警察局是作什么用?有超认协的人坐镇办公吗?
爱丽丝就这么走马观花着来到小镇南入口附近,得以一窥围栏后的风景:黄沙,高温和烈日。这一切完美符合她对荒漠的想象,以至于初来乍到的她完全按捺不住兴奋劲。少女把外套绕过后腰,两只袖子在腹部交绕,打上一个结。她脱下运动鞋,又提在手上,举起来挡住脸上的太阳光。
“好!爱丽丝,出——”
“你在,做什么。”
刚踏出第一步,某人便叫住了打算漫游“仙境”的她。爱丽丝回过身,笑着同对方挥了挥手——和她手上的运动鞋:“早上好,阿卡洛尼克小姐!我想出去走走!”
“等等。”治沙工程师对她上下一番打量,“你,会死。”
“诶?沙漠是这种地方吗?!”
“危险,沙子。”
爱丽丝闭上嘴,扑闪着眼睛,整个人歪过四十五度,似乎在思考刚刚那句话的含义。来自阿根廷的女士噤声片刻才抬起头,爱丽丝这才对上护目镜背后的那对绿眼。
“你,没出门,三天?”
“……咦?什么?真的吗?!这整整三天我都在房间里睡觉?!”
“差不多。”
“诶!?是大家在这落脚后把我抬下车的吗!?”
“我,你,扔进房间。”
“什——!这真是太麻烦您了阿卡洛尼亚小姐!!!我该如何感谢您呢……对啦,我请您去那边的餐厅吃顿饭吧?”
“钱,不行。
“没事的啦!我有信也哥给的信用卡,临走前也换了美元纸币,这点儿不算什么!”
“沙士币。”
“沙士币?那是什么?”
“瓶盖,货币。”
“诶!这里不是美国吗,原来还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啊!”
“不,列车,袭击。”
“袭击?”
阿卡洛尼亚微皱眉头,伸手指了指自己,又指向正在频繁眨眼的夜逃屋少女。
“落难过来,外来者。”
“爱丽丝,不记得?”
07.
“好咧!加油吧爱丽丝!啊哈哈——哈……。”
自嘲般的傻笑以长长的叹息收尾,爱丽丝整个人忽然塌下去,像一株焉了的稻草。(此举吓到了路过的鸟类镇民,但爱丽丝没发现他。)
据说超高校级们抵达“沙士镇”已是三天前的事。“被黄沙和风暴包围的西部城镇,这真是太浪漫了!”——尽管爱丽丝这么想,治沙工程师没接她的话,而是继续指出外来者、镇民和行李问题。“既然集结了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来点有挑战的活动也无可厚非呀!”——她如是说道,听得阿卡洛尼亚默默抿了口面汤。
“诶?不是这样吗?我这就去找超认协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
就这样,爱丽丝离开餐厅,径直朝警察局走去。但她心里也在直打鼓,身为夜逃屋的直觉告诉她这一切另有蹊跷,尤其是她还忘了从列车到沙士镇这段期间的事的话。
警局的建筑风格和旅店大差不差,门上却挂了块“禁止入内,违者击毙”的木牌。爱丽丝歪着头左看右看,窗帘是拉着的,门也是上了锁的。难道这里……真的不是一般的城镇?她眨眨眼。
“有什么事吗?”
她的左肩猛地向下一沉。
爱丽丝缓过神,回过头,与一只鹰对上视线。不,如果说牠是鹰,牠拥有的牛的头颅和蝎的尾巴又该如何解释?况且这种和“奇美拉”遭遇的时刻,她应该——
——“哇,你长得太酷了吧!!!是什么生物哇?!”
……前言撤回,鬼岛爱丽丝只是原地小跳外加挥舞双手,俨然看到新奇事物的小孩。“警长”依然扒着她的肩膀,稳稳地站在上面:“看不出来吗?我和你一样,都是人类。”
“原来你是人类?但……”爱丽丝又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这位自称人类的警长怎么看都没有人类的特征。她单手托腮,尝试用小脑瓜思考出什么。半晌,她终于一捶手心道:“也就是说,这里应该是仙境吧?”
“不,这里是所有人都拼命活着的现实。”
“啊、诶?现实?还是梦?是哪边?”
“是现实。”站在人类肩上的人类顿了顿,“你好像很失望啊。”
“因为,在仙境的话,大家就能无忧无虑生活下去了耶!”站在坚实大地上的人类对了会手指,“那,这里果然是超认协的活动会场吧?警长是超认协的人吗?”
这回,“人类”的颅骨开始微微震颤。爱丽丝红了耳朵,鼓起脸颊:“警长是在把爱丽丝当小孩看吗?我已经18岁了,是大人了!”
“是啊,是啊。”颅骨深部的嗤笑声逐渐停止了,“还能保持这种心态的大人,很有趣。”
“哼哼哼,对吧!爱丽丝可是了不起的大人!”少女双手叉腰,一副抬头挺胸的神气样,“话又说回来,警长在这住了多久了?”
“我们在这里将近五十年了。”警长说着挪到爱丽丝的右肩上,低头理了理羽毛,“遇到你们这些外来者还是第一次,让人非常感兴趣啊。”
“五、五十年!”爱丽丝捂住嘴,看上去有些难以置信,“这座小镇是你们亲手建的吗?在来到这之前,你们是在人类社会生活?”
“早就忘了。”警长说着拍了拍翅膀,“如果你离开原本的家五十年的话,你也会忘记的。”
“但是,”爱丽丝双手合掌,露出灿烂的笑容,“你们已经在沙士镇安居乐业,换句话说,你们的‘夜逃’成功了!太好了呢!”
“啧啧啧啧。”熟悉的笑声再度响起,而肩上的重量陡然消失。少女昂起头,一根羽毛翩然落下,而“人类”不见踪影。
“——觉得这里不错的话,趁这次机会在这定居也不坏啊,小女孩。”
“……诶?”
脚踩大地的人类歪着头仰望悠远的天空。
他刚刚说……留在这?
为什么?爱丽丝……很喜欢在日本的那个家啊……
就在她陷入思考的漩涡,她的肚子发出了不满的咕噜声。
08.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在这沙士镇,想吃饭就得有沙士币,想要沙士币就得打工赚钱,想有力气打工就得吃饭——总之,为了摆脱死循环,加上手上唯一的沙士币已用于前一日晚餐的鬼岛爱丽丝,决定步上前人走过的道路。只不过这回不是去漫游沙境,而是前往医院打工。
“嘿,那边的你(mate)!”
夜逃屋上一秒正要推门而入,下一秒就瞥见那位只蒙了下半张脸的先生向她走来。尽管对方只高了她半个脑袋,爱丽丝也不得不抬头打招呼:“早上好,纳撒尼尔先生!”
“早安,以及好久不见!出什么事了?”背景扮演者顿了顿,瞥了眼医院的门牌,“要给大夫看看么?”
“我没事,只是稍~微多睡了一点儿!”
话毕,爱丽丝才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用了日语,禁不住眨眼打量起眼前的“外国人”:“纳撒尼尔先生的日语好流利呀!你来过日本吗?”
“不瞒你说,在下是澳大利亚人,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
“哇哦!你说日语时用的自称特别酷!”
“多谢。”见爱丽丝的双眼变得闪闪发亮,他清了清嗓子也压不住话中的得意劲,“呼呼,要不要一起去医院看看?”
“真的吗?!”她拼命点头,“我非常乐意!”
“Great!”他打了个响指,“我们出发吧!”
于是她和他就这么闯进医院,前台的三人各有各有的百无聊赖:钟表匠伊姆霍特普·扎基几乎是趴在那,手上摆弄着一只病例纸折成的千纸鹤;一旁的穿孔师路允儿信手翻阅着病历本,看来千纸鹤的原料就是从这来的;唯一的镇民,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则打了个再响亮不过的哈欠,甚至没有正眼看过爱丽丝。
“您好大夫!我想在这里打工,可以吗?”
“当然。”大夫拿起一份报纸盖在脸上,整只鸟向后仰躺在座位上,“别动柜子里的实验性器材和药品,其他的随你便。”
听罢,爱丽丝留下一句道谢便匆匆跑向深处。纳撒尼尔本在在器械柜前左顾右盼,闻声又回头招呼爱丽丝过来:“看,这里有好神奇的手术刀,说是会变形成各种医疗用器具!还有无针注射器和智能辅助犬,配备很完善啊mate。”
“真的诶!”爱丽丝在他身边蹲下,双手抱住膝盖,尝试阅读上面的英文,“那不是超方便的嘛!”
“不过这东西得有权限才能取,”他指指贴在柜门上的告示,又伸手拦住欲开柜门的爱丽丝,“最好还是别这么干了。”
“也是呢,就算拿出来了爱丽丝也不会用,啊哈哈哈……”
“顺便一提,药房里的实验性药柜都也不行噢。虽然药瓶上都写着什么大象的,很让人在意呐。”
补充说明药物的人并非二人,循声望去只见伊姆霍特普笑着慢步走来,还向二人挥挥手:“呀嚯二位,调查还有意思吗?”
“还算好?就是便利到有些奇怪。”“爱丽丝倒是觉得超棒的!如果有人受伤的话一定用得上吧!”
“嗯,这样啊……”
缠着无数绷带的男人托腮,绷带下的眼珠滴溜溜转着扫过二人:“那么,你们二位来帮个忙吧!反正这医院闲到几乎没事干。”
“当然,如果是我能做到的话。”
“爱丽丝也没问题!不过伊姆霍特普先生是想要我们做什么啊?”
爱丽丝眨了眨眼,只见钟表匠举起食指,贴着嘴唇比了个“嘘”。他又招呼二人凑近了些,才露出绷带下的獠牙:
“来做一场实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