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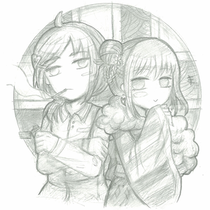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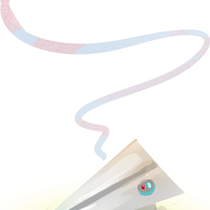

卡拉波斯上次来这个酒店是一个任务,来自执政者的绝密委托——众所周知井之都奥错大多资产阶级都是挖矿挖出的资产,然而这事要说运气。
不是所有一夜暴富的人都是理所应得,也有些该管他叫助纣为虐。
执政者不愿看到恶性循环,托某一个高瞻远瞩的掌事人的福,卡拉波斯在遗产手续还没办下来、猎人委托又接不到的空档期,接到了这个委托。
许多年前的卡拉波斯岂止榜上无名,连知道他家死的只剩他一个了的人都寥寥无几。
他还年轻,一点底气都没有,却偏偏要有自己的性格,连自己都觉得自己难搞;家里穷的揭不开锅那是夸张,但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是事实。
执政者总是对自己城镇里的常驻猎人有一张名单,卡拉波斯才成为了名单的最后一员;机密人员问他,我们要暗杀一个矿洞的老总,你愿不愿意来?
孤立无援的猎人立刻明白自己是被人算计了,他没有底气回答不来,却也没有底气接下单子。
他只好说实话。
“我不杀人。”
多年前他想不出为什么自己会被挑中半强迫接下这个任务,许多年后他终于有了成长;对方要拿他的经济账单那是易如反掌的事,而且他默默无闻,死后也不会有人为他收尸;机密人员煞有介事的点点头,跟他说。
“那你可以协助我们。”
生日和忌日在同一天实在惨无人道,但卡拉波斯自顾不暇;这场宴会在冬季,他裹着宽大的披肩,裙撑重的他有点掌控不好自己的重心;女装猎人递出自己准备好的请柬,脸上带着僵硬的笑意——他还不习惯丝绒手套,感觉自己有点捏不住手包。
“卡尔波斯女士,”侍从朝他引手,“请柬上提到了您的丈夫……”
“很不幸,他走楼梯的时候摔昏了头,没有办法出席。”这个问题不在卡拉波斯准备的预备列表里,他的视线触及到酒店尽头处华丽的大理石台阶,干巴巴地编出一段对话。
侍者不过象征性地关切询问,带到这位女士的座位之后便结束了对话,卡拉波斯把皮草的外套解下来,侍从接过就退了下去。
年轻女性孤身一人前来,她身材瘦长,穿着和其他夫人一样的礼服长裙——层层叠叠的裙子用裙撑撑着,全都靠束腰来维持它们美丽的造型。
然而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一个穿着紧身衣,蒙着脸的人,正缩着身体躲在他的裙子下面——卡尔波斯女士的裙子下还有个男人。
◇
卡拉波斯最终和机密委托的负责人达成了协议;他负责携带“凶器”,藏在他裙子底下的那位负责借刀杀人。
他按照第一计划在老男人的酒杯里加了强效泻药,接着把“凶器”运进洗手间守株待兔。
此刻已经成功了一半。
“他们叫我躲在一个男人的裙子下面的时候,”忍者从裙子下面一骨碌滚出来,嘴里居然还在说话,“我已经做好了被男人的体味熏死的准备。”
他用茫然又惊奇的眼神看着卡拉波斯,“可是你的裙子下面居然有香味……”是这个人带着香味,不是花香,不是人工的香精味,是植物和草木的气味。
什么鬼玩意。
那时候还相当年轻的女装猎人气得简直不能好好说话,继而他挑起眼角半讥讽地笑道——居然有那么点风情万种的味道,“劳驾,您,不如要点脸。”
刚从裙子底下钻出来的那位也意识到了谈话内容的问题所在,于是闭上了嘴,两个男人在女厕所里面面相觑。
“你怎么还不走?”卡拉波斯等了一会儿,忍者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意思,他终于憋不住问他,“你不是要去杀他吗?”
“你不是给他下了泻药吗?”忍者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在等他来啊。”
完全没有什么错误。
除了性别。
“这是女士洗手间。”女装猎人和他并肩看着面前一个个带着门的单间,“他就算被下了泻药也不会来女洗手间上厕所的。”
忍者和卡拉波斯差不多高,因而也算不上矮小这个词,想必从小训练那些缩骨的技能是很痛苦了——卡拉波斯是还没长开,对方则已经走到了终点。
忍者青年走到了门背后,把耳朵附在门上,倾听对面是否有动静;卡拉波斯在裙子底下的腿相互蹭了蹭,他松了一口气,安心地感觉自己的折刀好端端地绑在那里。
“别紧张,我没动你的刀。”忍者头也不回地说道。
夜宴当日出了一点骚乱——毕竟主角死了。卡拉波斯倒是不怎么慌,作为接应人员的正是他的发小;他自此之后没再见过那位躲在他裙子下面的暗杀猎人,不过他的名字开始逐渐传开——长得好看的男猎人还穿女人的衣服,本来就是个容易让人记住的特点;卡拉波斯二十四岁那年,他的接单逐渐做出了奥错的区域。
倒霉的忍者猎人正好在那一年死。
◇
千里壁垒•腰斩。
百玩不腻的裙底藏人梗。
卡姐可能年轻的时候动过心吧,我是说约炮,虽然之后发展也可能谈感情。
如果忍者君不死的话会变成炮友和同居人?但是他死了。
纪念诸位每个人年轻时都会有的那位知名不具。
卡姐真是我创作过的角色里最普通人的一个了……除了有女装癖。最初给他的key是蝼蚁于命运。
so,让我期待一下下一章剧情吧。
雪上加霜(中)
2060字
倦鸟回巢,双星隐现。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耸起肩膀,在交谈之中升了个懒腰,大张的口腔中似是能塞下大把钞票。
——然而他们守口如瓶。
他们无心地活动着酸痛的肢体抬头向外张望,西奥倏地收回目光,移动到远一点的便利店里。
他的心连同夕阳一同下沉。
在之前的几天里,他得到了一点线索,并努力把它们连了起来,然而这些点燃希望之火的纤细引线轻易地因知情者的死亡而断开,只留下一片狼藉的废墟。
西奥在事发后立即试着联系他所知道的情报贩子,一个没有联系,一个一无所知,还有半个——走南闯北的运货员也许会知道点什么。
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拨出那个号码,原因无他。
恐惧。
如果对方依旧一无所知,那么,他就真的不知该从何入手了。
西奥不是没试过利用网络,可他找不到正确的询问信息的地方,每次都是在白白的为谎言付费。唯一一次,他费尽心力解出了一套免费的、据说“奖励是能告诉你未知之事”的谜题,可在那之后没有任何相关人员试图与他取得联系。
无论如何,该先吃饭。
西奥站到了冷柜前,他的手机振动起来。
“不,我不需要,谢谢。”他挂掉一个推销电话,接着又一个打了进来。
“请问需要上个保险吗?”年轻女性的声音充满令西奥更觉疲惫的朝气,他想立即挂断,又有一点舍不得,心不在焉地施舍给对方慷慨激昂的宣讲一些回应。
——我为什么这样做?
他不解地质问自己。移情作用是他勉强能接受的答案之一,然而电话那端的声音太过清脆,并不像是火焰一样的瓦莲京娜。
可他还是站在冰柜前认真听了好一会儿,提了几个问题,甚至允许了心满意足的销售员下次再打来继续介绍。在挂断之后,他带着嫌恶的神色把这个号码拖进了黑名单——也许这是什么和声音有关的命烛。
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但西奥拒绝让那个模糊的念头展露真容,他隔着一条街眼看收容所的大门关闭,思忖着有没有可能半夜溜进那里头去,随即他因冰柜散发的寒气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把随手拿起的便当放回了原处。
不可能。
溜不进去的。
如果进去了又染上了病,却没发现瓦莲京娜——那该如何是好?
备受瞩目的新药并非百分百有效,晨星报社的大量人员死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我能怎样?我只是个普通的牙医。
西奥说服自己不要冲动,他看似冷静地坐回窗边又一次滑动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实则什么都没有读进去。纷乱的思绪与愧疚感沉重得让他抬不起头。期间有人来试着搭话,他们同样颓唐而彷徨,可西奥没有理会任何人。
他一直僵硬地坐着,低着头,直到自己对面的椅子伴着噪音被拉开。
运货员不请自来。
如果我有这样的体格和性格——西奥的视线短暂地落在古尔身上,又匆匆离去。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另一个人——他很快驳回自己的异想天开,开始用语言驱赶对方,运货员不为所动甚至开始享用晚餐,热食的香气钻进西奥的食管,他听见自己的胃部开始轻声抗议。
也只有胃部而已。
西奥的精神依旧被大片的阴霾占据,他冷眼看着古尔拿出属于他的那份酬劳,两片下垂的嘴唇胶合在一起,既没有道谢也没有动手接过的意思。然后他想起运货员也许为自己带来了其他东西,这才强打精神,遵照对方言语中的期望收下钱款打开饭盒——意外的还不赖,蔬菜足够清爽,没有什么让人心烦的色彩——按照每口咀嚼七次的频率安抚从一大早起就饥肠辘辘的身体。
然而缓慢的进食速度让他越是食用越是饥饿,真正填饱他肚子的是古尔不中听的劝慰。
一开始他说得还算在理,瓦莲京娜自由散漫极了,想到什么就会去做,可再后来……西奥不明白古尔既然和瓦莲京娜相互吸引为什么还要在话里话外否认她的价值。
他一点儿也不想听那些不着调的猜测和开导。
——你知道我们的什么?
他几乎要皱起眉出言指责,但他的口中还残留着古尔赠送的食物。
——我当然知道她不可能属于我。向来如此,她只属于她自己!
他想用餐具指着古尔说话,或者更干脆一点,把剩下的饭菜倒到送货员的头上。咀嚼变得更加彻底而迅速,西奥不得不承认古尔所言大多是正确的,但依旧为瓦莲京娜的选择而感到悲伤。一点蔬菜卡在他的喉咙里,让他如鲠在喉。
而运货员呢?他早已把自己的那份吃了个精光,惬意地瘫在座椅上将自己的想象东拼西凑成一把把刀刃,像掷飞镖似的不断往牙医的心上扎。
可就连这些东西,他也听了许久。
西奥喉头滚动,他直到最后都没有直接打断古尔,只是委托运货员帮自己扔掉吃到一半的便当盒,又在稍微消化掉呕吐欲之后转移了话题向古尔讨要先前预定的东西。
一支崭新的试剂被交到了他手里,而后是情报贩子的一点消息。这让西奥好过了一点。他看向窗外,夜晚伴随星星点点的灯火升起,照得外界像是他在终端上见过的海洋。而与诊所不同,充盈暖黄色光线的小小便利店,大概由外界看来会有如灯塔。
西奥重新挺直了背脊,傲慢地斜了运货员一眼。
“你的废话太多了。”
在他审视的目光下,后者收拢自己局促的笑意,嘴角的纹路变得紧绷起来。
这让他显得顺眼多了。
西奥接着慢条斯理地给他挑刺。
“你说的比推销员还要多……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在瓦莲京娜回来以后,我愿意听你说个够——长期有效——你要不要把这句话录下来?我可以再说一遍。”
这话已算是刻薄,但西奥随时能倒出更恶毒的来。他像只落单的河豚,一方面张牙舞爪地武装自己,一边又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的渴望袒露无疑。
——什么都行。来和我,多说几句吧。



“哥哥,我们家都不是尤金的人吧?”
很多年以前那个小女孩这么问他。
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对了,对了………………
“是与不是,都没有关系吧?”
——————
早六点,雪城的太阳还没有从终年不化的雪山头出现的时候,湿重的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在低智能AI-Real发出第一声蚊蚋声的时候,他瞬间睁开了眼睛。
就算有意保持,他也是25岁的人了。正常来讲再过5年就该听不见蚊蚋和现代的各种年轻合成音了。
——,
——。
第三声结束,Real再度回到休眠状态。别的功能都被他“拆”了,留下这个声音也不是为了叫醒他,而是给什么人提醒“这里的人醒了”和保持状态。
因为种种缘故——他还能听到这个声音15年左右。至于40岁往后的事情,
猎人能活那么久吗?
更何况他还是某黑帮的现任领头人。
——
时隔多年,他还是会梦见她。
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潜意识在作祟,亦或者是他有意为之。
他不想忘掉她。
“Jun,你还在找你妹妹吗?”
烟雾缭绕的某处地下酒吧里,有人这么问他。
“都这么多年了……”
“嗯。我不会放弃的。”他如此回答道,同样吐出一口烟——这可不便宜,自诩“遵纪守法”,自然是要多交一份吸烟税的。
“这么多年了,我也很想知道她是死是活,过得怎么样。”
然后酒吧里闯入了某个格格不入的人——瘦小又灵巧,透着不是这边的人的气息。
“——水野纯在哪儿?”
她带来了他最想听到的消息。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