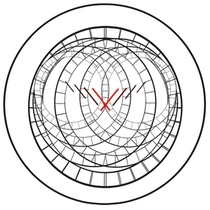一个由国王们主宰的世界,
君主与国王们的交流与日常,
亦或是非日常。
详细企划介绍请参照公告中“国王企划说明书”企划中途也可随时加入,欢迎各位新王的到来
国王企划
QQ群:535678101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陛下。”语毕,黑发男子清了清嗓子,并向面前的王行了个礼。
“欸——为了避免感染竟然托人转述给我吗,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呢。”
“(重点不是这个吧!!)”
“欸话说回来那个米勒夫人我好像听说过她啊……嗯嗯对……似乎是跟父亲有点来往。博学多才但是脾气坏的很甚至还无视王权。嘛不管怎么说都觉得就是个臭大婶嘛……”马隆拖着腮帮子在办公桌上(自认为地)小声嘀咕。
“(声音太大都听见了哦……)”
“过会把咱们的小医生叫来吧,我想问问他的意见。”
男子清楚得很,马隆口中的【小医生】便是指王宫里那位脑子里装满了各类药学知识并且在化学方面小有成就的天才少年【雷莫】,但是……
“不和大臣们谈谈么,陛下。”
“才不要啦——他们会把事情变得很麻烦的!”想到大臣们开会时那东一句西一句的唇枪舌战,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论和仿佛使人置身于菜市场一般的状态还是让马隆不禁感到一阵头疼。
“总之就是给给那个老大妈——啊呸,那位夫人和她的学生提供一个与外界隔离的住所以及各种资金和医疗手段对吧!”
“简单来说的话……是的陛下。”
“那就去做,据我所知火山附近有一个前不久因为矿工转移工作区域而废弃的临时旅馆,把那里整理一下让他们住进去……火山附近温度比城内高些,没有蚊虫亦或是行人所以不用担心病毒传播的问题。资金方面的话先提供生活所需的量,若是需要其他方面的到时候再提……”马隆深吸一口气“至于医生,我比较信任雷莫,当然了他要是不喜欢那老太婆——啊呸米勒夫人的话我们就去找王宫内其他医生,还有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
“没事,我去吧……”
位于自己左侧不远处的沙发上,传来了只有在雷莫刚睡醒时才会出现的慵懒青年音。
“雷莫——?你睡在这我都没……啊,关于米勒夫人的事都听见了吗?”
雷莫从沙发上坐起,脱离了积攒已久的温度使本来就体寒的他虚起了眼。
“嗯,其实一个小时前就醒了只不过懒得爬起来……”
“那属下就先……?”见自家国王日常犯蠢,他憋笑着准备出去。
“等等”马隆叫住了准备离开的那人“米勒夫人带病回国的事不许传出去,王宫内也不许跟其他人提起……对骑士长也不行!要是引起啥民众恐慌啊或是重臣造反什么的可太麻烦了,明白了吗。”
“是,属下绝对守口如瓶。”
他默默关上了门。
乡村田园生活要结束了(。
接下来应该是魔幻探险副本了(。
———————————————————
在第六天,迦亚期盼已久的回信终于到来。她神情激动,拿着信纸,把上面的文字细细看了好几遍才把它烧毁。“‘制造更多的灾难’,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迦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演员到场了吗?我想是的。宫廷也已经为他们搭建好舞台,现在只等好戏登台。”她这么想着,又叫来使女说:“我们在这里呆的够久的了,我的事情已经办完,是时候准备启程,去奇美拉的首都。”命令被传达下去以后,迦亚又感到百无聊赖,独自一人到庄园外的田野里散步去了。
这片又大又空阔的土地,散发着一丝像墓地一样的气息,这是迦亚想起了利斐利的教堂——那里也像这样,令人不禁心神安宁。
然后,她又一直往前走,走到山脚下的河边,站在那儿呆呆地瞧着河水想心事。今天的天仍然是阴沉的,看样子是要下雨了。迦亚叹了一口气,随后听到有人对她说话:“我从来没有在这一带见过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她回头一看,发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不算瘦弱的少年,他身上穿着的衣服干净而布料粗糙,像是在附近村庄出来玩的小孩。迦亚的眼神在对方身上转了一圈,才回话说:“我从北边的国家,利斐利来。”
“一个人?”
“和我的兄弟姐妹。”
“哇,”少年夸张的怪叫一声,“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国家的人,听说你们信仰死神,真新奇。你们有什么有趣的仪式,比如说活祭和自杀狂潮?”
“没有。这只是人的误传,我们信仰死神切尔滕,是为了延续其文明的灯火,不全是为祈求牠的庇护。至于自我了断,更是件会遭到众人唾弃的恶行。”迦亚回答。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我都听不懂你想说什么。”少年感到无趣,又跑走了。迦亚好笑的摇摇头,并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番谈话太过莫名其妙。
在庄园里的格哈德,可没有像迦亚那样的闲情逸致,他坐在躺椅上,手里把玩着一只玻璃做的双陆棋子。“我多次请求您带一些真诚的、能真心实意同我谈话的人来。”格哈德皱着眉头,望向他的使女,说:“您是蓝衣使女,该有分辨满口胡言的骗子,和有真才实学的医者的能力。”站在他旁边的使女身材苗条,挂着一副冷漠的面孔,握在手中的刺刀,还啪嗒啪嗒的往下淌血。她说:“在偏远的小地方,您想要我找怎样的人才呢,先生。您不去大城市找医生,而是在这里……我看,您只是在难为我。”
“我没有。”
“请听我说,先生。你对那些只会放血,灌肠的医生愤怒,命令我砍下提议您服偏方、服毒的人的头,我是能够理解,并甘愿照做的。但您不奇美拉的草药学半点信任,认为它违背了《医典》的基本,还对一个真心实意为您撰写药方的医生恶颜相向,把他赶走了。先生,我只是您的使女,无情的侩子手,我还能做什么呢!”
格哈德的脸色因她的话变得苍白:“原来你是这样看待我的,你这可恶、傲慢的侍女奥莱斯,我要像清理垃圾一样赶走您。”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先生。您早就说过要赶我走啦!在六年前。”使女耸耸肩,并对她的主人翻了一个白眼。这个蓝衣使女是隶属宫廷的首席女官。虽然她以使女的身份为宫廷处理事务,但也是拥有贵族头衔,出生大富大贵之家的世族子弟。
她比迦亚女王还要年轻,她才二十岁。她和利斐利多数女性一样,大胆、坚强,是个自由派。可她却没有像路德维希那样漂亮的英武气派,也没有快活的性格,从外表看,她总有一种模糊不定的冷淡气质。因此路德维希常叫她做‘拉托那’。
格哈德还想对使女再说些什么,却突然看见迦亚从门口进来了,于是他干脆站起身,给女王行礼。
“路德维希呢?我在哪里都看不见她,一大早她去哪了?”迦亚问他们。使女答:“在七点的时候,她就骑着马出去了,也不肯让侍从跟着,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
管家那匹备好鞍的马正站在马厩里。路德维希上了马,疾驰而去。
她刚出门的时候正好撞上做完早课的格哈德,格哈德用嘲笑她一朝转性不再怠惰。路德维希本来想反驳他,但是强忍住了。她按耐住自己的怒火,因为她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她骑马走过庄园范围内的树林和荒地,看到几只昆虫在空中低低的飞旋——这是快要下雨了的征兆,可是天上却不见一片云朵。
在她还年幼时,她就曾经骑马走过这条路,知道这里的每一处坑洼地,还知道在平坦的田地尽头有个小镇。她能回忆起镇里民居和商铺的分布位置,乃至它一些更加细小的地方,比如铺满小石子的峡道和发灰的石墙。因为她的母亲,出身奇美拉平民阶层、被卖到利斐利为奴时与主人私通的那个女人,她的家乡就在这里。
这个下等人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还生了几个杂种妄想继承家业。路德维希从小听着这些话长大,虽然没有对母亲的出身抱有不满或是鄙夷,但她始终深切地相信父母是不幸的,也不可能是幸福的。两个身份地位悬殊、过去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即是再深爱着彼此,也不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同,更别谈思想上、灵魂上的进一步交流。他们的爱情在她看来,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但要是现在还提起母亲的出身,或是认为过去的事情还可挽回,那就无异于不愿意正视已经盖棺定论的事,是软弱的表现了。
现在正好是集市的时间,路德维希在小镇的门口下马,踏了踏脚甩下沾在靴子上的灰尘,牵着马走进市集里。她这副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装扮非常引人注目,更多人用没有恶意的视线打量她,当有人认出她那张和母亲相似的脸,叫她‘露维亚’时,她就笑着向对方点点头,和对方寒暄几句。
路德维希依照母亲的嘱咐,去镇子上的成衣店买几匹绣有母亲喜爱的纹样的粗布。她故作冷漠,言词谨慎,可还是被店主那个听见她的声音、从里屋走出来的老母亲认出身份,只能她热情的问候里落荒而逃,手上除了布匹外还多了几条颜色艳丽的长裙。
这镇子对路德维希的热枕令她有些难为情。或者说,他们是对她的母亲泰蕾萨充满了热情,继而把这感情加付在女儿身上。不仅是路德维希,她的兄弟姐妹们也以有泰蕾萨这样性情温柔、心地善良的母亲为荣。这个开朗,正直,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的女人赢得了故乡的赞美,而她的女儿则因为这份关注而感到了无所适从。
路德维希一直牵着马走到镇尾,最后在一户农家的门前站住了。她把双手放在胸前,像个手足无措的少女那样深吸一口气,然后抬起手推开了门。“姨母,我是泰蕾萨的女儿露维亚,为您带来母亲的问候。”她说。
迎接路德维希的是一个热情的拥抱。盘起头发、衣着打扮入时的女人拉着她的手带她走进屋里,对她的到来表示惊喜。
路德维希难以招架这样热烈的场面,她磕磕绊绊的说:“是的,姨母,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最近母亲有和谈到您呢,她对您的思念依旧不减,托我送来她的问候。”
她把母亲嘱托的信件交出去,可对方不以为意,仍然执着的询问她的生活和情感上的问题,到最后,路德维希甚至以为自己只会说‘不是’或‘是’这两个词了:“是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今年二十六岁……不,没有婚配者,也没有为之心动的人……不用劳烦您费心,这种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不是这样的,是我穿不习惯裙子和颜色鲜艳的衣服……”
在与她这个平民的姨母的对话里,路德维希感到既含羞又慌乱,因为在利斐利,没有谁会、也没有谁敢直白的对她说私人的话题,对她表露长辈式的关怀。但是她总能在在母亲的故乡里感受它,她称此为‘甜蜜的烦恼’。
可惜路德维希不能只是泰蕾萨的女儿露维亚。
———————————————————
《医典》 伊本•西那的那本(
拉托那 Latona,罗马神话中的暗夜女神,神性是隐匿、模糊、静止
露维亚Luwia,路德维希的昵称

【突然最終事件炸出來的東西(劃掉)變革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的】
【其實zp和mf是先有結局再有故事的角色】
【各位請把這一段當作“還沒發生但總有一天一定會發生的事情”……親媽劇透(好像不對】
【以後有互動/活動還是會參加的會的只是這幾個月很忙而已嚶嚶嚶】
----------------------------------------------
滑輪因為承了重,在繩索的動作下互相擠壓摩擦而發出的細小聲響。無數的燈在他周身忽明忽暗,融合成一片柔和的光。蜘蛛的旗幟在他背後飄揚,雙頭蛇的旗幟在他眼前燃燒,被風吹散,碎成在他腳邊,甚至是在背後城市中飛舞的鮮紅花瓣,包含著火,絢爛奪目,彷彿在慶祝即將發生的事情——他記得捷芬登基的那一天,樞城也是這麼飄揚著花瓣,如雪一般,卻怎麼都感覺和四周的景象絲毫不相稱。
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什麼都錯了。
他閉上眼,感受空氣中緊張和期待的信號,所有眼睛都在他們身上,期待著這場鬧劇的最後一場戲。他停下腳步,前方那塊巨大的黑影一直延伸到他們頭頂。就要開始了,杜倫對自己說,接著在寂靜之中抬起一隻手。
那面黑影從中間分開,為他們敞開通往王座的道路。
掌聲響起。
【嘉戴諾王國 城堡內部】
杜倫帶著一小部分士兵踏入紅堡,將剩下的佈在城堡周圍,確保沒有人能逃走。樞城和紅堡都沒有城牆,雖然攻打簡單,但是因為散亂的結構,和城堡周圍那一片森林,要找到一兩個潛逃的人幾乎不可能。好在他們進來的時候沒有遇到任何阻礙,一路上殺死的人不超過二十個,都是梅菲斯手下的人。大部分城中的士兵直接投降,甚至加入他們的隊伍。杜倫一路上檢視扔下武器的侍衛,眼中雖然帶著驚愕,但更多的也是釋然——連他們都知道,比起殺一個督頓家的人,大災是更加可怕的東西。
無論是蒐集武器還是慫恿士兵和將領倒戈,和諾圖殿下一同帶兵攻入紅堡,說服梟爵在遙遠的西邊假裝對此視若無睹,都是他們計劃已久的,從捷芬將大印放入那奸臣的手中那一刻就開始了,只不過他們沒有想過這一切會來得如此之快,也從未想過事態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挽回的地步。最初他們的計劃只是以王無能和縱容腐敗風氣滋生為由攻進樞城,挾持捷芬逼他將王位讓給諾圖,在王權脫離了惡黨的影響後將其徹底清除,誰都不需要死,一切都會回歸正軌。
可是就在昨日,捷芬在王座上宣布要廢除舊法,編寫新的法律——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抉擇,杜倫聽到的一瞬間腦子硬是空白了好一會,一個統治的資格全部來自與神聖的王法的家族宣布廢除王法,拋棄那支撐了這個國家千年的根基,更重要的是,等於將撰寫法律的權力放到了梅菲斯和他背後的奸臣手裡——不止將大印放到了那人手中,還準備將整個國家交個那個人。
他們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攻打城堡,但就連這樣杜倫都覺得太晚,王做出的宣言早就不可能撤回,他們只剩下唯一的選擇。
“找出捷芬,扣上叛國之罪,砍頭示眾。”諾圖如此命令道。
為了國,這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更大更重要的事物,一個人什麼都不是。可為何他心中的躁動卻一點都沒有因為自己給的藉口而平息?
國王在暴動開始時已經不見踪影,連貼身的侍衛都不清楚在哪裡,杜倫想大概是捷芬自己心裡都清楚此時沒人會願意幫他,就打算只和梅菲斯一起逃走,無論如何,從他們到達樞城到佔領紅堡也只過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加上城中的內應幫忙,他們不可能已經逃出這棟建築。
內心深處,他卻有點希望捷芬已經跑了。就這麼結束一切,那個不負責任的細小聲音低語道,接下來怎麼樣都好,反正諾圖已經能穩坐王位了,要是找不到捷芬,也就不用殺他了吧。
一個士兵將城堡的圖紙拿了過來,杜倫接過看了一眼,迅速地開始指示士兵搜查整個城堡。“紅堡遍布暗道。”他說,“不要漏下,每一個小隊至少帶一名在這個城堡裡長住的人員,侍衛或者傭人都可以,無論是誰,凡試圖逃跑者立刻逮捕,要是有人持武器反抗,可以就地處決。”接受了命令的士兵分成小組散去,杜倫才回頭看向他背後的另一批士兵,“你們跟我去搜查地下室。”
這是你的錯,杜倫。
他在小隊前方,小跑下窄長的樓梯,不知道是因為原本這地方的空氣還是因為緊張,他覺得呼吸有些困難。
這都是你的錯,杜倫,你第一眼就看出梅菲斯心懷不軌,卻什麼也沒有做。
他和隊伍分開,選了一條走廊的分支走了進去,雖然地下室的秘道比上方更多,但大多也都是沒有出口的死路,不是被建築壓得變形就是被山坡上滑下的土塊堵塞。他也沒什麼心仔細尋找逃走的人,就算責任心驅使著他前進,可是在這個無人的走廊中,他的步伐已經變得過於沉重。
明明只要一刀就能將這些防範於未然,可是你沒有。
搖曳的火光下他扶著牆彎下腰輕輕喘氣,手扭皺了胸口制服的布料。就這麼回去,那細小的聲音又說,回頭,對諾圖說你找不到國王,你盡力了。
現在好了,捷芬必須以死謝罪,這全部——全部都是你造成的啊,杜倫,你還在想如何補救嗎?多麼可悲——
一聲突如其來的撞擊聲趕走了他的雜緒,彷彿瞌睡著的人聽到自己的名字,瞬間就將他腦中的弦全部繃緊。是金屬敲在石頭上的動靜。杜倫倏地直起身,朝著聲音的來源找去,摸索著石牆。
“咯噠——”
他面前的石牆稍稍裂開一個小縫,背後微弱的光線顯示有人在裡面,卻感受不到任何空氣流通——秘道盡頭的門還是封閉的。杜倫推開門,也沒有打算將其關閉,就這麼敞開在身後。他抽出腰間的劍,不管誰在裡面,剛才的聲響顯示對方持有武器。他問到濃重的鐵腥味。受傷了嗎?
裡頭的人聽見他的腳步,驚喘了一聲回頭。
“杜倫?”
杜倫停下,劍尖垂落指向地面。
捷芬笑起來,扔下手裡染血的利刃,提起燈向杜倫走來,白色的衣服上也有血跡,可是卻沒有任何受傷的跡象——杜倫本來想鬆一口氣,又因為自己找到了逃跑的國王而感到驚慌,他那不切實際的希望破滅地太快太安靜,以至於自己都還反應不過來。
國王走來時還像是什麼都不曾發生,外面沒有暴動,親王也沒有造反,他只是如往常一樣走來和杜倫寒暄,邀請他參加夜晚的舞會,每走一步都能在他心裡激起漣漪,或許他可以……杜倫的目光無意間掠過捷芬背後的黑暗,隱約辨認出一個人影,在眼睛逐漸習慣暗處時他終於看清了——
梅菲斯,那讓他一直憎恨到現在的人。騙子。叛國者。引誘他的王墮落的元兇。
此時此刻那黃眼的惡魔斜倚著鐵門坐在地上,沒有任何動靜,身下的血表示他傷得很重並且已經在這裡好一會了。“你……”杜倫開口。
“怎麼可能,放心吧,梅菲斯還活著,只是逃不了了而已。”捷芬回答。“我還以為終於有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但顯然你們都是一樣的,是嗎?”他抬頭,笑意被底下的悲傷和絕望啃食,不是為知道自己即將迎來的命運也不是為手中的王冠被人奪去——僅僅是因為一個人的背叛。“可是我做不到,杜倫,我沒辦法……”
“要是陛下希望的話,我能……”
“你敢!”
面前的人用着坐在王座上時的語氣呵斥他,他早已不需要聽從,但仍舊保持沉默站在原地。捷芬口中每一個字句都讓他感到難受,他永遠記得第一次見到捷芬,小小的手指纏著繃帶,眼中恐懼且無奈,捂著被打了的臉也不敢哭出聲,在那些人的掌中像個玩偶。他記得聽到捷芬一遍一遍地跟他說梅菲斯不一樣,還因此和他一整個月不說話。他記得看見捷芬背後那個身影,伏下身向他低語。他記得自己夢想過在擁諾圖上位後自己能接管這被放逐的王子。
捷芬走回走道後方,放下燈,蹲著檢視門邊幾乎沒了呼吸的梅菲斯,就算知道只是徒勞,眼神中依舊警告杜倫不要靠近。
他也記得他的王越發殘暴,不再聽從眾臣的告誡,疏遠親族疏遠貴族,將一切託付給錯的人,就連現在,知道了所有謊言背後的真相,也放不了手——
不都是你的無為造成的嗎?
“對不起。”杜倫說。
對方愣了一下,明顯對這樣的發展毫無準備。
“你道什麼歉?”他站起身,歪歪頭,眼裡不管原本包含了什麼情緒,現在都只剩下憤怒。“你憑什麼道歉?你不是以大義之名來抓我的嗎?不是來這裡跟我說我的統治已經結束了嗎?那就快動手啊——快說啊!為什麼還要裝作聽我的話,還在這裡跟我道歉?!”他順手撿起地上的劍向杜倫扔去,沉重的金屬落在後者腳邊,發出一聲刺耳的巨響,遠處的腳步伴隨而來,其他士兵聽見這邊的動靜了。
“我都已經在這裡準備好了,你卻來和我道歉?!”捷芬嘶聲的咆哮,快步來到杜倫面前伸手準備搶過他手裡的武器,黑暗中抓了好幾次也沒抓到東西。“有本事內疚,倒是一開始就直接站在我這方啊!”他沒有回答,咬著嘴唇幾乎能嚐到自己的血。
突然杜倫感到自己被什麼推向一邊,回神過來才發現是跟隨自己來到地下室的士兵。那士兵握住捷芬原本打算搶奪武器的手,側身一扭,就將捷芬制服,後者也沒多做掙扎,輕聲笑起來,和杜倫剛找到他的時候一樣。就如他所說,他已經準備好了。“長官!”士兵喚道,一邊用手銬銬住捷芬,其他人開始進入秘道,一些人去確認梅菲斯的狀態。“長官……您沒事吧?”
“沒事。”杜倫過了許久才開口。“派人去通報殿下,我們找到逃犯了。”
杜倫走上台階。掌聲,仍是掌聲,無止無盡,化成背景的噪音。他轉身背對白色的城堡,屬於王的城堡,面對群眾,那些為了他所謂功績而喝彩的人們,頭頂便是昏君和奸臣的首級,一排排的人頭,仍淌着血,在這蒼白的城市間卻也不顯得格格不入,好像這存在得理所當然。他面前站著諾圖——新王,不久前才加冕,就在這處刑台下,在被綁在處刑台上等待死刑的上一任國王面前。杜倫覺得這無比殘忍,可是這是必要的,人們要昏君死,而新王必須是推翻昏君的英雄……正因為他們來自同一個家族,流著一樣的血,才要用殘忍來證明他們之間沒有關聯。
新王從隨從手裡的盒子中取出一枚金色的徽章,將其掛在杜倫胸前的銀鍊上,作為對他為這次勝利做出貢獻的肯定,雖然他心裡清楚,這只是延後他弒君之罪的金牌,在他拿刀劍指著王家人的瞬間,已經注定要被送上斷頭台。
要是他當時為捷芬開啟秘道盡頭的門,或許此時便能和他一同死在這台上了吧。
杜倫的表情一如一個優秀的士兵一樣嚴肅,也包含著一個忠誠的臣子接受君主表彰時該有的喜悅之情。
已經太晚了。
他彎下腰,深深地鞠躬。
【對不起將軍的人設從頭到尾就是莓希望,銀不了】
【但DR你最後還是無為啊,懊悔心疼但你還是啥也沒幹啊(笑】
【構想是要呼應前置-1,怎麼開始的就要怎麼結束是不】
【和本家世界觀暴動的理由稍許不同】
【這期中發生的平行事件大概是mf發現事態不對,溜了溜了,zp發現mf要跑,國什麼的誰管,追上去在門口給mf一劍表示你往哪跑,不是說好不離開我的嗎?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mf背後的計劃其實還有後續,可是被nt搶先了,所以還是失敗,nt當了王也不咋地,都很失敗,反正……反正這些人欠下的總有一天也得還】



“在下今晚要回领地去。”
基麦拉正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办公,kurt突然出声使她抬起头来,试图使视线越过叠得老高的书卷未果后,她“啧”了一声从属于先王的大椅子上跳下来,绕到书桌前面去,向那个瘫在沙发上享受正太侍从膝枕的家伙投去了嫌弃的眼神:“躺在别人生殖器上是会戳坏脑子的,离年终祭还有一个多月,你想躲回去偷懒也未免太早了。”
“多谢关心,得了您的经验之谈,在下回头一定找个脑子试一试。”kurt偏头看它,双腿懒洋洋地架在一起,鞋跟直接怼在擦得发亮的沙发扶手上,“这不是有突发事件嘛——有头瘟猪闯进在下的栅栏了。”
“……病人?出现了希莱携带者?”基麦拉皱起眉,她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那场夺走了北方的银凤、让世界都为之颤栗的瘟疫终究是传到了这个国家,她不假思索地吐出极为冷酷的话语,“就算如此,用得着你亲自去么?让你的‘屠夫’来多少杀多少,尸体都烧掉。”
“知道您舍不得在下啦,”kurt一如既往地故意曲解了她的意思,还配合地露出羞涩和愧疚的表情,“冷落君主罪不可赦,但是同未婚妻会面也是在下应该做的事请,让你们任何一位感到寂寞都是在下的失职,不如现在多补偿您一些——”
“滚。”基麦拉已经对它迅捷的思维和无耻中的无耻形成了条件反射,迟些才去筛它话里的重点,“你要见马隆?那瘟疫携带者是从玛尔洛斯过境?”
“嗯哼。”kurt慢悠悠地翻身坐起来,用猫一样的姿势伸了个懒腰,“他说要亲自过奇美拉来一趟,翻过围栏的还是头自诩有文化的病畜,马科隆陛下当然上心。玛蒂尔达上午给在下传讯说已经逮住那家伙了,而玛尔洛斯的求助信估计明天才会以真人的形式寄到您手上。”
“让他不必来王都了,反正他也是从你的领地过境,就由你全权负责。”基麦拉理了理裙上的褶子,想起上次马隆抱着自己大腿一边哭一边差点把她的长袜都撸下来,她忍不住一哆嗦。
“谨遵陛下旨意——”kurt答应得异常迅速,上翘的尾音里带着难掩的欣喜,让基麦拉不愿去思考它感到高兴的原由,这个恶趣味的家伙只要能做完该做的事就好,其它她一概不问。
言毕kurt立刻就从沙发上站起来,由唐为它披上外套,基麦拉想起什么似的,朝唐勾了勾手示意他过来,斜起眼对kurt道:“让沙利文留下来,魔神节收尾需要人手。”
“您这是何苦呢,”kurt故作无奈地摊开手,“在下保证路上只跟他打一炮啦,还是在马上,不会耽误时间——”
“滚远点,立刻。”
基麦拉翻了个白眼,拽着唐径自踱回她的办公桌后面,把羽毛笔塞到唐手里让他去做她女王的功课,再绕出来的时候,kurt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书房里只剩下身后轻缓的落笔声。
“漆黑破开了漆黑的夜色。”
只有有幸目睹过它裹着黑色大斗篷骑一匹黑色骏马在黑暗中疾驰的画面,诗人才能藉由这景象的冲击力写出这样的诗句。
kurt走在一条只有它知道,并且只有它能走的路上。奇美拉的地下布满采空的矿脉和断层,像巨兽的血管,从作为心脏的首都一路延伸向四面八方,个别甚至伸出了国界。这种空层在奇美拉有小部分被改造成了别具一格的地下城,但仅限于位于城市地下的部分,连接彼此的道路一如既往在亘古的黑暗中沉默。
不过在能够寻到方向的情况下,这些悄怆幽邃的洞窟在理论上反而比地面地形复杂的道路还要安全和迅捷,从古至今有不少人试图把荒诞的理论变为现实,包括一路上被马蹄踏碎的那些白骨。
前方骤然转为一段陡峭的上坡路,开始有微弱的光线照过来,kurt由那匹识途的黑马带着它灵活地跳跃,它的眼睛在暗处反射着红色的光,像黑暗中燃起的火焰,也许这就是它不用灯火也敢行于黑夜的凭靠。
光越来越近,黑马看准时机从某个洞口一跃而出,鬃毛擦过密集的灌木丛,kurt拨开那些植被,建筑的黑色尖顶出现在它眼前,那是他的堡垒。
出了树林,kurt下马步行,走了一段路,它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提灯的人,看身材是位高挑的成熟女子,像是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女人显然也注意到它的出现,提起裙子向它的方向奔跑过来,他们看见彼此,都加快了步伐,碰面之后kurt向她张开双臂,两人拥抱在一起。
“噢,玛蒂尔达,”kurt把一只手放在女人的后颈上,让两人的身体紧贴在一起,笑起来,“一年不见,你的曲线越发傲人了。”
“先生还是老样子,爱寻人家开心。”玛蒂尔达与其说并不介意这种亲密的举动,更像是对它的性格烂熟于心,像母亲面对顽皮的孩子一样温厚地笑笑,“唐没有跟您一起回来吗?”
“陛下把你弟弟扣下了,跟利斐利的贸易需要他帮忙调度,忙完我会给你们一起放个假,这一年你也幸苦了。”kurt一边滴水不漏地胡诌一边松开了玛蒂尔达,接过她手里的雾灯抱着暖手,玛蒂尔达为它牵着马的缰绳,和它并肩而行,它开口问道:“在这里等我多久了?”
“两个小时。”玛蒂尔达从胸口绷得极紧的西装外套里掏出怀表看了看,“玛尔洛斯的国王陛下我自作主张替您拦下来了,他一个人来的,招待他用完晚餐后我就到这儿来等您。”
“唐也有你这么乖就好了,”kurt摸了摸她的头,“抓到的那小子呢?”
“他叫彼得里,学者米勒夫人的弟子,确认感染希莱,身上携带有一份文件,据他招供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术结晶’,文件莫斯莉安看过了,确实有价值,我已经安排人复制了一份。”玛蒂尔达不紧不慢地汇报,然后安慰似的冲它笑笑,“那孩子虽然顽皮,但比我更能讨您欢心不是吗?”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到了宅邸的门口,玛蒂尔达解下腰间的钥匙开门,一边回头看着kurt:“陛下没有直接向我说明来意,所以彼得里的事我没有告诉他。他已经睡下了,明天早餐时再安排会面么?”
“不用,你已经做的很好了。”kurt侧过身凑近她,笑容意味深长,“亲爱的玛蒂尔达,告诉我,你让他睡在哪儿了?”
“当然是您的房间,”玛蒂尔达还以会心的微笑,推开门把kurt迎进屋, “宵夜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其他需要还请吩咐。”
kurt大步走进长而空旷的走廊,屋内没有一盏灯火为可能起夜的人保留,唯有落地窗里照进的月光能够作为安慰,一片死寂中只有它身后玛蒂尔达咯哒作响的足音有一丝生气。
整栋建筑像是死的,没有代表时间流逝的钟摆声,也听不见仆人的鼾声,连灰尘都不愿在这儿的空气里漂浮,这里除了黑暗,似乎什么也不存在——除了某颗偶然降临此地的星星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散发着无法遮掩的光辉。
“明天早晨准备沐浴用的热水,”踏上通往自己卧室的楼梯前,kurt在玛蒂尔达脸颊上落下一个似有似无的吻,“两人份。”


致:尊敬的艾拉格特陛下
初次见面,我是玛尔洛斯的骑士长“幸”,因为马隆是个笨蛋不会写信所以由我代劳,虽说我也不会写。
抱歉失态了。
我们的王从信中最后一句得知沙芙王国有会唱歌的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决定要拜访贵国,大约一周后抵达,到时还烦请多关照了。
——玛尔洛斯骑士长幸
p:幸才是笨蛋
马隆才是笨蛋
幸是笨蛋
马隆是笨蛋
幸!
马隆!
【下面的内容一片混乱】
————————————————————————————
“等等,这是情书吧!你的关注点就只在最后一句吗?!”
“情书是什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