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由国王们主宰的世界,
君主与国王们的交流与日常,
亦或是非日常。
详细企划介绍请参照公告中“国王企划说明书”企划中途也可随时加入,欢迎各位新王的到来
国王企划
QQ群:535678101
二连击,我屁话太多,估计还有三连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药丸
其实迦亚是个丑女人你们不要被她骗了(
————————————————
迦亚的小公主在王都领受着宫廷的恩典。平日里跟随各式各样的教师学习,晚上则跟在女王身边参加舞会和晚宴,那些豪华的长眠使她变得目眩。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她通过自己擅长的观察和交流,试图弄清每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和宫廷的奥秘。
这个国家在最初给艾利亚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位国君的巡礼。旅途中,她总能看到比自己出生地还要破败的楼房和建筑,衣衫褴褛的百姓、被粗暴对待的奴隶和他们这一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贫富悬殊,使得习惯于简单朴素的民居的迦亚小公主惊讶不已,她突然发现,在辉煌的贵族和宫廷后面,原来是一个陌生的、人口众多的奴隶制国家。她把双手搭在胸前,跟在女王身后冷眼观察着这些民众,产生了单纯的好奇心,那种心情就像人们看到猛兽时的那样。
和他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利斐利另一位国君的继承人,阿道普•腓特烈•冯•沃伦波尼亚。他的谈吐令艾利亚感到失望,他野心勃勃,傲慢无礼,喜欢在背地里玩弄阴谋诡计。这样傲气的人,却因为艾利亚的优雅举止和聪明才智而产生了异样的难堪。由此沃伦波尼亚不热衷于和艾利亚讨论时政,他同她在一起,总会有相形见绌之感。艾利亚被他这样对待,于是认为他顽固守旧,不能友善对待身边的人,和他始终没能够变得亲密。
在这趟旅途的开始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在驿站时,他为了和我争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马车里来回跳动,使得点燃的煤油灯掉落并在我脚边破碎。”火焰从艾利亚长长的裙边开始燃烧,她大声尖叫,怕得立刻昏死过去。虽然最后火势很快被控制,这场意外只是虚惊一场,但艾利亚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穿着过膝的长裙。
起初,她对沃伦波尼亚的粗暴作风很是反感。在她心中,对方是个“小丑”、“蠢货”,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构想和主张。但是渐渐地,艾利亚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她承认在这个宫廷里,只有和他在一起,她才感到最安全。他们两个的年龄相同,都来自偏远的小公国,在这个他们不甚了解又暗藏危机的宫廷里,在国君庇护的阴影下学习掌权的本领,这是两个日子过得艰难的同道者的相互慰藉。
这次旅途归来后,宫廷生活又立刻把她卷了进去。她回到了玩弄阴谋、暗算欺诈的环境中。在王宫,艾利亚端坐在娜尔思女王旁,学习国君主持庄严的宴会。所有在场的贵族都是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她用目光扫视了这群聚集在国君身边、也将会在未来聚集在自己身边的达官显宦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她生活在一个不谙习俗的宫廷里,身边即没有推心置腹的好友,也没有为她出谋划策的谋士,只有一位即将伴随她数十年政治生涯的妄自尊大的、令人生厌的同龄人,而且到处都布满陷阱,稍有不慎即招致风暴。
身处这种逆境中,艾利亚更加思念她已经半年未曾相见的姐姐。她疲惫至极。但她还必须要参加舞会、出席宴会、更换服饰和妆容,还要防备女王随时提出的考验。
伊利亚同样对她怀有深切的思念,且这些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只增不减。自母亲带着剩下的伊利亚回到迦亚后,她开始为她物色身份相配的结婚对象。按照规定,伊利亚是不能年少风流但贵族地位不高的人缔结婚姻的。其实,她一直有考虑过与地位不及她的人结婚,甚至把地位的标准视为多余,只要对方拥有她向往的学识与聪慧,她就会对对方敞开心扉。
可是再暗自盘算一下,但她那丑陋的容貌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几乎使所有持重的求婚者对她不屑一顾。同样,伊利亚也对母亲安排的相亲宴会、介绍给她的粗俗的平庸权贵大失所望。因为她想要在爱情中寻求求知好学的伴侣,而不是成为一个无知而粗俗的妇人。
但也是在这些看上去永不休止的宴会中,伊利亚结识了自己余生的爱侣。他叫伊凡•拉姆齐,比伊利亚大三岁,举止文雅,酷爱艺术和文学,且才思敏捷。这使得向往文学和情爱的伊利亚为他倾心。而拉姆齐也赞赏这位十二岁少女的谈吐,认为她虽然年轻,但颇有鉴别、判断事物的能力。两个人打得火热,书信往来不断,以至于贵族中爱用恶语中伤别人的好事者开始用粗俗的言语议论他们。
一向冷静自恃的伊利亚点燃了自己,她时常给对方写情书,称呼他为“阿多尼斯”,赞赏他的才华,并把她的感情直言不讳地写信告诉他,即使那只是几行一挥而就的文字,一些热情洋溢的私语。拉姆齐则深深迷恋这样坦率、大方的伊利亚,如痴如醉癫狂到忘我的程度。
他把对方写给他的情书放在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时常拿出来翻看温存。有传言称有一次拉姆齐邀请伊利亚跳舞,他感到情难自已,忍不住把伊利亚抱在怀里,且没有受到对方的拒绝。
在当时,这段恋情不被看好。伊利亚的母亲认为伊凡•拉姆齐出身低微,倾向于让伊利亚和门第更加显赫的科勒•波尔塔•德•格哈德建立联系。他初见伊利亚时才十八岁,博览群书,谈吐优雅,言行举止中透露出身居上位的从容和自持。
格哈德从幼年起一直被各式各样的疾病缠身,他的生活和其他贵族的生活完全隔绝,直到最近他的身体状况稍微开始好转,他才开始自己的政治活动。格哈德第一次对外参加宴会,就被与众不同的伊利亚所吸引,对她产生了恋慕的情绪。他有一种没有来由的预感,认为像伊利亚这样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理解他这个病秧子心中所想,他们之间能够在心灵上进行更加亲密的交流。
然而伊利亚没有因为对方背后所代表的家族权势而对他动心,或者说,她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大贵族都没有好感,她认为格哈德“看上去如同一表人才,身体弱不禁风,承受不起风浪和磨难”。伊利亚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本质:他把阴险和歹毒都隐藏在傲慢后,实际上他既自卑又爱嫉恨。因此除了必要的问候外,伊利亚从未正眼看过他一次。
这样无礼的态度使得格哈德非常恼怒,他的恋心也被对方冰冷而讥讽的话语残忍打碎。作为反击,他当众评价伊利亚“聪明,机灵,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她与生俱来的叛逆”。到了后来,他甚至放话说“女性美好的顺从和矜持与她完全沾不上边,这位不懂得节制持重的小公主迟早会为自己的性格付出代价”。
实际上,自从格哈德和他的家族势力相继远离伊利亚的生活后,她感到轻松了许多。贵族之间的纷争仿佛离她远去,她得以和她同样对政事不感兴趣的爱人一起,像一个自学者那样学习,对什么事都感兴趣,日常表现也毫无窘迫和茫然之感。
但是他们仍然会讨论时政的趋向,因为她的妹妹艾利亚即将成为统治国家的国君之一。两个人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观点。拉姆齐认为国君该待人温和、仁慈,公正而不失偏颇的对待贵族、平民和奴隶。而伊利亚则觉得君王应该在理论上帮第三等级说话,而在实际上依靠一二等公民。要控制住这片光怪陆离的国土,非要进行一番大改革不可。有时候拉姆齐的顽固不化甚至令伊利亚恼怒,尽管平日里她总是很快就原谅对方,并主动表示和解。不过,一旦伊利亚接连几天闷闷不乐,拉姆齐收不到对方寄来的信件的话,他同样也会感到伤心失落。
是夜,鹅毛大雪飘散。
追忆之国的皇宫寝殿中,透过窗外淡紫色的云彩伴着白色的雪,窗沿边已经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屋内,层层帷帳里,一张大床上隐约有一个物体蠕动了一下。
“咚咚咚咚——”鞋跟踩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发出了急促的声音,一个人影飞快的从走廊的另外一头走向了这个房间,而落地窗外的漫天大雪又下的更大。
“我有急事找陛下——”他向走廊两侧的侍从说道,“我要亲自去叫他!”
不顾侍从的劝阻,穿着铠甲的黑发男人飞快的走到房间的门口,“碰”一声推开了沉重的房间大门,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但床上的一团棉被里仍然没有任何被惊醒的迹象,只是轻轻蠕动了一下。
闯进房间的男人微微皱眉,快步走到床边,顺手扯过挂在一旁衣架上的斗篷,“哗”一声掀开床帷,另一只手向着被子伸去——
“唉……唉?!希拉你干嘛唉等等好冷别拽我出来?!”
“别废话,邻国国王被祈母教杀害了,我们必须马上写信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压制邪教了。”
“什么……露娜那边居然……”
……
……
追忆之国国王楚斯散乱着长发,穿着睡袍披着披风坐在床边,听完了骑士长希拉的报告,沉思许久。
“也就是说,祈母邪教的罪恶已经一路向东蔓延到了我国边境,甚至有可能已经渗透到了我过内部,并伺机作乱……”
黑发的骑士接道:“没错,所以肃清邪教分子,并找出混入王都甚至宫殿的敌人,已经迫在眉睫,希望陛下能立刻做出决定。”
楚斯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大腿,“没错,而且必须和其他国家尽快结盟,祈母教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不是我国一个国家能清除干净的,而且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被它威胁,不久前外交大臣有提到伊诺尔和露易斯两国国王欲与我国结盟共同度过这次难关,而我也同意了两国的提议,以及克里斯特•马科隆王组织下的多国联合对希姆顿国的祈母教的攻打,但同时也要防备一些国家可能会趁虚而入……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王国骑士长--希拉。”
“是,陛下,如您所愿。”希拉单膝跪下回答说。
楚斯望着窗外飘雪的天空,轻声说道: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宿命和所谓的爱的话,就算倾国之力也不会让你们得逞。”

【①】
“王”
“……”
“王?”
“……”
“马隆!!!”
“啊啊啊什么事开饭了吗?!”
“你不是刚吃过吗。”
粉发青年无奈地扶着额头,看向面前这位不务正业的王。
“咳……我忘了……有什么事吗?”
“关于您前些日子占星所得的蚊灾的事,想出处理方法了吗。”
“啊那个……我去问了鸠磷来着……想让他放鸟去吃蚊子。”
马隆的眼神飘忽不定,似乎是想回避什么。
“被拒绝了吧,他说了什么?”
“是啊……被狠狠地拒绝了……说了什么【别想让我可爱的弟弟们吃那种恶心玩意儿!】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还去找了鸠晨。”
“你怎么知道?”
“按你的套路就是这样没错了,找他做什么?”
“……”
“马隆?”
“不要……说出来太丢脸了。”
“说。”
“唔……幸……”
他将视线移向面前的青年,并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不许撒娇,说。”
“唉……”
“就是……我问他能不能帮忙一只只拍……”
“……”
“——噗嗤”
“你笑什么啊!!”
“你是傻子吗哈哈哈哈哈哈一只只拍怎么可能拍得完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马隆飞速从座位上起来,捏住了面前人的脸蛋左右蹂躏。
“不许笑啊啊啊!!!”
“王,您要我配制的……幸?”
门被推开了,银白色短发的少年进入房间内。
“雷莫?马隆你找他配杀虫剂吗?”
“什么杀虫剂,王要我配制的是用来引诱蚊子的药水。”
“做那个干什么?”
“果然是一根筋啊……”被称为雷莫的少年有些不满地揉了揉自己紧皱的眉头“这种药水会配合胶水一同使用,用于……”雷莫突然停了下来,看向一旁的马隆,身体微微颤抖着。
“用于什么啊?”
“用于……黏住蚊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马隆你真是个人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的给我闭嘴啊!!!而且这样总比一只只拍的效率要高吧!!!”
【②】
图书馆内。
“打扰了。”
从门外进来了一位黑发男子,手里还拿着一份文档。
“kurt?”
“在下给您带了个好消息来,情报费就用身体支付吧。”
“……”
kurt,卒。
……
“所以到底是什么好消息。”
“在说那个之前……您能不能先把绑着在下的这根绳子解开?”
“不能,有话快说不说滚。”
“在下可是奉命来协助您处理事件的。”
“行吧……保持五十米距离。”
“……”
【③】
“王,我刚看见隔壁的kurt……”
“没事,他会在我们这里暂时住一段时间,拜托你件事,雷莫,把这份文档拿去,然后去通知工坊的人准备给士兵使用的防毒装备……需要的量和注意事项我已经写好了在这里面。麻烦了。我听说那种蚊子名为埃尔徳,在其他国家好像已经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一定要在它们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它们抵达玛尔洛斯的时间我大致也知道了……所以……”
“我明白了,请放心吧。”
雷莫接过他手中的文档,随后匆匆往城外的工坊跑去。
“唉……你还要在那里待多久?”
转身,面向走廊的转角处。
“啊啦……被发现了么,在下只是碰巧路过罢了。”
这个家伙。
马隆曾特地占卜过关于kurt的事,但不论是什么内容,都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被回避了。
也就是说,面前这个人是【不可预知】的。
“……”
“?”
“……”
只见马隆飞快地往后退了几步,并一脸嫌弃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五十米。”
“您说什么在下没听清啊。”
“滚!!别过来!!!啊啊啊啊啊来人啊谋杀啊!!!!”
于是王宫中多了两个飞奔的身影。
【④】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跳过不重要的部分
【⑤】
毒药。
这种毒药的药效能持续9个小时,也就是说9小时后毒素就会被自然降解。
虽说是针对这种蚊子研制的,但考虑到民众和其他动物的安全马隆还是发布了紧急指令。
【驱蚊当日的门禁时间从晚上12:00到早晨5:00调整为晚上9:00到早晨8:00】
【木材产地附近的居民必须在驱蚊日到来之前暂时移居至城内】
【因为药会附着在人和动物的皮肤上,所以请务必管理好家内的宠物以及牲畜】
————————————————————————————
“剩下的……按照计划,之前在图纸上圈出来的几处地方,把【那个药水】安置好。然后我和kurt会在晚上大约10点到达森林外围,就是和城外郊区连接的地方,士兵们会点燃毒药用来驱赶蚊子,风向刚好就是从南至北所以没有问题……幸你有在听吗?”马隆停住在图纸上滑动的手指,抬头看向身侧的人。
“有啦……哈——唔呣呣……圈起来的这几个地方还有风向的事,是你用了占卜才知道的吧?”
“是啊……话说你明明就是半睡半醒的状态吧……!!”
“才不是嘞!”
“啧……”他有些无奈地揉了揉眉间“算了我继续讲……主要就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把所有的都给处理掉,毕竟量实在是太多了,要是鸠磷能来帮忙的话就好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去找他谈谈的。”
“可别使用暴力啊。诶对了,通知参与这次驱蚊的士兵,让他们去工坊二号仓库找雷莫领防毒服。”
“明白了,那我先走啦。”
没有敬语,也没有什么表示告辞的动作,仅仅只是打开门又关上了而已。
“您家的骑士长可真是随性呢。”
“起开。”
马隆忍无可忍地往桌子底下踹了一脚,命中kurt的腹部。
“您可真是有活力呢,马隆陛下。”
没有因被踢中腹部而表露出痛苦的神色,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kurt摆着他那万年不变的面具式微笑从桌子底下伸出手抓住了马隆的脚踝。
“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有解决呢?陛下。”
“速战速决。”
【⑥】
驱蚊日当夜,晚上9:40。
“报告陛下!东面发现避过了药水并入侵森林的埃尔徳蚊!”
门被突然推开,一名士兵进入了房间
“什么……比预想的要快么。”他放下手中的书本,看向面前的士兵“骑士长呢?”
“抱歉并没有在队伍中遇到,需要派人去城内搜寻吗?!”
“不必了。”
马隆以往常的速度从座位站起来,身体却突然向前倾倒使他趴在桌面上。
“陛下?!”
“啊哈哈,被地毯拌了一下。你先归队吧,我稍微迟个几分钟。”
“遵命!”
房间内恢复了原来的安静。
“喂,你打算折腾到什么时候。”
“您这是在邀请在下吗?”
“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
于是kurt又挨了一脚。
【⑦】
“汇报当前情况。”
“是!您安排放置药水的几个地点都捕获了大量埃尔徳蚊,但仍然有相当多的蚊子已经侵入森林,当前正在使用奇美拉王国提供的毒药……”
“毒药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
“十点。”
“九小时的效果……也就是到早晨七点为止,去通知侦查队的监视森林周边区域,遇到漏网之鱼后……”
“后……?”
“直接捏死吧,嗯就这样。”马隆笑眯眯地对面前的士兵说道。
“(陛下您认真的吗……)”
……
早晨7:20。
尽管把目前能用的方式都用上了,可还是没能将埃尔徳蚊全部消灭。
“还有少量是吗……要是不能及时处理掉的话以它们的繁殖速度很快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了吧。”
“需要再使用一次毒药吗?”
“不……虽说毒药是够用,但已经来不及去通知民众了,人要是大量吸入这玩意的话还是会出问题……”
“马隆——”
“幸你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
他惊喜地转身,那里传来了幸的喊声,他熟悉的笛声,还有……
“那是什么……”
马隆指着幸身后的人和黑压压的鸟群满脸懵逼。
“傻吗,这是鸟啊。”
“不,不是……我是说你哪来的鸟。”
“这当然是向鸠磷……”
“马隆!”一旁天蓝色长发的青年突然停止吹笛,没等幸说完话就冲上前来怼着马隆的脑门一顿猛戳。“我可是看在幸说会给我你私房照的份上……啊不对!!算了理由不重要!要是我可爱的弟弟们因为吃了这恶心玩意而食物中毒的话我可是要每天晚上在你床边吹喇叭的!总之给我感激涕零吧!”
“疼疼疼!快停手啊我知道了!!”
“……”鸠磷像是在憋笑似的别过头去,片刻后将长笛移至唇边,向鸟群发出了指令。
【⑧】
事后。
“啊总之真是太感谢各位了,都辛苦啦——我已经吩咐厨师去准备晚餐招待各位了。”
“话说鸠磷你到底养了多少鸟……”
“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的弟弟们都很可爱就是了!”
“你说这话就不怕被鸠晨打吗……”
“别跟我提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大傻子!他一点都不可爱!!”
“啊对了kurt阁下今天还要住这里吗?”幸将头转向一旁正在品茶的kurt。
“如果可以的话在下非常乐意一辈子住在这里。”
“不可以!你给我滚回奇美拉去!”
“看来陛下您就算是劳累一天也还是非常精神呢~看来可以略过去泡温泉的部分直接——”
“来人啊快把他打包寄到奇美拉去。”
【附录】
“对了马隆,你打算怎么处理被药水黏住的那些蚊子?”
“这个嘛……我已经丢给工坊的人处理了,准备挑选部分做成标本,其余的统统丢火山口。”马隆面露微笑,似乎是非常高兴的样子“给奇美拉当做谢礼的那份已经直接交给kurt了,希望基麦拉那孩子会喜欢吧。”
“让我猜猜……药水里是不是掺了什么类似于——手工钻石中会使用到的成分?”
“不愧是幸,的确是哦,用那种药剂的话能完整保存埃尔徳蚊的基因成分,而且提取也非常方便,要是在研究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就好了。”
“但愿基麦拉陛下不要害怕蚊虫才好。”
“啊……我忘了这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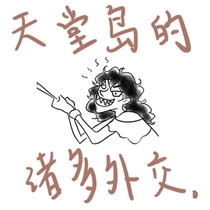

【蒸汽機-3】
【大概是對蒸汽機的後續處理做個交代,順便揭揭左手的壞心】
【嘉戴諾王國 城堡附樓三樓】
他想他曾經是有過別的名字的,也有過一個姓氏,只是一點印象都沒有了,連同曾經住過的地方,遭遇過的事情,父母,手足,全部都不記得了,唯一清晰的畫面便是那片焦黑的石板地,那排了字,燒紅的鐵棍。梅菲斯脫下左手的手套,摸著掌中那塊斑駁的異色皮膚。
“三打頭是西邊的黑市。”年幼的王子這麼說。“我在杜倫家裡看過……”細小的手指順著筆劃描出那排烙上的數字和字母,擔心的神情也逐漸浮現在臉上。“梅菲斯你……絕對不能讓別人看到,沒有身份的人會被趕出去的——”
“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放心吧。”
但最後還是賭氣般地將它一點不剩地抹除,就為了證明自己不是物品而是人。梅菲斯將手套套回去。或許不記得更好。
他推開一間房間的門,溫暖的火光令他的瞳孔收縮成細縫,他看著坐在桌前的人,雖然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卻還低著頭書寫,沒有應答的準備。梅菲斯將身後的門關上,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響,然後他等着,直到對方終於招手讓他過去。
“取到了?”身著正裝的男子問,目光仍舊集中在筆尖上。梅菲斯想著這個人大概也有六十歲,儘管外表比實際年齡看起來更加蒼老,身上還是帶著記憶中那股不可違抗的氣息——如果手裡再握著沾了水的鞭子會更相近,比起在皮膚上燒灼火和鐵,那是更令人害怕的東西。“聽說你們回來得很快,在瑪爾洛斯發生了什麼嗎?”
“沒有,過程異常順利。”梅菲斯回答,坐在男子對面的椅子上。“瑪爾洛斯國王要求的東西也已經在送去的路上。”
“聽說國王軟禁了公主。”
“是的。讓人稍微……修改過信件,捷芬一累就變得很好煽動,我該讓他多出去走走。”
男人終於抬頭看向梅菲斯,露出微笑。“做的很好。”
“謝謝老師的誇獎。”
“圖紙給我看。”
梅菲斯將紙筒舉過桌面,小心地不去碰翻墨水瓶或者堆疊的書堆。“似乎……效率比想像中的要低,也不是很安全的技術,如果要使用必須考慮各方的反對意見。稍早拿去給幾個學者過目,他們說這也能應用於交通運輸方面,不依靠人力和馬匹就能夠將大量貨物從國家的一端運到另一端,人民接受的程度應該會比較高。”
“你怎麼想?”
“我們擁有的影響力還不夠大,現在開始動作也太早了一點,就算能夠拖垮蛇家,王權也只會回到蛛家手中,諾圖誠然不是最理想的王選,他一旦上位我們能插手的餘地也不會剩下多少了。最壞還得考慮梟爵和舊貴族介入的情況……我們得先壟斷一條重點產業才勉強能和舊貴族抗衡,更不用說其他親王。”他停頓,觀察了下對面的人的表情,一抹疲憊的灰藍色中隱約透露出不甘——也是,他對自己說,在皇宮中再怎麼順利也沒有用,這個國家不僅僅是靠一個王在支撐的,有些東西,就算是捷芬將大印送給自己也無法輕易改變。“老師,我認為艾爾文斯大公的忠告並非沒有道理,要和舊貴族搶既有產業是不可能的……”
“不如從新的開始嗎——”
“是的。”
桌子對面的男人側過身,將圖紙展開,立在膝上仔細閱讀起來,眉頭緊鎖著,梅菲斯也猜不出那是在考慮方案的可行性還是對他剛剛的提議有所不滿。
梅菲斯自信自己能夠說服捷芬批准新載具的研發,只要不在謝爾門前搗鼓那個人也不會說話,最得利的尤德勒家族估計會選擇靜觀其變,另外的三家便僅剩跟隨的選項。在這個百年來都畏縮保守的國家裡面應用最新的技術,想必不會比和舊貴族爭奪一個礦或一片田簡單太多,但若是讓人們開始依賴速度與便捷,再逐漸替代掉人力……
這些被稱為王國的器官和脊骨的家族,可能比預期的還要容易撼動。
他的老師緩慢將圖紙收回,遞還給梅菲斯,順手把剛剛書寫到一半的信件撕成碎片。“行,我準了。”
梅菲斯鬆一口氣般地靠上椅背,想著自己終於也能給謝爾交代,連續長途旅行遲來的乏力感同時向他襲來,接下來他只需要應付捷芬就可以了。他閉上眼,有種乾脆就此歇下的衝動,聽見對方起身的動靜,然後一隻手忽然按在自己的頭上,也是他所記得的那份溫和,為了將所謂的神扶上神座而操勞,逐漸被消磨,而他能否理解都無關緊要。“老師手下的人手還夠嗎?”
“你不需要擔心這方面的事情。國王呢?在這裡逗留太久不好。”
“在將軍家過夜,明天還不一定趕得上早朝。”
“快回去,一周後我要聽到研發開始的消息。”
“是,老師,我知道了。”
【mf:去去去過夜去明天別回來讓我也歇歇】
【王國的貴族階級粗略是:頂上王家分了四家,每一家的孩子都有資格做太子,男女無分,雖然不是親兄弟姐妹但是有時候會以親兄弟姐妹相稱;王家之下五個舊貴族,其家長的頭銜都是大公,各掌管一方重點資源;再下去新貴族和其他】
【王國在二百二十六年前正式宣布廢除奴隸制,可是並沒有強制執行,只是慢慢地將奴隸替代掉而已,一般販賣人是犯法的(除非特例),可是購買/擁有不犯法,現在奴隸來源之一為黑市二為帶著銀色牛角徽章的人販,前者會給商品烙印,多為工作用;後者不會,多為娛樂用,一般也不被當成奴隸。和主線大概沒有關係吧不過和mf的人設有關所以提一下,設定全搬過來太多了就意思意思就好了】

“敬启诸王……?”
由文臣呈来的那份信函封着鲜红的火漆,那是一天前由他国使臣递交而来的邀请函,如今正被年轻的王阅览着。
“欸,居然是商会的联名信吗。”
阅读者略微沉默之后,兴趣缺缺的将那信函扔在了一旁。
“今天就到这里吧。”
“但是……王……”
那是伊瑞安接管王国的第五年。
偌大的议厅之中,寥寥无几的文臣都向那王座之上的青年低下了身子。
身为一国之君的伊瑞安只在每周的周五会来到这里,而所做的工作也只有听取文臣们在这一周中收集、汇总而来的国内讯息而已。
完全由心情来处理国事,自他从上一任王手中接管了这里后,昔日那个号称“宝石之国”的富饶国度也已经逐渐衰落,国内那日益壮大的起义军联盟与游行暴动都在宣告着这一事实。
“举办地在哪?”
“在世界的中心之国欧维耶,会以舞会的形式举办。”
随着世界新航路的不断拓展,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愈加频繁起来。而世界各地的商人们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借由此次舞会的名义来拓展新的商机与贸易对象。
“王,这正是个好机会,国内的宝石工艺品就算在他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上品,如果能借由此次与别国建立贸易合作,国民们一定也……”
“这样,那你去吧。”
突兀的打断了委婉进言的文臣,伊瑞安斜靠在王座上,将那信函用力扔在了那文臣脚边。
大殿之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肃杀,那文臣愣了愣,紧接着便是颤抖着抬起头,王座上的伊瑞安再没有多余的表示,饶有兴致的看着那文臣的反应。
随后那文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即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这无法琢磨的君王所杀,因为一句话也好,因为一个表情也好。
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臣失言了,请王不要怪罪!”
跪在那里的人将自己的头重重的磕向地面,在伊瑞安年幼时,服侍这位小王子的仆从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如此向他赔罪。
“欸,我又没有怪罪你,快起来。”
像是为了缓解压抑的气氛,伊瑞安干笑了两声,对群臣摆了摆手。
“这么远的地方我可不想去,就由你们作为使臣出席吧。”
他这么说着,起身离开了王座。
“……王,还有一事。”
“说。”
“城北的起义军已经……”
“给我派兵压下去。”
他顿了顿,停下了正打算离开的脚步,补充道。
“将他们的领袖带来见我。”
“那么其他人……”
“杀。”
随着议厅的大门被重新关合,无数国民的性命也随之一起沉寂。
使臣的列队在第二天凌晨时分出发了。
彻夜不休的镇压与屠杀才刚刚沉寂下来,穿过还未熄灭的战火,使臣们的车队踏着天亮前最后一点夜色来到了港口。
从航路去往欧维耶的方向只需半个月左右,这比马车要快上一倍。
随行的一队人马约有十多人,为首的使臣名为卡莱特,正是昨日向伊瑞安提议参加此次舞会之人。
虽说逃过一劫,但这也不是份好差事。
在航行的这段时间里,他不得不阅读所有能够查到的来访国名单与诸王的信息,虽说眼下国内的局势十分混乱,却也不可让外人知晓,否则将会多出许多窥视这片遍布宝石之地的眼睛。
如果有一天,这里真的变成无主之地,那么会是谁来接管这里?
所有人都在怀念着先王在世时,这片土地上的繁荣盛景。
但是眼下,伊瑞安还坐在王座上,那王冠也还在他的头上,如此军队和群臣就只能听从他的命令,哪怕他并没有身为王的担当。
随着海鸥的鸣叫与水手的指引声,船到港了。
处在世界中心地带的欧维耶如今被格莱塔女王统治着,她是欧维耶王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女王。
为了响应与筹办此次舞会,如今欧维耶王国上下都是一片繁华而热情的样子,无论是王族还是国民,所有人似乎都很享受这次的庆典。
这样一副繁荣而和平的景象,对卡莱特一行人来说实在是太久没有见到过了。
在表明身份与来意后,他们顺利的办理了各项手续,在明晚举行的舞会中,卡莱特将会以伊瑞安王国使臣的身份出席晚宴。
临行前,莫名的不安感也在蔓延着。
即使是身着配得上王国资质的华贵礼服,却也完全得不到相应的安全感。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次出行完全没有相应的护卫军队跟随,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已经算得上是万幸,在平安踏上欧维耶的港口时,随行的一位使臣甚至脱口而出了“感谢欧维耶的良好治安”。
无论如何,在舞会结束后就快些回去吧。
卡莱特这么想着,将那枚精致的红宝石胸针别在了礼服上。
王宫会场比想象中还要恢弘大气,却也没有太过招摇死板,所有的装饰似乎都能彰显格莱塔女王作为东道主的热情与其本身一直提倡的简朴作风。
因为是世界各地的商会联名发起的聚会,那么自然晚会的主题便是“贸易”,不同的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在各个商会的代表与诸王的简短发言后,留给大家的便是可以自由交流的时刻。
然而卡莱特此时却只想快些溜走,诚如格莱塔女王所说,贸易的最前提便是开放——而伊瑞安王国此时的国情,不用想也知道根本不会有贸易伙伴。
正当他打算默然离席时,却注意到了不远处正在与商人畅谈的另一位国王——瓦洛丹的国王,米尔.埃尔蒙多。
他所统领的瓦洛丹,被世人赞颂为黄金港。那是一个无比富饶之地,在米尔的贤明统治之下已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金银饰品的出口国。
而这个国家,曾是伊瑞安王国的贸易合作国,不过这已经是先王在世时的事情了。那时的米尔还未接管瓦洛丹,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也甚是频繁。
而后,27岁的米尔与18岁的伊瑞安同时接管了各自国家的统治权。
五年后的今天,二人所统领的国家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模样。
欣欣向荣与危在旦夕。
这可真是不妙啊。
而米尔似乎也已经注意到了卡莱特——他向正在谈话的商人微笑示意后,迈着不慌不忙的脚步来到了卡莱特的面前。
“您、您好!尊贵的瓦洛丹君主!”
虽然被吓了一跳,但卡莱特还是没有忘了应有的礼数,他连忙深鞠躬行礼,而米尔也大方的点头回应。
“阁下是伊瑞安王国的使臣吧?”
“是的,尊贵的王!在下是使臣卡莱特……请问您是如何知道我是伊瑞安王国的……”
“这个啊。”
米尔顿了顿,指着卡莱特胸前那枚红宝石的胸针。
“如此夺目的红宝石,只有伊瑞安王国才会出产啊。”
“您过奖了……”
如果能就此重新与瓦洛丹建交的话,说不定能够改善一些国内的局势……
但是如此强大的瓦洛丹,又有什么理由来与伊瑞安建交?
“阁下现在的君主……伊瑞安,他还健在吗?”
“您……为什么这么说?”
“不,只是觉得好久没有听到过他的讯息了。”
“……是的,王他还健在。”
似乎是确认了对方的安全,米尔脸上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他叫来了随行的几位侍者,带来了纸笔与信封。
“既然这样,我也很希望瓦洛丹能够恢复当年与伊瑞安建交时的盛景,请阁下转交这信函于你的王。”
甩手利落的签上自己的姓名后,他将信交由侍者叠入信封并封好了火漆。
“……是,我一定会带到的。”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有一封。”
在卡莱特差异之时,米尔将另一封信函交到了他的手中,但这封信上并没有收信者与火漆。
不明白米尔的意思,卡莱特抬起头,发现这位王正在微笑着。
“写封信是写给你们的,伊瑞安的国民们。”
“瓦洛丹的王……啊。”
在阅读了米尔的信函后,伊瑞安发出了一声感叹,随后便是良久的沉默。
“黄金港啊……真是繁华啊。”
“简直就像父亲在世时的王国一样……”
他坐在王座上,似乎有些出神。
“那,只有这一封?”
站在议厅王座阶梯下的卡莱特绷紧了呼吸,点了点头。
“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与瓦洛丹重新建交……”
“……随便吧,你们出去吧。”
“……是。”
在大殿的门关紧之后,跳动的火苗吞噬了那封来自米尔的信函。
“不!不,普拉玛夫,你这个金发的恶魔!”
衣衫褴褛的男人用两只满是鲜血的腿挣扎着,筋骨被挑断的痛苦就快无法阻挡他想要冲上台去杀死仇人的欲望了,但还是只能被两条铁链拖着向前。
“快,快放开我!让我掐死那个台上的伪善者……你们没有良知的——啊!”
急切的话才被罪人喊出,但男人马上就发出了另一声沙哑的痛呼,刽子手拧断了他的下巴,包围刑场的人群为此欢呼叫好。
他们一个两个面红耳赤,大声地赞颂着神的圣罚,感谢他们的天父惩罚了这个叛国之徒。
普拉玛夫背着手,站在高台上俯视着下方汹涌澎湃的人群。那些愤怒狂热的人民们高呼着加纳德拉的威名,又在罪人头颅落地的时候爆发出欢呼,几乎穿透了云彩。
待刽子手将尸体拖下血腥的刑场,他张开了双手,换来广场上的一片肃静。
“如诸位所见,侵犯神圣威严的罪人已被斩除,至此,我父加纳德拉的荣光倾斜于这片染满罪人鲜血的大地上!他护佑着你们——”
令人恶心的宣言。
扶着墙壁的,普拉玛夫用温热的湿布擦了一遍脸,半晌才从腹部传来的恶心感中缓过劲来。
在这阳光明媚,空气却微凉的天气里,他的旧伤最容易重犯了,但这可不是铁血统治者向他人示弱的理由。
“嘿嘿,还好吗?我亲爱的普拉。”
“你给我让开。莫兰德。”普拉玛夫回头怒瞪了王国的神授将军一眼。
“噢,是,是——国王陛下。”
莫兰德微笑着摊开了手,就把那颗刚从刑场上摸来的头丢到了角落里去,他知道普拉玛夫绝对是厌恶这个玩意儿。
“迷恋死尸的家伙要下地狱的。”普拉玛夫转过身来,捶了一下挚友的胸口。
“我只是沉迷那份沉寂,普拉玛夫。”
他不跟莫兰德辩论,转身唤了侍从,走了出去。
凄冷的凉日在天上挂着,传说中以神眼化的太阳散发着光芒,金光穿透单薄的云雾,却没给两层礼服的他带来一丝温暖。
再加上远地传来的噩耗,年轻的王早早逝去的消息。普拉玛夫一想到这个就叹了一口气,心中深怀对此的遗憾和感慨,也有些许的难以释怀——又少了个北方的贸易人力来源。
他不紧不慢地下了马车后,坐在新缮的精致花园里的外交首席大臣就一摇一摆地迎了上来,就连宽厚的远东绸服也难以掩饰这家伙的满腹肥油,同时花园里的侍妾们赶紧擦去了委屈的珠泪。
“啊哈,我亲爱的国王陛下,您今可算到了,来来,这是来自奇美拉上好的热烈辣椒酱和肋排……”
“瘟疫扩散到哪了。”普拉玛夫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席子上,手随意地搭在圣剑的柄上。
外交官有点支吾,嘟哝了半天才道出了有点骇人的事实。
才两星期的时间就扩散到了其他的国家里。
普拉玛夫低着头寻思着办法,同时抬手止住了面前这个再次欲献殷勤的圆球。
“那就这样吧,先封锁北方的所有城门,终止一部分外交贸易,询问城内的异国学者是否见过这种病状。”普拉玛夫皱着眉说,“如果能发现外部症状的话就隔离患者,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极端手段。”
大臣听着连忙点头,吩咐从官记下,接着起身凑了过来:“还有其他嘱咐吗?陛下。”
“有的……”
“是吗,那么就——”
砰!
周围的侍妾和仆从们大惊失色,胆小的跑了,牢记侍从准则的还站着,普拉玛夫也不急着叫部下去追那些有极大可能是共犯的家伙。
他站起身,用脚踢了一下脑门上的血洞在汩汩冒血的前外交大臣,又抽出了另一把火枪补了一发,才转身离开。
想刺杀的家伙,今天是第二个。
普拉玛夫在心里自嘲地笑了笑,当然没忘了叫人把那些辣椒酱和那个猪猡藏在手心里的银制钩爪拿走。
是心血来潮的凑凑乐!
格哈德的人设补完
本名科勒•波尔塔•德•格哈德 27岁 方伯
在初设里这家伙是个傲慢得不近人情、内心阴暗、睚眦必报的人(
可是写完以后发现好像……ry
————————————————————————————
科勒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真正长大的。他的成长似乎就体现在别人对他的称呼里:从被长辈们呼唤的小名“铃”,到“格哈德家的幼子”,乃至代表整个家族的颜面和权势的“格哈德”。回想起来,这也只是在短短几年里发生的事情。
科勒仅有的一张画像里记录了他曾经的病容:身形瘦削,脸色白得发青,黯淡的红发和无神的红眼,还有两片没有丝毫血色的薄唇。他一副随时会断气的模样,身上却戴刻有山杏花图案的耳坠和银链,穿着柔软的、未经过染色的丝绸。
他们家血统纯正的子弟们,都有着漂亮的红发和红眼,同时也都长着一副不详的早夭面貌。他们穿红衣服的机会要比别人穿黑衣服的次数还要多。这是命运安排好的戏剧,它执意要在这里呈现。
父亲从来就不喜爱他,因为这个孩子的身体太过虚弱。他还曾断言他绝活不过十岁,只给他安排几个医生和使女由得他自生自灭。 只是命运安排好的戏剧绝不会让他轻易退场:他对肉体上所受的疼痛的感觉异常迟钝,唯有神经方面的疼痛令他无法忍受;溴化物和温酒是他每日的必需品,后来他又有了喝咖啡和热可可的习惯,靠里面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如此一来,他磕磕绊绊的,倒也活过了成年。
科勒十五岁才离开束缚他多年的病房,去出席王公贵族举行的宴会,从各个渠道里搜集情报,研习其他人早已掌握的学识,了解日新月异的世界格局。 随后他渐渐意识到:他引以为傲的格哈德家,或是整个利斐利王国,都只是风浪里的一只小船。只有炼造一颗冷酷、毫无怜悯的心,才能不怕狂风,不怕孤寂,朝前直闯,把一切都压到底下,化为自己吞食的饵料。
他身上所有不近人情的态度似乎都消失了,锐意慢慢被隐藏在勃勃的野心之下。他天生就有股固执的傲气,他精明的灵魂越是被困在这副没用羸弱的躯壳里,他反而越是被激起了斗志。一个想法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中:我的才能不输给任何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能做更多。他们都该跪下给我行礼。
格哈德公国内部的关系远比想象要复杂。本家一共有四个儿子,除去他科勒堪堪能够治理好偌大的公国,但还是显得有些余力不足。科勒的父亲生前有个幕僚,负责管理公国的对外贸易,逐渐变得膨胀自满起来,这方面的生意本家始终想要收回。
余下还有叔叔姑姑之流的外姓人,还有一众乱七八糟的姻亲们。他们都一副豪气的贵族做派,以风流放荡、绚烂奢华为潮流,城堡里彻夜灯火通明,等到科勒四点钟起床做早课时,他们的舞会才刚刚结束。更有甚者,一面哀嚎本家不念旧情,一面又在暗地里和其他城邦的领主勾结,给本家的生意找麻烦。
伴随着科勒逐渐在上流社会里活跃,婚配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各式各样的适龄人的画像被送到他面前,外戚的老头子们自作主张,要把贵族的权势重新排列组合,争取得到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解。
科勒冷眼看着姻亲中那些老老少少对自己的谄媚态度,心中有另一番感受:这些好吃懒做、以宗族做靠山为非作歹的家伙,全都是要清理的蛆虫。科勒的想法和他兄长的意愿不谋而合。他为当时管理矿场的二哥出谋划策,同时也准备着一只脚踏入贵族的圈子里。
慢慢的,科勒的才华也在这个舞台上显露出来。他与世隔绝十五年,却仍然能够准确预测潮流发展的趋势;他擅长计谋,心中没有常人该有的同理心和伦理观,万事以家族的利益为先。 这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病秧子踩着一个又一个外戚骨血往上爬,得到了所有人的刮目相看。贵族们讽刺他残酷无情、内心恶毒,他也只把这话当作赞美来听,心情反而更加轻松愉快。
科勒总有很多事要想、要忙,因为他始终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不甚满意。而且从二十岁往后,酒精已经没有办法有效帮助他止痛,他要多费心力寻找替代品;同时科勒也意识到他的时间开始变得无比宝贵,每分每秒都是他在消逝的生命,他不该把自己的生命奢侈地浪费在种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上。
但有时,只是有时,他也会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十几年前,在科勒和路德维希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少女时,他们饮酒作乐,在花团的簇拥下读拉辛和拉封丹的作品。 路德维希曾问他:你怎么看待“爱”?
他回答:“爱”和“婚姻”一样,是神圣、美好的字眼,但从来没有人单纯的爱过我,对我抱有炙热的爱意。
科勒似乎对这两个词有种天真的向往。对于他来说,他渴求的不是能孕育子嗣的生育工具,也不是容貌昳丽的金丝雀,而是能得到一位认同彼此、贴近心灵的伴侣。他希望那样的人突然出现,然后闯入他的生命里,两个人共结连理,走完短暂的一生。
当时,路德维希用玩笑的口吻教训他说:铃,你想要被爱的话,你需要先付出爱。
可他该怎么样、对谁付出爱呢。从来没有人真心实意地爱他,母亲和兄长对他的爱以对他的同情为前提,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孩子活着就是在遭罪,且注定活不长久;那些精明的贵族小姐更加不会爱他,她们看中的只是他家族的势力。就连他身边的路德维希,也只是抱着猎奇逗趣的心态和他来往,想看看这个病秧子到底能够翻出什么浪花来。 没有的话就算了吧,科勒不无遗憾的想,但同时也认为:人不是没有别人的爱就活不下去的。
后来科勒得了一种常常吐血的病症,大量的吐血一个月总有一两回。这时他显得极度虚弱,属于无精打采,昏昏沉沉的状态。于是他认为自己命不久矣。科勒在自己最喜爱的城镇里挑了个建立在半山腰上的教堂,并与主教交涉,希望自己死后能够长眠在这个地方。他还为自己拟写碑文,上书:“终于自由了,谢天谢地,我终于自由了。”
当科勒把葬礼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的时候,医生却告诉他这只是喉咙出血症,没有什么危险,劝他避免过度劳累,多吃点南瓜派,尽量少说话。 如此一来,他像是能免于一死了。只是听了医生这话,在休养期间,他心中的失落反而比兴奋更甚。 他现在拥有的被众人称赞的才华,在他死后又能为他留下多少虚名?
兄长们的智慧、远见、学识虽然比不上他,但他们仍然是格哈德家勤奋好学的人才,假以时日,等他被埋入黄土后,兄长们一定能到达他至死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吧。 他从心底里迸发出了隐秘的、对拥有健康体魄的人的嫉妒。这是又一种打击了,他由于自尊心而无法接受自己正在嫉妒。于是科勒终于沮丧地承认,自己确实是家族中最可怜、最没用的那一个。
源自宗族的高傲始终镌刻在他的骨子里。他不想得到同情,也不会接受同情,更不会向任何人坦诚自己的痛苦,露出哪怕半点怯弱。
在这诸多繁杂的心事里,那些被层层浪涛翻滚带过的流水落花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
格哈德家以杏花为族徽:山杏的种子能经过加工提取氰化物
婚服-白色,丧服-红色,常服-蓝色,军服、祭服-黑色
拉丁语原文 Liber demum, Deo gratias sum liber dem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