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tterCrimeI-薩那西烏傳奇”企劃
是設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年代架空的奇幻向企劃。
企劃規則以計分戰鬥為主,穿插NPC解謎劇情。
企劃主要面向畫手及文手開放。
其他類型的作品允許投放,但不予計分。
企劃任務對玩家各類型繪畫合作與團隊合作能力有較高要求,
請慎重選擇參與。
企劃負責人:今枝瑞(QQ:1524928104)
企劃交流群:757977364
具體細節歡迎加群瞭解!
——谨记,“光景”只能在火山出现异常时产生了黑魔法能力时才能使用。
马德琳用右手撑起了伞,左手向前伸出,五指摊开,嘴角又一次挂上了那抹熟悉的笑容,眼中却是空洞的虚无,口中低缓的念起了那段咒语。
声音不大,仅有艾维斯听见了那阵如同歌谣一般的咒语响起,终究无法拯救她的那一抹绝望在心尖上,在这阵歌声中开出一朵瑰丽而妖艳的花。
“
Pure red, ultramarine green, amber
Giggling and fighting to get into the party
Titanium white, raw-umber and their hues
Watching the farce in silence *1
“
她再次感受到了口鼻被凉水淹没的难受,同时听见了那群远在天边,却早早感应到了咒术浮动而哼笑的妖精们,为这首魔法的歌谣发起和声。明明并非在耳边歌唱,但是那些声音像是融入了水中,进入了她的脑海。原先一片空白的思绪,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被高高低低的和声浸上了深浅不一的色块,炫目夺人的让人近乎失去保持清醒的能力。
浮躁的光元素渐渐聚集在她的手心,黑魔法的力量使它们互相碰撞、擦出火光,手心的伤口感到了灼烧的疼痛,光元素被染上了殷红,它们将那道血肉烧出了痂,但仍有颗颗血珠从那缝隙中流出,不断的飞聚到手握银刀的人偶。光元素没有失去光彩,中心包裹着变得褐红的血液环绕着马德琳,看上去像是一个个身着华服的舞者,轻盈且飘忽不定的上下起伏。
柯利弗一直在注意着马德琳的动作,在发现对方的咏唱不太寻常时,当下魔杖就挥出了一道火球试图打断,但是被马德琳身边的骑士以诡异的方式击毁了那道魔法——拥有感知能力的人偶高举起手中的刀,像是使用长剑一样的方式斩向了火球,火焰在触及刀光时就散去了光芒,随即被其吞噬。
“
Myriad colors become broken and merged
Seven sides prism reflecting the shadow of them
The light crowned the cloud with splendor
Heaven looms in the west *2
“
光元素们来来回回的擦碰,最终形成了一团团闪着雷光似的云朵,就像艾维斯前日在马德琳房里见到的那样——只是那时的云朵洁白无瑕,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散发着令人不安的血色微光。
咏唱还没有结束,马德琳像是无视了周遭环境似的,对于柯利弗的攻击毫无察觉。她眼前的景象逐渐模糊,脑中的色彩浮现在面前,像是转动中万花镜里的彩色碎片,不断的分离、破碎、结合,形成了一道道不同景色。像是一个人将死之前会见到的跑马灯,不同的是,她眼中出现的皆是陌生而又诡异的场景——鲜艳亮丽的色块所组合而成的风景一点也不美丽,它们混乱、冲突、充满矛盾,像是想要绞碎马德琳对世界的认知一样,像是风暴似的席卷了她的内心世界。
柯利弗想让林去干扰对方,但是林在专注于跟艾维斯的攻防——后者在听到马德琳的咏唱之后下手更加狠戾了,前者不得不耗费更多心力在他身上。柯利弗叹了口气,还是只能靠他自己想办法了。
那个类似守护灵的骑士人偶太过碍事,而且会吸取魔法这种事也很少见。柯利弗轻轻皱起眉头,又试着对马德琳发起攻击,这一次的中型魔法仍被刀光抵销,但他似乎见到马德琳的身子摇晃了下,看来那个人偶被攻击她自身也会受到影响。
多少有些抱歉,但柯利弗没有打算因此罢手,他开始咏唱另一种中大型魔法。蓦地,耳边响起了细语呢喃,还有嘻笑声——一只散发的盈盈白光的妖精出现在眼前。
不,不止一只。跟着马德琳的吟咏,那些向来不喜欢极端环境的妖精竟然被吸引而来,这是怎么回事?柯利弗被直面冲脸的妖精打断了施法,看见他微愣的表情,妖精们嘻嘻哈哈的笑着,在空中挥洒着微光的鳞粉,像是天使的祝福似的光芒洒落在了柯利弗和林的身上。
⋯⋯什么时候?林没有注意到那些妖精是从哪冒出,但从他们大多围绕在马德琳周身的样子来看,是因为对方的魔法造成的结果。虽然很想帮忙柯利弗打断对方的施法进度,但是艾维斯除了使剑之外还不时的对他发起魔法攻击实在让人难以分心,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群吵闹的小东西四处乱飞,有时还好奇的靠近观察打斗的两人,干扰着他。
光元素开始狂舞,妖精的加入让这场宴会更加热闹,他们嬉笑着手拉手跳起舞蹈,他们带起了成团的光元素一同欢庆,这一场盛宴,就要正式开场。
“
The door had opened quietly
Clouds cannot hide the glare of the light
They are coming
Between water and light *3
“
马德琳半阖着眼,耳边不再有任何声响,眼中已经虚无一片,整个人像是完全浸在了深海的幽暗处,不见一丝光明。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似的冰冷,也不知脑袋是否还能思考,想来应是可以的,因为她听见了来自妖精的耳语,他们顺着光元素的波动进入了幻象。
不同于上一次在房间的练习,这一次的声音清晰可闻——
妳要杀了他们吗?
不,她没有,用以制造幻象的光魔法存在的初衷并非如此。
但是妳要予他们以绝望。
是的。她没有犹豫。
妳不该深掘光元素的另一面,不该试图掌握这种魔法的使用方法。
她知道,这是她背负的责任,是她清醒的活着的代价。
妳不知道,妳就不该活着。妳让妳的父亲蒙羞,令妳母亲的牺牲失去价值,妳应该被绑在十字木柱上活活被火烧死,妳不配作为一个魔法师,心底只有烧成灰烬的过去和不见天日的永夜的妳根本不配使用光的魔法。
妳不值得受到光的眷顾。
妖精轻巧的话语如烧的火红的铁锤,重重的垂在她的每一根细小敏感的神经上,碾压了她本就摇摇欲坠的意志,将她堪堪维持的骄傲碎成渣宰。她被这些话语激的满脸涨红,呼吸急促,眼匡酸涩疼痛,但是远不及心中那股像是脆弱的玻璃底片上被拖拉出长长的一条痕迹一样,那是不可挽救的悔恨。
海水出现了波动,由心生出的,那来自深渊底端的凶兽发出了威胁似的低吼,妖精们双手环胸的哈哈大笑,像是在嘲笑那只被枷锁困住的猛兽除了吼叫之外就什么都做不到的无能。
犹如一只只看得见黑暗的困兽,失去了光之外又能做得到什么?妳早已什么都不剩了,没有家人,没有家族,甚至连性命都将要失去。妳清楚身后只有断壁残垣,若是想要回头,等待妳的只会是粉身碎骨,没有靠山,没得依靠——
说到最后,妖精们的声音与话语越发尖锐,像是指甲刮在玻璃上一般刺耳难忍,马德琳却无法捂住耳朵,因为即使这么做了也是无用功——她眼前的是幻象,妖精们却是真实存在。
——警告,“光景”将会强制使被施法者陷入最难以忘怀且沉痛的过去,但施法者也将会有被剥夺一切记忆和理智的可能。
几乎丧失了与其抗争的意志,视线越来越模糊,像是要将她蒸发似的,环绕身边的海水逐渐升温,在这之中却有一丝冰凉的水流拂过马德琳的脸颊,这让她想起了艾维斯那双带着凉意的手——如同他的魔法,总能在她失控的前一刻唤回她的理性。
她想起自己还在战场,艾维斯还在等她完成这个咒语,他们还要一起回去泉堂。她还有要守护的东西,不能在这里输了一切。
不,有一件事情说错了,她不是无所依靠。
家破人亡,在这个时代并不稀奇,尤其是对魔法师来说。
她不是一个人,她还有观星社这个坚实后盾,她还有一群性格鲜明的队友,更重要的是,她的身边有艾维斯。
马德琳习惯了一直向前,习惯了只以好的那面示众,从不期望有那么一天自己需要他人的保护。她总将艾维斯放在了需要守护的那方,却忘了对方也有保护她的能力。
她不是没有依靠,而是忘了怎么去依赖。
是过去的惨痛经历来得太过快速,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淹没,才让她下意识地不敢再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唯恐自己会撑不住下一次的绝望。但是,她仍旧撑了过来。
她无需光的眷顾,她自会使光照耀她身。
妖精的笑声在不知何时停下,整片虚无的幻象中似乎仅剩她一人,但是滚烫的温度不在,手脚也恢复了知觉。接着,光线破开了黑暗,穿过了重重障碍,光明终于重新地来到她身边。
或许老约克没有错,妳确实不会轻易的被光身后的影吞噬。
随着眼中所见都被光所覆盖后,火山的景象再度清晰,马德琳听见妖精们在她耳边叹息,也不知是在婉惜那名魔法师的选择,还是在遗憾事情没按他们所预期的展开。
不管怎样,妖精们按照约定,光元素在他们手中化作小小的七边形柱体,在空中排列成太阳的符号,接触到阳光之后即刻消散。
血色的人偶失去了形体,扑通一声掉落在灰色石岩上,摔成一摊血池,刀身重新恢复成原来的银色,木质柄手落在了马德琳手里。
“ Welcome to the feast of light. ”
柯利弗和林同时听见了马德琳与妖精的声音重合在脑中响起,他们同时抬眼看向那个已经结束吟唱的红发少女,一抹闪光略过了她睁开的翠绿眸子,看上去像是上等祖母绿反射出了妖冶的光。
两人的脚下同时浮现出一道红白交错的魔法阵。
“ Cliff Prime, Mobius Lin, do you see the spectacle? ”
这是他们还未失去意识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艾维斯回过头时注视着她的蓝色眼眸使她的人得到安慰,使她的心得以沉静,最后,她安心的闭上了眼,任由意识深陷黑暗。
那就是她的光,她仅剩的,唯一的光。
-
*1
纯红、群青、琥珀
在嘻笑着争取这一次的宴会名单
钛白、棕红和其他色彩
在一旁默默旁观着这一出闹剧
*2
色彩融合而又破碎
七边菱镜映出了他们的倒影
光为云霞渡上一层虚影
西方的天堂隐约可见
*3
大门已经悄然开启
云朵也遮掩不了光辉的耀眼
他们将要诞生
就在水与光之间
(部分有道翻译,部分自翻)

为什么?第一次见到艾维斯冲到她前头,拔出手中的剑与林的橙红相抵,看着那抹本该一直处于后援位子的身影,在这时挺身而出替她挡下了本该斩向她的攻击,马德琳讶异自己居然还有时间疑惑。
她想阻止他的行为,那不该是他的责任,但是不听使唤的四肢正在警告着她,已经失去继续战斗能力的人只会成为碍手碍脚的障碍物,任由对方宰割的鱼肉。
这时,身边的温度骤降,冷的她一个激灵——艾维斯注意到了她不在状态,即使是在激战中,他还是能抽出一点魔力提醒对方回神。马德琳急退身子,将视线重新放在战斗中的两人,后方的柯利弗并没有停下施法,却被艾维斯以水流抵消了攻击,他手中的剑因为附魔而微微闪耀,耀眼而又强悍,林的橙红在短时间内竟是无法对他作出有效攻击。
她从没有与艾维斯切磋对练过,但也清楚同样接受过贵族教养的对方实力不会差去哪,只是眼下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马德琳的预料——艾维斯强硬地阻止了她的继续,并且在柯利弗与林的夹击下还能适当作出反击。
火山的空气如滚滚热浪,将她的一颗心丢入沸腾的水里挣扎,反反覆覆。她想自己大概是疏忽了,要是艾维斯还没有拔剑,又是艾维斯这次没有说要跟着一起来,也许情况就不会如此糟糕——她可以像往常一样说不打就不打,直接离开这里。可是艾维斯居然拔剑了,他居然踏出了那一步,马德琳感到了混乱,接着是一阵恐慌。
这是不行的,她不能站在这里单纯的辅助直到战斗结束。柯利弗如何另说,但是林绝对是抱着杀死他们的心态战斗,这意味着艾维斯也无法留手。她终究不愿见到他手染鲜血,至少现在不要。
右手挥剑收回左手握着的剑鞘,剑上的血滴洒落地面,在地上开出一朵朵艳丽的红花,映在她的眼底如同渺小的红点,在心底溅起一圈圈微澜。
伞剑在分开时无法使用魔法,但是合在一体时,它又是一把大型魔杖。
即使光元素并不像极具攻击性的火元素一样善用于战斗,但是更改了频率的他们也能产生近似烧灼的效果,马德琳想做的就是像上次一样,造出带有灼烧能力的光球。
这种魔法的发动快速,尤其是在火山场最不稳定的火山附近更是如此,柯利弗看见马德琳身后蓄势待发的光球,也随即念起了咒语。
他们的咏唱几乎同时完成,出乎意料的,光球与火焰没有交互错开反而碰撞在一块,两个凝聚了法力的球体立即释放出能量,在半空中像是烟花似的炸开。由于距离接近,也波及到了林和艾维斯两人。
他们避开即时,倒也没有造成损伤,但这种简单的计算错误本不该出现在施法的两人身上。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中一方失误了。
“你的队友看来很不在状态。”发话的是林,一直面向着艾维斯的他很容易就瞧见马德琳在爆炸发生之后的面色变得难看。
可能是伤口造成持续失血,她的思维没有平常那么敏捷,连带着施法的时候出现了计算误差——要是再偏离一点就真的会炸到中间的两人。
她的脑子现在十分混乱,甚至不能好好的判断距离和光球的飞行轨道,这本是她最擅长的,可是现在的她却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别说战斗了,连最基本的辅助都做不好。
她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当年死神与她擦肩而过的那刻都不曾紧张过,就算是肖恩打坏了她的伞那时也没有因此在丢光球时失了准头,现在究竟是怎么了。
那也许是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恐惧,而她清楚的知道这股情绪的根源是什么,但是她不敢去确认——正因为太过了解黑夜有多黑,才会期望夜空中的星星永远明亮。
马德琳低头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即使长时间的练习过杖术和近战格斗,那依然是一双保养得宜的,白皙且柔软的双手。不过也只有她自己清楚,这双手沾染上了多少鲜血,多少的家庭因其而破碎,她不曾后悔过,因为这是不得不踏上的道路。
“总有人得去做那么一件事,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这一句话又跳入她的脑海,像是背后灵一样,千千万万遍的,在她没有失去提防的时候蓦然蹦出,令她不安且痛苦。
这样的情绪使她一阵手足无措,这很少见,不应该出现在她身上,但她确实再一次感觉到了那种失去什么重要事物的恐惧——又一次,这个字眼敲在她心上,像是那年夜鸣的丧钟,给她带来了家破人亡的消息。
这次又会给她什么?
想到这里,马德琳心头异常涌上一股怒火,命运多变且无常的玩笑使她面临了多次绝境,这一次又还想要做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她这次都不打算退让了。
取出了腰间的小刀,在手心轻轻一划,锋利的刃轻松破开了细嫩的皮肤,一串串血珠沿着刀背滑落,却在低落至地面之前停下,一滴一滴的血液团团聚起,竟凝聚成一个小小的骑士模样的血色人偶。
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似的,马德琳面容平静的看着不远处的战斗,并非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但她整个人的气质却突然显得格格不入——浑身泛着刺骨的冷意。
“
Cavalier, you will be without fear in the face of your enemies. *1
”
随着一句简短的咒语,银制小刀的刀身染上了鲜红,骑士人偶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竖直握起那把红色小刀,定定的悬空在马德琳面前。
艾维斯瞥见了那个人偶,许是预料到了马德琳将要做什么,向她投来一个担忧的眼神,但是她少见的忽视了他,故意的选择回避。
不想让他担心,但更不希望他根本上的违背自己的理想,旁人说他逃避现实也无所谓,她自会帮他守护心中理想的最后一块净土。
“
Have you received the letter?
The invitation letter with the words of praise write in light. *2
”
她还是念出了那句咒语,一句作为开启存在他人记忆里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一句将有可能夺走一切的灾难的开端。
—
*1 卡瓦利耶,无须畏惧你眼前的敌人
*2 你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函,那封以光芒书写了赞美词的邀请函
(以上为有道翻译)



身为医者却临阵脱逃,这是多么引人唾弃的一件事啊。
西玛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该这样赌气,特别是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柯利弗是因为自己受伤……可他真的、真的,无法再在现场待更多时间哪怕是一秒下去,令人窒息的空气无所不至地包围着他,而道恩的沉默成为了他逃走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多么可怕的沉默啊。他蹲下,把自己锁在臂弯和膝盖之间,制服上的鲜血不断地提醒着他——红色学会的魔法师为了保护他而重伤,甚至现在生死未卜。
他害怕那些失望的目光,在那一瞬间,曾经那些在自己面前死去的里政府人们的脸,他本来以为已经深埋的记忆,猛然地发掘出来。他能记得他们昏迷前绝望的目光,他们一起一伏的胸膛,最后断绝的呼吸。
“那不是你的错。”
然而,一切的安慰都并无任何的作用。他咬着唇下手术台,把自己关进小药房,把脸埋进臂弯中,一会儿就是湿润溽热的一片,他的眼球发烫,浑身哆嗦,无声地为自己的失败贡献着无力的泪水。也只有失败者,才会用眼泪为自己开脱,假装自己已经努力过。
本来该受伤的应当是我。他近乎自残地想着。不是柯利弗,也不是道恩。他对不起了两个人,而医者临阵脱逃,他更是对不起所有的病患。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他悄悄回了里政府。医疗部静悄悄的,从正式开战以来,旗塔无时无刻显示着一种萧条和死气沉沉,尽管大家对残局的挽回还或多或少地抱有希望,但是再没了从前那种自信的模样。似乎大家一瞬间都明白了——他们不过是命运摆布下的玩偶。
他穿过他曾经无比熟悉的医疗部走廊,拐进那件逼仄的小药房。它其实不应当被称作是药房,称作橱柜又好像太过夸张了。它在通往五楼的疏散楼梯的下方,不大不小的一个空间,门被隐在另一侧,被墙挡住,不是熟悉的人,鲜少会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后来,这个小药房就成了西玛的私人空间。
他跌跌撞撞地闯入里面——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潮湿气味扑面而来,那是他每一次受挫时积攒起来的伤痛的味道,而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味道安抚着他,让他平静下来,然后走出房间——他又是那个活泼的青年。
他倒在地板上,一些已经过期的药物散乱地堆放在一旁的小桌上。那是他曾经还在医疗部时攒下来的(因为夏佐并不允许他用一些很有效的药物),现在已经过期受潮。
他怎么能这样……?他痛苦地回想着,柯利弗——在危机的时刻挡在他面前,西玛只来得及惊叫出对方的名字,而下一秒,残忍的咒语已经击中了对方。
鲜血淋漓。世界变成了一片红色,一切都是淋漓的红色,让他难以辨清。已经说不清是愧疚还是愤怒,这些红色像是海浪,搅起惊涛,把他压在最深层的故事和伤痛都一并揭开。他想起有一个溽热的夜晚,他在月明星稀的天空下往旗塔赶,双手颤抖,全身冰冷,额头发烫。为了拯救他的同伴,他放弃了陪完父亲最后一程的机会,而再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医疗部的某一个病床前,一个人对他低语。戴维斯·普林斯死了,死在医院。那是死神一般的声音。
抢夺生命一向是危险的工作,而充满了赌博的色彩。西玛并不记得自己救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会永远地记住被自己害死的人的名字。比如……戴维斯·普林斯。
他的父亲。
比如西尔莎·南丁格尔。比如……
他无法忍受这样的无能为力,愧疚往往比其他情绪更容易摧毁自尊心极强的人,这个残忍的恶魔,会把一个人的尊严都踩在脚下,狠狠地碾碎。他会低语,告诉人们他们有多么无力和堕落。
西玛从未想过自己有多么引人作呕,现在,愧疚告诉了他所有的真相。
……
他的头重重地磕在桌角上,头颅中嗡嗡作响,鲜血从柔软的发丝中滑落下来,有些就干脆凝固在他茶色的发间。然而一片黑暗中,他看不见自己狰狞的模样——或许惩戒都会在这样的地狱中进行。西玛从未想过这竟会给自己带来快感,这和他人的伤害并非一种东西——那样,他还可以用仇恨反击。然而此时,随着鲜血从伤口流下,那是全然不同的感觉,有一种令人精神恍惚、飘然的感觉,好像一切的痛苦都可以随着鲜血流淌出去。西玛甚至有设想:这血,是不是该是污血的颜色?
他颤抖着哭泣,嚎哭到嗓子沙哑,再发不出一丝声音。道恩的目光……那是一种尖刀一样的东西,和道恩口中的那两个冷冰冰的词“让开”。
可他是医者。
让开。
可他是凶手。或许,什么也不是。
他挣扎着用酒精棉球在自己的手臂上近乎癫狂地擦拭,热量从上头随着蒸发消散,冰冷的触觉让他稍微好受些许,可无论皮肤怎样冷,都比他的心要温暖许多。
西玛从不觉得伤害自己能够怎样——今天他得到答案了,那是赎罪的快感,并且不会再次面对对方失望的眼睛。这是一种自慰的方法。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
他用注射器扎进自己的静脉,红色的血涌进透明的针管中。他用针头剌开皮肉,割破自己的手臂。他无法忍受这一切——
观星社巫师留下的淡蓝的印记还在闪闪发亮,西玛该感谢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离别的准备,而并不会让艾希礼再见到他伤痕累累的手臂。他不敢也不会告诉艾希礼的是,他可能要食言了。
无论是美丽的东方还是幸福的未来,他已经熬不到那一天,眼前只有无尽的苦难和伤痛。他跪在地上,血痕一道道如同闪电在他的皮肤上游走,丑陋得很。鲜血顺着下垂的手,滴到地板上,手心一片黏腻。疼是很疼的,但是这疼似乎疏解了心中的压力,甚至西玛一瞬间有那种冲动——如果割破自己的动脉呢?他会死在这里?
……不。
他还有疯癫的母亲,尽管他没有很多时间照顾她,但是她还等着他的玫瑰。只是,太累了,似乎呼吸都是一种负累。
西玛疲倦地睡了过去。
他梦到他所爱的一切人们。他梦到他的欢欣和悲哀。
他梦到他曾经在大学是那样的风华正茂,只是那一纸论文发出,他便开始承受无数无数的抨击和指摘。
“魔法?那种东西怎么存在?”
“魔法就是魔法,为什么要用科学来解释?”
人言可畏,不致人死,却也诛心。西玛从未想象过他在这样的声讨声中会百口莫辩,会日日夜夜被梦魇所纠缠,会被人唾弃谩骂,被人戳着脊梁骨嘲笑。那是他无法承受的否认,那时他以为,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代。
然而他想错了,一旦堕入黑暗,就没有再回到光明的理由。
只有更加地往下堕落。
遗忘咒的破除意味着什么?或许意味着他任性地想要揭发的真相大白于面前,或许也意味着诅咒的触发,他的家毁得一干二净。
而房屋坍塌的那一天夜晚,成为了他从未见过却是回忆中最为恐怖的一段记忆。父亲把母亲护在身上,天花板上的吊顶灯砸下来,他的头被砸出一个窟窿。母亲尖叫哭泣,丈夫在她的头上停止了呼吸,她听见他的安慰声戛然而止。
不幸只多不少,只要西玛不放弃呼吸。
他的每一个吐息之间,都隐藏着对魔法的渴望。他似乎是一个被上天捉弄的魔法的子民,却阴错阳差地不属于魔法界。而在普通人的世界里,显然,“神棍”并不受欢迎。
或许只有他自己坚信着,那存在,并且合理,有着一套自己的体系。
他的父亲死去,他申请调入前线——为什么?他从未想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是为了不让更多人重蹈覆辙,又或者只是为了——报仇。可显然,他无法在普通人和魔法师之间做出抉择,犹豫之中,毁灭的就只有他自己。
死?不可能。自杀永远都是懦夫的选择。
他想起好多好多事,虽然这些事仅仅只在梦中,或许只出现一瞬,醒来后西玛只会感受到怅然若失,而不会记得他曾经的抉择和纠结。他合上眼,安静地沉睡过去,鲜血的气味无比地熟悉,不过往往它跟硝烟的气味纠缠在一起,而少和西玛喜欢的这种味道——潮湿、阴暗结合在一起。而现在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像是生在黑暗中的红玫瑰,散发着与生俱来的邪魅气息。
“西玛!”
有人用力地摇晃着门把手,似乎是急了,门外发出一声巨响,小小的门应声而开,而整个楼梯内都震了震。那个人的脚步和声音都无比的熟悉,况且他能找到这里来……是个细心而值得信任的人。
长发。
人选只有一个了。
“艾泽尔……”他沙哑的嗓音轻轻地说,“对不起。”
他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笑容,看起来有些病态。他怎么还笑得出来?没有人知道,就连西玛自己也是,他从未想要自己的脸上,出现这样诡异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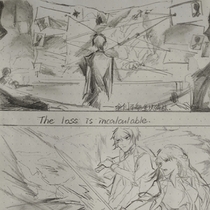
【真的有点忙这是初稿,没有改错别字没有改文法……等我学习回来改QAQ请各位先别看?】
“我很遗憾,那么按照事先说好的,我将为您多预留藏品三天,期待您的再联系。”
布兰奇垫着脚尖从楼梯上下来时,弥赛亚刚挂掉一个工作上的电话,还没等他将随手放在一旁的晨报拾起,肩膀上既熟悉又陌生的重量就使他骤然浑身一僵。
“今天没有工作吗?”
下一秒,布兰奇略带好奇的声音便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弥赛亚不着痕迹地呼出一口气,略微放松了一下肢体,才转过头去面对他一向不擅长应付的小表妹。
“客户取消了预约。”
他言简意赅地解释了一下。
“吃早饭吗?亚修塔出门前给你留了一份。”
布兰奇乖巧地收回了环着表哥脖子的双手,不一会儿又端着一份银质餐具盛着的早点坐到了他的旁边。
“我很高兴在家里见到你。”
她带着明显的好心情望着弥赛亚,半晌像是才想起来似的又接着解释了一句:“平常这时你们都不在家。”
弥赛亚愣了一下,很快便意识到布兰奇长期一人待在家里的寂寞心情。对于这个少了他十来岁的表妹他总是有种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的小心翼翼,纵使当年的洋娃娃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他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将她当做一个孩子看待。
“今天在家陪你。”
说完他努力将嘴角上扬,扯出了一个最接近微笑的弧度。
出于某些原因,弥赛亚对人与人之间的肌肤触碰极为排斥,唯一的例外便是布兰奇。十年前这个粉雕玉砌的娃娃第一次仰着头往他怀里扑时,弥赛亚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摆才好了。她像是块过于精致的零件,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弥赛亚生怕一不留神就将她磕坏,她又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使得他第一次有了温暖的概念。弥赛亚想回应她的亲近,却又不知该如何表示,幸好小布兰奇是极喜欢她又好看又心底里温柔的表哥的,亚修塔不在时她就跟在弥赛亚身边晃悠,久而久之倒也发展出了一套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等到布兰奇用餐结束,弥赛亚打开了一个天鹅绒的狭长盒子推到了她的面前。
“这就是今天本来要交易的那件藏品。”
盒子里,一条九块鸽子血红宝石串联的项链静悄悄地躺着,三块于左侧、三块于右侧,最后三块坠在银链子最下方,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他取出一双白手套给自己戴上,又取出一双示意布兰奇照着模仿。
“玛卡布雷特夫人,这是它的名字。”
他伸手轻轻点了点核心的那块宝石。
“看这里,这是一块蕴含魔力的宝石,它的颜色相较其它略深。这条项链有些年代了,银链子有了明显的氧化痕迹,唯独它周围的一节完好如初。”
布兰奇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就像小时候一样,她并不了解表哥的世界,但她珍惜与其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她不是很懂每份藏品背后的历史与故事,但这并不妨碍她当个安静配合的学生。
“它有什么用?”
“你可以试着感受一下。放松,收敛你一部分的魔力。”
弥赛亚将项链从匣中取出,放在布兰奇的手里。
“它在呼唤我。”
过了好一会儿,布兰奇才不确定地歪了歪头,露出了一个困惑的表情。
“它能激起人们心底的欲望,转化为对它的渴求。你的魔力很强,不受它的影响。”
他伸出手揉了揉布兰奇的头发,含着夸奖的意味。尽管期间又带着不太明显的一顿。
布兰奇开心地笑了起来,她平常也不常笑,这晌她的眼里似乎亮起了万千星辰,陡然有了生气。
可惜好景不长,弥赛亚又接到了他今天的第二通工作电话。
“我会早点回来的。”
他只好这么说。
再次跨进德•勃朗庄园时狄伦的心境有点难以描述,他从没想过他会反复与一个巫师打那么多次的交道。
布兰奇在他走进来的第一秒时就发现了他。她本在树荫底下喝着茶,这会抬起头来,给了狄伦一个同上回一模一样的疑惑眼神。
不知为何,狄伦瞬间就明白了那个眼神的含义,全身烧起了无名火。
——第二次了,已经是第二次了,布兰奇依旧没有记住他的存在,她视他为无物。
“把我的短刀还给我。”
这回他没有潜入,许是已经知道那是白费功夫,他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盛气凌人地对她要求道。
“是你。”
听到短刀,布兰奇眼底的疑惑渐渐散去,即使不记得对方的容貌与声音,上次他留下的伤口却依旧在隐隐作痛,早上用餐的时候还迫使她流露出了些许不自然,致使弥赛亚对她进行了询问,虽然最后被她用女生每个月都会有的那几天搪塞了过去。
“我们家不怎么欢迎客人。”
“没关系,我本也没打算来做客。”
说着狄伦猛然跃起,袖剑从他的右手上弹出,若不是布兰奇早有准备,怕是已经血溅当场。
庭院在瞬息之间变成了一座迷宫,带着的终年不散的浓雾,再次限制了狄伦的五感。
“除了幻觉,你还会点别的吗?”
狄伦讥讽,字里行间却又带了点咬牙切齿的意味。
布兰奇不为所动。
“你可以现在离开。”
迷宫中的藤蔓每根都如小臂粗细,张牙舞爪地将狄伦包围,只留出了背后一丁点空隙。
“你是在说梦话吗?”
狄伦后退几步,双手快速往腿边一抹、抽出了两把匕首。又借着空出来的间距向前俯冲,临到藤蔓跟前时突然发力,以低矮分枝为落脚点、以匕首为攀登工具,愣是硬生生地翻过了那堵由绿色植被构成的藤墙。
不过很快这些本该没有思维的死物便追了上来,前仆后继地阻止他接近布兰奇的身侧。
视线受阻,又有一堆杂草不知疲倦地纠缠,狄伦不由得有点烦躁。不过他深知破除幻觉只能对魔法师本人下手,便收敛了心神,耐心地等待机会。
他悄悄地将左手背到身后,换上了随身携带的袖箭,终于在难得感知清明的一瞬间对着布兰奇本人扣下了发射机关。
布兰奇这回没能及时察觉到,她仓皇之下只来得及侧了侧身,却不料使得袖箭击中了她胸前的羊角项链,本就仅仅是条普通人玩物的赠礼碎落了一地。
布兰奇站在那好半天没动弹,幻境在她受袭的那一刻就散了开来,狄伦毫无阻碍地看到她低着头站在自己右前方不远处,待她重新抬起头来,眼里竟是有了他从未见过的激烈情绪。
“这条项链是弥赛亚给我买的,我刚戴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说着庭院里刮起了风,愈演愈烈,最终夹带了冰雪,将整个小世界包裹了起来。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狄伦暗叫不好,呼啸的风雪迎面扑来,近乎带着要将他活埋的气势。
幸好因幻术的性质,他自踏入庭院以来实际上还没深入几步,纵使不太甘心,也只能做出再次撤退的决定。
临走前他直勾勾地盯着布兰奇,纵使风霜铺面也没能减弱他眼中的炙热分毫。
“记住,我的名字叫狄伦,狄伦•博拉奇。我们还会见面的。”
【PS:是开企前短文扩写】
西玛·普林斯在昏暗的傍晚中撞进了一家咖啡厅。玻璃门将一切风雪拦截在外,壁炉烧得暖融融的,柴火劈啪作响,活泼的火苗舔舐古朴的红砖,咖啡、奶油和一切美好的气味在这家温馨的店中的每一个空气分子中快乐地游走,好像把苦闷和悲痛也一并关在了门外。
他靠着窗坐下,望着窗外的雪,让自己冻僵的身体缓过劲儿来——他的手指尖无意识地触碰到玻璃,又因为突袭的寒冷而惊惧地后退。鹅毛一般洁白的雪,轻灵地降临,而被风用作了割伤人的皮肤的武器。他由此不可避免地想到一些别的事,然后近乎是神经质地忘记他们。他应当忘记它们的,因为他正穿着自己的那件波点衬衫,套着羊毛衫和羊毛裤,披着一件白大褂,像个落魄狼狈的学者。
像个在这个大雪纷飞、北风呼号的冬天傍晚,来到路边的一家小店歇脚的过路人——如同像一只麻雀偶然间停留在屋檐下。他被暖风熏得昏昏欲睡,窗外一都是白色,白色,白色。偶尔闪过的赶路的人影,孤弱地被白色淹没,天空给自己上了一个烟灰色的妆容,扯着嘴角狞笑着,落下铺天盖地的雪片,肆意玩弄着渺小的人类。
事实上,这双眼睛不久前看到的是鲜血淋漓、哀鸿遍野的战场。这双手触摸到的是同伴温热的血,在风雪中渐渐冰冷。澄澈的雪是否能够洗干净他眼中的杂质和动摇呢?——不会,反而如同巨石那样狠狠地压在他的脊背上,让他的呼吸都变得艰难。他颤抖地低着头,目光瞟着桌子下黑暗的角落。
那里干净得连一丝灰尘都不屑留下陪伴一下孤独的客人。
他的身体因为魔法师而孱弱,他的前程因为魔法师而僵化,他的心灵因为魔法师而绝望。他是最不该和魔法师产生联系的——他应当待在大学里,静静地做着他的研究,满怀着痴迷的、叶公好龙的梦,然后任由几年后它被淹没在岁月的冲蚀下。他难得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在冬天想起初春的幻梦。他穿大一号的白大褂,乘风奔跑时翻飞的衣袂,席卷起他梦想的碎片,带给他无尽的狂想。年轻的西玛在学院中快乐地奔走,抱着书本和笔记,那支狂想曲便骤然间到达了高潮——写一本关于魔法的书吧,藉由对于科学的信仰。那是一个热烈的夏日午后,他还记得是金色的阳光,给予了他这样的勇气和疯狂。那是青年跳脱的脑中的胡思乱想,那是和快乐王子一起驻守在冬天的燕子——因为爱和向往。
他离开大学时是那年的冬天,穿上里政府的制服时是再一年的冬天。那两个冬天都很冷,一次他脱下白大褂换上军装,又一次他脱下军装换上制服。他的心因此变化而伤寒,并且像是沉疴痼疾那样一碰就痛。但西玛还是偶尔地碰一碰,提醒自己不要遗忘;再后来,他就只能碰到回忆的遗骸,而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他已经是不算年轻了。他的生命——他这样决定,要为里政府的辉煌而燃烧,或者和它一起成为灰烬。他抛下了他年轻的梦,如同甩了他的初恋情人。
窗外白影晃动,屋内温暖的梦给予他体温。他的面前放上三明治和热牛奶,响动声把他从几年前的梦中惊醒。如若不是这声音,他或许可以在这小女孩的火柴燃烧的梦境中永远地呆坐下去,一直到有人来刺杀里政府的职员——唔,他坐了多久了?他有点东西吗?即使有,为什么那是一块夹着奶酪和生菜的三明治,而不是充盈着糖浆的华夫饼?
罪魁祸首站在他身边,斜着眼睛瞟他——都这光景了,里政府的职员还是这么懈怠吗?就连最呆的猫都比你要警觉:不知道我们——观星社——就靠着你们的脑袋拿奖金吗?
那我们一个个都要变成刑天的。这个中国传说从图书馆里流传出来,西玛立刻学以致用。他以嘴贫为乐,特别是跟艾希礼嘴贫。
里政府于你,真的那么重要?艾希礼漫不经心地问。他上下打量着西玛的白袍,这件西玛衣品的遮羞布在他们私下见面时无数次地出现。它的款式总让人或多或少联想到巫师袍,长得有些惊人,拖到西玛的膝盖以下。
我当是燕子,要陪着王子死去。
艾希礼说,怎么能是燕子呢?燕子是黑的。你是天鹅。白的。克莱登的天鹅。
艾希礼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个笑话。
克莱登?我早已不属于那里。这个熟悉的名词,曾经占据了他少年时的一切光阴和希望,然而他从那里被驱逐……西玛苦笑着,眼泪在幻想中滴入陶瓷杯中热腾腾的牛奶——他很早以前就是没有羽毛的天鹅了,那些雪白的羽和大雪一起沉睡在地下六英尺,在冬天寒冷时他就站在雪中,让洁白的雪花妆点他裸露的胴体,等到太阳出来,它们化去,留他一个人孤零零,湿淋淋、赤身裸体地站着。
*【I am covered with fine gold," said the Prince, "you must take it off, leaf by leaf.】
“咒印……”艾希礼沉默了一会儿,拉了个椅子在他身边坐下。这是他们常去的咖啡店,在夏天的时候它卖着观星派和冰饮,现在,暖融融的壁炉烤热整个小店,给它染上几分温暖的颜色。艾希礼在西玛对面坐下了,示意他把左手伸出来。
“托你的福,最近都没遇上什么事。”西玛把双手放到桌子底下,把白袍的袖子卷起来——因为天冷的缘故,白大褂里加塞了不少衣物,让他整个人都看起来丰腴臃肿了不少。他本就不会穿衣服。
然后他捉住毛衣的袖管,往上用力地推着,露出光裸的胳膊来。他颤抖了一下,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有别的什么。而事实上,他的右手微微地战栗,也不仅仅是因为天冷肌体取暖的缘故。做完这一切,他才把自己的左手臂展示给艾希礼看。
艾希礼沉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迅速地扫视了一眼周围,确认安全无误后检查起那个咒印来。西玛没有问他这是什么——尽管他心里通透地跟明镜一样,他能准确无误地背诵和念出这个复杂的拉丁文单词,即使他不拥有一根魔杖,而身上那套蓝色的制服,也让魔法与他来说成为了一种疯狂的奢侈品,只是想一想就能让他发狂。
追踪咒。
西玛阅读过红色学会编写的魔法教材——道恩给他的,他从来都不会放弃争取这样的机会。它们太过美好了,以至于他愿意为了它们粉身碎骨。他最喜欢的是一本《魔药学》,然后就是《魔咒学》,他把里面每一个单词都念得熟稔得似乎他们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像是漂泊异乡的旅人对于家乡话那样熟悉。
西玛却没有把这一切告诉艾希礼。
在艾希礼检查追踪咒的时候,西玛咽下了三明治中的那片奶酪,打量着对方。魔法师显然对西玛的凝视毫无反应,似乎是专注于他手臂上的咒印,又或者是对这样的目光感到习以为常,并不把它当做一种危险处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长得是很快的,西玛注意到艾希礼又拔高了一些,那双湛蓝的眼眸似乎也更加深邃。在磨练和相交中,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而现在,似乎是艾希礼该负担起保护者的角色了——这个咒印就是他以此自居的证据。
他认真的样子很好看。西玛在心里这样说道,看着艾希礼下垂的睫毛,随着目光转移轻轻地翕动,唇间慢慢地蠕动,似乎是在默念着什么东西。他仔仔细细地将它检视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松了口气,把西玛的毛衣拉回胳膊上。
“没问题。”他说,口吻中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教训,“接下来……多注意。我知道你又把自己置于险境了。”
西玛笑了笑:“你不要太担心。”
其实这个追踪咒下得实在很是无力,因为以西玛的行踪来看,狼来了的故事会重演许多遍,而这个正处于成长最关键时期的少年,显然也不该为他花太多的心思。西玛把白大褂的袖子也拉回去,臃肿得像是一根白面包的胳膊让艾希礼忍不住笑出声。
我们还能再度相见的吧?小天鹅先生。
艾希礼又一次露出笑容,那是发自真心的笑容,尽管西玛并不知道他有多少时间会露出这样的表情,但此时他感到了幸福。他叼着嘴里的生菜,轻轻地“嗯”了一声,又认认真真地朝着对方看——等一切结束,你也该成年了吧?我想要辞职,去看看东方,听说那边有一个很完美的世界。在那里,会魔法的人会受到尊贵的款待,我很喜欢……
那与你又有什么好处呢?艾希礼问,可他其实早已知道答案,只是期望它从西玛的口中说出,似乎这样就能给予最温暖的许诺和鼓励。
西玛轻轻地说,起码在那里啊,魔法师和普通人可以和平地共存,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他的眼中闪着几分恍惚的希望的光,好像是摇曳的灯火那样飘忽却灼热,好像这是他唯一的期冀。
*选自《快乐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