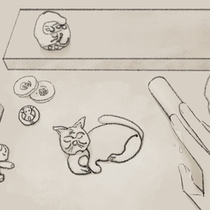“蒋平!你的酒钱!”
不知道谁喊的,从馆里递出来,到这街上也只剩个尾巴。被喊的那个更不在乎:是多了还是少了,若是少了自会有人追出来,若是多了,便算今日的心情钱。
心情好啊!哪里是这样容易买出来。她掏掏耳朵,好像真的没听到有人跟来,只剩风声了。今日风也好,风急,天高,自有飞白过耳,蒋平眯着眼,眼中世界左右倾斜,却觉着树里不太对劲:你也不见她有半分严肃,步子仍是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左踏时如虚凭风,要跌不倒,下一秒居然飞身便起,再回头已在树上,捉了条黑猫尾巴。
“又是你。”
这醉汉却用个笃定语气——她穿圆领,不系好,内衫居然还有百花楼带出来的墨痕,字迹妩媚,另有些风情,一笔歪了,连同口脂吻在她怀里。
被捉的人叹口气,说,我以为你醉个半死,怎么清醒成这样。
蒋平只问,找我作甚?徐止便答,找你酒钱。
黑猫一头乱毛,没睡醒的样子,掌心里摊着铜板,递给她。蒋平松了那尾巴,又落到地上,兴趣缺缺:只是跑腿?那不必了,你这小孩,留些钱买件冬衣去吧。
那长辫甩一甩,更像条漂亮的尾巴。徐止看着发呆,又不动声色移开目光,说,冬衣我有。
蒋平又问,找我作甚?徐止不答,仍在墙上。
这种流落小猫,蒋平也不太放在心上,兀自往前去了,哼一首曲子,调也歪了几句,随风吹得很远。
=
蒋平便是梦中杀人也并不奇怪。
她醉起酒来清醒得像鬼,平日里收住的拳脚打全一套,是排山倒海破竹来,烈风过野摧枯朽,更莫要提使刀:她也使刀,使刀更行云流水,千钧得怪异,好像压抑山洪一日起,恶鬼门关百年通,大开大合,只取首级,不屑手足。
手足?蒋平不信手足,手足不如刀,刀在手中,如天地间任我行,行路难时任我平。刀要挥去哪里,便可挥去哪里,手足却不可以!手足说不明白,是血肉魂骨,是梦中折钉,醒来又握着刀,忽然不知道挥去哪里!
于是真就醒了,那刀已入树中三分,再难抽出。她原先真要劈这树么?我看不尽然。那树是蛮力破土,生长在村口,生长在心口,教会自己原来有力气,便可挥刀拦路,斩断别人的生活。
蒋平看着手里的刀,心想,我便也要如此么?我便也该杀死谁么?
她又喝一口,要醉个痛快:谁也杀不死我。
=



临近新年,无论是什么店,生意似乎都不错。光这几天乌曜就送了有近十单,无不是一些达官显贵的定制品。今日倒是难得没什么人,祝影便给大伙放了一天假。
乌曜倒是无所谓放不放假,他实在是喜欢这份活计,每日走街串巷的送货,要是让他闲下来反而有些不自在,正琢磨着今日要不就去大哥的店里逛逛就听到自家老板招呼自己。
“乌曜,今日可有什么安排?”祝影倚在柜台上露出猫一样的笑容看着自家的小鸟。
乌曜看着祝影露出这样的笑容就知道这是有什么事要拜托他,要说乌曜在家身为最小的孩子基本上是有求必应,那都是他撒着娇使唤别人的,可到了这祝影身边他倒是乐得被使唤。
乌曜露出小狗一样的笑容答道:“倒是没什么事,老板有什么吩咐吗?”
祝影每次看到这小鸟灿烂的笑容都觉着像只等着主人夸奖的小狗,忍不住过去揉了揉他脑袋。
“不是什么大事,这不快过年了,想着去古今堂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送给我兄长,你要是没什么事便陪我走一趟吧。”
“行啊。”乌曜答应的爽快。他从没见过祝影的家里人,还是头一次知道对方也有一位兄长。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该买点礼物送给大哥和二姐,就算买不起跟着去长长见识也算不错。
——
听说古今堂是沈氏商会的产业,光是门脸就不是一般店面比得上的,乌曜还从没来过这里,一是这的东西他也买不起,二来他更喜欢去逛逛烟火味重的小店。
乌曜跟着祝影刚进店就有伙计迎上来。
“哎呀二位客官来的可是正好,咱们店新请了一座百玉观音,不管是求子还是祈福都灵验的很啊!那边是咱家的镇店之宝,碧玉如来像!您看……”
乌曜对伙计介绍的这些都不怎么感兴趣,没听两句就已经神游天外开始发呆了,不知怎么这店里十之八九摆的都得是些佛教之物,不是观音像就是什么佛珠,乌曜对着雕工是否精细也不甚了解,在他看来再珍贵的物件也不如一颗闪闪发光的铃铛。老板尾巴上那颗就不错。
祝影家也无人信佛,对这些也不怎么感兴趣,便打断了伙计热情的介绍。
“拿些你家别的来看看吧,不要佛教相关的,摆件首饰都行。”
“得嘞,那就劳烦二位客官坐着稍等片刻。”这伙计招呼二人坐下为两人斟茶,转身就进了后屋去找祝影要得东西了。
乌曜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就看着祝影坐在自己对面,似乎是觉着茶有些烫,吹了半天也没抿一口。
乌曜正准备招呼伙计上壶温茶,就听见坊内最有名的衣铺老板闻时有正巧前来,“祝娘子,乌郎君,好巧呀!”
乌曜跟着祝影起身回礼,就听祝影邀请道:“闻娘子,一起坐坐?”
乌曜起身为闻时有让座,转而坐在了祝影身边闻时有倒也并未推脱,应了声便落了座。老板招呼着上茶,乌曜也就顺道喊住了正要倒茶的伙计。
“我家老板喝不得太烫,还劳烦伙计上壶温茶。”
祝影到没想到乌曜还有如此细心的时候,一时反倒还有点不自在。
闻时有用眼神扫了扫二人嘴角噙笑,似乎发现了什么趣事。乌曜见过几回闻老板,母亲工作的绣纺常给闻老板的铺子供货,听母亲说闻老板的手艺一流,但却很少亲自制衣。
没一会儿伙计就端着壶温茶回来了,乌曜帮祝影重新倒了一杯,又为闻时有斟好茶。两位女子聊起了珠宝首饰,乌曜倒是插不上话,就在一旁喝着茶看着伙计放在一个个托盘里的珠宝在心里挨个评判。
这个不够透,那个不够闪,这个颜色又不好看,总之在他看来哪个都不如自己盒子里大哥送的那两块琉璃碎片。
祝影和闻时有看了半天似乎也都没有瞧上眼的。
“这古今堂如今多半都是些与佛教有关的物件,一时还真没什么和我心意的。”闻时有有些失望的摇摇头。
“这东西到都是些好东西,可惜我家无人信佛,不然那碧玉如来像的料子和雕工到真是上等,作为礼物是再好不过了。”祝影也有些可惜。
乌曜倒是有些奇怪,“我们国教不是道教吗?怎得全是些观音佛像。”
伙计笑道:“客人说笑了,当今皇后喜佛教,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听说连道观都拆了好儿座给寺庙腾地方呢!咱们这小本经营,肯定要紧跟上头的步伐啊。”
乌曜从不关心这些事,但这拆道观还是头一次听说。
既然没有瞧上眼的,三人也没多待。
“三位慢走,下次再来啊!”掌柜的这头为三人送行。那头便又有伙计迎着客人进门了。
“这古今堂生意还真是好啊。”乌曜不由得感慨。“不愧是这街上唯一一家珠宝古玩店。”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行告辞了。”闻时有拱手向两人道别。“两位有机会来光顾我家生意。”
祝影笑着回道:“闻娘子要是得了空也要来我家铺子坐坐啊。”
告辞了闻时有,乌曜才收起了有些客套的笑容。
“老板,我们可还要去别处逛逛?”
没在古今堂挑到合适的,祝影肯定是还要去转转的,她看着乌曜又恢复了平时的模样,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调笑道:“先随处逛逛吧,说来平时怎么不见你对我也这么一本正经。”
乌曜伸手揉了揉脸,想了想回道:"那当然是姐姐你和旁人不一样啊。"
“哦?哪里不一样?”祝影挑眉问。
乌曜倒还真没想过祝影对他来说有哪里不一样,或许是第一次的会面就暴露了自己本性,对方又会像大哥和二姐一样揉揉自己的脑袋,乌曜还未经过思考就已将祝影划分到了自己的舒适圈内。想了半天乌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得说:“可能是像我姐姐一样吧。”
祝影听到这回答一时有些气急,哼了一声便转身就走,甩的尾间的铃铛叮当作响。
乌曜对祝影突然转身就走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又说了什么惹了对方生气,连忙追了上去。
“姐姐等等我呀!这是要去哪?”
祝影只恨对方是个木头,这脑子就是死不开窍。
“我去买茶!”祝影回了一声脚下也没停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乌曜想了半天也不知自己是哪句话说得不对,只好默默得跟在祝影身后。
要问祝影之后消气了吗?
那自己选的木头鸟还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