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mmary:织造内部的时空并不连续,让她可以把十余年的路走在一起。来说再见吧。
阅览注意:全文2k+,内含(只有一个词的)斜体排版。前情提要https://elfartworld.com/works/9732392
裂隙内部被火光照亮。一团火坠进凝滞的内部世界,给这片没有太阳的荒域带来短暂的日出。
并没有身体撞击死棘冲击感,悬铃木收起护身的火焰,发现自己身处苍白无人的荒漠。她站起身,这里是她极为熟悉的地方,只是刺目的太阳被暗淡的紫色天光取代。正如那电台所说,这里完全就是“另一个”现实。周围散落着折作两半烧至焦黑的飞机骨架,好像这个世界有意挑选前世的终结剖给她看似的。刚好没有和这里道过别,她想,于是手抚上折断的机翼拍一拍,就当是说再见了。
这是一片无人之地,再往前走,走过皴裂的枯地,走过干涸的河谷,就能看到那个小镇。她知道怎么走,她的脚步愈发快起来,不知这个世界对现世的生命是如何处理的,会复制一个静滞的切片吗?也许能见到希拉、也许能见到贝蒂,也许能看到她们在遇见自己前是什么模样,也许能看到自己不在此时她们是如何生活的。
时空并不是连续的,原先几天的路程被缩短至数十分钟,很快能看到建筑的影子,熟悉的小矮房子伫立在那儿,房门半掩着。这应该是许久以前一个平常的日子,门口那棵树比她记忆中矮上一点儿,和建筑之间系着晾衣绳,此时,希拉大约在后院搓洗衣物,贝蒂则坐在门槛上逗猫狗玩。不过走近了才看清,那两团看似人影的实则是两只狩骨,感受到生命力的接近,它们活了过来。
啊,原来是这样。她对自己点点头,拳上燃起火,很快烧净了它们。原来织造并没有复制生命的能力,只好以死棘取而代之。
慢慢逛着整个小镇,本该有居民和动物的地方全都挤着死棘,她挨个处理它们,一边回想着它们企图充当的是谁。卖美味卷饼的夫妻、很凶又很会种花的老头、看守墓地的婆婆……然而狩骨不会烹饪,荆骨也不会开花,她在心里说,你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残缺的世界吗,一个死寂、凝固的复制品?她想起在贝蒂的科普书上看过,滴落的树液包裹虫子变作琥珀、死去的骨骸埋进地层形成化石,那些痕迹栩栩如生,可你还是没办法透过一堆骨骸看到恐龙活动的样子。
当然,离开裂隙她还能回到存在于真实世界的那栋小房子,但当它逐渐风化、失修,当她和过去的自己相行相远,从前的记忆也会变成这样的标本吗。
窗边少了她和贝蒂做的手工摆件略显空落,悬铃木花了一些时间用火焰灼痕在木窗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再见。
她感到平静,平静得有一点令人难过,而难过也很快消散,连同刚刚那一点期待一起。她走过曾去过的许多地方,城市或乡村,山谷或海岸,原本一心抱着追寻前世线索的执念来,却总忍不住玩过尝过体验过再走。它们仍还在她的记忆里熠熠生辉,这让她感到安心。她与它们挨个说再见。
红河城在这里还保持着它繁华的样貌,和她刚到这里时看不出区别,也许在过去几十年、甚至更久都是如此欣欣向荣。在她想着这里少了霓虹灯光色彩还是有些别扭时,终于有声音打破这一片死寂:那是凯莱布带着嚣张的呐喊,透过广播传遍每一个空间,叫瓦尔基里们过来,用自己的声音撕开裂隙。
她一路清除死棘,循着声音找到广播车,却没在车外看到“红凯尔”,只有一位诗人静静立在那里,半透明的,微笑着。悬铃木记得她,诺埃尔曾在城郊采访每一位路过的瓦尔基里,只为聆听她们的故事、为她们写一首小诗。她们聊过几句,悬铃木告诉她自己正在寻找那能为她讲述的过去,也许等找到了,再同她慢慢说。
“于是,你找到你的故事了吗?”诺埃尔一如既往语气轻柔。
悬铃木在她身旁坐下,靠着广播车车门,诗人也坐下来,一同望向远处那贯通天地的紫光。
“找到了,”她说,“我想应该从那个故事里走出来。我做到了,只是变化比预想的大。”她略微伸展开背后的羽翼展示给诗人。
“那么,你并不喜欢这样的变化?”
“不是。我不知道。”悬铃木想了想,补充道,“我也不知道这算喜不喜欢……我不清楚怎么面对它。”
凯莱布和其他同胞应该提前清理过附近的死棘,这片角落静悄悄,没有人来打扰她们片刻的休憩。诺埃尔的声音有些飘忽,如同一道吹得人面颊酥痒的晚风:
“你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啊。走在崭新的旅程上,我们一开始是会感到迷茫,如同下笔却不知从何写起。但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话要讲、而是想说的太多;这也并不是因为你害怕改变、而是有太多可能性在前方,不是吗?”
“蝉褪下它的皮壳时,也生出新的晶莹双翼。”诗人笑着,“你可以同它一样,歇上一会儿、沐浴充分了阳光再继续。”
她们在这里又坐了一会儿,诗人絮絮地同她讲述关于织造的一切。她想到自己用熔融的沙捏制的那些小玩意儿,大约织造也是这样捏制现世的镜像的,死棘和粗制玻璃有着相似的焦黑;包裹大块杂质的玻璃液滴落下来又有它们自己的形状,这就是瓦尔基里如何诞生。她又想到蝉虽然是长出翅膀飞走了,但蝉蜕还带着幼蝉的模样留在树干上,并不是消失不见,它会落下也可以被人捡走,也许被哪个小孩当成奇物宝贝起来。她这么想着,就讲了出来,诺埃尔轻笑着回应,她们站起来,万寿菊的香气从那微笑蔓延出来。
“我还是喜欢用自己的脚走路,比起坐车,”悬铃木望了望那辆涂着夸张标语的广播车,“我没有想用广播喊的……我想自己一句一句跟这里复制的世界说再见,这样可以吗?”
“啊,”诺埃尔有些小小的惊讶,随即轻而肯定地点了点头,“这就是你的语言。”
“谢谢你。我见过……你的语言了,”悬铃木比划着,“写得很美。”
“很遗憾我的灵装留在现世,不能为你写一首。”
“我会像你们那样,把我的感受写下来说出来。我会留下那些记忆的痕迹的,在忘掉之前。”
诗人消散于风中。
再见。
再见,她说。她向那道紫光走去,地上留下她的脚印。她能感受到说出话时声带在颤动,她的火烧起来时周围空气也为之流淌,她全心去体会这些感觉。这是生命力,与感触和记忆一样,与火焰和晚风一样,是流淌的活物而非静滞的标本。她想到,作为她名字的来源,悬铃木的树皮剥落后会在树身上留下痕迹,随着它的生长,也不淡去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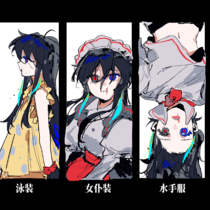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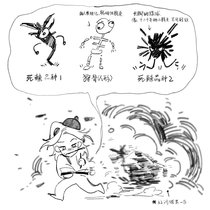
一些发生在1917年1月的前尘往事。(虽然但是感觉也可以响应一下字母挑战的killer?)
有关这位德军士兵的故事,请看来自受害人本熊的血泪控诉:http://elfartworld.com/works/9600207/
=========
叶夫根尼·季米扬诺夫转过身来,发现他的同伴不见了。
他们本该结伴去往前线附近收殓昨天下午那场炮火之后留在战壕里的遗骸。当天傍晚的时候步兵发起了一次强攻,把阵线往前压了几公里,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抓紧机会回收那些永远留在里面的战友。非常幸运的话,可能会有一两个睁着眼睛熬过了整个夜晚的伤员拖着最后一口气还没有咽下。
但是他的同伴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没有和他说一声。叶夫根尼迷茫地站了一会儿,压低嗓音喊了两声他的名字,然而没有得到回应。炮声在天快亮的时候停了,战场上只有从喀尔巴阡山脉吹来的刺骨寒风呼呼地吹过稀疏的灌木,留下空洞而凄厉的笑声。
……也许是做了逃兵吧。这个念头轻轻地飘过叶夫根尼的脑海。他倒是没有觉得特别意外,他们在罗马尼亚待了整整三个月,后退的时间远比前进的要多。如果有人因为残存的那点少的可怜的信心不足以支持他们继续忍耐这严苛的酷刑,那也不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
但他还得去前线收殓遗体。叶夫根尼在冷风里站了一会儿,思考自己有没有能力一个人把一具遗骸搬运回去,然后再找个新的帮手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现在他脚下站着的地方明天不一定还归他们所有,总得先尝试一下。
叶夫根尼把手伸进维克多·马西莫夫下士的衣领里,尝试将他以奇怪角度折断的颈椎扭回原处。他没有成功,尸僵和夜晚的霜冻让死者的皮肤坚硬得像块石头,他只好任它维持一个扭曲的姿势,努力把这位可怜士兵——至少是他剩余的部分——弄到临时的简易担架上。他没法一个人把担架抬起来,所以只能用雪橇式的方式拖拽。马西莫夫下士的肩膀和左腿分别在狭窄的壕沟里被卡住过两次,还有一次差点从担架上整个儿滚落下来。最后叶夫根尼直起腰来,喘着粗气,看着拦在面前小腿高的土坎,和刚才走过的距离——不到一百米,他目测——冷静地想,不行,他做不到。
要是他的同伴没有离开,这点障碍应该不会造成多大的困难。但现在他只有一个人,实在很难拖着一个成年男子的分量,穿过这片被来回拉锯的战线造就的,布满弹坑的地面。
他只能回营地找其他人来帮忙。
叶夫根尼松开手,用力搓了一把自己的脸,想用掌心让冻僵的鼻尖稍微恢复一点温度。随后他听见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沙沙的响动。他僵住了。
“……帕维尔?”他警惕地喊出同伴的名字,祈祷是他的良心——或者责任心,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发现,折回来给他搭把手。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不近人情,从灌木丛后面跳出来的是一个戴着钢盔、挎着步枪,全副武装的德军士兵。对方看起来像他一样对这个场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很明显地愣了有足足两秒钟,才开始扯着嗓子凶狠地冲他大喊大叫。叶夫根尼不懂德语——除了从战俘那里听来的诸如“吃”、“喝”、“痛”这样简易的单字,和大量用于咒骂的脏话。他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这很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当他看见对方的手正在摸向步枪的握把。
肾上腺素以极快的速度被剧烈跳动的心脏泵进他的身体,他的脑子清晰而冷静地想起来他今天没有在制服上佩戴能够标识他军医身份的红十字袖标——由于被血和其它污渍沾染得已近辨识不清,他在前一晚把它摘下来用雪搓了几下,晾在医疗站的药品箱上。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早晨出门的时候忘了将袖标别回去,也就是说,他没法向对方展示自己是个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非战斗人员。
——更何况能的话也许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些该死的德国人,你不能真的指望他们遵守什么公约。
叶夫根尼急切地摸索着后腰,至少他在出门之前记得把手枪挂在腰带上。谢天谢地,在他猛地一把将它从枪套里拽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像卡住马西莫夫下士的脚那样卡住它。
他双手握紧枪身,手指很稳,没有一点颤抖的迹象。在被送上战场之前他们培训过他这个,扳动击锤,让子弹对准枪管,然后扣动扳机。他根本没有来得及犹豫一秒。
火药击发的声音。德军士兵尖利的嚎叫。血液喷溅的扑簌声。火药击发的声音。灌木的枝条在挣扎中被拉扯而摇落积雪的声音。火药击发的声音。人的身体沉重跌落的声音。弹壳被甩出的清脆喀哒声。火药击发的声音。
直到血液从他鼓膜旁的血管流过的汩汩声逐渐淡去的时候,叶夫根尼才再度听见战场上一成不变的、冰冷的风声。隔着一条战壕之外的泥泞地面上倒着一具新鲜的尸体,仰着的脑袋底下静静地淌出一道细细的红色溪流。他移开了眼睛。
叶夫根尼在冷风里站了一会儿。他慢慢地把手枪塞回枪套,慢慢地转过身,顶着愈发猛烈的风慢慢地独自走回营地。他没有找新的帮手帮他回去搬运马西莫夫下士的遗体:当他回到营地的时候,连里的命令下来了,因为敌军发起了反攻,前线区域不再安全,非战斗人员和没有得到命令的战斗人员不允许前往。
没有人问他帕维尔去了哪里,也许是暂时没有。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那个德军士兵的事。交战在不远的前方进行,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又开始逐渐塞满尖叫的、呻吟的、哭泣的伤兵。情况和昨天或者前天没有太大的不同。
几个小时之后德国人的飞机掠过这片区域,投下了几颗炸弹。
叶夫根尼·季米扬诺夫死于这场轰炸。
-----
* 标题出自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我在勒热夫城下死去(Я убит подо Ржевом)》。虽然原诗写的是卫国战争时候的事,不过这种无名的荒谬感用在叶夫根尼身上总觉得还蛮合适的……原诗非常动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搜看看原文,或者来听听毛子改编的歌曲,b站就有,也很美味。
(送上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C4y1X7b5/)

“全……全押!我全都押上去!”
“喂,你这该死的怪物是不是出千了!”
“老板~再来一把嘛,今晚手气这么好,嗯?”
希弗晃悠着手里的锤子,从拐角处探出头来,又瞄了一眼远处赌桌上的纸醉金迷。筹码哗啦啦,酒杯叮叮当,嬉笑,咒骂,无数沉溺于金钱中的赌客在此肆意歌唱着运气的女神,声音在希弗所在的走廊都清晰可闻。她缩了回去,继续在走廊里踱步。自从各路瓦尔基里集中涌入红河城以来,赌场里的人流只增不减,凯莱布一开始还挺开心的,把脚踩在桌子上,扬言要趁机大赚一笔。结果那不得好死的大裂隙就这么巧合地出现在了凯莱布的命根子上。她还记得凯莱布在会议桌上那副便秘一样的表情,还有那三辈子也整理不完的骂人话,哎呦,真是好风景。
如果忽略之后骑士团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往赌场地下跑,导致凯莱布一连好几天都跟炸了毛一样紧张兮兮,一碰就爆,那这确实还挺有趣的。后来凯莱布好像找到了什么完美的方法一样,紧张的眉头一下舒展开来,还开始时不时往骑士团那边跑,好像一下子改邪归正了一样,前后态度转变之大真是令人始料不及。希弗乐着从装饰用盆栽后走了出来,盯住了前面蹑手蹑脚的骑士团成员,削弱了自己的气息,拎起了锤子。这么说来,那天那个自说自话的作家说的还真没错,血注既需要那种粉饰自己的大人物……
也需要她们这样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叮,当。血迹斑斑的锤子精准落在后脑,一下,两下。咚,啪。清脆的声响被血肉的粘腻声音替代,一声,两声。像这样自己为是,不听指挥,认为自己单枪匹马能解决一切的年轻骑士,骑士团里大概是一抓一大把的,像这样的人往往会有一把还看得过去的灵装……希弗满意地收下了这把短剑……还会有一身漂亮的制式装备……希弗欢快地收下了这身盔甲,把头盔丢到一边……当然也会有一个不算很瘪的钱包,希弗一并揣到了兜里。她把自己的作品丢进角落里的黑色塑料袋里,又把尸体拖到小房间内等待专人处理。像这样的人正是希弗暂且搁置自己工作,前来赌场当保安的最大原因。
血注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但那样的人往往会被凯莱布撕开喉咙丢在桌上,然后这样的人在短期内就不会再有了。只不过像那样优质的原料,如果出现在血注内部,是轮不到希弗去锻打的,只有在当保安的时候,她才能好好磨练磨练自己的打铁技术。她盯着这一兜子的漂亮装备,心里简直比熔炉还热乎。至于那些尸体怎么办,血注内部自然有解决的方法,有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有人能把尸体埋得天衣无缝……但是没人能来帮她拖地,她还得拿把墩布自己干活。
她把血迹清理完后,来换班的人也赶到了,于是她索性决定拎着自己的产品到酒馆里,找个角落继续蹲守。她一进屋就听见凯莱布在嚷嚷:“……染红舞台!只要你们的表演足够精彩,让台下那群蠢货流连忘返,你们就配得上我的奖赏!“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希弗瞄了一眼,在凯莱布身边看到不少熟人。她冷笑了一声,找了一个角落沉默地待着。等凯莱布的激情演说结束,她带着一群人走进了竞技场。希弗本以为没人会发现她,结果一个粉头发的小鬼却径直朝她走了过来。她眼睛怎么这么尖呢,希弗轻轻皱了皱眉。
“呦,这不希弗吗!老妹最近生意咋样?”卡托迈着一种悠闲的步伐靠了过来,搭上了希弗的肩膀。希弗看向别处,“还行吧,多谢关心。”
“呀,咋这么个态度呢,咱俩也算老熟人了是吧,“她使劲拍了拍希弗的肩膀,想把她往下压一压,方便说话,“听老大说你最近还当上赌场保安了?咋样啊干的。”
“还行,挺开心的,惹麻烦的人不少,有不少不错的原材料。”
“看出来了,不错。哦呦,这么一大兜子全是你的作品吧,真漂亮。”卡托轻轻踢了踢角落里的塑料袋,袋子发出令人愉悦的金属声。“里面有多少灵装啊?”
“没多少,都是不怎么稀罕的便宜货。”
“没事,我教你,“卡托拍拍自己的胸脯,指了指竞技场的方向,“你就在那边,把你那些便宜灵装该租的租该卖的卖,保你赚大钱!”卡托乐了起来,希弗想了一会,也开始笑。
“行了,干活去了——“卡托转身离开,又单足旋转了一下走回了希弗面前,她招呼了一下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门口等着的几个人,示意她们过来,“对了,把这个忘了,你瞅瞅这个。”
那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箱子,与当时凯莱布委托希弗送出去的箱子长得一样。她们对着希弗打开箱子,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灵装,无论是光泽,质感还是散发出的气息,希弗一眼就断定这里没有一件便宜货。她伸出手想拿起一件细细端详,却被卡托拍了一下手。
“欸,别动,老大要找我麻烦的。”卡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瞬,她示意那群人把东西送到竞技场,然后又扶上了希弗的肩膀,“你想要也有办法,老大最近开心,你要是去打角斗场打赢了,说不定她会给你一件宝贝呢?“
“嘁,不去,我还要命呢。“
“你都活多久了,再活下去可就真没你这铁匠的地位了。“
“滚吧你。“希弗笑着把卡托推开。
“哎,错了。不过老大最近还挺好的,喏,“卡托指了指台上面红耳赤的瓦尔基里,她们穿着兔女郎套装,一脸扭捏的在观众的喝彩声下舞蹈,“你看,打输了也没啥,上台跳个舞而已,这不很有趣吗……喂!放开一点啊!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卡托对着台上的人大喊,引发了观众的激烈反应。她指了指那个瓦尔基里,笑着看向希弗,希弗看了看卡托那比兔女郎装还暴露的衣服,也绷不住乐了起来。
“嘛,考虑考虑吧,你想打的话得抓紧喽,灵装发的挺快的。我得去跟老大交个差,先撤了,拜啦。”卡托挥了挥手,朝竞技场的方向走去。希弗也不再久留,准备离开酒馆。她考虑要不要找凯莱布报个名,却感到有什么尖利的东西顶住了她的后背。她把袋子丢到地上,举起双手。
“又见面了,希弗·史密斯。”维尔涅斯冷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酒馆里的喧嚣逐渐消失,希弗胸有成竹地转了个身,盯着维尔的眼睛。
“好久不见啊,你是那个……维尔涅斯,对吧。你那个神神叨叨的小伙伴呢,怎么没来?”
“托你的福,受了重伤,在医院里。”
“呀,真不走运,我都要心疼她了。”希弗放下手,叉腰盯着维尔的剑锋。
“你最好解释一下隐瞒规则这件事。”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这可不是我的责任,难道骑士团没有警告过你们吗?呀,真对不起,我忘了你们的人都在忙着揭开我们的小秘密呢,”希弗踢了一脚袋子,露出袋子里满满的骑士团制式盔甲,“你怎么向我隐瞒了这个呢,真遗憾。”
“你……”维尔深吸一口气,双手握紧了剑柄,死死盯着希弗。希弗却不慌不忙地收起了自己的袋子,用手轻轻把她的剑挪到一边。“你看,你们骑士团的人都很冲动……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你当真要在这儿闹事?我倒是不介意把你这把漂亮的剑收入囊中。”
维尔回头瞄了一眼,对上了无数不怀好意的目光,无论是刚刚还在起哄的酒客,还是舞台上面红耳赤的兔女郎,此时此刻,她们都拿着武器,盯着维尔。希弗挥了挥手:“欸,伙计们,没啥事,朋友,都朋友。”在一阵桌椅的摩擦声中,酒馆这才恢复了喧闹。
维尔长出了一口气,把剑收了起来,直接走过希弗身边,离开了赌场。希弗笑着挥了挥手:“再来啊~常来玩啊~”
离开赌场后,维尔打车前往了医院,西奥多正躺在病床上,用一个全新的本子写写画画,一边写,一边还在跟病床旁的埃利亚斯聊着决斗时的感受。她看到维尔进门,用那根好胳膊挥了挥手:“维尔,我的朋友,你看,埃利亚斯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本子。多么有意义,这或许是我文学旅途的新开始!“
“嗯,不错,谢谢您,负责人。“
“没关系,你们也辛苦了。”埃利亚斯笑着摆了摆手,“你调查出什么了吗,维尔涅斯。”
维尔遗憾地摇摇头:“我准备进入竞技场时又碰到了那个铁匠,如果我再在那里待下去,很可能遭到血注的围攻。”
“这样吗……看来血注确实在暗地里做着什么。辛苦了。“
“嗯……还有一件事,负责人。“
“说吧,维尔。“
“我在那个铁匠随身带的塑料袋里……看到了很多咱们骑士团的制式盔甲。“
埃利亚斯皱起了眉头,思考了一会。“我明白了,我会在下次会谈上质问凯莱布的。我还有工作,就先行告退了。”
“嗯,慢走。”维尔目送埃利亚斯走出了病房。
“欸,维尔,那头野兽大概杀了几个人?”
“从袋子里的东西来看,大概五六个吧。”
“哇,真是令人惊叹的战绩,想必她还会继续猎食,多么锋利的一把利刃……”
“快消停点吧,你又忘了是谁害的你了。“
“那不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仇敌也能一转变成挚友……“
仇敌也能一转变成挚友,真的吗?维尔暗暗问自己,心里不太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