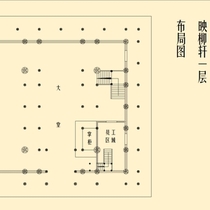西芙第一次见到张青,是在学校公园的石中树下,少女挎着双肩包,背着一个用粗布裹起来的细长的包裹,正惊讶的打量石中树。
那是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参天古树,顽固,不屈,挣扎,是活着的奇迹。
它的根由魔法作用,深扎在无缝的石中,石头摸上去是温热的,仿佛包裹着火,像某个传说里具现出的景象。
就在这一刻,穿着黑裙子的余弦和两人擦肩而过。
很多年后这件事在张青记忆里只剩一个模糊的画面,仿佛身处梦中。每每想起初遇,便如同有人在耳边低语。
说着石中若有火,相击而生光。
·
西芙并未在意张青,若是平常,她还有可能上前问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但今天不行,她很忙,忙着代替某个临时有事的老师去主持新生介绍会。
她到达教室的时候,学生们已经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兴奋的说着什么。
这是学校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和年龄参差不齐最高到达三十多岁的一期生不同,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来自世界各地,能顺畅交流多亏教室里复杂的语言魔法自动翻译。
她看了看手表,8点55分,还差五分钟正式开堂,顿感百无聊赖,倚在门框上,希望这五分钟从时间里抽掉。
西芙是个相当任性的人,做事凭兴趣,兴趣来的快去的也快,人生目标便是“找到能让我一直感兴趣的东西。”
有个黑发黑眼的男孩冲她吹了声口哨。
“老师你真漂亮啊。”
“谢谢夸奖。”西芙笑眯眯的。
“我叫拙仓濯,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是老师,是你们上一届的学姐。”西芙翻了翻花名册,拙仓濯,日本人,孤儿,有上顿没下顿,被生活逼出一手偷鸡摸狗溜门撬锁的好技术。“你们班的老师临时有事,来代替他主持下新生介绍而已。”
“哦哦,学姐你叫什么名字?”
“过会就知道了。”西芙不再理他,目光扫过一圈。
八点五十八,教室后排还空着一个位子,那个穿黑裙字的女孩坐在空位旁边,看上去十分沉重行李箱放在空位上。她没有跟任何人搭话,而是在人声嘈杂的教室里安静的看着书。
西芙认得她,入学时没能找到引路人杂货店的女孩,还是自己带进学校的。
十三四的正是骚动的年纪,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渐生萌芽,再怎么安静内向的孩子,在新环境中也难免蠢蠢欲动。而她是那么的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独自坐着,不跟任何人搭话,也没露出一丝局促和寂寞,仿佛全世界加起来都不如那本书有趣,让人不由好奇,好奇她到底在看什么书。
西芙直起身子,穿过阶梯过道,敲了敲她的桌子。
女孩抬起头,西芙有种错觉,那双眼睛并没有看向自己,而是越过肩头,落在更远的地方。
八点五十九,空位依旧空着。
“你……”
“不好意思让让。” 有人拍了下西芙的肩膀,用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口气打断了她的话,声音清脆利落,男女莫辨。
西芙很不喜欢有人从背后碰自己,下意识反身一个小擒拿,被对方轻而易举化解了。
扎着马尾的少女站在过道上,背着一个细长的包裹,比男孩还要英气的脸上道尽了什么叫满不在乎。
“力气真大。”她甩了甩左手,右手抄在口袋里,漫不经心的看着前方,“一整座岛屿都是学校,这也太大了,迷路了半天。”
这次不是错觉,西芙确定这个新生并没在看自己,而是透过落地窗看向外面。
春和景明。
“唉不好意思,麻烦你让一让。”她又重复了遍,语气十分敷衍。
西芙觉得被冒犯了,她抬头看向钟表,正好九点。
……郁闷。西芙磨了下牙,闪身往讲台走去,那个脾气古怪的女孩单手把行李箱拎到过道上,黑裙子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仍然看着自己的书。
她做完这些,一屁股坐到座位上,谁也不理,在乱哄哄的教室里神游天外。
得,俩怪胎凑一起了。西芙在心里耸肩,拍拍桌子。
“安静,安静。”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小鬼们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自己,这种感觉还真有点让人发毛。
“我叫西芙,西芙米兰特,你们学姐。”西芙咳嗽了声,手指无声的挠了下讲桌,心想你个十九岁的人对着群小孩怂什么呀,“老师临时有事,我替他主持下新生介绍。”
“学姐你头发金灿灿的,真好看呀!”拙仓濯打断她的话,脸上笑嘻嘻的,学生间响起一阵压抑的笑声,倒没有多大恶意,起哄只是孩子天性。
西芙目光扫过后排,一阵服气。
所有人注意力都在讲台上,就那俩人还在干自己的事。一个神游无我,一个专注看书。
有一种人,坐公交时身边空位是最后一个被落座的,乘地铁时是绝对没人在身边挤的,天生有种孤寂气场,驱逐生人。
马尾辫显然就是这种人,即使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走神,周围同学和她的距离都明显比其他人要长上三分。
没什么理由,只是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
这种下意识行为导致马尾身边空出一个残缺的圆,缺口就是看书的黑裙子。
她丝毫不为所动,在身边人炸刺般的气场里安若泰山,那样子太过镇定,连对方不经意间露出来的锋芒都在她面前变得柔软圆润,折了个弯绕过去,反倒像面盾牌,将黑裙子和教室里躁动的气氛隔离开。
西芙竟然有点钦佩了,心想有种怪胎不愧是怪胎。
“看我,先别做自己的事了。”她说。
穿黑裙子的女孩合起书放到桌上,看向西芙,只有马尾辫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谁想先介绍下自己?”西芙问。
“我!我叫拙仓濯,听名字就知道是哪儿的人了吧?”那时拙仓濯十三岁,一米五的个头,头发半长不短,因为生活原因而显得有些不修边幅,“擅长——偷窃。”
他掌心一翻,变魔术似的亮出个红色手机,跟拙仓隔了一个座位的女孩低低惊呼一声,嘴里叼着糖,妹妹头刚好遮住脸颊,双手在口袋里翻找什么。
“别翻啦你的。”拙仓把手机还回去,一群人下意识护住了自己的包……
“你这人……”她咔嚓一声把糖咬碎了,拙仓全神贯注警惕她发难,结果对方只是从包里翻出第二根棒棒糖叼上,“我叫钱糖,糖果的糖,喜欢甜食,会点功夫。”
西芙注意到马尾辫的脖子动了下,终于有点兴趣似的看过来 。
“唔,没什么好说的了。”她看上去有点迷糊,就这么断了话头,坐回位子上。
新生陆陆续续介绍完自己,西芙的目光移动到最后两人身上,竟然有点意料之中的平静。
“这位穿黑裙子的同学。”
“嗯?”
“介绍下自己。”
“好。”她站了起来,意外的顺从礼貌,“我叫余弦,女,13岁,身高149cm,住在挪威的中国人,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弟弟,魔杖的外貌是黑色钢笔,擅长制作人偶……”
她越说众人脸色越怪,这一板一眼的介绍仿佛有血有肉的人偶,西芙说你介绍下自己吧,她就介绍了,完全不像人会说的话……
“可以了可以了,打住,请坐。”西芙赶紧制止了还要继续说下去的余弦,于是她又说了声好,安静的坐下。
气氛有些凝固。
“余弦?cos吗?数学还是cosplay啊哈哈哈哈!”拙仓笑了几声,空气好像重新流动起来,“还有一个人没介绍呢,是吧?”
西芙看了眼花名册,唯一一个后面没打勾的名字是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组合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姓名。
马尾辫懒洋洋的站起来,说 ,我叫张青。
然后一屁股坐了回去。
·
2004年,张家龙头张阿耶带回一个4岁的男孩,名叫诺言。
2008年,张阿耶的长子死于车祸,寄养在次子家的女儿张炎逃过一劫,刚过8岁生日。
又许多年过去了,某一年春天,张阿耶被人一刀毙命,凶手不明。接替掌舵人位置的既不是次子张义,也不是孙子张顷。
那年诺言一夜登顶,站在高处和想要拉他下去的人斗个不死不休。
那年张炎留下封信,不知所踪。
那年活泼爽朗的张顷变得沉默寡言,随父亲一心一意打理武馆。
那年张青进入魔法学院,做了史上最简短的新生发言。再往后许多年,这四个字渐渐变成松山城里催命的咒,谁都知道四字过后,要么你死,要么我亡。
那年诺言十六,张炎十六 ,张顷十八,张青十四。
那年,二零一六年。
这个世界不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是由故事构成的。
——Muriel Rukeyser
-蒙马特在老式摇椅上开始诉说-
我就要开始我的故事了,所以请你做好,不要乱动。N,不要吵,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坐下来。
一切要从那个令我终生痛苦的午后开始说起。我的恋人、我的蒙帕纳斯在那一天自杀了,上吊,一根粗麻绳从我的生命里永远地夺走了他。他死得时候为我留下了一栋家具齐全的房子、柜子里的三包面粉和十二颗鸡蛋、一大沓干净洁白的稿纸、两瓶戴阿米牌的墨水——一瓶瓦格纳一瓶斗牛士——一把万宝龙的王尔德以及二百六十五篇的童话。
你知道的,这颗星星以童话故事为食。走在街上,连锁超市里的一块布鲁克庄园牌苹果酥要两个半童话,一瓶璜家牌的啤酒要三又三分之一个童话,这些你们应当都很了解了,但在他死后我去店里问过才知道,一副结实牢固的棺木要整整两百六十个童话。
于是那一天,当我从墓园走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就只剩下五个童话了,但我还是穿过马路,走进了酒吧。在那里我花了四个半童话点了杯大榔头,又将最后半个童话讲给了我的大学室友听。
我在那一刻开始身无分文。
我摇摇晃晃地走那房子,那没有蒙帕纳斯的房子。那时已是深夜,我坐在他常常写童话的那张桌子前,看着面前空白的稿纸。
“那么您是从那时开始写童话的吗?”
“不,N,不要那么着急,我还没那么快长大。那天我坐在桌子前,流了一整夜的眼泪,终于在凌晨时分睡着了。”
第二天我饿得不行,在为自己煮了两个鸡蛋之后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想着能不能找到那么一两个被我父亲或是祖父或是不知哪个辈分的亲戚漏下的童话。我当然是失败了,哪里都没有童话,我只找到了蒙帕纳斯留下的一份菜谱,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如何制作一个童话。
我们家上述至少七辈都是依靠童话为生,花费一个个不眠的夜晚和一瓶瓶墨水来养活了一大家族的人,也是因此,我们家中的人很少替人打工。
但我不同,到了我这一辈接受这样命运的人是蒙帕纳斯,我则在遥远的地方学习物理,研究原子究竟怎样组成一个世界。
简单的来说,我不会写童话,完全不会,因此就算拥有了那张菜谱也无济于事。
但飢饿接踵而至,当家里连一粒面粉和一个鸡蛋都找不到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们。
它们在我的头顶唱歌,但我知道真正能够懂得它们歌声的人不却不在这里。那个晚上,我在梦中见到了蒙帕纳斯,他递给一张稿纸,上面用他那好看的花体写着四个字——玻璃悬崖。
第二天,我开始动笔了。
按照蒙帕纳斯留给我的菜谱,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主菜、辅料和汤底的配合,以及几天的炖煮过程,我不停地写啊写,只希望能够配出一个看得过去的童话。
“您就是这样写出玻璃悬崖的吗!”
“是的,是的,在这样不停地尝试了七天之后,我发现我写出了一个童话,之后它就成了你们都知晓的玻璃悬崖。”
再往后,我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尝试,你或许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人的变化总是微妙且拖泥带水的,没有哪个人是真正能拜托过去的,我也一样。我从二十岁开始重新学习如何成长,迈着几乎微不可见的步伐,一点一点地想更靠近自己理应拥有的未来。
我什么童话都写,充满微笑的、含着泪水的、放声大叫的、痛苦哀嚎的……这些都是我从自己的过去看到的,我在不停地书写着,本以为永远不会停下,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我亲爱的N,就是你来到我窗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看到N的脸的那一天,我忽然明白,我写的这些故事都不过是我自己的过去,年岁渐长,我已然写尽了我的故事,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但您还在为我讲这故事,就像刚刚那样不是吗?”
“那是故事吗?那不是故事,N,你要记住,没有主菜没有辅料没有汤底,我不过是在干巴巴地叙述罢了。世间有很多人都将这样的故事叫做童话,真是恬不知耻,一个人永远要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才应当下笔,没有灵魂的故事再多也不过是糟粕。”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当某个晚上,你躺在床上看到那些星星时,你会明白其中必然有一些是属于你的,你看着它们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话,肯定有办法在天光大亮的时候握紧那些星星,去对抗未来的。”
“真的吗?蒙马特先生?我可以?”
“可以,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但我要你相信更多的东西,更多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
“我要你相信文字的力量,看不同的文字组合成句子,逐渐在人们心中发酵。用象征和比喻攻占读者的心脏和大脑,让他们分不清感动缘何而来。将漫长的生命一句简化,将短短的剎那扩充饱满,用上笔墨拼上心智,收尾时亦只让旁人见到干脆利落的句点,毫无累赘。将腐败的物件泼上色彩,伪装成新的成品,将死亡在某个世界继续书写,永不停息。
N,你要相信,只要你有能力,你的笔就无所不能。
无论怎样的故事,充满欢笑或泪水;不论怎样的风格,从古老东方到神秘西方;不论怎样的时代,从没有文字、如同野兽般狂吼的世代到巴别塔有朝一日再次建成、原生语言不过是隔着玻璃供以观赏的未来;你都要去写,你都要能写。你看,N,你看,你的手会写出这些故事,这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们都埋在你的心里,在夜里对着你的大脑嚎叫,威逼利诱你将它们写出来,赋予它们生命。
幸福或痛苦时根基,生活的平淡或壮烈是平台,载体是每个年轻或不再年轻的生命,它们无一不消亡在你的笔下。
这是你的世界,你的故事,你笔下的每个人都有你的影子,你看着他们某个人的眼睛,会觉得何其相似!
所以不要怕,N,往前走,拿着我给你的笔,继续走下去。奋笔疾书有时,停滞不前有时,狂笑和眼泪亦有时,那些都是你。你睁大眼睛仔细看,这就是你将要过的生活,你要全心全意接受它。”
“我对你诉说这么多,多到几乎要覆盖我的后半生,N,你看好,看着我的眼睛,你看得出它是什么颜色吗?”
“绿色的,蒙马特先生。”
“是的,是的,现在你看清楚这双眼睛了吗?”
“我看清楚了,先生。”
“好的,这样很好……你去吧,现在就去吧,N。”
这样说完之后,蒙马特在那老式摇椅上,轻轻阖上了眼睛。
TBC
朋友們你們好,就在剛剛我決定先不鹹魚了,我要去談戀愛了,謝謝大哥,朋友們再見,再見!

那还是去年深秋时候的事。
纪持把目光从面前的课本上暂时挪开的时候,正巧捕捉到窗外两人合抱的高大桢楠摇落了几片叶子下来。午后的阳光极好,金灿灿如有形质一般,铺在葱绿的叶片上泛出一层熠熠的金光,一晃神仿佛挂了满树的黄叶似的。
那时候他刚刚参加完外祖父的葬礼一个人回到学校,将将错过了分宗之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到教务处补办完缓考的手续,他沿着台阶一级一级爬上器宗教学楼门前的小平台,刚好是午后阳光最好的时候。晨昏时分准时漫过山涧的雾气早已经褪尽,从平台上望下去能一眼看到山脚。向阳的山坡上零星生着不少黄桷树,在这个季节里挂了满枝细碎的金黄,间杂在依然苍翠的桢楠和香樟中间,瞧来分外惹眼。
现在是上课的时间。教学楼前安安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纪持略微犹豫了一下,也不知为什么没有拐往宿舍的方向,而是迈步进了教学楼。四年级的这堂课是冶铸理论,在用的那间教室敞着门,从走廊尽头远远地就能看见谭枢老师正在讲台上授课,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认真地想了想要不要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听课,然而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上课的那间教室隔壁还挨着另一间稍小的教室,格局有些别扭,如果不是安排不下,一般很少会有课排在那里,于是也就约定俗成地变成了一个默认的自修教室。这会儿或许因为大家都有课,自修教室里并没有人,课桌上零星散放了几叠课本,算是占位的意思。
纪持随意拣一个空着的位置坐了下来。教室里隐约可以听见隔壁传过来谭老师讲课的声音,谭老师的音域偏低,语调又温和,再隔了一面墙,几乎只剩下连成一片的、模糊的絮语。纪持支着耳朵努力分辨了一阵没能听清内容,也并没有执着,他呆坐着出了会儿神,然后悄悄地把手探进了外套口袋里。
手指最先触到的是棉布干燥而柔软的质感,掏出来的东西缠着深蓝色的布条,像使用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似的,泛着洗褪的柔和的白。他把它摆在面前的课桌上,一层层打开缠裹的棉布,露出一枚色泽黯淡的三清铃来。黄铜制,形制是最普通的那种,几乎可以上一年级《法器通识》的教科书,铃身上錾着的经文依稀还看得出似乎曾经涂过银,然而已经十分陈旧,剥蚀得只剩下斑驳的痕迹,就连镌刻的经文本身也有些模糊,看得不太真切。
纪持用手指抚了抚那一圈细密的小字。他并不需要看清楚才能知道经文的内容。那是《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在他十二岁那年暑假收到蜀山修仙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前的很久就会朗朗复诵的第一篇经文。他第一次学到这篇经文就在这枚铃铛上,当时外公把他抱在膝盖上,大手环着他的小手,要他用双手紧紧地捧住那枚铃铛。
要恭敬,不可以乱摔。外公当时是这么说的,表情依然慈蔼,语气和态度却是郑重的。
于是他便恭恭敬敬地跟着外公诵读那些似懂非懂的句子。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后来他入了蜀山,外公很高兴,每年的寒暑假都要拿着他的成绩单,展开来看一遍,笑眯眯地夸他,然后再反复看上好几遍。再后来外公已经拿不稳他的成绩单,他就守在病床前念给他听,每一科都要念三遍。外公答不上来话,但还能看着他笑,就好像在说,纪持做得很好。
外公过世于咽喉癌晚期。他记得似乎就在不过几个月之前,当他在发下来的宗门志愿申报表上填下器宗两个字的时候还在想,等他把锻术学得再好一点,就可以给外公做一枚新的。那枚铃铛太过老旧,把手上有着经年累月留下的划痕,铃舌缺了一小块,摇出来的声音里总带些刮擦铃壁的杂音。
可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他有些迷茫地想。
深秋的风已经稍微带一些凛冽的味道,朝西的大片玻璃窗虽然浸在明亮的阳光里,却仍时不时被风吹得哐哐震动起来。临近讲台有一扇窗开了一半,卷进几片银杏的叶子来,随性地飘落在浅色的地砖上。
下课铃响得有些突兀,随后渐渐扬起了嗡嗡的人声,过了会儿就有三五个学生陆续走进自修教室里来。似乎是更高年级的学生,纪持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纪持,只在走进教室见到有人在时稍稍放低了交谈的音量,稍有些好奇地看了没穿着校服的他一眼,也并没有待很久,只匆匆取换了课本就离开了。到上课铃再度响起之前周围已经又安静下来,自修教室里仍然只剩他一个人坐在靠后排的位置上,四周安静得连模糊的讲课的声音也听不到,不知道从哪里传来隐约的呜呜风声。
“……纪持?”
有人呼唤他名字的时候,纪持下意识地先挺了挺后背才回过头去,就看见谭老师站在后门外,胳膊底下夹着几本书,另一只手上拿了盒矿石标本,正从敞开的门口朝里望进来。
“谭老师。”
谭老师是纪持到了器宗之后才开始担任他们导师的。低年级的时候,纪持那个班炼器相关的课程由另一位老师教,他并没有上过谭老师的课,却也知道这位老师以耐心和蔼出名。然而开学还不到半个月他就因为外公病重请了长假,直到两个月后才回来,他其实没有想到谭老师居然还能准确无误地从背后叫出他的名字。
见他回头,谭枢便温和地笑了笑,从后门走进来。纪持稍微有些局促地想要站起身来,又被谭枢摆摆手示意坐回去。谭老师身量极高,讲课的时候穿一身素黑的宽大道袍,看起来几乎有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然而他把书和标本往纪持旁边座位的桌上一搁,在纪持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视线倒是勉强拉了个平齐。
“你外祖父的事,老师也听说了。我很遗憾,请节哀顺变。”
谭老师语气平和地这么说着,带几分恰到好处的关切,不让人觉得疏远,却也并不是那种令人尴尬的过分热络。
“课业有什么跟不上的地方,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跟老师说。”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言语,甚至可以说得上平常,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语调的关系,听起来真挚而又亲切。纪持垂下眼睛,努力压了压突然涌到鼻腔后面的酸涩,轻声道了一句谢。谭枢便也没再多说什么,起身轻柔地拍一拍他的肩膀,像是打算离开的样子。一时之间也不知出于什么想法,纪持突然匆匆地出声叫住了他。
“谭老师……”
谭枢便站住脚,嗯了一声,偏过头来等他的下文,纪持自己却蓦地紧张起来。他一直没敢抬头,目光盯在那枚老旧的三清铃上,悄悄地蜷了蜷手指又强迫自己放松下来。谭枢也没催促,只安静地站在旁边耐心等待着,就像一堵挡开风雨的温柔而坚实的墙。
“……我想问问您。”
最后纪持带点犹豫地开口,食指小心翼翼地搭在铃铛的把手边缘,仿佛那是什么声音高一些就会弄碎的易碎品似的。
“这个,能修好么?”
铃身上有一道裂纹,大约一寸来长,横贯在上面看起来像一条狰狞的伤疤。大概出于道业倾向使然,谭枢从刚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面前的这枚铃铛,但纪持没提,他就只不着痕迹地草草用余光扫了一眼,并没有细看。现下纪持既然主动提起来,谭枢便又坐回他对面的位置,容色端正地朝那枚铃铛伸了伸手。
“我可不可以……?”
纪持点了点头,谭枢便郑重而小心地托起那枚铃铛细看起来。
他这一生见过数以千万的各类法器,这枚铃铛不是最平凡的,但也远远谈不上是最强大的。那一道裂痕泄了法器内循环往复的气,铃铛上残存的灵气单薄,却还算纯净,器型中规中矩,铸术亦只平常,然而在他的手指底下微弱共鸣着的气息温柔而又质朴,透着仿佛呼吸一般起伏的活气。谭枢用指尖来回摩挲几下裂纹的边缘,又轻轻叩了叩铃壁,沉吟了片刻。
“若是想和原来一模一样,恐怕有些难度。器物本身修补好很容易,主要是气的走向……”
他将铃铛稍微偏转了一个角度,指给纪持看。
“……在这里有了些偏差。倒也不是说不能在修复的时候牵回原轨,只是器形上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外观大概就做不到完全的一致了。”
说罢谭枢把铃铛端正地摆回去,看了纪持一眼,似乎稍稍犹豫了一下。
“看你的取舍吧。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
“不。”
似乎是觉得自己脱口而出的拒绝实在太没有礼貌,纪持有些惴惴地抬眼瞄了瞄谭老师,似乎想确定一下他有没有生气。
“不是的谭老师……我的意思是……”
谭枢莞尔,带了点鼓励的眼神看看他,纪持便定下心神,深吸口气,语气认真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这是外公留给我的遗物,我想自己来。”
他抬了眼睛去看谭枢,表情里带着些微弱的期待。
“我,能学得会的,对吗谭老师?”
谭枢看了他一会儿,随后温和地微微笑起来,平稳却坚定地答了他一句“能”。纪持反倒像是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似的,抿了抿嘴唇垂下目光,谭枢便自然而然伸出手去轻轻摸一摸他脑袋,语调温暖。
“……你外公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快要有一年了吧。他与谭老师的师生缘分,到现在,也已经有整整一年了。那个时候谭老师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又完成到哪一步了呢?
纪持悄悄抬了眼往讲台上看过去。谭老师正耐心地等所有人完成随堂的习题,窗外的光线明亮而不刺眼地投在他侧脸上,挺拔的鼻梁就像破开了一道光。纪持赶在他觉察到自己的目光之前飞快地低下头去。
谭老师,我也想成为你的骄傲啊。
【注】
· 标题来自那句著名的满清文字狱典故,出处有不同的说法,然而我的本意其实只想说后半句,大家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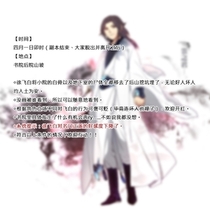
虚实两阵一起跑,我分身术潮强(不
成功化身流水账狂魔,互动的大家都没写到几句……不好意思响应,只好跪下…………
已经好久没插上板子了(呆滞
上接徐飞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上)http://elfartworld.com/works/105541/】
见徐朗二人都不言语,林鹰扬只道他们旧雨重逢不知从何开口,就也不再接话。方才见得徐飞白只靠内力便可为阿朗驱毒,使他恢复如初,林鹰扬悬着的心也落下了一半。
那日林鹰扬因身携阿朗配刀在八卦田被徐飞白救下,带回住所疗伤。修养期间,他曾向徐飞白问起当日八卦田是否还有别人。徐飞白回忆片刻,便告知林鹰扬除他之外未曾遇见旁人。几日相处,林鹰扬认定徐飞白不是说谎之人。既然出口处只有自己一人,那应当是连海生伤势不重,已经先行离开了。
思及至此,林鹰扬也心生懊恼。整日想着行侠仗义,结果做起事来却是这般德行,也不怨连海生负气,只能怪自己太过没用。
许是心里有愧,也是不肯承认失败,林鹰扬得知徐飞白准备去万贤山庄寻阿朗后,即使被其以有伤为由婉拒,仍执意要一同前来。今日水潭旁有幸一见高手过招,自己这伤号果然成了累赘。不过既然阿朗已无大碍,林鹰扬虽惭愧,也不再纠结于此。
半月前同行四人,如今已有三人平安,只有谢楠云还不知身在何方。
林鹰扬原本盘算着找到阿朗后再将谢楠云之事告知二人,如果可以便一起去寻她。但是现在情况不同,还有另一件事情,他想自己去探查清楚。
刚才在水潭前,徐大侠与一人遭遇,当时他虽在远处看不真切,却也隐约在那人后方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若那几人正如自己所料,此去就不宜和任何人同行。
下了决定,林鹰扬便拿出先前为阿朗准备的衣物伤药,细细叙述了自己上次离开地宫的经过后,借口说方才碰见个熟人,与徐朗二人就此告别,向两人相反方向去了。
自水潭前折返已过了半日有余,却毫无自己要找之人的踪迹。白兜了几个圈子的林鹰扬只得返回那处小门环绕的厅堂,想着继续往地宫深处探索。
大概是耽搁太久,此时厅堂四周小门紧闭,空旷无人,比半月前更添几分肃杀之气。
今日故地重游,难免回想起当时种种。虽然心情大有不同,林鹰扬却觉得若是重回那日,他的所做所为也并不会有何变化。
生来没有那种气魄,恐怕这辈子也做不了大侠。
不过此时实在不是思索反省的时候。林鹰扬在厅中四下徘徊,正愁着该去何处,就在一面石门上发现了同行时谢楠云曾经用过的记号。林鹰扬大喜,遂决定沿此路前行,先行找寻谢楠云。
经过一段与当初自己与连海生离开时相似的迷宫,不知寻了多久,昏暗处隐约见一女子倚在石壁旁休息,定神细视,正是谢楠云。
此时谢楠云已被困十数日,衣角沾灰,脸上脏污,左手臂活动也不太自然。见林鹰扬找来,她有些惊讶的站起身,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色来。林鹰扬却是没想到谢楠云这般反应。他本以为被抛下的谢楠云理应有些怨气,谁想却看她喜形于色,心中更是愧疚。
谢楠云见他无恙,也不谈自己遭遇,开口便问起其他二人情况。得知连海生平安脱身,阿朗也和朋友结伴离开,谢楠云更是喜不自胜,仿佛身上的伤痛都在此时飞了去了。
面对如此的谢楠云,林鹰扬自感汗颜,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从随身携带的东西里掏出衣服干粮递给谢楠云。东西递了出去,才意识到这地宫实在没有女孩子换衣服的地方,难免有些尴尬。谢楠云却是没想到这层,随手将东西收入行囊。整理一番之后,两人便结伴继续探索。
短的我也好尴尬……
柿子在之前八卦田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有缘虚阵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