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前因后果
O快要恋爱了?
阳光射进二楼检验科的玻璃,单调房间内冲入一剂暖色。苏乐山看了看窗外那抹暖黄,伸出指尖轻轻的捧住阳光,微紫的指甲恢复了点血色。这是温暖的感觉。
就如这实验室一样,苏乐山也好似改变了那么一点点。
那个风尘仆仆,满脸严肃只说一句“谢谢。”就好似把空赶下岗一般的苏乐山,踏着轻快的步子,语气温和精神爽朗,用一个微笑对天羽空说道,“早安,辛苦你了,空。”,交接时苏的嘴角细微上扬,给人的感觉不再如之前那般冷淡而死板,虽然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实验报告风格,但温软的语气却使这些话语散发出大男孩的木讷感。当这个大男孩穿上白大褂,带上眼镜,熟练的带上手套的那一刹那,踏入实验室的一瞬间,仿佛注入了灵魂一般。目光如炬,闪闪发亮,举止恰到好处,干脆利落,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自信。周转于各类奇怪仪器之间的他并没有给人一种紧张感,反而很怡然自得。这种自信在近期表现更为强烈,苏把忙碌变成了一种充实,而不是压力。
不知是最近苏变得更加高效,还是闭院以后少了许多任务,苏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能够站在实验室里,静静的晒一会儿太阳。
我这是怎么了?苏乐山笑自己。明明这是我以前最害怕的时刻。一个人在实验室的时刻。
孤寂,落寞。即视感和现实的强烈对比无数次将他拖入深渊。
如今的他却看着空气中的小尘埃被光照亮轻柔的飞舞,像个闲来无事的小孩子一样。
无来由的,苏又勾起了唇角。因为雷明就在隔壁,他知道这点就足够驱散所有的不安。
是啊,我这是怎么了?若换做别人,苏断然不会去关心他有没有打架,受没受伤,更不会冒失的闯进别人的屋子,强硬的说要察看伤势。
若换做别人,苏决然不会让他踏进休息室一步,更别说让他睡在里面。
可那是雷明。
如果说苏什么时候对雷明产生好感,大约是在听说到他的流言蜚语之后。
当苏乐山从空那儿听说到雷明以前那些或真或假的风光事迹时,没有惊吓也没有嫌弃,只有一个感觉——这个孩子体会过人生。所谓浪子回头,大致如此。
他是比自己好上千百倍的金子。
“苏……”初识时,雷明对着自己的胸卡皱着眉头半天不说话,
“乐(yao)山,”苏低头无奈一笑,“不过你想读成乐(le)或者是乐(yue)都没有问题。”
“虽然说名字是取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苏小声的呢喃却被雷明听到。
却不想,自那以后,每每唤他全名,雷明叫的,都是乐(yao)山。
再到后来,无论是日常的问候,还是深夜送的咖啡,都让苏觉得雷明虽然粗枝大叶还是个榆木脑袋但是很真,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源于本心,活得自在逍遥。也让雷明对苏的好意与其他寒暄客套都不同。
当苏意识到雷明给自己的是安全感的时候,便是雷明死赖在休息室里的时候。每当回想起早已离开自己的研究所伙伴们,只要抬眼望一眼在休息室里安静玩着手机的雷明,不安恐惧全都烟消云散。
“你睡吧,我就在隔壁。”你睡吧,我知道你在我的隔壁。现在,变成了依赖感。雷明睡在休息室不走后,苏有些窃喜。这是他的求全方式,他的保持距离。他的努力,苏都看在眼里。
如果说这是喜欢,我承认,无可辩驳。
可这是爱恋么?
伤脑筋……苏乐山想到这儿不免眉头一紧,出了实验室准备去休息室后拿盒维他奶,他在熟识雷明之后少喝了很多,所以把藏在实验室里的全都放回了休息室。
可走到时,却发现白色屏风后挂着一套白色制服和七七八八立着的日用品,一副努力收拾好却还是一团糟的样子。
这家伙,不会打算住在这儿吧!一时间,苏内心不知是喜是悲,也不知这些东西是该丢还是该留,呆愣在原地。
“哟,还没下班啊。”而肇事者就这样从容自若的走了进来,丝毫没有介意。一副这儿就是我家那样的理所因当。
见自己愣住不说话,雷明嬉皮笑脸地似要抱一下。出于本能,我随手就端起了窗台上的仙人掌。
“不行,这盆开花了。”却在下一秒心疼起陪自己许久的仙人掌。
便抄起桌上的杯子,毫不犹豫的泼了过去。
我……在干什么?
看着雷明滴着水笑着冲着自己笑,苏心不由一紧。我干了什么?
“傻愣着干啥,还不快给我点纸。”
“食堂,你去不。”雷明似乎一点事儿也没有的问到。
还不想吃饭,苏自然的摇了摇头,“我过一会儿去。”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改口到。
是啊,我还不想吃饭,可如果和你一起,那再好不过。
这是爱恋么?苏心头的伤还流着血,苏的心还住不了人。
这是友情以上 ,恋人未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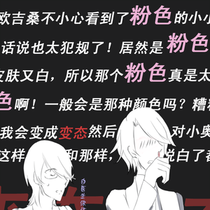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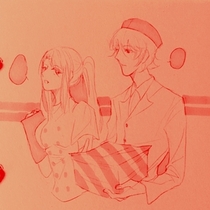
打卡。OOC致歉。
孤身一人的浅羽夕颜END线开启。黑历史开启。
死亡END预定。
谢谢观看,世界再见。【躺倒】
正文
“你射杀多少蓝鸟都没问题,但要记住,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一桩罪恶。知更鸟唱歌给我们听,什么坏事都不做。它们不吃人们园子里的花果蔬菜,不在玉米仓里做窝,它们只衷心地为我们唱歌。这就是为什么谋杀一只知更鸟就是一桩罪恶。”——Harper Lee
第三周的浅羽夕颜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床被子。
她见到乌狸先生的时候,是星期一的下午,女孩子躺在床上变换着各种姿势玩电脑打游戏,几乎乐不思蜀。
和女孩子一样好看并且有着柔顺的浅亚麻色长发的乌狸先生敲了敲浅羽夕颜的房间的门并推开之后,看到的,是女孩子坐在床上按着手柄发出了奇怪的哀嚎的崩溃的脸。
她在打游戏,并且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搭档的事情。
浅羽夕颜觉得如果是她她都要生气了,可是乌狸先生——虽然一开始浅羽夕颜把他认成了温柔可亲的大姐姐,可是当乌狸先生一开口,浅羽夕颜就立刻明了了眼前的人的性别,不过她并没有询问这件事的缘由,她直觉上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谁都可以触及的。乌狸他看着浅羽夕颜,伸出手来拍了拍她的头,露出了超级温柔的微笑问她要不要去看电影的时候,夕颜感到了无比的羞愧。
毕竟她差点忘记了这件事,但是对方并没有为此而责怪她,真是太温柔了。浅羽夕颜庆幸着自己的幸运,一口答应了下来。
冬日里料峭的寒意已经渐渐消融在越来越温暖的风中,不过即使那样晚上依旧还是很冷的。整场电影浅羽夕颜都在咔嗤咔嗤地啃着爆米花宛如一只仓鼠连脸颊都鼓了起来,可是身旁的人连谴责都没有,只是无奈地拍着她的头。电影散场后两个人漫步在走廊里,浅羽夕颜转过头来看着身边的人,他的笑非常温柔,侧脸俊秀,然而深棕色的眼瞳中空空洞洞,无星无月亦没有任何的光芒,仿佛藏着无数的故事。
浅羽夕颜忽然就想,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藏在心中无法说出口的过往吧。
谁的瞳孔里都映着一个无法得到的人的影子。
女孩子笑了起来,那是一声很短促而且轻的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笑声,可是她能感到自己身体的温度从指间渐渐流失,心都要揪痛起来,那种痛一瞬间炸裂开来,几欲昏厥过去。
可是浅羽夕颜只是脸色白了白,而后神色如常的与她的搭档告了别。
她是在半夜跑到爱川湖边的。
女孩子踮起脚尖轻轻地推开门,在月色下奔跑,她亚麻色的头发在夜风中飞扬起来,这个想到什么就会立刻去做的姑娘,在半夜痛的几乎睡不着的时候,忽然想起了爱川的七大不思议。
于是她悄悄爬了起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连头发都没有扎起来,就跑了出来。
她内心不知为何生出那么多的恐慌,仿佛这样奔跑就能逃离什么,可是她的体质过于娇弱,只是奔跑了并不很长的一段路就开始气喘吁吁,然而心脏的抽痛还是没法停止,而这时铃声忽然就响了起来。
浅羽夕颜慌忙取出兜里的手机,她苍白的指尖颤抖着,几乎要抓不住手机。
那首钢琴曲固执而反复地响着,在空旷的走廊中回荡,夕颜按下了接听键,对方的一声轻轻地呼唤几乎要让她落下泪来。
“姐姐。”她忽然就捂住了自己发出的带着哭腔的声音的唇,任由自己落了泪,而后在对方染上了惊慌的担忧声线中,告诉她,“我想你了。”
感谢世界,你没事。
于是心脏那样的抽痛似乎也可以忍耐下来。
她在空无一人的月色中,坐上了船,她举着桨乱划一气,在湖面上转了两圈,才被温柔的波浪送到了湖面中心。
而湖中心的倒影中,空空荡荡。只有温柔的月光。
浅羽夕颜看着湖中心愣了良久,忽然就躺倒在船上大笑起来。
承认吧,你谁都没有爱过。
My mother has killed me,
My father is eating m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sit under the table,
Picking up my bones,
And they bury them,
under the cold marble stones.
谁在大笑?谁在痛哭?又是谁,坐在一旁哑然无言。
能记得的是少女掌心的温度和坚定的表情,告诉自己别怕。
世界终究成了一片漆黑。
我的母亲要杀了我,我的父亲要丢弃我。
我的姐姐坐在了谈判桌前,与我的父亲对峙,终究据理力争,使我获得了活下去的权利。
拥抱最终救赎了谁啊,这苟活的人还是要将那偷走的岁月尽数还清。
浅羽夕颜咽下喉头的腥甜,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
可阳光下,她仍然无知无觉的微笑着。
仿佛不知道自己会迎来怎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