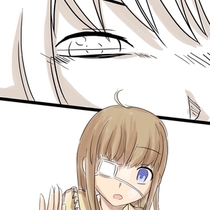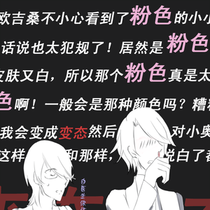保田秀一和楚医生的相遇。稍微写写两个人各自的过往。欢迎指点~
=========================
保田秀一匆匆赶到食堂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半。
平日里就算错过了用餐高峰,总还会有些刚刚结束了繁杂手术的医生护士,或者贪玩晚归的年轻患者;可是现在,大厅里几乎什么人也没有。保田秀一端着盛有食物的铁质餐盘,茫然地望着空阔静寂的饭厅——洁净的白色墙壁,白漆的地面和清一色配套的白色桌椅——也许是食客太少的缘故,这偌大的空间显得分外空旷——并且森冷。
黑发青年觉得有些窒息。他不喜欢待在室内,尤其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夜晚——如果食堂的餐具可以随意带走,他更愿意选择爱川湖边那个可爱的木质凉亭。
一整片苍冷的白色中间,只有一处渺小而突兀的黑色,像是晕开了一块小小的墨斑。一位医生坐在大厅正中的位置里,一言不发地应付着面前餐盘里所剩无几的食物。那男人看起来比他年长一些,一对儿细长的凤眼透着种凌厉与干练;黑色短发打理得整整齐齐,就连白褂下面着的立领唐装,也是深黑色的。
那人胸前漏出的一小截儿铭牌上明晃晃地印着一个“白”,可他却是黑色的。
保田秀一不认识这位医生。他右手的小指不知何故只有短短一截——那让他看起来有些可怕。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黑色的医生突然抬起头,挑着眉眼对保田秀一招了招手。“来坐么,您?”男人用一种京味儿十足的腔调说:“今儿可清冷。”
秀一眨了眨眼。他在原地浑身僵硬地犹豫了好一会儿,发现对方依然好整以暇地等着他过去,只好捏紧了手里的餐盘,几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保田秀一——他知道这个后脑受创的孩子:青年昏迷不醒的时候,男人曾受托为他验明颅骨的损伤状况。
楚江白看着那孩子把手里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放在他对面。他有对儿剔透的绛色眸子,映着饭厅顶灯投下的白光,像是血红的璀璨宝石;虽然身材颀长、身形也足够结实精练,可是单薄的臂膀让他看上去仍是个未及弱冠的孩子。
他听说保田秀一失去了入院前的所有记忆。
“白……”黑发的青年小声说,眼睛直盯着他胸前的铭牌。
“楚江白。主治医师,骨科儿。”楚医生把铭牌从大褂的皱褶里拉出来。
青年面无表情地低下头,沉默在餐桌上蔓延开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秀一。保田秀一。”
“今年多大了?”
“好像……是十八岁。”
楚江白把最后一筷子沙茶牛肉放进嘴里,展开食堂附赠的餐巾纸擦了擦嘴。洁白的纸巾几乎立刻便被略泛着红的汤汁沾污了。
十八岁呵……多曼妙鲜活的年纪。——那一年的夏雨,倒在暗夜里的、被触目惊心的血泊和暴雨所湮没的夏雨,不也正是这如花儿初绽般的年龄?
“楚医生……”
男人回过神来,发现对面的青年正定定地看着自己。
“小拇指……疼么?”保田秀一犹豫地问,“它为什么不见了?”
楚江白把右手举在两人之间,让那一小截儿残肢完完整整地暴露在青年的目光之中。
“曾经痛得刻骨铭心。”他回答,“年少轻狂所应得的训诫——这儿的饭菜不合您胃口?”
男人轻描淡写地岔开了那个关于雨夜、关于夏雨,关乎死去和新生的话题。
保田秀一愣了愣,顺着楚江白的目光看向面前的食物。盘子里堆积如山的蘑菇通心粉被他的叉子不断翻搅着,却并没动几口;当做饮料的、巨大的玻璃牛奶罐却是已经见底儿了。
“不……”青年血红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慌乱;他垂下眼睑,睫毛在面颊上留下一小片灰色的阴影。“也许……有一点。”
楚医生隔着桌子向前探出身体。“保田秀一。”他用一种谆谆善诱的声音说,“还记得……母亲的味道么?”
楚江白的问题已经超出骨科医师的辖域了。保田秀一抬起头,发现对方细长的凤眼正炯炯地盯着他瞧,带着迫人直视的霸道威压。
没有记忆的青年抿了抿嘴。他想告诉对方自己什么也想不起来,脑袋里着实只有空白一片——可是一种太过熟悉的味道哽住了他的喉咙,让他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舌头上柔软温润的触感,带着些许鸡蛋的清甜——节约的缘故,砂糖加得并不算很多;加上微酸适口的番茄酱——
甜的煎鸡蛋卷。
那是谁?他突然想道。
那个会把盛着加了番茄酱的煎蛋卷的、绘有三色堇的盘子端给他的人,是谁?
——那个笑着嘱咐他要细嚼慢咽的,是谁?
尖锐的剧痛在他脑袋里炸裂开来。酸涩从他如若刀绞的心底里翻涌而出,可是还未及从咽喉、从眼中奔涌宣泄,便生生被止滞了。
保田秀一苍白的手指攥紧了裤子柔软的布料。
——那个扶起因跌倒而哭泣的、年幼的自己,温和地教导他男儿不应哭泣的人——是谁?
倾盆的暴雨砸落下来。透骨的风夹杂着冰冷的雨水,恣意肆虐在昏黄的天与地之间——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寒冷。一个怀抱紧紧地包裹着保田秀一,将他幼小稚弱的身躯与那寒冷的世界隔绝,像是令人心安的温暖襁褓——
——是谁抱着自己奄奄一息的稚弱身躯,赤着双脚奔跑在覆世般的雨幕之中?
是谁跪在医院冰冷的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救救我的秀一”?
被他遗忘的——是谁……
“秀一?”一个声音穿过疾风骤雨,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你看上去不太好。”
一个沙哑的字符从他微张的嘴里挤了出去。
“救……”
远远地,传来一声叹息。“放松——跟着我,放轻松,秀一。”一双温暖的手掌包裹住了他疼得几乎就要裂开的头颅。
。
TBC
。
=============
好巧两个人的过去多少都和雨有关系~
接下来楚医生给秀一按摩头部的画面就交给秀一了~~XDDD
秀一记得定时来我大骨科按头~【你

*OOC请告知
*没法给自己发糖只好隐晦的发点别的cp的糖
*希望好吃
-------------------------------------
今晚的夜空很美。
我百无聊赖的坐在值班室望着窗外,一双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天空中闪烁的明星。今夜有雾,但并不厚重;月亮弯着腰掩在它后面,活脱脱一个害羞的恋爱少女。这样的它散发出的迷濛的光,让我不由得想起手术台上类似的光亮。它用自己尖锐的一角挑起一边,半遮半掩,影影绰绰。我着实是个没什么想象力的理科生,只觉得夜色很美,却再也想不出甚么好的语句来形容它了。于是只好更换了一下叠架的双腿,无奈的继续翻动着手中的书籍。
夜晚的爱川医院很静,没有需要急诊的病人慌张的脚步声;也没有家属哭天喊地的躁动;连病床被推进来挪出去的轮子转动的声响都没有一点。说是我很享受,也可以说静的可怕。然而这样的寂静搭配上这样的夜空,不知怎的,我突然有种想沐浴在月光之下的冲动。低头看一眼腕上的手表,距离换班的时间还有一些,只好无奈的叹气,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了文字上。今晚本不该我值班,但无奈闭院后工作量骤然增大;加之我并无其他事情可做,便欣然接受了这份额外的任务。
但此时此刻,从小到大都身为模范生的我,满脑子都想着翘班。翘班后找个无人的地方,喝点什么。心中并无烦恼也无苦闷,但一旦这个想法冒出来了,便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了。
“还有多久呀……”我自言自语的问道,低头看着腕上的手表。十点一刻,还有一刻钟,只需要再等一刻钟。
时间像乌龟一样慢慢爬过。无心再看书的我几乎要昏睡过去,这才有人来接班。我向他点点头,又露出一个暖心的微笑,然后便朝着超市的方向走了过去。
想法在心里还没有太过成型,因此决定看见甚么便买甚么的好。从超市走出来的我呆呆的望着手里的两瓶啤酒,瞥了瞥嘴,最后还是没有把他们送回去。我不嗜酒,也不反感;但它着实有令我苦恼的地方。
或许品酒是意大利人的天性,从小,隔壁家的大人——也就是穆杨的父亲——就教我品酒。与其说是品酒,不如说是饮酒。他当真是把我当成了好苗子来训练。日积月累下来,我也算是对酒有了一些赏鉴之能,连带着有了一个好酒量。还记得大学时的校联欢会,就像是大家都知晓了我的过去想要考验我的酒量似的,一位接一位,一杯接一杯的来与我碰杯。记不清那日究竟听到了多少次清脆的“叮咚”声,反正最后我的脚边全是烂醉如泥。
我不知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酒量大是否是好事,知道的是自那之后便没人敢叫我去喝酒了。
想起往事,我不由得夸张的扬天长叹一口气,也顾不上周围是否有人。蓦的睁开眼,只瞧见不远处的天台在向我招手似的闪耀。我又看了看手上的两瓶酒,掂了一下分量。估摸着那里无人清静,我也喜欢高处,便再次向着搂的方向走了回去。
---
当我略微有些气喘吁吁的推开天台的门时,一阵风恰好席卷进来。那风并不算寒冷,反而带着些许独特的温暖,吹着我的白色外套和工作裙。我苦于双手拿着的啤酒,无暇去阻拦那几乎就要乘风而去的短裙。短暂的微风过后,我看见了天台上的另一人。
那人穿着代表病人身份的住院服,却套了一件与之极其不搭的黑色夹克外套,此时正用双臂肘拄在天台的栏杆上。他身子微微摇晃着,似乎还在哼着歌。
“黑川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连忙打招呼道。
他怔了一下,随即转过身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脸,道:“小胡桃晚上好呀!”
“晚上好~”
“黑川先生怎么会在天台呢?”我问道。
“窝窝窝…√窝是来看scenery的,”他说:“绝★对不是伤心>>欲绝想要一个person靜靜才跑上来的!”
我尴尬的看着他,有些忍俊不禁。我是个笨蛋,不会安慰人,也不会说开解别人的话,无奈下只好晃了晃手中的啤酒。
“那……要来喝酒吗?”
“好!”
他一下子到了我的身边,我们俩对看了一下,默契的直接席地而坐。我是拿了一次性杯子上来的,虽然不太适合喝酒,但也只能凑和了。我把酒瓶放在两人中间的位置上,开了其中一瓶。先倒了一杯给黑川,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接过一次性杯,迫不及待的干了下去。
“慢一点喝呀,黑川先生。”我忍不住提醒道。
呷了一口啤酒,我又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些酒,但没敢多给,生怕他又来一次刚才的壮举。
他喝一口,我便倒一杯。如此反复下来,那一瓶啤酒已经见了底。我光顾着给黑川倒酒,自己杯中的水线几乎没有下移。
几杯啤酒下肚,他终于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胡桃桃你知☹道吗,醫★生他真的好かわいい~~~”
“松本医生?”
“不!是、夏、夏树<<医生!好想跟他出去约♥♥♥会啊~~~”
“嗯……”
“但是!为什么医生不懂……”他用几乎哭出来的语气说道:“好想……”
“好想……?”
“好☀想让他认识real的我嘛!”
说着,又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不能再倒酒给他。从他手中接过杯子,放在了一边对他说道:“黑川先生,慢慢来。”
“呜呜你说夏★树♦先♥生…他是怎么看me的?”他问。
“诶?我想,他应该也是喜欢你的。”我回答道,“因为经常和黑川先生在一起呢。”
“但是…但是……”
正当我思忖着如何让他相信而不再如此丧气时,天台的门被一脚踹开。
“你们俩,声音大的在楼下就能听到,”那人看着我们说道:“想不开就去找神前,上天台解决不了问题。”
“诶?我不是……”
“黑川一个病人就算了,胡桃你怎么也跟着瞎闹,”他截断我的话,继续道:“医生要内心坚强,不然怎么给患者做表率。”
我的视线不由得飞向了他手里的酒瓶,又向上看着他的脸。我思量着,他可能和黑川是一样的心情吧。不过是有备而来罢了。那些话又何尝不是在说给自己听呢,只是不知道他又是为了谁而苦恼。
一瞬间,我有些羡慕这样的苦恼。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感情,感觉上来说有点像我对很好的朋友的感觉,但又哪里不太一样。我苦于不能理解他们,只是烦恼着究竟哪里不一样。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随口问道:“德川先生,不介意的话一起?”说着,举起一次性杯示意着。
他迟疑了一下,习惯性推着鼻梁上的眼睛,并没有拒绝。
有人把盏同欢自然是再好不过,心中存在郁结的人更无法拒绝一个酒品良好的酒伴。我递给他一个一次性杯,心里还不自主的想着幸好超市的杯子是按打儿卖的。
德川和黑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们俩一边闲聊着,他一边慢慢的喝着。似乎是来了性质,还从兜里掏出一盒烟,磕了一根出来。他看着我,用眼神询问着我是否在意。我摇摇头,他便将烟点上,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放任那些白烟从嘴中冒出,跟随着清风飞向浓雾。
我看了看一旁死求活磨的要继续喝酒的黑川,坚定的摇了摇头。虽然平时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但醉酒后更是磨人。
“他怎么了?”德川问道。
“哎呀。在为和松本先生恋爱而烦恼呢。”
“松本吗,他似乎有说过让我帮他治疗性冷淡。”
“居然有这种事……”
“虽然没说为了谁,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吧。”他又吸了一口烟说。
我不无赞同的点点头,反问道:“那德川先生又是为了谁而苦恼呢?”
身边传来了被不知是烟还是酒水呛到的德川先生的咳嗽声,似乎是我问了他意料之外的话语。我连忙拍着他的后背帮忙顺气,一边致歉。
过了好一会他才摆摆手说没事。把因为咳嗽而快要掉下的眼睛扶回正确的位置,随手拿起身边的杯子,却什么也没有倒出来。几瓶酒,在三人的强势攻击下早已告罄。
“非常抱歉,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道歉道。
他尴尬的看着空空如也的一次性杯,无奈的放下,看着我道:“既然被看出来了就没办法了,毕竟也不是甚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上条,上条柃,”他说:“我很担心他。”
听着这个名字,我在脑内检索了一番。我的记忆力还不错,加上每天和阿空一起巡查病房,因此病人们大多都认识。终于我想起来了。
“应该是患有被害妄想症那位吧?”
他点点头道:“是,虽然不严重,但是让我操碎了心。”
“睡了?”
“睡下了。”
“所以出来喝酒消愁呢,”我笑着说,“有没有感觉好点?”他喝的不是很多,刚好是最适合消愁的剂量。
“一点吧,还是担心他。”
“唔,那就去看看吧?刚好也没有酒了呢。”
我看得出,他对那位上条先生要比一般的病患更加关心。如果说是甚么暴露了他焦虑的内心,我想一定是紧缩的眉头。以及说起上条这个名字时,嘴角不易察觉的弧度。
他没有说话,似乎也在思考着上条先生是否会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下定决心似的站起身来,低头对我说了声好。
他拿起自己带来的那个酒瓶——如今已经是滴酒不留——朝着下楼的方向走了回去。我没有看他,而是苦恼的盯着就差要嘴里冒泡泡的黑川。在德川先生的脚步声停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天台的门被推开的声音。紧接着,两个错综的脚步声响起。一个走远,一个靠近。很快,我就看到了那人被月光拉拽出的影子。
“松本医生晚上好呢,”我回过头打着招呼。
“很晚了,就算年轻也不能这么挥霍。”他看着我和几乎倒在地上的黑川先生说道。我认为他更多是说给黑川听得,便轻轻的推了推旁边人的肩膀试图让他清醒过来。
“黑川先生,松本医生来找你了哦。”
“唔唔……我一定是在做dream……★呼噜>>呼噜★”
“醒醒呀,不是梦。”
松本看不下去似的,一把抄起烂醉如泥的黑川,微微叹气。
“下楼梯小心点呀,松本先生。”
“嗯。”
“时间不早了,你…”
我微微一笑,接过话来:“好的,作为年轻人会好好爱惜身体的。”说着,摇晃着手中的一次性杯。
他点点头,看了一眼怀中酣睡的黑川——他正亲昵的呼唤着松本的名字。松本怔了一下,俄而低下头附在他的耳边。
我依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我猜测是黑川的名字。我上前帮忙把天台的门打开,听着哒哒的脚步声,目送着他们走下楼梯。
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着只余下几个空酒瓶和一次性杯子的天台,没有坐回原地。我来到刚才黑川先生趴过的安全栏前,也将双臂搭在上面,用双手撑着两颊。刚刚被风拉扯走远的浓雾恋恋不舍般又悄悄跑了回来,继续与月亮你侬我侬。
我歪着头看着,并无睡意;心情很好,嘴角不由得上扬起来。一些音符不由自主的跑进脑海里,我便轻轻将他们哼了出来。
我谛听着自己哼出的旋律,心想这大概是一首孤单的曲子,没有歌词陪衬的孤独的调子。
*主线打卡
*并不是所有《雷雨》都是伦理剧,也可能是动作片【别想歪
*祈祷楚哥别再抽中雷明了,亲情剧情不适合恋爱企
*楚哥这么帅你们还矜持什么,要么扑倒他要么躺下让他扑啊【正义脸
======================================================
山雨欲来风满楼。
雷明是绝对记不住这类文绉绉的词句的。
只是当他习惯性上天台打算放松下神经时,迎面看见楚江白背对着自己双肘撑在天台栏杆前的矮墙上,脚边的地面横七竖八躺满了烟头,脑海里立刻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上述诗句的念头。
黑云压城城欲摧。
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靠,倒霉。
楚江白听见身后的动静,不慌不忙地松开了指间还剩了大半截的香烟,任由半支残烟加入到满地烟头的行列,这才挑起半边凤眼打量着站在五米开外、摆出防御性微笑的那个男人——
“雷保安。”
楚江白的声音很沉很稳,过于清晰的吐字方式,仿佛枪支咔地拉开了保险栓。
“刚才的广播想必您也听到了,真是不巧哪。咱们好像又碰上了。”
雷明吧嗒吧嗒咬着尚未点燃的香烟,双手插在裤口袋里,很不文雅地抖了抖腿,这全是他当小混混时候的习惯性动作。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过去的坏毛病在面对楚江白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复苏。
“有话直说呗。”雷明翻了个白眼,“绕弯子累不累。”
“——对您,我楚江白没半点儿兴趣。不过既然咱们都被困在这地儿了,就还得劳烦您陪我演上一出儿。”楚江白边冷冷解释着边向前跨出一步,迫胁性的目光咬上了对方的视线,“我有不得不出去的理由。”
“就是要我假扮成情侣配合你拿疫苗是吧?”
“不错。”
雷明呸地一声吐掉嘴里咬得变形的廉价香烟,朝楚江白勾了勾手指。
“喂,来根烟抽抽。”
楚江白掏出还剩几根烟的烟盒,从中取了一根抛给雷明。
雷明接住,麻溜地往耳后一别,又笑着扬了扬手。
“两根,你记得的吧。”
楚江白微皱眉头,干脆将整个烟盒都扔了过去,然后沉声道:
“回复呢。”
雷明毫不客气地抓住烟盒往口袋里一塞,歪头望着楚江白凛冽的脸色。
“哦——”他拖长音调,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老、子、不、干。”
见楚江白不语,他调头便朝门口方向走去。
“我可以保证。”楚江白猛然出声道,“只要你肯配合,待我离开这里后,一定把你那俩心头好给救出去。”
如他预料的那般,前方的身影顿住了。
“检验科的苏乐山和护士站的阿兰,对吧?我有调查过,你跟他们关系匪浅。怎么样,这个交易你不吃亏。”
“姓楚的!”对面传来愤怒的咆哮,“有种就冲着我雷明一个人来,别把无关紧要的人牵扯进来!你丫不就是心里不爽快想挑事儿不是,行!少磨磨唧唧地老子现在就在这里跟你单挑!”
“好!”楚江白厉声说道,“今儿晚上七点半,就这儿碰头。按规矩谁赢了就听谁的,随便你来多少人。”
他从雷明身边大步冲过,一甩袖子。
“告辞。”
晚七点半,楚江白准时来到楼顶天台。推开冰凉的铁门,但见今夜无月,仅一盏孤零零的照明灯映亮了天台地面一隅。有凉风从黑暗中钻来,又从黑暗中消失,四下里一片静寂,偶尔传来远处马路上车辆的鸣笛声。
楚江白等了半晌,仍不见雷明的踪影,不禁轻蔑地冷哼一声。
“哼屁,”头顶后方冷不丁传来说话声,“老子没逃。”
楚江白回头朝发声处望去,只见约三米高的配电房上蹲着一团人影。只见那黑影在他的注视下懒散地站起身来,扑通一声跳落到了他面前。
“你一个人?”楚江白挑了挑眉毛。
“废话,老子说过单挑的。”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般,楚江白低声发笑。雷明只觉脑后风声一紧,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在肚子里暗暗骂了声娘。
要说在医院里最不想和谁动手,答案无疑只有一个名字。
雷明从裤兜掏出烟盒,用嘴叼了一根,又抽出一根扔给楚江白,嘴里嘿嘿笑着说:“请你的。”
楚江白捏着自己上午给出去的烟不屑地哼了一声。雷明没管对方的嘲讽,自顾自地点燃了烟,然后把打火机抛给了楚江白。
楚江白单手接过,啪地一声压出火苗,将烟头凑了上去。
雷明动手了。
趁着楚江白低头点烟的工夫,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照着鼻梁就是一拳呼出。
楚江白只觉眼角余光一暗,身体已然后退一步,右手格挡住对方的拳头,同时猛吸一口气,烟头红光瞬间燃起,他抛下打火机,接下了对方的第二拳。
“呵,偷袭。”楚江白哂笑,“街头上下三滥的下数。”
“对你还管什么他妈的下三滥还是上三滥,”雷明咔地一声踏碎了掉在地上的塑料火机,收回拳头提腿朝着对方胸口飞起一脚,“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来头,反正八成跟我一样——”
楚江白腿风紧随而至,足尖正中对方膝后区的那块菱形凹陷处,不待他将腿收回,对方已然踉跄后退,左膝弯曲一时竟是无法直立。
“……果然不是什么好货色。”雷明咬牙,嘿嘿冷笑,额上流下冷汗。
楚江白徐徐上前,面色从容地吐出一口烟雾。
“没想到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雷明向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聪明人,但老子并没有瞎。”处于下风的男人一边摆出防御姿势,一边从牙缝挤出话来,“除你之外,这辈子老子还真没有见过打着三个耳洞,还断了小指的医生。”
楚江白用下巴望着他,冷漠的眼神里压抑了一道带着煞气的精光。
“不过道上的人像你这样的……老子倒他妈的见过不少。”
左腿依旧阵阵麻痛,眼前那人却已在说话的这段时间里,正不紧不慢地向这边靠近。
一步。
两步。
楚江白迈出了第三步。
这时他离雷明仅有一臂之隔,提腿就朝对方胃中狠力踹去。如果这一脚踹中了,没个十来分钟怕是爬不起身,即使没中后退一步躲开了,一条腿不灵活的家伙也不是他楚江白的对手。
正当他如此思索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雷明不退反进俯身冲来,楚江白的鞋帮擦过雷明挡在身前的手臂,瞬间手腕处的皮肤和布料一并破裂,雷明咬牙抓住楚江白腰间的衣物,将全身的力气都聚集在肩膀上顶住对方的腹部,大吼一声撞了上去。
若是别人,给这一撞必定不是撞翻就是被撞飞,但楚江白反应何其迅猛,腰部吃力的霎那间已知不妙,左脚急忙抵住地面,踢出去右脚迅速收回,下盘努力调整着身体的平衡以及强行压低了重心,再加上雷明左腿被他踢伤使不上太大的劲儿,这一下硬是没有被撞飞出去,而是连连后退了好几步,直至后背狠狠撞上那根金属灯柱。
不知是本来就没有装牢实,还是螺丝被这一击给撞松了,总之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眼前顿时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