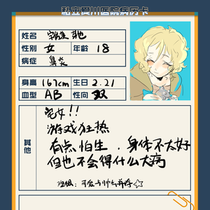室内弥漫着情欲高涨时特有的缱绻气味,黏腻的呻吟不断从颤抖的喉头溢出。
阿兰自背后被人拦腰抱住,在极度快感中叫嚣的肉体失控地抽搐着。他弓着脊背,像一具毫无反抗力的性爱玩物任凭别人肆意处置,滚烫的前额无力地抵在床单上,头发被唾液和汗水粘在嘴角及脸颊两侧。
从这个角度,他可以看见自己湿漉漉的分身随着捅入后穴的每一次冲击上下摇晃着,充满情色冲击的画面让尖锐的耳鸣声轰鸣着刺穿了他的头骨,大脑神经瞬间紧绷到极点。
肉穴在高扬的快感下死死绞紧深入其中的阳具,激得身后那人发出低沉的嘶吼,俯身贴紧了身下这具正不断颤抖着的躯体。
阿兰浑身哆嗦了一下。那人炙热的唇舌正在吸吮啃噬着他脊椎上的节点,并朝着肩胛骨下方一口咬下。
他两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整个人就要往下倒。
身前的床单上立刻浸上了点点白浊,还有少量射到了阿兰自己脸上。
这时从背后伸过来一只有力的胳膊揽住他的胯部,雷明从对方的身体里退出来,摘下粘糊糊的安全套扔进床下的垃圾桶里。阿兰喘着粗气瘫倒在刚刚射精的地方,任由床单上的精液弄脏自己,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之后他们便很有默契地各躺一方,一个开始摸烟盒,一个开始玩手机。直待到雷明点燃第三只烟的时候,阿兰大概是发帖和聊天玩得够了,终于开口打破了沉寂。
“喂,你。今天心情不好?”
他用脚踢了踢雷明的小腿,歪头打量着心不在焉的对方。
“说说看,是不是跟上次那个匿名告白的人有关。”
雷明哼笑一声,眯缝着的眼睛透过烟雾不知道看向什么地方。
“怎么,被人家甩了?”阿兰兴奋地凑上前来,满脸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八卦之光,“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嘛。”
雷明叹了口气。
“……那个匿名的人倒是有段时间没出现了……”
“哦——怎么?不出现了,所以你想人家啦?”
雷明也不晓得是没有听见阿兰的话,还是故意答非所问。
“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人家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的嘛。”
“憋着不难受么,要是我的话只怕对方不知道我喜欢他呢。”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说话做事不经过大脑啊?”阿兰啐了一声,“真是个猪脑子,太白瞎你那张脸了。”
“你丫的不就是看中咱这张脸了嘛。”
“拜托你要点脸……你也就只剩这点脸还可以看了。”
阿兰抢过雷明的烟,顺势跨坐到他身上,将床头柜上的保安帽扣到雷明头上,吸了一口后仰头朝天吐出。
“为了一个完全没有真实感的人心情低落,你也够没出息的。”
“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我——”
雷明欲言又止。
“我好像喜欢上一个人。”
阿兰带笑的表情僵了一下。
“什么?”
“你认识检验科的苏乐山医生吗?”
阿兰叼着烟想了很久才摸着头慢慢回忆道:“之前我去检验科找空的时候,好像是见过一个男医生,戴着眼镜很严肃不怎么说话的样子,不过我想不起具体长什么样子了——不会吧,你什么时候跟他打过交道啊?”
“嗯,就是他。”
阿兰一脸吃坏了东西的表情,然后突然噗地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哈……”
雷明看着阿兰,皱起了脸。
“笑屁。不行啊?”
阿兰打了一下雷明的帽子,烟灰掉到了床上。
“拜托,用脑子想想啊……你俩完全就不是一类人好吗,我真好奇你怎么冒出这么个天方夜谭的念头?说说你算什么,你连大学的门槛都没摸过。人家是什么,研究生!哈哈哈……小混混恋上高材生,你们是在搞笑吧!”
雷明张口结舌地半天反驳不了,沉着脸啧了一声,侧身又要去摸烟盒,却被阿兰一把按住。
“说真的。那种书呆子,你看中他哪一点?”
令阿兰惊讶的是,听见自己这么问的时候,这位平时吊儿郎当的保安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柔和起来。虽看上去面无表情,但眼睛里隐约藏着满满的笑意,似乎还夹杂了那么一丝不好意思。
“他……笑起来特别好看。”
雷明不禁想起苏乐山在实验室里工作的背影,每次都能让他在窗外驻足凝望上很久。那一天他站在窗外,无意中看到苏乐山捧着暖咖啡展露笑颜的景象,恐怕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真的,幸好他不经常笑,不然早被别人拐跑了。”
终究是没能压住心中的澎湃,雷明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不受控制地向上翘起。
“我之前没这样过,我想对他好,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丑话说在前面,你们不合适。”阿兰坐在雷明身上,双手撑在两侧,将脚一先一后地搭上了雷明的肩头。“不过既然你一门心思地往死胡同里钻,我也懒得管你们就是了。”
阿兰的身体比起一般的男性要柔韧得多,他双脚绞在雷明的颈后向前一带,将对方的身体勾到自己面前,凑上嘴唇将口中的烟雾缓缓送进了对方的口腔之中。
“不过你们要是闹矛盾,我会忍不住鼓掌的哦。”
他带着明烈直率的表情,一脸坏笑着说。
“切……”雷明拿他没办法,只好骂道,“妈的别再勾引我了,想干死我啊。”
“再来一次嘛——”阿兰用手指轻蹭着他的小腹,像蛇一样地缠了上去,在他耳畔娇声悄语,“……人家好想要。”
一旦感觉到对方顺应了自己的意图,阿兰便轻咬住了对方的嘴唇,先是慢慢地舔舐挑逗,然后进一步试探和深入,再至唇舌交战呼吸紊乱时,已是欲火一发不可收拾。
雷明从阿兰疯狂的热吻中夺回喘息之机,说道:“等一下,我拿个东西。”
“别拿。”阿兰双臂缠上雷明的肩膀,不让他动,“那玩意儿不戴也没关系。”
“不行。”
“我说不用就不用!”阿兰强行吻上去,舌头灵巧地在对方口腔中游动挑拨,透明的唾液顺着嘴角滑下,掉落在雷明赤裸的胸膛上。
“我想要你射在里面……”阿兰在雷明耳边细语呢喃,“……这样更舒服。”
他拉下雷明的帽子遮住对方的眼睛,用手指抹去残留在对方胸口的液体往后穴上涂去,一边扩张一边轻轻哼出声来。
“啊……嗯……”
像是听见召唤般,雷明朝发声的方向抬起头来。阿兰低下头,用乳首去蹭雷明的嘴唇,被一口含住的瞬间,酥麻感从膝头顺着神经直奔大脑。
雷明捧住了阿兰的侧腰,像舔舐糖果般用力吸吮着两颗坚挺发涨的乳粒,粗鲁地噬咬着小小的红肿的乳尖,他吻得越是粗暴,阿兰的呼吸就越是急促。
腹下直立的坚挺被一只颤抖不已的手扶住,接着便接触到温暖的肌体,面前传来忍痛的闷哼声,有什么柔韧的软肉正一点点反复吞吐着,最终将他的分身完全包裹住。
扶在腰上的手加重了力道,撑着阿兰的身体加速上下运动,只听得交合处的水声越来越粘稠,撞击声也越来越干脆急促。
阿兰咬住帽檐,借助着身下的冲击力一把将遮住对方视野的物品甩开。不顾身上被唾液、精液和汗液弄得粘糊糊的,他用身体紧紧贴住雷明,从对方身上传来的炙热体温和强烈的索求,使得富有弹性的肉壁像是拧紧了螺丝般吸紧了体内的阳具,惹来了一阵更加激烈的撞击。
“啊啊……”
阿兰失声叫了起来。
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冲击下,对方的手指碰到哪里,哪里便像失利的战场一般节节败退,当雷明的手指抚摸上脊背时,阿兰射了。
随即他便感受到有黏液似乎正顺着后穴流至了大腿根部。
阿兰精疲力竭地躺到了一旁,他听见雷明正从纸盒里抽了几张纸擦拭着刚才被他射到胸前的精液。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听着身后穿衣服悉悉索索的动静。
“阿兰。”
他听见雷明叫他,但他懒得应。
“你背后的那个疤,是怎么来的?”
“哦……那个啊,”阿兰终于在床上找到了手机,一边摁亮屏幕一边答道,“之前读书时候跟一个男生交往来着,因为走得太近,就被同学传得风言风语的。”
“后来他为了证明跟我没有关系,就拿烟头烫我来着。”阿兰漫不经心地说,连眼睛都懒得离开屏幕。
雷明愣住了。
“想起来那家伙还算是我的初恋呢,哈哈。”
阿兰正准备将编辑的文字发出去,突然间一只手臂穿过锁骨前方揽住了他的肩膀,背后的伤疤被亲了一下,随即耳边响起一个压低的嗓音。
“那是他没有眼光。”
头发被人用力揉了揉,脚步声从身边迅速远去,阿兰那句“你恶不恶心啊”的抱怨硬是梗在喉头未能吐出,随着脚步一起消失在那记短促的咔嗒关门声后。
#兄妹回忆杀系列
#冬音视角
#文笔渣如狗
#胡桃姐友情出镜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的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
——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冬天又到了,细雪打着旋从窗外坠落,在病房的窗上凝出一小片冰花。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忘了锁上窗子,稚名冬音赤着脚从病床上跳下来,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窗推开一线。
天空在弥漫的雪雾间模糊,住院楼前榉树孤冷的影子被素笔勾勒出一线,但更远处的景象就全然是揉成一片的白色,隐晦而不明着。
冷肃的风从窗隙间灌进来,卷着小片的雪花掠过她的指尖。冬音收回手,盯着看手心六角形的结晶,在开着暖气的病房中融化成细小的水珠。
稚名冬音喜欢冬天。
或许是因为名字的缘故,她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季节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共鸣,尽管冬日的大多数时候她都只得待在温暖的房间里,隔着窗户看纷扬的落雪。
病房门外传来脚步声,冬音飞快地合上窗户,几步跳上病床。床边放着刚翻了一半的小说,她将书页打开到书签的位置,假装自己正欣赏书中的一副插图。
“稚名医生你这是被人打了吗?”
“是狗咬的。”
“诶,医院里有狗啊?”
“我私人收藏的橱柜里就有。”
交谈声隔着门扉传来,披着白大褂的实习医生手忙脚乱地推开门,夏夜体贴地接过她手中的厚重册子,摆在病床对面的几案上。
“胡桃姐姐!”冬音合上书,欢快地招手。
胡桃朝她眨了眨眼,露出一个安然而甜美的微笑。阳光沿着朝阳的走廊落进来,在金色的长发间渲染出一小片明丽的色彩。
其实检查病房并不是胡桃的工作,虽然她热衷于护士的职业,天生的笨拙已经注定她无法胜任护理的工作。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手脚麻利,在无需动手的工作上胡桃显得相当靠谱,其他人也就默认了她这种抢占护士工作的行为。
胡桃在查房的名册上记下时间和床号,夏夜接过笔,在主治一栏潦草签下自己的名字。
“是你啊…冬音的主治医生?”胡桃有点惊讶地盯着册上的名字。
“看起来不像吗?”夏夜笑着问。
“那倒不是,我以为你们是兄妹。”
“的确是兄妹。”
“啊,是这样吗。”
胡桃略带尴尬地笑了笑,在记录的最后打上确认的标记。
医院里并没有主刀医生不能是病人家属的规定,但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保持绝对冷静是手术最基础的要求,任何多余情绪的干扰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误。
越是在乎,越是容易失去,正因如此,世界上才有了“悲剧”的存在。
心电图上的线条稳定地跳动着,
“最近的病情很稳定,过段时间应该可以下一次手术。”夏夜看了眼测试仪上的数据,在病床的边缘坐下。
这时候他看起来倒是相当正经了,可惜脸上胡乱贴着的纱布将仅有的严肃破坏殆尽。冬音扳过哥哥的脸,替他重新把纱布贴正。
“你是笨蛋吗?”冬音叹了口气。
夏夜没有回答,他靠在床沿上睡着了,阳光沿着玻璃落在他的脸上,浅色的发梢被金色模糊,骤然显出种与本人气质截然相反的温软平和来。
寂寞的,温柔的,就像冬天里第一场坠落的细雪。
冬音模模糊糊地将这一刻的场景与记忆中的那幕拼合在一起,并因此而微笑起来。
***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孩童的记忆总是紊乱而模糊的,即便是亲眼所见的事物,在脑海中拼凑起来的时候也势必受了主观的臆想,从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貌。
冬日降临的时候树木的枝叶开始枯落,枯折的落叶堆积成一片,被风卷着扬上天空。
祭坛上摆着黑白相片,两旁堆着花灯和果篮,棺棂停放在房间的正中,走进门的时候有人发放白色的纸花,花上夹着别针,参加葬礼的人就接过来,规规整整地别在胸口,然后将香典搁在门前的几案上。
按照惯例,告别死者的时候要穿黑色的礼服,冬音站在人群里,只看到来来往往的黑色。诵经声和悉索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声与影的海潮铺天盖地,几乎要将她吞没。
这时候有人走进了门。
稚名夏夜站在门口,沉默地注视灵堂中的景象。他没有穿黑衣,也没有戴上纸花,那身白色的西装在清一色的黑潮中显得突兀而乍然,就像坠入清水中的一滴重墨。
不知怎地冬音总觉得这一刻他和这里是格格不入的,这和打扮或者到来的时机并无关系,甚至也未必关乎于他本人。人们并不欢迎他的到来,仅仅因为他不属于这里,即使在棺材里躺着的是他父亲的遗体。
后来冬音才知道那天夏夜是从婚礼上赶来的,没人知道他从哪里听到的消息,但他确实来了,来得如此匆忙而不合时宜。
嘈杂的人流分开一条通路,夏夜沿着黑色的缝隙走过来,朝她伸出一只手。
“别怕,我来带你走了。”他轻声地说。
天上开始下起雪,小而薄的冰花旋转着落下来,融化在行人的肩头。
冬音伸出一只手去接落下的雪花,夏夜偏过头看她。
阳光透过云层,落在结了霜的地上,雪和人都在光辉下明媚,就像隔着纱的幻梦。
寂寞的,温柔的。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