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人类光辉的未来。”
——【PHANTOM幻影】
《妖区编号H-372》
本企为企划【妖区编号】系列第二期,以架空现代都市为基础的异能x怪物战斗题材企划,养老向,时长约两个月,需打卡
人设不审画技只审设定,文画手均可参与
本企将与终章同步结束,进行时间为3月17日00:00分 至 3月23日23:59分,逾时将不再接受任何新投稿,企划页面将会关闭,敬请留意。
所有主线打卡期已经结束,于打卡期内(一至三章)没有任何一次打卡的角色将被判断为【于幻影任务中死亡】,错过打卡期的玩家可于终章时段内补卡,投稿tag为【内部记录】→【日常互动】并标注补卡,但此阶段补卡只能计算作角色的最低限度存活,敬请谅解。
本期企划《妖区编号H-372》至此所有主线剧情发布完毕,再次鸣谢所有玩家的参与,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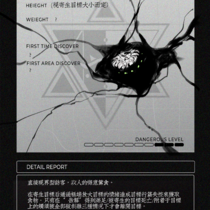


最低限度地打一下卡
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单纯地喝早茶罢了。为什么感觉他俩常驻在新界啊?
-
年关刚过,细雨便在街头巷尾悄无声息地飘落,云层低垂,压得整条街道湿漉漉的。
转过一个弯,数盏灯笼的红光透过微薄的雨幕打在薇拉脸上,将她的面容连同脚下的石板路都照出一片模糊的暖色。斑驳的木制招牌在风中摇晃,发出吱呀的声响,四面的墙上贴着快要剥落的纸质广告。薇拉看了看眼前这座略显古旧的茶楼,又看了看身旁的海明轩,递过一个疑问的眼神。
“走吧,忙了一个通宵,去吃点东西。”褐发男人将滑落的登山包往肩上一挎,率先踏入其中。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暖洋洋的热流扑面而来,混着茶水味和食物的香气。茶楼里热闹非凡,虽是早间,一张张木桌旁却坐满了客,茶杯与碗碟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各种琐碎的闲聊交织在一起,形成大片嘈杂的音浪。忙着端茶送水的服务生瞥见两人,先是一愣,随后有些拿不准地用英文说:“两位?”
“两位。”异口同声的普通话和白话,让那可怜的年轻人更加摸不着头脑。幸好,一位穿着制服的主管匆匆赶来,拍拍服务生的肩膀示意他继续去忙,朝风尘仆仆的二人露出笑容:“大堂刚好还有一桌空位,不介意在角落吧?”说完就率先走在前方引路。
一盅热茶,两件点心,普洱的沉郁内敛的淡香飘在空气中。薇拉坐在靠墙的位置,指尖轻点着瓷杯,海明轩端起茶壶给她杯中添到八分满。
“我都不记得上次看见雪是什么时候了。”他端起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又重新续上,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念欧洲了?”薇拉难得有闲情调侃他一句,“等忙完这阵,请个假期去北方,应该还能赶上雪季的尾巴。”
她拿起筷子,手指微微一抖。尽管薇拉早就掌握这种便利的餐具的使用方法,但每次实操总还是有些不太自然。所幸她没费多少力气,就夹中了那只散发诱人香气的叉烧包,顺利将其放入碗中,却不送进嘴,而是出神般地盯着它金黄色的外皮。
“八仙居……失踪……碎肉……叉烧包……”旁边桌上的谈话悄然飘进耳朵,神秘的窃窃私语音量不大,但充满了笃定。薇拉的思绪不自觉地被引到这些议论上。海明轩似乎也注意到了,轻轻抿一口茶,“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幻影午夜前后发来的报告书。你专注在分析送来的样品,可能没注意。”
“这么说,八仙居失踪的人和虚异访客有关。”她若有所思地夹起叉烧包,一口咬下。松软的外皮带着甜香,内里的叉烧馅入口即化,肉香与酱料完美融合,层次丰富又十分和谐,简而言之,确实好吃。
海明轩耸耸肩,“还以为你真的从叉烧包里看到了某种生物组织呢。”
“虽然不是这方面,但……”她不置可否,抬起眼,神情依旧是一副冷淡的模样。“你尝一口就知道了。”
他满腹疑惑,拿起一个包子,谨慎地咬下一点在嘴里细细咀嚼,“有什么发现吗?”
“趁热吃,很好吃。”薇拉顿了顿,露出个带点狡黠的笑容。
壶中热气袅袅升起,水雾氤氲,墙外仍是灰蒙蒙的阴雨天。
或許是災殃二字解鎖了什麼吧,那種病理性的執著已經有一段時間沒纏上響了,那種它一出現所有想法被強制扳斷的不適感消失了,而響也好一段時間沒再見著它了。
響現在在幻影過的還算不錯,這裡包吃包住,同事也很友善,薪資條件也很好,就是有些時候需要出一些任務,來應對那些統稱為訪客的妖異。
但這也不成問題,他只是討厭寫報告而已,連自己幾歲都不知道的傢伙,就別指望他會有能把報告處理好的能力了,訪客沒跑就已經是盡忠職守了。
響才這麼想著,上頭的任務就下來了,幻影發布任務的方式其實挺隨便的,可能你人在附近就直接送過去了,任務檔案基本上也是同事隨手交付,這次也不意外。
只是現在這個“同事”不正常了。
“怎麼了嗎?我們可是好久不見了呢~”
雖然換上了西裝,但那折扇跟長髮,響絕對不會認錯,他從沒想過會以這種方式重逢,災殃又回來了,雖然似乎變得有些不同,但那絕對是它,伴隨著災殃出現的還有那種病理性的執著,而且似乎更嚴重了。
當人時常經歷疼痛的時候,他們會漸漸習慣進而逐漸不再痛苦,可當人被從那疼痛的環境剝離,並開始習慣安逸時,之前所承受的痛楚將能碾碎他們,現在這個情況就發生在響身上。
他現在甚至能夠清晰感覺到那些本屬於自身想法被扭斷的痛楚,那就像是骨頭碎裂開那樣,本來只是想法潛移默化的往災殃存在的方向改變,但現在那個過程被顯化了。
自我逐漸剝落的抽離感跟莫名的疼痛,這兩種感覺漸漸將響吞噬,如果就這樣吞噬的話倒也能算是一種解脫。
但不管怎麼折磨,這些甚至不算是真正“疼痛”的感覺根本無法讓一個身體健康的男人昏去,響只能夠被迫承受這一切。
等他終於支撐過來時,災殃已經不見了,剛剛遞給他任務文件的人是秦石,他也沒發現甚麼異狀,就這樣走了。
剛剛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般,響拿起任務文件,勉強的坐到工位上,發抖的雙手甚至要將文件抖落在地,兩臂施力才停止晃動
“不自控的四肢、渙散的思想,如果再加上一點對器官的渴望......那不就是喪屍了嗎?”
“老大派的任務還怪巧的。”
香港大學的醫學院最近發生了一起怪異事件,幾名大學生將一名新生反鎖進大樓的停屍間,結果到了隔天,卻發現受啃咬的屍體和吊在天花板上的新生,幾人被新生攻擊,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
就倖存者口述,他們幾個本來只是在執行社團的迎新儀式,之前他們也有被反鎖過,就沒發生異常,不知這次是什麼情況,新生就發瘋了,嘴裡吼著肉之類的單詞撲來,幸好他站最後面,及時的把停屍間的門蓋上,這才倖免於難。
後來警方調查現場,發現停屍間的門,不管用甚麼工具都無法破壞,索性把封鎖線拉上便將案件轉交幻影了。
就算現在的響人格快要崩潰了,但他也不打算放棄任務,切肉刀拿上,便一瘸一拐的往港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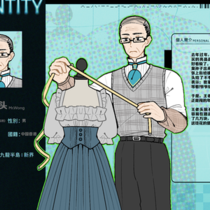
/没有前言。
阅读愉快!
其一:“梨花带雨”
从10000米的高空落下的梨花花瓣有多重?
在缓慢的飘摇减速下,它轻柔得只有拂过的点滴痕迹。
如果落下的花瓣包着一块冰呢?
2017年,春,二月。
清晨的雨花台盖着一层浅淡的薄雾,头顶的阴霾云层里是即将下落的雨滴。
既然雨不曾落下,那现在下落的是?
少年狼狈地就地一滚,来不及抹掉糊眼的泥沙血水,便再翻一遍。二次滚地多了些准备,显得标准得多,少年迅速起身,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直穿空旷的人行道,想要越过树林,躲入远方的建筑群。
危险,危险!不能被击中!
自步入平和社会后不再运作的生物预警系统被重新唤起,身体先大脑一步动了起来,躲过致命的危险,随后才是反应过来的思维,找到安全的方向。
天上的散落的白点稀稀拉拉,却无法忽视任一一个,跑起来只需一两分钟的距离如隔天堑,只寄托于迈步得更快一些。
三百米。
“铛!”
伞柄与落物碰撞,金属伞柄瞬间弯折,但下落的趋势也被改变。
两百米、一百米。
“噔、铛!”
仅为遮风挡雨而用的伞骨已不堪重负,扔下折得狰狞,无法再借力的折叠伞。少年深吸一口气,助跑伏身,堪堪滑进一片连檐长廊。
危险和雨滴下落一样来去匆匆。向建筑内疾奔了一段,少年才意识到如同催命符一般的清脆击打声已经停止,穿堂风刮过脸颊的凉意,带着冷汗、雨水和腥味一起混入水汽中,而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满身灰土,半张脸还盖着血。
“…下雨了?”过了许久,嘀嗒响声里才有一点喃喃自语,少年抬起头,再看不远处,分别躺着一团折叠伞与半面折扇,伞架畸弯,扇骨毁半,再远些,散着几片梨花瓣。
其二:未闻他名
2025年,春夜。
“感觉…今天喝了杯会记一辈子的东西。”
罗sir披着件运动外套,坐在收银边的桌子上吸着热橙汁,嚼着果肉碎,“好像是麻酱、混了些芋泥珍珠什么的,看上去一模一样!哎、一口下去……阿摩师傅,我这个月都唔要喝奶茶了啦。”
挽着长发的男子从后厨走出,将一碗餐蛋面放在罗sir跟前,只说:“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
“阿摩——阿摩师傅哎!”罗sir完全不接受这么平淡的反应,扯着摩因的袖子道,“我吃不完,你也吃几口。”
摩因并不饿,别过身子想去拍掉袖子上的爪子,罗sir早有预料般换了手,抓住了另一只袖子,摩因也立刻换边点去…好胜心起,电光火石间便过了几招,最后以罗sir掉了枚贴片,摩因皱了块袖子,以及一句面要凉了收尾。
罗sir吃了两口,见摩因盯着眼下的疤,笑道:“点样,男子汉的勋章还没看够?那梨花冰小时候划得了,现在想划也划不上啦。”
摩因摇摇头,觉着这话一股痞气:“当时怎么不再扎深一点,才给你长记性,吃你的。”说罢抚平袖口,伸手帮罗sir把贴片贴回眼底。
饭毕,罗sir收拾着碗筷,絮叨讲点工作上的趣事,摩因听着,分心在后厨轻点着食材库存,默默决定晚上冲拿铁加双倍奶。
洗好碗顺便拖了地,罗sir打了个哈欠,顺口说道明天去楚姐那喝酒便准备告辞,走至门口时不忘将门口的牌翻至close。
“后天再见啦!小摩师傅。”罗sir收店锁门千锤百炼一气呵成,完事挥手告辞。
“后天见,阿阑。”
摩因招呼完便闭了店门灯,走去后屋准备冲咖啡,一头青丝由黑转白,至此,街村为专人所点的最后一盏人烟也熄灭了。



斑神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向柏见讲起与自己的能力有关的事。
周末,夜晚,从五年前开始就一起去的酒吧,只不过今天没有坐在最醒目的吧台正中央,而是挑了一张既不靠窗也不靠近酒吧氛围的角落桌子,熟识的老板端来炸马铃薯片和鸡蛋三明治时还开玩笑道“就好像特工接头一般”。
“说不准还真是什么秘密任务呢!”柏见用相似的调笑语调回应,视线不着痕迹地落在对方端着小食篮放下的手又收回,待人走远后才拿起手边的易拉罐晃了晃——确认罐中还有多少啤酒,他一贯的做法——托着腮说,“他身上的也没有你的多。”
“慢慢来,至少现在什么也没发生,也没有因为不当使用能力而失语三年嘛!”斑神说着没有多少安慰意味存在其中的安慰之语。
而柏见举着啤酒罐一动不动,连目光也没有从他身上移开,于是他马上心领神会道:“还是想听失语症这部分?”
“嗯,爱听这个。”
“从前有个小孩儿得到了说什么什么就会实现的能力,但当时他还控制不好自己的能力,于是在春天郊游时说‘说不定会遇上暴雨’,导致春游从头到尾都湿漉漉的;口无遮拦地对同学说‘再这样下去马上会摔一跤的’,紧接着被这么说的人就左脚绊右脚在平地上摔倒,偏生又有这样那样的混乱和意外,最终演变成了从楼上滚下去,打了好几个月的石膏。于是祸从口出的小孩被同龄人讨厌了,被喊作‘乌鸦’,决定不说话之后又被喊作‘小哑巴’,不知道是不是沉默太久,他想反驳的时候发现当真发不出声音来了。”
“哇,好老套的故事,儿童文学都不会写的类型。”柏见毫无起伏地用颇夸张的语气如是点评并催促,“然后呢然后呢?”
斑神在他期待到发亮的眼神中轻轻叹了口气,做了一次深呼吸确定酒精还没漫到脑子之后才往下说:“直到某一天他又被别人为难了,说实话他已经觉得很无聊并且懒得回应,但是他崭新出厂的新同学——”
“等下,崭新出厂是什么形容,上次不是还老老实实地介绍为‘跳级上来的新同学’吗?”
“你倒是还记得……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讲出来嘛!总之,那位新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替他出头还把人打了,提着人的脑袋准备往墙上撞的时候他觉得不行,就下意识开口喊了‘停下’,然后失语症就这样离奇地从他身上离开了,虽然代价是回去以后他发了好几天的高烧。”
“或许可以增加一些细节,”柏见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桌面,“时间是傍晚,晴朗的天气,濒死的太阳的光辉一览无余,那个‘崭新出厂’的新同学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对那孩子的不言不语感兴趣甚至也想欺负一下子,还很想看他被欺负了会怎么反抗——本打算袖手旁观的,可毫无缘由地就翻过窗台到了那孩子身边。
“‘停下’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某种奇异的……应该说是能量?在那段走廊上降临了,抓住了新同学的手,那种触感没有硬度也没有材质,或许只是一团扭在一起的空气,但是仍然在抓着别人头发下了狠劲要往墙上撞的手上剐蹭出了血痕。
“事情解决了,那个小哑巴拔腿就走。可是新同学觉得哪能就这么算了,他好歹得把伤口的债讨回来。所以他追上去,喊他‘小美人鱼’、‘乌鸦先生’、‘斑神君’……”
“须完,”坐在对面的人突然开口打断了柏见即兴而起的喋喋不休,“你好烦人。”
柏见瞪大了眼睛,连啤酒罐都放下了:“你说现在?还是那时候?喂,我要伤心了!”
斑神被他制造出来的声响吓得一激灵,按着太阳穴将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才模模糊糊地抱怨:“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称谓排除出脑子……”
那些飞扬的碎发都耷拉下来,柏见扶着桌沿小声嘀咕:“好嘛,于是为了让新同学闭嘴,小哑巴又说了一句‘止血’让他的伤口停止了流血。明明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挺像个英雄啊骑士什么的……”
“拜托,你一开始明明也抱着看我热闹的想法,”斑神拉开啤酒罐的易拉环,把啤酒放在他面前,笑道,“好啦,现在我们已经这样凑在一起好几年了,有什么好难过的。”
安慰很有效,那双如紫水晶的眼眸在被识破的下一秒就盛满了细碎的笑意,装了三秒失落的柏见表情又飞扬起来:“因为你没有拒绝我嘛!我又对你那个能力蛮感兴趣。不知不觉就在一起这么久了,不过——”
说到严肃的部分,他的声音压了下来:“可你从来没说过你是怎么得到能力的。为什么?”
“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也没什么好讲的呀。”斑神先生一点点啃着手里的马铃薯片无动于衷。
“才没有。我那次……”柏见组织了一下语言,“那次看见的、突然出现的、像故障电视机屏幕一样的裂隙展开,从那里面出现了东西、简直是险象环生。”
实在难以编织起语言去覆盖自己关于不可描述之物的那段记忆,柏见吞吞吐吐连比带划了好一会儿,又泄了气地把手放回桌面上,下了结论:“哪怕能够处理那些东西的人马上赶来了,我也差点死掉了!真的很危险。虽然那之后我也得到了能看到‘线’的能力,还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你的能力是怎么来的?”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这里。和柏见投过来充满期待的目光对上视线,斑神启开他今晚的第二罐啤酒,抿了一口:“真想听?”
“真想听。”
“唔。我应该有说过我是七岁开始可以使用这种力量的吧?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了,回想起来大概是做了个梦。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危险。”
“梦?”
“嗯。和这里并没有什么差别的街道,大楼错落有致,只不过外观全部是用玻璃之类透明的材质覆盖的,内里的钢筋架构都一清二楚,建筑群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哇,不管是对居民还是交通来说都很不方便呢!”
“没关系,那里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街道上一片死寂,建筑物的表面一尘不染,比起‘城镇’这种有人气的说法,其实‘摆件’会更合适吧。那儿没有生命也没有灰尘的存在,像是……嗯,瘟疫,玻璃瘟疫在阳光下驰骋。”
“喂喂,”柏见喝空了今晚第五罐啤酒,把空锡罐重重按在桌面上,“变得费解起来了,什么玻璃什么瘟疫的,做成出版物的话读者可不会买账哟!”
斑神保持着笑眯眯的神态,对他的听众发表的牢骚也未置一词:“毕竟是梦嘛!梦残留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简而言之,那时候,那里,只有我一个生物存在,然后就是‘祂’——”
斑神停顿了一下,换了个更慎重也更贴切的人称代词,柏见听着这个小小的变化,挑了一下眉毛,不过并未发表评价。
“‘她’在那段时间恰好在这片街道的上空游过,堂而皇之、悠游自如。我想是因为那里没有任何一束目光投向‘她’,转念一想如果万众瞩目‘她’也依旧会我行我素地行进着、盛开着。”
“梦里的确充满了矛盾却自圆其说的逻辑。”柏见打了个响指,“可盛开?那个生物、哦,不是生物……‘她’身上有花吗?”
“‘她’其实像乒乓球树海绵,又像水母,还有点像教材书上神经元的图片。”斑神摸着下巴回忆,“停在我面前垂下触肢的时候又像一束别致的捧花。可‘她’实在太大了,比两层楼还要高,那样的话应该是一束五六米高的捧花,我还没有‘她’一根触肢一半高。身体中段应该是脑袋的部位微微低垂,巨大的眼睛和我对视。
“眼睛的颜色和我的一样,”斑神把一侧鬓角按在耳后,拨了拨品红色的耳坠,“眼睛里跳跃着白色的八角星。那是不可理解之物,那双眼中盛满了未被了解之失以及跨越时空的伟大思想。然后我就向‘她’开枪了。”
“等下、等等,枪这部分怎么没说?哪来的枪?”
“没说吗?是宾馆的无面人交到我手里的。”
“无面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那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宾馆在别的地方,到处都是无面人。我有五官,但是他们不排斥我,其中一个还给了我手枪。当时不知道怎么的,我就向‘她’开枪了。
“那一刻我听到田村先生又在嘲笑我、诅咒我。我想我一定从他这次的话语中理解了什么并说了什么,不记得了。”
柏见眨眨眼睛,他知道“田村先生”是斑神固执地对他父亲使用的称谓,也知道父子关系差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还记得这位“田村先生”被记录的失踪时间正是斑神七岁时。
这其中有什么关系吗?他并没有问出口,而是安静聆听。
“……老实说开枪的那个瞬间,我应该无意识地把‘她’当作母亲了。虽然‘她’既不会唱哄睡的歌谣、也没有温柔的气味和长发,甚至没有一副人类的面孔,但是你也知道我没见过母亲,七岁的我在那个瞬间拥有了‘母亲’。”
“哈……这种话像儿童教育读物里缺少母爱的典型案例会说的。所以才是‘她’?”
“所以才是‘她’。开枪以后我就什么都听不到了,玻璃瘟疫疾驰的世界恢复寂静,也许是枪声破坏了我的听觉,也许是声音和氧气都在子弹射出的那一刻被剥夺。那枚小小的东西燎着火花撞向‘她’,可‘她’只是毫无感情地注视着——或许其中涌动着温柔的情愫——子弹在视线中逐渐被看清直到恢复了静止时能够观测到的形态。那枚子弹停在了触须间,随着‘她’那些漾着柔柔水波的触须发出越来越相似的光芒。
“无端地,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已经不再能够触碰到那颗子弹了。它已经撞向了另一个层面,和‘她’成了性质形似的事物。”
事情越来越离奇了。柏见板着脸敲着桌子,沉默着思考着,两人的酒桌上环绕着刻板又富有规律的“橐橐”声。斑神继续往下说着:
“然后听觉就恢复了,我又开始听到声音。像母亲收到了来自孩子的礼物一般温柔的咕哝软声,模糊中一点一点搭建我被破坏的身体机能。
“我再次和那双闪着白星的眼对视。那双眼睛里亮丽的品红色开始流淌,沿着‘她’的脸落下,侵袭天空、渗透大地,却从来没能离开我的视线。
“——原来那些灼眼的颜色已经流入我的眼睛里了。
“品红色开始蔓延,攀上墙壁、遮蔽天空、包裹住天上一大一小的两轮月亮,而后一切都开始在亮丽的颜色里轻快地跳跃着融化。梦中的我在这一切的中心无意识地吐出一个音节,残存的路面与建筑在不会拐弯的音节中直直地破碎开去,天地坠落、日月崩塌。”
“——你坠入了不可思议的太平世界?”看过同一本书的柏见轻声接上下半句。
“不,”斑神笑着摇摇头,“我在家里的地板上醒了过来,发现时间过去了三天,身体还在发着低烧,差点要死了。我说‘我有力气去给自己准备一点退烧药’,身体照做之后,我去了田村先生的书房。他就在那儿,从我说第一个字开始就用惶惑的目光看着我,这之后他就离开家,再也没回来。”
斑神想再开一罐啤酒,伸出手去却只摸到了喝得干净的空罐,他从过分投入的故事会状态中脱离出来,扭头一看,那一侧已经被柏见用喝空的易拉罐搭了个毫无美感的建筑物出来,在酒吧的灯光下也闪闪发光。
他又叹了口气,做了收尾:“就这样,我得到了异能。不过不像梦里那样一个字就能让太阳落下,你也清楚的,只能拿来烧开水。用不用对世界影响都不大。”
“哪有的事!不是因为这个才会和我待在一起吗?”
“如果没有这项特质你就不和我玩啦?”
“才不是,但一段关系的开始不就是对某项特质感兴趣吗?”
“也是,人都有特质,有些人会对某一项特质感兴趣,一些人不会,社交圈就是这样筛选出来的。”
“又是泛论!”
闲聊的时间即将结束,柏见在调笑之后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毕业以后就走?”
“嗯,我也去找找属于我能力的因缘。会给你写信的,放心。如果想我的话可以按照邮戳来找我。要是实在搞不明白你得到了什么能力,不如就找我来帮忙。”
“那就说定了!”黑发的青年把喝尽了的啤酒罐放在桌上,一锤定音按灭了这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