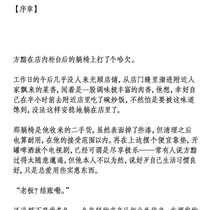“为了人类光辉的未来。”
——【PHANTOM幻影】
《妖区编号H-372》
本企为企划【妖区编号】系列第二期,以架空现代都市为基础的异能x怪物战斗题材企划,养老向,时长约两个月,需打卡
人设不审画技只审设定,文画手均可参与
本企将与终章同步结束,进行时间为3月17日00:00分 至 3月23日23:59分,逾时将不再接受任何新投稿,企划页面将会关闭,敬请留意。
所有主线打卡期已经结束,于打卡期内(一至三章)没有任何一次打卡的角色将被判断为【于幻影任务中死亡】,错过打卡期的玩家可于终章时段内补卡,投稿tag为【内部记录】→【日常互动】并标注补卡,但此阶段补卡只能计算作角色的最低限度存活,敬请谅解。
本期企划《妖区编号H-372》至此所有主线剧情发布完毕,再次鸣谢所有玩家的参与,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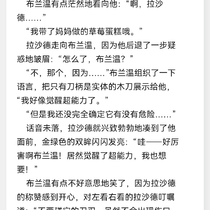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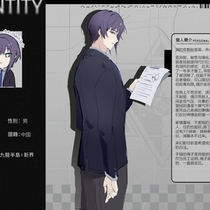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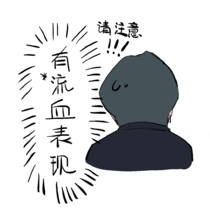



柏见须完在敲门前多多少少有些迟疑。
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地址。斑神持续一年寄来的盖着香港邮戳的信最早的那一封就塞了一张名片,上面明晃晃写着他现在的地址,近来的一封信则像是察觉到了他的处境一般,又塞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名片,仿佛在催促着他让他完全有理由来找自己一般。
他也确实动身了,实际上来香港有一段时日了,却因为在和不知道哪一团空气怄气所以迟迟没去找斑神。循着以往的经验,他尝试着在这座城市立足,想着最起码有点好气色再去找朋友。
哪想做过便利店店员、快餐店服务员和商场的化妆品销售之后,一天的工资还不够他在像样的酒店睡上一觉再好好吃一顿的花费,大少爷在花光了家中带出来的积蓄——还肉眼可见地气色更差了——即将无处可去之时,到底是放弃犯倔来到此处。
还在费尽心思组织语言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许久未见面容却几乎没什么变化的斑神就站在房内,神态自若地笑着望向他。
斑神出现在他视野中的那一刻,那些消失了几年的线也重新出现。这些线一定比过去还要多,红色、绿色、蓝色,铺天盖地而来,霎时间淹没了他的视野,连带着房内惊鸿一瞥所见的电视、沙发、暖黄色的灯光、光洁的大理石桌面、摆在其上的酒杯与酒……
耳边充斥着电视机里传来的天气预报声“明日有雨”,那人不声不响地看向他,或许在笑、肯定还在笑。但是他的眼中爬满了各式各样压抑许久迸发出来的各色的线,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最后他捂着脸遮住自己的双眼吐出一声呆呆的感慨:
“啊。”
-
“有客人?为什么准备了两个酒杯?”进门并在沙发上休息了好一会儿,直到那些缠绕着两人的虚构的线平静地贴在地面、墙面和天花板,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之后,柏见发问。
“在等你呀。”斑神给他倒酒,酒液漫到了杯中约五厘米的高度才停下。
“你知道我要来?”一个疑惑被解开,另一个疑问又浮了上来。
“上周看到你在卖化妆品了。”他的声音又带上了那种轻快又揶揄的笑意,“这之后每晚喝酒都要洗两个杯子。”
“哈——?!”闻言正要直起身子拿酒的柏见又重重地把自己摔回沙发靠垫里,发出表演欲旺盛的怪叫声,缓了一会儿才重新坐起来端起酒杯,“所以,你就这样等我找上门来?”
“就这样等。”斑神侧着脸,略长的鬓角向一侧垂下,颜色醒目的耳坠折射出灿烂的光辉,“既然你来了,不论过程是怎么样的,结果肯定要来找我。既然结果没有任何影响,那就等着你准备好就是了。”
一如既往地镇定,从来不会被任何事影响。他所憧憬的特质。柏见想着。他抿了一口酒,四玫瑰威士忌,浓郁的甜味久久不去,天花板上的光也暖融融的,好像焦糖和蜂蜜一起落了下来。
在这样的氛围下不被酒精影响委实太难,他一口气将杯中的酒喝干净,任由那些虚构的线上虚构的蜜糖滑落下来,好似要形成琥珀一般把他包裹其中。他的手指小幅度地抖了抖,那些线却并没有随着他的动作动弹,依旧柔顺地贴着房间内的平面。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道:“毫无头绪啊。”
“怎么?”
“线的事情。过去几年明明没怎么再见过,见到你的时候铺天盖地地涌出来了。老实说,很影响视野,苦恼啊。”
“还是只有我身上缠着这么多?”
“对。像蜘蛛结的网,密密麻麻的。”柏见将视线的焦点投向斑神,落在他手腕上纠缠得看不清颜色的杂乱的线上,“虽然现在什么也没发生,但仍然在意得不得了。这莫不是预言什么的,或者干脆是和你有关的麻烦?可是碰不见摸不着拿剪刀也没办法剪断,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不成?”
“另一端不是缠在你身上吗?和你有关的话应该不会是坏事。”斑神倒是乐观地这般说着,又给他的玻璃杯满上五厘米高的酒液。
“可还是想知道藏在线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嘛!”他吐出颇具无理取闹意味的话语,又在沙发上伸展自己的身体。
“哎呀呀……其实这几年我也碰见了一些和能力有关的事情,稍微也了解了一点。”顺着他的诉求,斑神也思考了起来,“激发了异能之后,还需要无机物媒介才能把它施展出来,只要手里好好地拿着什么……我不太确定以前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用钢笔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的话,我的能力的确得到了比较稳定的输出。虽然成功发生的事还是很微不足道。”
他在柏见的目光里碰了碰自己的耳坠:“用这个也可以,还更方便点,不过说出口的话还是比文字更容易消散。
“没准你得到的能力现在也只是待机的状态,只能给你引导却不能实质性地发生……这事还蛮玄乎的,或许该这样:怀着像泛泛之论那样不可言说的心情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样事物上,说不定它就会显现。要试试吗?”
又在说这种听不懂的话了。柏见想着,没有回应。事实上他的思绪已经顺着斑神的话语沿着河流顺流而下,他看见斑神睁开的眼——望向他,充满了无动于衷的温和——然后是在话语之间开合的嘴唇,其间整齐排列的牙齿、若隐若现的牙床,片刻之间口腔间涌上了品红色,顷刻又被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蜜糖淹没。
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线从地板上墙面上活泛起来,像一张张开的大网要死死裹住他,纷杂的色彩缠绕着他的视野和思绪,带来密不透风的溺水感。他想说点什么,或许该让久别重逢的老友别担心他的,可是陷在这样的状态里什么也说不好。
“须完。”他听见斑神远远地轻轻地喊他的名字。在缤纷的线中出现了一条特别的线。和那些纠缠的颜色不同,没有多余的环绕或者弯曲,也没有黏糊糊的蜜糖,它是这样不染纤尘、洁白无瑕,直直垂在他面前,如同上天垂入地狱的蜘蛛丝。
他感到身体里空洞洞的,某处传来“沙拉拉”的回信,有如海浪拍击礁石。
没怎么犹豫,他抓住了线。
“啪”的一声,他手中的酒杯承受不住压力应声而碎,玻璃的碎片倒映着周遭色彩像一只被摔碎了景色的万花筒,那些线条愈发狂乱,如沙尘暴那般拔地而起。他下意识站起身来,怀着“添麻烦了”慌乱地想要去捡起玻璃杯的碎片,却没注意自己被刺破的手上伤口里就滞留着一点点发光的小小碎屑,于是按住大理石桌面的下一秒,这张倒霉的桌子也四分五裂轰然倒地。
等等、等下?!
他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补救一下,但是言语带着令人安心的熟悉的魔性已经降临。
斑神说:“好了,停下。”
线如潮水瞬间退去,最终汇聚在某一个点——某一个人身上。耳边恢复寂静,柏见看着斑神向他走来,残存的意识只能想着:好可怕。
可是也好绮丽。
斑神的手指落在他的眼下,指腹擦着他痉挛的眼睑,随后覆盖住他不受控地转动着的眼球和颤抖的虹膜,连同那些滚落的温热的眼泪也一同敛去。
“好了,够了,”那个人重复指令,“你该休息了。”
-
一点刚刚开始探索能力时出的岔子。
这之后两个人歇了一晚上。第二天从后遗症中恢复了的柏见先生打扫了玻璃杯和大理石桌子,此后一个星期都在照顾为了按住友人不当使用的能力而过度使用能力导致持续发烧的斑神。
之后又花费了一些代价弄明白了鼠群的具体效果,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控制自己的力气。
響什麼都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在那個風平浪靜的6/14發生了些甚麼,以及在那天對他伸出手的白色人影。
但看著眼前的黑色信封,被削去的記憶似乎鬆動了些,可這不是重點,面前這個蛞蝓狀還會發出奇怪聲音的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
響如此想著,便面不改色的開始狂奔,他本以為以他一個兩年資歷殺豬販的體力,能夠擺脫這坨臃腫的蛞蝓,但他錯了。
當他腳步發力蹦出的同時,那條“蛞蝓”早已纏上了響的全身並發出了磨砂機般的叫聲,隨著力道加重響的意識開始模糊,意識漸漸沉入自收到信封以來所發生的一切。
那還是今早的事,響一如既往的在攤販上分肉準備販賣,當他還在用鈍菜刀跟豬排骨鬥智鬥勇時,一道聲音打斷了他
“災殃,九龍才是你的歸宿”
正因鈍刀無法剁斷排骨而煩躁的響抬頭望去,正想開口趕人離開時,眼前的景象讓他腦內一片空白。
“為什麼是你?我日日夜夜腦海裡都是你的存在,當時你帶著這把刀叫我來香港,我二話不說的就游泳過來了,你知道.....”
眼前五官完美衣著華麗的白髮身影,在出言引起響的注意之後,便一言不發,只是拿出一封由精美黑色信封包裝的信遞給響,響正想出言叫人....
突然,白髮身影身軀爆碎,眼前三眼六腳形似獅狀的妖物再次出爪而來,響下腰堪堪躲避,爪尖削去他一搓頭髮,右手撐地彈起躲避尾掃,響的面上已經冷汗直流,伴隨著汗水的還有憤怒。
“屌你老母,老子攤販都沒了,它人也沒了,今天這刀剁不碎排骨,但絕對會剁碎你的頭!”
此話一說完,響便被拍飛出去奄奄一息。
於此同時,那頭獅狀妖物也像被揉捏的紙張般扭曲變形最後消失。
接著便是剛剛的一切了,被蛞蝓纏繞結束回憶的響,又見面前白髮身影出現,一樣是那個對眾生毫無在意沒有顏色的神情,也一樣是那句熟悉的話。
“災殃,九龍才是你的歸宿。”
於此同時,蛞蝓和白髮身影消失,摔倒在地的響,看著手上的信封,慢慢的讀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