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前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水汽迅速的凝结在眼眶内,化作温暖的雨滴。
舌尖还残存着酒心糖果的味道——蓝色的,有点清凉的薄荷和海盐味,稍微带点高浓度酒精的辛辣,连带鼻酸和沉重的呼吸一股脑的打包进了知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脏的痛苦回流到了脑内,白夜一瞬间觉得有点头重脚轻,那种久违的感觉正在逐渐将身体吞噬,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紧握在他手中,那张和糖果一样蓝色的糖纸反射出破碎的光,在颤抖的指尖细碎作响。
我是怎么了。他有些迷茫地想到,水滴不断滑过脸颊,那些伤心的事情正源源不断地回想起来,像是突然坠进了无光的深海,口鼻处呼吸出的空气化作漂浮着的气泡,在伸出的手边破碎。
你看,白夜看着因为自己的反应而慌张的两个人想到,又给大家添麻烦了。当那颗糖放进自己的掌心,普通的拆开包装纸品尝,思考着会是什么效果时,一切都还在可控的方向。他并不是很小心谨慎的类型,而且看到飞过来的燕玄小姐时,他就联想到了琉奈。比起对大部分事情都无所谓的自己,妹妹总是乐于尝试,用笑容面对一切——琉奈一定会想吃的,他想着,所以自己先尝试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魔法并不会自己选择生效的对象,所以他告别已久的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在这不合时宜的瞬间。
"你还好吗?"在他模糊的视野里,刚认识的人温柔地递上纸巾。
"我没事的。"白夜撑起笑容,用手背拭去泪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明明没有哭的理由,在避开视线的深呼吸里,他一遍又一遍的想到。
没事的,那些都......过去了。这样的安慰早已成为习惯,过去的他在深夜的房间里,在无眠的夜里,在奔波的生活里,在拉着妹妹的手,走过每个春夏秋冬的时间里,都曾经这样对自己说过。
没事的。
已经用很长的时间接受了父母离去的事实。
没事的。
妹妹还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
没事的。
没事的。
......嗯,没事的。
可那份从心底涌上来的悲伤还是缠绕着他,甚至变本加厉,沉重的压在胸腔,每次呼吸都像磅礴的大雨。自我安慰的话语好像成了谎言——白夜突然有种被看穿的不安,我并不是在欺骗自己,他想,我曾经也想放声大哭,只是现在不想了。
本以为泪水已经成了自己身体中最无用的一部分。
那是无法容忍的软弱,是前行必须舍弃的东西,是悲痛后逐渐不在意的感情。
......是既定的事实,是倒计时的生命,还是无法挽回的一切。
是偶然惊醒的一刻,在世界里刮起的狂风暴雨。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眼泪还没有停下,安慰好像起了反作用,白夜还是重复着那句抱歉,将从眼睛中落下的东西的又化作自己的一部分。
"哥哥——"他好像听到了琉奈在呼唤自己的声音。希望她不要吃到什么奇怪的糖果,如果和自己一样掉眼泪,一定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白夜想着,找个只有两个人的地方,他会负责接收自己血缘所有的痛苦,不要让她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感到慌张。
她应该笑着,像往常一样,最好体验一些美好的魔法,就像喜欢的漫画情节那样。
因为水汽而朦胧的视野里,要守护一生的人就在此刻,飞着来到他的身边。
"哥哥,你看我是不是很灵活?哎?你怎么哭了?"
"没关系......我没事的,琉奈。"白夜听见自己笑着说道。
对,和往常一样。
???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天掉过眼泪,今天入睡要比平时快得多——闭上眼睛后,身体轻呼呼地飘向空中,是久违的轻松。
所以在睁开眼,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地和瑰丽的天空时,白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还在梦里。
天空闪烁着,夕阳和清晨交替出现,星星和白云打着招呼,太阳出现在黑夜里。不合常规的天幕下,是盛大的婚礼。那些今天才见面的人分散在花篮、气球和丝带旁,带着笑容,挽着洁白的婚纱,整理着自己的西服袖口,交响乐队演奏着梦中的婚礼,鼓点轻响,大小提琴和鸣,钢琴占据了大部分的主旋律,和人群共舞。
他们好像没有具体的对象,只是在音乐响起后,翩翩起舞。是在等什么人吗?白夜在星光洒下的光芒中捕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最后看到琉奈从舞台正中央登场。
她穿着白色的婚纱礼裙,是很适合她的那种,没有太过繁杂的装饰,也没有过大的裙摆影响移动......移动,白夜紧张地伸出手,但琉奈好像是没注意到这边,只是轻盈地在人群中穿行,好像从未受过身体的影响。她和其他女孩一起欢笑着,风拂过兰色的发梢,洁白的丝带装饰得正好,一切都在闪闪发光。
旋律悄然变化,人们拉起她的手,簇拥着她,像浪潮一样拥抱着自由的少女,跳起圆舞曲。裙摆旋转成完美的圆,夜晚的阳光像聚光灯跟随着每个舞步。这是一场没有对象的婚礼,因为琉奈是每一个人的新娘——此刻,只要享受单纯的爱,和永远的感情,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瞬间。
"琉奈。""琉奈亲。""小琉奈。"白夜听到很多人带着笑容在呼唤她,于是舞步更加紧凑,直到一曲终了,他们讲完了所有甜蜜的话语。
"哥哥。"最后,他听到妹妹像往常一样呼唤他,带着跳完舞后闪闪发亮的眼神。
"琉奈。"白夜在人群的尽头回应到。
他脚下是柔软的草地,是清澈的湖泊,还有即将走向12点的时钟发出哒哒响。他看到自己,又回到身体,最后将视线落在右手小指上。
那是一枚显然尺寸不同的女式婚戒。
"我会永远守护你的。"
萨克斯吹出最后一声尾音,盛大的婚礼落幕,天空只剩漆黑,他默念着,在只剩一人的世界。
*因为真的很水希望大家别看,ooc的部分也不要在意就当没发生过
众所周知,我和我弟弟是双胞胎。跟我们不太熟悉的人,会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有的时候熟人也会分不出。为了让别人能分清我们,我们两个刻意地做了一些区分。
首先是发型上,我的刘海是左分,我弟是右分。我们都不近视,但我戴着一副平光镜。服装上,我穿红色系,他穿蓝色系,个性上是他比较稳重,我比较跳脱,这样其他人就能从这些简单的区别中把我们分开。
不过,来到这里之后,我俩一下子变成了两个彩虹瀑布,面对的又是一群陌生人,我们就一下子玩心大起,拉着每个人来玩猜猜谁是哥哥的游戏。
我玩得很开心,但我弟没有。来这里三小时后,他非常严肃地跟我分析了现况:我们被不明生物绑架,与一群陌生人一同困在会馆,食物只有糖果,这里疑似存在魔法和超能力,幕后黑手的正体不明,目的也不一定像它说的那么简单。他还怀疑那个会说话的头纱是不是经过改造的无人机,想去把它抓下来看看,但它飘来飘去的,我们也抓不到。
我安慰他,你放宽心,天塌下来有哥哥顶着,我弟哈哈大笑,指着旁边一群身高一米九的大汉们,说天塌下来还轮不到你顶着。
其实我弟也没有那么担心,因为这都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解决不了的事就别担心,我们到了哪里都要过开开心心的日子。会馆的主人还算客气,说是房间还在准备,今晚就在礼堂里睡大通铺,结果铺床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羽毛乱飞的激战现场,进展之快忍不住让人怀疑有人在其中搅混水。
以礼堂的中间为界限,我们这群受害人很自然地被分成两组,乱七八糟地对打起来。我打人,我弟打哈欠,找了个好地方把自己埋起来睡了,留我一个人在战场上搏命,这就是当哥哥的应该做的。
我拿着枕头,问对面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头发乱乱的青年愣住了,说他叫黑霰。我说好嘞黑线哥!当头就是一枕头。黑霰被我打懵了,问我,你就是这么打招呼的?我说打招呼打招呼,精髓就在于打!
于是我们都拿起枕头往对方身上招呼。打着打着,又有新的人出现了。您哪位?哦,朴允赫是吧,您中文真好,打一下,什么,中韩混血,怪不得中文这么好,再打一下。您又是哪位?马和龙?马文龙?哦,戎马一生的戎,懂了懂了,打一下。您又是哪位?总觉得我们在哪里见过,哦舞城铃小姐,您中文真好,我这不是搭讪,真的不是,打一下,啊您手劲真大,我被打倒了,要一百万才能起来,您又是哪位,安乐是吧,打一下,小卢是吧,打一下,什么,我们是一个队的?不好意思,打错了,我先挂了!
转头一看,我弟躺在地上,委委屈屈:我被偷袭了,就是那个金发的男人干的,我起不来了,需要两百万才能起来。
我心想,我弟比我还敢要价。
我问他你不是睡了吗?他说本来是睡了,结果差点被人当枕头砌进堡垒里面,还是爬起来了。我说那正好,我去睡了,你来打下半场。
打了半天,我确实也有点累了,几乎是躺下就立刻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眼镜被我弟拿走了。
这意味着什么,不难猜测。
据说那天晚上,“我”精神百倍地闹了整晚,把会馆里的人集邮一样地打了个遍。
请问有人回收不要的弟弟吗?我这里可以免费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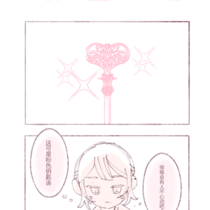

嘿嘿来自一些很久没动笔的人的摸鱼,希望可以表达出我想要的东西(以及没有错别字)xx
在构想里还会有下文(。)如果我不犯懒的话
------------------------------------------------------------
十一月的东京,还未下过雪,天上不见一丝云絮,灰而澄澈的天空无边无际,干爽的气息叫人心情舒畅。
八云慎打开手机,打入一串信息。收件人显示为“小雪”,打字框的正上方摆着一条已读未回的消息。
“今天小雪就要到我家做客了呢,真是期待(^_^)”
这种情况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并不罕见,有时他会对这种冷淡感到些许不满,有时又仿佛接收到一些可爱的害羞情绪,而更多的时候这种小事很快就会被繁重的课业挤到脑后,直到下一次想起“泽城雪”这个人的时候,才会再次想起那条已读不回的消息。
他飞快地打字:“小雪会在学校门口等我吗?”
消息发送,他看着手机屏幕,托住下巴的手指习惯性地挡在脸前,遮住嘴角的笑意。
嗡嗡。
“这种像老妈子一样的事,我才不会做。”
嗡嗡。
“我在这里等你。”
嗡嗡。
一张照片紧跟其后。
他感到心中一动,紧接着双手握住手机,飞快敲击屏幕。
“咖啡馆吗?真有小雪的风格呢。”
“你坐在哪里呢?”
已读,没有回复。
教授适时地走上讲台,开始授课,他直得合上手机,向往常那样安慰自己一句“兴许正在忙呢”。因为他知道,这种小事是很容易搪塞过去的。
“你坐在哪里呢?”
这是一处靠墙的座位,一个近似栅栏的屏风分割了它与大门之间的空间,几串漂亮的雪花装饰和毛玻璃都是很好的掩护,对一些不愿被往来过客频频察觉的好静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泽城雪以比往常更长的时间看着最后那条消息,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是有些不舍地滑走了聊天窗口。
她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这些坏习惯,不过刚来日本时,她也曾痴痴地在SNS上和陌生人聊过一个通宵。可能是因为与人交谈的热情被个把琐事过早消磨,如今与人结缘并维持某种关系对她而言是并不是容易,也并不重要的事情。
更何况八云慎,关于他的种种行为,她都感到十分不解。她想不到对方粘着自己的原因,毕竟如果只是为了享受一些成年人的快乐的话,是不必以这种即将越线却从不真正靠近的距离留在自己身边的。
大部分人将其定义成“追求”,但小雪不相信这个。就算在心里也是这么认为,但她仍旧要说服自己这绝不是追求。或许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场求爱显得不必过于粗俗罢了,和那些吧台桌旁虎视眈眈的男人没有本质区别。
“您的冰美式。”服务员放下杯子。
在之后的时间里,她看了两集电视剧,注意力却总是难以集中,也更快地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可爱的小熊冰块变成了两粒冰渣,软踏踏地躺在杯底。
她的身体也因此冷了下来,将那件轻飘飘的羽绒服披在身上后,她听见了门前铃铛的响动,一个熟悉的脚步走了进来。
走进咖啡馆后八云慎忽得明白了,为什么小雪要把约会的地点选在这里。
他笑着同服务员招呼“我已经有约了。”随后自然地环顾起周围的顾客,慢慢地踱着步,走近了不远处的一块屏风。
他乍一眼发现小雪和平时打扮得很不一样,但细细观察后又发觉似乎不一样的只有那消失的高高的发髻,她把头发散了下来。它们被浅蓝的羽绒服包在下面,只有几绺薄雾般的发丝漏了出来,在兜帽上倔强地挺立着,弯成一个圆圆的光环。
他看见对方微微侧了侧头,却没有看向他。八云慎笑了笑,快步走上前去。
“抱歉,等很久了吧。”他落座在对方身前,将羽绒服脱下放在身旁的椅子上。
小雪抬眼看向他,并没有表情,但眼睛很亮。“也还好,我也猜你会这个点到。”
“这个咖啡馆——我本来以为只是很符合我对小雪的印象而已,现在看来可还真是不止如此。”
“嗯?怎么说?”
他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记得和小雪初遇的那天也是这样,我坐在那家酒吧里,就是从那个角度看向窗外的你的。”他指了指那个方向,对方微微偏过头去,嘴角悄悄勾起。
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对于别人的提问,她总是给出回答却又不愿承认。
“您的热水。”服务员放下杯子和菜单。
“不过那天雪下的很大,不像今天那么晴朗,真是幸运,可以和小雪去到很多地方了。”
“你想去什么地方?”
“嗯……既然碰头的地点是小雪定的,那不如接下来的行程也都交给你吧。”
“我想你跟别的女孩子出去玩时,一定不会把这么费脑筋的事交给她们去做吧。”
“这当然是因人而异的,像小雪这么有主见的话,我也不介意被牵着鼻子跑。”
“我很有主见吗?”
“哈哈哈……毕竟你选的这个地方可是不管离我的学校还是住处都超级不顺路的位置呢。”
“原来你觉得这是有主见啊,那说不准是我故意整你呢?”
“那就不要停下,继续这么做吧。”八云慎拖着脸颊,微笑地看向对方。
“您的冰美式。”
小熊冰块在杯中咕噜噜地打转,最后停在了面向栅栏的位置。不过从它的设计考虑的话,那两只透明的眼睛却是一只看着八云慎,一只看着泽城雪的。
小雪脸上终于露出了明快的笑容,她把咖啡倒进装着冰块的被子里,用小勺搅动着,小熊再次旋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