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诸多神秘千古流传,
神明与怪物皆非儿戏,
人与其历史编织万年。
亚当的子孙与莉莉丝的孩子,
孰是孰非早已无法分辨,
有多少人能放下过往的偏见与仇恨?
但也唯有放下过往,缔结约定。
千百年的怨恨痴缠,
在一夕一夜间断结。
人们从此不再知晓那异常,
但神秘依在,并将永远在。
那亚当的聪慧子孙们,
与众多的怪异结为同盟,
一同化作人类的坚盾,
——名为“埃癸斯”。
正因如此,世界的齿轮今日也正常转动。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世界的半架空企划,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并无法完美还原欧洲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你又旷工了?”
“哪儿能啊,我这是早早干完提前下班。”
八月的爱丁堡夏花极为灿烂地开放着,争奇斗艳般,将四处都装点地五彩斑斓。阳光和丽,正是出门的好天气,街上熙熙攘攘,走在路上,很容易就能听到几句随风飘来的笑语。温格转身避开两个迎面闯来的嬉戏打闹的小孩,弯弯眼睛回电话那头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为自己辩驳。
对面笑了笑,气音从听筒里漏出来,让他嘴角也情不自禁跟着扬了扬。
“那好好享受你的下班时间吧,”对面就差把你看我信吗写到他脸上了,还不忘提醒他,“小心被抓到了。”
“怎么会呢——”温格拖长了音调冲着对面摇头晃脑,“他们哪一次抓到我过——唉不对,”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挺直了背,沿着石头路向前的脚步也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秋果你这是在套路我?”语气颇有点委屈的意思。
“嗯哼,那就要我们伟大的执行司成员猜喽。”唐秋果的声音清爽干净,跟春风掠过窗铎一般毫无杂质,笑起来眉眼弯弯,脸上还有个小酒窝,可甜可甜。温格没打视频看不着她,却能很轻易地想到秋果此时的模样。这个时间的秋果往往不是在舞蹈室就是在回宿舍的路上,她安静地收拾好练习用的道具,关上舞蹈室的灯,然后看着沉寂的夜幕就着偌大的落地窗倾泻在教学楼顶层的舞蹈室里。温格年假的时候曾经去过几次秋果的学校,见过那个她几乎每天都与之为伴的舞蹈室,知道那里占了几乎一整面墙的镜子、光滑的木质把杆、堆满储物间的道具、笨重的蓝牙音箱,以及夕阳下旖丽的黄昏和夜色中漫天的星河。秋果有时候锁了门就走,有时候回头看看,也不开灯,就站在那里看漆黑一片的空教室,看从窗户中透进来的湛蓝色的天光。
唐秋果学的是古典舞,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一直到大学读了这个专业。温格五岁学的钢琴,两人又年纪相仿,因而这样说来,秋果学舞的时间比温格学琴还要长那么一些。温格很喜欢看秋果跳舞,第一次跟她见面就是在舞台上,说她的摄人心魂也许夸张了点,但一句令人神往却非言过其实。后来和秋果熟了之后,温格就更常见她跳舞。那会儿他俩上高中,一个音乐生一个舞蹈生,都是文艺汇演的常客,课余时间排节目更是少不了的。学校音乐教室本来就少,又要分配给学生上课,又要匀出给特长生排练的空间,一来二去两人就挤到了一个教室。温格用教室前面的钢琴,秋果用教室后面的舞蹈镜,端得是明明白白。温格慵懒,有时候练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坐在琴凳上,安静地看秋果跳,看她缓缓地下腰,又行云流水、状无声息地翻了个身。她细长好看的手随着音乐的鼓点律动,而这鼓点也一下一下地敲进了温格的心里。
都说日久天长就会成为习惯,而温格看着看着也变成了嗜好。他从琴凳上挪下来,调音箱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这些习惯养成了以后就没再变过,纵是后来忙碌,称得上一句聚少离多,一旦他们在一起,就还是那个十六七岁的样子。秋果站在舞蹈室的中间,对着镜子,而温格坐在舞蹈室靠墙的椅子边,守着那个笨重的音箱,一声清脆的响指,音箱顶上的唱片就呼呼转,摇出一首穿林打叶,晃上半道圆月疏桐。
想到这些,温格就忍不住弯着眼睛笑,周遭万花灿烂,可到底也比不上对面的人。他被秋果一句话哄住,把被套路的事也抛到一边儿,照旧笑着问她:你还没回去?
准备回了。秋果回答他,又问:那么温格先生这是准备去哪儿?
“爱丁堡艺穗节,大小姐要不要看看?”温格把视频打开了,秋果带着笑靥的脸很快出现在镜头前,他把摄像头转了转,让镜头朝着周围,欧式城堡、长廊、绚烂的花卉以及偌大的露天舞台很快挤满了屏幕。他就这样连着耳机,絮絮叨叨地讲:“一年一度的艺穗节,音乐戏剧舞蹈马戏什么都有……十岁前几乎每年都会被带着来,可惜离开苏格兰后就没了这回事。狐狸哥,啊,就是卢卡,你还没见过他吧,贝克街侦探联盟的家伙——他前些日子刚来过,说看了一场有趣的表演,体验感还不错,我就来故地重游一回了。”
他有点遗憾:“可惜你今年回校太早了,要是留到八月,就有机会碰上了。”他从小贩那里买了一串果串,在镜头前晃晃,向她眨了眨眼,“我觉得你会喜欢这里的。”
“那就希望明年的温格不要这么忙咯?”秋果笑起来,“后面是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吗,我听到那句台词了。”
“啊莎翁,”温格看了眼舞台上穿着精灵服的一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经典老番了。”
“你约了下一场?”
“还是秋果了解我。”温格咬下串串上的草莓,嘟囔了句好甜,得到了秋果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冲她眨眨眼,看她很自如地穿过教学楼的连廊,走到了校道上。“是《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他说,“还记得吗,叶先生曾经向我们盛赞过的那部歌剧。”
“当然。”说话间秋果已经穿过了林荫道,她头上的发带随着她的动作一扬一扬地,看得温格有些心痒,恨不得伸出手去碰一碰,“所以是蓄谋已久?”秋果一语中的,笑弯了眼睛。
“是呀,我的大小姐。”温格利落地认,开心的神色里又露出点得意的神情。这下秋果怎么着都能想象温格使了些什么法子才在埃癸斯得到了近半天的假期了。
“维吉尔和斐瑞应该没空陪你一起去吧?”她问。
“是啊,他俩忙着呢。”温格一想到他的两个发小就直叹气,一个月前,因为要处理几个家族的内部大事,维吉尔和斐瑞就跟他们的父辈一起飞到了德国,至今未归,在联络中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总而言之,他们错过了这场爱丁堡的盛会。“不过他俩指不定也不想我呢,尤其是维吉尔那小子,”他不走心地翻个白眼,“他可对和斐斐独处的时间珍惜得紧。”
“不过我也是请了朋友一起来的。”末了温格又说。他放心地看着秋果走进宿舍楼,最终停在了房间前,抬手敲了敲门。
秋果早猜到了,这小子看演出都不肯一个人去看的,铁定会拉个家伙和他一起去,他的两个发小都是惯常的冤种,进了埃癸斯,跟他相熟的自然也少不了,对此全是见怪不怪。她不问,因为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他们都不是急于一时的人,姑且惯着来日方长。中国到英国,四千八百三十四英里,八个小时的时差,那头还烈日当空,这头已经是满天星子了。于是她打个哈欠,朦胧双眼睛,跟他说了晚安。
温格的嘴角扬着,跟秋果通话让他心情不能更好。他收起手机,望了望人群的尽头,恰好看到了一撮熟悉的白毛穿过人群,向着他站着的雕塑来。于是他难得提起精神,向他招了招手,成功收获了一个有些震惊的表情。
狐狸哥:事出反常必有妖,无事殷情非奸即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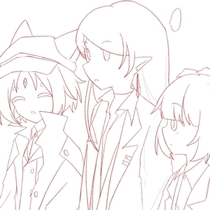



※三千字写了三个星期,好恨加班,但我还是要建设一下肖珮
※再次谢谢约书亚
※因为剧情实在是安排不上所以就只能提一句伊森和甘农啊啊啊我给你们跪下道歉…………
肖恩·沃森本来是去白立方画廊看展的。
今天是周末,没有加班,更没有紧急召唤,他便临时决定趁展览还未结束时去逛一逛。自旺兹沃思镇 (Wandsworth Town) 登车,北上的铁路线摇摇晃晃地载人出行。可说不清是何原因,青年并没有在克拉珀姆站下车,而是又坐了两站,把自己送到了沃克斯霍尔。
既然已经到这里了,何不继续换乘呢?于是他又登上维多利亚线,在牛津圆环 (Oxford Circus) 下车。风景并没有多大变化,总归是在市区内,阴沉的天配上阴沉的脸,伦敦惯常的风景线。再走几步路,就可搭乘88路,在切斯特大门 (Chester Gate) 下车。
左折右拐一番,把什么实验室什么咖啡厅都甩在身后,直到横跨一条长街,再踏进一片绿荫,目的地总算近在眼前,并以一片鸟语花香迎接这个笔直走来的年轻人。
“玛丽皇后玫瑰园”。
八月,酷暑依旧,就连往日争奇斗艳的玫瑰花,此刻看起来也有些蔫答答的。据说这座伦敦最大的玫瑰园里种了足有三万株玫瑰,不同的品种还有不一样的浪漫名字。环形小径两旁花草繁茂,喷泉立于正中,正不断抛洒出难得的清凉——然而这一切都与肖恩·沃森无关,他来,只为证实一些猜想,而这猜想在明晰之前,忽被眼前的景象分散作一团雾。
地球上的生物皆有其纲目属,异种也不例外。虽说比不上“科学分类法”那样明确,大抵上也有个划分。
比如此时此刻,他的面前就有一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扭着细茎,摆着绿叶,以普通植物无法做到的姿势“胡乱舞动”。这就是“卓德”,即树精花精一类的统称。这朵玫瑰花似乎无法变形,只能一边努力摆动,一边把沉甸甸的花朵往旁边倾斜,看似想“分享”,又苦于说不出人类的语言。肖恩顺着方向转头,映入眼帘的是足有一人高的尖形“草柱”,显然在这玫瑰园里是一类景观装饰,除此之外便只剩稀稀拉拉的人声……等等,人声里混杂了一阵极有规律的闷响:刷,刷,刷,哗啦,刷,刷……
他凝神细看,随即了然于胸,叹了口气。
冠以皇后之名的玫瑰园本就是易受窃之地,更何况这里还生长着无数卓德,他们的本体可是极佳的附魔材料,在黑市上向来都是抢手货。
解开纽扣,捋起袖口,确保证件随时能掏出来,然后,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上去。他盯准了那个躲在“草柱”后,挖土挖得头也不抬的“小偷”,脑内迅速规划出了一套方案。
“你——”
“先生你好,我怀疑你正在盗窃玫瑰园里的玫瑰花,请你立刻放下工具,随我走一趟。”
人还未走近,台词却被抢了个正着。
肖恩·沃森止步,看着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灰发青年熟练地掏出证件,“AIGIS”一词连同下面的姓名一齐闪过视线。这名青年——约书亚·阿莱斯特·休斯,样貌秀气,头发稍乱,不知为何风尘仆仆,一手拿着眼熟的证件,另一手拎着一件外套,见肖恩愕然,更是眯眼一笑。
花园噤声一秒,铲子落地时“咣当”一响,惊得玫瑰花们纷纷拿叶子遮住眼睛。小偷顿时慌不择路,抱着怀里的黑包袱就向旁奔逃。约书亚·休斯“哦”了一声,手朝背后伸去,但还未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肖恩便抢先一步,脚下使绊,抓住小偷胳膊向后一折,只听“嗷”的一声惨叫,小偷的包袱便滚落一边,露出里面的内容:几朵奄奄一息的玫瑰花卓德。
证据确凿。
“身手不错。”约书亚吹了声口哨,适时递来一副手铐,完美解决了肖恩“出门没看黄历”的燃眉之急。
咔!
“盗窃罪。你被捕了。”
肖恩·沃森亮出自己的证件,毫不留情地宣告道。
闻言,匍匐在地的小偷更是一通挣扎。
“放,放开我!这里那么多花,我只不过是挖几朵走,再种新的不就是了,有必要抓我吗?苏格兰场就是这么对待普通市民的?!”
迅速交换眼神,约书亚·休斯蹲下身,笑眯眯地指着地上的花说:
“既然是‘挖’花,那你为什么刚才要跑呢?行,先不提这个,先生,你知道你挖的都是什么品种吗?喏,这可是不列颠特有的……”
趁约书亚吸引住小偷的注意力,肖恩·沃森朝一旁化形为人的玫瑰花卓德使了个眼色,示意这位管家扮相的花精上前来。而这位管家卓德显然极度愤怒,看见小偷劈头便是指责:
“是他,就是他,偷花贼!这几只卓德都还小啊,被人挖出来就再也回不去土壤了,只能等着枯死……我这玫瑰园每隔十几年才会诞生一只卓德,他可倒好,一边偷还一边扬言要卖到黑市去,我,我势单力薄,又阻止不了……”
“谁说我要卖到黑市上了?!就这几只能卖几个钱啊,都不够我塞牙缝——啊……”
管家卓德话还没完,小偷就扯着嗓子大喊,面红耳赤地反驳到一半,才反应过来不对劲,嘴巴张张合合几次后,终究垂头丧气地不再说话了。
“行了,有什么话等到了地方再说吧。最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不然咱们‘苏格兰场’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把小偷从地上提溜起来,约书亚·休斯和肖恩·沃森最后交换了证件。方才没看清,原来还是执行司的同事。对他表示感谢后,肖恩目送他抓着小偷离开了玫瑰园(沿途收获了一众围观视线),自己则转身,继续证实刚才的猜想。
“你是这里的管家?”他问。
这个化作人形的玫瑰卓德从外貌看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不知为何穿了一身低调的礼服,站姿也极为恭敬,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管家”。他微微鞠躬,收起刚才那副着急忙慌的模样,语含感激地回答:
“正是。鄙人乃这座玫瑰园现存最年长的卓德,负责关照并培养‘后辈’。”
“原来如此。”尽管卓德之间并没有类似义务,不过肖恩·沃森没有强调这点,“那么,我可以咨询两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您和方才那位离去的先生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必定知无不言。”
“……好,”青年不适应地清了清嗓子,“我要问的问题,事关近期的一桩‘魔女’谋杀案。”
在常人的世界里,“女巫” (Witches) 一词仅漂浮于对女性的形容以及历史书中,只有少数人才知道,世界上真有“魔女”(Enchantress)。这支女性种族由始祖莉莉丝繁衍而来,长生不老,神秘强大。在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之中,埃癸斯亦曾与魔女敌对,后来签订和平条约,才因此慢慢定型,演变为现在的格局。
当然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和肖恩·沃森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并没有关系,不过从别人口中听说的“魔女谋杀案”——八月七日清晨,一具魔女尸体被人发现于白教堂区,且尸体被取走了部分器官——这才是最令他好奇的。
但凡具备超自然方面的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魔女体内的器官是稀有的附魔材料,虽没有用卓德附魔的成功率高,但贵在稀少,且可用于制作猎魔武器。
肖恩·沃森极少见到魔女。与埃癸斯达成合作的魔女统称为“夜目”,偶尔会现身于公司内部。即便如此,他依然很少亲眼看见。听说遇害魔女“伊丽莎白·桑德伦斯”生前喜爱音乐与艺术,他本打算去画廊看展的同时碰碰运气,但中途转念心想,或许玫瑰园里的卓德会更了解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才来到这里。
然而,在肖恩表明来意后,管家卓德摇了摇头道:“很抱歉,我们与这位魔女不熟。她的确时常会来这里看看花,但也仅限如此。”
不意外。肖恩心想,本来也只是兴趣使然才来,要真能打听出什么,那才是不正常。正当他想回复时,又听管家若有所思地说:
“不过,昨天有一位血族先生与一位幽灵先生也曾先后来打听过类似问题。”
肖恩微微皱眉。
目前知道这桩案子的人应该还不多,假设把范围缩小到埃癸斯内部,那么幽灵……埃癸斯里的幽灵可不少,血族……青年的脑内浮现出一张打过几次照面的同事的脸,听说那是位老血族。按下念头,他说:“说不定过会儿那位把小偷缉拿走的先生也会过来问你这个问题。”
管家“啊”了一声,歉疚道:“哎哟,这可真是。瞧瞧这不凑巧的,就像伦敦反常的天气,真让花难捱。”
花难不难捱不知道,反正人是挺难捱的。青年摇摇头示意没关系,正准备走,却被管家招呼到了一旁的阴凉地。
“您看,这里长的有普通玫瑰花还有卓德,虽说品种相同,但因为今年伦敦的天气实在是过于反常,这花开得倒不如往常好了……”
“然后呢?”
听见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女人好奇地侧头看他,问道。
“然后,”肖恩·沃森想了想,“然后他就‘伦敦天气对植物的影响’这个主题讲到六点,结果画展关门了,我就没过去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他讲到六点你就听到六点吗?没看出来你这么老实呀,肖恩·沃森先生。”
“他讲的内容确实很有意思,天气因素不但影响普通玫瑰的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卓德的成长——”见她半惊讶半无奈,他清了清嗓子,说,“总而言之,这就是你告诉我的这起‘魔女谋杀案’的调查结果了,不知道这样你是否满意呢,珮洛菈·司切尔小姐?”
“当然满意了,能请到灾害司第一大忙人为我调查份外的谋杀案,我可不敢有怨言,”放下茶杯,手背支起下巴,珮洛菈·司切尔用那双青绿色的眼仁儿轻易捉住他,“不过,我猜你还没有忘记接下来该做什么,对不对?”
他喉头一紧。
“是……继续去画廊帮你再调查?”
不。她不生气,缓缓摇头道,当然不是了,亲爱的。
当然不是。她把这四个字咬在唇齿间,极轻极细,却叫他再也无法逃避。
谋杀、魔女、案件,一切尚未得解或将来也不会有解的谜团,其实都比不过眼前的她。
把一张票放进他手心,柔软的指腹刻意停留片刻。珮洛菈眨眨眼,“这,”并强调地一顿,“才是头等大事。”
那是一张仅限一晚的通行证,带他暂时摆脱整个非人类世界,尽情投向阿芙洛狄忒的怀抱。
肖恩·沃森想起了很多事。包括在管家卓德讲解的中途,那位来自执行司的约书亚·休斯折返到玫瑰园里,意欲寻求关于魔女的答案。包括在讲解完毕后,管家卓德欣然摘下一朵普通玫瑰,当做他听完这场长达三小时的“讲座”的谢礼。
而那朵玫瑰——此刻正静静站在这张两人对坐的桌面上。
珮洛菈起身。在离开救助中心前,她再一次瞥向桌上那个从未出现过的花瓶,以及瓶中那朵微垂的香槟色玫瑰。
老旧的时钟从客厅传来,遥响在格尔森的卧房。让人从书中黄金屋顿时清醒,返回到现实,他正读着一本以精神论为主的文学小说集,虽然小众但里面却包涵许多热门书本里无法看到的大胆词汇和想法。
其中有一篇文章里的话吸引了格尔森的注意:
“信仰的大同对不同人的群体来说是否真的影响至深。”
正当格尔森专注于此的时候,突然一道声音将他再一次……拉进真正的现实。他摇了摇头,转头看向坐在自己身侧的洛汀,对方半抬起了手悬在空中,想是刚准备唤他醒来。
好吧,看来他昨晚睡眠质量确实不行,果然不应该熬夜将工作和没看完的文章在同个晚上一起收拾了。
“……格尔森先生,需要休息一下吗?”
“没事的,洛汀小姐,我们下去吧。”
格尔森起身与洛汀先后下了车,二人打算先去解决午餐的问题,随后就去对邪教进行调查。
此时他们身处在汉堡,作为德国第二大城市的同时也被誉为“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格尔森一到这里就看到了部分正在通行的船只,他以前只从书籍和电视上了解过,只是今天才亲自来过了。
风吹着水平面涟漪不止,德国九月份的天气温度并不能算得上好,他里面穿的是一款便于出行的装扮,外面还套上了棕色的风衣。当然这并不是他自己选的衣服。
他和洛汀穿的同样是棕色风衣,两人的衣服颜色搭配怎么看都有些不一样的味道,格尔森想着如果拉芙娜在的话肯定会给他拍个照然后意味深长的拉长声音调侃自己。
格尔森和洛汀正考虑着去哪家餐厅时,不远处传来十分嘈杂的声音,其中夹杂了一些奇怪的叫喊。两人的目光一同朝向那边看了过去后,暂时搁置吃饭的心思,前往源头。
当他们赶到那里时映入眼帘的景象倒也算不上多么恐怖,只是多少有些说不上来的混乱。人数很多,这群人的精神格外亢奋,有的甚至在互相打架斗殴,有些路人在边上没有靠近。
“邪教徒么……”
“格尔森先生……那里面似乎有人在地上……”
格尔森目光看过去后发现地面上确实有个人被打着,不过会不会也太眼熟了?
洛汀跟格尔森说了一声之后便参与进去拉架,试图让情况稳定下来些。格尔森便观察着周边情况。
(那不是,克莱尔么,怎么臀部上还有个叉子……)
格尔森这么想着,他甚至还看到群架里面还有位女士的身影。包括那边有个外面桌子被掀翻了的店子。
(那位小姐似乎有些眼熟……似乎是颜小姐?)
从刚才过来格尔森就发现了他们打架斗殴所在的地方旁边就有个以海上航线为主题的餐馆。要说为什么,那地上有很多残杂剩饭。
“……海员杂烩?”他没有品尝过这道菜式,倒不是反感,只是格尔森实在不喜欢这道菜的咸味程度。正思考着便发现那边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他看向那边,瞪大了眼发现他们还抓了一个刚才参与了打架斗殴的邪教徒。
在四人对邪教徒进行盘问过后得到了一些信息:他们刚吃过海员杂烩,这道菜在德国甚至有个独特的传闻。
“只要你吃完一整盘这个,就会变得天不怕地不怕的?还异常勇敢?”
这种东西简直和哄小孩吃饭一样,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个?
“颜小姐也是来调查这些事情的么?”
格尔森看着有着黑色长发,面带笑容的温和女性。
“我本来正在那家餐厅坐下,不过还没吃几口东西,桌子就被另一桌人掀翻了,真够奇特的对吧。”
美丽的女士虽然面带着笑容但不知道为何可以感受到她的一些恼怒,这让格尔森想起刚刚她在人群里很利落帅气的动作。
四人同时分享了克莱尔手机里记录下来的他们发起争执前的一些人物场景和那些菜品的照片。但是,你确实不能指望2g彩屏老旧手机的清晰度有多好,但至少能看出个大概。
得知其他二人还要去进行调查的事情后与他们打了招呼便分开来。
四人告别之后。
格尔森联想到那群邪教徒的异常,在这里吃饭可能也不会再有胃口,于是他果断提议两人离开这里。
“洛汀小姐,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解决饱腹问题吧”
“好的,格尔森先生……”
两人离开前格尔森看了一眼餐厅服务员从地上,餐盘中清理起来的生牛肉,顿时有些许反胃和不适。
他肯定以后也不会想吃这道菜……
今晚自己肯定会增加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