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这场所谓的「游戏」让心空荡荡的,往日的自信、希望被无尽的惶恐取而代之。一直抱着凌驾一切态度的我无疑被打了当头一棒。
我倚在床头上,什么都不想做,仿佛一下子失去目标的壮志凌云之人。
就在我朦胧间快要睡着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哪位?”我走到门前,问道。
“海藤白辑!十七君现在有空吗!”门对侧的海藤君似乎很激动。
“啊……”我打开门,“海藤君有什么……”
话未说完,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便把我向后推,最后摔在墙上。迟了一些,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有液体在胃部翻滚,涌向咽喉。
“咳咳咳……”我剧烈地咳嗽着,手扶墙壁勉强站起来。“海……藤……你……”
……为什么我会被莫名其妙打了一拳啊?!
我努力回想着自己是不是做过惹怒别人的事,但来不及回忆,海藤君就大摇大摆地踏进我的房间冲着腹部打了第二拳。
“咳啊……”将近一天没有吃东西,胃部收到强烈刺激的我只是吐了些酸水,我跌靠在墙角,痛苦地捂着腹部。
——怎么回事?!难道我……
我努力抬起头,海藤君正露出一副兴致勃勃的表情,看他的动作,似乎离第三拳不远了。
——我的事被……?!
我惊恐地看着对方,腹部的强烈疼痛迅速辐射到四肢,平日就缺少体育锻炼的我此刻更是手无缚鸡之力,更不要说站起来打回对方一拳了。
“海藤……君……你做……什么……”在他把我打晕之前至少也要问个原因——屈服于自己体质的我这样想道。
“打架呀!”海藤君兴奋地说着的同时,对着我的脸打下第三拳。
“十七君的脸——真是太可爱了——让人忍不住打下去呢。”
——你是变态吗?!
被给予了可观的动能,惯性带着我的身体一下子撞到床边。头部与尖角剧烈碰撞后,温热带着铁锈味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啊啊,我还醒着……
我的脑内只剩下这一句话。
——我还醒着,醒着呢……
“十七君?!你没事吧?!”海藤君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么过分的事,用力摇着我。
“我……我还有意识……我看到……祖国了……红色的……海洋……无产阶级……伟大的……”
“十七君?!”海藤君似乎被我故意说的胡言乱语吓到,胡乱从他的口袋里翻出OK绷,“别担心我会负责的!”
“海藤君……”我痛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话。
“怎么了十七君?”
“能不能先把我扶到床上……再继续蜷着我的胃就……”
“我知道了!”说着,海藤君便元气满满地把我抱到床上,元气满满地给我贴上并不规整的OK绷,甚至连止痛药都准备好了。
——合着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吗?!
“打架果然是享受青春啊——”他擦擦额头的汗水,感慨道。
“享受个鬼啊!还有这哪里是打架明明只有我一人被揍这不是欺凌是什么?!”我严正抗议。
“欺倒是有啦,凌的话……十七君也想试试嘛?”海藤君看着靠着床板虚弱的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你想成为阶级敌人吗?”我瞪了他一眼。
“开玩笑啦开玩笑,”海藤君摊开手笑着说,“果然和十七君打过架整个人都超好了呢。”
“抱歉我一点都不好——”我按着依旧在翻滚的胃几乎要哭出来。“海藤君你出去吧让我歇一会儿……拜托了……”
“那么我就不打扰十七君了,”海藤君走到门口挥手,“下次还想再打一架啊!”
“再打我就准备好斧子了。”我对已经关上的门恶狠狠地说。
3
房间里总算清净下来,但我的胃部依旧火辣辣地灼烧着。整个身体正受着物理疼痛与饥饿的煎熬。我躺了一会儿,决定出去吃点东西。
——但愿这幅样子不会让别人看见。
我一瘸一拐地推开门,走向休息室。
——尤其是……
“十君?!你没事吧?!”背后突然传来女孩子的声音,我一怔。
——尤其是黄泉……同学……
糟糕了。不愧是「不幸」,这份不幸让我遇见了现在绝对不希望遇见的人。
“我……没事,不用担心啦就是有点小意外。”为了不让黄泉同学担心自责,我强忍疼痛笑着说。
——黄泉同学,千万不要再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了……
“不可能……十君你伤得这么严重,一定又是因为我……我……”黄泉同学悲伤地低下头,再次后退几步,与我保持三米的距离。
“真的,真的啦!别人做什么事哪能是黄泉同学能控制的!管他是不幸还是好运,什么都阻碍不了人心不是嘛!”我扶着墙,一步步走近。只有伤过一次才体会到战士生死边缘的艰难,我现在总算体会到这一点。
“十君,别走了!你现在……”黄泉同学担心地看着我,她似乎想伸出手扶我一把,却又犹豫着将手缩了回去。
我这次依然主动伸出手,“吶……如果黄泉同学无论如何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的话——”
“十君……?”黄泉同学终于上前扶住摇摇晃晃的我,把我的手搭到她柔弱的肩上。
“——扶我去休息室,帮我煮份咖喱好不好?”
“十、十君你确定要吃我做的饭吗?”黄泉同学脸上写着“吃了我做的东西会更不幸”的表情,为难地劝我。
“没办法呀……”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不在意云云,黄泉同学恐怕不会接受,我便扯出之前被源调侃嘲笑的理由:“我……连煤气灶都不会开啊。”
吃过黄泉同学热腾腾的咖喱——当然也是把胡萝卜全部挑出来的——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活了过来。
“谢谢你啦,黄泉同学。”
黄泉同学少有地换下那副扑克脸,微微笑着,“我才是要谢谢十君啊,十君对我这么……”说到一半,黄泉同学的眼眶通红,几滴眼泪顺着眼角滑下。
第一次见到女孩子在自己面前哭,我有些慌了神,顾不得还不太听使唤的身体,猛地站起来擦掉她的眼泪。
“别,别哭啊黄泉同学……”
“对不起……十君……我……”黄泉同学的眼泪仿佛决堤的洪水一般,打湿我的衣袂,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身体抢先于思维行动,我抱住了黄泉同学。
“没事的……我不会再让浊雨一个人了,我保证。”
浊雨一瞬间露出安心的表情,但下一刻,一直以来的本能使她推开我后退数步。
“十、十君……”浊雨低着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在地面绽开水花,“我……”
浊雨继续后退着,随后跑出休息室。我愣在原地,早已忘记身体的疼痛。
——到底,到底怎样才能让她走出自己禁锢自己的不幸啊……
我向着休息室入口迈出几步,无力的虚脱感使我踉跄着失去平衡。我正做好撞向地面的准备时,却倒在一个人的怀里。
对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我扶到休息室的床上,然后拿出一块板子写起来。
「没事吧?」
泽城哥竖起板子让我看清上面的文字。
“嗯……抱歉让你担心了。”
「刚才黄泉路好像哭着跑出去了,发生什么了?」
“……大概是我的错吧。”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浊雨一定很困扰吧。我自责地想。
「年轻真好。」
泽城哥带着羡慕写道。
“泽城哥……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十七你还太小了。」
“所、所以说不是那样的啊!”我胡乱摇着手,拼命解释,但对方似乎认为那只是我害羞而已。
「加油!」
写下这两个字,泽城哥便把剩下的咖喱盛到饭盒中带走了。
我叹气,看来自己因为身体的问题搞砸了不少事,改天一定要找那个罪魁祸首算账才行。
勉勉强强把自己撑死来,我打算先回房间休息。出了休息室的门,我却看到泽城哥倒在了那里。
“泽城哥?!”我拼命摇着他,但对方雷打不动地死死趴在地上。试了试发现他还有呼吸,我松了口气,暂时无视自己快要散架的身体,深一步浅一步好不容易把他拖回房间。
——是有某种疾病吗?休克症?!
“这到底算什么啊,一连串的事。”我筋疲力竭,瘫坐在泽城哥的床下。
意识逐渐远去,一切都仿佛笼罩着浓雾一般,模糊而恍惚。
远远地,仿佛听见有谁在说话,声音隔着一层屏障,只能依稀辨别出少量词语。
——“这家伙……什么……”
——“倒下……扶过……”
——“……觉得……学生……杀戮……”
——“……继续……保持……”
“……?!”不知过了多久,再次醒来,我发现自己回到了我的房间。我坐起来,思考着方才的对话是否是真实。
尽管只听到了少量的对话,但如果将事实串联起来那将是——
我……
我竟然……
身体的疼痛减轻很多,我翻出带来的笔记本,写下文字。
我得做些什么。
我必须要做些什么。
1
学级裁判结束之后,我没有片刻停留地返回自己的房间。嗡嗡作响的大脑一下子将我拉入虚无。
突然出现的尸体,调查,学级裁判,自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确,的确没有人夺走他人的生命,但是小丑他自己却……
为什么?
我仰面倒在床上,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自杀,然后伪装成他杀,随后言论被误导,大家险些搭上性命。
该死,如果能在那之前和他说上话就好了。或许如果能知道他在想什么的话,现在也能理解他了吧——那个看上去很孤独的人。
最后能够推理出真相,多亏了海藤君和源——没想到源那家伙竟然这么厉害。
——源……
我一直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对方绝非善类,就像言哥说的一样。谁知道那种平时装傻卖呆实际上一直在观察分析别人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虽然我也是大差不离。
啧,说到底还是同性相斥。不过对方似乎表现着对我很感兴趣的样子——他完完全全没有在乎我的敌意。或许他知道我因为个人目的不会做得罪别人的事。
就像昨天那样。
马上就到夜晚时间,大部分的学生早早回到屋子,无事可做的我便找出第一天早上费尽千辛万苦才买到的报纸看了起来。
已经和外界断绝联系的第三天,即便是早已没有时效性的报纸对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不过如果有出去的那一天,我这个算不上政治家的政治家也一定要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都补习一遍才行。
这样想着,我先将报纸翻到国际新闻——那里说不定有我家乡的消息。
会是哪个领导人又出访了吗?我这样想着,但映入眼帘的却是——
「中国■■遭遇特大群发自然灾害」
怎么可能——受灾地正是我祖父母居住的地方——我机械一般地读完触目惊心的伤亡损失数字,忧虑煎熬的心情将大脑冲击得一片空白。
——我怎么还能若无其事地待在这里?!
我把手中的报纸狠狠摔到墙上,无视宣告夜晚时间的广播,撞开门狂奔出去。
——出去……让我出去……
已经顾不得被别人看见我这样慌张样子的后果,我疯狂敲打着紧闭的出入口。夜晚无法射入月光的漆黑与无声的寂静渐渐拉扯着我,将我与心中挂念的家乡活生生地剥离。
我蹲坐在门下,埋头于两膝间。眼眶灼烧般地疼痛着,心灰意冷的我却哭不出来。
“……你没事吧?”不知是谁房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随后黑暗中人影小心翼翼地靠过来。
糟了……被别人看到自己这幅样子……我往最好的方面想着,轻轻问了声:“言哥?”
“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损失最小的人的是言雨吗?”对方小声喃喃道,“很遗憾,我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个陌生人。源夏树,我是个心理医生。”
听到对方的名字,我下意识猛地起身后退一步,想到有些不妥,我只好维持站立。
“……晚上好。”我淡淡地搭了一句。
“没关系,你没必要对我这样防备。”借着昏暗的光,我看到源脸上善意却让我毛骨悚然的笑容。“就这样害怕在我面前暴露弱点吗?还是说,唯独不能让我抓住?”
显而易见地,对方将我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变化全部翻译成了心里活动。可怕,这样的人非常可怕,在他面前我藏不住任何秘密,我的目的、我的一切都会被他知晓。
“找不到和我相处的方式吗?”源顿了顿,“没关系,十君用十君本来的自己和我交流就好。”
“都被你看穿了我也就不套伪装了,”既然心理战敌不过对方,我只好退步,“刚才的事,你不会说的吧?”
“当然,”源向我伸出左手,“不愧是懂得变通的政治家。”
“你不拿这说事的话我倒还能保持最基本的友好。”
“对我就不像对其他人一样装出一副温和的样子博得信任呢,不过这样的选择倒是很明智。”
“哼,伪装对你来说跟看笑话差不多吧。”我伸手用劲握了一下,“请多指教。”
“原来政治家的真面目是这样的。”源收回被握得有些发红的手,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
“小看我的话把你打成阶级敌人也没有问题。”我认真地冷笑道。
“那还真是特殊待遇,不胜惶恐。”
我对源无法解读的、似乎是伪装的温和态度有些不耐烦。“还有事吗?没事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想被电视里的人逮到违反校规。”
“嘛十君又在撒谎了,”源继续微笑着说道,“这样淡定的你,肯定发现校规的漏洞了吧?如果因为不想和我说话就盼着赶快回去的话,说实话我有点受伤啊。”
“你想怎样?”
我看着对方略显单薄的身影,心想这不会又是个因为性格而孤独一人的家伙吧。
“你想的没错,”源指指远处的休息室,“一起吃个夜宵如何?”
“没想到你这家伙竟然会做饭。”我恣意地把手搭在椅子的靠背上,哼着歌晃来晃去。
“我看上去是那种生活无能的人吗?”源煮着速食咖喱,回头问道。
“嗯?我只是用家乡的思维而已。”
“政治家,你这副随随便便的样子没问题吗?”
“反正平常根本不可能这样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不试试?”我跳下椅子,从水池里摸出两个盘子。“试了之后,遇到需要以这种方式相处的人也能应对自如了。”
“你觉得我需要用这种不良一样的方式相处?”源接过盘子,借着燃气灶微弱的光源开始盛咖喱。
“呵,你希望换成别的也没问题啊。”我抬起下巴斜视对方,“杂碎,把东西端过来。”
“独裁者大人还是算了吧,我可是好心好意煮了你喜欢的东西啊。”源随手把盘子向我面前一推,拉开椅子坐在对面。
“哦?你倒是蛮清楚的嘛。”
“是啊,我晚上的时候可是看见一位生活残废的大少爷想煮咖喱但死活不会开煤气呀。”源露出报复一般地笑容,扬着语调说道。
“啊啊啊闭嘴说出来太耻了啊啊啊——”我满脸通红,拍案而起,身体伸过半个桌子,“不会又怎么样有谁规定高中生必须会做饭吗!”
“没有是没有啦,你以后想吃我给你做就是。”
“你这家伙……”我低头,尴尬地坐下往口中狂塞咖喱。“……你把胡萝卜挑出来了啊……”
“晚上的时候你不是也把炒面面包里的胡萝卜都挑出来了?不喜欢吃嘛?”
“你这家伙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你啊~”源用手撑着下巴,笑笑说道。
“讨、讨厌啊你。”
“你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闭嘴啊!!!”脸上有种燃烧的热度,我迅速收拾餐具扔进水池。“我、我回去了。”
“嗯?吃好了嘛。那我也回去好了。”源也同样收拾好,跟上我。
“姑且说一声……谢谢款待。”什么都不说觉得不太合适,我勉强挤出一句谢谢。
“那么十君,家人的事也不要太担心。”源在大厅挥挥手,“晚安。”
他怎么知道——?!
源望着意料之中的我的惊讶表情,关上了房门。
看来对这家伙的印象要重新组建了……
我复杂地看了最后一眼大厅,回到房间。
命运总是捉弄人的东西。在这夜晚之后的时间,那名叫落合设的少年便正式给这场游戏拉开了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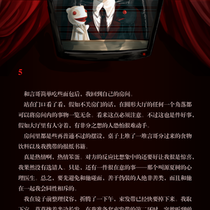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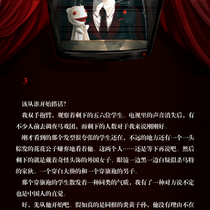





“五十六,你是守夜人吧?”
被关进游乐场的第五日,最后三人聚集在被烧焦的旋转木马前。伴着刺鼻的焦炭味道,Seth叫住了一言不发的五十六。
本已荒废的游乐设施历经一场火雨后更显的惨惨戚戚,而那深处,是早已死亡的斋藤千木。
五十六已经不需要回答。在他沉默的表情中,恰恰存在着存在能凌驾于语言选择的真正雄辩。
五十六的目光停留在面目全非的斋藤身上,长发遮盖住半边脸,许久,他讽刺地说:“原来你是狩猎者啊……苏九真是留了一手好棋。”
“这样啊,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吧?”铃见五十六默许,便拿出卡片,投下五十六。
“是啊,”Seth步步逼来,“自从查出你的身份我无时无刻都在忍耐,现在终于可以把你揪出来了。为了小九我必须赢。”
“为了我这种人忍耐?Seth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为了我这种虚假的人何必啊?”
——我这种人啊,实实在在的没救了。
——正因如此,我这种人做出什么事才都不奇怪吧!杀人也好,欺骗也好,装作事不关己也好,反正是【我这种人】——
五十六扶着额头大肆苦笑。他在他拿到身份卡的那一刻就撒了谎:第一天晚上,他和塞壬亲手杀了苏九;第二天装作惶恐和震惊,在夜晚将明江残忍地分裂开来;第三天晚上杀掉古屋,而在塞壬被揭出身份之后,第四晚放火烧了不断向他挑衅的斋藤。
他早已不觊觎回去,回到他牵肠挂肚的友人身边。他早已没有了资格,在他接到身份卡不得不去杀人的那一刻开始。
“所以说……我这种人早就……”五十六点下投票框上自己的名字,“早就……”
身份卡随着断断续续的温热水珠洛在地上,咔地一声轻响,仿佛为悲痛哀嚎。而它的主人似乎早已接受了命运。
“……回不去了。”
——所以,永纪,凌零,永别了。
一切谎言与虚伪皆是真实。

目睹真正死亡的那一刻,五十六才觉得自己在城巷中经历的打打杀杀根本不值一提。死亡所携的沉痛代价,是那些社会青年靠本能的怒意支配而起的争端无法比拟的。伤痕可以治愈,而逝去的生命却再也无法挽回。
现在,五十六在他十九年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恐惧,以及,沉痛的悲哀。
三十分钟前,他还懒懒散散从睡觉的地方爬起来。
一刻钟前,他还优哉游哉地在颓圮的游乐园中晃荡。
直到五分钟前,他听见了Seth的哀嚎——
随后,他默默看着Siren狠狠摔下手边的医药箱,远远站在一旁。闻讯而来的人们纷纷驻足于一米外的界限,那仿佛是被硬生生分开的两人生死间无法跨越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或许远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加悲痛。
这些突如其来的事变让之前对一切都不在意的五十六动摇。
不久之前,Seth和苏九还卿卿我我地赖在一起,说着让五十六后背发麻的情话;秋月一边叫着五十六大姐姐,一边和整日目中无人,准确来说是目中无猴的古屋吵吵闹闹;有些害怕的小明江被铃安慰着;Siren很贴心地问大家有没有受伤;山崎和斋藤虽然看上去不容易接近,但也和大家说说笑笑的……虽然被带进了奇怪的游乐园,五十六看到他们也便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再过不久大家就能回去了。
那时候,他还盘算着和他的学婊友人以及上了观赏人鱼的船现在还没有联系他的朋友抱怨抱怨。
现在,他忘记了一切。
他茫然地看着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回应。双眼无神,被动接受着,认知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古屋忘我地肆意大笑,仿佛一个孩子得到了心仪已久的玩具。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一旁的斋藤同样兴趣盎然,但不同于近乎疯癫的古屋,他的嘴角有意识地上扬。
一直低着头的Seth脸上写满了怒意,向丝毫对生命消逝没有痛惜之情的二人大吼:“你们够了吗?!给我闭嘴!!”
Siren也同样愠怒地看了看疯狂的二人,转而默默收起他那散落一地的医药品。而斋藤似乎另有打算,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俯身帮助Siren。
“为……为什么会这样……”明江紧紧抓着铃的衣袂,缩在她怀中。
“这都是谁策划的?!告诉我啊啊啊——”秋月和山崎颤抖着,失声痛喊。
“一定,一定要惩罚凶手。”铃拥紧明江,坚定地说。
“一定。”Seth的脸上写满毅然决然的神情,“苏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无论如何,都要凭它……”
五十六深呼吸,闭上眼睛,将自己置于深邃的寂静。
——这样的死亡,真的不想接受啊……
——可是,不做不行了。为了死去的苏九,也为了我们自己,必须,必须把那个罪孽深重的凶手抓出来。
会是谁呢?五十六仔细端详着八位同伴。思考了很久,他最终还是锁定了一直很可疑的那个人。
——死亡,带来悲痛的死亡吗……
——如果死的是我这种人,就没有人会伤心了吧?
——如果我这种人也可以保护大家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吧。
五十六在卡片上输入那个名字,随后,自嘲地苦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