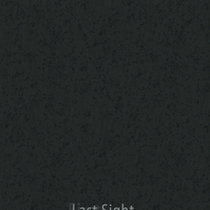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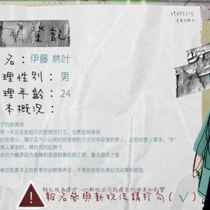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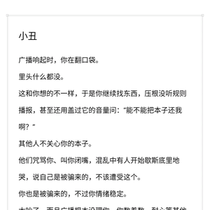


依旧是序章……到企划结束应该能写完吧
*
*
*
《循》
(三)
他让苏拉叫自己“杰克”。
这大概不是个真名,苏拉想,这样的人不会是“杰克”。
这样的,穿着考究、佩戴着许多派不上用场的装饰物、腿脚没有问题却拄着手杖的人。
他们并非并肩前行,巷子很长,但是太窄。他俩的身形能抵上2个半的李尔,男人比苏拉还要高几公分,他的步子比苏拉要大,跟在后头时好几回踢到苏拉的脚跟,像个急于押送小偷的警察。显然他习惯这步速,并且走路时没有低头的习惯。看见苏拉回头,他甚至还颇有礼貌地笑了笑。
啊呀,他该叫“费南德”、“麦迪逊”,或其他什么音节更长更不好记(李尔管这叫“富有意义”)的名字,又或者干脆只告诉他姓氏。
觉得上当受骗了?不不不。
“要是再早两个月,您管自己叫【香烟盒】我都会信以为真。”苏拉嘀咕着耸耸肩。
“我更喜欢雪茄。”男人说,“你要来一支吗?”
“不,谢谢,我试过香烟了。”
“雪茄不是烟。”
“就那样呗。”苏拉耸耸肩。刚学会吐烟圈的时候他是挺喜欢烟的,连气体灌进鼻腔的异样感都能无视,但新鲜劲总是会过去的。
男人也没坚持。他不住往四周看,注意力好像大多放在层层叠叠的涂鸦上,它们从路面生长到潮湿的墙面,有部分像树木般顶破砖瓦延伸到墙顶。
“你要去的赌场就快到了……哦!小心脚下。”苏拉跃过一箱空酒瓶,“这些箱子里可没什么好东西。”
“你打开看过?”
“打开过,也不小心踢翻过。一般都是些碎掉的酒瓶啦、垃圾啦、放过头的腌鱼啦之类的。你没看过吗……也是,你看起来就不会去碰它们。”
他听见男人的笑声。“相信我,我开过的货箱一定比你多。”
苏拉怀疑地看向他,对方却没再多解释,而是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抓了一把路过的风,又在他的注视中突然蹲下身。摘了一只手套去摸地上的泥土——苏拉这才发现这里的地面是湿润的。
可今天没下雨。
“感谢带路。”男人的指尖快速地敲在手杖顶端,他像是知道苏拉在想什么一样地说,“快要下雨了,小朋友。你该回去了。”
“可还得绕过两条巷子才到您说的赌场哪。”苏拉抬起头。现在还是深夜,但无疑天气明朗。月色皎洁,伴随星星和路灯一起闪着光,完全不像有雨云。
可男人说,“我闻见了。所以,我得先去照看我的宝藏。”
巷子里果然藏着好东西!
苏拉做了个“请”的姿势让开道,可他盯着男人的双眼闪闪发亮,一看就没打算走。
“好吧,好吧,它只会出现一小会儿,禁不住耽误。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男人投降似的叹了口气。脸上却挂着快活的笑。“来吧,来见见我的宝藏……人类。”
苏拉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可他当然不会有听力问题。
他确实说了“人类”!
——这是第一次被李尔以外的人看见、并且被当成人类!
苏拉哼起曲子跟在男人背后,踩着他的影子玩儿。
男人则注视着小巷深处。他像听见什么了一样侧过头,而后前行,停止,转了个弯,又停止。
在这之后,飘忽不定的风才将声音送到苏拉耳边——求饶与怒喝。
也许有人受伤了!
苏拉立即加快脚步,可男人的步速和先前相同,牢牢挡在了他前头。
“先生!请让让先生。”苏拉翻着口袋催他。“我们得跑起来了,我听见有人需要帮助!哦我能做些伤口缝合什么的,他们会需要我的。”
“……医生?”男人挑眉。
“李尔说我只能算见习医生。不过我已经学会了消毒、止血和基本缝合……就是几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
“很快就会有。只要您等在这儿。”
等在这儿?
“大部分人不待见幽灵。不过只要您等在这儿,数到300,这问题就不复存在了……您能数到300吧?”
“那我数到300。”苏拉没犹豫太久。
(1,2,3)
男人又绕进一道弯,那个在求饶的声音扯着嗓子叫唤,“杰克先生!!求您帮帮我,杰克先生!”又惶恐,又满是期待。
所以他真是“杰克”啊!苏拉小小地“哇”了一下,不过马上又继续起自己的任务了。
巷子深处。
“晚上好,莱曼先生。”而杰克,他停下脚步,像在散步时遇到友人般客气地躬身,尽管他有看见一只脚正不住踹着对方的啤酒肚,让他西瓜虫一样蜷着身体匍匐在地,没法好好回礼。
“站在那别动!我把他包里的钱分你三成。”正踹着莱曼的那个人体型不算结实,气势倒凶悍。就算知道和脚下的倒霉蛋相熟的人来了也没回头,踢人的动作越发狠。
只用脚踢大概是因他一只捏着酒瓶,一只提着切肉用的厨刀,再没有多的闲暇。
“我要全部。”杰克说。
(31,32,33)
“别做梦!”打劫者爆了句粗口,又狠狠给了莱曼一脚,“反正你去赌场也会输个精光,早点松手给我不好吗?!”
莱曼梦呓般小声道着歉,身上的赘肉因受到挤压而蜷成波浪。
接着,这打劫者又来瞪杰克、不幸的是他的视线只到杰克胸口。
他挥着刀,冲向他。
(78,79,80)
“莱曼先生,我的老朋友,您最近实在消瘦不少。”
“谢谢您,杰克先生,感谢您……”
“看样子,您是来还钱的?”
“是、是是的。我这就去把钱给对接人……”
“别急着走。您看,我是赌场的老板,自然该保护客人。可这是外头,又是私人时间。我得象征性收些报酬。”
“我...”莱曼避开他湛蓝的双眼,虚弱地攥紧皮包。
可杰克压根没看它。
“您想说什么?”他注视着赌徒,抬起手杖、猛地往下一跺。被他踩在脚下的打劫者发出痛嚎——他的手被贯穿了——吓得几只老鼠吱吱叫着跳进阴沟。
(122,123……)
“怎么了?”守在巷口的苏拉吓了一跳,探出半个身体往里看。可杰克梗在他和那两个人之间,他只瞧见了叠在一起的摇晃人影。
“我、我很感激!!我感激您先生!!” 莱曼不知自己正亲口推开说客。他伸长了脖子,从喉咙里逼出的叫声和老鼠差不多尖。
不过苏拉还是听清楚了他在说什么,摸摸鼻子把身子又转了回去——“感激”是个好词,里面的情况一定没问题。
(138,139,140)
“很好。”杰克点点头,“劳驾,帮我擦干净手杖,然后我们再谈正事。”手杖的末端仍卡在打劫者掌心,碎骨和蓬起血肉簇拥着它,让它像一株顶破地面生长的竹。莱曼蹲下的双腿发软,但还是死死瞪着那儿,脸颊上肌肉抽动。他捣了几回才拉出手杖。在那之后也没起身,而是徒劳地蜷缩着、擦着血水。
(179,180,181)
“我要一只眼睛。”一截碎玻片突然抵在他的下眼皮,把他吓出短促的泣音,又被塞进他虚握的拳心。(由于满手是汗,它实质上是被嵌进去的)
然后是一支火机。
“别紧张,莱曼先生...”杰克捻出支雪茄,这次,莱曼立即护着火苗替他点燃了它。
“谢谢。”杰克冲他笑了笑。碎玻片割得莱曼满手血,他却只是往裤子上擦了擦,肿胀的肌肉扯出牵强的笑容。
(202,203,204)
“一只眼睛。”杰克又说了一次,“我不是个吝啬的人,您可以用它抵两成债。”
“……两成……债。”莱曼迟缓地复述。他脸上爬满了汗水与绝望,嘴角却还在向上抽动“两成债……”
(234,235,236)
他举起胳膊,鲜血淋漓。
(239)
杰克又说,“我忘了说,不一定得是您自己的。“
莱曼愣愣地看向杰克,后者利刃般的视线下坠,下坠,钉在片刻前掰断他手指的打劫者身上。
(241)
火光在玻璃片上跳动。
莱曼浑浊的眼被照得透亮。
【tbc】
滑铲
*
*
*
关于阿尔文与施纳贝尔
1
施纳贝尔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他踩着椅子、爬上桌子、只为取走阿尔文的眼镜
他成功了
他在晕眩中看见新的世界
阿尔文眯着眼,差点没接住他
2
施纳贝尔尝过的第一样东西是花
苏拉带来的
藏在口袋里,紫色的,小小一枚,扁折而平整
他哄施纳贝尔取下口罩,给他吃下它
干巴巴的
是热的
3.
施纳贝尔用手指梳头发
阿尔文送了他梳子
他用它来扎面条,一齿能扎上一团
换掉三把梳子后,阿尔文学会了一些简单发式
4
施纳贝尔喜欢贴着人
猫来蹭腿的时候,施纳贝尔也来
狗来小憩的时候,施纳贝尔也来
开饭的钟点,猫和狗都叫唤着往食盆跑
施纳贝尔坐着,脑袋靠在阿尔文的肩膀一点一点
坐诊的时候, 病患的手在桌上
施纳贝尔的在阿尔文衬衣里
阿尔文以为这是因为他讨厌寒冷
他像是需要冬眠,碰到温度低时会显出困顿的样子来
可说着“好热”的时候,他还是会抓住阿尔文的手贴到自己脸上
“很热,阿尔文,我帮你降温”
这让阿尔文的脸更热了
……施纳贝尔是不是故意的?
5
施纳贝尔喜欢繁复的服装
闪着微光的网纱,折射五彩的珠宝,嵌在发间的金属发钗
“我想去舞会”施纳贝尔说,“舞会可以穿着闪亮的衣服,对不对?”
施纳贝尔抬起头,阿尔文正看着他
乌鸦将藏品收进巢
施纳贝尔把它们都收在眼眸中
至少,阿尔文这么认为
6
施纳贝尔不擅长人类着装
明明连是否拥有实体都不好说,他却被困在一团衣服里
“阿尔文,我放不下手了,帮帮我”
“阿尔文,我的头发卡在衣服底下了,不太舒服”
“阿尔文,为什么我的手和脖子共用一个出口?这很挤,人类真的喜欢这样吗?”
“阿尔文,阿尔文,阿尔文”
阿尔文原本也不清楚女士服装是如何穿着
……原本
7
施纳贝尔相当喜欢甜食
于是阿尔文带他去参加以“家里的女佣特别擅长做甜点”的友人的宴会
他的目光追着施纳贝尔,而后者在小蛋糕间穿梭,差点决定住下来
“你在看什么,阿尔文?”他的朋友则在看他
“……甜点”阿尔文说
之后的一段时间,施纳贝尔经常获得试吃
“阿尔文,那里也在办宴会吗?”施纳贝尔离开时问
他看向的是这栋宅邸的后门
还没吃掉的食物被倾倒在路边,和脏污的街道混在一起,冒着热气、散着甜香
可它们注定不会成为道路的一部分,几只嶙峋的手正挑拣着,迅速让它们消解
一根警棍抽打在那些手上,叫它们往回缩了缩
但接着,它们像被饵食引诱的鱼群,在投食口翻涌得更加激烈
“我们是付了钱的!”它们的主人尖叫
阿尔文什么都没说
他的目光掠过他们,抓着施纳贝尔的手往另一个方向走
“阿尔文,那里也在办宴会吗?”
“……不,施纳贝尔,不”
“他们有甜点,他们在起舞。如果不是宴会,他们又是在做什么?”
“黏上蛛网的蝴蝶会做什么,施纳贝尔?”
“等待死亡?”
“挣扎”
8
施纳贝尔是阿尔文一个人的
只有阿尔文看得见他
可偶尔,施纳贝尔会说“苏拉告诉我……”
又有时,徒然堂的女人会问,“他今天没和你来吗?”
感谢上帝
施纳贝尔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9
阿尔文喜欢施纳贝尔
施纳贝尔知道得很清楚
他问过
他也回答了“是的”
10
施纳贝尔尚不理解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