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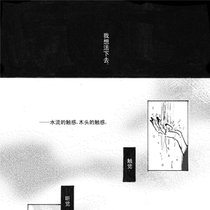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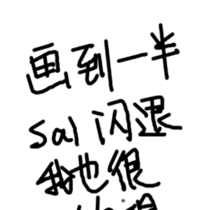
非常自作主张的互动。凉子真好啊,藤华真好啊,蛾子真好啊。
女孩子真好啊!!!
没有和亲妈们商量具体细节,如果有ooc请打我修改(总在说
——————————
鹿又家所住的老房子,筑龄17年,是家中长女凉子出生前新建的。那时的确还是新居,街坊邻里们都上门祝贺,好一番羡慕。而今长女长成了大姑娘,房子业已变成了老房子,酱油和柴鱼汁的气味深深渗入榻榻米里,障子门的木框被家中的孩子们抠出了一个个小凹凹。
这两层独栋的民居,不顶大,却也绝不小。带一方整治得井井有条的院子,院中栽有一株染井吉野樱,色白而蕊丰,木枝呈圆拱形,将整个院子遮住半扇。据说从商的家主人正因看中了这株樱树,这才将这片土地盘买下来,在此之上建起了鹿又家的新居,如今一家五口生活在这里。
在无需陪着凉子的时候,这个家中的小院子就是真黑最长呆的地方。
这同她与凉子结缘前,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同。在之前还在徒然堂时,或许是由于念过于稀薄的缘故,真黑清醒的时间并不很多,这次醒来,本也以为不过是数日光景,待不到下一个造化之日,便又要沉沉睡去。
她醒时也很安静,只呆在古董店深处,挨着窗,闲时点一杯茶,或把弄二三熏香,看窗外风吹云涌,一日便也就过去了。
也有满心好奇的九十九上来问她:
“你在看什么?你总在这里,不会闷吗?”
那金贵华彩的发簪化成若紫发色的少女,明眸纯纯,姣美秀致。女孩不等她回答,又咬着手指道:“哎呀,对了,我头一次见你,合该自我介绍的。你好呀,我是,我叫,我……咦?我叫什么来着?”
她抓了抓长发,险些碰掉了头上簪着的飞鸟金簪,然后瞧见金簪上的紫藤,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九十九笑容变得羞赧起来,她说她什么都忘记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存在,都开始变得难以确认。
“但是,你看,我的确就在这里啊?”
纸矢藤华摊平手掌,将之伸给真黑,像是急迫的想证明什么一般。
“我就在这里啊。我就在这里啊。虽然我总记不得,但是……”
不知怎的,说着这样的话,女孩的声音却越来越弱,透出几分古怪的不自信来。
她默默的将头垂了下去,沉默了一会,才赌气似的开口说道:
“至少、至少我还记得我喜欢团子和樱饼,我并没有忘!”
女孩鼓着脸颊看着真黑手边的茶碗——不久前,她刚刚因将其误认为那种加了糖的茶饮品而将之一饮而尽,苦得眼泪汪汪——愤愤地补充:
“还有,我不喜欢抹茶!太苦了!”
……
真黑止不住觉得有点好笑。
你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有一些人,数十年过去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就算回忆不再,记忆模糊不清,不变的东西依然不变。而人尚且如此,物品只会更长久——因而老旧的物品必将被时间摧毁,且总会有新的东西代替他们活跃在下一个时代。
真黑并不怀疑这一点。她乐于坐在小院前的走道边,看院中孤零零的樱花树,看团团簇簇的一重樱压弯枝头,大团大团的粉白色花儿垂到她面前,鹿又家的次女杏子捧着竹编的小篓子,偷偷采了小半篓花儿,喜笑颜开的说要厨娘用来做点心。
小姑娘前段时间掉了颗门牙,因此说话有些漏风,笑时也总不忘捂着嘴。
付丧神坐在那里,杏子围着她转了两圈,眨着眼睛问她:
“大姐姐是什么人?是姐姐的朋友吗?”
真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她给了小姑娘一颗糖,摸了摸她的脑袋,没有说话。
杏子收了糖,朝她露了一个缺了门牙的笑,然后抱着她的小篓子一溜烟跑走了。
付丧神再度笑起来。在这个家中,凉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而杏子却还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两姐妹的长相很有一些相似,眼中闪着光,笑容很讨喜。这笑让她不免想到从前……
很久很久以前。
她看着一个小姑娘一点点长大。
回忆是这样一种古怪的东西:
有的人想要牢牢抓住,它却无可抑制的从指缝中溜走。
而也有人总试图忘却,它又顽固而狡猾的闪现在眼前。
还有一类人。可悲的人。记忆的每一个角落都清晰可见,眼前的每一刻都不间断的成为过去,他们活在现实中,同时也活在回忆里。
真黑直到现在也仍觉得那个小姑娘就在眼前,对方常趴在她的膝头嬉戏,眼神晶亮,乌黑的长发摊了一地。
然后她看着她的面颊消瘦,变得日益沉默,眼中的光彩渐渐熄灭,最终填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失望与灰色的漠然。
这一切仍然在她眼前。
凉子在她的眼前。椿姬在她的眼前。院子里孤单的樱花树,精致的缠梅枝银香炉,天保四年三月昏暗的油灯和明治三十八年三月的那条小巷。
一切都在她的眼前。
那么,究竟回忆才是现实,又或者现实正是回忆呢?
*
杏子没一会儿又再度跑了回来。
她抓了一把糕点,草饼与小豆糕之类的,虽然与樱花毫无关系,但小姑娘看起来却并不怎么在意。她跑到付丧神身边,嘿嘿笑了两声,然后塞给这个安静的大姐姐两块自己还未啃过的草饼,自己叼着啃到一半的小豆糕,转身又跑掉了。
真黑注视着她跑开,手中的草饼软乎乎的,还有一丝被小姑娘捏在手心时残留的热意。她将之放在身旁,有蝴蝶路过她的眼前,古怪的被若叶和蓬草的气味吸引,扇着翅膀停落在团子上。
“用来赏花,的确还不坏。是不是?”
付丧神将目光投向那蝴蝶,轻声自语,“可惜没有茶……”
鹿又家是商户人家,对子女的教育也更西式。真黑习惯的那些红钵紫砂当然已没有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然不是。
付丧神挥一挥手。那蝴蝶便振着翅膀飞了起来。
“嘻。”
有什么人发出了一声轻笑。
正如在花枝间飞舞的蝶,影影绰绰露出些许跃动的痕迹。那东西踩着红桐色的厚底木屐,“、” “、”“、” “、” “。”像是舞蹈一般在风中踩出随心的旋律,那松纹锦织的翅膀被风微微鼓起,连着大把大把搅动缠绕翻涌的长发,展开两翼舒展着肢节呼的缓缓伏在了地上。
“嘻嘻。你好呀。下午好呀。”
披着被衣的女性展动着脊柱站了起来。蝴蝶从花间飞落,落在她被衣的素色菊纹上,像是为之迷惑,甘愿成了妆点女人美貌的装饰,温顺的展开了自己艳丽的翅膀,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抖动。
“哎呀。真不错哩。蓬草,那东西烧起来的气味太讨厌啦,我不喜欢,可草团子,我却不讨厌,这真是怪事一桩呀。”
那女人这样说。她点了朱的唇弯起好看的形状,明眸潋滟风流,黑发在脑后用细长的金钗微微挽起。自顾自的说完话,竟也不顾他人回应,又自顾自的坐了下来,她学着真黑坐在廊下被磨得光亮的木板地上,晃动着深色衣摆下的双腿,显出一种奇异的天真与无忧愁来。
和这份无拘束的美丽一同而来的还有浓重腥咸的血腥气,付丧神动作顿了一顿,她转头看向杏子跑开的那扇门,又看了看手边的两块草饼,然后收回视线,将其中一块朝女人的方向推了推。
“不介意的话。”
她做了一个请用的手势,自己拿起另一块,悠然放入口中。
“……”
对方将审视的目光放在她的身上,这目光一转而逝,消失在粼粼妩媚的眼波之下。
女人于是也伸出赤红色的手爪,拈起甜菓送至口边,糖粉扑朔朔地洒在她身上,被空着的另一只手毫不在意的掸去了。
“唔姆。”
她鼓动着面颊认真的咀嚼,略略仰起脑袋,声音不甚清晰的评价,“不太好吃。唔。……也不难吃啦。”
满开而如雨下的樱花落在她微扬的面上,女人仍晃动着双腿,哈哈笑着抖动身上的被衣,花瓣纷飞,那只蝴蝶也抖抖翅膀飞起来,女人伸出手,让它停在自己赤红色的爪上。
她忽的起了兴致,跃起身子,踩着古朴端庄的步子在花枝间旋转,旋转,盛极的花随着这阵风在空中律动,蝴蝶绕着她的衣袖上下翻飞,如瀑长发同衣摆交错摇动。
女人无疑有这样一种魅力:
在毫无遮掩的展露着躯体成熟丰饶的风情的同时,又在无意间缭绕着赤子般的纯情与懵懂。
真黑慢吞吞的咬了一小口草饼。的确就像是对方说的那样,这粗糙的菓子称不上美味,却也足可以应景。正如对方对自己的气息无甚好感,却仍能像这样平和的交谈那样。
真黑问她:“若下回你来,便备些你喜欢的茶点。你喜欢什么呢?”
女人便答:“可多啦。扭糖,你听过吗?在我的故乡,我们把金色的糖丝绞在一起,制成许多形状,顶好看,而且可甜了。还有、哎、还有不少的……我一时记不得,还有许多的。”
在她的故乡。
那舞动着的人影放缓了动作,朱红色的唇越发勾出甜蜜的弧线。她用双手撑起自己的被衣,咯咯窃笑着看飘落的花瓣被自己卷起的微风再度吹起,而她则躲在被衣下,叫那让人安心的阴影投在自己身上,像是被一方独立的世界包裹,藏在茧壳中躲避这世界。
直到一边的付丧神问她:
“故乡啊……真是叫人怀念。你还记得吗,自己的故乡?”
“……”
——女人的舞动忽地停止了。
她的舞动停止了。只有蝴蝶还上下翩飞。
“……”
自那素色的被衣下,骇人的光闪转而逝,某种沉静的阴郁涌动。
“我记得的。”
女人说。
“我记得的。”
她说。
“我想了好久。我回忆了好久。我都记得的。”
蝴蝶抖动着翅膀,缓缓将落在她素色被衣的菊纹上——自被衣下倏而探出一只血爪,将那蝶一把捏碎揉烂,细小的磷粉自爪中飘落,那些破碎的细小闪光正映着女人一张无邪气的笑脸,她款款朝付丧神走来,然后停在对方的一臂之外。
“我记得呀。都记得的。那些山与水,生着金色苇草的浅滩,泛着湿气蕴凉又柔和的圆木搭在小湖旁……我记得呀。我记得呀。”
“……是吗。”
真黑看向女人。这是她头一次这样仔细的瞧她,仔仔细细的看过她的面庞,她多情而明媚的眼眸,然后九十九垂下眼睑,显出些许疲倦——对方和她是天生相克的东西,一旦女人不再遮掩她满身的狂乱与阴郁,她的本能便也自然的做出反应,迅速的消耗起自身精力来与之对抗。
付丧神将身子靠在一边的门柱上,神色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是呀,你记得的。你一定都还记得。”
她喃喃自语,不知在想些什么,竟就这样慢悠悠的合上了眼。
“你记得的。你怎会不记得呢?若不记得,又怎会这样追寻呢?”
但若真的都记得,却又有什么好追寻的呢?
付丧神的话音渐浅,落樱撒了她满身。
她竟像是睡着了。
“……”
女人用宽大的袖口遮住自己的神色,她注视着眼前这个存在极淡的九十九,眼中冰冷而漠然。
她缓缓伸出一双异形狰狞的血爪,一点点绞上九十九脆弱的脖颈。尖锐的手爪微微刺入皮肤,忽地收紧——
*
鹿又凉子回到家时,自鸣钟刚敲过五下,妹妹杏子迎头撞进她的怀里,正因吃了太多甜菓牙痛而被母亲一路追赶。
少女有些好笑的捏着妹妹的衣领将小家伙交到母亲手里,戳戳她鼓起的脸蛋,然后被反口咬了一口。小姑娘在她的手指上磨牙,用的力道却不大,豁了一块的门牙在凉子看来也显得异常可爱起来。
她摸摸妹妹的脑袋,然后忽然觉得有些奇怪——往常这时候,真黑总安静的守在她身旁,今天未见她出现,便不免疑惑起来,总觉少了些什么似的。
凉子绕过家人向屋里张望。她很快便在庭院的门柱旁发现了那熟悉的绯色衣衫的一角,走近一看,便见付丧神倚着门柱似是睡着了,她身上还盖着一件凉子从未见过的素色锦衣,绣着大朵菊纹,栩栩如生。
少女不禁对着这一幕露出了笑容,她探头去看院子里的樱树,花瓣徐徐飘落,枝干上已隐约长出了细嫩的新绿。
花开到最盛时,总归已离凋落不远了。
鹿又家小院中的染井吉野樱无声的垂下花枝。
繁花落了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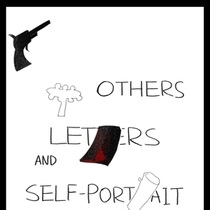

上篇传送: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028/
终于写完了这个序章,字数差点破万,写到呕血……
风油精和鹤田姐姐稍微原型出镜,因为戏太少了,根本不好意思关联(。
耶终于可以开始还互动了!!
————————
7<<<
我那时的境况,绝算不上好,可若真要计较,且也不能说就那样糟。
到底父亲的家系尚保有几分尊严,一应吃穿用度虽不如何好,但也并不如何坏——或者在贵人们的圈子中,如此这般已算是极不体面,不像样子了,可我那时却浑然不觉,分毫不以为意,全不放在心上。
就连唯一收到的那封情信,最初时,也是不在意的。
8<<<
椿姬回复书信,最初时闷闷不乐,不情不愿。
叫她来看,是极不乐意写什么优雅俏丽的诗句,做出甚么知情识意的贤良的。可却也晓得,万不可置之不理,又或直言拒绝。
还能如何呢?女儿家的名声,统共不过那么一些,美貌尚且需将小心保养的长发叫人‘无意中’瞧见,风雅文识,也便只能往这往来书信中瞧了。
便这样,这往来竟也绵延了数月,称得上喜人了。宅内早已风传,言辞切切。有说那头的贵人可是出入殿上的人物,尊贵自不必提了。也有说那公子虽将将奋发,可家学毕竟颇有脸面,是官拜一等的人家的子弟,待到明年开春,少不得便要被封个少纳言来做,亦或直接当参议也未可知呢!
家中的女公子被这样的贵人相中,却不是一件好事?需知,黑貂皮再如何贵重,也是那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可大不相同,往日尊的,现且也变成贱,物件尚且如此,更妄论人呢?
椿姬却并不觉如何欢喜。不如说,她甚至开始心生怯意。
她已与那贵人隔着垂帘说过一两句话,自此便被周遭看做是极亲密,确信好事很快便要可以成就了。
可这好事,究竟该要如何成呢?便是成就了,又如何呢,难道往后的日子竟还能比现在的要更好,天底下竟还有这样的幸福可奢求吗?
她既心中惶惶,拿这样的问题来问,那沉黑柔和的付丧神便用沾了淡淡香蕴的手轻轻托起她的脸,半长的黑发落在小女公子的面颊上,冰冰凉凉,顺着脸侧滑开了。付丧神闭起双眼,面颊虚虚贴着人之子的,椿姬看到那鸦一般的长睫微微颤动,对方沉郁而微凉的声音不意间滑进耳孔。
她唤她:
“椿。”
“……正因你许愿,我才会出现。”
她说。她像是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带着某种莫名的笃定。
“所以,一定没问题的。渴望也没关系,奢求也没关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直到你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
付丧神微微睁开了双眼。
椿姬看不清那些朦胧的黑色的真意。
她张口欲言,却又说不出话来。
而那说不出口的期盼正是:
她也想要相信自己可以更加幸福。
9<<<
您看,我正是这样一个欲求过重,且自识不明的可笑的人。随您笑话我罢,因这本就可笑至极,以致无可推脱,就连自己,亦有时禁不住笑起来,竟成就一种快乐的氛围,也算是奇事一桩了。
不必我说,想必您也足可以猜想出当时情状。我这般渴求幸福之人,在这京中,便如海边砂砾,不下凡百,实在无甚特别之处,芸芸众生而已。
我唯一的幸运,以致于至今所有的泰半幸福,皆来源于同真黑所结下的缘分,她陪伴着我,我呢,当然亦从未想过同她分别,这理所应当一般的幸福使我渐渐蒙了眼,瞧不见其他了,瞧不见别人,自然便也瞧不见自己。
须知:
欲求生鬼,人心生怪。
人若不时刻瞧紧了自己的模样,说不得哪一日再看时,镜中映出的,可不就要是青面并獠牙了么。
……
没有错的,正如您所料的那样。
那位递来情信的贵人,原也是无意要娶我的。
10<<<
说一个无甚关联的题外话——
椿姬已经有些年未想起过母亲的事了。
在她幼时,听老宅中的下人们说起过不少风言风语。
他们说,母亲原也是大家之后,祖上颇有渊源,虽流着贵人血脉,可到底是破落了。
他们说,毕竟恐她承不起这样的福气,便只做得侍妾,虽是真心喜爱,但到底是不曾起念要带回宅中,更无须叫夫人知晓了。
他们说,夫人到底还是知晓了这无足轻重的恋情,母亲因这贵人的怒意而终日惶惶,苍白憔悴之容貌,竟也楚楚可怜,惹人喜爱,有一时期总忽地眩晕,一查便是有了身孕,家中皆喜。
他们说,父亲对母亲可说爱之入骨了,便是知晓母亲有了身孕,不便相聚,却仍是在与旁的女公子有约的日子中,偶也会差人送一两首情意绵绵的爱歌蜜语来,足可见是置于心尖尖上,再诚心没有了。
他们说……
……
椿姬已许久未再想起这些事。
面前握着她的手的贵人,面敷白粉,目光脉脉,着一款樱袭,委实潇洒不凡。那动情的神色却忽地从那张可爱的面上消去了,因这叫人可怜,仪态又质朴可爱的女公子忽而问他,可愿许正妻之位。——这是从何处吹来的话呀?真是叫人糊涂,全闹不明白。她是如何能说出这样令人困惑的话呢?
这公子本想着,他确是爱花之人,且不介意费些钱财——钱财于他又算作什么呢——将这娇怯可人的女公子供养起来,可她的话语,实在叫他吃惊了,惊觉面前之人毕竟是无父母教养的,那根性足可叫人怀疑她或者还有没有祖上的丁点高贵,处在他这样的位置,人人都会知道,与那种贪婪而又善妒的女子攀扯,是极不明智的。
椿姬瞧着他,白面的贵人松了她的手,拿帕子掩一掩唇,未再同她对视一眼。
椿姬已许久未想起母亲的事了。
但今日,片刻之前,她却忽的想起下人们口中的那些话。
她想起,她曾听他们说:
母亲在生下她月余之后的某一日,病死在草屋破旧的寝床上。
据说落尽的最后一瓣晚樱洒在她面上,尽管失了血色,苍白而惊惶,到底还是楚楚可怜,惹人怜爱的。
只这一回,莫说情歌,竟是连一两曲像样的挽歌也无有了。
11<<<
……如何呢?
是否正同您的猜想一般,让您也要在心中叹一声痴呢?
不论如何,您若要笑,便请吧,但也请您可千万不要怀抱丁点对这痴儿的同情,同您说,这是极没有必要的。
实话对您说罢。我对那位公子,投入的感情实在浅薄,称不上爱,更加谈不上因此而痛苦了。这样自白,委实羞人,且盼您不将我视作那等逢场作戏的轻浮女子,虽全是稚气与不安下结下的缘分,忽地断掉,到底还是叫人心中郁郁,并不好过的。
可笑之处在于:
尽管那时我已开始惶惶不安,已隐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贪婪与丑陋,却仍不愿死心,不愿去看那清楚明白的事实一眼,只背过身去,好似那丑陋的东西便就此不存在了一般。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实在也无甚么好讲,我仍像从前一般,日日与真黑在一处,或者到底受了些影响,简直可说要离不开她了。这似是同她自身的某些特质有关,我未曾仔细询问,只晓得在真黑身旁时,世界也安定下来,恰如茶叶缓缓沉入杯底,又似清香袅袅散入浮空。
我总瞧见真黑,真黑却似能瞧见更多我见不到的。
她有时同我说起一些闲话,谈起先代收藏的一枚血玉,或是不知从何处传至这家中的白瓷鹤纹瓶,言中总似藏有绰绰深意,带几许笑,眨眼便转过去了。
那个异常缓慢的冬日也逐渐过去,在每个转年的节分时分,我总见付丧神备起茶点,悠然的轻挽衣袖点一两杯茶,她仍坐在缘侧,面向庭院,院中异常早开的樱花扑簌,真黑像是与什么人轻声交谈,不论我怎样睁大双眼,也依然还是瞧不见的。
我瞧见樱花落入茶碗,薄粉的花瓣如一叶扁舟,荡起一圈无声的碧波。
一阵春风袭来,春日的暖意同馨香迷住了我的眼,等再看时,茶碗已空,只花瓣仍留在碗底。
真黑转头看我,弯着眼睛无声的轻笑起来。
我那时从未料想过,在这之后不久,也正是这一年的春日,我便真正识得了……所谓‘恋慕’应有的模样。
12<<<
最初的契机,来自院里那株花儿早早盛开,又早早凋谢的樱花树。
翻墙而入的少年人围着一株樱树兀自踱步,时而颦眉,时而自语,那烦恼无限的模样,看得屋主人竟也一时对这不请自来的恶客说不出甚么谴责来,更是被这番举动逗乐,拿衣袖一掩面,止不住笑出声来。
少年人羞红了面,慌慌张张上前赔礼,但见家主人娇娇妙龄,一时拘礼,又禁不住后退,动作滑稽可笑,面上更红,终于连头也抬不起了,只用袖子遮着面,低声诺诺,说明来由。
原来此人正是当朝神祗官中的末等,专职典籍的少史,平日里惯与些神异之物为伍的。因察觉到老宅院中樱树异常,这才一时冲动,翻墙来看,未料到这样荒废的老宅中竟还有姬君居住,这才无意唐突,实在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过呀。
少年人语气已平静下来,耳尖却还通红,他偷偷抬眼又瞧了一眼那遮着半张面的姬君,只觉炫目异常,顿时深深伏下,不敢再多看了。
椿姬哪里能不注意他的举动呢?当即亦粉了面,垂下眼去不言语了。
13<<<
我与他的相识,在那时的我看来,真似一场梦境,飘渺而朦胧,如在花间看人,影影绰绰、奇彩斑斓,而那些时光又是那样真实。那之后不久,他又再度上门拜访,提一盒香膏,拙手拙脚说是致歉,往来之间,约定下回自不必提了。
我逐渐也惯于他的到来,总翘首以盼,心中雀跃,溢于言表。
便连真黑亦侧目,不知是怪我总扰得她不得清宁,还是因看出了旁的什么,而有意开我玩笑。她自开春起,便似身上抱恙,平日里总爱浅眠,回的话越发少起来,这时难得精神,合了一方梅花与我,教我制成熏衣散香,又取来绢布戏绸,叫我制出香包来。
我看她面上笑意,又羞又急,止不住反驳:
“可我、我制了香包,又要赠谁呢?”
付丧神便说:“总不是赠我。…嘻,椿也已成人哩……”
她的眸中融开一片暖意,冲散了眉宇间尚留的两分未散的倦意,那一种神色,我至今也还是记得的。
香包到底还是制成了,也到底未被赠给真黑。
我晓得那人往日是不如何在乎熏衣的,可那之后不久,少年人身上却总透出梅花香方的香气。这似乎很预示着什么了。
我总有些敏感,每每禁不住面红,他亦面露羞赧,伸手去搔头,却碰掉了头冠,又是好一阵忙乱。
他某次来访,极神秘的说要还香包之礼。从怀中取出的物件极受珍重,叫我也不免有些不安。但待包裹打开,里面的物什真可说叫人大吃一惊了,我禁不住瞧了瞧自己从不离身的黑檀数珠,又凑近去看被他带来的那一串,同样黑润圆融,竟像是一藤双生似的。
他道,早已觉出我手中的数珠非是凡品,这边特地追查一遭,竟查出一前朝素有高名的僧人,留下的数珠与我的系出同源,因听闻此为有辟邪压秽之能的佛物,几经波折,终于还是想法设法收入手中,便想借此机会赠之与我。
我虽觉香包委实值不起这样的回礼,但此时我与他之间,早已日渐亲密,并不很在意这些虚节了,加之想到真黑,不免兴致盎然,当即便要收下了。
可唯有今回,付丧神忽地按住我的手,面上缠着是我未见过的一缕寒意,她的视线落在被柔布小心包裹的数珠之上。
她忽然张口道:
“这个不行。”
14<<<
付丧神没有看那张同自己极相似的面孔。
她只是注视着那串与自己采了同一根黑檀木制成的数珠,语气淡淡,或者还带有一两分自己也未注意的隐晦的怒意,阐述着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个不行。”
这个不是清净之物。
已经不是了。
不行。
那除她之外无人能视的男人无奈浅笑,两人同样的身披僧袍,同样黑发齐肩,黑珠耳饰下挂一点红缨,眉心点一点朱红,微笑时柔和沉静,似抚平一切的清润流水。
那男人现在正这样轻且淡的笑着。
但真黑丝毫不为其所动。
她不再多言,甚至抬起手,拢住满脸担忧的椿姬,遮住她的视线,将她塞在自己身后。
男人轻笑了一声。
“你‘落下’了。”
付丧神终于看向对方,一瞥后再不愿多看,微抿着唇移开眼去。
“……退开吧。”
竟是连一句话也不愿再多同他讲了。
15<<<
因真黑的坚定,我最终也未收下那串数珠,而叫一片热忱的他颇感疑惑,怀着失落与伤心离去了。
我只不知如何同真黑说话,心中又是疑惑,又是歉疚,因想起那人被拒绝后伤怀的神情,心里也止不住泛起痛来。您瞧,我虽听从了真黑的心意,但却无从理解,更为此而对付丧神暗怀怨愤,只不说出来罢了。
真黑却不解释,她一贯是这样的,话不很多,总淡淡的。我往前极爱她这般,那时却觉出几分消极,生出不满来。
她只对我说:
“那物不祥,不可牵连。”
我那时并不太懂得她的意思,说一句实话,便是此时懂得了,也已于事无补,毫无用处了。真黑看起来极疲倦,我已记不清她如此疲态是从何时起的,或者是那日见过那串数珠之后,又或许是在早前樱花凋谢之前,亦说不准,便是在那个冬日,我同那贵人不再往来之后……
我自那一日与那贵人分别后,脑中总隐约回荡着某些模糊的念头,一时觉得总该像真黑言说那般怀抱希望,一时又想,不若便让时间停在此刻,长长久久才好呢。而一个更加可怕的念头,轻易是不敢想起的,一旦起念,便似大病一场,体虚神乏,定要长久的倚靠着付丧神,才可稍稍好转,好似从对方身上抓住了一丝摆脱的力气,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已知道,那最令人惊惧的,总是最贴近真实的,因现实总凄凄惶惶,才越发叫人恐惧,不愿多想一分。
而对于我来说,那总是避开不看的念头正是:
我这样的人,本该是连现在这般的幸福,都无资格享有的。
16<<<
我到底还是未能将真黑的忠告转告给他。
在那之后不足半月,有他的一位同僚来拜与我知道,数日前,那好人奉了命调查一处神异,及至夜半未归,翌日上峰领人去探,果然已遭祸事,挖心剜骨,好不凄惨。
黑檀数珠不知所踪。
17<<<
这破败的老宅子,庭院荒芜,顶生蓬草,墙壁斑驳爬着青藤,阳光一照,间隙生辉,尘土在光中轻舞。
在这家中,终于久违的迎来一件好事。即:
那疯疯癫癫总独自说话的家主人,虽长久的郁郁寡欢,逃过了适婚的年纪,但近日来总算提起几丝精气,与下人们说话似模似样,不再独自低语,或唬人般突然笑起来。
家中这几日忙于打点行装,逢人便说与人听,原是要出京远嫁,做陆奥某地体面人的正头太太呢!
这可不是福气么!虽说出了京,于这姬君的声名体面来说损失颇大,先祖也要叹息,可家道中落,大抵也只能这般。如她这样的年纪,有人愿娶,已是不易,怪道家仆们皆欢天喜地,没一丝不满的。
这家的女公子,也是生得美貌,虽疯癫,传说得过癔症,但这癔症现在看来,毕竟已是好全了,无碍了,达官贵人们想到这家渊源,多有遗憾的,平头百姓们却多有艳羡,称这正是好日子要开始呢,世人所求,不正是这样的幸福嘛!
椿姬也这般想。从前毕竟是自己走岔了,因得到太多,便被蒙了眼,竟忘却身份,奢求些万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来。因有真黑在,心中便总念着,真黑总会替自己带来幸福,这是千真万确的,可自己奢求无度,又得哪样结果呢?付丧神也力竭,终日昏沉,与自己说话的力气也无有了,自己呢,手中空空,心中也空空,甚么也未抓住。落得这般结局,可见幸福实不可强求,哪样的身份,便过哪样的生活罢。
明日便要出发离京,再看一眼广间缘侧与庭院,已无付丧神的身影,头次察觉木板褪色腐朽,内室阴湿杂乱,庭院可憎不堪。
远非自己记忆中的模样。
椿姬一眼也不愿再多看了。
18<<<
我的故事,大抵便是如此,实在寻常至极,无甚好说与人听的。
您若当真耐着性子听完,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者嫌我噜苏,或者尖辣指出某处并某处偷工减料,也都未可知。请您原谅,非是我小气吝啬,不愿全部叫您知道,只不过女人家的悲鸣啼哭,萋萋哀愁或是歇斯底里的自怜自哀,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又有什么好叫人知道的呢?总归不过是一时愁绪,揭过便也好了。我便不总一一赘述,恐伤了您的心情,也恐叫您嫌烦。
总之,事情便是这样,我终于接受这一切,拾起手上的数珠,决意将之留在老宅,细心妥帖的收拾起来。
真黑越发倦了,每日长久的昏沉不醒,偶尔醒来,只以目光对我,不说半句话,我开始时无从面对那暖和却又渺然的目光,后来就已习惯,镇定自若起来。我已决意要解放她,不叫真黑再为我吃受半点苦难,我正与我的母亲一样,祖上有尊贵的血脉,家中却已破落了,这样的人,本就不该谋求自己承不起的一切幸福,我向真黑许愿,已是贪心,且还不满足,以致真黑日渐虚弱,而所谓的幸福,更是送到我的手边,却也还是抓不住的了。
我会解放她。即便她已虚弱至此,到底还存留着一两分复原的期望,只我需不再奢求,不再期盼,这便是救她了,是叫她不再费心费力了。
我要嫁的人,年过四十,相貌如何,我也无从得知。只知道他家中很有几份薄产,家学也算可看,且能许正头,便很理当欢欢喜喜的嫁了。我不带真黑一同离京,恐她总会受我影响,难以复原,但又极想知道她对于这一门婚事的看法,若她赞同,她应会赞同吧?我也便更加能说服自己,更欢喜的离开这盛京。
但到底我是听不见付丧神的声音了。
真黑已经睡了。
19<<<
现在,您或许已经了解了一切,又或者没有,不论如何,就请您听一听我的请求罢。
若牵连您与我之间的缘分,正是那温润圆融的付丧神,若您还可与她牵起手,听她轻言慢语,若您还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我已失却了的机会的话——
我请您——请求您——
请您,和她……
一定都要幸福。
————————
因为最后考虑了很久还是删掉了一个真黑视角的片段,所以有些事情可能还是需要解释一下……
椿姬和真黑之间一直有某种误会。
椿姬觉得自己许愿,真黑会消耗自身的力量来帮她实现愿望。但事实是,因为她有想要幸福这样的念,真黑才会化作人形。
这样的一个误区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旦椿姬开始怀疑自己不配得到幸福,她的念就会变弱,真黑也会因此而变弱,而看到这一幕的椿姬越发深信这是自己贪心不足导致的,以至于最后放弃了希望,向现实妥协,以期望这样能让真黑回复正常。
但她放弃了希望也就意味着念的消失,真黑不会因此而回复,而是会因此陷入沉睡。
这个故事唯一一点希望就是,真黑毕竟没有完全消失,这就证明椿姬虽然说放弃了希望,选择了妥协去嫁一个根本不熟悉,大她好多身份也不如意的男人,但是心底某处肯定还是藏有一丝对生活的肯定的……大概就是这一丝念支撑着真黑继续存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