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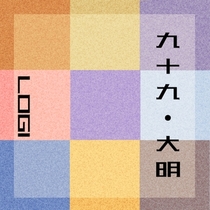




反正全是npc,那我就直接发了吧(……
先扔白露,等20号再改分类……
虽然逛窑子,但是很清白!
————————
出得上方门,入得桃花坞,河心一叶扁舟徐徐来,船家立在后边板儿上,缓缓地摇那杆儿,小舟自桥洞下过了,瞅着岸上的卖花小郎,便递出几个大钱,掐一串花来,是要送与搭船的贵人去的。
下金陵五六日,一朝梦至姑苏城。
离了秦淮烟雨十六楼,便也是离了那轻纱软帐嫣红柳绿。时人言秦淮夜色霓虹,便如仙宫瑶池,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红灯笼金铃铛不及入夜便挂出来,香粉女郎们倚了画栏,黛眉细细挑,眼波粼粼飞,将胭脂在手掌心里头揉淡了,再轻轻拍到面上去。
又高高梳了发髻,簪金分心的钗子,纱造的绢花,嫌绢花不美的也有,便候着延河走的贩花人,挑着个竹编的大篓,赤脚踩着草鞋便来了,篓上盖着湿布巾子,布一掀,内里露出茉莉香串子来,花儿鲜才摘采下,保了湿气半点不败,还带着清凌凌的水珠子,三五一串的也有,串成手串的也有,还有用丝线掉着,做成个耳坠子。
不止楼里的姐儿争了来买,民人也有买的,小夫妻簪不起金银,那家男人就去买个花儿,捡着篓里那半开不闭的,给自家婆娘往木头簪子旁一插,女人脸上的笑影便止不住,却还嗔一句,没得为些个野花骨朵儿,就花得这个冤枉钱。
可到底还是高兴的,花儿一簪,不光满屋子生香,晚上还难得加一碗红肉,油盐糖俱搁足了,肉香花香在一处,用过了晚饭便要吹灯。
而这姑苏比金陵,便又另是一番风景。
水巷小桥,细舟绮罗,茉莉花也还是卖的,却更水更娇嫩,布衣纱裙的小娘子要得支花簪子,还未往发间比划,就已叫卖花的小郎夸得飞红了面,扭身跺一跺脚,把衣带子搅个不住。
船家将团花送到贵人手上,瞧岸上香软亭锦绣楼,还笑一回,压了声音上前凑趣,道:
“虽不比那头十里珠帘,夜里羊车出得门,十回里未必没有一回往此来。”
声音里透着股子神气,不敢明着说,怕叫人捉去砍脑袋,只朝天上一努嘴,便知道说的是那太祖皇帝,三宫六院都有,偏就贪楼里姐儿那个味儿,又是建十六楼,又是认妓生子,甚个事儿没干过,只不许人说。
那乘船的贵人是个白面的年轻公子,也不嫌小舟粗糙简陋,求的便是这般滋味,贴身的小厮且不叫在船上伺候着,另有自家的画舫,在后头远远跟着。披了袍子在前头立着,玉面银冠秋水暖,两袖空空只乘风,可不是雅事一桩。
接了船夫递来的茉莉花,嗅得满鼻香,便笑一笑,连着船资一道,给了一个小银角儿,船夫一过手便知心实足有三两重,笑得见牙不见眼,搓着手与那公子见礼,叫他有甚个只管吩咐,胸脯子拍得咚咚响,再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白面公子便叫他寻着岸边青石砖的台阶停了船,又给了一角碎银,令他也不需做旁的买卖,只在此处等候,这几日还要他的乌篷船。
放着镶金镶银的画舫不坐,非要乘个乌篷船。他既赏钱给的厚,船夫自不将这好买卖朝外推,就见那公子自个儿掀起袍角上了街,也不知往何处去,收了银子,船篷子里一趟,难得躲个闲,背地里还笑一声,真个怪人。
岸上人一路走走停停,大街小巷的铺子逛着,还买得一包豆糖,这也不是甚个值钱玩意儿,小本的生意,自家做得了,扎个小亭就在路边叫卖。
寻常富贵人家且嫌豆粉没有自家磨的细腻,等闲不拿正眼瞧,白面公子却停下买了,还叫多撒些豆子粉,卖糖的陈娘子见他好性,调笑一句莫不是买给家中小夫人,那公子却把手一摇,将油纸包的豆糖晃晃悠悠拎在手上,一转头,竟直接登了红云楼的门。
卖豆糖的陈娘子满脸的笑就变了个味儿,还道是哪家新婚燕尔要讨正头娘子的好,原不过是买给那红粉桃花瘴里的粉头的,却道也是,那个男郎不贪欢,天下乌鸦可不是一般黑,妓院对过且还开着贡院的门,那些个读圣贤书的,不也一径只捧着些个妓子,作些酸诗,写些酸句,便似天上有地下无了。
陈娘子心头那些子嘀咕略去不提,且说这红云楼,倚水而建,轻纱软帐,雕栏玉阁,锦绣辉煌,在这姑苏城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红粉香窟,便是比着金陵的醉仙轻烟翠柳,也不差什么。
楼里的姐儿半是官妓,半是私娼,大多自小便卖进去,叫假母请了诗书先生,又教琴棋书画,这般调教出的姑娘便极难得,等闲不叫人见,纱帐子后头露半面脸儿,花丛里头见一段掐细了的腰,绣花开富贵的屏风下一对金莲,便能叫一干子士子丢了魂,大把金子银子奉了去,再不吝惜。
白面公子进得红云楼的门,门口的鹦哥一声声的叫茶,门内的姐儿们瞧他生得俏,都很愿意凑到跟前,叫鸨母一把全拦了,腆着笑脸亲迎上去,将他引上小楼,掀了轻纱帐子请他进去。
底下有年岁短的小丫头便吃惊,挨着人嚼舌:“怎地转了性子,叫人进了月娘子的屋子。”
有呆的久些的姐儿便拿染了花汁儿的手指点她一回,道:“那里是转性子,不过是那郎君手头大方,听说又是个有身份的,月娘子待他青眼,一年也来不了三两回,给那头却送足了银子,那里还会拦着。”
口里说的月娘子,便是此地有盛名的诗妓,娇名唤惜月。都说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儿,哪想一夕间家里糟了祸,自家流落到这地界,鸨母爱她好颜色,字儿也识得诗文也做得,又会琴又会画,有意捧了她起来,精心调教两三年,捧出来做得个花魁娘子,时人都晓得月娘子花名绝艳,不叫她看上眼的年轻俊才,再入不得娘子的帐子。
入得这腌臜地,女孩儿便再不想着还能清白出去,见得多了酒后那些个丑态,倒也不羡慕寻常女儿家嫁娶,只羡慕这月娘子,只想自家有一日得了这风光,便也如意了,哄得恩客存下银钱,待年纪大了,未必不能自个儿梳起头来,另起一灶自做买卖。
再瞧一眼小楼上那金贵纱帐,又想上去那金玉公子翩翩好颜色,心里头艳羡过一回,也晓得左右与自家无关系,帕子一甩,自回内屋去了。
却说那公子入得纱帐,内室焚了香,却非浓香,若有还无,只淡淡。云锦屏长条案,不镶金银,只挂玉饰,还拿竹段扎得个小屏,隔出半扇琴房。
进得门,便有小婢垂首领在案前坐了,又有一婢上了茶食,金丝肉酥牡丹饼儿,却不上茶,因晓得茶必是要娘子亲点的,两个俱都懂得规矩,也不朝白面公子面前站,垂着头默不作声又退出去。
自屋内摆设到下人规矩,一应既清且雅,半点不似在这样地界,瞧着案上一块胭脂红绣连枝茶帕子,坐案首的客尚未出声,内里的珠玉帘子便淅沥叫一只玉手掀起来,人未至,声先到,便听一声笑,一个清亮女声传出来。
“赵公子金贵人,怎有空朝奴这里来呀。”

我比我自己想象得还要拖沓.jpg
在青楼开黄腔,很合理对不对(
——————————————
赵衔将袍角都展得平平的,手虚搁在膝上,不声不响眼瞧着面前女子净了手点茶。
只见好一个金桂玉阁的月娘子,真真肤如玉雪,面若芙蓉,云鬓乌乌叠叠,也不妆点,只簪个玉丁香在发间,白玉的朵儿似隐还现,说不出的贞静。
月娘子一举一动天宫仙子似的点了茶,又将玉葱指尖拿帕子擦过一回,这才正眼瞧了对坐的赵衔,她垂着眉眼时尚不觉得,只一抬眼,便露出一双神采飞扬灵巧杏仁目来,通身一股子清清冷冷月宫仙子的气儿,到这儿便先散了一半,她与赵衔相处从不遮掩,说出的话也再不似发间那枚玉丁香。
连一把嗓子也不似寻常软红娇媚,既清且朗,道:
“赵公子高名,便奴屋中两个侍儿也读过三两张散游随记,遇着好天儿,还惦念着去寻仙山脚下那徒然堂,公子仙境也去得,可不是成了金贵人,怎的好叫这般人物上奴的榻,折煞奴。”
一席话夹枪带棒,没一个平缓音,赵衔却不在意,端起茶饮一回,照旧温和和的说话,还赞一句茶水清而味甘,品出炒茶时一并搁进去些个香花叶子。
这却不是外头买的茶,而是月娘子自家制的了。
那花魁娘子一拳头捣在个棉花絮子上,自家也无趣,伸手拈了个金丝肉酥吃了,外头金丝炸得金黄焦脆,里头肉酥味醇香浓,只在她这屋子能吃着这般的点心,肉酥俱是专有的秘方制的,鸨母竟也依着她藏私,不叫供出来。
吃得一个肉酥,唇上抹的口脂叫沾掉不少,她抹得淡色水红的口脂,只为了做个清婉模样,心里却说不上喜爱,这样做派,本也不是她的性子,想东想西,一时愈加躁起来,将茶碗端起来饮个见底,胸口那点气闷这才好些。
赵衔慢条斯理吃完一盅茶,见她静下来,这才重又将茶盅搁回去,在袖里摸了一回,先触到那船夫巴巴的献来的茉莉花,却与此物无用,指尖绕过了,抽出张折了一折的信封来。
将那信封一点点展平了,也不急着递,就扣在桌上,拿手微微压着。
月娘子拿眼瞧了,才四平八稳的在案上推过去,接到手里一捏,扁平一片,且不知装得是个甚,也不着急叫她打开,只道:“姑娘必知我心意,再妥帖没有的。”
说得一句话,坐下还没三刻,竟起身便要走,月娘子也不拦他,左右他二人间无需讲那些个虚情,她既不拿他当能拢住了的恩客,也晓得这赵三天生的冷心冷肺,看她自家也不过似看个红粉皮囊。
最爱洁不过的人,大面上不显,背过人去别个上过手的碟儿盏儿都笑眯眯的砸了换新,帕子一指头一指头细细擦了,抹过一遍,整个叫扔了。
这些个月娘子再清楚不过的,把唇角一勾,明知他再不会碰自个儿,却非要刺他一刺:
“赵公子这便要走?好歹留下一夜,便奴不得心意,也自有卿卿伺候得,免叫那起子嚼舌头的笑了去,还道公子银枪怕不是个蜡头,一竿子且进不得洞。”
赵衔眼皮也不抬,半点不吃她这般激将,非但不跳,还笑一笑,只道:
“我与姑娘之间,旁个误会,便也罢了,只姑娘白璧人儿,再不能这般拿自个儿调笑,损了自己清白。”
这会子讲清白,便是花魁一夜值千金,付得千金照样得陪一夜,入了这虎狼地,那里还有甚清白可言?
月娘子拿扇掩了面上冷笑,道:“奴算得哪块白璧,公子自来不稀得碰的,与公子又有那样关系叫人误会?”
赵衔本背着她欲走,听得这话,倒回转过来,侧了半面脸,叫她瞧见那温和眉眼里一点冷光来,他生得一双蜜棕色眼,知他甚多的月娘子却瞧不出半点暖,便面上带笑,一双眼不经意间还是带出冷来,不识他的再瞧不出破绽,可要她说,不过是照猫画虎,有形无神,学了上头那一位的言行,内里却依然还是那冷戾的性子。
便眼中那点光,也很快叫掩住了,只听那人轻笑一声,缓缓道:
“我与姑娘……总归沾着亲呢。”
“你……赵叔明!”
手里头扇柄子立时叫捏紧了,月娘子厉喝一声,面色猛地沉下来,胸膛起伏,她与赵家沾得哪门亲,双方心知肚明,此时提起却早已是个笑话。
还未张口再说,赵衔竟还往回走了两步,将自进门便提在手上的油纸包搁在月娘子面前,只作瞧不见她一把指甲抠进肉里。
“姑娘惯爱吃的,说家中做的不对味,偏爱街上买来的。”
说得这一句,再不管月娘子双目冒火,自掀了帘儿出去。
背后的人心里将他骂得百十遍,张得朱唇,却一字儿也吐不出,恨恨盯着他出了门,果然冷心冷肺,自来头也不回,咬得一回牙,知晓自家生气也无用,索性将一壶茶水饮尽了,舒出一口长气这才好些。
这才取出赵衔递来的信封,随手撕了开,里面竟半个大字也无,只掉出个干瘪的草药叶子,月娘子医术也读过一囫囵,左右翻看,认出是枝一见喜。
一见喜,穿心莲,苦胆草,那个名儿都合,却不知这打的是甚个哑谜。
可不论是甚,总归不是他乡遇故知,见了她喜。将名儿在心里头品过一回,再想想如今姑苏这地头来了那些人物,月娘子心头一跳,既惊且喜,一下子竟立不住,扶了案歪歪坐下。
嘴里细细不住自语:
“难道竟是这样,竟是这样,这便终于要动那人了……这么些年苦胆都尝得,人终于送到面前,可不是喜,可不是喜……真个到了时候了?”
不明不白念了几句,又去拆案上那油纸包,见了里头豆糖手都是抖的,挑得一块放进口里,面上又似喜又似悲,囫囵嚼吃了,只觉甜腻腻从舌头尖一直腻到嗓子眼。
这哪里是她惯爱吃的,分明爱吃的另有其人。
送这个,不过是激她一回,叫她兀要忘了那人儿。
不爱吃这口甜的,吃得这一块,却还伸手去再取一块,面上要哭要笑的神色俱都按耐住了,只一双杏仁眼里藏不住的泛出悲与狠色,指甲刮在案上,生生撇断了两根,半点不觉痛,反而笑起来。
“那里需要这般试探激我……”
那家破人亡的仇,若有一日能忘,她如今且不会站在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搞的,总之就这样吧(抓头
之后所有的章节都会丢一个汇总到这里来。
因为我很懒,所以可能并不会实时更新。
————————
序章·湖中仙
一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208/
二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231/
三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278/
四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386/
五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594/
六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2838/
七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3384/
八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4005/
九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322/
十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480/
完: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558/
一章·侠义客
一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786/
二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838/
三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5932/
四章: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6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