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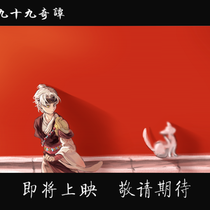


杏姐专场!!
写着写着就心疼起来。序章完结前的最后一张,稍微有点信息量,下一章收尾,点一些前面埋的伏线,会再死一个人。
我终于快写完了,叹气,还是要到3w字了……
让我再说一声:赵衔你这个辣鸡!!!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朱杏要寻那画中器魂说话,原还很顺利。
既要说话,便要灵器魂魄显出形来。她先略略打量过一回王家备下的屋子,果然与自己求的不差什么,窗上贴了青竹纹的冰砂纸,朱杏还倾身出去瞧过一回,隔着院墙再看不见那方小荷塘,回身把窗也闭紧,这才满意的点一点头。
她往日跟在母亲身边,行得多看得也多了,自然知道手上灵器的凶险——却也非是说就有能耐伤了她了,只她身边跟着昼间深夜两个,不说还只是个浊气缠身的灵器,便是来个老道些的狂百器,要伤她且还不能。
说着凶险,实是物器本身险得狠了,是清是浊俱在一念之间,半点受不得刺激。深夜同她说,也不必多费口舌,只将浊气都净去,自然也就好了,可朱杏咬咬唇,到底驳了他。
她心里头首先想的,是必不叫那画中灵害了王公子的性命去。器灵与人,在她瞧来实是同样的,灵器与狂百器,也说不得就有多少不同。
人有入了执疯魔一辈子的,器难道就不许一时蒙了头走岔了道?
且说这岔道,于旁人是蜀道崎岖难登天,说不得于事主便是清朗舒平锦绣团呢?
朱杏便总想着,不拘人或是器,总要听过对方的话音才好。这念头在她心中已久,有些个道理,她似是知道,又似不解,像是隔一层黄纸,细蒙蒙一层,却总也戳不开。
一时戳不开,也不打紧,总归这桩事归她做主,便由着自己的心思来安排。
将山水图往案上摊开来,灵物吃她一记大亏,缩着不肯出来,图面上便半点不露,清凌凌的墨意山水图配边上一只掐金点翠白瓷瓶,竟在这当口还显出了几分雅来。
朱杏先与山水图说话:“请姑娘出来一见,先前匆忙出手伤了姑娘,很该赔个不是。”
画儿静悄悄,只一味不回答。
深夜身后头一条尾巴摆了摆,叫朱杏拿眼止住。
接着便又自报家门,说了一些软和话,仍不得回应,那画灵早先叫常山来查看时,钻出画来唬了这官儿一跳,可换得朱家这个娇滴滴的小娘子,还未见便叫拿钗子掷了个对穿,晓得对方厉害,再不愿出头。
最后还是昼间轻笑一声,同深夜两个一左一右走到案前站住了。
他也不再提深夜说过的那些话,只道:“娘子,也想一想那王公子罢。”
此时磨得越多时间,那被困在画中的王公子可不是生机越薄。
他们家的娘子心善,事事想着留有余地,念着以理以德,可世道那里就这样容易,双全之法,那里可得。
昼间却也不点她,左右朱杏往后日子还长,先时不懂,何时碰着跟头,摔得痛了,也便懂了。
朱杏咬了唇,她的心是善的,决断却也极快。
她心里定了主意,便将皓白手腕一翻,掌中生出一朵白焰,只小小一朵,驱使了往山水图上引,奇的是火苗遇纸张却半点烧不坏,却扑朔冒了一缕黑灰轻烟,接着便响起尖利惨叫,见一点黑点自画中湖内翻涌,须臾湖水竟真个荡起波来,一墨色女子身姿自湖水里扑朔着翻滚上岸,惨叫一声弱过一声,黑色烟雾顺着画卷边沿一滚一滚溢出来,先是流淌一地,接着便渐渐凝成个韶华女子模样。
细长慢挑柳叶眉,紫阳清月翦水瞳。分明是二八年华的娇柔美人儿,面盘盈盈薄施粉黛,眉间贴得画钿,一双唇却不红润。
非但不红润,还微微泛着青乌,连着一双玉手伸出,也是死灰色。
那画中灵受得白焰灼烧,虽画烧不坏,那些浊气却与她相缠日久,极难分扯,烧着那些脏物,便同烧在她身也无两样,只觉烧得皮开肉绽,再忍耐不住,自画中扑腾出来。
她甫一落地,知道是眼前之人害她受苦,忍着焦灼便要扑将上去,昼间深夜两个那里能叫她再动弹,一边伸了一条臂膀,便将画灵死死按住,她再要挣扎,身上却已叫烧得没有力气,又那里能扭过那两个积年的活阎王,只赫赫地喘气,一双多情含泪桃花眼隐隐现着红光,牢牢钉在朱杏身上。
朱杏一言不发。
她是头一回这样近瞧着身缠浊气的器灵被灼烧的模样,收回那一小朵白焰,她面上不显,心头却说不出的五味陈杂。
决意的也是她,动手的也是她,这会子再说些心软不忍的话,只显得矫情。
朱杏也不品自家心里那些酸甜苦辣,努力正了面色,同画中灵说话。先问她王公子在何处,画灵不答,又问她为何如此行事,也不答,朱杏想了想,再问:
“可知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这一个问题,总算叫那只一味沉默的画灵变了神色。她先是颦眉,张口说“姓李,家住簪花巷子”,可说完自己却又恍惚起来,两弯柳眉狠狠拧起,眼中仿若含了秋水盈盈,泪珠子要掉不掉,声音讷讷:
“奴姓李,住簪花巷子,姓李,姓李,奴要寻三郎呀……奴要寻……”
她细细说个不住,本已叫烧掉些浊气,清醒许多,这一下竟又疯魔起来,手里衣袖也叫扯烂了,黑气猛然翻腾。
朱杏却狠下心,再不拖沓,也不惧那翻滚的黑烟,张口喝道:
“非也,你不姓李,也不住簪花巷子,李小姐早早去了,你却将将才生!抬头好好瞧瞧,你却还不醒么!”
一字一句落地有声,那画灵怔怔然一抬头,眼前陡然清明,正瞧见自己半身落在画纸外头,另半身犹在画中,心头猛地一窒,张了口,却再说不出话来。
朱杏斥过她一场,眼见她似是醒悟,语气便又不由软下来。
“你并非李家小姐。”她轻言轻语,话儿却不含糊,“你乃李小姐所藏画作,因受物主执念影响,生出一段神智来,你便是这画,画便是你。”
见画灵怔忡,目中红光消退,眼角眉梢戾气水色渐消,却露出几分茫然无助,像是出生婴孩一般懵懂起来,朱杏顿了一顿,叹了口气又道:
“去者已去,你因李小姐执念而生,却很不必将自己也困在这执念里。你既非是李家小姐,王公子如何便也与你无干系,放了他出来,不害得人命,自有你安身之处,往后如何过,全还在你一念间。”
画灵听她温声说话,本已有些听住了,神色越发缓和,只听到要将她那三郎放出,却抠了手抿了唇,不言不语。
她心里头且还懵懂,说话做事全只凭本能而动。先时一门心思以为自己是李家娇娥,一意寻心头藏着的那个三郎,拉了人的手,也不知是想着要将好儿郎一同带下水,还是要叫那好人拉了自己上岸。
画灵自醒来那日,便是长在水中的,她沉在塘底,一时烂泥烂草自面上的孔洞灌进来,有意哭喊,也只灌得一嗓子泥沼,可便是如此,痛苦得狠了,也只死不去,腕子叫水草缠着,抠断了指甲整个掀翻过来,也不流血,只日日肿胀窒息,却偏不死。
再之后她总算上得岸来,深恨这片湖水,却也离不了这片湖水,离得远了,整个身子再不成型,如一滩烂肉自骨架子上头扑朔朔往下落,叫水一泡,却又是还娇嫩红颜,只得泡在湖水中,支着身子立在岸边,浸在水中的身子一阵阵发冷,这时便又想起,她心头有个三郎,远看近看都是极好的儿郎,可他怎地就不拉她上来。
画灵既不识得自个儿是谁,也说不出这三郎是谁,想起那人仿若雾里看花水中观月,心头一阵阵的痛,又是苦又是涩又有甜,分不出滋味。
她生出来不过几年光景,头脑昏沉,不清不楚,直到山水图叫王公子得了去,日日观赏夜夜把玩,才头次出得纸面,自己却还浑然无觉,见着个儿郎,口里只会唤一声三郎,那里想王公子竟应了,自然认定了他,几日下来,叫王公子拉着她的手,一气扯进了画卷里。
此时听朱杏说她非是李家小姐,一声如雷轰然炸响在耳畔,将往昔镜花水月一时砸了个干净,兼之浊气损消,脑内清明,也晓得了自己原是那样来历,可叫她就这般放人,到底还是不肯的。
朱杏听她没声,也知并不这样容易,只她也没再闹起来,便已经算得是好兆头。当下连哄带劝,细细开导:
“我看那王公子,也未必便是你要寻之人,王家两年上一次京,等闲进不得李家大门,王公子要与李小姐有私,他却那里来得这样大能耐?家中行三的儿郎那样多,你若过不去心中那道关,此间事了,我便陪你去寻那人又如何?只你不害人,寻到了解消心结,谁也不拦着你去。”
画灵身上黑气愈消,懵懂的眉宇间又添出两分理性来,听朱杏说得恳切,竟好像也懂得了她讲的道理,虽仍是踌躇,却并不那样坚决了。
她忽地抬头,颤颤地拿眼去看朱杏的眼,盯住了她不松,蠕了蠕唇蹦出几个字来:
“与我、找、人,说、好了……?”
她声音轻脆脆的,透着叫朱杏再没想到的稚嫩,说是童音也似,同先前那把甜腻婉转的嗓音再不相同。
在场一人二器俱都明白过来,先且那娇腻甜音是李小姐的嗓子,这时这把清脆嗓音,才是属于这画中灵的。
朱杏止不住露出个甜甜笑脸来,伸出小指头停在画灵面前。
“说好了。我们拉钩。”
那画灵歪着头瞧了一会,也学着朱杏模样,伸出青白的小指头,冰冷的手指缠着朱杏的,一人一器却都不觉得凉,絮絮说起话来。
一个说:“找、到人,我不、害他、”
另一个就点头:“嗯,我陪你找。”
一个又说:“我就、想、问、问……为何不拉、我、我、主人、上去。”
另一个就道:“嗯,问问他,为何不拉你主人上来。”
一个停了停,犹犹豫豫还问:“这、回、必不叫、我、再、落水了罢……?”
朱杏心里裹着一股子热意,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坦。吸了吸鼻子,用力点一点头。
“你且放心,必不叫你再落水的!”
画灵便抿了唇,面上现出几分活泼的笑影来,她伸手朝画卷中一捞,便见素手上多了一片衣袂,再一看,却是个年轻公子叫她捞在手里,形销骨立面色青白,却总还出气,是那王家公子无疑了。
那王公子看着狼狈,一出画卷,竟还有力气抬一抬眼皮,一眼便瞧见近在眼前的画灵,唬得牙关咯咯作响,也不知那里来的力气,竟将两手一挥,扭身瞧见旁边站着的朱杏,更是心生指望,不住挣扎起来。
一边挣扎,一边口中还骂:“兀你这鬼物——!巧言误我!救、救命——”
他几言讲得画灵面上先前那点子血色尽失,眸光点点摇曳不住,几乎拉不住他。王公子此时奋力一挣,人未能离得画灵之手,身子却是撞出去半边,晃得案台支撑不住,一边摆放的那只掐金点翠瓷瓶两下一摇,倾倒侧翻过来。
谁也不知瓶内竟装得大半的水,这一翻到,立时便浇在画灵人身并本体的山水图上,整张图都仿若淹在水里。
本已消退的黑雾顷刻间再起大盛,朱杏只听得一声痛苦尖啸并男子闷哼,骤起的狂风刮在她面上,眼前却黑风雾绕,一应全看不真切,只觉夹煞带怨,隐约听得女子啸中带哭,反复只念:“水、水、不落水、不要落水……”
她心中大急,一时也不知是否自己错觉,只觉又听见了那轻脆脆的声音泛着哭腔,朝她怯生生的求救,可耳里明明只有不成声调的异物嘶嚎,昼间深夜只将她护得牢牢的,怨气与浊气愈加浓重,又听得几声硬物断裂声,眼前声势猛地一收,只见一黑影破窗而去,朱杏却不知为何,把甩袖便要去追的深夜抬手拦了一拦。
她眼眶干涩,自己也说不出为何拦着,索性不提,越过昼间深夜两个,探身去看案台。
王公子无声无息的躺在案前地上,脖颈横扭着,背脊也弯了一折,脸色仍青白,脸上孔洞却溢出红来。
而置在案上的山水画,果然已没了踪影。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三万字内序章写完有望……
————————
事已至此,再拖延不得,朱杏便叫王老爷整治一间空屋来,要收得画卷之灵去。
便这屋子,也随意不得,既要南面有窗,好增一增阳气,又要对门无树,免得撞着了煞,最好是左抱右的格局,再指点将屋内铜镜摘了,如此种种,张口便来,王家下人原瞧她年岁小的,这下也再不敢小瞧,只当来了个仙女儿似的厉害人物,他们少爷此般可不就是有救了。
朱杏虽肚子里头有的是货,真个动手的机会却是少,本自己也虚掬着一把汗,一通指派下来,竟也平添几分信心来,定下心还宽慰王老爷,只道:
“只把门窗拢住,不叫见那池子,也不叫见水,必不刺激了她去。令郎君此时无事,我瞧着那灵器当是还能说得通话的。”
与王老爷是这般说,却又偷着将赵衔叫到一边,与他换了一样说辞:“恐灵物难驯,一会子我屋内请画中灵出来说话,赵公子与常公子便莫要进去了罢。”
其实单赵衔进去,倒也还无妨,她心里头想的还是那常山。眼瞧着此人有异,与书本子上头传下来的转世投胎之说有几分相似,却又难以确认,恐常山进去,又有意外祸事,这才劝在门外候着。
朱杏虽不将话挑明,赵衔与常山同窗数年,却很晓得一些事情。
先前那画灵直奔常山而去,是众人都瞧见的,不独此,赵衔还晓得,这常陆之此番险些叫抓花了脸,如何还能这般平静自持,半点不漏出心思来?不过是这样事于他再不是甚么新鲜事情,已是惯了的。
见这厉害的朱姑娘也这般说,赵衔心里头琢磨一回,为着那点子情谊也收了些心思,暗叹一句罢了,转头便去寻了常山。
不知常山去了何处,赵衔也不自家去找,只找了王福贵,劳他亲自走一趟,将常山找了来。
王福贵此时正站着瞪眼。
比着朱杏的要求,王大总管挑挑拣拣,给择出个南面的小院子来,原也不住人,备着招待客人用的。院里还有四五间房,内里摆设一个样,虽不说白玉砖金丝床,也是雕梁画栋,家具摆设一应都是酸枝木黄梨木的。
王福贵只挑一间阳光最足的,指两个小厮里外检查一通,瞧院墙上没得爬山虎,屋里不说铜镜,连个澄澄亮映人影的茶盘子也不留。便是这样,犹还放心不下,又实再没甚可添改的,将小厮都打发远了,只自个儿抄了手在游廊上伸脖子,盼那朱姑娘早些解救了他们少爷去。
赵衔来求,他可不是应得快,站着干等心里头焦灼,有些事做,也好少些胡思乱想,便也不吩咐小厮办,自去找那常山常公子去了。
朱杏进得小院,里头静悄悄无人,几间屋子转一圈,一打眼便见赵衔站在案前,酸枝木缠花案上摆得个收口掐金点翠瓷瓶,因无客,等闲不插花只空摆着,却收拾得干净,一丝儿灰尘也不沾。
瞧见她进门,赵衔便识趣要退,口里只说:“王总管寻陆之兄去了,收拾好的屋子,只等着朱姑娘来。”
说完又觑一眼那画,替那王公子说一两句感念的话,旁的也不多说,转头出了小院。
他出得院子,午后日光正好,照得通身暖洋洋的,王福贵已寻了常山来,一溜小跑的跑回来,急急同他见了礼,又跑起来。
赵衔同常山打一个照面,按着朱杏先前同他说的那般拿话去劝常山在外等候,原还以为定然难以说服,腹稿打了一通,谁料常山竟也不争,显出几分无兴致的模样,听得他说进去要妨碍公务,便不再提要进去的话,只抱着他那些大理寺卷宗,默默站着不说话了。
他锯了嘴沉默了一时,等得一阵,回转过来又朝着赵衔皱眉头,同他说自己的顾虑。
“那张画毕竟出自你手。”
同赵衔这样说,回头去看小院,院门已紧紧关起来,“人若救得,倒不妨事。若出意外,只怕你还要担些干系。”
他心有顾虑,赵衔却不将此事放在心上,闻言只一笑,到底想到王公子生死不定,在王家宅子里,还是将笑淡了去。
“劳陆之兄挂心。”赵三公子话一出口,便见常山那厮把眉一挑,晓得对方定要说些“并不曾挂心”之类不中听的出来,再不给他张口的机会,快口道,“那画中之灵先时见得一遭,若有干系,怎的也不会舍了我扑了你,可见同我是不相干的,便谁要怪,寻此做由头,也站不住脚,再不惧这个。”
还一点他未说,王家是商,赵家是官,再是赵家前些年党争失利,赵老大人依旧是稳稳的占着二品大员的位子,更不必说这几年渐渐复起,王家便是儿子一遭死绝,王老爷也再没得胆子来寻赵家的晦气。
这些话,只不与常山细说,却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赵衔心中坐定,清楚那画中灵怕是个不知道事的,与他攀不上干系,便也不多说,叫他不进院子,就也不进,只同常山一处在外头候着。
他打眼去看那处小院,日光高照着,瞧不出一丝荫翳,院门落了锁,又拿木条子死死栓住,里头半点动静也无,连带着进去守门的王老爷同王福贵也不见声响。
常山等着这边的信儿,心里头还想着前头那见了人就跑的婆子,嘴里就道:“待朱姑娘出来,还是将那余婆子领了来,便她不知道什么,也总要问过才好。”
赵衔眸光微闪,也点点头:“我与你同去。”
又怕常山左性,只一门心思要断清李小姐旧年溺水之谜,反丢了在大理寺好好的前程,有意要与他提一提,只说:“要问倒是无妨,只不能过执,若无结果,便不好一意深究,李氏罪官家眷之身,与之攀扯,只怕惹得上峰不喜。”
常山并不耐烦听这些,却也知赵三一番好意,胡乱点一点头,应一声。
“我省得。不过为公事尽一份心,多问一句罢了。终归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
他一句话方讲完,前边院墙边忽地刮起一阵风,花枝草叶随风摆,倏尔又一道黑红光芒自院中冲天而起,黑风铺天一般从两人面前卷过,猛然扑向天际,立时再不可见了。
过得一息,才听哭号声自小院处传来。
二人便是先时不知出了怎样变故,此时听闻哭声,也知道事情发展不妙,拔腿往院里赶去。常山还只一味急切,跟在他后头的赵衔却略一勾唇角,须臾又放下,再无人瞧见。
他偏头又看一眼黑风扑去的方向,拿扇掩了面眯了眼,心里琢磨了一遍方才常山说的话,倒觉得很是贴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以心谋一回,这可不就是成了么。
————————
赵三:事成最好,不成拉倒。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本来还想着放常陆之进去把水搅得更浑,想想这人进去搞不好要没命,算了算了,还是稳着点。我人都没进去,哪个还能怀疑到我头上,嘻嘻。
终于写完啦!!!
还是超过了3w字,捶地。
赵衔,辣鸡。
——————————————————
天方蒙蒙亮,更夫照旧执了梆子,大街小巷敲过一轮,这些时日,敲更也提心吊胆,盖因近日京中不太平,连连有人在夜色中失了踪迹,夜里巡街的,绕城打更的,连着那早起挑货出来卖的行脚商,都紧起皮来,再不往那人疏的地方去。
这些且同宅子里的大户人家无甚干系,五更天一过,就有大户人家的小厮丫鬟出来开得院门,坐在角门前候着挑豆花的行脚小贩来,饶一碗豆花就站着吃。
簪花巷子里王家在门檐上挂起白绸来,里头扎起棚子,买来白麻纸纱,家中老夫人灵前哭得昏过去,叫下人抬着请郎中来扎了两回金针。
王公子年纪轻轻便去了,虽算不得夭折,不必一口棺材随意葬了去,可以入王家祖坟了,但到底白发人送黑发人,举家上下哭个不住,连着下人也不敢伸头,衣裳换了素色,头上簪了白花,厨上都捡着素食来做,便是原无事的,也叫折腾得丧起了脸,为王公子真情实意的掉下几滴眼泪来。
王老爷置在外头的小妇不声不响,挑着这时候上了门,拉了两个成了人的儿子便哭起灵来,口口声声要自家儿子心疼命不好的弟弟,心里一味的得意,拿帕子掩了口,不叫笑意露出来,王夫人眼里冒火,恨不得提起扁担自将这小妇打出门去,那王老夫人却叫个小妇往地下一跪,在上首一口气儿没喘上,又扎得一回金针,嘴角歪斜,竟瘫了半边中了风。
王公子人没了,对上头报说是叫精怪害了去。大理寺将结果写进卷宗里,便算是了结了一桩事情,卷宗入了库,再没得人多问一声,原也不是甚要紧事情,只常山一个仍紧着眉头,存着几分挂心。
更夫在巷子口歇了脚,便提着铜锣绕去城南。路上遇着个年轻公子,锦衣玉带,沾晨带露,生得面白锦绣,见得更夫也露一丝笑脸,抬手作个揖,惊得麻布衣裳的黑瘦汉子不住往边上让,抚着心口还道:“折煞,折煞。”
定得一口气,又摇头晃脑叹一回贵人好涵养,自家能与这般人见礼,想想也得意起来,一时将同行失踪的祸事都忘了,脚下有劲,提溜着看家的玩意儿,意气十足的一路打更,向南面去了。
那年轻公子却转进小巷里,无人深巷砖墙湿润,红砖间爬着层苔藓,更夫却未瞧见,几块碎砖间胡乱夹着纸片,一截木料支棱出来,听见人声,就有细细声响自底下透出,凭空伸出一条美人玉臂,再往下,半身湿淋淋的落水美人便气若游丝从纸面里探出身子。
“救……救救奴……”
一声呼救细如蚊吟,手却颤颤巍巍伸到人面前了,梨花带雨,眉眼颤颤,好不可怜。
年轻公子却恍若不闻,连着伸到面前的柔荑,都像是没瞧见一般。他既不理会那泣血呼救,也不去拉美人的手,隔了一步站定了,打量几眼,慢条斯理掀了袍角屈下身来。
他拿帕子包了手,才去拎了那根红花梨木画轴,那画灵细细的哭,眼中仍是懵懂,却再与之前不相同,桃花翦水目中血光愈盛,自王家脱出后,她背了王三郎一条性命,再压不住通身戾气,抓了自她跟前过的男人取那一点精元阳气补足自身,这些天下来,又何止害了几条性命。
画灵探了爪儿勾得眼前人衣袍,本体叫他捏在手中,却不若平常,竟生不出反抗加害之意来。她也不知就从那里生出一股子亲切,毫无道理的便孺慕起来,原要将人拖下了水,现也不想了,只小心翼翼勾着这公子的衣袍,温温顺顺低垂了眉眼。
那年轻公子仍是慢条斯理的,将画儿卷起来,还轻弹一弹沾着的泥灰,末了,才看向那做了温顺模样的画灵。
“不过插了柳条,竟真得了树荫。”
他温声笑了一回,还伸手去理一理画灵沾了水湿濡的额发,又拿巾子替她拭了脸,收起画卷,还迈着不疾不徐地步子朝巷子外头走。
外头两个小厮远远跑了来,口里叫着少爷,攀附在那公子肩头的画灵先是目中露出血光,身子猛然绷紧了,叫年轻公子拿眼一瞧,便又软绵下来,不知怎地竟懂了他的心思,自消了自身行迹,把身一扭,还钻进画中去了。
年轻公子便抚了画轴,轻声浅笑,不知是同画灵说,还是同自己道:
“这几日你且饱腹没有?更夫行商,那里好滋味。也不必急,过得这阵子,我便离家带了你寻人去,一个不成,便再换一个,总能替你寻一个‘三郎’的。”又拍一拍画卷,温言温语,“在此之前,且与我去会一位故人罢。”
画卷便似是稚儿般挨着他,嗡嗡一震,再不动弹。
*
王公子的灵棚扎起来,后院的那处小院叫王夫人恨恨拿木条封起,再不愿看那伤心地。
王家上下乱了几日,竟还无人整理那院子,破窗且还破着,案台子地板砖上水已干了,留了大块的水渍,那白瓷瓶许是在混乱中叫人扫了一把,摔在地上碰个粉碎,无人往那屋子走,自然也无人收拾,满地的碎瓷片渣子,下脚且没有地方。
常山隔得几日来,给王家包了一封奠仪,站在小院门口张望一回,求了王福贵暂且拆下门上木条,要了那满地的瓷片碎渣子。
再三问王福贵可有遗漏,又亲眼将屋子全看一遍,不独看这间屋子,还将小院中旁的屋子也看一个来回,这才收了包袱,默不作声出了院子。
赵衔与他相约了今日一同上门来拜,上过了香,还吃得一口灵堂的豆腐宴,瞧见他拎得个油纸包,面上一奇,却不说甚么,常山也不同他多说,拎了一包碎瓷,辞了眼下泛青的王老爷的送,又往大理寺去。
他朝同僚借得了粘土膏子,将散了一地的碎瓷一片片对上口儿拼接起来,拼得最后几片,有个小吏往他跟前探了探头,说前头衙门方又接着一桩案子,瞧情形同您前头跑的王家有关的,常山瞧他一眼,那小吏生得细细长长,似竹竿般,晓得他与大学士沾亲的,弯了腰弓了身子在他面前讨好。
见常山瞧他,便堆个笑脸,凑近了做耳语状,道:
“还是那个王家,听说今儿又死了个婆子,死个下人倒也罢了,偏身上沾了一滩水,现下乱起来,都说是那精怪又回来搅风搅雨呢!”
常山手头一顿,隔了片刻,才回问了一句:“那死了的婆子,可是洒扫的余婆子?”
小吏伸手挠挠头,那里就记得个婆子的名儿了,瞧常山的模样,便一气点头,还故作神秘与常山道:“您瞧着,这里头会不会还有什么隐藏的案情?前头那王公子的案子,是不是暂且不结案,连着这新案……”
话音叫摆手打断了,常山止了他的话头,拿一把大钱给他,算得是个跑腿的辛苦费,却不叫他再说,前头他自个儿对这案子结的不那么满意,现时却又不知为何改了心意,“案子结了便是结了,没什么再深究的。”
他挥退了小吏,瞧着自己手上这最后几片碎瓷,沉着脸将之一一拼上了,可对着拼好的瓷瓶默然半晌,又伸手将之朝地上一砸,稀里哗啦又砸得粉碎,出门叫了小厮,将满地的碎瓷收拾了丢出去。
他自此再不提王家,也不提原还要去寻,现却已没了的余婆子,只把这桩事死死压住,便当从未有过。
可常山自己心里到底是忘不掉的。
小院里房房都在案上摆了个花瓶不假,可也只只落了一层灰,再没那一个里头是盛了水的。
他自王家拿来的那些个碎瓷,拼完整了,细径圆身的瓶儿也还是少了半边的脚,正摆着瞧不出不妥当,可但凡受一点儿摇晃,都必要翻倒下来。
常山叹一口气,只将眼一闭,再不去想着这些了。
第一章
那個人留給我的最初的印象是寬大、溫暖的手掌。然後是,非常溫柔的、好像能給人力量似的眼睛。接著,是明明看起來緊緊抿著,卻相當柔軟的嘴唇。是的,那個人留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但是——眼前的卻不是。
躺在高野明里床上的那個東西,絲毫沒有屬於人類的特征,硬要說其實是昆蟲之類的玩意——不,可能連昆蟲都不是。那蒼白的節肢與腐臭氣味,還有床上溢出來的粘稠的液體,以及被黃色黴菌侵蝕的身體,看起來都像是外面行走的“那些玩意”中的一員。
要說與明里先生相似的就只有……
那雙粉紅色的眼睛。
“明里先生……?”我試探性地向著那怪物問道,對方不置可否地咕噥著,向我的方向湊了過來。
我看到那東西,不由得感到惡心了起來。不,不對,這怎麼可能……那個病,被簡稱為喪尸病的病毒,是不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將人類的軀體改變到那種程度的。我在內心提醒自己,下意識地向後退去。“那隻”見狀,也並沒有追過來。
……
總之先在離開之前找找看明里先生留下來的東西吧。
明里先生的家我來過不下幾百次——之前的房間比起來現在的樣子差的不是一星半點。他明明應該是有條理、擅長收拾房間的類型,但是現在這裡卻……
且不提桌面上髒亂得看不出家具原本的顏色,廁所也被奇異的黴菌覆蓋了半壁,廚房——因為城市的電力供給已經消失,早就不能用了,只剩下一面被油煙染成了棕褐色的玻璃。除了這些外,家具就像是經過了地震一般,有不少已經到了完全不能用的地步。
明里先生生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不對,明里先生還沒有死。
我提醒自己,走向了凌亂的桌面。桌面上的紙筆出奇得亂,明里先生有收集墨水的習慣——其中一罐也已經被打翻了,粘稠的墨水乾涸在桌面上,將其中一張紙完全黏在了桌面上。
我的眼睛不經意掃到了桌子上的那張紙。
那確實是明里先生生前的字跡——但是,比起來他平時寫字所有的那種游刃有餘,這封信的字看起來相當凌亂。我試著將信從桌面上拿起來,但是乾涸的墨水意外的牢固。
再這麼弄下去,說不定會將紙張撕壞……這麼想著,我就放棄了將其從桌面上取下來。反正,放在上面也並不會妨礙閱讀。
“不知道會是誰看到這張紙。
我是高野明里,自由撰稿人。
但是現在,在外出的時候感染了那個病毒,恐怕能保有理智的時間不多了。
我誠摯地希望找到這張紙的人,能將其轉交給我的戀亻夕痛苦
死 要
……”
後面的字跡已經凌亂不堪,根本看不出那是有著一手漂亮字的明里先生所寫。
——那個人最後就是待在這裡,寫下了這封信嗎……那麼……在床上的“那個”……是明里先生的可能性,說不定真的……
咣當。從身後發出來難以讓人忍受的巨響。
我應聲轉過頭去。巨大的白色百足蟲在蠕動著,緩緩向我這邊走過來,似人卻非人的五官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是,我卻感覺到他在注視我。
“明里先生……”
那雙與明里先生無異的粉色雙眼正盯著我看。
我重新為自己整理了一下今天發生的事。隨後,我開始打掃起來明里先生的住處。
明里先生在家裡養了一隻貓,事到如今也不見了。貓都是養不熟的生物,我猜是災難開始之後就跑了吧。我看著空空蕩蕩的貓籠,突然生出了一個想法。
——我費了些將明里先生(?)放進了巨大的籠子中,雖然這樣對他來說很抱歉,但是不這麼做,我也會很危險。
做好這些之後,我開始盤算今後的事。明里先生的住處處在近郊,比起我之前出逃的地方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人口密度少的地方,喪尸的數量也會比較少。這是活下來的倖存者們總結出來的規律。
乾脆就以這裡作為基地,一邊尋找生存下來的方法,一邊為明里先生找變回去的方法吧。一定沒問題的。
首先是周邊的地圖——我按照自己的記憶粗略地畫了畫四周的建築分佈。喪尸們通常喜歡待在一個地方,重複生前的生活規律——如果能夠記錄他們最常去的地點,就能省下不少力氣。
然後是武器——明里先生有打高爾夫球的習慣,我輕而易舉地就在陽台上找到了一根高爾夫球桿。有了這個,能夠很輕易地在喪尸接近之前將對方的頭部集中。
接著就是最重要的問題,明里先生被感染,飲食結構也一定發生了變化。我回憶過去見過的喪尸,幾乎所有喪尸都有想要將人類或是同類的大腦吃掉的慾望。
總之先去試試看吧。我拿著高爾夫球桿,帶好口罩,走出了明里先生的公寓。
除了自己的食物外,我也“打獵”來了明里先生的份。回到明里先生的公寓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了。將那些東西平攤在地板上,細心地切割掉頭部之後,我將其遞給了籠子裡面的明里先生。
真的會吃嗎?我忐忑地看著籠子裡巨大的百足蟲。後者在觀察了一陣放在籠子中的大腦後,磨磨蹭蹭地走了過去。蟲類的口顎部緩慢地抓住喪尸的頭顱,接著快速地吞了下去。幾乎是一瞬間,籠子裡面的喪尸頭顱就不見了。
明里先生變成的蟲露出貪婪的神情,又看向了我這邊——是還想要嗎?我咽了口唾沫,將另一個喪尸的頭顱拋了過去。明里先生又張開他的嘴,將食物盡數吞了進去。無論我將多少東西放進去,明里先生的胃口就好像無底洞,無論餵進去多少,都沒有停歇的意思。
“……你真的是明里先生嗎?”我向籠子中白色的百足蟲問道,對方發出了一串微弱的咕嚕聲。
真是,會向喪尸蟲子問問題,我大概也是寂寞得瘋了吧。
在我餵食過明里先生之後,它很快就陷入了睡眠,靜靜倒在籠子的底部。看到趴在籠底的明里先生,我也決定去好好休息一番,擦洗一下身體。
“晚安,明里先生。”我向明里先生說過晚安之後,磨磨蹭蹭著上了床。
……
將我從夢境中拽出來的是從客廳發出的巨響。拜喪尸潮所賜,我的體質已經變成了無論發出什麼聲音都會馬上清醒的類型。
我抓起身旁的高爾夫球桿,盡力不發出聲音,繞開殘破的家具向著客廳走去。然後,腳不小心踢到了什麼物體。憑藉著我在睡前點燃的人力燈微弱的光線,我看到了……
——那是由鐵絲編制成的籠子的碎片。
明里先生……難道……我驚愕地抬起頭,看向四周,卻在哪裡都沒有看見白色的百足蟲的蹤跡。壞了。我抓緊高爾夫球桿,看向四周。
難道明里先生逃跑了嗎……
就在這時我聽到了從陽台那兒發出來的微弱聲響。我順著聲音的方向,小心翼翼走了過去。
月下,我看到了奇異的景象。百足蟲盤踞在陽台的一角,然後從表皮開始碎裂,每一次的碎裂都會迸發出濃稠膽汁似的液體。就這樣,過了不知多久,已經膨脹起來的百足蟲徹底碎裂開了。
然後從裡面露出來的是,奇異的怪獸——那簡直就是將人類的頭顱鑲嵌在有著堅硬外骨骼的昆蟲上一樣。那頭顱——並不是我記憶中的明里先生,倒不如說像是高中時生物教室裡面擺放的肌肉人檯般赤裸,能夠輕鬆地看見表面的肌理。
“那個,明里先生……”
對方好像聽見了我的話,扭過頭來。
果然是明里先生嗎。
我的手松下緊握著的武器,不知為何感到倦怠。明里先生只是冷漠地轉動那雙渾濁的粉色眼睛,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我。
“我做的一切,真的是有意義的嗎……”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得到答案,我向對方問道。雖然,我並沒有在期待明里先生能夠答話。
出乎意料的是,明里先生蒼白的嘴唇翁動著,重複了起來:“意、義……”
難道他能聽懂我的話嗎?我吃驚地看向對方,試探性地繼續問道:“能再說一遍嗎,明里先生……?”
“說……紅色……”
“明里先生還記得我嗎……?”
“記、……”
“明里先生喜歡貓咪嗎?”
“喜歡、貓。”
“明里先生的家人呢?”
“家人……”
雖然沒有明確的回答,但他確實是在對我所說的話起反應。究竟是為什麼——是因為我來了,還是因為我餵食給他了同類的大腦呢?無論是哪個原因,結果都很令人意外。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暗示自己快些鎮定下來。隨後,收拾起來明里先生造成的殘局。明里先生既沒有攻擊我,也沒有走近,只是繼續待在陽台上,用那粉紅色的眼睛沖我投來冷漠的一瞥。
沒關係的,我想著。只要繼續這麼下去,明里先生他一定可以回來的。既然已經能夠確認餵食同類的方法有效,明天一定能有新的進展。
想到這點,我不忍對著粗略繪製的地圖露出笑容。
第二天早上,我在收拾好房間之後出了公寓。最先決定去的地方是超市。
儘管明里先生住的地方是近郊,但這裡的超市也已經像別處一樣,沒有食物可以掃蕩了。雖然還有少數狗糧之類的貨品擺放在貨架上,但這總不能說是一個好選擇。
就這樣,我開始了今天的狩獵。
說到底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那個時候我放開了明里先生的手的緣故——沒錯,一定是這樣。
那已經是喪尸潮剛剛開始時發生的事了。
我和明里先生在職場上是作家和編輯的關係,因此除卻日常來往外,也有相當分量的工作交流。那天晚上,我的提議被明里先生拒絕了。本來也是普通的小事,但是不知道怎麼就變成了不合的開端。或許是因為之前積壓的不合沒能得到解決吧,平日溫和的他因為這樣的小事生氣了。
在爭吵之後,他甩開了我的手。我呢?因為生悶氣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沒有再聯繫明里先生。等到意識過來時,整個城市都陷落於喪尸潮中。
明裡先生的變化也很大,現在已經從百足蟲變成了形如人面蜘蛛的喪尸。不過,比起他原本的個性,現在的他只是不停地重複我們的回話的復讀機而已。既然籠子已經放不下他,我只好將他放在他的臥室內。
我也對喪尸的捕獵越來越得心應手。根據積累下來的經驗,我發現廣場的角落似乎最容易聚集起來喪屍。其餘的地方則包括老年中心的街角和學校。喪尸們日復一日的重複著自己生前的行徑,究竟是還有過去的思維呢,還是只是像本能一樣進行一日循環。
無論答案是什麼,都已經不重要了。
而市郊這片區域暴民們所佔領的地方,則在超市的樓頂上方——那些人有槍,所以我通常避開那裡行動。至於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武器,或是他們以前的身份,我都一概不知道。
說完這些,說說明裡先生現在喜歡吃的食物吧。明裡先生比起女性喪屍的頭,似乎更喜歡吃男性的大腦一些。明裡先生在過去就是吃炸雞咖喱的時候把炸雞留到最後一口的人,根據我的觀察,他總是把男性的頭顱放到最後再吃。
大概這也像每天去老年中心和學校的那些喪尸的所作所為一樣,是生前遺留下來的習慣吧——不知出於何種自信,我相信眼前的“怪物”就是明里先生。或許是那些讓人無法不去在意的細節吧——他的眼睛、還有那些習慣,他偶爾停駐在窗前、神情裡匆匆掃過的思緒,都讓我更加確定他就是明里先生。
如果他不是的話,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注視著正在進食的明里先生。
現在,明里先生的外表又變化了一些。雖然總體而言還是像人類的頭顱嫁接在蜘蛛身上,但是被堅硬的白色外骨骼所覆蓋的區域又減少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如同攏聚的肉瘤一般崎嶇不平的鮮紅色肢體。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好事,但是每次餵食後明里先生的脊椎都會伸長,隨著時間的發展已經慢慢長出了人類男性的胸腔。
“明里先生?今天的感覺怎麼樣?”我將為他捕獵來的肉食放在地板上。
“明里……還好……”
“我白天的時候一直不在家,讓你寂寞了,非常抱歉。”我看著明里先生抽動他那八條被肉瘤所覆蓋的腿,緩慢地移動再猛地扎下去啃咬人腦的模樣。這景象有些駭人,可是自從明里先生變成現在這幅樣子之後,他就再也沒有顯露出要攻擊我的意圖。
果然,他就是明里先生吧。
“寂寞……唔……”
“是哦,寂寞……對了,明里先生以前很喜歡讀書呢,雖然現在這樣子要讀書有些勉強,不過,我來講講看故事吧……”
“故、事……”
“——明里先生以前講過的故事,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故事是這樣的:一個患有恐男癥的女性……”我回憶著明里先生講述故事時的神情、他的聲音和他的動作,明明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卻好像才在昨日發生那般鮮明。
明里先生靜靜地聽著,非人的眼睛似懂非懂。他的嘴邊還殘留著晚餐的碎屑,我便將那些東西輕輕刮了下來。明里先生並沒有要咬我的手的意思,只是伸出來勾狀的舌頭,輕輕舔舐起來我的手指。
“不行哦,這樣會感染的。”我抽回了手指,摸了摸明里先生的頭。明里先生被我的動作嚇到,縮回了墻角。
簡直是讓人聯想到小動物的模樣。
“真是的,別害怕啊……反倒是我應該害怕吧?”我向著明里先生說道。
明里先生好像要拒絕我似的,搖了搖頭。
“真討厭……”我為自己整理了明里先生的床,不過,現在我還沒有要在對方的床上入睡的打算。將臥室再收拾了一邊之後,我把臥室的門鎖上,回到了客廳休息。
躺在已經褪色的沙發上時我才想起來。今天忘了說晚安。
明明以前明里先生沒有對我說晚安,我是會對他生氣的,到了現在,反而是我不會對明里先生說“晚安”了嗎?……或許是我太累了吧。
抱著那份獨屬於自我的焦慮,我睡了過去。
做了奇怪的夢。
夢中的明里先生被割裂成了好幾片,過去的樣子,怪物的樣子,還有其他的模樣,每一片都不同,每一片都是他,每一片都在叫著我的名字。但是,夢中的我清楚,無論哪一片都不是真正的明里先生。不是的,明里先生不是這樣的,他應該是——
更加,完美的。
名為高野明里的那個男人在我的觸摸下化成了碎片。
更加,溫柔的。
第一次見到的明里先生是戴著眼鏡還是不戴眼鏡呢?
更加,可愛的。
眼前又出現了舔著我的手,被我叫做明里先生的怪物。
哪個都不是明里先生,哪個都不是明里先生,明里先生,明里先生,明里先生,明里明里明里明里明里明里明里——
從胸口傳來的是被重物擠壓的窒息感,鼻腔裡則滿是腐臭的氣味。越來越多的明里先生將我壓碎。我明白的,我明白的——
將我喚醒的是胸口異常的疼痛,隨後我看到的是既不是人類也不是明里先生的某物。
喪尸……!
我掙扎著想要站起身來,高爾夫球桿在我睡覺前被放在茶几上——可惡,明明只有那麼短的距離,我卻夠不到。我試著將對方從自己身上推下去,但是,對方的體重比想象的要重,不能憑藉我的動作甩下來。
那隻喪尸不停地滴下唾液似粘稠的液體,濁黃色的眼睛盯著我看。
再這麼下去會被感染……果然已經不行了嗎,掙扎到這個地步,還是難逃一死。這樣的話……
明里先生,真的很抱歉……
就在我決定放棄的時候,從臥室的方向傳來的聲音將我們兩個的注意力同時吸引了過去。出現在眼前的是粉紅色雙眼、形如蜘蛛的明里先生。他冷漠地掃視了一眼我們,好像在看什麼事不關己的風景似的。
果然明里先生已經不是生前的明里先生了嗎,比起我,他會選擇眼前的同類吧?還是說,我們倆都不具備提起他興趣的要素呢,那個明里先生,會放任我被吃掉吧?
我放棄了繼續思考,閉上了雙眼。
然後,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被劇烈的物體運動所打斷,我不得不看清眼前的現實——明里先生跳上沙發,咬向了同類的咽喉,接著,他以人類無法想象的氣力扭斷了那名喪尸的脖子。已死之人脆弱的脖頸如同筷子那般被輕鬆折斷,隨後,從那具喪尸的軀體中噴濺出了大量污濁而腥臭的血液。
——這具尸體的模樣我認識,那是每次來明里先生家都會打上一句招呼的管理員太太。
明里先生撲向已經不動的尸體大快朵頤。我則矗立在遠地。
我被明里先生救了。這一定是因為他聽到了那個時候的聲音,從臥室裡趕了出來吧——我走近臥室門前,看到門鎖已經被破壞了,似乎是被明里先生撞開的。在夜裡,我除了被襲擊時並沒有聽到什麼特別的聲音——難道明里先生是在那時直接撞開門從裡面出來的嗎?
明里先生沒有受傷吧……我回過頭去,看向剛剛吃過了夜宵的明里先生。人面蜘蛛百無聊賴地躺在地板上,一點聲音都不發。因為他四肢顏色的關係,有些難檢查清楚她酒精有沒有受傷,不過看起來似乎並無大礙。
比起明里先生,更可能出問題的是我。
雖然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任何受傷的痕跡,但病毒也可能通過體液傳播——管理員太太不停地漏出體液,我說不定已經在不知道的時候被感染了。
或許到不了天亮,我也會感染病毒,變成喪尸。
“明里先生……”
明里先生並沒有回應我。說到底,就算我變成喪尸,現在的明里先生大概也不會在乎吧。不過,到了這種時候,之前的隔離反而沒有任何用處了。比起明里先生,我竟然是被完全不熟的人感染的……究竟之前在幹什麼呢,我?我自嘲地笑了笑,從後方抱住了明里先生。
明里先生大概是因為困惑而發出微弱的聲音。
“可以和你一起睡覺嗎,明里先生?”我輕輕問道,明里先生並沒有回答,我將那個當做是默許,牽著明里先生那未能發育出的人手,回到了臥室。
之前覺得髒兮兮的床鋪,到了現在也沒有再去在意污垢的必要,反而如同柔軟的搖籃一邊讓人安心。我維持著拉著明里先生手的姿勢躺了下去。明里先生起初想要離開,但是很快就安分了下來。
“明里先生記得自己第一次和我見面的時候,是戴眼鏡還是沒戴眼鏡嗎?”我看著被粉紅色黏菌所覆蓋的天花板。心情意外的平靜了下來。明里先生是回答也好,不回答也罷,也已經沒問題了。
“明里先生呢,之前就想問問看了,以後想要一起住嗎?”
指尖觸摸到了明里先生柔軟的、章魚般的腿部。
“一起住、好。”明里先生模糊地回答道。
“這樣就算結婚了吧……呵呵,一起住的話,明里先生喜歡貓,我卻有鼻炎,大概只能忍著了吧。明里先生呢?會想要孩子嗎?我不是很擅長應付孩子,但是如果是和明里先生很相似的孩子我倒是也沒有問題……”
真討厭,越說越停不下來了。
“孩子……”
“明里先生喜歡孩子的吧?”
“不喜歡……”
“那就不需要了,只有我們兩個,還有小茶(貓的名字)……一起住在這裡,好好地活下去……”
“你、休息。”
“在催我睡覺嗎?真是,明明平常都是反過來,也不早了,確實是該睡覺了……”儘管再次醒來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是我了。我死去之後,明里先生會吃到我媽?還是成為同類呢?不論哪個是答案,那都是明天才需要考慮的事情了。
我不知為何,重新有了說晚安的餘裕。
明里先生有些驚訝地看向了我。
“晚、安……”
“嗯,晚安。”我輕撫著明里先生被肉藤覆蓋的四肢,合上了雙眼,期許自己能做個好夢。
……
粗糙而滾燙的什麼東西摩挲著我的臉頰,那東西的觸感和體積喚醒了我。睜開眼,我被淺灰色的什麼東西佔據了視野,那東西輕柔地蹭著我的脖子,繼續用粗糙的舌頭舔我的臉。
是明里先生。
“別這樣啦……好癢,你是貓咪嗎……”我嘟囔著推開明里先生的身體,緊接著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像想象的那樣成為喪尸,“放開我……”明里先生好像很委屈的樣子,但是並沒有說什麼話,只是磨蹭了一會兒爬下了床鋪。
我並沒有變成喪尸,而是繼續這樣以人類的形態活了下來嗎……我看向放在角落裡表面斑駁的鏡子,裡面的倒影與我平常的樣子無異——無論是雙眼還是皮膚,都並沒有受到感染的跡象。
明里先生擺動著蜘蛛似的肢體,好像要安慰我一樣爬了過來。他用那雙過短、未能發育為成人手臂的畸形肩膀碰了碰我的臉。
“怎麼了……要去吃早餐嗎?”我抱著不知什麼心情,開起了玩笑。
第一縷朝陽輕柔地穿過窗幔,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