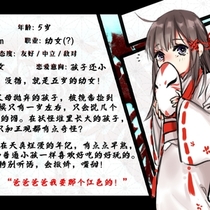被摩西一个广告惊醒。
从论文的海洋里翻身爬出来填坑。
总字数:8221
感谢各位和我互动,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请联系我修改!
最后是一个寝室内部梗,据说没有舞伴就要内部竞技决出人选穿女装跳女步,just搞笑一下不要当真(……
小少爷戏份不多就不响应打扰啦,以及时间不够了无情的删掉了几个好室友的戏份,但你们要知道我还是爱你们的。真真的。
昏头昏脑复健,生死时速和死线竞走文。质量堪忧。慎入。(我回去写论文啦——)
————————————————
普拉瑞斯曾经许多次设想过,当他真的成为霍格沃兹的一员,当他站在所有人面前将分院帽戴在脑袋上,那一刻他到底应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才能够让那顶从不沐浴的魔法帽子能够好好的看清他身上那些自认为属于斯莱特林的好品质。
或许帽子会劝说他,说他的勇气足以去格莱芬多,或者他的智慧也可以成为一个拉文克劳……不,没有赫奇帕奇,不要赫奇帕奇。普拉瑞斯从小就听格莱芬多毕业的母亲大加赞赏赫奇那些愉快的学生们,那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学院,但是他很确定自己一点儿也不适合那里。不管怎么说,他都要坚持住自己的想法——普拉瑞斯是那样想成为一个斯莱特林。
没错。普拉瑞斯在心中默默想道,他自然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斯莱特林,就像是他的父亲一样。
诺斯家今代的家主人,普拉瑞斯的父亲正是一个沉稳而内敛的斯莱特林。他的体格算不上很强健,举止言行却充满力量,那种掌控全局时才会有的自信与气魄令他的独子向往而为之折服,年幼的男孩子天生对于强者的向往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寄托,在普拉瑞斯比现在还要更加年幼的时候,曾抱着母亲的膝盖满怀憧憬的说,“我以后也要像父亲那样。”
奥罗精英啧了一声,捏着幼子的脸蛋纠正这个美好的憧憬:“说错啦,小北极星以后要和妈妈一样做奥罗才对呀。”
她的小北极星鼓着脸,将脑袋埋进她的膝头,用行动表示对母亲这段话的拒绝之意。
而现在,在霍格沃兹大礼堂仿制星空的高顶天穹之下,在四个学院泱泱百人的视线注视下,普拉瑞斯举着比他脑袋要大出一大圈的分院帽往自己的头上戴,突然间意识到,或许想要成为一个斯莱特林,并没有自己过去曾想象的那样难。
他撑着帽子的手还未放下,一个声音就仿佛在他的耳畔突然尖声大叫,那刺耳的声音穿脑而过,两面回响,普拉瑞斯一时脑中嗡嗡,鼓膜作痛,他提醒自己这是严肃的分院仪式,这才强忍着没有立刻把帽子给摘下来。
然后他这才反应过来,刚刚分院帽在沾到他脑袋之后立刻大叫的那个单词到底是什么。
“Slytherin——!”
没有考核,没有评定,没有“孩子我能从你的脑海中看见智慧闪光,真的不考虑去拉文克劳?”,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在走上台不足十秒钟之后,普拉瑞斯·诺斯如愿以偿又似乎怅然若失,带着他那头和周围众人飞速融合打成一片的闪耀金发,坐进了斯莱特林的队伍之中。
*
这个开局算起来其实应该是完美的。
如愿以偿,进入了父亲曾所属的学院,除了先前紧张的心理斗争,和开学前的种种自我展示的准备全部白费令人颇感失落之外,对于这个结果,普拉瑞斯心中没有任何不满。
他坐在斯莱特林的长桌上,周围是用低调而又显得贵气的银绿色装点校袍的学长和学姐们,那些高年级斯莱特林们看起来每一个都气势迫人,那是一种在普拉瑞斯看来同自己的父亲有些相似,让人向往的气势。
斯莱特林的一年级新生因此而感到兴奋不已。他竭力压制住这种飘飘然的感觉,面颊却还是不由自主的红了起来,两眼止不住的发光,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学姐看了脸蛋红扑扑的新生一眼,伸手替普拉瑞斯取了一杯南瓜汁,她一直微扬着下巴,显得矜持而高傲,对待新生时手上的动作却可称得上是轻缓柔和,普拉瑞斯微红着脸同金发的学姐道谢。
新生分院结束,校长站起身开始说晚餐前的最后几句祝词。普拉瑞斯直到这时才有心思观察霍格沃兹这一任的校长,对方出乎他意料的年轻,并且是一个体态端庄、气质柔和厚重的女人——这样说,倒不是他在性别上有什么差别思想,只是,你看,不管是不是出自巫师家庭,或许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都曾经幻想有那么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胡子老头,会从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的奇妙糖果,还会变出各种奇妙的小法术。
那个形象或者睿智或者狡黠,但不管怎么说,那就是魔法的标志,是一扇新的大门的领路人……而现在,这个曾模糊存在于普拉瑞斯心中的领路人的形象,已然被眼前的校长艾玛·怀特的身影所取代,女巫师在面对她的学生们时,笑容满溢着慈爱,普拉瑞斯甚至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别开视线,将目光转投到隔壁赫奇帕奇的长桌上。
在那里,露易丝·坎贝尔坐在一群赫奇帕奇之间,那张餐桌上热热闹闹,南瓜派和火鸡腿在学生们的脑袋上方飞来飞去,露易丝不知和人说着什么话题,正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脑袋上蓝色的缎带前后摇晃。
普拉瑞斯瞪视了她一会,对方却始终没有注意到他。这让他不禁颇感无趣,心中意念狠狠的叫了几遍对方的全名,坐在黄褐色獾院长桌上的人始终和周围的人一起吱咯乱笑,没有半点接受到讯号的意思,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召唤小伙伴的注意力这个念头。
坐在他另一边的一个男生用手肘抵了抵他的胳膊。
“嚯哟,刚入学就关注起隔壁的小姑娘啦。”那男生看起来并不比普拉瑞斯要大多少,淡色偏灰的的短发不是很服帖的支棱着,他轻浮地吹了声口哨,又推了一下普拉瑞斯的胳膊,像是在赞赏他一样说道,“动作很快,不错嘛!”
在普拉瑞斯回话之前,另一边的学姐倒是在听到这段话之后颦起眉头,多少带有一些责备地低喝了一声:“注意场合和用词,洛佩兹。”
男生装模作样的做了一个道歉的动作,面上还带笑,显而易见并不当做一回事,他朝普拉瑞斯眨了眨眼睛,“洛佩兹。伊莱·洛佩兹,二年级。……麦克唐纳学姐越来越凶啦,我家的姐姐也这样,凶得很。嗨,现在的姑娘们啊。”
“越来越凶”的麦克唐纳学姐又瞪了他一眼。普拉瑞斯注视着满脸不在乎的洛佩兹,心目中那些有关于沉着冷静强大骄傲的斯莱特林形象默默的崩坏了一角,他一时语塞,只好通过给自己捞鱼块和鹰嘴豆来掩饰。
餐桌上此时已经被各色英国美食占领,在喧闹的大礼堂中,只有斯莱特林的长桌多少还保持了一个算是有序的音量,没有显得太过吵闹。
普拉瑞斯又给自己舀了一勺肉馅派,对于露易丝被轻率的拿来打趣这件事,他心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因而沉默了许久,这才顺着方才伊莱·洛佩兹的自报家门,对着长桌自己身边的几个学生做起自我介绍来。
他努力压住自己的语调,模仿几位高年级学生的样子,试图表现出一些处变不惊的特质来,但这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毕竟还是太过于难了,因此在报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剩下的一些像是炫耀的话从他嘴里滑出,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普拉瑞斯·诺斯,能被分到斯莱特林真让人高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毕业的!”
这话令在场的好几个学生都忍不住露出了微笑。父母双方之一是斯莱特林——或者干脆双方都是,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在这方面都拥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看着这个脸颊泛红,还要强作镇定的小男孩,纷纷表示非常能够理解,并且也非常……想要使坏。
有句古话说,新生是霍格沃兹的宝藏——什么你说并没有这句古话?不,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座的每一个学生,都曾经经历过新生这个阶段,不论现在的他们已经是如何的意气风发气势十足,新生在他们的学长学姐眼中,永远是不折不扣的小可爱。
人一旦可爱,就很容易被使坏。
普拉瑞斯忽然觉得背后有些发毛,却又找不到缘由,不禁茫然四顾。
周围的学长学姐纷纷表示:什么都没有,小小年纪不要想太多。
刚刚结束自己的新生时期,顺利升上二年级,迎来了新一批小可爱的伊莱·洛佩兹左右看看,自来熟地拍了拍普拉瑞斯的肩膀,朝他露出了一个混合着心照不宣和幸灾乐祸的古怪笑容。
“加油啊,小北极星。”
他说完,张扬的大笑着从普拉瑞斯的餐盘中截走了对方刚取来的糖浆布丁,美美的咬了一大口。
*
普拉瑞斯很快就明白了洛佩兹的言下之意。
在晚餐时,所有的新生显然都受到了来自学长学姐们的额外照顾,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吃下了超出正常食量的食物,一些性格不太坦率的孩子更是备受青睐。
被抢走了糖浆布丁的普拉瑞斯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坐在对面的一位学姐挥动魔杖,将另一边的几盘蛋糕移到了他的眼前,而在男孩满脸通红的强调“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吃甜食”“蛋糕什么的一点也不男子汉”之后,几乎餐桌上有的每一种甜点,都伺机出现在了他的餐盘里。
他在前辈们‘关爱’的注视下,硬着头皮将这些东西都吃了下去。
……好吃。但男子汉的尊严使他倔强,拒绝承认。
麦克唐纳学姐给每个新生发了一些药片,在吃下去之后,腹胀的感觉顿时减轻了许多。这些吃撑了的小家伙们排成一排,跟在几个级长身后被带往位于地下地牢深处的斯莱特林休息室,一路上没有人说话,霍格沃兹城堡内部的装饰令众人看得目不暇接,直到报出口令,带领他们穿过狭长、低矮的过道,前方的级长们这才停了下来。
展现在普拉瑞斯眼前的是这样一种场景:
由石头垒砌的四壁,表面有微微的水痕,泛着绿光的圆球从上方垂下,高高低低漂浮在众人头顶上方,中央摆放着一些皮革座椅,正对着座椅的那一面墙壁镶嵌一座暖炉,燃烧着的炉火是幽静的碧绿色,在暖炉之上,是一整排装饰着反复雕饰的玻璃窗。
普拉瑞斯隐约看见一道黑影自窗外划过,他紧盯着外头那种混沌不清的景色,惊讶的发现他所看见的黑影,竟然是一条章鱼巨大的触角,微微卷动着在窗外摇晃。
斯莱特林的休息室竟然是建在黑湖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普拉瑞斯竟觉得,自己脚下的地面,似乎也开始随着水流摇晃起来。
他心中雀跃,聚精会神的听级长们宣读一些注意事项——这个部分结束得很快,斯莱特林似乎并不打算搞什么煽情的新生欢迎会,高年级们只是丢出一本斯莱特林守则,简短的告知新生们,“以斯莱特林为豪,你们的身份为豪。如果做出违背身份的事,要么聪明些别被发现,要么做好承担责任接受惩罚的准备。”
虽然简短,但是对于新生们来说,确实是极为有煽动力的一番发言。今年的男学生会主席出自斯莱特林,当他面对新生们说出这些话时,他同身边那些高年级们面上自信而又高傲的神情,令自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显得格外有力。
普拉瑞斯注意到,站在主席身边的高年级男生之中,有一个有些熟悉的面孔,他隐约记得自己在特快列车上曾险些和对方正面相撞,并且没有来得及道歉,就被露易丝拉走。这个高年级的斯莱特林看起来并不和善,普拉瑞斯希望对方并不记得这件事,以免因此而对他——或者露易丝——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我很愿意提醒你们。”
男学生会主席麦克唐纳说道,他是五年级的女级长卡蒂·麦克唐纳的亲兄弟,“在你们接下来的求学旅程中,你们会逐渐了解到,在霍格沃兹不仅会有充实的学业,还会有更加充实的社交活动。”
“比如说……”他朝新生们眨了眨眼,满意的看到这群小家伙充满期待的骚动起来,才接着说道,“下个月会举办的万圣节晚会,我想这会是你们在来到霍格沃兹之后,第一个尝试自己邀请舞伴参加的舞会。”
麦克唐纳提出了一个让人期待的活动。
但是对于舞伴这件事,显然一年级的学生们的反应不如高年级的学生们要来得热烈。
一个高年级男生耸了耸肩,拍了拍身边另一个男生的肩膀:“我们院女生太少了……如果今年邀请不到女孩子,那就只好和这家伙打一架,输的人女装跳女步了。”
被他勾住肩膀的男生跳了起来,一把将他推开,从鼻腔中发出了一声完美的嗤笑,“少做梦了,我可是有女朋友的。”
他随即被一边数个红眼的单身汉拖走,一路上传出类似惨叫的打闹声。
麦克唐纳也耸了耸肩,给有些傻眼的新生们提出建议:“我们院内部女生太少,有机会的话最好能把其他学院的姑娘们带回来……嗯?不明白我的意思?没关系,再过几年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大概就能明白了。”
他说得意味深长。
普拉瑞斯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知道自己心中的斯莱特林形象又崩塌了不少。
学长们……似乎在外面的表现和进了休息室之后的表现……有些不一样……
他多少有些麻木的这样想着,在一群开始热切讨论舞会舞伴问题的高年级生中间,和其他许多新生一样,感到不知所措,瑟瑟发抖。
麦克唐纳学姐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她没有参与这个话题,而是拿了一本书,坐在了一盏铃兰形状的小吊灯旁。普拉瑞斯心中的无措因为她的表现而有了一些缓解,他开始放空脑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最先想到晚上要给家里写信,告之父母他顺利进入斯莱特林这个好消息,这里和他想象的一样棒(呃……大概是吧)。然后他又想到被分在赫奇帕奇的露易丝,对方晚餐时对他的无视令他很不开心,但他还是会大度的原谅她,没有办法,露易丝就是那种粗枝大叶冲动又莽撞的人,真的怀疑她为什么没有被分到格莱芬多,不过赫奇帕奇也不差,他记得露易丝一直憧憬进入赫奇帕奇。就和他自己想要进斯莱特林一样。
然后周围杂乱的信息中有一条进入他的脑海:万圣节晚会。为什么晚会一定要有舞伴不可呢?过去的万圣节,他们都会被默许去问大人们讨要糖果,露易丝还会特地准备一份糖果给他,那个蜂糖花火的味道真是不赖……但是这些都同舞会和舞伴没什么关系,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跳舞,露易丝总是踩到他的脚,并且把他的手拉得生疼。舞会似乎并没有哪里特别吸引他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不能够都像麦克唐纳学姐那样保持冷静呢。普拉瑞斯偷偷看了一眼似乎正在沉心阅读的学姐,在心里这样想。
然后他注意到那个在列车上曾遇到过的学长不知何时起坐在了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对方有一头同周围许多学生一样值得夸耀的金发,一双绿眼睛让人觉得锋利且冷酷。他看上去就像是对于万圣节这种话题半点也不感兴趣的那一类人,他坐在对面,让新生不免觉得有些拘谨,普拉瑞斯正在犹豫是不是该整理一下头发或者衣襟来缓和一下这种拘束,就听到对面的学长毫无预兆的开了口。他的声音有一种同他整个人一样的冷肃感。
但是普拉瑞斯却听到他说:
“麦克唐纳小姐,您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
普拉瑞斯猛地抬起头,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对面的学长仍旧是那一副对舞会毫无关注的冷漠模样,但这一次普拉瑞斯注意到,对方其实从头到尾都只将视线放在了他身边的女级长身上。
接着,他看到仿佛在认真读书的麦克唐纳学姐迅速抬起头,毫不吝啬的露出了一个不是很矜持,一点也不高傲的灿烂笑容,没什么犹豫的点了点头。
“好啊。”
“……”
普拉瑞斯默默站了起来。默默退到了一边。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合坐在那里。
到这一刻,这个满怀憧憬的斯莱特林新生终于艰难的说服自己承认了一件事:
斯莱特林……这个斯莱特林似乎和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
“普拉瑞斯·诺斯来到霍格沃兹的第一天,就这样顺利又完美的结束了。”
“……你这句话,是在说给谁听??”
“说给我自己听。”
普拉瑞斯板着脸,回头去看阿莫米安,“我在试图说服我自己。”他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补充,“……现在立刻乖乖回休息室,不要自找麻烦。”
“然后你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在往休息室的反方向走!而且就快要宵禁了!”
阿莫米安有些烦躁的抓了抓自己红色的长发,眼神开始因为不耐烦而显得很有攻击性,“我可是要回去了,我才不想刚开学就因为晚上乱晃被抓——”
他朝普拉诺丝龇牙咧嘴,露出两颗尖锐的虎牙。阿尔伯特·吉恩·阿莫米安同样是今年斯莱特林的新生,两人在来时的小木船上曾有一面之缘,或许在今后,他们会成为关系不错的好友,但显然目前他们之间现在甚至还称不上认识。
阿莫米安说着,就停下了脚步。
“我要回去了。”他说,面上闪过一丝犹豫,很快又被不满和骄躁遮掩,“如果你今晚因为在城堡里迷路而被扣了分,可别指望我帮你隐瞒。”
普拉瑞斯很不能接受他这样毫无根据的假设,反驳道:“我不会的,我会在宵禁之前回来!”
红发男孩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他往回跑了两步,忍不住又停下来提醒对方:“不管你要去哪——离宵禁不剩多少时间了——”
普拉瑞斯深吸了一口气,“……你说得对。”
他扭头奔跑起来。
十分钟后,斯莱特林新生停在了地下一楼一副巨大的水果画像旁,对着画像上巨大的苹果、香蕉、葡萄和梨,普拉瑞斯终于注意到自己犯下的一个可怕的错误。
虽然他曾听家人说起过霍格沃兹厨房的入口在地下的水果画像处,而赫奇帕奇的休息室离此地不远,可是这附近——怎么看也不像是有休息室入口的样子啊!
这是一条空空荡荡的走廊,墙壁上装饰着好几幅巨大的挂画,在尽头的转角处,一些用途不明的圆木桶被随意对方在角落里,除了木桶的尺寸较寻常要大一些之外,不论哪里都看不出有些什么特别之处。
普拉瑞斯抬起手来去摸那副水果画像,发现自己只能摸到最下方的葡萄,踮起脚的话,勉强还能够得到再上面一些的梨。但是这个发现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毫无帮助,他开始后悔起来,或许他的确不应该在没有弄清地点的情况下贸然离开休息室,或许他应该提前写一封便条,让学校的猫头鹰帮忙送信。
最关键的是,露易丝在赫奇帕奇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吗?她那样开朗,赫奇帕奇人据说又一向很好相处,他来找她干什么呢?看看她第一天住校会不会不适应?看她晚餐时的样子吧,她哪有半点不适应!
但是他离开休息室的时候没有功夫想那么多。普拉瑞斯有些沮丧的靠在木桶上,心烦意乱的胡乱敲击木桶盖子,“咚咚咚”的敲击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回响。他只是在学长学姐之间坐卧难安,昏头昏脑的跑出来,阿莫米安试图拦住他,但是没能成功,然后……
普拉瑞斯叹了口气。哪有什么然后,他连赫奇帕奇的休息室入口都找不到。
他赌气又用力敲了一下木桶,然后猝不及防被从桶里喷射出来的什么东西喷了满头满脸。那似乎是一种香醋,带着呛鼻子的酸味,木桶朝他“呸呸”像是吐口水一样吐出最后几滴醋,桶盖静悄悄的又合上了。
斯莱特林新生被这突如其来的,来自一只木桶的报复行为喷个正着,愣在原地回不过神。
在他身后,有人大笑出声。
普拉瑞斯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那样猛地跳起来回过身,只见一个穿着黄褐色滚边校袍的赫奇帕奇高年级靠在墙边弯腰大笑,注意到他的反应,对方轻咳了两声,努力止住笑意朝他摆了摆手。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会说出去的。”
赫奇帕奇男生生了一张娃娃脸,面颊边只有一小缕头发是淡蓝色,作为特征来说十分醒目。他想伸手拍一拍普拉瑞斯的脑袋,但被男孩后退一步躲开了,他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好脾气的朝他笑。
“你是新生吧?”他问,也不等普拉瑞斯回答,自顾自的说下去,“没记住开门方法?不用担心,时间久了就记住了,我们赫奇帕奇的新生难免都是要被醋喷个几回的嘛,今天我带你进去好了,下次要记住——咦,等一下。”
男生突然止住话头,似乎终于意识到有哪里不对劲似的,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男孩。
然后他露出了一个有点难以言喻的复杂表情。
他面带纠结:“金发,小少爷,板着脸,不太可爱……这么明显的特征……等一等,你该不会不是我们院的新生吧?”
普拉瑞斯:“……”他什么时候有说话的机会了。
*
不幸暴露身份被证实不是赫奇帕奇新生的普拉瑞斯失去了一个大摇大摆走进赫奇帕奇休息室的机会。
“我倒也不介意带你进去。”那名险些错把一条蛇带进獾窝的学长这样同他说,“但是马上就要宵禁了,再不回去我就不得不扣你的分数了。”
他展示自己的级长徽章给普拉瑞斯看,普拉瑞斯顿时对霍格沃兹对于的级长的选择产生了一丝质疑。
受到质疑的赫奇帕奇级长负责任的提着他的衣领将他送回斯莱特林休息室门口,在知道他是其他学院的学生之后,这位学长亲和的态度倒是没有改变,站在斯莱特林休息室门口,笑容灿烂的目送他走进休息室,一边还招手:
“我是摩西·格林,小学弟下次看好时间再来玩呀——”
随即他就被几个高年级斯莱特林抬起架走,从他们离开的方向传来了一些诸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要抓我们的小蛇去煲蛇羹”“摩西你们的鸡养得怎么样了”之类意义不明的对话。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赫奇帕奇要养鸡,但普拉瑞斯还是下意识的对蛇羹二字打了个冷颤。
接近就寝时间,休息室只有寥寥数人聚在炉火前写信。出乎他的意料的是,阿莫米安竟也坐在皮椅上,看到他走进来,红发男孩朝他重重的哼了一声,然后从皮椅上跳起来,并不和他说话,而是直接冲进了一旁的寝室入口。
普拉瑞斯对着他背影消失的方向发了会呆,他一时觉得对方或许是特地在等他回来,一时又觉得多半是自己多想,摇了摇头,他转身决定先找到自己被分配的寝室,今天是过于劳累的一天,普拉瑞斯决定在写完给家里的信之后早些休息。
露易丝一定很快就能适应的。怎么想也不需要自己担心。
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寝室,不知出于怎样的安排,霍格沃兹的寝室常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共住的情形出现。普拉瑞斯事先确认过自己未来的室友,发现其中有两个二年级,其中一个正是晚餐时坐在他身边的伊莱·洛佩兹,而剩下的三人全都是高年级的男生,这让他在推开寝室大门时稍稍有些忐忑。
而当他推开门,迎接他的第一句欢迎是来自五个室友齐刷刷的注视时,这种忐忑被数倍放大,普拉瑞斯抿了抿唇,在突然安静的空气中准备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普拉瑞斯·诺——”
“诺斯,我问你,万圣节你有舞伴了吗。”
没等他说完,黑发红眼的二年级生就面无表情的打断了普拉瑞斯的自我介绍。他是柴佩西家的小少爷,在纯血里算是比较惹眼的人物,普拉瑞斯和柴佩西少爷算不上认识,但至少互相能说的上是脸熟。
普拉瑞斯心中涌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在五人的注视下,他几乎是想也不想便回答:
“有,当然有!”



真的只是来狗的旧粮
就只有这么一点啦——————
一轮圆月挂在无星的夜空。
比夜色还浓的漆黑翅膀盖住高大的躯体,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屋主缓慢的呼吸清晰可闻。
窗外的月被乌云掩去瑕光,没多久,雨滴便叮叮咚咚地敲击着屋檐,顺着外壁淌进地面,积起一个个小水洼。雨夜奏响的小夜曲唤醒假眠者,黑色羽尖不安分地舒展开来。
金色的眼在黑暗中熠熠生辉,仿佛除了那光亮,倒映不出它物。随后一双锋利的、状似鸟爪的脚踩在地板上发出一阵吱呀声,尖端深深地嵌进脆弱的木头里,想必会留下几道难看的爪印吧,宇贺神伊墨却完全不在意,他只是静静地伫立在卧室,凝视着窗外。
雨仍旧在下。淅淅沥沥。
闪电划亮天空,雷声回响。
只有心跳声应和着震耳欲聋的春雷。
宇贺神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远离原地,拥有良好夜视能力的天狗将整个屋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连一只蛾子都没有。
推开门,迎接他的是空荡的长廊。
早知道就不买那么大的房子了。宇贺神不知多少次叹气,但始终都没有将这一栋他嫌弃空旷的大屋卖了换够一人住的小屋。
再空也没关系——
越是空旷,哪怕是做一些小事,也会有细微的回音。而天狗的听力同他的夜视一样灵光。
楼下传来千寻的脚步声。
想来这会儿自家女佣是准备就寝了吧,宇贺神随手拉上卧室门,嵌在墙壁上的油灯中燃起簇簇火焰,点亮通往楼梯的道路。天狗火随着主人的惬意心情摇曳。
他站在楼梯口,将头探了出去,“千寻,睡了没,我们来吃夜宵吧。”
收拾妥当的千寻浑身一僵,突兀的乌鸦声线落在夜里着实吓人,千寻结结实实地被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少女按着胸口,仰起脸瞪他,“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哎呀,我饿了嘛,就满足我一下——?”
宇贺神仿佛没骨头似的瘫在楼梯扶手上,懒得挪动步子向下走两步,背后橙色的微弱火光竟将那身向来如墨的身影衬出些暖色来。像是被妖邪蛊惑,千寻应了声好。
就在下一秒,少女的手就被牵住,被拉着往厨房走了一会儿千寻才惊醒,立刻就逃离温热的源头,猛地抽回手。这只臭妖怪!刚刚还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同情他真是瞎了眼,千寻愤愤地揉着手。
“不好好握着会摔跤喔。”
这就得寸进尺起来了,老爷果然还是老爷。千寻深吸一口气,说出来的话怎么听还有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点上您得意的火不就行了,天狗大人。”
顿时,几团火焰环绕着少女翻飞,甚至有一团绕着她的手臂转着圈嬉戏。千寻没去搭理宇贺神玩性大起的炫技,忍耐着翻白眼的冲动,快步上前走在了他的前头。
“如您所愿。”后头悠悠地传来宇贺神的声音。
戏弄自己就这么好玩?这家伙如此高兴的样子确实少见。千寻咬咬牙,步子不由地又加快了几分,这下宇贺神是彻底被甩在了脑后。
但他的确是听见了他的小女佣说还有些油炸豆腐,那可是他的最爱之一,淡淡的笑意浮现在金色眼底。轻轻一扇翅膀,转瞬就贴近女孩的妖怪低声在她的耳边说着什么,激起女孩更多的恼怒之情。
再空也无妨。
这里有南云千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