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族大会?”尤尔娅·马尔蒂抬起头,眨了眨眼,“您要去那个?”
“去看看。”尤裡卡明明是自己提出来的,却比谁都显得兴致索然,百无聊赖地用食指指节叩击桌面。
尤尔娅把他的书递过去,应了一声。虽然大众认知中,猎人与血族总是不共戴天的——教会猎人不算——但她明显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我还真没想过您会去。”
她的雇主尤裡卡是一位残月血族,不过一直对于这种事情显得兴致缺缺,所以尤尔娅一时半会还真没想起这个活动——作为猎人,她倒是有些血族朋友,所以含糊知道一点。
“去看看。”尤裡卡明显已经开始觉得麻烦,回答也敷衍地沿用前句。
“可我不能跟您一起去吧?那我是在附近的城镇等您回来,还是怎么样?”
虽然说作为猎人去血族大会明显就是挑衅找死,但作为一个刁难的雇主,尤裡卡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吐槽:“明明是我的保镖,结果却只拿钱不工作啊。”
“哎呀,您也可以不去的,我帮您怎么样?”
看起来纤细的女性实际上相当暴力,久经锻炼的猎人可不是他这样柔弱的小血族能够比拟的。虽然尤尔娅依旧微笑着,但尤裡卡明显从她的笑容中读出另一种意思。
尤裡卡咳嗽一声,生硬地转移话题:“反正就是这样,我得过去几天。”
“好的,到时候我帮您收拾行李,马车也由我订……对了,小心身体,不要去月下宴哦,您还年轻呢。”
月下宴,作为嗜血血族的活动,其中的淫靡秽乱不言而喻。因此尤尔娅虽然是开玩笑,倒也三分认真地提醒。
但尤裡卡只是冷笑一声,精神阳痿·家里蹲贵族·对人交往毫无兴趣!的尤裡卡先生高傲淋漓尽致,他回答:“那种地方有什么可去的?我对性交没什么兴趣。”
嗯嗯,知道您不行了。尤尔娅委婉柔和地一笑,回答道:“是呢,那我就放心了。”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原来如此,要不再带条围巾吧?”
“……你问我到底为了什么啊??”我回答你你一点也不在乎啊?!
尤尔娅理直气壮:“嘛,本来就觉得尤裡卡先生不会感兴趣。”
她说完之后就去帮尤裡卡收拾东西,自从这位麻烦的贵族上次出门居然打算全部买了再丢掉之后,尤尔娅就决定按着帮他好歹收拾个差不多的行李,不然家里钱迟早给他败光了。就算钱不是她的,她也看不下去!
即使看着保镖忙忙碌碌,也完全不打算帮忙的尤裡卡明明一直信奉有需要买就行了,现在却理直气壮地指挥起来:“那个衣服我要带着,对了,那本书也帮我收拾进去吧。”
尤尔娅拿着书,往他脑门来了一下。
虽然表现得轻巧,但你要说尤尔娅真的毫不担心吗?也不尽然。她是人类,并不理解血族,只是包容并且接受血族的一切不同,但这种因为岁月与本来产生的隔阂并不适用爱就能适应的,血族大会会聊什么、会发生什么、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都不是她能够以自己的阅历推理出来的——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血族与人类的差距,不仅仅是仇恨与身体那样简单。也许在双方对立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泾渭分明。
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甚至认为这份不同是应该的,所以才更应该接触不是吗?但担心还是让她一再叮嘱一些杂事,注意安全之类的:残血血族总是弱势的。
“那边应该有许多厉害的血族,所以要小心,不要跟人矛盾。要记得好好打招呼,但是别勉强,不喜欢就回来,一个人也不要凑合,记得多穿点衣服……记得回来找我。”
你是我母亲吗?尤裡卡虽然这么想,但面对这份不加掩饰的关爱,他并没有说出什么,只是移开视线应道:“知道——了。”
尤尔娅并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收拾了很多东西也不能确定尤裡卡会不会用,但也没办法。她穿了兜帽袍子,在夜色中于大会附近相对安全的一个城镇下车,目送尤裡卡的马车远去。姑娘眨眨眼,夜深的晚上实在是没什么人,于是意识到自己没什么事做。
倒也不至于没有尤裡卡,她就不知道干点什么好。陌生的地点并没有阻拦尤尔娅,她熟练地找了个旅馆,把自己的行囊收拾好休息,准备第二天去街上逛逛。
某种意义上,这是放了假,她在周围四处乱逛,准备买点礼物回教会去,比如玛卡里亚姐姐会不会喜欢蝴蝶结?安纳托哥哥应该会喜欢这个奇怪的土偶?……手指落在想要拿起来的项链时停顿了一下,她像是陡然惊醒一般,转身把那朵人工水晶中镶嵌纯白百合的饰品放回去,连同那只红狐狸的玩偶一起。
事已至此,她倒不想叹气,又或者伤心了。这本来就是一场抉择……爱是勇气,如果非要有一种情绪,那她更觉得骄傲且祝福。
饰品暂时不用了,但是阿尔文先生应该会喜欢这个戒指?总是送种子也不太好,那么西比迪亚先生的话就……
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都不是完美无缺、坚不可摧的,比起个人的感情,总有一些无法撼动的东西。况且就算表露出冷酷的一面,她也并不觉得这次事件就会让爱彻底消失,更不会就此觉得幻灭又或者对哪一方失望。硬要说的话,她不认为谁就全然有错,观点这个东西,总是根据自身立场去决定的。
非要说的话,尤尔娅·马尔蒂可能觉得自己才是卑劣,她抽身事外,所以用局外人的目光围观这一切,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对于双方,不都是一种背叛?偏偏她还想如往常那样、爱着每一个人,并不作出表态。
她承认这一点,所以更加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站到任何一方那边去,还接受着米路不希望给她添麻烦的爱与教会并不明令追查她的好意……
不该细想了,尤尔娅闭了会眼,把东西全部挑出来付钱。她有点想尤裡卡了,不知道现在他还好吗?真希望他不要跟人起什么矛盾。
尤裡卡在好几天后才回来,他看起来跟走之前别无二致,甚至显得更加无聊,面对尤尔娅的询问无精打采:“他们要打仗了,没兴趣。”
“噢……这样啊,”尤尔娅检查了一下他,安下心来,“您确实不应该参加,不然会受伤的。”
“你怎么表现得像个局外人一样。”
“那您是想我冲去血族大会自杀式袭击,还是跟教会同归于尽?我现在是您的保镖。”
“哼……”血族发出不置可否的声音,他突然有点促狭、带些毫不掩饰的恶意与揶揄,“可是,最后也会开战吧?你会杀了我吗?你可是猎人啊。”
“我会保护你的。”
尤尔娅很认真地回答。
她是局外人,但并不永远都是局外人,有一些她能改变的、她应该保护的、她爱的,那她就不该再旁观。
“即使与人类为敌?”尤裡卡觉得她只是客套,但尤尔娅的眼神并不作伪。
“实在不行,就想别的办法,比如把你打昏带走隐居什么的……无论如何,会保护好你的。尤裡卡先生打不过我不是吗?而且你也不是这种人,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我还是有这点眼光,所以相信着你的啊。”
“呜哇……好恐怖,你怎么老是想着攻击雇主啊!”
“我很在乎您的。”
尤裡卡沉默了一下,他依旧显得有点嫌弃:“知道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才不会做。”
他向来觉得自己不受重视,所以从没想到会从突然的角色中获得这样的关爱,喜悦吗?那是自然的,所以尤裡卡显得有点不习惯,抿着嘴不知该继续什么话题。
但尤尔娅只是笑了一下,她的情绪总是被这样掩盖下去,轻轻拍了一下尤裡卡的肩膀:“好了,风尘仆仆的,您先去换件衣服吧。我给您准备了礼物。”
抓了几个同族当背景,就不艾特了,卡文写不动,小学生文笔,凑合看吧(目移)
————————————————
礼堂内已经有了不少的血族,那种微妙的感应也强了起来。艾维斯顺着感觉望去,看到了一名短发,带着不少耳钉的嗜血血族。而他也看了过来,确实是那张熟悉的脸。他是艾维斯的第一位子嗣,也许现在叫私生子更合适,毕竟当初连真名都没有来得及给予。
思绪回到了120年前。
“大人,求您救救这个孩子,医生说,以他的身体情况,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他,他才19岁,还这么年轻!大人,求您了!”
艾维斯看着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妇人跟抱着她同样流着泪的男人。他确实受到了这两人的帮助,而他们的孩子,那个年轻人他也见过,是个很聪明的人,本身没有什么疾病,只是因为是早产儿,身子一直都不好。一个已经成年的聪明孩子,确实可以。
“我可以救他,但是他会变成我的子嗣,我会带走他,如果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了。”
“接受!只要能救他!我什么都愿意!只要让他活着就好!”
“好。”
几天后批准下来,艾维斯也将那个男孩转换成了血族。男孩因为体质的原因转换成功后就累的睡了过去,而艾维斯因为一些原因,本身也很虚弱,索性打算先去休息一下,等男孩醒了再给予他真名,没想到,等他再次醒来,男孩一家都已不见,而这间屋子里散落的灰尘则说明他们已经离开很久。
艾维斯收回视线,看向走上台的萨诺长老。
另一边
“查理斯,你在看什么?”一个看上去不过十一二岁的男孩好奇的顺着查理斯的目光方向看了过去,只看到几个站在一起的古老血族。男孩收回视线,撇了撇嘴:“那些老古板有什么好看的?他们身上简直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查理斯笑了笑:“你说的太对了,麦伦。但是那个红发的家伙,我想他或许是我血族层面的父亲,我曾经幻想过许多次我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但是,一个老古板,天啊,简直无法接受!这简直是耻辱!好想毁了他!”
“会有机会的,在那些老古板的老巢,毁掉一个他们的成员,天哪,这简直,简直!”麦伦浑身颤抖,露出一个略显病态跟疯狂的笑容。“我想到了,让他在他的那些同伴面前舔我的鞋底,这一定很刺激。”
看着走上台的现女王莉莉跟残月科雷塔,艾维斯不由蹙眉,很想直接转身离开,但因想知道会议内容,暂时忍住了,只是眉头皱的更深。而他的血亲梅兰莎,还有几位实力很强的同族,例如那位奥斯顿先生,则没有犹豫,直接转身离开。
会议并没有因为几名血族的离开而中断。嗜血乌列克的死亡,教会恶劣的态度,以及……现女王莉莉就是失踪的女王莉莉安。
女王的消息令场内开始喧哗,又有几名古血离开了会场。艾维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心底发出叹息,他突然对继续下去失去了兴趣,于是便跟随身着红裙的Cherry一同离开。
“怎么,这个会议开完了?”梅兰莎拿着高脚杯,端详着里面的液体,见他进来,随口问了一句。
“不,我提前出来了。”艾维斯坐在她的对面,拿起血仆适时放于桌前的血液细细品味,血液甜美的味道平息了他有些烦躁的心情。
房间一时陷入沉默,两人都没有想要说话的意思,直到坎进来,才打破这份安静。
“居然都提前走掉,也不知道叫我一声。”
“所以后面发生了什么?”
坎挥手,示意屋子里的血仆全部离开。等他们关好门,他才继续说到:
“现任的女王莉莉就是女王莉莉安,曾经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呵呵。乌列克是被那个教会的神父毒死的,人类还真是掌握了不得了的力量呢。”坎轻抚趴在他腿上发出呼噜声的猫,接着道:
“萨诺长老说他放任西比迪亚是为了探查教会的秘密,还有,那些教会猎人异变是因为食用了教会所谓神的血肉,那是一种跟湖骸相似但是更令人作呕的液体。”
“啧……湖骸已经够恶心死了,他们是怎么下得去口的?”
“谁知道呢,或许在选择背叛那一刻,那些背叛者的感官就失效了。”坎依旧对教猎很是不喜。
“难道我们要等那些背叛者传出消息才能行动吗?这种一切都被别人掌控的感觉真是不好。”
“萨诺长老在征求意见,直接攻打教会,或者再次跟教会和谈,我更倾向于主动进攻,至少主动权要把握在自己手上。”
“我跟你一样,教会既然能坑害女王一次,那么再次和谈,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好事。”
“不愧是挚友呢~”坎后靠,姿态颇为轻松。“那么,说完正事,就聊聊其他吧。那个时不时看你的小嗜血是怎么回事?”
艾维斯想了想,觉得坎问的应该是查理斯。
“查理斯吗?他是我第一个子嗣……不,现在应该叫私生子更合适。”
坎挑眉:“还真是看不出来,你居然会有私生子?你对那个小嗜血跟对维奥拉完全不同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艾维斯将查理斯的事详细说了一遍,末了,加了句:“我也没想到他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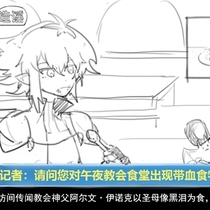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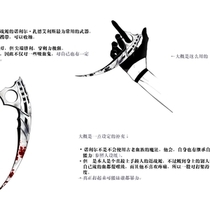


推荐与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50825/ 这篇文合起来食用。
—————————————————
比尔·哈珀做了个梦,梦中自己在暴雨中行走,腿上烂了个窟窿,腹部也烂了个窟窿,个个都有碗口大,全身骨头咯吱作响,雨水直接落在眼睛里,睁也睁不开眼,只摸索着往前蹭,像个叫丝线强行提起的人偶。
他梦见自己刚和唐娜打了一架,全不讲逻辑。对方生着成熟的身体和一张十多岁女孩的脸,下半身肿大了三四倍之多,长满梅毒花疮,黑色黏浊液像件大麾,把她整个人裹住,只一张脸仍然干净,用那张稚嫩面容冲猎人微笑,呼唤他。下体中细窄的纺锤形缝隙里横七竖八插着许多个流血的头颅。
比尔难以移开目光,他认得出来那些孩子的脸,正是他幼年时期所生活的孤儿院里那些总粘着他的弟妹们。
她们用稚嫩孩童嗓音歌唱,声音又尖又细,一如往日在孤儿院时那样,暴雨中许多只小手左右拉在一起,绕着他打转,歌唱不休——
“捡石子丢石子
跳呀跳房子
左脚抬右脚跳
转了一圈换脚跳”
他们那圈子越收越紧,笑声穿过耳膜直插进比尔脑袋中央,那些贴近了的小孩纷纷抬起脸来,面上没有五官,只有蠕动的黑色泥污。
“比尔!为什么你不和我们在一起?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起玩呢!”
他们异口同声问道,有个孩子撒气般踢了一脚游戏用的石头,使其撞在比尔小腿上,猎人一低头便看见那石头是颗乱跳的心脏,而他胸口的位置开了个洞,雨水积聚于内,直接望得见另一头房顶上的烟筒。那些孩子七嘴八舌地追问他,歌谣越唱越快,笑声愈发急促,“我们全等着你,哥哥!而你却跑啦——跑啦!”
比尔·哈珀发不出声音,梦境中这猎人在接二连三的质问中再组织不起勇气,那些怪物咕叽作响,头颅从面孔处坍塌,旋转着用小小胳膊紧扣住他的腰腿。猎人落荒而逃,脚下瓦片砾石尽数滑脱,他由孤儿院大屋顶部坠落。天降浊雨,劈头盖脸,比尔翻在装尸体的推车上,紧跟着又二次摔落,四肢摊开倒在被滚烫雨水浇透的泥地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骨头不痛。他那心脏离题相当远,激狂乱蹦依旧使他耳鼓震动。唐娜摇荡着肿胀身躯爬上孤儿院屋顶,那些往下滴挂的孩子围住她,无数张脸均朝向天空,听上去那么高兴,几乎歇斯底里:
“捡石子丢石子
跳呀跳房子
左脚抬右脚跳
转了一圈换脚跳”
而猎人拖着被掏了洞的身体在大雨里败走。
说是走,其实仅是用肩膀顶着墙在往前蹭。翻江倒海的感情在他胃里滚动,呕出来的却只有内脏受伤导致淤积的血块。
酸雨腥臭,泥土腥臭,喉咙和牙缝间也全是血的腥臭。
也许是求生的意志让他的双腿在动,也许是惦挂的名字让他仍然在走。他扶着墙蹭动,手底下凹凸不平全是一个个代表名字的道儿,曾用血划在墙上,如今均反过来割裂他的手指。
他混沌地挪着,像条四肢骨头全被砸烂的老狗。
医生在爆炸后的纳塔城内找到这样的比尔·哈珀时,对方几乎坍塌在地上,手心里紧握着一块石头,横竖看不出和其他石头有什么区别,可对方依旧攥地死紧。这猎人指甲缝里全是血污,身后的一段墙壁乱糟糟划着许多个血道子,全干涸了,痕迹和着黑灰硬抹上去。
斯塔夫罗金医生检查了对方的脉搏——尚且活着,但离死不远。
接着他捧起对方的脸,很是端详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老朋友。
这就稀奇了。
医生可以称为老朋友的人为数不多,活着的更是寥寥无几。比尔·哈珀毫无疑问占据其中一份。即使三十五年里他两见面的次数两只手就数的过来,可对方却是最好的那一位朋友,而且到目前为止,尚还算活着。
为证实这判断是否准确,医生检查了臂弯里猎人的储血器。右侧大腿,由一个孩童血罐改装而成,罐体体积过大,因此小半截只得暴露在外。早年间曾流行采用硬质材料制作血罐,若是遇到极端天气,他那罐子就有炸裂的危险。于是当年脑袋还算灵光的医生做了点修改,在它内部填了个软套管,这样外部硬质的壳若是炸裂,只需要用随便什么东西把缝糊起来——哪怕泥巴也行,就能保证大部分处于体内的储血胆不受伤害。气温骤变也能使内部借着人体保持一个较稳定的温度,血液活性应当不受影响,外壳如遭意外损坏,短时间内也不会使猎人丧失战斗能力。
这不是万全之策,只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一点改进,相当于给个房间做了内外两扇门。
——不会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面前这千疮百孔的家伙必定是比尔·哈珀。
斯塔夫罗金医生尽量轻巧地将老朋友扶到自己肩上,调整对方脑袋的方向,不能让舌头压到气管。
比尔比他目视效果要轻不少,可能跟储血器几乎泵空了有关。
医生稳当地从碎石砖块中滑出去,猎人像破烂稻草填充起来那般挂在他身上,手和腿都怪异地垂下去,尚没有死,所以关节依旧柔软。医生一动,它们就跟着摆动,反而比僵硬挺直的死人更怪异。斯塔夫罗金与猎人比尔·哈珀极少数的几次见面场景均颇为戏剧化,对方每次都把自己弄得破烂不堪,伤痕遍布躯体,操心劳力使他耗损飞快,衰老因此更早降临在他的老朋友身上。
每次猎人总烂糟糟地躺在手术床上,手脚张开,这里是鲜血,那里是创口,骨头断了却还撑着脖子嘴硬,自称自己好得很,可一点事儿也没有,斯塔夫罗金尽是瞎操心,不如管好他自己家里那点事。三番两次如此,进而使医生对其产生不恰当定义,即比尔·哈珀此人是伤痛的集合体,是各式扭曲疤痕堆积起来的一个人形。
原外科医生这行当干的久了,靠面孔区别人的能力就会下降,进而以偏离角度观察病人。开了腔后,人的骨髓与动物未曾有区别,腹脏里器官七七八八也就那么排列。大量出血造成的腥臭味儿闻久了像海水和烂掉的鱼虾,腐化以后更加没有差别。医生记忆人脸的能力正因精神问题逐年减退,最后只能十分可笑地依靠缝线,伤疤和痛苦呻吟时的调子辨明身份。
他们实在鲜少会面,比尔·哈珀是只迷失在海中的小船,医生总也不知道他荡到哪里去,又什么时候才想起来靠岸看看。这流浪猎人深爱的母港——他曾生活的孤儿院已经毁灭多年。仇人遍寻不得,家灯再无法点亮。这艘孤船只噙着满腔愤怒做桨,撑起渺茫希望做帆,如此勉强乘浪游荡。
年月久了,猎人们总觉得比尔·哈珀是块瘢痕累累的石头,一张嘴又臭又硬,性格霸道,实在惹人讨厌,渐而少有人与他混在一起。斯塔夫罗金医生却觉得他是一团蜷曲的肉,背朝外的那面全是伤口,结了痂又脱落,表皮摸上去变得铁硬,可始终不是块石头,如果拿刀子把他藏在最里面的软肉扎透,这流浪猎人也就死了。
工会猎人们分为几拨子,狮子和虎豹交往,鬣狗和兀鹫结群,苍蝇蚊子又独自聚成一窝,剩下的个体则脾气古怪又为人孤僻,于是便全单独来去。
——可要是这些孤狼叫人捅上一刀。
医生时常会想,要是这些孤狼叫人捅上一刀,刚好捅在要害上,比如心啊,喉咙啊,那便倒下死了,没有人知道。孤狼寥寥无几可的朋友在远方成年累月等着,等某一天那杳无音讯的老家伙风尘仆仆路过,走近他们,把沾满灰土的脸伸给他们亲吻。于是他们放下心来,笑着责骂对方,嫌弃几句能种花的面皮,结了板的外衣。接着端出酒来,斟到酒液满涨出边沿,再狠狠将杯子碰在一起。
但这些了不起的独行侠总是某一天突然融化在阳光里,就像猎人伯翰·卡德尔那样。对方活着时曾教过医生如何使枪,被医生看做朋友。他是个好人,顶好的那种人,生着个笔直挺拔的脊梁骨,声如洪钟,脾气暴躁,但坦荡又慷慨。
老猎人,老英雄,愿他长命百岁,生也欢乐,死也欢乐,杯中总有酒喝。
但这样的人也叫剁成了碎块,像颗铁块铸的老树整个倾倒砸在地上,树冠连花带果摔得粉碎,满地都是糨子,几乎无从捡拾。卡德尔,卡德尔老爹,曾算是猎人工会的大人物,现今已几乎无人记得。他叫人剁成碎块倒是轰动一时,所有受过恩惠的,结过仇的,仅凑个热闹看稀奇的,全乌泱泱聚集起来,都伸着脖子想看一眼那位卡德尔老爹究竟碎成了什么样。是二十来块?三十来块?还是三百来块?
稀奇啊,多稀奇啊!就算在纳塔城内,也少见这类堂而皇之体现恶意的事件。
医生现在已无能力辨别自己当时的心情,只记得自己看着围在周遭的那些人。男人,女人,孩子,每个工会猎人,每个停下来看一眼的人,每个惊慌而紧张,隐隐透出些兴奋的人。斯塔夫罗金反复思考——他们是不是都砍过卡德尔一刀?
动手的人并非杀人专家,只是以杀人的形式宣泄恐惧,因此什么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专家不会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毫无意义剁成那么碎,即使是数个成年男人,把大骨头剁开也要花许多力气。可偏偏他们就砍了,猎人卡德尔的脖颈被砍了,手臂被砍了,腹脏和手指都被砍了,就连股骨也不例外,他们甚至试图将那两块硬骨头分成不规则的三段,但不得要领,刀法恐慌的令人憎恨,那一根骨头上面前后足有六七个半指深的豁口。
斧头留下碎屑崩裂的损伤,条形,角型,大量皮下组织出血,肉块深紫色,全是斑点;刀具创口细而窄,边缘整洁干净,肉曾尝试愈合,增生使创口肿胀;钝器则区块状磨损和凹陷,擦伤,挫伤, 挫裂创,肌肉组织所受破坏比骨头更惨烈,每个痕迹都毫无必要又拖沓难看。
这种粗糙荒诞的集体犯罪行为把医生吓住了,他至今不知道究竟几个人参加了当时的行动,光是砍人手法轻重就辨得出四五个家伙下了手,还得算上那些难以分别的——猎人卡德尔实在被剁得太碎,捡拾和缝合的人们看了难免陷入无从排解的怒涛,这怒涛会让手指麻木,因此斯塔夫罗金医生只能不停地想:他们是不是都砍过卡德尔一刀?
医生尚清醒时实在无法理解什么原因会致使此类事件发生,开头他几乎傻在原地,只看着夜莺艾德蒙拄着拐杖,拖了断腿去收集肢体——好夜莺,愿他受祝受福——先是放下健康的那条腿,接着慢慢地,小心地再放下那只断腿,完整地使自己跪在地上,捡起一块连骨带肉的东西。他那拐杖动作中吱嘎作响,前后摇动。斯塔夫罗金医生盯着他,从后脊梁骨里打了个哆嗦,没来由的恐惧涌上他喉头。
肢块越多,信息越多,于是整件事,整个死亡迟滞着显露出恐怖形状。而等他陷入疯狂后,揣测犯罪动机变得无足挂齿,自然更没了追究的必要。只有猎人卡德尔的死状插在他脑后勺最里侧,像根针长在里面,拔不出来,一想起来便转动着扎人。
有时他坐在问诊台后面,一个猎人无休无止地开合嘴唇,讲些无足挂齿的小灾小病,什么疮,什么关节炎,什么头痛脑热,家里的血罐营养不良却不肯吃饭,储血器接口位置总磨得他肉疼。费恩·莫里斯诺这头母狼幽灵般悄无声息从诊室门口经过,下巴颌和眼睛视线抬平,落在差不多地方,脊梁骨又直又坚硬,总坚定不移地望着前方,就像伯翰·卡德尔。
那根针在医生后脑勺深处一下一下旋转着刺痛他,不过是些陈年旧事,头痛也无伤大雅。医生认为此时应当专注工作,于是把注意力强行拉回面前唾沫横飞的猎人身上,脑子里却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他是不是也砍过卡德尔一刀?
“医生,您吩咐我给血罐吃点荤腥的,她贫血,我照做了!那血罐儿又闹脾气不肯吃东西,怎么搞的!难道下水炖的肉汤就不是肉汤了吗?”猎人喋喋不休,“我可已经够宠着她啦,嘿,他妈的,小妮子一身公主毛病,可怎么办呢,养都养了!她成天在家里蹲着,一天天尽坐在窗台上拿手指梳头发,全天见只有那会儿显得高兴点,哪知道我在外面多么辛苦……卡拉乌洛夫几次想租了她去用,我没答应!”他又垮下脸,反复念叨:“可得罪人了,可得罪人了——您知道卡拉乌洛夫吧,话讲不通!”
医生慢了两三秒才蹦出个单词来,他使目光从猎人嘴唇移动到猎人鼻梁正中央,合乎礼节地悬在那儿,空洞又迷茫,好像刚被从很远的地方强行拽回来:“谁?”
“卡拉乌洛夫啊!马尔穆特那帮子人里头的——嘿,您记不得了?高个子,使两柄斧头,喜欢这么抡着,樵夫卡拉乌洛夫啊!”猎人把腰背往下弓,脑袋缩在脖颈里,空落地前后挥舞双臂。
医生把头颅向左侧微偏一点:“我不记得,他装了什么样的储血器?”
那猎人腰又直回去,脑袋从脖颈里伸出来,往后仰了仰,椅子吱嘎作响,摇头晃脑地笑着:“——您看您,他跟马尔穆特一堆儿的,哪里会有储血器——噢!他们这一帮人都不装储血器,只用血罐儿,您大概全不认识吧!”
医生又把头挪回原来的位置,极是认真地答道:“我知道马尔穆特,阿比西奥提过他,脸孔漂亮,脑袋不错,可惜胆子太小,而且死了。”
椅子腿嘎巴一声落回原位,那猎人安静下来,似乎没想到马尔穆特这么个极狡诈的家伙突然就死了。他是苍蝇里的苍蝇,臭虫里的臭虫,最擅长趋利避害。卡德尔死了,艾德蒙瘸了,他只会过的更加滋润,和一帮同样蝇营狗苟的家伙混着,好不快活,如今却突然死了!谁想得到!且更让他吃惊,这消息是从医生嘴里冒出来的,马尔穆特不肯往身体里塞储血器,自然也不会让医生记得,这狗东西,倒是很会爱惜自己。
那猎人撵着问道:“他死在您这儿?”
“死在外面。”医生答道。
求医的猎人倒不太在乎马尔穆特死活,只是唐突收了死讯,难免迟疑,可等他回过神后,已没机会再问,医生自顾自开始写诊断。
费恩·莫里斯诺把马尔穆特杀了,这件事不知道在哪儿突然就发生,又突然结束,也许有一天银枪猎人莫里斯诺也会不走运倒在哪儿,同样不被人知道,过了很久才会传出消息。不过在猎人工会,这样的故事全很正常。有人活,就有人死。所有人都活着,那世界怕不就乱了套,就连伯翰·卡德尔这么样的一头狮子也突然被杀了,变成一堆肉,涂在地上,碎的叫人头晕目眩。
对话就此告一段落,那猎人还消化着崭新死讯,医生提笔,看着自己在诊断上写下“动物下水请处理干净,用百里香,胡椒和盐腌渍。但如果有正经肉,请直接给血罐吃肉。肉炖煮时应剁成很多小块,糊在地上,手指碎肉,脊骨碎肉,脾脏碎肉”,他骤然停笔,平淡且干脆地把诊断后半截涂掉,紧接着另起一行写道,“把肉炖烂,您的血罐牙齿不好,请注意清洁,牙周发炎会使血罐无法进食。再给您的血罐买一把梳子,不要缺了齿,这对她的精神状态有好处。”
最后他把这张大量涂黑的诊断塞给面前那猎人,对方知晓这就是结束讯号,屁股刚抬离凳子,阿比西奥就拖过椅子坐下来,堂而皇之把一条腿跷到医生大腿上,等对方替自己清理储血器上附着的缀生组织。
伯翰·卡德尔死的太突然,像道使人束手无策的霹雳。以至于医生在日后的年岁都专心注意着,祈祷这辈子别有那么一把刀子能同样穿透比尔·哈珀。往常这稀客胸骨断了,肋骨断了,一条胳膊叫上着夹板了,被医生发现,蛮不高兴地摁在诊室里,眼睛左右打转,硬梗脖子吵闹说身体没有大事,垮着张脸逮住机会仍会溜号,看来脑袋十分清醒。比尔这时便总令人生气,考虑当下就该把他两条腿都打断以示惩戒。可他偏偏活的倒还算很好,满身伤口通过治疗均可以愈合,那能要他命的软肉被紧紧蜷在最里面,充满敌意,偏颇地拿刺儿保护着,没受一点损伤。
比尔·哈珀孜孜不倦撑着他那艘千疮百孔的小船,四处破浪遍寻归途,令医生觉得一切总是好的,即使只用蜘蛛丝吊着一点点希望,对他的老朋友来说仍有理由拼上性命去战斗,那么这一切也是好的。
十年前某个夏季,天气热的空前绝后,先是大旱,随后暴雨。医生在路上捡到流浪猎人时,满天滚烫的雨水直碌碌砸下来,地面吸满旱灾导致的热气,水进不了结板的土地,因此全黄浆一样遍地横流。
比尔·哈珀倒在地上,被浸着半张脸,流血不得止歇。
彼时尚神志还算清醒的医生捧起流浪猎人那张脸,认为他离死只差一口气,希望渺茫,最好还是予以其解脱,因对方看起来如此虚弱,而且痛苦,伤口叫泡的发白,就像死人翻鼓出来的油膏,即使立刻治疗,对方也可能死于感染。斯塔夫罗金那亲爱的妻子刚变成一滩烂肉,前所未有地动摇了他的信念,令医生口中只尝得出苦涩,怀疑让患者无痛苦的死会比苟活更好。
他盯着手心里的头颅,对方棕褐色的头发全湿透了,胡须许久未理,使人的脑袋看起来像条快断气的杂种狗。
浑浊的雨水在猎人脸上,手上,眼球上流淌,比尔・哈珀正从医生手心里向地面融化,颊侧皮肉垂挂,身躯向下坍塌。斯塔夫罗金疲惫至极,已产生些精神问题的前兆,恍神时看见手心里分明是一颗狗的头颅,褐色眼球几乎不聚焦地瞅着他。这狗仍想吠叫,看不着目标却愤怒地想咬断某一些喉咙。于是斯塔夫罗金医生放弃了予以其解脱的想法,向他的病患俯下身去,遮住雨水。
比尔·哈珀恢复意识时,并没有立刻睁开眼睛,他侧耳倾听许久,察觉周遭竟很安静,既没有湖骸缥缈悲歌,亦没有刀兵炮响,只有火焰噼啪,四围没有活物。于是他放下心来,这才缓缓将眼睛睁开,却正撞上一对悬在半空的绿眼睛。
猎人几乎立刻摸向腰间火枪,抓了个空,掌心触着了没铺褥子的硬板,短短两秒钟,后背上打架似的渗出一层细密冷汗,那骇人的绿眼睛却笑起来:“——比尔,醒了!爸爸!比尔,醒了!”
斯塔夫罗金医生掀开临时居所的门帘,矮身走进来,停在老朋友身边,比尔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环境,这才发现那对儿亮到骇人的绿眼睛属于医生的女儿朵拉。这姑娘坐在他胳膊边上,满头金光灿烂的毛茸卷发像小动物般蹭着猎人手臂。
“比尔,你觉得怎么样?”医生轻声问,不容对方回答,先是掀了掀眼皮查看瞳孔,紧接着抬起对方胳膊,默数脉搏,五根手指像五个冰坨子,冻得猎人直打寒战。直到此刻,直到该死的斯塔夫罗金检查完毕,轻巧地在比尔·哈珀身侧坐下时,猎人才确切意识到自己已从噩梦中醒来。他眼珠来回打转,先是狠狠闭上眼睛,接着又睁开,这幅画面并没有变动,昏暗狭小的安置点室内一共四只绿眼睛,全都一眨不眨盯着他。
他妈的,兹米亚·伊万诺维奇·斯塔夫罗金全须全尾地坐在那儿,看起来全没损害,而比尔·哈珀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储血器几乎泵空了,导致他直犯恶心。
医生半晌没等到回答,转而问他那人偶般的女儿:“他睡得如何?”
斯朵芙菲利亚——朵拉回答:“不好,爸爸,比尔磨牙,呜呜叫,还哭了。”
猎人猛地从床上支起上半身,想坐起来,最好立刻夺门逃跑,半年内再不要出现在这对儿父女面前,可他刚一动,就被医生一把掐住肩膀上的麻筋给强摁了回去:“——别动,现在没有镇定剂了,浑身疼?这很正常,忍着点。”
“湖骸呢?”猎人嗓子哑得像烤干的砂锅锅底,直往外泛血腥气,背还绷着,不打算妥协。朵拉跳下床去,把水罐和水杯一起端过来,对方看也不看,抓过水罐便一通猛灌。女孩放下托盘,依偎在父亲怀里,只伸出半个脑袋瞅着猎人咕咚咚喝个不停,接口回答道:“一只也没有了,湖骸。歌谣,现在由夜莺唱着。”
像为证实所言不虚,她挽着父亲的胳膊,庄重张口,模仿夜莺猎人诵唱着的调子,惟妙惟肖,只是连苍老的音色都模仿了去,和那张十三四岁女孩的面孔实在不搭。她那父亲却很欣慰,慢条斯理将女儿两鬓乱发纷纷归拢到耳后:“倒是醒的刚好,比尔,过两天就是冬至节。”
朵拉停止歌唱,用一双缠满绷带的胳膊扣着父亲手臂,像小鸟落在自己最喜爱那一截枝上,怡然自得地摇晃。比尔·哈珀看着这舐犊情深的一幕,面上毫无感动之色。兹米亚也许情况开始好转,也许比半年前他们分别时更疯。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撕下一块皮膜来:“兹米亚,帮我摘掉储血器——你做得到,对吧?”嘴皮上新鲜疼痛电火花般闪烁,随即黯淡,猎人听着自己的声音,细细琢磨,感到它从未如此清晰,从胸腔里直蹦出来,轰隆滚过嗓子眼,每个词都像冷掉的铁块,硬邦邦砸在地上,“时候到了,我得走了,我得去结束一切。”
就是这样。
猎人对自己默念,没错,就是这样,他们在等我,唐娜,里奥,雷迭戈……兹米亚会理解的。
他低头,又灌了一口水,没有看朋友的眼睛。
过了有两三分钟,当沉默已变成种煎熬,比尔·哈珀听到医生堪称柔声细语地回答:“……比尔,即使摘除这个器械,您的身体也无法恢复如初。鲜少有猎人能真正脱离血液世界,您很难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您保证不去做危险的事,您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对吗?”
“对,当然啦。”比尔·哈珀听到自己蛮不耐烦地回答。
又是一段沉默,他妈的,今天太多沉默了,比尔·哈珀像在炭火上焙烤。
“但作为朋友,比尔,我很高兴看到你尝试做出改变。”兹米亚在用他冷冰冰的手指敲打手背,颇有节奏,食指,中指,无名指,倒过来,无名指,中指。
猎人感情上很想看着他朋友的眼睛,可理智遏止了他——别看,别他妈和他对视,他会发现的,他会发现你撒了谎。
他的选择很正确,半晌后,医生再开口说话时声音已平稳很多:“今天不行,您的身体太虚弱。冬至节前,我将为您做储血器摘除手术。”
“那就这样吧。”猎人回答,手里那只叫汗水弄得溜滑的水罐被放下,他往后一仰,接着翻身背对兹米亚躺好,阖上眼睛,“——那就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