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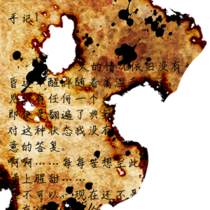





恩斯特要去花园采一束花。以往这项工作并不由他负责,但他决定今天亲自去采花。他像以往一样,仔细地洗漱完毕,换上干净的衬衫,从下到上扣好六颗扣子,套上代表神父身份的外套,再把黑色的圣带挂在身前。最后他擦亮了眼镜——在冬天是那么容易起雾——再戴在鼻梁上。恩斯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理了理几根不安分的头发,便离开了起居室。
白昼越来越短,天亮得也越来越晚,这时天还只是蒙蒙亮,气温比白昼更低。恩斯特怂了怂肩膀,想驱除包裹着自己的寒意。冬日悄无声息地到来,寒冷使一切失去原本的色彩。光线变得冰冷,绿树变成枯枝,湛蓝的天空变得惨白。而大教堂中的人也变得少了起来,因为寒冷,大家都不愿在外随意走动,见面时也像是害怕损失热量似的,不愿意多说几句话。空荡和寂静包裹着这纯白的高大建筑,给一切拉出长长的阴影,显得更加空旷,更加肃穆。
从纳塔城返回到大教堂,庆典结束后已经历数月,平静的教会生活几乎使他淡忘了一切。恩斯特回到了神的身边,投入到永恒的生活与工作中:读书,访谈,写作,整理文稿。外出的经历和规律的生活使他开始稳步地书写着,他好像获得了平静,也顺应了自己的天职。他也以为过去的时日和唐突的念头已被冰封,可上面已经出现裂痕。他路过了那尊纯白的圣母像,她不断地落泪。
去花园的路还是那么长的距离,但因为人少寂静,好像花了更久的时间走到。在这一路上,恩斯特没遇到任何一个人,就好像大教堂里其他人并不在似的。他回忆起童年时,大教堂可是个热闹的地方,多少人在这里来来往往,而自己只能在病室里看着其他人在教堂中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如今,他终于在这大教堂中获得了自由(当然只是相对的),但这大教堂却如此冷清,无人陪伴。他一步又一步前进着,感受着柔软的鞋底,以及光滑的大理石、松软的泥土、坚硬的石子所带来的不同的触感。这种感受过去对他来说是多么奢侈之物。他沉迷于这轻快的步伐中,最终忘记了自己已经到了花园。
这座花园虽然没有归属,但大家都知道照顾花朵的人是阿尔文神父。冬日的寒冷中,除了一些耐寒的花朵——例如三色堇、黄水仙或山茶花,还有雪白的圣诞玫瑰,大多都转为温室中培养。恩斯特刚来教会时,阿尔文曾让他在自己忙碌时帮忙照顾花朵,于是也将这些花朵的名字和样貌,还有习性,大致记住了些。久违地和这些花朵相遇,恩斯特感到有些感慨,当时还是春天,这里的花开的样貌并不如此,而且一片郁郁葱葱。现在,只有温室里还有些绿色,其余的地方草已经枯黄,少数的花朵点缀在其中。可他此刻没有心情去怜惜那些小花,他直接推开了温室的大门,去寻找他想要的花。温室内气温适宜,湿度极高,绿叶和盛开的花朵遍布各个角落,有灌木,有盆栽,还有爬藤植物试图抢占宝贵的光照,这一切让人仿佛瞬间置身于南国的丛林。他张望着,看着好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仅仅是这么小一个温室,就足够让他迷失。
“你在找什么?偷花贼。”
恩斯特吓了一跳,但也没有特别惊讶。毕竟来这里的人,只会是阿尔文神父。他回过头,看见高大的神父向自己走来。清晨的光斜射进来,透过绿叶洒在他的身上,让他身上的金色配饰像金子般闪烁,而洁白的长袍则被染上神圣的光晕。无论何时遇到他,他都如此平静而安详。他不会有自己的苦恼吗?不会遇到困难的事情吗?
“神父大人,早上好。”恩斯特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
阿尔文以笑回应:“你在找什么?还是说只是在这里找到夏日的回忆?”
“我打算去献花,神父大人。”
他们上一次好好聊天,应该是在恩斯特离开大教堂动身去猎人工会之前,他提交了一封诚恳的申请信,希望阿尔文允许他离开教会去采访,因为这对他的写作非常重要。那个时候恩斯特非常忐忑,自己可刚回来不久,一下子就要离开,根本不像是虔诚之人应该有的行为。可阿尔文只是听他讲着,简单看了几眼申请,便批准了——包括准备了马匹,还推荐了护卫(回想起来,若不是一路上有费恩陪伴恐怕到不了目的地),一切都安排得周到。恩斯特感觉有些受宠若惊,他给自己设计了一条苦修的道路,可神父却待他善良。然而回来后便是忙碌,他连汇报都没来得及,却巧妙地在这个清晨相遇了。
他有很多话想跟阿尔文说,但却不知从何说起。思考了一番,他从一路上的见闻开始讲,接着是认识的猎人们,纳塔城和工会的风光,最后传达了尤尔娅和帕拉帝索的问候。他一边说的时候也在回忆,那些经历依旧生动,细节也依旧具体,但却好像是过了好久,又像是从别的书里看到的故事,蒙上了一层别样的色彩。阿尔文只是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听完后,他闭上眼,舒了口气:“太好了,看来你收获颇丰。不过你回来得晚,我还担心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
恩斯特赶忙解释,他只是在纳塔城多留了几日,让神父担心了。之后,他们又惯例谈到了恩斯特的工作,阿尔提到他从其他人那里听闻《圣女传》书写得顺利,这令他感到欣慰,表示自己也想读读看。恩斯特听到了心中一惊,没想到大家竟在背后谈论。这些日子他的写作确实有进展,而且会给圣女本人和一些相关的人阅读,就这样传到了阿尔文的耳边。但那些内容在恩斯特的心中还远远不算成稿,自然也无法给阿尔文看。他害怕阿尔文失望。“还需要整理一段时间,神父大人……我只写好了一部分。”他羞怯地说,“等我完成了,再请您过目。”
“加油,孩子。不过努力也要适度,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阿尔文又眯起眼睛笑了笑,“不过你这么早到这来,是有什么事吗?”
听到这里,恩斯特才恍然醒悟,回答道:“我是来采花的。”
“哦,是你。”阿尔文将恩斯特引到一个角落,那里开满了百合,“请便,需要多少就采多少吧。”交代完之后,阿尔文便离开了恩斯特的身旁,去照顾其他的花朵了。百合们都直直地生长着,在最顶端开花,就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这一刻的绽放一样。恩斯特拿起一把花剪——一把精致而小巧的黄铜色的剪刀,使用得很爱惜——去剪他需要的百合。一靠近花朵,那熟悉的芬芳就更浓郁了。这一株还有花苞没开,这一株形态看起来不好,这一株花朵看起来比其他小……他精心挑选着合适的,终于剪下了足够数量的花朵。他把这些花朵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扑鼻的香味让他有些头晕。采下了这么多,花园中还剩那么多。恩斯特多看了几眼剩下的花朵,便转身向阿尔文道别,离开了温室。
他抱着一捧花朵在初冬中走动,而百合的花香让他觉得这是在夏日,让他感到一种错乱。为了摆脱这种不适,他仔细思考起当下的事情,和昨天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去献花。他回想起很多,关于花——昨天下着小雪,就像花瓣一样落下,凄美覆盖了的它的寒冷,让一切都有了一种温和的美感——就好像降临节或者任意一个冬季节日的雪,充满着祝福与喜悦。昨天的仪式就笼罩在这样的喜悦中,仿佛在冬季迎来一场迟来的丰收。
仪式结束后,一位偷偷观看了仪式的圣女找到了恩斯特,她仿佛也被这种喜悦所感染。一般来说,在如此人来人往的地方,恩斯特会避免和圣女有直接交集,而那位年轻的圣女执意拉住他,对他诉说。
“恩斯特神父,请原谅我拦住你,但是您看到了吗——您一定要记录下来这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以前只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这居然是真的。我想着,也许都是一种夸张,实际上这里会像是刑场一样一片死寂,圣女会控诉或者哀求,但是这仪式却如此神圣,鲜血的喷溅是如此的艳丽。我却在这里感到了神的存在——这是我和神离得最近的时刻。您知道吗?那些祷词,我们在背诵的时候,文化不好的或年纪小的都不理解呢,又或者像我,也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是需要背下来所以记住了。但是,在仪式上听到那些祷词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词的全部意义——您明白那种感觉吗?哦,您不是圣女,平时和我们念的应该不太一样。但您应该能感觉到,毕竟您的心离圣女们是如此之近。在仪式上,我感觉那些话正是对神说的,神就在倾听,即使我看不见神,但我能感觉到——因为我也念着那些祷词,但开口时发现喉咙发声的感触不一样,从骨头传来的震动也不一样,散播到空气里的声音也不一样,每个字眼的意思也不一样,这一定是因为神在倾听的缘故。还有空气也和往常不同,呼吸的方式好像也变了,还有雪也让人一点也不觉得冷,这真的很奇妙。是神的注视,神的倾听,神的抚摸改变了这一切。当意识到神的存在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我吗?我刚才感觉自己快要昏过去了。”
少女的声音在诉说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高昂,欢欣使得红晕充盈着她的面颊,让她看起来像三月的花朵。恩斯特一言不发,他知道她会继续说下去。
“以前听故事的时候,我以为圣女会不甘,会反抗,可当真正感受到神的时候,谁又能不信服呢?可能因为我的领悟不够高,只有在这仪式上,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神。那些年长的圣女们,肯定一直都在聆听神的声音,她们的心中一定早就被涤尽,让自身只为了神而存在。我也想成为那样的圣女,整日能感受到神,最好赶快迎来十八岁,前往神的身边,不然剩下的生活都已经变得无趣了。恩斯特神父,如果您写到我的故事,请您务必把我写得更虔诚一些。我终于明白自己就应该是神身边的人,这就是我的宿命。我希望属于我的献祭快点到来,这样我的生命才能真正拥有意义。”
恩斯特当时仍处于恍惚之中,可圣女的热情紧紧攥住了他几乎要随风飘走的意识,让他清醒地看着眼前的人,记住她说的每一个字。小雪依然飘荡在两个人之间,观看人群的仪式已经散去,而鲜血……溅洒出的鲜血,星星点点残留在薄薄的积雪上,就好像只是一个受伤的猎物,不经意间走过了那里。圣女倾诉完毕后,恩斯特和她一起回到了大教堂。在路上,一看到了其他的圣女,她便马上跑向了她们身边。恩斯特看着她们的背影,取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他多么希望奇迹发生,比如这副眼镜上附有魔法,能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而当他带上擦好的眼镜,世界并没有一丝改变,雪顺着风打在他的脸上,遇到体温后迅速地融化消失,四周的人群间的空气沉淀着仪式后的满足,而死去的人不会回来。
恩斯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除了冬季的凌烈便是花香。他继续向教会的西南角走去。
那天仪式结束后,恩斯特去看望了圣女珍珠。自从舞会后,珍珠便不太外出,恩斯特也有一阵子没有见到她。因为珍珠的特殊性,以及恩斯特工作上的必要性,恩斯特被批准去她的房间看望她,不过当然同时也有其他修女在场。不过即便谁在,都无法打破他们交流之间的隐秘性——和珍珠的交流是极为特殊的,除了所有圣女最后都会听不见以外,珍珠也看不见,唇语或写字也无法交流,必须要在她的手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才能对她说出想说的话。而写了什么,就算是普通人盯着看,也大多无法理解。于是对珍珠说过的话,也就成了两个人的秘密——至少恩斯特是这么觉得的。在询问珍珠的过程中,恩斯特花费了很多时间,这项工作需要十分的耐心,但他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因为她如此特殊,特殊到恩斯特觉得,也许圣女这个身份是适合她的,若不是这样神圣的身份,她也许会活在泥泞的苦难之中,是圣女的身份轻盈地包裹着她,让她接受到了足够多的温柔与爱意,还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但一切又是值得的吗,又或者只是自己缺乏想象?对于珍珠的事,他总是拿不准,同情这个词在她的面前已经显得浅薄。
珍珠所居住的那间昏暗的房间,让恩斯特想到童年时代度过的病房,因为朝向不佳而永远阴暗。珍珠坐在床上,头转向窗外的方向,也许是因为她感受到了光线。不过恩斯特可以看到,外面的冬季天空一片灰白,在那小小的窗口显现出一幅剪贴似的静止的风景。但由于听不见也看不到,珍珠一直都不能知道有谁来了,有谁在。她永远地活在寂静与黑暗里,暴露在虚无与危险之中。向照顾她的修女示意后,恩斯特坐在了床边。也许是为了照顾只能靠触觉生活的珍珠,她的床垫比教会通常用的都柔软,床单也要光滑许多,每次恩斯特来到这里,都会忍不住要抚摸一下,因为这像极了自己童年时的床上的触感。而感受到了人坐下的动静,珍珠才将她的脸面向了恩斯特。窗外的光照亮了她苍白而光洁的面庞,还有紧闭的眼上长长的睫毛。“是谁?”伴随着她的声音,睫毛也跟着微微地颤动。恩斯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已经习惯性地向上摊开——在她柔软的手心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就这么通过掌心交流着,就像是往常一样。珍珠开口回答的声音和手指在掌心中划过的声音交替响起,若不注意,就好像是她在自言自语。恩斯特多么想要靠近她的世界,可他不知道只有黑暗和寂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纵使在幼年时曾经见过一切,也曾经听见过心爱的人们的声音,而在时间的流逝中,那世界像久远的油画一样逐渐剥落,所有的声音也化作同一片潮声。他该说些什么呢?恩斯特在圣女的手心写着那些词,例如“雪”、“冬天”、“教会”、“写作”和一些人名,而圣女也静静地用触觉倾听着,等恩斯特写完那些句子再回应,偶尔也会被一些有趣的事情逗笑。他丝毫没有提起“圣女”、“献祭”、“仪式”、“血”这些词,恩斯特想,既然珍珠看不见,就意味着她有权利不知道这些事情。在离开前,恩斯特在她的掌心写下:“关于圣女的故事我快写完了,可惜不能念给你听或者让你看到。”
“没关系的,我相信您写下的,就是我们真正的故事。”珍珠回答道,脸上带着恬静的微笑。
真正的故事?什么是真正的故事?那些属于珍珠的永恒的黑夜与死寂里,世界的真实到底是什么?他想到这便痛苦不堪。他已决定不去以自己的感受去揣摩他人,可死亡、黑暗与无声的恐惧抓住了他的心,让他无法继续思考下去。恩斯特望着四周,冬季虽然不算舒适,但仍然有它独特的魅力。朝阳的光已经逐渐升起,给怀中的纯白花朵染上了些许暖色。恩斯特仍然置身于芳香中,一想到这些香味至少珍珠也能感受到,得到了些许平静。
一转眼,他已经来到了圣女堂前。花田在寒冬已经枯萎,可墓碑仍然耸立,而且又在角落中新添了一个。若不是经常来,谁又能发现这里增加了一块墓碑呢?恩斯特走过去,看着那小巧的大理石墓碑如此崭新,反射着明亮的光泽,上面刻着圣女忒弥斯的名字,与跨度为18的两个数字。这块墓碑不知在何时早已准备好,因为圣女们的离去早已注定。墓碑下的土壤也是新的,是夜里的葬礼时玛歌亲自埋上的,她那时的动作就好像是在种植什么一样仔细。恩斯特站在墓碑前,觉得自己心里空空荡荡。他什么也不能干,只好在坟墓前放下两朵百合。紧接着是下一块墓碑,再下一块墓碑……一些自己依稀记得的名字,素未谋面的人的名字,比自己年幼的人的名字,孩童时在这里见过的名字,已经看不清的名字……他轻轻拂去墓碑顶部的落灰,又用手指擦拭刻字,最后把百合放在墓碑前。愿鲜花能陪伴你们,他想。
打理好后,恩斯特仍不舍得离开。他在这小小的墓地间徘徊时,修女玛歌的身影映入眼帘。她缓缓地走来,走近,停在了忒弥斯的墓碑前。
“你居然来得这么早。”玛歌还是一贯的表情与态度,声音也平稳,可仔细看却能发现神色稍显疲惫。恩斯特问候了一声,便同她一同去看那墓碑。渐渐地,恩斯特发现她的眉头皱起,目光也渐渐垂下。平日里玛歌总是面无表情,甚至是看起来有些严肃,但恩斯特一看就明白,那些感情压在她的心头——愧疚、痛苦、自责……责任感与爱使她不得不背负那些。
“感谢你挂念这些孩子们。”打破两个人之间的寂静的是玛歌的话。但恩斯特又该如何作答呢?自己的挂念是如此微不足道,就像蚂蚁无法撼动大树的一丝一毫。而玛歌在圣女们身上投入的心血,和作为刽子手亲自执行的心境,岂是随意可以比拟的?洒在身上的圣女鲜血的气味与温度,还有第二个人能感受吗?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便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寂静重归于小小的墓园。
“我听珍珠说你去看她了。她很高兴。”玛歌说着,似乎想让凝滞的空气有所流动。
“是的……我和她聊了聊最近的事情。”恩斯特回答道,讲出的话在空气中转为白雾,“她……知道自己是下一个被献祭的吗?”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生日。”
恩斯特只是呼出了一口气,但没有再说话。过了半晌,恩斯特才问:“她们死后会去哪里?真的会去神的身边吗?她们在那里会获得幸福吗?”
“幸福……什么是幸福?她们活着的时候已经算是幸福……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也是一种幸福……活着只是活着,本身并不是一种幸福,人也不可能为了幸福活着。”玛歌的话语听起来有些悲观,又像喃喃自语,仿佛是在说给她自己听一样,“只有在年轻时才能毫无痛苦地死去。这个时候,她们还不知道活着意味着什么,自然也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她们享受着足够的关怀与爱,也品尝着谎言,以为献祭是像是花朵、蜜糖、宝石或者什么其他美好的东西一样,漂浮在这样的概念里。而一旦她们品尝到了真正的痛苦,意识到了生活的真相,遇见了难以割舍之物,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夺去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残忍的……所以我们只能让她们隔绝这一切。虽然对于神职者,这种与世俗的隔绝是需要的,但在她们身上是绝对必需的……”
恩斯特静静地听着,心想早有些人对自己说这些话就好了。他从昨天开始就沉浸在一种不真实感中,因为大家都为圣女的献祭感到欢欣雀跃,仿佛意识不到仪式中一个女孩的生命被夺走是一件恐怖而悲伤的事情。他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和身边的人交谈,他们的日常在继续,进行着和以往相同的行为,而恩斯特的思绪早已分崩离析。他融入不到自然的谈话中,只想大声叫喊你们刚刚见到了一个人的死,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可谁也不在意这些。无法说出的话卡在他的喉咙,让他感到窒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在以往看来是那么的善良而友好,而在此刻的恩斯特的眼中却像是非人的存在。这个世界竟是这样的,人们会为一个无罪的少女的死而欢呼。而被献祭的少女也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深受感动。生命到底是什么?她们的死又换来的到底是什么?而又是什么让天平取得了平衡?他不明白,他在道路上恍惚地行走,他在纸笔前出神,他在葬礼后的深夜里恸哭。那种异样的孤独感再次袭来——他不明白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和其他人划分得如此不同。
直到现在,听到玛歌的话语,恩斯特才感受到了一点宽慰。剥离了仪式的意义,圣女的献祭得以用“死亡”来讨论,并且保留了世俗化的悲伤。玛歌似乎在合理化一些东西,那是她处理这些悲伤的方式。而圣女的虔诚,仪式的喜悦,好像也都是为了合理化一些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规避实际行为的残忍。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献祭也是必要的——尽管恩斯特不明白个中缘由。在这些悲伤的外壳上,恩斯特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东西,他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也许是一种秩序。那东西确实有一些美感,但并不意味着恩斯特或玛歌要接受它,只是它确实存在着。
而此刻,他们两个人站立在那外壳下,静静着注视着圣女的墓碑。晨风吹过,百合的香味散开在空气中。
“那我又能做些什么?”恩斯特问。
“你已经做得很多了。”玛歌答道。
因为白天还有正式的工作,两人即便还想多留,也只能各自离开。玛歌知道恩斯特会回去继续书写《圣女传》,而她要去带领圣女们做晨间祷告。
在玛歌的眼里,恩斯特当然也只是个孩子,和被献祭的圣女们差不了几岁,因此他的心思也很容易被察觉。他与其他那些和圣女们有所交集的人很像,迷失在一种深深的失落里。那些人往往很难前行,总是停留在某一刻,不断地回顾、追寻、诘问一个不存在的回应。而有些不同的是,他总试图为圣女们做些什么,记录也好,陪伴也好,来献上一束花也好。他停留在这里,却没有停滞。但她也担心,也许有一天他会被累积起来的悲恸冲垮,无法再面对这些,毕竟他还很年轻,迟早会遇到刻骨铭心的那一刻。但是恩斯特多虑而敏感,那些客套的场面话一定不能安慰到他,于是她说了那些话。
不只是圣女,这个世上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甚至死得痛苦、难堪、毫无意义。然而这颗星球不会因此停止转动,太阳还是会升起,一切必须要继续。如同圣女们听不见,却仍要唱响圣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