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正x少女歌剧
文画/主线/强制打卡/
撕卡/投票排名/适龄18+
「在约定之地,
将此花予你。」
报名参与企划前,请先在qq群过审,并且于elf上传人设卡。
「阳光啊,照耀着这有七座城门的忒拜的最灿烂的阳光啊,你终于发亮了,金光闪烁的白昼的眼睛啊,你照耀着狄尔克的流泉。」
听到幕布后那歌队一同咏唱的歌声时,无论是墨绮飞诗还是渊上白鸟,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飞诗是因为尚不知道地下舞台与revue代表的真意,白鸟则是因为更私人的理由。就连白雾中她所见的幻象,都是与渊上家双亲的赌约,那么已逝之人的事情,应该已经深埋在她的脑内,而非被作为舞台的燃料提取出来。但这曲子,这歌词,是《安提戈涅》。也就是说,要么是她掩埋的过去终于反过来掩埋了她,要么是……舞台应和着另一个人的愿望。当然无论如何,白鸟也没有办法开口去问,你也失去了什么人吗?何况既然身在舞台上,就只剩下了说台词的余地。……特别是,在自己的对手好像确实没那么清楚情况的时候。
「安提戈涅,我的姐姐。」她急切地说,「克瑞翁已经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或哀悼那不幸的死者,使他得不到眼泪和坟墓。你当真要去埋葬他吗?」
「我不愿意人们看见我背弃他。」安提戈涅说,「你愿不愿意同我合作,帮助我作这件事? 你考虑考虑吧。」
「事情非同小可,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妹妹退却了,「我请求你,不要和城邦对抗。不可能的事不应当去尝试。」
「你这样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真是活该。尽管告发吧!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我就更加恨你。」
明明知道仅是台词,白鸟依然觉得被人当胸扎了一刀。刀刃深深地卡在肋骨里,埋进肺部,在每一次呼吸间带来剧痛。她无可抑制地落入遥远的回忆里,又回到那个炎热的、连尸体的腐败气味都无法完全遮掩住的夏天。
那一年,她也只有十一岁。房间里除了双亲外,就只有尸体躺在她面前。然后,她终于咽下一口苦涩的悔意。
如果能更早一些就好了。
「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不利于路数的时候躲避霜箭和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办法,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只是无法免于死亡。」
新响起的歌声让她清醒了一些。安提戈涅背朝她的方向,跪坐在那死者的尸体前,在上面洒了一把沙土。在没有办法掘墓的时候,这就是埋葬的完整仪式。她原本应该走下去了,但是一阵风吹来,将尸体表层的沙尘拂去。于是安提戈涅又从另一侧走上前来,再次洒下一把沙土。然后旋风再起,她就这么重复着这一工作,仿佛重复才是唯一的幸福。没有希望的不安、没有“探索”的使人焦虑的冒险性,也没有回忆的忧伤。曾经存在的,现在依旧存在。沙土在她身下累积,堆成高塔,铸就囚牢。
于是白鸟知道,她必须改变原本的剧情,否则这样的轮回只会一直继续下去。当她将那句篡改的台词说出口的时候,一束白光照到了她身上。现在,白鸟与飞诗终于平分了舞台。
「高贵的克瑞翁,有人违背您制定的法令,将那尸首埋葬了。」
「那人是谁?」鲜红如血的幕布后有一个威严的男声回应她。
「是我的姐姐,安提戈涅。她为这事情而欢乐,为这行为而喜悦。」
这是背叛,确凿无疑的背叛,与送她的姐姐去死无异——但那终究只是舞台上的角色,应当隐瞒秘密的妹妹不会为自身行动逻辑的改变而愤怒或悲伤。但白鸟对飞诗感到一些抱歉,因为这完满的、无尽的重复,显然出自飞诗的愿望。而后,愤怒的统治者对安提戈涅作出了宣判。
「把她带到没有人迹的地方,活活关在石窟里,使整个城邦避免污染。」
大地随着判决而震动。沙土凝结成死白的石墙,将安提戈涅吞没在其中。并非人世,并非冥界,并非即刻就死,也并非能生存下来。于是,少女说出最后的台词。
「唯有死亡才配做我的桂冠。」
靠在石墙另一面,沐浴在虚假日光下的少女口中吐出的,不是剧本中写就的话语。
“抱歉。我想要前往新的明天。”
她不会许下让死人复活那样的愿望,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过去。因为无论过去的哪一环发生了偏转,站在这里的都不是现在的她。何况,她早就知道要拿到什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想继续现在的生活就得不被发现,想自己决定婚事就要表现出色甚至夺得第一。过去可以思念、可以缅怀,但绝不能重演。
我没做错,她想,我必须继续下去。
仿佛那团白雾再次蔓延而来,雾中传来逝者的声音。她说,没关系,能看到你表演得这么出色,对我来说也是慰藉。雾气宛如女孩纤细的双手,温柔地将她拢住。
“不。”
白鸟闭着眼睛,向面前斩下一刀。胁差的刀柄上,鲜红的宝石灼热而温暖。
“我知道你不在这里。”
雾气翻卷,向半开的幕布后流淌而去。舞台上冷得惊人,仿佛如果滴下泪水,就会在落地前凝成一粒冰晶。白鸟呼了口气,忍耐住心中沉重的叹息。
如果能和你早些成为朋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办法和你互相理解啊。
那些,从雾里不断回归的无声之声——无法成为过去的时间回声。

在难得地获得了一个拥抱之后,白鸟好像整个人都开朗了几分。只不过因为再抬起脸的时候满眼是泪、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导致她有些不敢在上课以外的时段和同学搭话,生怕被人看出哭过。至今为止看破又说破的只有千极一个,于是白鸟决定自欺欺人地装作没有其他人知道。一到下课,她就匆匆地走出教室,生怕被人追上似的,差点要跑起来了。那双靴子在楼梯上踩下几级,忽然停了下来,转了个向。目标不再是下一层的练习室,而是三楼的空教室。昨天身体几乎脱力没办法过来,今天倒是正好——她透过走廊上的窗户,看到一名面容寡淡、几乎毫无特色的少女,正在编织着什么东西。
低头看了一眼腰带上的蝴蝶兰,白鸟抬手敲了敲门,隔着一段距离开口问:“是……入道云同学吗?”
宛如植物般的绿色眼睛转向她,声音听起来连惊讶的气力也没有:“是的。”
“这个,”白鸟从腰带上解下别针,上前几步,“是入道云同学做的吗?”
“是。谢谢你愿意收下。”芽的语气称不上温柔,只是毫无起伏。白鸟将它戴了回去,又问:“可以告诉我熏香是什么吗?”
芽几乎是有问必答:“是佩兰的蒸馏精油。”
白鸟点点头,仿佛放下了一切伪饰,诚挚地看过去:“记下来了。谢谢你!”
其实芽也不是很了解熏香的作用。但是依照习惯,向别人这么示好是被允许的。她只是再次道谢,并等待谈话结束。白鸟没有再留,青绿的马尾在身后摇曳着,很快就消失在教室门口。芽转过头,看到一只鸽子扑棱棱地从朝外的窗台上飞走了。
而白鸟走出教室,仿佛了结一段心事般地下到一楼,却恰巧看见两名少女正一同往医务室的方向去。如果是别人也就罢了,但那头长发挽起的方式绝对是祢宫,而另一头蓬松微卷的金发属于爱娃。她一震:难道是被挟持了?还没等想清楚,双脚就已经悄悄跟上。在她们走进医务室之后几分钟,白鸟也趁周围没人的时候溜进了门。隔着一层帘子,她清楚地听见了那边传来的笑声。
……真的假的?是那个祢宫同学啊?
白鸟诧异地侧过头,本来只是下意识地避开,却正好和坐在桌前的医生打了个照面。她一瞬间差点蹦起来,凭意志憋住了已经冲到喉口的尖叫。这、这太失礼了。医生没有在意她的窘迫,扬手请她在椅子上坐下。她迷迷糊糊地走过去,落座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该说些什么。于是,几乎没有思考,嘴唇就自己动了:“……我之前,确实有从您妹妹那里得到关照。”
与那时的不忿相异,现在的白鸟平和了很多,甚至带着几分感谢。她得到了再生产、得到了个人舞台、得到了胜利的机会。如果不是在那种境地中以命相搏的话,她恐怕还沉浸在失败的绝望里。
医生了然地问:“不和她亲口说吗?”
“才不,反正她肯定能知道。”白鸟稍稍鼓起脸颊,仿佛在赌气。反正和医生说也是一样的吧,她这样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帘幕的方向,然后悄悄笑了。
看到渊上白鸟在咖啡厅打工时,樱班的同学们原本不是那么诧异的。令人更加惊讶的是,她原本几乎是标志性的高马尾消失得全无踪影,长发被剪得不到齐肩,看上去……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也不怪她们这么想。一份报纸已经详细地揭露了她身份的虚假,连同多年前一名顶着她名字入葬的女仆也被提了起来,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连九条家也提出了再议婚约。渊上家大失面子,本想装傻到底坚称绝无此事,然而几件家族内部的秘事一出,本就因糟糕的财务状况忙得焦头烂额的大人们不再管白鸟的事情,明面上以忤逆的理由将她从家中除名,同时断绝了一切资金供给——虽说本来就没有多少,而时院的学费并不会退回来。因此,白鸟开始在时花剧场对面的RoseCrown兼职了。
当然,对于白鸟来说,这反而是件好事。唯一有些麻烦的就是点单时要一口气把名字全念出来,不过,经过歌唱与念白训练之后,她可以做到以平稳的语调和偏快的语速清晰地念出“特制容颜巧克力佐法式海绵蛋糕三重雪山蛋糕”,或者“淡黄油风味丝绒拿铁与手捣柠檬玫瑰香红茶”,诸如此类完全过长的名字,并且对此的态度还是“长名字是店里的特色”,虽然有点苦恼但全部接受了下来。
她礼仪周全地接待了同班同学们,安心地收下尚在正常范围内的小费。黑白相间的身影穿梭在餐桌间,相称得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在这种时候称赞她适合做女仆什么的,未免太戳人伤疤了,几个人互相看看,到底只是多点了几份甜品,并在用餐后被提着裙角的白鸟优雅地送出门去。
过了人最多的时候,白鸟舒了一口气,转过头打算歇上几分钟,却隔着玻璃看到了一个浅粉的身影。九条百子推开了门,热络地开口:“小白鸟——!”
这是客人,是客人。白鸟提醒了自己两次,摆好营业用的笑容走上前去。百子绝不是第一次来,却兴致十足地打量起店里,点了双份的甜品,然后要白鸟坐在对面陪吃。白鸟只是坐了下来,警惕地一口没动,准备听她说些什么。在闲谈了几句没营养的杂事之后,百子终于迈入正题:“话说,小白鸟还想和我成为一家人吗?”
白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困惑:“我以为婚约已经解除了。”
“不不,我弟——妈妈可非常喜欢你。”百子摇摇头,忙不迭地补充,“不愿意也没关系!你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就当是我们家的女儿一样!”
“还是请让我拒绝吧。这份善意太重了,我还没有到那种需要依靠别人才能活下去的程度。”白鸟平静地说,“我有自己的工作。”
“啊,工作!”百子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拍了拍手,话语冲口而出,“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工作呀?在我们家,薪水又丰富,休假又多,而且还可以自由恋爱呢!”
仿佛有个开关被按下了一样,白鸟脸上慢慢地浮现出不带温度、仅是出于礼貌的笑容。这次开口时她说得很慢,语气却不容置疑:“我认为目前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那么,那边的人还在叫我,失陪了。”
她转过身,迎上下一个黑发的女性客人。一直等到对方点好餐,白鸟才开口:“谢谢你装作和我不认识。”
“你太客气了,本来我就该在外面这么做的。”大上她几岁的女性说,“看起来你过得不错,真是太好了。”
“你的报导对我带来的只有好处。”白鸟轻声回答,“多亏了你,我才能自由。”
“你说要给我个大新闻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跳。”
“那确实是个——哦,不止一个大新闻,不是吗?”
两人不约而同地弯起眼睛,藏匿一个秘密的微笑。
这是大正十二年的春天,一位曾就读于龙胆花班、却早在第一学期就退学的女学生的葬礼。
实际上,渊上白鸟并不想来参加葬礼。但无论是婚礼还是葬礼,都是社交的重要一环。这名逝去的同学也曾在时花就读,然而并未与她同班,甚至没有几次照面,让白鸟难以产生真实的悲伤,好在(好在?)没有什么人会注意这点。宾客们并不都保持着沉默,当然有将少女的死当成谈资的人,因此白鸟能悄无声息地躲在阴影里,从悄声说话的人们口中听到一些流言。
据说死者性子古怪尖刻。任何一个表现不够好的大小姐都可以被冠上这样的名号。
据说死者是从时院自主退学的。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理由,但退学到底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华族也不可能为此召开什么说明会。
哦,还有。据说死者是自杀。该论调一出口就引来了驳斥。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为什么会自杀呢?她又不像那些庶民出身的学生,又或者一个女仆……再差一些,一个农家的孩子,那些上不了时院的庶民,甚至要更命硬呢。所以,一个人推定,万一真是自杀了,那也一定是读书读坏了脑袋。
听到这里,白鸟就不想再听下去了。所幸,最后一个宾客到来后,众人就从座位上站起、在棺材前排成一条不带丝毫暖色的长队,从葬仪师手中取来花朵放进棺材,遮住已被收敛的遗体。出于尊重(当然不是对死者而是对她家族的),他们都没有出声。棺材的另一头,那名年轻的死者在仅有黑白的相片中看着这一切。线香被点燃的那端仍然有稀薄的烟雾飘起,遮住她的眉眼。而房间最深处,是一帘平整的鲸幕。
即使白鸟再次屏住呼吸,也没听到一声应由亲近之人发出的哭泣。对华族来说,尊严就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吗?为自己女儿的死而哀哭,难道就会损害他们的尊严吗?
转眼间,她已经排到了靠前的位置。棺木的黑色给人沉重之感,白鸟尽可能轻柔地放下一支小雏菊,和它的同伴靠在一起,遮住了死者的半个面孔。实际上,遗体露出来的部分也只剩这么多了。
忽然,白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给人平静之感的长发,有着严冬中常绿林带的青色。她转过半张脸,手中落下一支洁白的雏菊。这并不是个适合打招呼的场合,所以白鸟保持了沉默,只是远远地望着。那张脸上无悲无喜,双眼像山顶不化的积雪,却与一旁线香长燃所洒落的灰烬十分相似。
那朵雏菊恰好横在亡者的脸上,遮住了她无法看见春天的双眼。
“你在这儿干什么?”
九条百子的背后响起一个声音。是个年轻的女声,悦耳,优雅,离她不算太远。她从废楼的门口转过头,看到巷子里走出一个人影。青绿头发的少女,偏偏有着鲜红的眼睛。短裤和短袖看上去就是个正当年纪的女大学生,只是这副打扮在夜间未免会有些冷。
“哎呀,这地方看上去挺好玩的。”百子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几步跑到对方的面前,“怎么?要一起去探险吗?”
“不了。”少女谨慎地退开一步,“你不觉得有点渗人吗?还是早点回家吧。”
“哎?那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呢?”
“我在夜跑。从附近经过的时候听到这边有人声,所以过来看了一眼。”
百子盯着少女,盯到对方想要开口说话,猛然绽出一个笑来。
“啊~是这样啊!那你能陪我回家吗?”
“……啊?”少女一时间张口结舌,仿佛想要拒绝,却一时间找不到理由——实在是百子的态度太过理所当然,让人下意识觉得应该接受。她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于是百子高高兴兴地来挽她的手,再次被她躲了过去。但百子终于在走到自家门口前问出,她的名字叫白鸟。
白鸟在把百子送进门后,终于叹了口气。对她这样新生的血族来说,抛却作为人类的习惯还是有些难的。比如,她应该对送上门来的食物满怀喜悦地取用,而不是把她从可能被袭击的地方带回安全的家里。
她再次接近废楼,而后潜入阴影。血族们有时会在这里集会,好在今天没什么人在。白鸟刚刚推门上楼,就撞上一双同样血红的眼睛。
“是白鸟啊。”白发的少女眯起眼睛,虽然外表看起来和白鸟的年龄差不多,实际上却已经当了不知多久的长老;何况,她属于那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不只是说秘盟,统治这座城市的亲王正是Ventrue,他们大多身居高位,被称为蓝血也是名副其实。略千极在其中属于相当低调又温和的那类,因此她的下一句话在白鸟耳中才更加石破天惊:
“你什么时候和猎人有交情了?”
“……猎人?”
白鸟愣了片刻。她知道猎人们致力于追踪或摧毁怪物,但她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猎人。说到底,他们也只是人类而已,外貌上不会有什么表征。不像血族们,即使有那么些特例可以拥有正常的体温、与活人无异的灵气、饮食的能力,大部分也只是会动的尸体而已。所以她才避免和活人碰触啊。
“刚刚被你送回家的那女孩。”千极出言提醒。白鸟一个激灵,突然明白了什么。
……所以说,那家伙是来调查的猎人?明明一副那么无害的样子?既然那么善于伪装,是不是已经察觉到她的身份了?糟了糟了糟了……她下意识地抱住了头,迟迟地听到自己已经把这一切说了出来。在一位长老面前,这是何等的失态!他们总说暴徒这一氏族(Brujah)易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现在自己岂不是把指控坐实了吗?白鸟哀鸣一声,开始为自己的抓狂而道歉,忽然感觉肩膀上被拍了拍。
“没关系的。现在你知道她的住处了;而且,有头脑的猎人们不会贸然开启战端。你没有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白鸟终于松了口气。忽然,她的头顶落下一点重量;是千极抬起手,顺了顺她色泽鲜亮的头发。
奥林波斯山一片喧哗,十二神齐聚于山脚下,厄瑞克透斯在多岩薄地上所建起的城池前。这城邑如今虽然鄙陋,然而他日必将成为最光荣的城邦之一。十二神中的两位,为争夺这座城市的命名权,一直吵到了主神宙斯面前;于是主神择定了这个日子,为他们进行裁判。所有城池的居民都站在广场上,手持各自的一块陶片;他们有权决定,要尊奉哪一位神祗。
“我是克洛诺斯与瑞亚之子,海神、地震之神、风暴之神,神圣的波塞冬。”乐乐浦世凪站在神座左侧,几乎与她登高的三叉戟立在地上,甚至还有水滴从尖端落下,折射出虹光。
“我是宙斯和墨提斯之女,智慧女神、战争女神、艺术女神,光辉的雅典娜。”渊上白鸟站在神座右侧,仅持一柄胁差,而非女神那柄战无不胜的长矛与用美杜莎的头装饰的盾牌。
两人的目光相撞,却是白鸟先动了。她将刀尖插入地面,立即有细嫩的新芽从土壤中长出,迅速地抽条长叶,在开过一茬细小的白绿相间的花儿后,结出椭圆的绿色果实来。
“这是橄榄。”白鸟优雅地举起一只手,让枝叶沿着自己的手臂向上生长,“它的树干是优质的木材,果实既可以吃,又可以榨油,是和平与丰饶的表示。我允诺你们幸福与自由,让你们健康且强壮。”
人类们默不作声,而小小的波塞冬动了。她以与外貌毫不相称的力度,重重地将三叉戟刺向地面。土地立即裂出一道深深的伤口,海水蔓延而出,翻卷的雪白浪花化作一匹与其同色的骏马,额头上有一颗黑星。白马悠然地踏过地面,留下深深的蹄印。
“此乃我之馈赠。”世凪傲然地举高三叉戟,海水仍从尖端近乎锐利地落下,“跟随我,仰望我,尊奉我,我赐予你们在任何一场战争中的胜利。”
白鸟稍稍皱了皱眉。对于一个有大量的河流、并且靠近海案的城邑来说,海水称不上礼物,而马匹也有些不便。按照原典来说,自己也该是赢的那个。想到这里,她抚了抚橄榄的叶片,笑道:“我的礼物比你的更好。战争只会带来痛苦,而人类应在自由与幸福中长大。”
“那么就投票吧。”世凪看向她,眼中并没有任何白鸟以为会存在的东西。期待、了然、凶狠、平静,都不存在于那片绿色中。
宙斯扬了扬手,赫尔墨斯宣告道:“此刻即是裁判之时,向那两个罐中投下陶片吧!这座城邦若是归属于雅典娜,便叫做雅典;若是归属于波塞冬,便叫做波塞冬尼亚。”
标明雅典娜的那个罐子里,很快就积了一大堆陶片。白鸟朝世凪投去视线,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还能表现得如此平静。这座城市会被称为雅典,是已经确定的事实。难道说,世凪会重演那一幕吗……“波塞冬一怒之下淹没了特里亚平原,将阿提卡沉入海底”?如果是那样,她也准备好了应对。
两个陶罐很快就被装得半满了。不需凭借主神的权能,凡人的肉眼就判断出哪边更多:是属于雅典娜的那个。白鸟上前一步,准备迎接自己的胜利,却听到赫尔墨斯清朗的声音喝道:“根据投票结果,将雅典娜放逐!”
如遭雷击的同时,白鸟意识到了这是什么——雅典的陶片放逐法。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就连苏格拉底都无法幸免。
“为什么?”她看向那些投票的女性市民们,刚刚她是以多么欣慰的眼睛看着她们投下罢黜自己的一票,“你们竟敢放逐你们的女神!”
有些人背过身去,而一声尖叫传来,几乎刺痛白鸟的耳膜:“我们又不想死!”
波塞冬是战争之神。那涌出的海水就是威胁:如果人类不尊奉他,那么他将带来痛苦与死亡,以无穷无尽的战争毁灭城邦。
白鸟一时怔住,随即咬着牙从橄榄树干中拔出了刀,青枝碧叶轰然倒塌:“明明我和你们才是一边的!”
“雅典娜,你想反抗父亲的权威吗?”世凪将三叉戟正了过来,明明比她要矮,看她的样子却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是宙斯的女儿,你属于他。她们不是属于自己的父亲,就是属于自己的丈夫。”
“难道你甘心接受这一切吗?”白鸟刺出一刀,满怀怨毒与愤怒,“嫁给某个完全不了解甚至没见过的男人,冠上他的姓氏,然后一生都被绑在他的家里,死了都要和他葬在一处吗!”
“嗯,对我来说,那就是幸福哟。”
这完全是世凪真心的话。她几乎是诚恳地劝导着白鸟,连攻击的速度都放得很慢:“这样一来,其他的家人也能幸福哟。”
白鸟怒号着,掩藏秘密的理智终于被烧得一干二净:“他们才不是我的家人!我只是作为替代被养大的,庶民出身的女仆而已!”
“这样哟。”世凪的眉毛动了动,“那么,你应该感恩哟?现在的生活,比之前的要好很多吧?就算想要反抗,也只是小孩子的胡闹哟。”
——那根弦绷断了。白鸟完全放弃了闪躲,把全部的心神都投到刀上。更快、更快、还要更快,否则不足以斩下闪耀,斩断自己周身的束缚。世凪娇小的身体,此时变成了麻烦的障碍。直到三叉戟的尖端将她的披风钉在地上,背靠地面的白鸟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的侧腹与脚腕留下了数条狭长的伤口。她感觉不到痛。愤怒依然在胸口燃烧着,尖叫着——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看,又弄伤自己了……”世凪低下头打量着那些伤口,从三叉戟刺下的裂口处,咸味的海水再度涌了出来。海神继续说着:“你现在有的一切,都是渊上家给你的哟。没有钱的话,就没法上学。为什么享受好处的时候不说呢?被你替代的那个人,要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定也会满足哟。”
海水充满了整个舞台,水面还在不断上升,很快就淹没了平躺的人的头颅。世凪看向水面上的倒影,不知为何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稍微冷静一下吧,她无声地对水下的白鸟说,但却没有看到任何气泡冒上来。咕咚、咕咚。白鸟咽下一口又一口海水。好苦,好咸,如同泪水,不能一饮而尽。水体压迫着她的全身,好像要把她压碎了。无法呼吸。好想流泪。好想抛弃所有的悲伤。如果可以变得透明、溶化在水里的话——
白鸟切断了自己的穗带,从水中坐起身体,被打湿的头发贴在脸上,继续朝下淌着水珠。如果说刚才是不想放弃闪耀的话,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心情了。披风顺着水漂远,她没有投去任何视线,甚至并未给自己的对手留下一句话,就沉默地乘着电梯离开。
电梯一路将她带到顶楼。幻想的舞台上留下的水迹,也在回到现实时被蒸干。
空气没有水那么沉重,允许她在最贴近天空的地方歌唱。今夜无星无月,人工湖的水面上却波光粼粼。白鸟张开双臂,带着纯然的喜悦与抛下一切的轻松感,向着如同他人口中描绘的未来一般闪闪发光的、广袤无垠的黎明,踏出一步。
凌晨五点,白鸟从梦中惊醒过来。日轮红得刺眼,宛如流血一般。好像被什么所指引着,她怔怔地爬起来,轻轻地推开门,而后开始奔跑。在废墟一角,原本靠近人工湖的地方,立着一个金色的人影,仿佛早已等待她多时。
那些天鹅哪里去了?白鸟抛下这个念头,朝那个熟悉的身影跑去。然而,她越是靠近,步伐却越慢。仍然是医生那张脸没错,但气质不太一样了。医生就绝不会穿这么鲜艳的颜色,或佩戴如此之多的首饰,除去颈环、耳坠与戒指外,她颈边还盘绕了两圈珠链,莫名地泛着白骨的珠光,美得像一只重获自由的野兽。生物本能的示警在白鸟的脑内尖锐地鸣叫着,可某个想法让她向前踏出一步、又一步。
她在这里……她不在这里……奇怪,她在这里?白鸟像只视觉失灵仅剩嗅觉的动物,走到对方面前时,才惊觉自己已经走出了这么远。一根手指就点在她的眉心,语气有些奇异的熟悉,莫名地让她想到茶与酒的混合物:“我(她)就在这里,把你的所有记忆串接起来吧,那一切合在一起就是我。”
白鸟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将停留在自己皮肤上的那只手握在手中,声音不安定地发着抖:“啊……是我看错了。美是某种人类无法理解的恐怖,每一种恐怖则都是生者对于死亡的预演……”
仿佛没想到她会这么做,祢宫的眉毛抽了抽。白鸟就这么盯着她,眼睛睁得越来越大,竟然自言自语起来:“那么,我问你应该就可以了……吧。你知道……在这里活过的人,没有出现的人,还会出现、不,还有哪些活着吗?”
“只有你们这些对死亡的形状触不可及的生命才会试图理解和描画它的形状。也好,反正你此时浑浑噩噩,不如就把接下来亲眼所见的一切当成噩梦未醒——”那只有着尖锐指甲的手反握住她的,将白鸟用力一拽。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反抗,白鸟只觉得身体一轻,才发觉扯住自己的手凉得刺骨。她之前怎么都没有发现?然而当她将视线投向四周,顿时为不应出现在现实的景象而愕然。周围的废墟和天色都如同融化一样淡去了,而有着金褐色皮毛的狮子,正在啃噬直立的人形。少女们静默得宛如羔羊,被砌进石质的雕像中,即便如此也无法保持永久的存续;碎裂成块的雕像们、有着她熟悉的同学的面容的少女们,正被几名狮面人身的侍者收敛起来、打扫干净。
一声惊呼差点就从她的喉咙里钻了出来,幸好白鸟深深咽了一口气,将声音坠了下去。她几乎是下意识地挣扎起来,然而那只宛如利爪的手的钳制刚刚松开,她就不受控制地向下坠去。比刚才更快地,白鸟扯住一只近在咫尺的手臂,地面终于重新回到她的脚下。然后她意识到这是祢宫。
“还算识相呢,”祢宫头也不回地说,“不然你不会想知道自己会掉进什么地方。”
白鸟差点又想松手了,靠仅剩的理智抓得松了一些。意识到对方没有把她扔下去的打算,她才攥紧了手。声音忽然从前方传来:“你不是想要知道你身边的人们现状如何吗,别盯着我,看看周围吧。”
仿佛被什么所指引着一般,白鸟抬起头,看到了自己的脸。由大理石复刻的她带着近乎哀戚的笑意,额头却突兀地裂开一道缝隙。
石像的裂口还能恢复吗?她问,在从祢宫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又心存侥幸地询问碎块的下落。但想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些她没见到的人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也不是你眼睛的疏忽。”引路的主人叙述着,仿佛这是一段历史,“那就是死亡,齑粉一样轻飘飘的死亡。”
有什么忽然卡住了她的喉咙。白鸟想要说话,想要叫喊,却连一个字都无法吐出。并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障碍,令她窒息的,只是单纯的沉重感而已。
四周的场景已然变成了和式的长廊,白鸟被扯了一下,便愣愣地挨着祢宫坐下,扯住她的袖子替换了手臂。在那个短暂的、松开手的间隙,她脚下的枯山水砾石不稳地荡漾着,告知她此处也并非现实。少女们的石像依然宛如永恒般静默地伫立着,凝视着她。白鸟仿佛被这目光扎了一下,转过头急切地问:“即使碎掉了……也不代表死是吗?还是说你的定义与我们不同,还要彻底遗忘才算?”
“……大概就是你这样的敏锐让我可以对你多出一些小小的耐心吧。对于像你这样,要依靠肉身禁锢住灵魂才称得上活着的生命,映射在此地的粉碎就代表着意识已然逃离人世,这是确凿无疑,绝无回天之力的死亡。而因粉碎而模糊难辨的面孔和身形,也自然无需你去辨认了。”祢宫挑了挑眉毛,不知该算是赞许还是责怪,或许两者兼有,“在那种规模的灾害蹂躏之下,这样的死亡再泛滥寻常不过。但你很奇怪,渊上白鸟,你的肉身并无折损,但映射着你的塑像仍然发生了迸裂。你的意识和未来又变得不够活跃,这简直是对我先前工作的直接投诉。”
白鸟猛地抬起了头,清楚地听到她有些失去耐性的话尾:“你的前路不仅了无妨碍,甚至还会因为此次劫难所致的他人之死而更显一片坦途,你到底受什么拖累。”
“在这样的灾害面前,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那样的话,我就真成了冰冷的石头。”少女轻声回答,“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会感到高兴的。我唯独不希望……我的未来,要将他人的死作为垫脚石。”
“连坐享其成也少不了背负自责,这份寡断啊。但是,即便这人心道德如同律令一般不许你为自己所得而欣喜,难道你也要放任它变成你今后所有行动的负重吗?”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语气却变得温和了下来,“因为悲伤,因为懊悔,你似乎又无法把自己坦然展示在舞台上了。难道把自己变成分明灵魂充盈的假死者,就能告慰真正的死亡了吗?”
“……医生?”
这语气无疑属于祢宫百目,然而对方没有回应她的呼唤。白鸟垂下头,继续说了下去。
“如你所言,我终究只是个凡人而已。我们没有翅膀,因而无法靠自己飞行。时间会把一切都掩埋掉,让我现在的悲伤和后悔,都变成能一笑而过的东西;所以,现在我必须容许自己坠落。”
她放开了扯住那袭宽袖的手。沙砾立即将她捕获,而一只手迅捷无伦地握住了她的手腕。
“别急着自顾自陷进去,渊上白鸟。不要以为你要去到的是什么想要脱身也随你心意的地方。”那只手的主人说,“虽然我见多了这里的塑像随时间与劫难湮灭的景象,但无论是哪一部分的我都不希望太早看到你也融进流沙碎石之中。”
白鸟扶住台阶,再度坐在廊下,看到几头狮子围拢过来,嗅闻她的衣袖与头发。她惊慌地往祢宫的方向靠了靠,后者比了个手势向旁侧一挥,它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这下,白鸟和祢宫说话的声音都弱了几分:“……我要说下一句话了,你承诺不会松手,我再说。”
“当然,渊上同学,用你给予了信任的那个我的身份作担保。”
啊,是她,这是医生。白鸟几乎要感动得流泪了。她像个故意犯错的坏孩子那样,局促地抓紧了手中的衣袖,嗫嚅出声:“我只是想试试。……试试你会不会抓住我。”
年长的女性并没有生气,只是继续说了下去:“可是你要知道,虽然在此时我能够仅凭一己私欲不让你沉溺于既有的死之中,但离开了这里……或者说,当这个噩梦醒来的时候,我也要确认,你能够有充足的理由和气力回到生者应在的舞台上才行。”
少女仰起头,注视那双细长的、睫毛垂落时宛如鸟羽的眼睛:“医生,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明白的。我不止为我一个人而活,所以也不会轻易死去……至于理由,我也有。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罢了。”
“死的恐怖与生的愧疚仍在召唤你,那不是你该听取的,你应秉持的死仍应当是那个美丽而遥远的概念,无论它在你面前掳走了什么,你只能继续书写自己的故事,直至它的亲吻为你的结局封蜡。”
这声音是如此温柔、如此平静,仿佛已经如同流水一般、一眼看遍了她的整个人生。白鸟不自觉地发起抖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在一片平静的紫色中找到自己的身形:“……我好害怕啊。我好害怕啊,医生。”
她的话声好像一个幼子忽然被弃置雪地,所发出的哀哭一般。那是人类最大的恐怖,是被笼罩在死亡投下的阴影下,发觉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长存的绝望。所有人生命的终结,一条仅有自己可以走上的路的尽头。从无有到乌有,可以忽视却无法逃离、可以想象却无法理解的,无。
“你不止为你一个人而活,这个念头就如同你袒露心绪之时一同露出的烙印一般,首先你学会不把它带来的疼痛当做形成动力的鞭笞,而如今……”深色的发梢垂坠而下,宛如编织纽结用以占卜或记事的细绳,几乎与其投下的阴影同色,“渊上白鸟,再深刻的烙印也有结痂褪色的时刻。它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但现在的你或许已经远离了使其反复破溃,久不愈合的根源。”
宛如天启,宛如神谕,宛如轻柔地将噩梦中的人唤醒。她最后说:“你不必再为了它而坚持不再轻易死去,而我也并不觉得这会削弱你生的动机。”
勒紧喉咙的窒息感缓慢地褪去了。白鸟避开石像的视线,闭上了眼睛:“我可以对……自己完整地活着这件事,自己得到您的偏爱这件事,还有……自己受益于这场灾难的事,而感到庆幸吗。”
“你清楚这桩桩件件在这天灾人祸,断壁残垣之中都称得上凡人至福,若是毫不为此而庆幸,我反而要特别小看你了。”
即使是如今的白鸟,也能轻易地从变换的语气中辨明,如今是哪一位在出声。那美丽的凶兽继续说道:
“感到庆幸,酝酿希望,并且登上舞台将其传达,如此也就不是卑劣的窃喜了。那岂不是人们最喜欢的光明伟岸之行吗,而你的理由和决心,也正是向着那样的未来才生发的才对。”
大概是还有些恍惚,白鸟竟然有勇气抓着她的衣袖,像小孩子似的摇了两下:“……请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我如果真有怨怼,刚刚何必把你拉进这里,任由你在余震中跌倒,被坠石砸死才好。”
虽然这话听起来像是还在生气,但白鸟的精神忽地一松,将自己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所以我不是说了,为得到偏爱而庆幸吗。”
眼看着那些狮子又投来目光,她赶紧又说道:“其实我还有问题。与我自身并不怎么相关,但也不只是为满足好奇心的问题。”
“……你这会儿不想着要坠下去了?”祢宫没计较这说法,终于舍得一个笑脸,而白鸟堪称莽撞地问道:“你能看到多远之后的未来?人类灭绝的那一天吗?如果你不能在时间中往复,到了那一天,你又会如何呢?”
“你在关心自己远远目不能及的问题呢,渊上白鸟。比你和你今生所有荣耀的死亡更远。”
“那还真是遥远。”白鸟并不觉得这话语傲慢,反倒若有所思,“而我必须也只能生活在当下才行。”
“这不是说出了刚刚进来时的你绝对说不出的话吗。若不是你的手还拽着我可怜的袖子,我恐怕会想给你鼓掌呢。”
“……那就不必了!如果我的愿望有实现的一天,到那时候,才需要掌声。”
“选拔的胜者,被称为top star的那一特权吗,其结果要见分晓可是余日不多。若是你剑指那一处,也就更不该耽搁在刚刚的生死为难之上了;当然,耽搁在此时与我共度的噩梦之中,也是不妥。”愿望多半也就那几个,祢宫可以猜得出来,“能问出刚刚那种为人之身不应该过度好奇的问题,看来你的心绪已经舒展开来许多,不再受无关外物侵扰了。这样的话,你也就不必留在这里,更用不着我提供这本质为侵蚀的庇护,此处无力困住灵魂的人之沙砾不再能够使你溺毙……你还不放开手吗。”
如同身在梦中、或许也确实身在梦中般,白鸟喃喃道:“……这是坠落,还是飞行呢。”
“真是冥顽不化的思考方式,又顾虑起来了。不触及死的坠落,不超越生的飞行,并无区别。你就醒来吧,今晚那争夺闪耀之顶峰的舞台上可还留有你的席位。”
祢宫没有想到,白鸟转过脸来,松开手之前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医生说,我信任的那个你……但其实不只是她。我当然信任你。”
天鹅展开了翅膀。飞行和坠落之间,只有一纸之隔。但那双翅膀承载的愿望,终于展露出了具体的形态。
「我要成为top star……然后让一切想要活着的人们,都不必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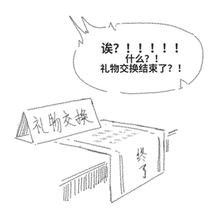

观众想必会大感诧异吧。从一开始,激烈的乐声与喊杀声便将剧情推向了高潮,仿佛为了彰显舞台主人的迫不及待般,装置几乎是超负荷地开始运作。武士们或持长刀,或持弓箭,投身于杀戮的舞池之中,连敌人的头颅都来不及收割,自己的尸骨更是无暇收敛。几乎是顷刻之间,人的身体就如同薪柴般堆满了地面,而一弯月弧朗照高台。笼罩高台的重重帘幕上,映出两个人影。
“晚上好,今井同学。您见过如此的良宵吗?众人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要将这高楼推倒、寺庙烧尽呢。”
端坐于左的人影声音悦耳,仿佛乐见这场暴乱般低首看去,长发高高地挽成一束,从后脑直垂而下。
“那些只不过是凡庸的庶民而已。在我们中,有异心的人是你吗,渊上同学?”
正坐于右的人影短发齐耳,语气与坐姿同样高傲却有礼,并未向下投注半点视线。
“不错。这种凭出身注定一生的时代该结束了。”渊上笑道。尽管这不是原本的剧情,但确实是她应有的心声。早一些结束,她也能早一些变得自由。而生为华族、也作为华族成长的今井驳斥得毫不留情:“身为华族却心向庶民,真是异想天开——或者说愚蠢。”
她曾经也面对过这个问题。即使不是出身华族,但被华族所供养,她的正当性也自然失去了;但被业火灼烧过一遭后,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加上既然婚约已定,隐瞒身份也不再有其必要。再出声时,渊上仿佛有些气息不稳,却咬紧了牙关:“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托名华族,以身相代,正是为了今天。”
不能说她没有期待。她一直想象着,其他人知晓她身份后震惊的表情与反应。哪怕是被欺骗的恼怒,或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厌恶——但对手的回答平淡到让人失望。
“那又如何。你是胜不过我的,只会被我碾碎而已。”
仿佛并不关心敌手的过去,今井起身拔刀。藤原朝臣兼光的刀刃一闪,便在帘幕上割出十字的形状。渊上挥刀的速度几乎与她相同,只是胁差到底无法像双刀那样同时斩击,只能反复两次以刻下同样的形状。透过星痕般的破口,随处可见堆叠的尸骨。红色染尽她们的双眼,仅有渊上露出不忍之色。今井已经以双刀之一架住她的胁差,之二在她身侧留下斩裂的伤口:
“现在露出这种表情有什么用?破绽太多了。”
渊上嘶声退开几步,伤口中洒落点点星光:“别一副自己永远不会变成弱者的样子。太高高在上的话,摔下来可是很痛的。”
今井只是挽了个刀花,刀锋指向对手:“我确实不会,即使谁能超过我也只是一时的,我会站到最后——何况现在你是弱者。”
“就是你这种口气最让人生气啊。”渊上握紧刀柄,向前迎上刀锋。然而双刀轻轻松松地拨开了这一击,再度于她身上刻划下伤口。星屑漫舞于空中,今井投下的话语比任何人都要傲慢:
“没有努力的人,努力得不彻底的人,还请乖乖闭嘴吧。”
“——什么?”
熊熊的火焰刹那间烧遍了舞台。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有些橙黄,有些赤红,有些瑰紫,有些白炽,仿佛整个世界的灯火都倾倒下来,以她的伤口、她的血肉为燃料,火舌爬上高台,怒视明月。帘幕纷纷被风倒卷而起,台上的二人视线相对,再无任何遮掩。
“你——怎——么——敢——这——么——说!”
那是渊上白鸟的怒吼。她的话语比火焰灼烧的哔剥声更响、甚至更快。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一切,怎么敢断定我就没有努力?光是活到现在就已经拼尽全力了!你知道因为放了太长时间没有一丝热气的饭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在值夜的时候为了听清楚声音整晚都睡不踏实是什么感觉吗?你见过有人死在你眼前吗?”
那都是她十一岁前经历的过去。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中。因此,每砍下一刀就仿佛是在斩断过去的自己一般。她一边高喊,一边向前。连瞳孔都晃动着、如同不稳定的火苗一般。
“你曾经想尽办法去模仿一个人吗?你曾经对着名册与日记读到深夜就为了叫得出每个陌生人的名字吗?你曾经在舞蹈和演技的课上想晕过去、终于晕过去了然后又被掐醒过来吗?”
她们已经一路打到了高台的边缘,仅差一步便会坠落。胁差指着今井,然而白鸟的双眼却看向台下,声音中染上了某种殉道者般病态的狂热:
“看啊,这个人造的赝品骗过了多少人!鼓掌吧,喝彩吧,这难道不是我最棒的、持续了十年的演出吗?”
然而这一步仿佛天堑般无法越过。对其他人而言,所有的苦难都只是故事,而非现实。今井的双眼无波无澜,没有半分融化的意思:“那是没有意义的事。连让我感兴趣都做不到。”
这一击里两人都用上了全部的力气。白鸟整个人都被打飞出去,撞破数层帘幕,不得不重新回到幕布之后。纯白铺展而下,十字星的中心只有今井的身影。她宛如审判般,看向倒在地上却依然握着胁差的少女:
“你的愿望不会达成。这种场面根本就不会在现实中发生。你的火已经点燃你自身。”
白鸟的影子在幕后站了起来。火势渐大,咬住了白布的边角。她的声音战栗着,和台下的哀鸣一样,却透出一分令人心惊的决绝:
“既然如此,至少我能选择自己的结局。”
胁差穿透了她的小腹,折翼之鸟委顿于地。火焰一瞬间变得金黄明丽,如同凤凰的羽毛淹没了整间屋舍。帘幕被火焰烧尽时,倒下的人影已经消失,只有完好无损的披风轻轻落下。
今井上前几步,长刀切开穗带,纽扣崩落,金色近乎黯淡无光;刀刃深深地插入地面,刀柄末端,有红色的死星闪烁。野火不甘地应声而熄,黑色的余烬与星屑彼此混合,安静地掩埋所有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