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正x少女歌剧
文画/主线/强制打卡/
撕卡/投票排名/适龄18+
「在约定之地,
将此花予你。」
报名参与企划前,请先在qq群过审,并且于elf上传人设卡。

“……总之,就是这样。”
白鸟一口气将自己的想法说完,千极点了点头,问她:“你还记得当时的状况吗?那间屋的窗户是朝什么方向开的,你待在什么地方,那名猎人在室内的位置,还有她视线的朝向?”
那是一间别墅。白鸟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才没觉得她是猎人——那家伙身上一股有钱大小姐的味道,活得天真肆意,毫无防备地把后背暴露给她,还在她走出一段距离后从二楼窗台远远地向她招手。
这一个黄昏里,猎人站在二楼的那扇窗后,背对着窗户,所以白鸟是大大方方地扒在窗外向里看的。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白鸟看见她的口型,但唯一能辨认的是“会长”。然后,猎人结束了通话、收起徽章,等她转过头的时候,白鸟已经顺势落到一层,然后离开。想到这里,白鸟猛然一惊。如果千极没有引导的话,她不会回忆起这个细节。既然她能看到猎人,那么猎人也就能看到她;即使她没有触动任何可能是咒文的花纹或护符,也已经靠近到猎人应当能察觉的距离了。也就是说,她的猜测大概没错。妖精形态是金鱼的那名换生灵,用梦华遮掩了她的存在。
仿佛看出了她的窘迫,千极又说了下去:“猎人们和我们大致保持着平衡的共识,毕竟在他们看来,人类面对的不止一种敌人,还有恶魔、狼人、其他超自然生物。不用担心他们忽然想掀起战争,因为我们会赢。”
说到最后一句时,她的语气仍然十分平静,就像在诉说一个公理。白鸟稍微平静下来,又问:“我们现在,只要等待就可以了吗?”
“不。”长老开口宣布了自己的命令,“现在的时期不允许我们静候。你们也知道,血脉浓厚的——实际上九代以前的血族们,都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虚弱,有的干脆直接沉眠,打算等新的时代到来;现在失去任何一名成员都将是有生力量的极大损失。去调查吧。白鸟,留一下。”
爱娃拍了拍白鸟的肩膀,很快走出了房门。白鸟一直等她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才开口:“那时候……是因为缺少人手,才让我留下来的吗?”
“我就猜你会想到自己的事。”千极轻松地捧起她的一只手,以自己的两手包覆,“不是的。”
白鸟作为血族的诞生是一个意外。常年作为血仆被饲养着生活的她,在反抗的时候喝尽了主人的血,迎来了初拥;发现她的血族们将她带去审判,而千极判她无罪。血族对创造子嗣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未经长老许可就初拥人类,面临的刑罚最高是死。而只有长老有权杀死同族。
“我想说的是你很重要,所以在调查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长老这么说着,交叠的皮肤之间竟然传来温暖的错觉,“说‘是’。”
“是。”白鸟条件反射地说,而后才升起一丝担忧。她不清楚千极是第几代的血族,但衰弱和沉眠……她看向对方,肉眼看不出任何虚弱的迹象。希望这位可尊敬的女士、这位长老一直在这里,白鸟默默地许愿。不是向神。
一竖栏杆从中劈开了月亮,因而夜幕呈现出蒙昧而漆黑的颜色。栏杆的两侧,是一名囚人与另一名囚人。一名高束长发却委顿于地,垂眼看着自己脚上的镣铐,与脚腕上新鲜的淤伤;一名随性地坐在窗边,被截断至肩头的白发简单地束在脑后,时不时仰望夜色。
“还有多久,我们就会被绑上车去?”白鸟没有抬头,仿佛也没在期待答案。千夜看了过来,将根据月相推测的时间告知于她:“很快了吧。不只是我们,其他巫女也没有成功地祈雨。”
从这里可以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哭声。有的还能哭,有的已经彻底失去了声音。白鸟低低地说:“如果这次没有成功,我们就会变成祭品了。”
“你还在担心吗?”千夜关切地问,“接下来的舞需要摒除一切杂念。”
“是的,我当然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法跳请神的舞……如果有余裕的话,我还想救其他人。”白鸟将头埋进抱膝的双臂,声音沉闷而无力。她的动作幅度都非常小,唯恐牵扯到镣铐的锁链,打破这份长夜的寂静。千夜正了正神色,将双足从一侧移到另一侧,明明这双脚上也系着长链,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你的脚上也被铐上枷锁了,所以跳不起来;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枷锁当成腿的一部分,适应它,用枷锁起舞,把它也变成你的舞蹈。”
见了这胜于雄辩的示范,白鸟的双眼睁大了些:“……我会试试的。”
牢房门忽然被重重地推开。铁与铁相撞,发出尖锐的响声,让这一排牢房里的人顷刻间活了过来;一时间四处尽是哀哀哭声,并非不是没有人谩骂,而是那些人早就失去了舌头或是更多。一个严厉的声音震怒地喊道:“让她们最后试一次!一天之内雨还没有降下来,就把她们处死!”
巫女们拖着长长的锁链来到室外。以舞台而言,她们终于得以走到台前,这筛选了无数人的台前;然而锁链一直延伸到幕后,拖动间全是不和谐的音调。而等到终于轮到白鸟与千夜上前时,她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染得一片赤红。那红色仿佛就映在白鸟的眼中,为她染上颜色:
“神啊……一定是因为这位陛下太过残忍,才不愿降雨吧。”
与白鸟的哀恸不同,千夜冷色的眼中,晕上一层愤怒的火彩:“即使跳舞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你也、我们也依然来到了台上。要试试我之前的提议吗?”
她没有听到回答,少女们相对而立,双双跳起神乐舞来。她们缓慢而坚定地旋转,摇响铃铛,摇动纸锤,好像那是一面旗帜。枷锁并未影响千夜的舞步,但白鸟被锁链一绊,好像折翼般跌倒在台上。无论是对舞者还是对神来说,这都是无法容赦的过失。她试着爬起来,却又一次摔倒在原地。就像被线提着的木偶一般,她持续着站起又摔倒的动作,然而直到舞蹈结束,雨依然没有落下,而白鸟依旧跪坐在地上,手脚被血泥浸染,仍是鲜红的一片。千夜半蹲下来,并没有试着伸手去扶她,只是深深地将双手按进泥土之中:“你太累了,所以不跳舞也没关系。你可以软弱,可以迷茫,可以不去看未来而继续痛哭;你也可以乖戾,可以嚣张,可以是舞台上那个不讲道理的鬼。”
“我依然系着枷锁,如今已经成了残缺之物,若是再这么跳下去,在旁人眼中一定出奇怪异。”白鸟抬起自己的两手,血色仿佛已然深入骨髓,连带着她的声音都不稳起来,像风中摇曳的烛火一般,“难道……这就是「鬼」吗?”
“没错!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有枷锁,就是残缺或者怪异的,但是那也无所谓,世界上就是有鬼的存在的!”千夜指向自己的额角。伤口、不,那是一枚幽蓝的独角,是她藏于身内而刺透皮肤的锋芒。鬼只是存在于此处,如同惊雷一般。
这世界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它容许万物生长,默许数罪横行,准许千夜流转,也允许鬼的存在。春日的雷鸣惊醒百虫,也惊醒群鸟。它说:你可以仅仅只是燃烧。
一盏灯在月畔幽幽地亮起。在星火之下,白鸟缓慢地爬起身来。
“既然如此……我承认我的本性。”
十盏百盏千盏万盏,灯火在夜幕之后渐次点亮,以至于彻底掩盖了月亮的光辉,将黑夜烧成白昼。灯光汇聚到白鸟身上,让她从胸口的旧伤处开始燃烧。无法锁住火焰的镣铐落到地上,丁当一响。
“吾乃——火之迦具土。”
这团人形的火焰不知疲倦地燃烧着,双眸赤红,飞散的长发青绿,而周身莹蓝,甚至略略发紫。伤口依旧不断地滴着血,却成为了她最好的燃料。身负弑母诅咒,又被父亲斩杀的产灵,如今仍然生存在这里,满身疮痍,却不再囿于悲伤,只需要贯彻存在这一要义。
“这可不止是鬼,而是化身为神了啊。”千夜稍稍眯起眼睛,抬起手臂指向天空,“来吧,建御雷!”
被她唤来的落雷准确无误地击中她的身体,劈断了发带与锁链,但还有一截挂在脚腕上,烙下了闪电蜿蜒的形状。细小的电弧在千夜的身侧点亮,让她的头发无风自浮,而她毫不在意地向白鸟伸手,是一个邀请的姿势:
“——来大闹一场吧!”
火焰迎面而来。千夜轻易地躲了过去,向白鸟投出落雷。雷电将火焰劈落在地上,然而惊雷落处,新的火苗再度燃烧起来。火之迦具土且战且退,建御雷穷追不舍,雷与火相撞而后爆裂,仿佛无数庞然而危险的烟花。但不对劲,火的烈度控制得太低,不像是爆发应有的样子。千夜将视线投向地面,随即恍然:白鸟引着她一路过来,借雷将牢房与锁链全数劈开,在一片大火中,根本没人顾得上被关押的巫女,她们得以毫无阻碍地溜出宫室。建御雷赞叹一声,跟着打出一道电光。火之迦具土跟着落下火雨,溅射而出的花火恰好为重获自由的巫女们指明方向。
“这就是你的愿望吗?真是美丽。”
这份不屈的意志、点燃自身的激情、连对手都要利用的狡黠,都只是为了达成渊上白鸟的愿望。她要她的歌声,成为指路的明灯。
“这是我将靠自己实现的愿望。”
她将手按在胸口,仿佛在一盏灯中安放烛火,而淌下的血即是烛泪。这枚灯盏将在舞台上长明,摇曳、闪烁、爆裂、熄灭,直至走完漫长而短暂的一生。
“让你久等了,”白鸟从灯火中抽出了胁差的刀柄,刀刃被她身之火淬炼,隐隐投出朱红的色泽,“接下来,我们好好打一场吧。”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金铁相击的铮鸣一声,是千夜猛地扭动腰部,使出的一记踢击。在她足底闪光的利刃,正是由那段锁链锻造而成。虽然这一踢又准又重,白鸟依旧以胁差的抖动卸掉了大部分力。已经不会也不必逃避了,她如同疾风般突刺出去,火花在刀刃之间迸溅,又融入她的身躯,好像一次又一次被反复锤炼的铁;千夜单脚点地,带刃的单腿舞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回旋,是一场杀气腾腾而美得惊人的旋舞。就好像从来没有表演得这么出色过,一次又一次刷新自己的极限记录。千夜下蹲的回旋踢并未扫及白鸟的双腿,白鸟骤然提亮的灯光也没能影响千夜的感官。即使已经超越了舞台的范围,即使被过去的酸楚与悔恨包围,她们依旧将自己投入表演中,仿佛永远不会落幕。是的,虽然在过去品味过了无力与劣等感,但如今不应该说是大器晚成吗?唱吧,跳吧,这是革命的最前夜,已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了!她们宛如同伴一般对视,在未能击中对方时击掌,在被击中时喝彩,在白刃相交时相视而笑。人生的帷幕已经拉开了,就继续这么一路冲向前吧!
“怎么不试着靠近过来了?”千夜的气息仍然很稳,仿佛高强度的动作并未带来负荷,实际上汗水已经涔涔而下。
“别想骗我走进你的攻击范围。”白鸟喘着气,说了句谎话——对短兵器的使用者来说,一路积攒的经验都告诉她不要离得太远,长兵器接近的速度会更快。话音刚落,她就轻身而起,仿佛长出双翼般朝千夜所在的地面滑翔而去。千夜迎了上来,踢出一道不可逾越的弧线,但满身破绽的白鸟不闪不避,只以一个异常刁钻的角度将手中的胁差投出。
她赌赢了。
纽扣高高地飞起,披风与幕布一并滑落。从幻想回到现实里来,她们才意识到自己和对方都气喘吁吁,满身大汗。白鸟深吸了口气,盯着千夜的脸,信誓旦旦地开口:“雷鸣同学……真厉害啊!刚才那几下都好漂亮!绝对会成功的!不管要做什么,都绝对会成功的!”
胜利的甜美溢满她的喉间,此刻的赞赏又完全发自真心。因此她也知道,对方的回答不是谎言:“你也是,渊上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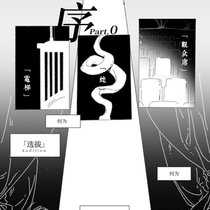
舞会的第一支曲子即将过去。忽然,白鸟听到了两个笑声。她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然而,两个影子飞快地跑过了整个舞池,引起了一阵骚动。那些繁复华美的珠宝饰品没有一件被落在地上,只闪耀出蝴蝶翅膀一般的光泽,就裹挟着笑声一路掠出门去。在那个瞬间,她感到一阵嫉妒。哪怕只是一瞬,但她们如此自由。
白鸟抬起头,看向青莲,仅用困惑的眼神发问:要追吗?然后,她从学生会长的表情里知道了答案:没必要把事情闹大。于是舞会继续,刚刚被分散开的人们再次回到了应有的位置。在一个转身里她看到,有两个女孩子摔了一跤,但立刻仿佛无事发生地爬了起来。
舞曲的调子开始变化,到了交换舞伴的时候。白鸟与青莲互行一礼,而后分开。正巧,刚刚摔倒的其中一位少女就在她边上,表情倒是平静沉稳,但留袖和服下的身体一定还隐隐发痛。白鸟向她伸手作为一个邀舞,而其他看到那一幕的人自觉地退开以防被波及。标志性的浅绿色头发,几乎与之相同的绿色和服,以及金色的花纹——那是常夏院家的纹章,那么,这就是常夏院咲常。于是白鸟刻意地跳得慢些,几乎只是在拉着咲常走动。真正与她共舞的时候,白鸟才觉得自己很有远见。
……这孩子是怎么在不太会跳舞的情况下,摆出一副专业舞者的气势的?
好在,咲常逐渐找到了一些节奏。她们的共舞还称得上是轻松愉快,毕竟将别人的八拍变成自己的四拍,出错的概率就小了很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发现咲常在短短的四拍中看了两次门的方向。它已经被关上了,两名少女的身影也去得很远,但就像是被蛊惑了似的,总觉得那阵笑声还在耳边。
“真好啊。”白鸟替她开口,“能中途离场,到外面去。”
咲常略微有些吃惊,脸上浮起一片薄红,很慢地点了点头。白鸟几乎不用分辨,就知道她要说的是前两个字是“但是”。
但是不能出去。家里是不会允许她们这么做的。和那些穿着时新洋装的混血大小姐们不同,常夏院与渊上都是传统的家姓,像扰乱舞池冲向外面这种事,不管理由为何都是极为严重的失礼。白鸟自己会因此遭到至少禁闭三日并减去一半食物的惩罚,她一点也不想知道其他人家的处置方式。
“……但是真的很美。”
咲常喃喃地说。白鸟起先有些不明所以,但在她转到咲常的位置时,也透过窗户看到了一望无垠的绿意。不,不是草坪和花树,这毕竟已经是晚上了;是萤火。它们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屋外,不知疲倦地飞舞着,比她们头顶奢华的吊灯,更能激起内心的悸动。至少白鸟在那一瞬间也想要逃出去了。
“回宿舍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她对咲常说,主要还是在安慰自己。后者露出一个很浅的微笑。她们都没踩到彼此的脚,可喜可贺,这支曲子马上也要结束了。
忽然,在对上青莲从一旁投来的视线时,白鸟意识到了什么。为了配合咲常的步子,她刚刚跳的……虽然有些粗疏,但确实是男步。幸好,会长没有不解风情地用之前那句“我只会跳女步”反问她,而是似笑非笑地开口:“渊上同学的舞跳得不错。”
啊,被发现了。白鸟没有装傻,没有辩解,反而十分自然地开口恭维:“只是在模仿刚刚的会长而已。”
然后她眨眨眼睛,走向下一个舞伴。

在那个秋天过去一半的时候,深雪完全从病中康复了。在白鸟的坚持下,她不安地一直歇到过冬。当然,白鸟对父母的说法中隐瞒了去仆人房探病那部分;那是深雪教她的。要是让谁知道了她有可能害大小姐生病,别说她自己了,父母都可能被赶出去……或者遭遇更糟的事。她本能地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最容易的一种。对她来说。
女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白鸟曾偷偷向深雪抱怨。她们必须为了成为某人的妻子拼命努力,争取选中一个可靠的人,不要流连花街或者和侍女偷情,至少在头生子出生前不要。抗拒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对未曾谋面的男人有什么感情,只是为了自己婚后的地位。白鸟说起这些来的时候,十一岁的生日刚过,却完全像个大人了。深雪惊讶地听着,感觉自己从没想过这些东西。不,其实是没有选择权。白鸟说,你当然可以。尽管知道她的本意并非施舍,深雪还是感觉到一阵羞耻烧红了脸颊。
她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比如,深雪就没有什么在白鸟面前说不的权利。在她的一切都来源于其他人的时候,她又怎么能反抗呢?
就像白鸟也不能反抗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她们来说,没有不成婚这个选项。
在这个冬天,白鸟生病了。起初只是咳嗽,却重得仿佛要把内脏都咳出来;随着天气一天天冷下去,白鸟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呼吸也非常困难。深雪近乎惊恐地发现她越来越瘦,精神也时好时坏,身上有些热却不是发烧,时不时喊自己的头很痛。而深雪的待遇也一天不如一天;她不再有唱歌和看书的时间,几乎一直留在白鸟身边。在白雪压满枝头的时候,白鸟忽然说:“对不起。”
深雪讶异地看着她,听白鸟缓慢地换着气,吐露出她前一天听说的事:“母亲说,人的命……是可以、互相换的。我们两个年龄一样,长得又像,她就说……要拿你的命,来换我的。”
这种迷信的说法,渊上夫人一向相当不以为然的。深雪的口中仿佛衔着一枚钱币,让她无法出声。她该感叹什么?是祝愿白鸟尽快好起来,还是叹息这绝望的母爱?
“但是,你不要怕。”白鸟忽然抓住了她的手,眼睛亮得摄人心魄,“用我的来换你的——你来成为我吧。”
深雪飞快地甩开了她的手,拼命地摇着头:“你在说什么?告诉我,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
“你来,成为,渊上白鸟。”白鸟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做不到了。”
“没有这种道理!我做不到,别难为我了!”深雪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迎面撞上了一个女人——是她妈妈。她松了一口气,这么莽撞虽然免不了一顿骂,但大概不会挨打。然而妈妈只是看着她,直到深雪回身跑开都一言不发。隔天,深雪被要求出门采购。她已经有段时间没跑腿过了,因此出门时还有些兴奋。只是越往回走,心头越沉,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她放下东西,一路跑向白鸟的房间。自己的父母,白鸟的父母,都在房间里站着。床上安安静静的,听不见白鸟痛苦的喘息了。是痊愈了吗?深雪如此期望,但她知道真相。因为,就连一点呼吸声都没有。
白鸟已经不在这里了。她的父母平静地对她宣布了新的决定。
“从今天起,你就是渊上白鸟。”
她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被妈妈拉进房间的时候,还在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哀求。但妈妈总是说着“这都是为了你好”之类的话,让她的骨髓中都升起寒意。妈妈,难道,是你……
是听到那句话之后,为了女儿的生命、又或者为了女儿更好的生活,对白鸟做了什么吗?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无名的少女怔怔地想,原来你死的时候,你的父母也不会哭。
自从白鸟上一次前来拜访后,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千极并不对她的再访感到诧异,不如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白鸟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与安慰,而教团需要九条家。教主十足耐心地亲自迎接了九条夫人,听她诉说自己遇到的种种事情。
比如,她嫁入的这一支在九条家本来不怎么受重视,直到长辈通过进口商品起家,才坐稳了位置;应该称为婆婆的女人是来自英国的小姐,百子就是借母亲的关系出国留学的。她嫁给的是比自己小两岁的次子,后者是个认真的人,总是在外学习新的知识。
说来都只是非常简单无聊的事情,但千极并不觉得乏味,只是在一旁听着。恐怕,白鸟需要的只是这些。那个残酷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在她的手边,然而她太过恐惧,捂住自己的耳朵移开了视线。那也没关系,时间总会给出答案,预产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倒计时,孩子一旦落地,渊上白鸟便将不复存在。就像在这黑暗的室内,唯一亮着的烛光一般。
忽然,盯着烛火的女人停下了讲述。千极发现她在颤抖。
“……这件事,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她想要的是真话,所以千极点了点头。白鸟沉默地垂下头,刘海遮掩住眉眼,也遮住了她脸上所有的表情。在昏暗中,她被拉长的影子远远比她庞大,仿佛黏附在背后的污浊之物一般。千极这才发现,她过往的同窗如今竟然如此渺小。在那个凸起的小腹中,有什么不祥地蠕动着。
“我……自从怀上这个孩子,就越来越不像自己了。”白鸟轻声说,“它寄生了我,蚕食着我,剥夺我的体力和外出的权力,让我一点点失去理智,变得精神不稳。”
“你想好了吗?”千极向她伸出一只手,白鸟宛如抓住救命稻草般地握住了。她的手心拢着细汗,因为某种深入骨髓的寒冷而微微发抖,声音低得像一句耳语:“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帮帮我,她仰起头,双眼无声地如此诉说。浓得几近流血的、预兆毁灭的鲜红色,正在她的眼中流淌。千极略微愣了一下。这意味着数之不尽的麻烦,教唆是一回事,真正给她帮助又是另一回事;一旦发现她的堕胎与教团有关,哪怕只是为了脸面,九条家都会追究,不是明处,也会在暗处。如今的白鸟可以提供的助力,不一定多于她会招致的损失。稍微安抚一下,然后给她没有效力的药,再慢慢地切断联系,这是最稳妥的。千极垂下的蛛丝本来就飘渺又脆弱,但白鸟眼里只有这根弦牵系,倒显得它格外坚韧了。
千极抬起空着的那只手,轻柔地将掌心覆在白鸟的手背上,像握住一块冰,或一团火。
“我知道了。一次的量足够了吗?”
白鸟惊愕地抬起头,本已生出绝望的双眼陡然绽开绝非出自善意的狂喜。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罪了——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影响了我的判断,你默许了,你纵容了,所以你有责任,被扭曲的愿望如此诉说。隔在两人间的唯一一盏烛火终于因燃尽而熄灭了。
但是,不管她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切的一切——白鸟在黑暗中低下头去,额头抵在千极的肩上——仅仅是因为,她留恋这只手的温暖而已。


——咚!
法槌落下,侧面的铜片与桌面上的金属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两座高塔从舞台两侧相对着升起,天幕上点亮一盏盏星光。两名少女扶着面前高约本身的木质台桌,打量起对方,没用几秒就认出了彼此。
对清浦雨来说,不认识班长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对渊上白鸟来说,作为班长当然记得每个同学的容貌。当然,她们都没有任何退缩。
「你便是那基督徒商人请来充作律师的鲍尔萨泽博士吗?」白鸟开口问道,「按照威尼斯的法律,我的控诉是可以成立的。我要从这基督徒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来,作为我借款的替代。这借约他是承认的。」
「那么犹太人应该慈悲一点。」雨抬起一只手,做出降雨般的手势,「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
「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当!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约执行处罚。」犹太商人将胁差刺入面前的台子,木头如同融化的黄油般将刀刃吞了进去,仅余刀镡附近的红光一闪。
「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呢。」女扮男装的律师同样将日本刀扎入了木台中,目贯上的两枚宝石是同样的红,「你要他的肉有什么用?」
「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犹太人的眼中闪着冷彻的光,「你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人?」
话音未落,鲜红的雨已经落了下来。然而这雨仅落在律师所在的一侧,或者说,清浦雨的那一侧。每一滴雨都是某人的血,它们透过清浦家女儿的身体,只将她足下的高塔染得越来越红,仿佛从舞台下方不断地注入水体,充填进整座塔楼。
那并不是她的过错。然而,她的家族确实依靠吞食他人的血肉得以成长。作为家族一员的雨,手上没有沾过血,然而又怎么能当作自己仍然一无所知?雨下意识地想要从高塔上离去,然而,她的脚下依然是流淌着的深红,让少女只能收回脚步。
从对面的塔楼上,忽然传出一声带着怒气的喝斥:“把头抬起来!”
雨惊讶地看了过去。一向温和又乐于助人的白鸟,竟然紧皱着眉、全身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息。她握紧刀柄,将它从木台中一寸寸扯出。木头发出吱呀的响声,缝隙中竟然涌动着浅粉的肉芽,一被刀刃划破就冒出鲜红的血珠来。然而,她仍然没有松手,反而任那些赤色染满自己的胁差。
“你想逃跑吗?还是说想反抗?”白鸟高声问,“想做什么的话就做啊——舞台不会为你而停下!”
忽然间,雨明白了。拉扯着刀柄的是她的愿望。虽然明白要战斗、也觉得自己的梦想有实现的必要,但是刚刚的血雨让她迟疑了。与其说是白鸟在质问她,不如说,舞台将它的意志投射到了白鸟身上,用人之口催促她的意志。必须——必须继续表演下去。
律师叹了口气:「看来是没有什么能改变你的决心了。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法律许可你。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
犹太人骤然松手,那柄刀刃再度被吞没:「公平正直的判决。」
「且慢。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
在律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幕布后几乎是立刻响起了令人惊心的掌声与狂笑。那些声音如此熟悉,以至于雨甚至觉得,自己出庭辩护是一件错事。
「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在满座喜悦的呼声里,商人的话悠悠地响了起来。
「难道犹太人就不是人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白鸟的声音里饱含感情。仿佛她所说的并不是剧本上的台词,而是心灵中激荡所振出的回声:
“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他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所以,你仍然要为他们辩护吗?”
雨看到白鸟的手指已经握上了刀柄。她有一瞬间的泄气,而后咬紧牙关:“那要怎么办,站上舞台这么奢侈的梦想……我一个人要怎么承担?”
即使讨厌自己的出身,也没办法切割得那么干净。即使想要反抗,也无法做出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寄希望于选拔,希望最后能够实现一个……符合世俗上的大义,而且不用自己做出改变的平和舞台。毕竟如果没有家族投注的资源,她不可能有机会学习声乐、表演与舞蹈。
“啊,我知道了。”
白鸟垂着头,额前的头发遮住了她眼中的神情。她忽然猛地挥动刀刃,将木台自上而下斩为两半。血肉流淌而下,刀身亮如白银。
「我要控告,这律师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他的辩护自然也没有效力。只因为她不是个男人,却是个女子,不是自罗马来的青年博士鲍尔萨泽,而是贝尔蒙特富家的嗣女鲍西娅!」
雨所在的高塔轰然崩塌。这并非剧本的走向,却是被舞台接受的发展。她抓住嵌在木台上的刀柄,两枚内蕴星光的宝石一闪,将一注灵光投进她的脑海。日本刀轻而易举地被拔了出来,而雨情不自禁地开口问:
“……班长,你明明是贵族派的华族。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为什么……舞台将你分配到了被侮辱的那一边?”
白鸟脚下的高塔裂开一条缝隙。仿佛在她斩开木台时,自己的胸膛也同样被剖开,将最真实的想法暴露出来。鲜红与暗红混在一起,如同瀑布般的血流喷溅而出,像一个真正的伤口。她没有回答任何话语,只是带着愤怒的眼神从高塔顶端一跃而下,向着雨坠落的方向扑来。
“只要你是个女人,就必然是被侮辱的那一边!”
胁差的刀刃将雨颈侧的穗带挑到最极限的弧度。然而,日本刀要更长。
“只要你还是华族,就和我一样……!”
两枚金色的星光应声而落。少女们不分彼此地坠入了血海之中,从头到脚都被染得鲜红。白鸟忽然想,她们确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