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这次的故事,是关于三个男人的午夜大冒险。依然BUG很多,请海涵!
————————————————————
都说冬季是个好季节,我却不知它好在哪里。一年的终末,万物归于寂寥,只会让人想起诸多唏嘘的往事。
姑苏这种南方城市,就算降雪,也只会是一层薄薄的意思。所谓落雪之音,结果就跟下雨没什么区别。
至于我,只要进入冬季就好像立马就会睡过去,除了抱着暖炉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在下名为八重,乃是一名流落到此地的倭国作家。说是作家,其实也不过是替青楼姑娘们写些唱词糊口罢了。
在下寄居处,正是姑苏城内一座名为“闲月”的青楼。有旖旎环抱,衣食无忧,简直就是身为作家的梦想,而我正踏在这梦想之阶上……
“我搁炉子边上的红薯上哪去了!”吼声犹如虎啸,名为阿香的姑娘从暖炉边上揪出一个我。
“我说阿香啊,红薯就是要给人吃的嘛,如果烤过头就很可怜了呀。”我如此说道,然后看到阿香冷笑一声。
如果不是这么火爆脾气,应该会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才对。
于是我就在这种连鬼都能冻死的天气里,再一次地,被扫地出门了。
“这也太凄惨了吧?”清海说。我俩一同坐在避风的廊下,各自对冻僵的手哈气。清海乃是一名云游僧人,光凭法号是绝对想不到这个和尚是什么秉性的。
对我表示了差不多百部经书那样分量的同情之后,清海马上转折:“小僧我最近每晚都会被接引去一个奇妙的地方,温暖又有很多人吵闹,非常有意思呢。”
“……你该不会是冻到极致产生幻觉了吧?”
“如果能在这样的幻觉中西去,也是幸福啊。”
“…………”
要详细询问他是怎样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清海是个标准的,双目失明的僧人。根据他的说法,自己打出生就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样子。
世人所见之物,其实都是皮相。听见的,闻见的,也都并非真实。清海认真地表示,所以我这是佛缘。
……如果人人都能像他这么豁达,那世间怕是根本不会存在不幸了。
“难不成是你口中的那位娘娘干的好事?”
“施主真是聪慧。小僧确实每晚都在纷繁嘈杂中听见她的声音。”
“……她到底是人是鬼啊!”
“实不相瞒,每次都忘记问。”
“……”
事情就是如此。这位僧人似乎一直在与一位只有他能感知到的女子交流。
时常对着空无一人的方向说着“阿雨说得对啊”,“小僧我也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对方到底说了什么。
…………根本就是一个疯子。
路上行人匆匆,蓑衣斗笠与伞往来接踵。飘过来的雪那可是相当漫不经心。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不禁开始担心今晚到底要去哪里过夜。
要是冻死在街头的话,不知道阿香会不会肯拿出一点钱来为我买口棺材。……不可能的,那个女人比铁公鸡还一毛不拔。
“大师今晚有着落否?”我询问道。
“阿雨说今晚也可去她的住处叨唠,夜宵是素食果馅酒酿小圆子。”
“……”
“看来我俩如此合得来的份上,大师有没有考虑让我也沾点光呢?”我倒是要看看他每晚蛰居的住处是他的幻觉还是真有其事。
“你的话……”和尚突然转过头来对着我,他双目紧闭,并未睁开。但我不禁心里有些发毛,觉得确实是被人注视着。
“你的话……”清海说,“恐怕去不到那里。”
“哈?!”
“我是说真的,你去不到那里。”
“……那里究竟是哪里啦!如果是你的幻觉的话,我确实进不去就是了!”
“如果施主是担心今夜天气过于寒冷,可能会出人命的话……”
“怎样?”
“反正都是皮相,舍去了便是~~”
“…………”
“啊呀,施主是舍不得吗?”
“废话啊,我还想多活好多年呢!最好能儿孙满堂地在床上死去!”
“儿孙满堂地在床上死去啊……”和尚突然沉吟起来,“那真的是你的期望么?”
我被他一问,竟然语塞。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一阵巨响,有什么东西从屋顶上砸落在地。
……
“施主,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地了?”
“大师好耳力,确实有东西掉下来。”
“……听起来还挺沉。”
“那可是相当地沉。”
摔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一个活人。只不过因为落地姿势太过难看,很难形容给和尚听。这个人背着一个看起来精巧复杂的箱子,如今结结实实压在他身上。如果要去报官,恐怕只能对仵作说出“可能是被自己的箱子压死的”这样的死因来。
那个从天而降的角色动了动,突然飞快地爬起。 “二位真是好雅兴,竟然在这飘雪时节于廊下促膝相谈。
本来就肚子饿,还很冷。当然是没好气的。“这位道爷有何指教啊?”此人虽然穿得莫名其妙,但确实是一位道士没错。
“贫道听到你们在说些有趣的东西。”这位道人随随便便行了个稽首礼。
“没钱,不会找你算卦的。”我十分冷漠地说。
“……我还没说什么话呢!”道人说。
“出门在外最要小心四种人,女人小孩,和尚道士。”话是这么说,但这四种人我基本都碰上了。
所以也可能就因为这样,我才至今都境遇凄惨。
“真是至理名言!”这位道长由衷地说。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会随着麻烦一起来的角色啊。
“贫道唐隐,除了算卦捉鬼,最感兴趣的便是好好过日子,最后幸福地寿终正寝。”道长说。听起来根本就是与主线无关的人生履历。
“……难不成你觉得和一个穷作家外加一个疯瞎和尚搭话,也算是好好过日子的一部分吗?”
“事实上……因为我听到了你们谈论的有趣事情。”这位唐道长说,“这位大师,你可否听到您那位阿雨姑娘谈论起关于她们这个族类中,有其他存在也在此城中活动?”
“您这样一说,倒是有耳闻……”
“如何?”
“需要小僧帮忙打听一下吗?”
“再好不过了,唐隐拜谢。”
“只是道长想要寻找的是怎样的呢?”
“请大师附耳过来……大约是这样。”
“……………………喂你俩不要当我是透明的啊!”也不知道这俩人的脑波是怎么突然搭上了线,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就这样相互交流起奇怪的事情来。
“嗯嗯,我也觉得兴许去了那个地方。”
“毕竟是青楼女子……”
“要是惹了麻烦就糟糕了……”
“………………都说了不要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我拼命抗议,但是毫无效果。这两个人仿佛前世早就认识一样。
“施主,听说你是住在一座名为’闲月’的青楼里是吗?”和尚突然回过头来。
“……居然蛰居在这种地方,这位施主真是人不可貌相。”道长也跟着帮腔。要你多事。
“怎么?你们是要怎样?”我问他俩。
“贫道有一个不情之请……”那道长突然十分正经地说道。
“所以这就是你带着两个吃白食的回来的原因?”阿香倚着门,襦裙退到胸口,正想借口这样很冷啊去给她提上去。
和尚道士站在我身后,一副正经出家人的样子。
“呃,这位道长说近日这附近有些诡异之事,乃是一非同寻常的精怪所为,掐指算来,兴许会在今夜叨唠此处,所以……”
具体的事情要形容起来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干脆这样说就好了。
“……你信么?”阿香看着我。
“……当、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如果你出事要怎么办?”
“想不到八重你这么关心小娘子我啊~”阿香笑面如花,伸出手指戳我心口,“果然只有你这个男人最有良心了~”
接着阿香表情一沉:“不要以为用这种话哄骗老娘,老娘就会收留你们这几个穷要饭的!”
“…………这样说二位大师道长也太失礼了!”
“失礼?那你倒是告诉我,怎样才算有礼数呀?”阿香凑过来,她身上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真是叫人酥麻。
“呃……这个嘛……”未等我整理好语言,阿香顺势将我一推,我立马从台阶上滚下。大门铿锵有力地在我眼前关上。
真是个懂得捉放手腕的女人,就算是这样被扫地出门,我作为男人的那部分竟然也喜不自胜地对着空气欢呼。
“果然不会像计划中那样顺利……”道长说,“那照目前来看,只能在此蹲守了”
“…………说不定会冻死啊,看你的表情还以为会有什么高见,隔着一堵墙,里面是暖炉和酥胸,外面是天寒地冻。未免也太惨了吧!”
“有的时候,人就是需要拼一下的。”道长十分严肃地说。
“这和您之前所说的为人处世之道似乎不是很符合……”
“为人处世之道就是用来打破的,不然还叫什么人生。”
“…………”
我不禁为这句话鼓起掌来。
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三人顺着墙根坐下,开始等待。“和尚,你今天很沉默啊。”我对身边的清海说。
“阿雨说小僧是榆木脑瓜,只知道蹚浑水,一气之下已经先回去了。”和尚如此说道。
“那还真是有点惨。”说起来这种情况难道不就是,为了兄弟义气和女人吵架的桥段么?不过为何连和尚都有青睐的女人啊,虽然不知道是人是鬼罢了。
“八重先生,清海师父与那位女子的因缘很深,不是旁人所能道哉。”道长说。
你这个人,是有读心术吗?
“我可以看到两股纠缠许久的线,没有尽头。不过也许,在今世会有一个截断。”道长说,“不过那与我等都没有关系。至于你的话……”这家伙凑过来端详老子的脸,距离近到可以完全看到他的胡渣。
“你的话……嗯……”
“我的话,是要怎样?”
“……你这个面相,是个薄情之人。”
“…………要你说。”
“除了会让人伤心之外,别无用处。这种面相真应该张贴在大街小巷,让姑娘们离远一点。”
……够了喂。
如此闲聊着,三个勉强算是无家可归的男人靠在青楼的外墙边。雪时停时下,不久天暗了下来,青楼上下点起了灯笼,每个窗户里都透出了温润的橘色灯火。
姑娘们此时应该已洗漱装扮完毕,坐在有暖炉的屋子里,等着老鸨招呼。那些恩客要等天色再暗一些才会来,这隆冬季节里头,女人的体温怕是再好不过的抚慰。
……总觉得这样一想,在外墙的三人看起来更加凄苦了。
“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冻死了。”我说,“眼前已经出现了幻觉。”
“……既然都知道是幻觉,那一定还不会死吧。”道长说。
此时青楼大门已开,人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可那幻觉未免太过真实。”我指着街道尽头说。“那里……好像有个人。”
不禁如此,我似乎听到了幽幽的歌声。那歌声如泣如诉,一字一句。却并非我所熟悉的那些个唱词。
生……生……死……死……
未……忧……而……获……
只……晓……歌……舞……盛……不……知……伶……人……苦……
歌声幽婉,有着不同凡响的邪性。我听着那一句“生生死死”,突然眼眶一热,以为是流泪,用手一摸竟然是血。
“善哉,有邪气。”和尚说。这话音刚落,道长突然蹿了起来。“今日终于等到你了——!”
那歌声骤停,我颓然倒下,这冰冷的雪地瞬间让我清醒了大半。
“……!?!怎么了?!”
眼看着道长使出了雪上飞功夫,背着他的箱,一路蹿去。
“施主您自个儿保重~”和尚说,他拄着跟竹杖,竟然一边敲着地一边也速度不俗地往前快走而去。
独留我在青楼的墙根,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就好像魂儿随着先前的歌还没有归位,所见所闻所听所想都隔着一层纱。
我恍然转过身去,却见青楼往来恩客与姑娘,犹如群魔乱舞,面容扭曲,谈笑狰狞。我大骇,不由倒退几步。
“清海!道长!你们……你们等等我!”如此追着另外两位消失的方向,落荒而逃。
如果在平时,我一定会击掌庆贺,在这个异国城市里所遭遇的怪谈,绝对是写作的好题材。但此时我只觉得见什么都十分恐惧,在街上狂奔疾走,连连摔跤。和尚与道长也不知所踪,只有不小心被我撞着的路人,咒骂和尖叫钻入耳中。
后来想来,那一准是那奇异的歌声所带来的效果。但此时我根本无暇去推断,又一个趔趄,彻底摔进了雪里。
这雪堆竟比别处深了许多,我花了好久才从中爬出,却被雪迷了眼睛。眼中冰冷胀痛,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睁开,就这样摸索着想要站起,脚底则连连打滑怎么都没法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四周的声音渐渐褪去,就好像雪越下越大,终于淹没吸走了所有的声响,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寂静。
然而这寂静并未持续多久。
紧随而来的是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嘈杂的喧嚣。就好像我突然被扔在了一个人声鼎沸的集市上一样。
眼睛依然睁不开。我无从辨认自己到底在何处,也因此更加恐慌。这就是那个和尚平时的感受么?只有声音和触感的世界。
“哎呀,又是一个生人。”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从我耳边溜过。
“看他这样子,怕是没有来过此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今晚真是热闹呢,先是有个邪气的玩意过来了,刚才又跑过去一个道士,还撞进来一个和尚,现在又来了位俊俏小哥。”
俊俏小哥是说我吗……
不过听那人说的,难道道长和清海也都在这个方向?
“呃……劳驾诸位,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
听了我的话,那些人沉默了一下,突然都笑开了。“什么地方……这厮真是没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闯进来,看来是活腻了~”
“该说不幸还是万幸呢。与那和尚不同,这个俊俏小哥儿可是没有主的。”
“没有主的话,那就好办了……”
我只感觉到气息的临近,却又不是很对劲。寻常人的气息凑近,会感觉到实体。然而在此处,除了忽远忽近的人声,和这些男男女女的说话声,我竟然感觉不到半点“真正有人站在身边”。
一定是脑子坏掉了。
此时突然有人捉住我的袖子。“八重,你竟然在这里!”未等我反应过来,我就被这人拽着跑了。
“等等……!这是?!”
那人却并不理会我,只顾拽着我跑,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只能拼命跟上脚步。腾出来的一只手只想把眼睛扒拉开。
“不要睁开眼睛。”那个人说。
“哎?”
“如果睁开的话,就会从这个地方消失,回到生者的世界。”
“生者的世界……难道说这里是死人的国度吗?”
“说是也并不是。只是一些对尘世还有留恋的家伙,找借口留下来的地方罢了。”那人说道。
如此说着,对方的脚步慢了下来,终于完全停下。喧嚣依然在,但比起先前这些吵闹的声音好像已经跑到身后去了。啊,这就是所谓的灯火阑珊处了吗?
“你还是像过去那样,遇到奇怪的事情就义无反顾地追着寻找答案。”那个人说。
“……说得你好像认识我一样。”
“没错,认识哟。”那个人说道。
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喂,你这家伙……”他说,“为什么要顶着我的名字行走在世上啊?”
这一句话落下,我的心好像被重重地锤了一拳,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是你……?”挣扎着说出这几个词,却受到了对方明快的反应:“对,是我。”
双手被对方捉住,冰冷的触觉蔓延上来。
“以我的名字,八重出道,在江户那边写些私下传阅的故事,然后交给画匠作画,到今天也有十多年了。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写出与《平家物语》齐肩的作品,但到头来也只能写一些怪谈故事,讲述武士和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他说。
“写不出的时候简直想要自杀,而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觉得手中的笔在背叛自己,明明自己想要的不是这样的,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保持着人前的光鲜,只是为了遮掩自己窘迫的灵魂。故作洒脱的样子,也是因为自己不能为任何事情负责。这样的你……”指尖的冰冷温度已经浸透了手臂,“不觉得很辛苦吗?”
“……”
“非常辛苦啊。”我仰天长叹道,就与古往今来所有被忘记的失败者一样,终于找到了那个同样也不会被记住的,长叹的时候。
“但那不是你的梦想吗?”我说。
对方沉默了,指尖的冰冷竟然停滞了蔓延。
“我是武家的长子,原本这双手是要拿起武士刀的。”我说,“我对父亲说的是,时代不同了,接下来是不用打仗的时代了,就算没有武士的名号,我也能够以别样的方式有尊严地活下去。”
“结果被老人家狠揍了一顿。老顽固真是不懂顺应潮流。”说到过去的事情,我坦然起来,“如果你还在的话,一定会竭力阻止我老爹揍我这件事吧。”
对方仍旧没有说话。
“可惜那个时候你已经死了啊,八重。”我喊出了曾经并不属于我的那个名字。
八重樱花,结果你的命运也如樱花般在尚未盛开时就凋零了。
“借用了你的名字,决定以一个出道作家为人生目标的傻瓜,就是我了。”
“…………”
“总要有人记得梦想。”我轻声说。
“虽然我做得并不好,根本比不上你啊。如果是你的话,在我这个年纪,早就成名了吧?就算拼命努力去做也不可能达到你的程度,要说辛苦的话,这样内心的煎熬才是最痛苦的。”
“真是个愚蠢的傻瓜。”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对方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是吃力不讨好,我都这么努力了,结果还要被正主抱怨。”我说。
“并非抱怨,只是叙述事实。你就只能是个傻瓜,除此之外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
“呃啊,出现了!毒舌八重的灵魂击打!”我大声喊道。
……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这是我的梦想吗?”青年对我说道。
“哎?”我不明所以。
“事到如今,就算如此辛苦也没有想过放弃的你,真的只是因为,那是我梦想?”
呃啊,这家伙,比活着的时候更加直击人心了。
“…………因为感觉到了幸福。就算卖不了钱,就算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我也会感到幸福。”我认真地回答他的询问,也算是认真地回答着自己。“但又觉得那样是对你的背叛,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向前走追寻幸福而去了呢?”
我听见了笑声,那是一个十八岁的,兼于男孩和男人之间微妙年纪,清脆的笑声。
“并没有背叛这种事,你这个笨蛋。”我的鼻尖被人用手指戳了,“看到你找到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东西,我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不知何时开始,指尖的冰冷已经无影无踪了。
“死去的人的时间已经停滞,而活着的人得奋力向前。”他对我说,“就这样一直跑下去吧,八重!”他拽住我的手,重新飞奔起来。
喧嚣声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开始奔跑,飞奔过时间和记忆,飞奔回到了最初的原点。那不过是两个少年,在夜空下的田野间,萤火虫飞舞的时刻。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想象的事情,需要有人记录下来呢。我想成为作家,写出不亚于《平家物语》那样的作品的作家。
那一定是很棒很棒的事情。另一个少年说。
……
雪几乎已经不飘了。
“看样子会回暖。”坐在廊下的道长说,他拿起酒壶敦敦敦,衣衫上多了些口子和血迹。“喂,你这小子,瞪着我的样子好像在说‘这家伙好像一条丧家犬’啊?”道长冲我说道。
“呃……”
“看样子,道长这一整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和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倚在竹杖上,一副很没所谓的样子。
“你要怎么‘看’啊喂。”道长回敬道,接着敦敦敦。
“……你们两个。”我突然有种脱力的感觉。
“鬼市好玩吗?”清海突然说。
“……鬼市?”
“在这个季节很容易撞进鬼市。”道长补充说明,“人鬼殊途,只不过在某些时刻,两个世界会交汇在一起。”
“据说能够见到故人。但如果哭泣的话,就会再也无法梦见对方。”清海说。
“哭泣啊,怎么可能嘛。”不过就算如此,我也不会再梦见他了。
“啊,果然是见到了。”清海高兴地说,“我就说过施主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不要一直念叨我!你们两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吗!”我指着僧道二人的鼻子,“那个奇怪的人影到底是谁啊!我好像差点就被他害死了!”
“是狂百器。”道长说,“人类生前所用的物品如果沾染了邪气就会变成糟糕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样子很帅就是了。”
“如果放着不管的话,会出大乱子。不过……”道长三度敦敦敦,真是好酒量。
“恐怕也是到此为止了。”道长将酒壶立于脑门上,看不出来这家伙对杂耍还是蛮有天赋的。“人生又不是故事,哪来那么多必有回响的结局。不过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想留有遗憾而已。”
“…………”
“道长您悟到了。”清海双手合十。
“到你了大师,别想蒙混过关。”道长毫不客气地指着和尚,“中途你去了哪里?”
“小僧梦见了前世。”
“哈?”
“”
“原来我这一世依然在轮回中的原因竟然是女人的眼泪,啊哈哈哈哈~”
“…………”
“…………”
我就说这和尚才是最深不可测的。
道长说,“啊呀没酒了。喂你,有没有十文零钱?”
“什么鬼!我怎么可能有零钱!”
“只能去讨饭了吗?喂大师,我们一同去讨饭吧。”
“讨饭这种事也能勾肩搭背一起去的吗!”
“不想饿死的话,你也一起来啊。”
“…………我才不要!”
雪彻底停了,天也开始放晴。冬天终究是会过去的。
第二刻,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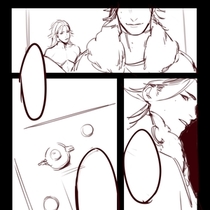


灵山中风常有,生的双袖伴着林涛飘动着,因她双袖宽大,这么空空荡荡地动起来,越发显得她本身单薄起来,一身白衣的生甚至比她本身那一块布料还要显得弱小。
黄鼠狼站在她身后,随时预备着伸出手扶住她。风渐渐大起来,生的袖子东摇西摆,却始终带不动孤零零的身子,女子只是站在山石边,久久地遥望着下方。
“我的家乡那时,天和地没有尽头,和灵山是两个模样。”生开口说,“羊有许多,地鼠也有许多。你说过你以前常常喜欢食鼠,我就总是想起来。”
黄鼠狼并没有回应生。一串细密的踏叶声逐渐远去,他朝深山中走去。而生也并不回头,只是出神地望着。
灵山太高,喧杂声是传不上林根的,只能看到人群在花林和高屋中徘徊,仿佛一卷画忽然活起来。几声极俏的鸟鸣起伏,某片青叶抖了一抖,摆脱了一滴晨露。
孟莘在徒然堂门口站着不知道多久了,她原先嫌地上脏,如今累起来,便不再在乎自己的白衣裳,气呼呼地坐了下来。形形色色的人路过她,有男有女,神色各异,偶尔一道奇异的目光会投到这个小女孩身上。她极快地不耐烦起来,脚趾藏在硬靴里蜷着,手指扯掉了自砖缝里冒头的绿芽,带出一些棕土。
店员的声音靠过来:“黄皮子没那么快回来。他不常待在这里。”
孟莘不抬头,宁愿装模作样地把玩那片叶子。声音的主人并不管她,又走了回去,过了一会她就听到店内有人说道:“可不能让再多的人学着她在门口坐着,像乞儿坐破庙,像什么样子?不如走进来吃茶,等不等到黄大仙,那可要看缘分的。这可是徒然堂!哪里来的枯坐就能见面的道理?”
这人摆明了把话说给孟莘听,她竖起耳朵,但没分辨出是哪个人的声音,耳边又隐约传来店员低声的劝阻声,怕是哪个熟客看不惯她。孟莘憋住一口火,窜起来跺了跺脚,往外走了两步,差一点忍不住,要冲进去与那人对骂,她气急又委屈,心里把矛头指向黄鼠狼。
躲着她干什么?她又不吃人,剥了他皮的人也不是她,她也没有嫌弃这家伙本体是一块鼬皮!次次问过店员,无论哪个店员都说黄皮子去了山上,山上那么大,她又隐隐约约有点害怕,不敢只身上去寻人。实在不行,只好捉一捉他回来领饭的时候,谁知道她自己饿得双眼发花,这个人还是不见踪影。
虽说他不是人,但也要找饭填肚子吧?她可是亲眼看到店里有些灵器和人一般烹茶做菜,还招呼她去吃。想到这节,孟莘的脚底终于一阵发虚,她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犹豫了半晌,她折回徒然堂门口,偷偷往里边看了一眼,客人少了许多,转过来又是几张陌生面孔,一个也说不上话。正举棋不定的时候,身后不知道来了什么人,一把把她推进了门,孟莘收不住脚,趔趄了几步,抬头的时候整个屋子的人都在看着她。她恼羞成怒,回身就要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结果还没看清始作俑者的样子,对方就把什么东西塞在她怀里,落几声笑,疾燕般去远了。等孟莘反应过来,发足追上几步,已经全然来不及。她只能气得骂了几声,回头一看,已经没有人再注意她。
店员过来引孟莘去偏僻的空桌边坐了。她记起怀里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包桂花糕,顿时肚子又响了几声,掂起一块吃了,倒是比家里做的还要美味些许。
店里安静下来。孟莘吃着,落了些桂花糕的粉末在纸上,沙沙响了几声,仿佛树叶影子摇摆时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