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三头老虎各自盘踞屋檐,压低着身子,喉咙里发出警示的低吼,其中一虎动了动爪子,瓦片翻飞,掉在了地上。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像是一种信号,三只凶兽缠斗在一起,从屋顶撞落到了室内,在普通人眼中像是房梁支持不住瓦片的重量,倾倒了。
塔兰看得真切,引发这现象的那三头老虎,其中身形最大的白虎是觉拉,外表和寻常老虎无异的是这家主人造的业。
那凶虎是从一幅画卷中生出的灵,凶虎的主人已经被它杀害,但这灵却不肯离去还伤了无辜的人,先前觉拉和它打斗时占了上风,但突然出现了另一只白虎,对方敌我不明,现如今都打作了一团,觉拉显得有些吃力。
凶兽之间的战斗不是人类可以参与的。
塔兰在被凶虎袭击时伤了腿脚,一时无法起身,他的身旁躺着被开肠破肚吃了一半的富商,那人的肺腑和血散在地上把塔兰的白衣污了个透彻,看架势手在巧的洗衣妇都洗不干净了。
这趟浑水可不是自己找上来的,塔兰并没有义务救人,他不是道士,不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因果报应,这人种了什么因便得什么果。
但波及旁人就不应该了。
这家主人是个富商,生性爱虎,家中物件十件里面有七件是和老虎有关的,虎骨,虎牙这些都是寻常收藏。他出钱雇佣猎户去捕杀老虎,乡里称他是个大善人,当猎人给他送去一只未断奶的小虎时,富商睁大了眼惊呼一声,连忙让猎户杀了小老虎,做了件玩物。
这人若是真的爱虎便不会做出残害老虎的事来,人对喜爱事物的表现真是矛盾,颇有叶公好龙的架势,想必他收藏的那些“虎”的来路也不全是光鲜的,背地里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外人不知道,他自己可清楚。
只可惜这个人不会在睁开眼睛夸耀他得到收藏物的故事了。
受邀到富商家里塔兰并不情愿,往日里塔兰也很少接受这种邀请,之所以会蹚这趟浑水还是为了拿回自己遗落在虎丘山的物件,东西虽小但意义重大。
那是姐姐的遗物,也是她留给自己唯一的东西了。要是普通东西丢了,那就丢了吧,说明他命里该有这一劫。
塔兰回忆那日虎丘山,正是佳节,民间自发组织了庆典,富家子弟们邀请了许多乐坊到搭建的歌台上展示才艺。自己安身的乐坊也受到了邀请,他原想推脱,结果被管事姑娘连人带着琵琶轰了出来,觉拉笑他连一个姑娘都可以将他抱走。
住处不让回,只能跟着自己的师傅们一同前往。
在节日里朝廷放得宽,没有夜禁,夜里倒是热闹,货郎捣弄着稀奇玩意儿,小贩也吆喝着小吃,师傅们带着塔兰四处转悠让他开了眼界,待她们游玩够了才一个个不情愿地拿起吃饭的家伙站到台上,和对家赌气似的比起了手艺。
美人抚琴争艳,尽管已是秋日,叶正黄,百草枯,但自她们的琴下却生出了春意。
塔兰坐在乐师的队伍里轻轻拨撩着管事姑娘给他的琵琶,琵琶虽说不合他的手,但也不影响演奏,他听身旁的人热烈地讨论着新得来的琴谱不禁笑出声。
台上有一女子,伴着乐师的独奏,翩然起舞,姣好的面容犹如盛艳牡丹,一双含着笑的凤眼将台下的男子的心魄都勾去了,惹得女伴们不满地扯紧手绢。
乐坊之间的比试也算是商品展示了。
自家乐坊收场后,塔兰被独的推出去试了本事,这倒也不困难,他的天赋不言而喻,着实是惊艳了一把,更有登徒子想问管事买他一夜,有特殊喜好的人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塔兰卖艺不卖身。
现在安身乐坊也只是暂时的,兴许过几日他就会离开姑苏城,起初到乐坊他只是想住几日而已,没有身份住店可是很难,幸好那些烟花柳巷不要什么身份证明,乐坊的管事看他对乐器颇有研究,便留了他,但塔兰提出了不签卖身契的要求,管事应了。
再者塔兰也没有卖身契可以签。
在收拾家伙回乐坊时一人将塔兰拦下,来人一副纨绔子弟模样,语言却意外的切实,塔兰静静的听着那人说话,觉拉在一旁告诉他个大致。
公子哥讲他父亲近日得来了一幅珍贵的虎啸山林图,想邀请宾客到家中欣赏,于是就想邀请塔兰到家里为宾客表演。
公子哥讲完后塔兰投以微笑表示回绝,在场乐师不少又何必只请邀自己一个人呢,再者,近期事物如此之多,塔兰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听罢,被拒绝公子哥好似喝醉一般撞到了塔兰身上,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耳坠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掉的,不排除是那人有意为之。
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自己已经是落在脏水沟里的鱼了,结果也在这里,自己果然不是番僧。
觉拉跟着自己去了富商家,进门不久就表示出了对这家人喜好的厌恶,任谁都不会喜欢一堆和自己形态相似的死物,塔兰对觉拉的不满没有任何表示,这和自己进出红室没有什么区别。
富商的儿子对塔兰热情,在宾客入席前带着他在院子里走了一遭,也不管塔兰听不听得懂讲了许多自己父亲藏品的故事。宾客到席之后这些故事又在被说了一遍,众人闲谈之际话题引到近期城中的一件怪事上。
近期城里的打更人总是说在巷子中看见大型猛兽的身影,有胆大的人凑上去看却是发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内脏,混着泥土染着斑驳的血迹,兴许是野狗互食也说不定。
一时众说纷纭,但还没有结论闹得人心惶惶。
众人戏说是不是富商家养的老虎们化作精怪跑了出去,所以才没有人发现城中野兽为何物。
富商笑罢,叫小童到书房里取今日宴会的主角,小童久久不来,富商面露难色自己领着客人到书房。只见房门大开,富商踏入房间惊叫一声便跌坐在了地上,好奇的客人跟着进来瞄了一眼吓得慌了神,居无一人想起要求报官。
那小童被刨开了胸膛,仰面倒在地上,头颅不翼而飞,血落在了展开的画卷上,画上赤竹颜色艳丽唯独不见应该在画中的老虎踪迹。
混乱中一滴粘稠的液体落在一位客人的头上顺皮肤着留了下来,他疑惑地摸了自己湿润了的脸。
血。
客人抬头望向房梁,对上了一双惊恐的眼睛,血液自眼睛的主人鼻尖低落,入了客人的眼。烟云凝结,一头虎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它松开口随后头颅坠落。
旁人尖叫着跑开,富商在听到尖叫后才回过神,连滚带爬地往门外逃,在半个身子都出了门槛时又被拖回了房中,门槛外的地上留下了一串绝望的血色抓痕。
————————————————————
想要杀死灵就需要杀死器。
不出意料凶虎的本体就是那副画,两条人命是个麻烦事,在解决完这件事之后自己又要踏上旅途了。
塔兰笑得勉强,画卷在离自己三米外的地上,先前自己还可以正常活动,凶虎察觉到他的意图后一掌将他拍出几米,现在他算是半个伤残想要靠近更是困难了。
大意了这是他自己问题,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觉拉。
塔兰看不到觉拉和其他的老虎去了什么地方,但是耳边的兽吼还在,属于觉拉的声音还在,他稍微可以有一些底气。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觉拉这样和人或者物打斗着,自己一次次的陷入危机,对方又怎样一次次的解救自己,如果自己不从那片竹林里把他带出来,他会不会更自由......
或者还是在那里一直无声哭泣。
塔兰摸上腰间的萧,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划痕,有新有旧,新的划痕还在凭空增加。
自己不是累赘,至少要为觉拉做些什么。他深吸一口气,手指触着满是血污的地面慢慢的移动到柱子旁,靠着柱子站了起来,他的五脏和四肢都在作痛,仿佛要散架一样。
他一步一步地挪着步子,在房间里找着从自己手里飞出去的耳坠。
觉拉和另外两头老虎战场又回到了书房,拉开距离后,觉拉警惕地护在塔兰身前。
“你还可以对付吗。【藏语】”
塔兰觉得他的声音此时此刻一定很难听。
“很难对付,但不是不能解决,你的东西找到了没。”
“找到了,接下来怎么做。”塔兰指着凶虎掌下的一抹朱色,镇静地说到。
觉拉鄙夷地呲牙没有说话像是在思考问题,一张虎兽的面孔也能有那么多表情,放在平时绝对是很逗趣的。
“你要命还是遗物。”
“我都要。”
“麻烦!早干什么去了,”觉拉凶道“只有一次机会,一刻间!你拿到了我马上带你走,扰乱大了,会有人来处理烂摊子的。”
塔兰默允,朝着柱子后挪了挪,觉拉勾起爪子,猛的扑向前,卯足力气朝着一只老虎的脸挥去。
三虎各自为立,否定了塔兰一开始想的画卷中有两头虎的构想。
又是一阵野兽的撕咬声和低吼,三只老虎又打作一团,塔兰抓准凶虎挪开步子的时机,跑到到耳坠的附近一把捞起那物件。
算准时间,觉拉从战斗中脱身,巨大的虎型化作男子姿态,他快速的揽过塔兰的腰,带着对方冲出书房......
“小子,作何感想。”
“......疼。”
结缘部分暂时还没写好,先把能想到的发了出来【ntm
我!踩线!打上了!!!!
——————————————————————————————————
秋意渐浓,即便江南之地,出门也需披上件厚实的衣服了。邻家精力无限的孩童在树杈间跳上跳下,扒拉了几个石榴下来。
“你可小心些,摔了下来,又要让爸妈担心。”警告的话语在书生的嘴里转了一圈,还是跑了出来。街坊邻居的孩子与他并不熟,他也早已过了爬树的年纪,但这孩子摔在眼前的一幕他实在不愿真实看到。
“没关……”大话还没说出口,就看着那孩子的脚底一滑,要不是情急之下把手里的石榴扔了下来,就要来不及抱住树干了。
不过对方似乎并没意识到刚才的千钧一发:“你看,我说没关系吧。”
颜查宇摇了摇头,无奈地笑了。早知道就不说出来了,反正就这么点高的树,也摔不出大事,长个教训也好。
于是这个看上去有些少年老成的读书人把手背在身后,转身进了自家的门。一如姑苏人家的格局,迎着门口的是影壁,再朝里面就是一间门厅。上了年纪的门房眯着眼睛坐在门口,对着他的老茶壶一下一下地点着头。门房虽不识几个字,肚子里却装满了故事,就像他的茶壶,就算不放半片茶叶,只泡上一壶白水,倒出来也还是一股茶味。颜查宇小的时候,他常抱着自家小少爷讲故事,他也成了这位小少爷为数不多的忘年交之一。如今他年事已高,便安排他做看门这类轻松些的活。颜查宇记忆里,当自己觉得自己的话语有些“能力”时,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不过对方只当是孩子年幼,错把一些巧合总结成规律,误以为只要把坏事说出口就不会发生。而颜查宇在母亲过世后,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注定会发生的事无法避免,何须多言。
绕过影壁,天井左右是两个小小的厢房。阳光四四方方地投下,给寒日里的人带来些许温暖,闲来无事的仆人蹲在墙根,孵着太阳,聊着闲话。中间的天井地面是用一条条深青色的砖铺就而成的,在水乡湿气的氤氲下,不常走的地方已经长出了一层细密的嫩绿色,更里面的墙缝里,羞羞怯怯地钻出了怕太阳的蕨类植物。
再往中间走,跨过门槛,就置身于第二进门厅里了,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着一幅匾额,上书“世德流馨”四个烫金大字,一边一溜小字,诉说着这副匾额的来历。想来是当年颜家祖上官至三品时,同样来头不小的同届赠与的。时过境迁,颜家业已式微,而以匾额相赠的那家,不知是仍旧钟鸣鼎食,还是同样经历了沧海桑田,大不如前呢?查宇叹了口气,幼时的自己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是有些许异能的普通人,怎么挡得住时间的滚滚洪流呢?
穿过这座门厅,走进长廊,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栋宅子中点睛之笔的存在了。颜家的宅子不大,却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气势,全赖这一片小小的院子。提到院子,就不能不先说一下园中的池子。姑苏城里常见园中池塘大多依照地势,或圆或椭,边缘流畅,围以假山花木。独颜家的池塘有棱有角,呈“凹”字形,边缘立着一溜雕花的石栏杆。池子中间围着一座小亭,亭畔堆有假山,穿过假山山洞,则又是另一番风景。这儿也曾是颜查散和伙伴玩乐的一片天地,如今他们高中的高中,备考的备考,就剩他这为数不多的闲人了。他本无心进取,父亲催得也不紧,便这么得过且过了。
不过,闲人也有闲趣,近日恰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城外天平山上的红枫大概也到了观赏的时节,不如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去,权当是枯燥生活中的一点歇息。于是他打定主意,派下人传口信去了。
姑苏向来以小桥流水而闻名,周围却也不乏名山大川,就如这儿所养育的子民,既有善良体贴的心地,也有忠义报国的气魄。而天平山也与一位能人志士有着不解的因缘,就连植于山上的这百余株枫香苗也是他的后人所栽植下的。如今这片枫林已茂密成林,或许有朝一日,时代变迁,它们也会消散于战争的铁蹄之下。或许是由于眼前这片艳丽如火的枫林,颜查宇也被勾起了一丝秋日的寂寥。不过正所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或许也只有这么思考,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与其这么杞人忧天,不如好好欣赏难得的美景。
虽比不上五岳名山,但天平也占地颇广,从自己的沉思中回过神来,同来的有伴们已不知上何处去了,唯余他一人立在满铺着金红色枫叶的石板小径上。奇怪的是,路的远处,火红的尽头,却是一片淡粉,不像是枫叶,反倒像是三月里盛放的桃花,再往后便是一连片粉墙黛瓦的建筑——姑苏一带常有的建筑。
颜查宇虽对怪力乱神之事还抱有些怀疑,然而关于徒然堂的传闻却早已在姑苏城内不胫而走,甚至有时为了教训不听话的孩子,家长还要凶道:“再哭,再哭就被抓紧徒然堂里回不来!”于是大多数小孩便会抽抽搭搭地止住了哭,顶多忍不住再抽噎几下。查宇没被这么吓过,毕竟家里没几个会去管他的人。母亲在他十岁时就不幸撒手人寰,父亲则在外县任职,下人们则巴不得他开开心心的,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这么想着间,颜查宇冒冒失失地走到了桃花林的尽头,现在,他在月洞门面前,他甚至觉得自己在被审视着尽管这扇门并没有突然开口说话,或是有什么志怪小说里才有的行动,就像消逝,变化,万物的终结,它们无声无息地环绕着你,侵蚀着你,让你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变成了另一样东西。很久以来,颜查宇就觉得穿过门后,自己就和先前站在门前的自己不再一样了,或许是丢失了什么回忆不起的片段,又或者是知道了什么无关紧要的实施,再或者更早之前,它也曾间隔生死,阻断联系。
或许这扇门就是死亡本身?跨过了它,就是一片未知的地方。有朝一日,自己总会跨过它——不管世事如何,颜家的少爷有着超尘的气质这点早已名声在外,恐怕自己某日真的羽化而登仙,旁人也不会有多惊讶;可是他也清楚自己没这么无忧无虑,可以的话他也希望这样的时日保持下去,永远不要改变。当局者迷,颜查宇又怎么会知道,世上大多数人皆是如此,乞求着永恒的到来,却又无时不刻不苟延残喘着。
“回来,我的桂花糕!还我桂花糕!!”稚嫩的声音在桃林深处响起,伴随着另一个有些疯癫的笑声,飘忽不定地传进了颜查宇的耳朵,打断了颜查宇的思绪。
“吹牛说要起去看海,结果上这儿来偷我的桂花糕,早晚有一天你要……”声音渐渐弱了下去,不知是因为距离离得远了,还是当事人自觉不妥,收了声。
不过被骂的那位似乎并不在意,还是一句话顶了回去:“早晚有一天回去的嘛,今朝有桂花糕我今朝醉~!”
“你赔我桂花糕!”被偷了桂花糕的那位像是被踩了尾巴的一样,追了上去。依稀看到两个不高的身影在桃林间追逐着,一蓝一粉,像是春天刚出窝小麻雀,叽叽喳喳地翻腾着。随后又踩着树枝,翻进了墙内,连颜查宇都不禁要被逗笑了。
不论如何,起码死亡没有躲在这扇门后。这位再常见的不过的书生迈开步子,跨进了他不曾预料过得奇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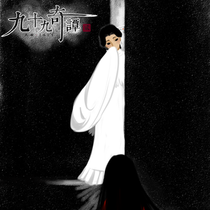

诗云,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十竹离开家门后是往北走的,他碰到的第一个决定落脚的地方,是苏州城。这里和杭州一样,过了秋分时节,河道里的流水便开始渐渐少了。天空越发高远澄澈,地上的晚稻也渐渐饱满而显出金色。这些是城郊的物候景象,城里则不论春秋,一律都如宋时那位伟大词人笔下那样繁华。
更何况八月节到了。
十竹收了说书的摊子,摸了摸行李卷儿里的钱币。摆摊说书挣来的钱实在不是很多,好在灵器对于口体之奉的要求没有人类那样急迫。实在没有办法,捕一只野雀烤一烤也是能凑合过来的,只是拔毛太麻烦。他曾经在山里用袖中的刀片抓过鱼,然而刀片对于刮鳞来说又有些勉强。况且,既然进了城,就不能搞那些野路子了。万一一个不小心抓走了某个显贵的宠物,他这辈子就别指望把一肚子的故事传出去。
秋天,天黑得要比夏季晚一些。往常这个时候,掌柜会为作坊的伙计们提前半个时辰放工。那些还是孩子的学徒经常拿了钱跑到街上,他们回来时往往抱回一堆吃食玩物。十竹自己想尝尝小伙计们买回的桂花糕,却不忍心偷吃这些孩子卖手艺换回的好东西。对这类东西的向往转化为了对中秋节的好奇,所以他一直呆在苏州城边缘的一座小桥边上,静静等待着黑夜的降临。
随着天空的颜色逐渐转深,一盏盏灯开始从河两岸的这头亮到那边。各家店铺的管弦丝竹渐渐响了起来,逐渐形成此起彼伏的声势。河上的行船里也逐渐飘来歌声和酒令的声音。趁着过节出来卖东西的商贩占据了桥的两侧,不知是谁头一个叫卖,很快就像着火似的,一整条街都变得热闹起来了。
有雅兴的人在此时会在清静的地方赏月吟诗,图热闹的就像十竹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随意溜着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看个新鲜。如果不是囊中羞涩,他此时已经抱了一堆好看却无用的各类小物件了。
天终于彻底黑了下来,城市的灯火也彻底亮了起来。他看到人群正往城外涌去,那个方向是虎丘山,他对这座山的印象,就在于以前刻过的一本讲伍子胥的话本——那里是孙武练兵的地方。
以及,十竹最熟悉不过的那些艺人的入话。
“玉盘悬东楼,佳人伫西山——”
“年年岁岁月如盘,岁岁年年人相异——”
“八月桂花熟,千灯映姑苏,小人这里一祝各位事事常如愿,二祝各位身体常康健,三祝各位年年得归家,团圆如冰盘——”
真是应景……
十竹放慢了脚步,他看了半天,选了一位自己觉得最顺眼的摊子。这位老兄已经讲完了入话,开始唱曲儿了。他边上还坐着几个给他伴奏的人,待他念了段白,一阵乐声响了起来,他也开始唱起来了。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栏。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已吩咐催花莺燕借春看……”
啊,这是牡丹亭。
十竹记得这个故事,他自己也非常喜爱这个故事。没有谁敢私自刊刻这本书,最初他看到的也是手抄本——然后,刻工师傅用他刻出了游园惊梦,冥誓还魂。他忍不住走上前去,拣了一个好位置仔细听着,兜里的钱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边上收钱的女人手里。这出戏到底勾起了多少少女没有死掉的爱恋与渴望,十竹并不清楚,但引得杭州城里一名美艳歌女跳桥,却是他所目睹的事实。
身边忽然有人说道:“这本子……大概也没谁敢刻了吧?”
另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回答:“这不一定。”
十竹转过头,说话的是两个青年,他没看清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只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头发分开两边,眉心中带着一点红印,这是那个年纪略轻的。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被艺人的表演吸引,而是专注于另一种更“大”的事情。 “总会有人刻本子的,只要有人爱看,有人会买。”
“你也会说这样的话吗?”
“行个好,今天过节就别消遣我了。”
十竹目睹他们离开,直到他们走出了几步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看着那两个青年站在了另一处唱曲儿的地方,亮嗓子的人总是比讲平话的更具有吸引力——不过其中那个更年少些的越过了人群,来到一个讲平话的人的面前,说书的老兄周围的人虽然少些,不过也挺热闹了。十竹摸了一把兜里的钱,索性买了个桂花糕也凑了过去。
那个年少些的青年忽然和他四目对视住了,那种目光不像寻常百姓,它就像尖锐的利刃,能够刺到你心里隐秘的地方,他移开了视线,觉得自己背后有点发毛。青年说了句话,并没有对着他说,而是对着那个讲平话的说的。
他说:与我说一个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