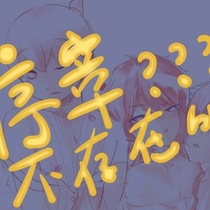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来到徒然堂的人类,多少有那么点奇怪,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正常扔,只是玉梢觉得自己怎么总是遇见这么些奇怪的人。
“.…..”玉梢抬手在这人眼前挥了挥,对方也没有什么反应,或许是真瞎,她想,看不见是一回事,这人笑的倒是挺开心的样子,“在这里做什么?”
好歹这人不是聋子,玉梢看见他指了指自己腰间的那把横刀,似乎是之前遇见过的人。
估摸着是刚刚买下这把刀的买主,玉梢也不好多做阻拦,侧身让开一条路准备让人走的时候才想起,这人看不见,似乎也不会说话。
但是看不见又怎么会买下这横刀?
或许是假象。
玉梢皱了皱眉头,看见了那人手里还握着一支萧,猜想着,最后她牵起萧的一头很轻的拽了拽,而后向前走去。
要从这个地方走到店门外并不是很远,玉梢没有看见应该在的引路人,想着对方可能正在自己的田地里忙活,既然被自己遇见了随手帮一把也没什么不好的。
被从这里带走是一件好事吗?玉梢曾经这样问过自己,最终并没有得到答案,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去问问别人是不是想要被从这里带走,或许这个问题去问那些已经被带走的灵器才是正确的,但是能够回得来的,愿意回来的,寥寥无几。
“为什么选择这把刀?”玉梢问道,她猜想这个人或许不善言辞,也没有期待过他给自己一个回答。忽的,她的手被拽了一下。准确的说,应该是握着的萧被往后拽了拽,似乎是在叫住自己。
那支萧被从自己手中抽走,取而代之的,是男人的手指在自己的手心画着什么笔画。
“护……身?”玉梢歪了歪头,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人写的是这两个字,她正在学习这个年代的字体,虽说和自己所处的时间的字形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字体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
“我能……”玉梢抿住了双唇,没有再说下去,反倒是那人读出了自己的心思,拽着自己的手,又写下了两个字。
“外头在下雪,你怎么来这里的?”玉梢和那人坐在树下,她不知道这是一颗什么树,只是知道在这个时间,躲在这的阴影下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迷路进来的,或者可能是有谁指引的吧。】
他的字写的也不好,有些歪歪扭扭的,还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些错误。用词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原的人。玉梢只能跟着他一边写一边说。
自然是知道这人不是不会说话,更不是看不见,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去戳穿,每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玉梢没有哪个想法去把每个人都看的透彻,她自然也没有这个能力。
至少现在的交流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多只是麻烦了点,这并不会带来什么不便,自己与他的交流应该也止于今天而已。
“你是西域人?”
【按照你们的说法,是的。】
玉梢的手心有些痒,虽说有茧子,但是她还是在那人手指滑过的时候微微收拢了一点手掌。
树影婆娑,随着风吹过的轨迹,光线闪烁着,有点晃眼。玉梢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她稍稍回想了一下,才记起自己原本是想要做什么。
重新回过头去看那个人类,穿着打扮确实不像是这里的人,闭着的眼角有些上翘,看上去似乎是很开心的样子,应该是找到了灵器的喜悦?
要说不好奇是假的,可是玉梢知道这件事情并不重要,问出口对谁都不好,为什么装作瞎子,又为什么不远千里来到中原。
她抽回手,抱住了双膝,抬头去看,晴空万里,这里说到底还是幻境,不能算是在人间了。
风吹过,落叶掉在玉梢手边,自己来自哪里至少还有印象。但是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已经忘了,也有人说是自己把它藏起来了,为了能够代替谁活下去而藏起来的。
我想活吗?
或许不想,又或许想。本来器物就没有活着这个说法。灯影流转,岁月变迁,人总是会死,自己又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他们薄如蝉翼,自己又何尝不是。
“你觉得……灵器愿意离开吗?”
若是没有缘分,即便是带离了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办法看见的,虽说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但是每每自己溜出去的时候,都没有人能够注意到自己。
如果。
这个只能够用如果来打比方了,“如果你看不见他。”
如果他不愿意离开这里。
【你不愿意离开这里吗?】
那人写着,这次是在自己的手背上。
“我……”我应该是不愿意吧,但是我有东西需要去找,那就必须离开这里吧。
【你有什么目的?】
玉梢摇头。
【你有想要的东西吗?】
玉梢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她有,她应该是有的,就算是这幅身躯被破坏,就算是被玷污,自己也有必要去找到那个东西。
【我也有,所以我要他,就算他不愿意。】那人拿起了自己的萧。【人总是不择手段的。】
他或许开口说话了,又或许没有,玉梢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全当这人在用文字和自己交谈。箫声悠扬,多少带了点悲怆。
“你身上,有白粉的味道。”玉梢吸了吸鼻子,没有打出喷嚏来。那是花街柳巷的味道,是女子身上的味道。一个乐师,一个有着缺陷的乐师,途径大雪,身上却带着这种香味,多少让人有些误会,“你要去找什么?”
【一个人。】他停下了吹箫的动作,抬起手闻了闻自己衣物上的味道,而后又放下了,歪着头朝着玉梢。
“你能找到吗?”
【我总要找到的。】
“希望如此。”玉梢站起来,重新握住了那支萧,拉了拉,“多停留不好,我送你出去。”
总要找到的,希望如此。事情永远不会那么简单就结束。要迈出第一步或许也不那么难。
【你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
他回过头和自己这么说着,玉梢不能出店,没有店长的画押,她踏不出门。
横刀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两个人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她不能明白被带走的灵器的心情,也还不能明白去寻找一个可能永远找不到的东西的人的执着。

是雨天。
玉梢坐在亭子里歇脚的时候下的雨。与本晴空万里的天气忽然的就落下雨珠来,好在今天本来就没有什么预定,在亭子里坐着看雨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绣球开的漂亮,只可惜估计这场雨过后就得蔫了。
土质过于湿润的话对于这种植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玉梢并不懂花草,只是看着那一团团的花朵在雨天里淋着多少有些可怜。
徒然堂四季如春,但并不代表不会下雨,这次的雨点还挺大的,突如其来所有人都没有准备,玉梢是运气好才躲进了这个亭子。
“啊呀,已经有人了吗?”雨滴搭在油纸伞上的声音逐渐靠近,最终停在了距离玉梢约几步远的地方,“是否介意?”
玉梢点了点头,那女子穿的华丽,裙摆倒是一点都没有湿掉,头上的装饰多到让玉梢想起了那些贵族,总是带着金色的钗画着有些夸张的妆容,手上拿着绣着精美纹样的团扇,不论到哪都是一股白粉的味道。
“你便是那新来的唐弓?”
阴雨天气总是人烟稀少的,好在温度不像是外界那样冰冷,多少不会因为一场雨就急剧降温。玉梢有些困,对方开口问自己是不是唐弓,迷迷糊糊间也就点了头。她早就已经不记得自己生于何年何月,更加不记得那是哪朝哪代,只是隐约记得战乱结束之后的样子。
“你可听说过盛唐之世。”
玉梢摇摇头,她醒了醒神,想着或许这人是来找自己叙旧的也说不定,只可惜自己没有什么能够给她说的。
“隋唐过度之快,只在几日之间。逼禅让便成国舅而后称帝,其后几代依旧战乱不止,盛唐不过是对比而言。”玉梢打了个哈欠,她知道的确实不多,前半确实是她曾经见证过的,后半是现今得知的事情。
那人没有再说话,似乎是在思考些什么的样子,雨倒是越下越大,打在砖瓦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比起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词更像是敲击在杨琴上的声音。
“你生于何时。”她问,而后又言,“或许我该叫你声姐姐。”
“我不记得了。”她吸了吸鼻子,“你出身贵族,不该与我姐妹相称,我于战场,你于宫廷。”
差别太大了,“叫我玉梢就好。”
前后恐怕只不过相差了几十年的时光,那也已经足够王超改头换面一番,玉梢不清楚自己被埋后的事情,只怕眼前这人是只知晓宫廷内的事情。
“我问你,你知道初期时有谁叛变被诛了九族?”玉梢突然想起这事来。转头便问,分明是正午时分,天上反倒是劈了雷下来。昏暗的景色,亮堂了一瞬,那人长着一双鸳鸯眼,看上去反倒是像只有些狡猾的猫。
“不知你说的是哪家。”她笑起来,一身华服此时此刻反倒是像沾了血,前朝几代人的努力和牺牲,不论是权力斗争还是保家卫国,自己的时代确实早已过去,自己的主人也早已死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事到如今被问起有谁被砍了头,杀了家人,倒真的是答不上来,反倒是更想敲开这人的脑子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什么样的东西。
“哪家……”玉梢低下头去,要问起哪家,她还真不好回答,既不能答育有一双子女的,又不能说谋反的那家。
“再之前的事我不清楚,只是在我这代,死的人也不在少数,要是真的想知道,那也只有出了这姑苏城才有可能。”杨雨霖这么说着,更多的实际上是在劝诫和嘲讽,不论是谁,只要有些常识都不会这样问,又或者这人确实傻的可以。
“姑苏……”
玉梢似乎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若是真的有需要,可能真的会独自一人想办法离开姑苏去找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吧。
“你真的想出去?”
玉梢没有回答,似乎是还在思考的样子。
“总会有人愿意带你出去的,在那之前,不如好好享受。”杨雨霖顿了顿,“你也不像是贫苦人家的,除了骑射,可会歌舞?”
玉梢愣住了,雨还在下,只是比刚才小了许多,绣球的花瓣被打落了不少,树叶也落下来盖在了上头,要问自己是否会歌舞倒还真的回答不上来,她没有学过的可能,更不记得前主是不是精通这些。
拖了一会,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表示否认。
“你要不要学?”
雨落春庭,一曲断肠。
如果现在有人匆匆路过院子,或许能透过雨帘,远远望见有谁在亭中起舞,一红一蓝,歌声不断。
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抬手之间也不带有金粉银沫,更没有莺莺燕燕花团锦簇。
不存在君王,更不存在观赏者。衣袂飞舞,似是流水,又带刚毅。
唯有一弓,一钗,一亭。
真要说起来,这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性,共同点或许也只有主人的离世,其缘由也只能总结为时事造人。
她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天平,以一种奇怪的重量保持着平衡,一方忘了所有,一方忘不掉所有,这个天平永远不会倾斜,但是这个天平也永远不会成立,命运是一种令人苦恼的东西,死亡并不会让事情变得好起来,永远只会变得更糟糕。为了权利,为了地位,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
谁死了都不能怨,但是有不得不怨。
谁都没有错,却也谁都有错。
杨雨霖怨,怨得成了灵,玉梢也一样,她只是怨得连自己的怨都已经忘了。现在又马不停蹄的,想要把这种情感找回来,在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大范围内,在自己能够活动的最大范围内。
她们都保有着生前的样子,那不是自己的样子,而是自己主人的样子。如同她们那般,活着。
“你恨吗?”杨雨霖问着,朝前进了一步。
“我忘了。”玉梢答着,又朝后退了一步。
雨点打在好看的雕花栏杆上,最终放晴了。
“忘了也是好事。总不需要像我这样,总是怀恨在心。”
玉梢看了一眼杨雨霖,没有再朝后退。
“我想,我应该想起来。”
她最终,应该是选择向前进一步的人。自己呢?或许只能停在这里,又或者朝另一条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