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玉梢看见的不是外面的景色,而是黑暗的,如同墓室中一样的环境,黑暗、冰冷有些发潮,混着泥土和奇怪的味道。
我不要。
心里有谁在这样喊着。
我不要,请让我出去。
玉梢一下握紧了胸口的布料,这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在喊,绝对不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张开自己的嘴。
好痛。
好痛啊。
胸口就像是被针戳了一样,一下一下的疼,一阵一阵地逐渐的从胸口扩散到上半身,连着腿脚都一起发软,最后,蔓延到脑袋上。自己没有受伤,那里都没有撞到也哪里都没有流血,根本没有伤口。
这都是假的。
可是真的很疼。
玉梢跪在地上,或者说反映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匍匐在地面上了。她想要出去,剥开这个黑暗的环境出去,这里不是她想在的地方。好不容易从哪个地方,从哪个像是地狱一样的地方出来了,不能再回去。
那里就连虫爬的声音都没有,就连风吹过的声音也没有,更别提四季和灯火。戏文里出现的亡灵和僵尸也不存在,哪里有什么冥界,哪里有什么地府。单单被关在那儿就已经是折磨。
是啊,是啊,我想要被带出去。
玉梢闷哼着,挣扎着,像是一个疯子一般在地面上手脚并用的,想要爬起来。
她不知道地面上铺着什么,或者没有铺什么,她只觉得一切触碰到地面的地方都在发烫,烫得像是有什么虫子逐渐逐渐的带着热度爬上来。
我不能留在这里,不可以,我要出去,我已经不会再成为陪葬。
于是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爬起来,耳边响彻着轰鸣,没有人会来救自己,也没有人会来可怜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只有自己去做。首先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出去。
盗墓贼。
对,盗墓贼!那些人类呢!把自己从墓里挖出来的人类呢?就算他们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现在的线索也只有那一行人,他们说过了。要把我擦干净了卖出去!
玉梢跌跌撞撞地向前,步履蹒跚,双手在前方的空中挥舞着,不知道应该抓住什么,又想要去抓住什么,最后她撞到了架子,又或许是衣柜,亦或者只是一根柱子,她只知道自己确实地撞到了什么。
“什么声音!”
耳鸣一下停住了。那种灼热的温度和疼痛感也一下消散下去。有人,外面是有人的。
已经是谁都好了,就算是恶鬼,即便是怪物,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
门被打开了,玉梢借着烛光看清了,这里只是一个仓库,昏暗,宽敞,地面是防潮的干草,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而自己,已经落在了地上。
“那把弓呢,快拿出来,有客人指明要它。”看上去像是领头人的存在这么说着,穿着有些简陋的人就跑了过来,把自己捡起来了。
蓝色的弓身,雕刻着细小的花纹,弧度精巧,弓弦依旧泛着光。
有人要把我带走。
仿佛这一切都是梦一样,自己不再孤身一人,有了意识有了实体,被人从黑暗中刨开,砸碎了硬生生地重新塞回人声鼎沸的地方,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世界。
这是真的吗?或者确实是梦?
玉梢没有看见买走自己的人,也不知道对方出了多少钱把自己买了下来。
【你过来。】
自己听见有人这样说,甚至向自己伸出了手,周围的人像是见了鬼一般。
可这并不影响什么,不影响自己离开这种鬼地方,外面已经是夕阳西下,路人手上都点上了灯笼,那个人的手是暖的,牵着自己,一步不停地向前,而自己的另一只手里则是抱着自己,那把蓝色的,雕刻花纹的弓。
【再忍一忍哦,很快就到了。】
对方似乎是这个语气,又似乎不是,玉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她也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理解去听取,只是一个劲的,像是人偶一般朝前走着,迈开了步子,跨上台阶。
“哎呀,是新的孩子吗?”
猛地抬头。
那个带自己来的人已经不见了影子。
在自己眼前的也已经不是街景,取而代之的是穿着有些古朴的女性,她躺在莲花池中,自己站在池边,双手抱紧了那把弓,指尖通红,衣衫不整,甚至喘着气。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别哭了。”
“我没有。”
玉梢张开嘴,声音沙哑,她自己都不相信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语调。自己的声音敲击着心脏,打碎了灵魂,最终从里面抽丝剥茧,小心翼翼又粗暴地把所有的感情撕扯出来,一切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又全部都重新开始。
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又即将拥有一切。
“这可真是,来了个别扭的孩子。”她脚边的两只兔子似乎是被这个动静吵醒了,缓慢的爬起来,看看站在湖边的自己,又看看那依旧睡在榻上的女子,“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先去整理整理自己吧。”她顿了顿,“阿芷,你既然来了,也就别在那里看着了。先来帮帮人家。”
玉梢猛地回头,确实有人躲在了柱子后面,黑色的长发随着倾斜身体的动作晃动着,在夜风中发这柔光一般,她笑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似乎是对于被发现这件事情感到了有些害羞,又像是恶作剧被戳穿了那般有些小小的失落。
阿芷跑上前来,一点都不介意玉梢有些带着杀气的眼神,抓着她的手就往前拽,“那我先带她去了!店长晚安!”她朝那人喊着,玉梢回头去看,两只兔子已经又睡下了,那个女性朝自己挥了挥手目送着自己离开。
“要去,哪里?”玉梢脚下磕磕绊绊的,但是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叫住这个女孩子,只好一路跟着往前奔跑。
“先把你整理一下啊!还有还有!这里很大哦!要小心别迷路才是!”阿芷看上去开心的很,一路上都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啊,对了对了我叫阿芷!你呢!”
“我——”
玉梢被拽着奔跑,一路上连话都说不清几句,手上还抱着那把弓,更是不方便,她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带去哪里,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是哪,只是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危险的样子 ,要说这里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家,那是完全没有实感的一件事情,就连这是哪,谁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把这里称作自己的家?
“到了哦!”玉梢一下子停下来,差点撞在了阿芷身上,说起来一路上岁数虽说她牵着自己,自己都只是隔着布料,根本没有见她伸出过手来,“是温泉哦!”
温泉?
听见这个字眼,玉梢终于是回过神来,抬眼望去,确实是温泉,在岩石中间,似乎是被人修正过的样子,硫磺味道浓重的天然温泉。
“嘿诶!”
“诶?!”
玉梢只觉得脚下一空,手上的弓和头上的发簪就一块落入了那姑娘的手里,自己则是直接跌进了温泉池里。温热的,甚至有些烫的水浸没全身,因为过于的意外,玉梢就这样睁着眼睛沉到了池底,从水面下能够看见那姑娘双手叉着腰开心的样子被水面的波动扭曲着又逐渐的趋于平静。
“噗哈——!”
好不容易从池底爬起来的时候,已经整个人都是湿淋淋的了,胸口剧烈地起伏是因为在水下呆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氧气不够造成的,这也同时使得玉梢说不出话来。
“为……为什么。”单手抹掉了脸上的水珠,又把长发撸到脑后去,玉梢发现阿芷已经脱了鞋,撩起裙摆坐在了池边。
“因为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啊。”阿芷双腿晃晃悠悠地踢着水花,双手捧着自己的脸,“总之先暖和暖和再说别的事情呗。”
玉梢沉默着,坐在水中,体温从指尖开始,逐渐的上升,沉默一直保持到了玉梢的双颊开始泛红,阿芷才伸出手把玉梢拉上来。
“这里是徒然堂,你听说过吗?”阿芷问着,“对了对了,你叫什么呀!还没有告诉我呢。”
“玉梢。”她一边摇着头一边回答,跪在池边的动作没有持续很久,玉梢站起来,撩起裙摆开始挤水,在这样的夜里,她站在池边,全身还冒着热气,一边试图弄干自己的衣服一边思考接下来的事情。
自己确实出来了,从哪个空无一人的地方逃一样的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
“我说我说,明天我带你一起看看徒然堂好不好!”阿芷也站起来帮着把衣服弄干,“不想一个人的话可以和我一起睡一晚哦!”
“不是,我……诶?”
“呼呼——,一起睡呗,没什么不好的!”阿芷笑的开心,有牵着玉梢到处走动,借着月光,一点点地开始介绍徒然堂,一直到深夜,阿芷开始打起了哈欠的时候才终于到了能够休息的地方。
和墓与仓库不同,这里好好地有着床铺,有着梳妆的台子,俨然一间闺房的样子。
“快来快来!”阿芷拉着玉梢,一点也不避讳的样子。
“不是,你等一下,怎么说都有点不好吧!”玉梢被这样拉进放进,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了,就算对事物冷淡如她,一口气就这样和别家姑娘一起睡觉多少还是有些拘束。
但是这些顾虑在沾到床沿的一瞬间就消散不见了。
阿芷还在考虑应该怎么哄骗玉梢的时候,发现对方摸着柔软的铺子,一下安静了下来。
果然还是累了嘛!
阿芷鼓鼓脸颊,看着这人兢兢战战毫无神采地走进店里,迷迷糊糊地被带到店长身边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了,仔细一看,不是已经面色惨白了嘛!或许这人自己不知道,别人可看得明白的啊!
“要睡了吗?”阿芷拍拍软绵绵的被子,拉着玉梢也不放手,“晚安哦?”
失去意识的时候,玉梢只能看见阿芷笑的开心的样子,抵抗的心思全部被那张笑脸抵消了去。
如此失态,可能还真的就只有这么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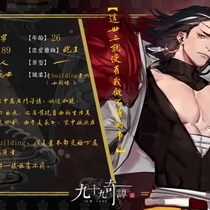


本来打算先摸个现pa的,但打开文档才发觉现pa还要再想名字……从入门到放弃……(别放弃好吗
算了还是先摸完序章剧情吧。土下坐给女朋友道歉。
在死线的间隙用绳命摸鱼,头发-1-1-1-1-1
末尾杏姐我的亲姐露了个脸,下章才是她的主场……先飞吻一个。
————————————
李家小姐极有可能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相好。
推断出这一可能,常山下意识的斜眼瞟了一眼赵衔。
赵衔被他这一眼激得连连摆手苦笑。
他摇头:“莫要瞧我,这事,这事……哎,荒唐得很!”
这话倒说得很是。在场之人没有不点头的——从失踪的王公子到内藏玄机的山水图,再牵连出那早已亡故的李家小姐,本是一无人愿管的志怪案子,那里料到顺着那蛛丝般的细线朝下头摸索,竟牵扯出这许多事情。
可说起那最关键的王公子,且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呢!
常山抱着山水图,心里头有些沉重。
他倒是不如和怀疑这赵三,因晓得对方实非那等禀性轻佻的人物。
且不说赵母今儿还在替小儿张罗着群芳争艳的美人图,便是逢佳节踏春,那也是几多香帕子绣袋子恨不能砸进赵三公子怀里头——可这温文公子待谁都有礼,却也是待谁也瞧不见半点特别之处的。
赵衔若有朝一日有心仪之女子,又何须如此鬼祟,行那等私定终身池边私会之事?
思索无果,常山又问几个老仆:“那日真个就没人瞧见,那荷塘边除了李小姐还有甚么旁的人?”
这显而已是个极不死心的问题了。也只有常陆之这般倔又这般谨慎之人,心思才仍在这事儿上盘着不走脱。
因你想,昔年李大人官场得意时,连个赏花宴都群邀百官极尽奢侈之能事,排场摆得就差比龙椅上不理事儿的那位还大些。这样一位官老爷,家里千娇百宠捧在手心子里头的嫡出女儿莫名惨死,便是有半点可疑之处,李大人莫不是还能不查?
再退一步说,便是李大人吞得下独女夭折这口老血,失了身上一块心肝儿肉的李夫人,却也是决计不会罢休的。
那时尚且没得人替溺死的李小姐做主,只得叫一干子奴仆陪着小姐一道走一趟阴间路,宽慰阳世父母心,此时换了你一个大理寺小司直,便能额间描个弯月充那青天大老爷,叫人沉冤昭雪了?
一众老仆毫无例外纷纷摇头,常山眉头越发紧,挥手示意他们可以退下。
瞧着散去的众老仆,他拧着眉问一旁的王福贵:“原李家的下人便只有这些人了?可有未到的?”
王福贵底气不足,面上的笑带着点尴尬:“却还有一人不在场,倒也没什么可叫官人挂心的,料想那老货也不知晓些什么重要事情。”
常山不买他的帐,听有人未至,立刻追问:“是何人?缘何不曾来?”
王福贵无法,只好一指地上孤零零一把竹扫帚,语气很无奈:“便是洒扫的余婆子,也不知方才好端端的发起什么癫,现下已派人去寻,这婆子平日最会躲懒,可是不好找到。”
说的竟是那一瞧见他们,便扔了笤帚转身就跑的洒扫婆子。
依着常山的意思,便是现下立刻亲去寻那婆子问话,那也是使得的。可从方才起便若有所思的赵衔却用扇子将他一拦,道一句且慢,一双眼便落在王福贵身上,这公子眼神很怪,瞧得王大总管心里头发虚,额上几欲冒汗。
和气的赵三公子开口依旧和气,说的话却叫王福贵脑门子上那几滴汗,终于滚了下来。
只听他道:
“李大人为人宽厚,惯来礼贤下士,不拘士商之分。昔年李府的赏花宴,从不乏商贾人家……今日衔一见王大善人,便观之可亲,只觉面善非常,不知王总管可否替衔解惑,今日府上主人,可是昔时李大人座上贵客的那位王大善人?”
*
王老爷五年前是否入京,又是否受邀赴了李大人府上的赏花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要知道并不很难。
王福贵抹着汗没敢乱开口的事儿,王老爷颓丧地叹了口气,眼也不眨便应下了。
“行商艰难,隔年入京走动一番,乃是王家的定例。”
王老爷解释道。至于在京中如何走动,为何走动,他没详细说,却觉得在场之人该是你知我知,大家心知肚明,自有一份默契在的。
官商官商,别看士子中有多少瞧不上商贾铜臭的清高人物,真正计较门庭书香不沾铜臭的,又有几个讨得了好?
江南富甲的王大善人做得大官老爷的座上宾,那些裹在江南名产锦绣缎子里抬进官老爷府邸的金砖银条一箱又一箱,称作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土仪,权当表个心意。
官老爷见着这样的心意,自然没有不舒心的。商贾们也满意得很,这是桩不坏的买卖,能为接下来一年的生意买个依靠,舍些银子铺条官道,不仅不亏,且还赚了呢。
见多了赵家门庭往来,赵衔对此果然心领神会,微笑点一点头,只常山不言不语,赵衔猜测他约莫心里也清楚,只是他这样的人物,向来是极厌烦此类事情的。
王老爷接着感慨:“那年李家赏花宴,我接了李家的帖子,便带洹儿登门拜访,那里知道会出那样事情……”
他说到一半,忽地神色一变,那双先且没什么精神的小眼睛中猛然闪过精光,一瞬间从颓然老父转而成了一个精明商人的模样。王大善人面色不太好看,甚至可说有些泛青。
他满面怀疑,惊道:“两位缘何问起此事,莫不是……我儿失踪一事,竟同那场旧事有了甚么牵连?!”
赵衔与常山对看一眼,他二人种种推测,不过发生在这半日间,且因牵扯到陈年旧事,拿得出的证据更是少之又少,纵然一切似乎都叫一条暗线隐隐串联,可到底能否叫王老爷信服李小姐落水与王少爷失踪两件事间的关联,二人却都没有多少自信。
可却也不能不说。
常山挑着重点,将调查出的事一条一条与王老爷说了。
王老爷越听面色越沉,听到后来,已是胸口起伏不停,哆嗦着从一旁的王福贵手里接了两丸药丸吞了,这才呼吸顺畅些,小眼睛中泛起水光来。
他捶自己胸口,语不成句,声音发颤:“洹、洹儿,当日我便疑心,问他去了何处,却只是支吾不说……如今这宅子,也是洹儿极力要求盘下的,他说爱极这园子,我便也信了他,他、他——”
王福贵一溜烟的上来给王大善人抚着背,好歹叫将这一口气呼顺畅了。
“我儿糊涂!”
王老爷的悲痛是半点没有假的。
他虽与家中老妻算不得多恩爱,但对这个嫡出的儿子,却是真心的痛惜。心里还想,待自己将来两腿一蹬,他这打拼来的东西,还不是留给儿子的?
可你若要问,既然痛惜,如何外头还有一位夫人,又冒出两个那样大年纪的公子,叫家中爱子被下人偷喊一声三公子,好不尴尬,那里却有这样的痛惜法?
却不曾想,男人在外头置了宅子,叫外头人称宅子里那位一声夫人,可那里就真的同家中明媒正娶的正头太太平起平坐了?
外头夫人生的儿子,就胜过那拜过宗族,进过祠堂,给祖宗牌位磕过头上过香,写进族谱里头的正经少爷了?
小厮青松碎嘴嚼舌,同常山言道外头两位少爷说不得那日便要翻身,却不知他家老爷现下心中又悔又痛,甚至想着:哪怕当初带着去李大人家赴宴的不是嫡子,而是随便那一个外室子呢?也好过叫他的洹儿遭遇此难,便是拿两个儿子去换那一个,怕也是愿意的。
瞧着王老爷真情流露,常山忍不住动了动嘴,赵衔却拦在他前头开了口:
“往事难追,为今之计,怕也只有亲见一见那‘画中女鬼’,才好探个究竟了。”
他没叫常山将话说出口。
依赵衔对常山的了解,他觉得对方多半是要叫王老爷且慢哭丧,毕竟那王少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常山是断不会承认在他追查的案子里,胆敢有尸身不在他眼前过一遭,就自顾自死掉的死人的。
作为一个大理寺寺官,这无疑是一个好品质。
但在现在这般凶多吉少的情况下,赵衔认为此人还是不要开口,免得给王老爷带来什么不该有的期望的好。
常山也不知有没有领会赵衔真意,他将目光放在手中的画卷上,那红花梨木的画轴上贴着张黄纸,是出赵家前,赵衔不知从何处摸出来的,说是外出游历时一高人所赠,虽不知效用如何,但聊胜于无……
王老爷面露急切,“常大人,这……”
想到那女鬼,王老爷心里头到底还是慌得很。他觉得那位赵公子说的是个馊主意,可想来想去,抛开这馊主意,竟也没有旁的法子可以想。
到底儿子还是重要的,王老爷叫王福贵往前站了站,自己又尽量不动声色的往后退了几步,这才拿恳求的眼神去看常山。
心里还想着,早知如此,便不赶先前请来的那些个道士神婆出门了……
几双眼睛俱都钉在常山手上,这画自被他收起,一直像是一幅普通的画,没表现出半点异常,似是已安稳了。可常山心中却隐隐泛着些许不好的预感,直觉叫他立刻抛开手中之物,可旁的不提,光说要想完成此次的任务,画中之谜就非解不可。
他抿着唇,一手稳稳的脱住画卷,另一手揭下那张其貌不扬的符纸。
若要问这符纸灵不灵,常山此时会回答,是灵的。
在揭掉符纸的一瞬间,他便感到有阴冷之意顺着手掌盘绕上来,胸中躁动更胜。
而待他缓缓打开画卷,与先前的山水画,甚至与他曾见过的画中女子都不同,只见画面上墨黑一片,常山崩紧了臂膀,在画卷大敞那一刻,果断扬手将画整个朝无人处用力掷了出去。
与此同时,画中黑气骤然暴涨,赫然成了一扭曲的人形,那黑色人影扭动着黑烟缭绕的身躯,发出咿呀怪叫,只在四人中稍作犹疑,旋即猛地朝最近的常山扑将过去——
“破!”
一声清喝猛然破空,同时想起的还有一声清脆的撞击声。
黑影发出一声凄厉尖啸,整个身子忽地少了一小半,在众人未反应过来前散为阴冷的黑色雾气,瞬息便钻回了那落在地上的画卷中。
它突兀出现又突兀消失,一切只在倏尔间,竟似是梦境。
只一支嵌着精致造花的花簪,落在常山脚边地面上,提醒几人一切皆为真实。
众人抬眼一瞧,只见大堂入口处,正亭亭站了个豆蔻年纪的粉衫少女,柔柔朝他们露了个笑脸。

横刀和大哥离了乐坊又不知道跑哪里快活去了,不过他也不在意,塔兰并不在意器和器主是什么关系,他不会去使用他们,在自己看来那很别扭,对大哥他们也是。
一个人的时候塔兰总是喜欢发呆,望着街上来往的游人,坐在乐坊的窗框上吹奏自己制作的竹笛,竹笛的声音盖不过姑娘手下琵琶,他也不气索信合调衬了那琵琶与歌声。
游人驻足望向高台不见一位歌女,却只见年少白头的塔兰荡着腿吹着笛子,熟悉这乐坊的人都惋惜――这年纪轻轻就盲了目,哑了声。
冬日早已过去,小贩在街头叫卖着粗粮小食,姑娘们换上了新衣,在院子里比较着那家的公子哥送的礼物最为贵重,那个最合自己心意。
绿柳抽枝,压抑了一个冬天只埋汰在店里着实可惜,小姑娘扯着塔兰的衣服偏生要他伴着出去添置铅华胭脂,这一趟吧,自己的脸又要造罪了,不去呢,自己的耳朵要遭罪,定夺下来还是去了比较好。
说起来这女子的兴趣来的快,去的也快。前一秒还欢喜的拉着自己购置胭脂布匹,下一秒见那初春桃花,要自己为她折花,自己不肯,便不顾女子风度折下花枝恼怒地塞进了自己怀里,拉着姐妹们走远了,完全不顾自己是否还回得去乐坊。
自己在这人群中手里捧着枝桃花,难免有些奇怪,塔兰微微睁开闭着的眼,看着手上开了花的桃枝。
“你在干什么?”玉梢望着在人群中不动的塔兰,忍不住出了声。
玉梢又向人要了可以出入的符了,想趁着春色望望花,可惜的是她时间算早了,百花还没有开,今天她唯一见到的花,就是塔兰捧着的这支。
“哪些姑娘丢下你走远了,不去追吗?”玉梢看着姑娘们离开的方向,转头对上了塔兰满含笑意的眼,一蓝一金和那家养的波斯猫一样,也和店里的哪位娘娘一样,漂亮的打紧。
这人果然的不盲,对他的关心可是多余的,玉梢想到。
“你要回去了?”
玉梢有些扭捏,难得遇到一个见过的人,对方可能马上要回家去了,这一趟自己又得是一个人了。
想要一个人陪而已,这样的话无法对人说出口。
不知是不是被对方看透了心思还是什么,只见塔兰闭上眼侧头,用手点了点自己的头发示意玉梢,玉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发髻,摸下了一片桃花。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自己一直在看人群都没有留意过路边拿来的桃树,让别人提醒自己头上有东西,失态了。
玉梢的表情有些绷不住了,塔兰还是那幅笑眯眯的样子,活脱脱是一只猫,她再次伸手想要确认自己头上还有没有花瓣,手却被塔兰握住了,玉梢愣了神。
塔兰松开玉梢的手,挨近她,将落在她发间的花瓣取下,放入了自己刚刚被乐坊姑娘塞给的香囊里,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将开了桃花的桃枝稍加修理,当做簪子插入了玉梢的发间。
“这可有够傻的。”
待塔兰弄完,玉梢推开他。
“......美人桃花面,很漂亮――”
到底是人漂亮还是桃花美说不清楚,看吧这人果然不是个哑巴,说起话来油腔滑调。
“比起桃花我更喜欢,梅花。”
可惜这个天里见不到梅花了,梅花开都时候自己还在店里积灰。
玉梢摆手作势要把头上的花枝取下,在塔兰的注视下又放下了手,换得了塔兰又一个微笑。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除了笑就没有其他表情。
塔兰从腰间抽出笛子,握着笛尾,玉梢握住了另一头。
“接下来呢?”
塔兰不做答,只是用笛子牵引着玉梢,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虽然乐坊的师父们很少会关注这些,但入乡随俗,对人太过逾越就是冒犯了。
“你不回答我,我可要走了。”
塔兰松开手,玉梢握着笛子不知道该干什么。
【等我一下――】
塔兰张开,没有声音出来,玉梢还没有反应过来,塔兰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这个人要是就这样丢下自己,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一定把他送上天,她保证。
玉梢呆呆的站在原地不是,她走了几步,街旁的豆浆小贩招呼着她过去。
“姑娘在等人吧,来喝碗豆浆暖暖肚子吧,我家豆浆可是老字号了!”
玉梢摸了摸身上,钱袋没有带,不好意思的回到:“抱歉呀,我身上没有带钱呢。”
“没关系,算我请你的,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等着,怪可怜的。”
一个人等着嘛......对啊,自己一直在等着什么。
温热的豆浆不添任何佐料,一口下肚暖意便升到了心里,玉梢放下碗,坐在小贩摊位的椅子上,计算着塔兰离开了多久。
半个时辰了。
自己真傻,居然真的等了这么久。
“谢谢店家的豆浆,我想我等的人不会来了。”玉梢起身拍了拍裙子。
“要走了嘛?下次再来呀,你说着小伙子气不气人呀,让你一个大姑娘等了那么久!”小贩替玉梢打抱着不平,玉梢再次谢过店家,朝着徒然堂的方向走去。
“店家,如果他回来了,请告诉他,桃花也很好。”
自己出来太久了,该回去了,不过下一次,下一次见面一定要狠狠教训这个放自己鸽子的混小子。
玉梢摸着头上有些不精神了的桃花,晃动着手中塔兰留下的笛子。
卖豆浆的小贩歇了精神,塔兰回到了遇到玉梢的地方,他手里攥着一支做工细致的梅花头簪,不见玉梢,游人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