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我想去治病。"曲花花说。
"哦,好,那你走吧!"美男巫师冷酷的挥挥手,并不打算拦着,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找到自己重要的东西,比如赶紧吃顿饭。
曲花花试着深吸一口气,然后伸出手按住自己左边的胸口。那里传来富有节奏感又充满力量的跳动声,心脏是如此的健康,可是却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而曲花花对此也毫无感想。
“…保重。”抬起头朝美男巫师道别的曲花花发现自己的身后空无一人,美男巫师早就不见踪影。
真的是巫师啊……曲花花想,觉得应该佩服一下。
雨后的梅山格外清新,湿润的充满植物气息的空气钻进曲花花的鼻腔,附在他的皮肤上。曲花花这就抬起脚,深一步浅一步地往低谷处走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山脚处隐约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曲花花仔细看了一会儿,又听到了器械碰撞发出的叮咚声。但是距离太远了,他不能听清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于是曲花花默念了一遍“我现在很振奋!”后加快了脚步,朝着声音的地方赶去。
映入眼帘的是热闹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摊贩,曲花花从没见过这种热闹的景象,梅山总是很安静,就是一百只鸟同时唱歌也抵不过这种人来人往的气氛。
太过震撼甚至让曲花花完全没有留意身后早就消失不见的山路。
不过,很快他意识到了更严重的问题,这儿的人,操着一种难懂的语言,实在和自己的语言差别太大,曲花花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完全听不懂,不要提寻找名医了,甚至可能买不到一个馒头!
山下的世界好可怕…曲花花只觉得头大,但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判断,母亲以前讲过,日本是一个国家,国家又分成很多城市,也许是会有完全听不懂的方言。
这种时候,最好买一份地图,然后冷静下来吃点东西。曲花花冷静得思考着。
“这位小哥,瞧你白白净净的,怎么穿这么破烂的衣服啊,瞧瞧瞧瞧…连个鞋子也没有,你脚疼不疼啊?”路过的大婶无比担心,实在忍不住拉住这个站在街道中间半天没动的青年。
曲花花回头,以一种绝对的迷茫面对热心的大婶,怎么办,她在说什么。母亲说过就算是方言,也一定有迹可循,可眼下这种奇特的语言,硬生生是一点母语的痕迹也没有。
"呀…这怕不是个傻的吧……"大婶一下撒手了,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
怎么这种眼神…曲花花觉得奇怪,又想起母亲说过,微笑是重要的礼仪,于是曲花花扯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试探地说:"您好?"
也许是太久没有看到过这么秀气的小伙,大婶刚刚松开的手就又抓了回去:"哎呦,是外来人啊,这可真是…来来来…我啊,是茶馆的!"她腾出一只手,做出倒水,喝水的动作道:"茶馆,茶馆,喝水的,吃饭的!"
曲花花若有所思的看着笑的满脸褶的大婶,得出了她可能在要饭的结论。
"这…我身上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曲花花立刻开始摸腰包,但他哪里有什么钱,只掏出个雕刻挺精致的木头小雀,这是他的拿手绝活,没事会刻着玩:"这个…这个…可以卖钱…!"他也学着大婶,开始比划,指指小雀,指指大婶。
两个人一老一少,在街上互相比划,场面很是滑稽,曲花花一把把小雀塞进大婶的手里,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快速转身走掉。
大婶顿时一懵,也忘了继续比划,看着曲花花的背影,大婶一喜:"外来小哥好兴致…还送人家这种见面礼…"
曲花花逃也似地快速走开,也不忘左右看看人声鼎沸的街道,看起来像是祭典一样,连招牌上的字都连接很困难,那么这里,究竟是不是日本…?可梅山明明就在日本境内……
美男巫师漫不经心的那句"梅山的错吧"究竟是什么意思,梅山不是普通的山吗?
发生这种快速思考的情况,应该会紧张吧,曲花花默念"我很紧张!"
天色渐晚,曲花花从最热闹的时候,逛到了散场的时候,街边渐渐燃起了许多形状好看的灯笼,酒楼里也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聊天声。
再然后,形状好看的灯笼也渐渐消失了,只留下有些无措似的曲花花,和高悬空中的弯月。
入夜了…曲花花终于感到一丝凉意,不由打了个寒战。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并不是日本,而是别的什么地域,这下子可难办了,原本就从未谋世面的自己,一下还来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
怎么来的?曲花花回想,似乎也就只有,走下了山,走来的?徒步?徒步走到了别的地域?这下曲花花开始思考,他是不是应该脚痛了。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曲花花打了第二个喷嚏之后,他看到了视线可视范围内唯一一个有灯笼亮着的建筑。
门匾上有三个字符,曲花花看不懂,屋顶却突然传来一声惊呼:"霍!好一个拾破烂的!"
曲花花当然是听不明白的,但是既然路上就他一个,可也只能是对自己说的,于是他抬头,看到屋顶上垂下一双腿,不一会儿又冒出一个脑袋。
"你能看到我!"房顶上的人一下就感受到了视线,兴奋的爬了起来:"收破烂的,你能看到我!!"
无论怎么看,上面的人都很兴奋的样子,曲花花迫于外来人暂时宛如残障的压力,还是露出了礼貌性的微笑。
屋顶的人更高兴了,头顶的大草帽都掉了下来,隐约看到凌乱的后脑上扎着一个小小的辫子:"我眼神好,你长的真好看!哈哈哈哈,我的有缘人是个帅哥哈哈哈哈!"
曲花花静静地看着那人自言自语,清澈的声音句尾总是上扬,听起来还不错,只是不知道这人在笑什么,半夜这么大声没问题吗?
门匾上的三个大字被曲花花暗暗记下,但他并没有进去看看的意思,身无分文,还饥肠辘辘,他决定看看哪里的破楼还有空地…
治病的路好艰辛,曲花花觉得这种时候肯定要充满决心,于是他默念"我充满了决心!"开始寻找今晚的栖身之处。
反正全是npc,那我就直接发了吧(……
先扔白露,等20号再改分类……
虽然逛窑子,但是很清白!
————————
出得上方门,入得桃花坞,河心一叶扁舟徐徐来,船家立在后边板儿上,缓缓地摇那杆儿,小舟自桥洞下过了,瞅着岸上的卖花小郎,便递出几个大钱,掐一串花来,是要送与搭船的贵人去的。
下金陵五六日,一朝梦至姑苏城。
离了秦淮烟雨十六楼,便也是离了那轻纱软帐嫣红柳绿。时人言秦淮夜色霓虹,便如仙宫瑶池,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红灯笼金铃铛不及入夜便挂出来,香粉女郎们倚了画栏,黛眉细细挑,眼波粼粼飞,将胭脂在手掌心里头揉淡了,再轻轻拍到面上去。
又高高梳了发髻,簪金分心的钗子,纱造的绢花,嫌绢花不美的也有,便候着延河走的贩花人,挑着个竹编的大篓,赤脚踩着草鞋便来了,篓上盖着湿布巾子,布一掀,内里露出茉莉香串子来,花儿鲜才摘采下,保了湿气半点不败,还带着清凌凌的水珠子,三五一串的也有,串成手串的也有,还有用丝线掉着,做成个耳坠子。
不止楼里的姐儿争了来买,民人也有买的,小夫妻簪不起金银,那家男人就去买个花儿,捡着篓里那半开不闭的,给自家婆娘往木头簪子旁一插,女人脸上的笑影便止不住,却还嗔一句,没得为些个野花骨朵儿,就花得这个冤枉钱。
可到底还是高兴的,花儿一簪,不光满屋子生香,晚上还难得加一碗红肉,油盐糖俱搁足了,肉香花香在一处,用过了晚饭便要吹灯。
而这姑苏比金陵,便又另是一番风景。
水巷小桥,细舟绮罗,茉莉花也还是卖的,却更水更娇嫩,布衣纱裙的小娘子要得支花簪子,还未往发间比划,就已叫卖花的小郎夸得飞红了面,扭身跺一跺脚,把衣带子搅个不住。
船家将团花送到贵人手上,瞧岸上香软亭锦绣楼,还笑一回,压了声音上前凑趣,道:
“虽不比那头十里珠帘,夜里羊车出得门,十回里未必没有一回往此来。”
声音里透着股子神气,不敢明着说,怕叫人捉去砍脑袋,只朝天上一努嘴,便知道说的是那太祖皇帝,三宫六院都有,偏就贪楼里姐儿那个味儿,又是建十六楼,又是认妓生子,甚个事儿没干过,只不许人说。
那乘船的贵人是个白面的年轻公子,也不嫌小舟粗糙简陋,求的便是这般滋味,贴身的小厮且不叫在船上伺候着,另有自家的画舫,在后头远远跟着。披了袍子在前头立着,玉面银冠秋水暖,两袖空空只乘风,可不是雅事一桩。
接了船夫递来的茉莉花,嗅得满鼻香,便笑一笑,连着船资一道,给了一个小银角儿,船夫一过手便知心实足有三两重,笑得见牙不见眼,搓着手与那公子见礼,叫他有甚个只管吩咐,胸脯子拍得咚咚响,再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白面公子便叫他寻着岸边青石砖的台阶停了船,又给了一角碎银,令他也不需做旁的买卖,只在此处等候,这几日还要他的乌篷船。
放着镶金镶银的画舫不坐,非要乘个乌篷船。他既赏钱给的厚,船夫自不将这好买卖朝外推,就见那公子自个儿掀起袍角上了街,也不知往何处去,收了银子,船篷子里一趟,难得躲个闲,背地里还笑一声,真个怪人。
岸上人一路走走停停,大街小巷的铺子逛着,还买得一包豆糖,这也不是甚个值钱玩意儿,小本的生意,自家做得了,扎个小亭就在路边叫卖。
寻常富贵人家且嫌豆粉没有自家磨的细腻,等闲不拿正眼瞧,白面公子却停下买了,还叫多撒些豆子粉,卖糖的陈娘子见他好性,调笑一句莫不是买给家中小夫人,那公子却把手一摇,将油纸包的豆糖晃晃悠悠拎在手上,一转头,竟直接登了红云楼的门。
卖豆糖的陈娘子满脸的笑就变了个味儿,还道是哪家新婚燕尔要讨正头娘子的好,原不过是买给那红粉桃花瘴里的粉头的,却道也是,那个男郎不贪欢,天下乌鸦可不是一般黑,妓院对过且还开着贡院的门,那些个读圣贤书的,不也一径只捧着些个妓子,作些酸诗,写些酸句,便似天上有地下无了。
陈娘子心头那些子嘀咕略去不提,且说这红云楼,倚水而建,轻纱软帐,雕栏玉阁,锦绣辉煌,在这姑苏城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红粉香窟,便是比着金陵的醉仙轻烟翠柳,也不差什么。
楼里的姐儿半是官妓,半是私娼,大多自小便卖进去,叫假母请了诗书先生,又教琴棋书画,这般调教出的姑娘便极难得,等闲不叫人见,纱帐子后头露半面脸儿,花丛里头见一段掐细了的腰,绣花开富贵的屏风下一对金莲,便能叫一干子士子丢了魂,大把金子银子奉了去,再不吝惜。
白面公子进得红云楼的门,门口的鹦哥一声声的叫茶,门内的姐儿们瞧他生得俏,都很愿意凑到跟前,叫鸨母一把全拦了,腆着笑脸亲迎上去,将他引上小楼,掀了轻纱帐子请他进去。
底下有年岁短的小丫头便吃惊,挨着人嚼舌:“怎地转了性子,叫人进了月娘子的屋子。”
有呆的久些的姐儿便拿染了花汁儿的手指点她一回,道:“那里是转性子,不过是那郎君手头大方,听说又是个有身份的,月娘子待他青眼,一年也来不了三两回,给那头却送足了银子,那里还会拦着。”
口里说的月娘子,便是此地有盛名的诗妓,娇名唤惜月。都说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儿,哪想一夕间家里糟了祸,自家流落到这地界,鸨母爱她好颜色,字儿也识得诗文也做得,又会琴又会画,有意捧了她起来,精心调教两三年,捧出来做得个花魁娘子,时人都晓得月娘子花名绝艳,不叫她看上眼的年轻俊才,再入不得娘子的帐子。
入得这腌臜地,女孩儿便再不想着还能清白出去,见得多了酒后那些个丑态,倒也不羡慕寻常女儿家嫁娶,只羡慕这月娘子,只想自家有一日得了这风光,便也如意了,哄得恩客存下银钱,待年纪大了,未必不能自个儿梳起头来,另起一灶自做买卖。
再瞧一眼小楼上那金贵纱帐,又想上去那金玉公子翩翩好颜色,心里头艳羡过一回,也晓得左右与自家无关系,帕子一甩,自回内屋去了。
却说那公子入得纱帐,内室焚了香,却非浓香,若有还无,只淡淡。云锦屏长条案,不镶金银,只挂玉饰,还拿竹段扎得个小屏,隔出半扇琴房。
进得门,便有小婢垂首领在案前坐了,又有一婢上了茶食,金丝肉酥牡丹饼儿,却不上茶,因晓得茶必是要娘子亲点的,两个俱都懂得规矩,也不朝白面公子面前站,垂着头默不作声又退出去。
自屋内摆设到下人规矩,一应既清且雅,半点不似在这样地界,瞧着案上一块胭脂红绣连枝茶帕子,坐案首的客尚未出声,内里的珠玉帘子便淅沥叫一只玉手掀起来,人未至,声先到,便听一声笑,一个清亮女声传出来。
“赵公子金贵人,怎有空朝奴这里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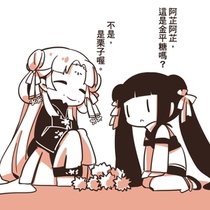



“玉指揽风风不住。茜纱窗昏。舟上摇波波不停,渡影重温。”玉梢拖长了尾调,唱着不知从哪听来的词句,仗着没人见得着自己,也就慢悠悠地晃过集市,找了家看上去就有些寒酸的茶馆。屋檐上滴着水珠,收起手上的油纸伞玉梢只听见雨滴声如同珍珠系数落地的声音,哗的一下全落在地面上。反弹起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圆点混杂着店面的倒影最终消失在骤雨之中。
将伞搁在桌边上,玉梢也不能指望店小二来问自己是不是要些茶点,自顾自的拿起已经凉了的茶壶往那白瓷青花的被子里倒。还未甄上半杯,那壶就空了。
玉梢也不在意,放下茶壶捧着没有温度的,甚至有些许凉意的杯子往肚里灌下一口茶。
寒意从口中一直线地路过背脊,浸满四肢,似是被埋入冰雪那般弥漫全身。
这天气,人来人往的谁都匆匆而过,又是下午时分,再过一个时辰恐怕是各家都要准备起晚饭来,店小二昏昏欲睡的,茶馆里清净得很,歌女早就已经回厢房歇着,为数不多的客人不是轻声细语地交谈诗词,就是独自坐在那和自己一样看人来人往。
“上元溪旁点荷烛,千盏承诺,怎奈雾锁红尘客。”玉梢没有再唱下去,雨声不歇,那几句词曲被淹没在雨滴和油纸伞之间不断的声响中。整个世界从那被漆红的门柱之间看去像是蒙了薄纱,行人在其中穿梭,用一把油纸伞挡开那料子匆匆前行。
怎奈雾锁红尘客,阴差阳错。
玉梢眯起眼睛,侧着头看那个姑娘。黑色的发梢滴着水,像是水晶的链子装饰着繁复清雅的发型,几片银杏样子的发卡也在闪闪发着亮,和树上长青的叶子那般泛着光,在雨水的打击中叮当作响。
她没有挡开那层薄雾,更没有匆匆而过,而是站在雨中等待那糖画师傅给她弄出个什么来。
可能是银杏。玉梢猜想着昏昏欲睡,思绪沉重地似乎是被什么软乎乎的被子压住了似得,无法挥去的像是被蜂蜜裹住了的粘稠感那般。
那姑娘转过身来了,手上拿着的是用糖浆画出的梅花,晶莹剔透,枝叶丰满,缀满了花苞。她也不急,慢悠悠地就走过来,玉梢一颤,对方似乎是看得见自己的样子,径直走来,也不避开人群,硬生生在伞花丛中劈开一条路。
那店小二听着有水溅开的声响便也醒过来,转头就看见那姑娘湿淋淋地坐在那。也是吓了一跳才想起来问问是不是要杯热茶。
两口热茶下肚,玉梢才尝出来这似乎是白茶。淡过头了,也亏得这店能营业到今天。
“你的主人呢?”
“无主。”玉梢答,手指抹了抹杯沿,看着里头的茶水泛起波澜,“名曰玉梢。”
“韩梅梅,道士。”
玉梢敲了敲桌面引来了那店员,梅梅配合地点上了一盆茶点,黄豆糕甜得恰到好处,咬一口再混着茶也算是一桩美事。
玉梢也不多说,捻起糕点往嘴里塞,她确实好事,但是又喜欢半途而废,毕竟活得太久,对新鲜事也只有一瞬间的兴趣了,多想想也毫无乐趣可言,也就成了今天这番有些麻木的样子。
“雨天还出来吗?”
“没人说过雨天不能出来。”油纸伞上的水珠已经形成了一摊水迹,缓慢地流向店外形成水迹,梅梅发丝上滴下来的水珠也一样在周围形成了一圈深色的印子,玉梢是担心这姑娘受凉,但是看着对方也丝毫都不在意的样子,便不去说些什么。
“你能看见我。”
“我能看见很多东西。”梅梅回答,撩起耳边垂下来的长发别到耳后,又给自己到了半杯茶水,“你呢,出来找什么。”
“这话可是暴露了你自己。”玉梢甩甩袖子,宽大的布料灌进风,这时倒也显得风流。
两人对坐对饮,也不是酒,但也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从古至今谈论的东西从文化礼节到食物茶点,衣着样式到风流雅事。
“真的变了很多。”和她所知道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自己心里所存在的那些稀松平常的东西已然成为了他人或唾弃或认为遥不可及的事物,就连那些平日里随处可见的住房今日也变为了古迹甚至不可寻的文字描述。
“朝代几经更变,你认识的东西已经不见了才是。”梅梅也无意嘲讽,只是实话实说,这些东西或许对于他人过于残酷,但是眼前这人倒是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甚至兴致勃勃的想要了解各式各样的事情,一点也配不上那种清冷的气场。
“你也不像是刚才那样子。”玉梢点了点自己的发簪,“松了。”
梅梅闻言去扶自己头上的那些装饰,银杏的发簪有些落下来了,似乎是被湿了的发髻压塌的,她用力地往里头插了插,露出一截小臂,歪着头,收着下巴,眼角微微朝上,俨然一副美人图的样子。若是自己那时的被文人见着怕不是要夸赞一番肤如凝脂乌发如瀑才是。
“你在等人吗。”
“是啊。”
玉梢没有说下去,只怕这人在等的,是已经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或者是已经回不来的人才是。
这世上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少,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少,至少就玉梢认识的人中,十有八九有着些不同常人的执着。
不过说来也是,自己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以类聚,要是自己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那也说有些奇怪的,徒然堂的客人也好,器物也罢,那些冥器也好,清净师也罢,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不如说没有这种愿望的人实则少数。
“记得保暖。”玉梢沉下思绪,撑着脑袋去看那店门外的景色,裙角被打湿,水塘被搅乱,时不时听见有人抱怨秋风萧瑟凉意入骨,也听闻远处似乎是飘来琴声。
“老人已经到了要睡觉的时辰了吗。”
“不如你们小辈,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不顾一切。年轻是好事。”
“长着一张少女的脸真能说得出口。”
互为独自一人的存在,伤痕累累,不知什么是人情世故更不了解毫无执着毫无牵挂的感受,只是增加着伤口,承受着周围人和自己的厌恶和视线。
血流不止痛苦万分,却依旧披着人皮长着人心混杂人群之中,孤独对于她们过于高贵,更多的,是无处安放的寂寥。
终于写完啦!!!
还是超过了3w字,捶地。
赵衔,辣鸡。
——————————————————
天方蒙蒙亮,更夫照旧执了梆子,大街小巷敲过一轮,这些时日,敲更也提心吊胆,盖因近日京中不太平,连连有人在夜色中失了踪迹,夜里巡街的,绕城打更的,连着那早起挑货出来卖的行脚商,都紧起皮来,再不往那人疏的地方去。
这些且同宅子里的大户人家无甚干系,五更天一过,就有大户人家的小厮丫鬟出来开得院门,坐在角门前候着挑豆花的行脚小贩来,饶一碗豆花就站着吃。
簪花巷子里王家在门檐上挂起白绸来,里头扎起棚子,买来白麻纸纱,家中老夫人灵前哭得昏过去,叫下人抬着请郎中来扎了两回金针。
王公子年纪轻轻便去了,虽算不得夭折,不必一口棺材随意葬了去,可以入王家祖坟了,但到底白发人送黑发人,举家上下哭个不住,连着下人也不敢伸头,衣裳换了素色,头上簪了白花,厨上都捡着素食来做,便是原无事的,也叫折腾得丧起了脸,为王公子真情实意的掉下几滴眼泪来。
王老爷置在外头的小妇不声不响,挑着这时候上了门,拉了两个成了人的儿子便哭起灵来,口口声声要自家儿子心疼命不好的弟弟,心里一味的得意,拿帕子掩了口,不叫笑意露出来,王夫人眼里冒火,恨不得提起扁担自将这小妇打出门去,那王老夫人却叫个小妇往地下一跪,在上首一口气儿没喘上,又扎得一回金针,嘴角歪斜,竟瘫了半边中了风。
王公子人没了,对上头报说是叫精怪害了去。大理寺将结果写进卷宗里,便算是了结了一桩事情,卷宗入了库,再没得人多问一声,原也不是甚要紧事情,只常山一个仍紧着眉头,存着几分挂心。
更夫在巷子口歇了脚,便提着铜锣绕去城南。路上遇着个年轻公子,锦衣玉带,沾晨带露,生得面白锦绣,见得更夫也露一丝笑脸,抬手作个揖,惊得麻布衣裳的黑瘦汉子不住往边上让,抚着心口还道:“折煞,折煞。”
定得一口气,又摇头晃脑叹一回贵人好涵养,自家能与这般人见礼,想想也得意起来,一时将同行失踪的祸事都忘了,脚下有劲,提溜着看家的玩意儿,意气十足的一路打更,向南面去了。
那年轻公子却转进小巷里,无人深巷砖墙湿润,红砖间爬着层苔藓,更夫却未瞧见,几块碎砖间胡乱夹着纸片,一截木料支棱出来,听见人声,就有细细声响自底下透出,凭空伸出一条美人玉臂,再往下,半身湿淋淋的落水美人便气若游丝从纸面里探出身子。
“救……救救奴……”
一声呼救细如蚊吟,手却颤颤巍巍伸到人面前了,梨花带雨,眉眼颤颤,好不可怜。
年轻公子却恍若不闻,连着伸到面前的柔荑,都像是没瞧见一般。他既不理会那泣血呼救,也不去拉美人的手,隔了一步站定了,打量几眼,慢条斯理掀了袍角屈下身来。
他拿帕子包了手,才去拎了那根红花梨木画轴,那画灵细细的哭,眼中仍是懵懂,却再与之前不相同,桃花翦水目中血光愈盛,自王家脱出后,她背了王三郎一条性命,再压不住通身戾气,抓了自她跟前过的男人取那一点精元阳气补足自身,这些天下来,又何止害了几条性命。
画灵探了爪儿勾得眼前人衣袍,本体叫他捏在手中,却不若平常,竟生不出反抗加害之意来。她也不知就从那里生出一股子亲切,毫无道理的便孺慕起来,原要将人拖下了水,现也不想了,只小心翼翼勾着这公子的衣袍,温温顺顺低垂了眉眼。
那年轻公子仍是慢条斯理的,将画儿卷起来,还轻弹一弹沾着的泥灰,末了,才看向那做了温顺模样的画灵。
“不过插了柳条,竟真得了树荫。”
他温声笑了一回,还伸手去理一理画灵沾了水湿濡的额发,又拿巾子替她拭了脸,收起画卷,还迈着不疾不徐地步子朝巷子外头走。
外头两个小厮远远跑了来,口里叫着少爷,攀附在那公子肩头的画灵先是目中露出血光,身子猛然绷紧了,叫年轻公子拿眼一瞧,便又软绵下来,不知怎地竟懂了他的心思,自消了自身行迹,把身一扭,还钻进画中去了。
年轻公子便抚了画轴,轻声浅笑,不知是同画灵说,还是同自己道:
“这几日你且饱腹没有?更夫行商,那里好滋味。也不必急,过得这阵子,我便离家带了你寻人去,一个不成,便再换一个,总能替你寻一个‘三郎’的。”又拍一拍画卷,温言温语,“在此之前,且与我去会一位故人罢。”
画卷便似是稚儿般挨着他,嗡嗡一震,再不动弹。
*
王公子的灵棚扎起来,后院的那处小院叫王夫人恨恨拿木条封起,再不愿看那伤心地。
王家上下乱了几日,竟还无人整理那院子,破窗且还破着,案台子地板砖上水已干了,留了大块的水渍,那白瓷瓶许是在混乱中叫人扫了一把,摔在地上碰个粉碎,无人往那屋子走,自然也无人收拾,满地的碎瓷片渣子,下脚且没有地方。
常山隔得几日来,给王家包了一封奠仪,站在小院门口张望一回,求了王福贵暂且拆下门上木条,要了那满地的瓷片碎渣子。
再三问王福贵可有遗漏,又亲眼将屋子全看一遍,不独看这间屋子,还将小院中旁的屋子也看一个来回,这才收了包袱,默不作声出了院子。
赵衔与他相约了今日一同上门来拜,上过了香,还吃得一口灵堂的豆腐宴,瞧见他拎得个油纸包,面上一奇,却不说甚么,常山也不同他多说,拎了一包碎瓷,辞了眼下泛青的王老爷的送,又往大理寺去。
他朝同僚借得了粘土膏子,将散了一地的碎瓷一片片对上口儿拼接起来,拼得最后几片,有个小吏往他跟前探了探头,说前头衙门方又接着一桩案子,瞧情形同您前头跑的王家有关的,常山瞧他一眼,那小吏生得细细长长,似竹竿般,晓得他与大学士沾亲的,弯了腰弓了身子在他面前讨好。
见常山瞧他,便堆个笑脸,凑近了做耳语状,道:
“还是那个王家,听说今儿又死了个婆子,死个下人倒也罢了,偏身上沾了一滩水,现下乱起来,都说是那精怪又回来搅风搅雨呢!”
常山手头一顿,隔了片刻,才回问了一句:“那死了的婆子,可是洒扫的余婆子?”
小吏伸手挠挠头,那里就记得个婆子的名儿了,瞧常山的模样,便一气点头,还故作神秘与常山道:“您瞧着,这里头会不会还有什么隐藏的案情?前头那王公子的案子,是不是暂且不结案,连着这新案……”
话音叫摆手打断了,常山止了他的话头,拿一把大钱给他,算得是个跑腿的辛苦费,却不叫他再说,前头他自个儿对这案子结的不那么满意,现时却又不知为何改了心意,“案子结了便是结了,没什么再深究的。”
他挥退了小吏,瞧着自己手上这最后几片碎瓷,沉着脸将之一一拼上了,可对着拼好的瓷瓶默然半晌,又伸手将之朝地上一砸,稀里哗啦又砸得粉碎,出门叫了小厮,将满地的碎瓷收拾了丢出去。
他自此再不提王家,也不提原还要去寻,现却已没了的余婆子,只把这桩事死死压住,便当从未有过。
可常山自己心里到底是忘不掉的。
小院里房房都在案上摆了个花瓶不假,可也只只落了一层灰,再没那一个里头是盛了水的。
他自王家拿来的那些个碎瓷,拼完整了,细径圆身的瓶儿也还是少了半边的脚,正摆着瞧不出不妥当,可但凡受一点儿摇晃,都必要翻倒下来。
常山叹一口气,只将眼一闭,再不去想着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