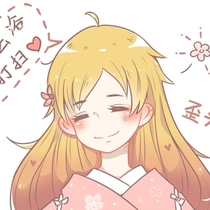最后的最后,经历了曲折的9天,诸位游客终于解开了福音镇的谜团,重新回到了“现实”。
恭喜各位,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假期呢。
企划六期已经结束,更多后续信息将在企划群内及微博公布,敬请关注。
※我写文太慢流水账还OOC结果被NPC打了.jpg
泳池派对似乎是每艘豪华游轮必备的玩乐手段之一。
纵然是第一次乘船,但电视剧他也没少看(被逼无奈),没想到自己有生以来居然也能体验到如此富有金钱气息的活动,真是……十分没有干劲。
说实话他只想回房。但房间隔音并不能完全阻断夜晚的欢歌,青年索性踏过地面上游移的彩光,在开放式酒吧的吧台旁坐下,随意点了一杯酒。
他仍然没有认全——甚至根本懒得认全甲板上的游客。不过特征突出的人,他大致有个印象,例如离他不远的白发青年与满面粲然的少女,总记得似乎名字也很拗口……梦什么十什么的……
静间蓝一秒放弃。
喝了一口酒,青年正准备发呆,又见那头惹眼的红发飘逸而过,走了几步坐在泳池旁,竟旁若无人地咬起了雪糕。静间一口酒噎在喉头,差点把自己呛个正着,又想起她之前连番电话轰炸,威逼他不准说出去,不免心下无奈,偷偷叹了口气。
谁知她居然察觉到了。
红发女性四下张望一番,咬着雪糕向他走来。静间心道不妙,这是要当场灭口吗?但青年还未来得及动弹,便被一脸郁郁的高桥九歌逼近。
“……Hey。”
Hey你个大头鬼啊。
静间不知她想做什么,只好点点头:“……晚上好。”
九歌笑了笑:“我是高桥九歌。请问您为什么一直看向我这边呢?”
鬼才想一直盯着你看啊。
静间蓝又忍住了。八年孽缘教会他有些话打死都不能说,除非他想被打死。他清了清嗓子,道:“没什么。如果给您带来任何不快的话,请容我道歉。”
于是她笑眯眯地指了指吧台:
“这倒没有。吃冰淇淋么?我请你。”
青年也不由舒了口气。
“谢谢,不必了。……我是静间。”
这一刻,像是某种隐秘的契约瞬间成立。
不过这种建立于“孽缘”之上的契约也很容易破裂。
听见九歌招呼深泽姐妹过来吃冰淇淋,静间不禁皱了皱眉。他捏住杯脚,观察着向自己走来的女孩——实琴和他对上视线,也攒起细眉,复又放松,朝九歌摇摇头:
“谢谢,不用了……”
九歌点点头,又开始感叹起来:
“哎呀,实琴和……唔,姐姐和妹妹一个活泼一个文静,真好呀,我也想要一个性格互补的姐姐……”
……嗯?
青年警觉地看向女性,但见她似乎全然没有察觉的迹象,又摇摇头,小声咕哝道:“……你得了吧。”
小女孩听闻夸奖,顿时睁大眼,慌忙点头。
“姐姐……美琴很好的!”
“哎呀,是吗是吗!”九歌也回以一笑,同时不动声色地踩了他一脚,疼得静间险些摔碎酒杯——高桥九歌可不管,无视了青年的眼神控诉,继续笑眯眯地说:“真羡慕你们俩啊!”
实琴则点点头,目光在两个成年人之间转了一圈,露出不解的神色。
静间总算缓过气来,佯作无事地笑了笑:
“……没什么。别在意。”
深泽实琴只好又点了点头。
小孩子的戒心也许并没有那么重。尽管防备他,但一遇上新的情况便会短暂忘却。
又或是——他所指出的细节其实没那么重要呢?
但无论怎样,猜测就仅是猜测,没有证据,没有实际检验的话,一切都是空谈。
那么,下一步……又应该怎么走?
暗自观察着人群外沿的实琴,青年细细摩挲着杯脚。
全然不觉自己已深陷其中。
而“国王游戏”似乎又是所有泳池派对的必备游戏之一。
静间蓝自然没有丝毫兴趣,但听人群中央的白发青年宣告“每个人都有几率被抽中”时,还是无奈地留在了原地。高桥九歌向来喜欢这类游戏,一溜烟便钻进了人群,留他一人坐在原地。静间叹了口气,喝光了剩下的酒,正准备偷偷回房时,忽然听见有人说:
下一位幸运的国王是——深泽实琴!
这句话留住了他。
随意游荡的彩光刹那集中于那细瘦身躯上。小女孩微垂头,有些迷茫地走上前去,环视众人后,犹疑地说:
“……那就请3号和27号……两人三脚绕泳池一圈吧?”
这个颇显稚嫩的“命令”逗得在场人发笑。
就连静间也忍不住笑了笑,他索性再要了一杯酒,坐回刚才的座位。一束白光停留她脚边,将她微白的脸蛋涂抹得更苍白。他又想起傍晚深泽实琴的回复,像一根鱼刺正巧卡在喉头,取不出、咽不下。
然而,与他的心情正相反,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欢笑,随即,追光灯离开了小女孩,她重新走入阴影中。
静间蓝也收回了视线。
很快,第二轮开始了。
静间本还在犹豫是否要回去,忽然瞥见身旁座位上的少年满面郁结。心下一动,青年抬手要来一杯冰淇淋,顺着吧台递了过去。不知为何,场内服务员又为少年端上一杯苹果汁。静间蓝正想笑,心说谁这么巧和他“撞了车”,便猛地察觉到一股目光,而这陌生的视线又与少年的回应搅在一起。
青年抬起头来,望见了不远处的“来源”——是一名青年,看上去与他年纪相仿(或许还要更年轻),打扮普通,样貌清秀却不算出众,唯独眼神很可怕,气势汹汹的像随时要冲上来干架。
静间一头雾水。记忆中根本毫无交集的人为何突然对他(静间还仔细确认了一番)产生如此强烈的敌意?可敌不动我不动,青年虽说满腹疑惑,也不愿上前探个究竟,听闻少年礼貌道谢,便点了点头:
“……常有的事。别在意。”
正在聊天的新同伴忽然就被拽去参加游戏,而且还是两次,换作谁都得郁闷。
这时,方才那名青年竟怒气冲冲地朝他走了过来。
“蓝原,这位是?”
姓“蓝原”的少年也被吓了一跳。
“不认识……气场感觉很像我的一个老师,只是感觉。”
静间心想干脆就顺势介绍自己——没想到甫一开口,那头便传来了“惊喜”:
下一位国王是姚柒玖!
追光灯随即将眼前的陌生青年从顶至踵淋了个遍。
姚……姚什么?似乎不是日文名,说起来他刚才和少年搭话的时候,日文腔调也有些奇怪。目送青年远去,静间蓝挠了挠头,又看少年再度沮丧,便拍了拍他的肩,继续刚才的话题:
“直觉真准,我的确是老师。”
少年顿时振作,惊奇地望向他。
“真的啊?那您是教什么的呢?”
“这学期教的是……计划数理学应用特论。不是什么有趣的课。”当然,学生做发表时的苦痛神情他也都看在眼里。
蓝原差点呛了一口苹果汁:“这……您是大学老师啊?”
“是啊,”静间笑了笑,“怎么了?”
“没……没什么,”少年小小地刨了一口冰淇淋,“我也快要上大学了。”
高中生啊?那还真年轻。静间忍不住又笑了。
“加油啊。”
少年不知为何有些诧异,扶了扶眼镜:“谢……谢谢。”
当然,至于那位半途被请去当了国王的姚姓青年,静间蓝到派对结束时也没能和他再说上一句话。
什么都不会,写到哭泣。
1.
“它”还在附近来回走动。
而十几个闯入者躲在灌木丛后,屏住呼吸以防引起“它”的注意。
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说得出那是什么。“它”像是几种生物被剪刀剪开又被胶水胡乱黏在一起,长得丑陋不堪。“它”仿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悠闲地踱在这篇草地上,脚下的草窸窣作响。
矢崎晴树扭头看了看同行的人,幸好没有任何人受伤。
而“它”,矢崎想,又是怎么在这个已经没有饲养员,没有游客,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迹象地方存活下来的呢?
似乎是因为什么都没发现,“它”又转身慢慢地走远了。
今泉慎司低声说:“这还真是……惊险呢……”
而高桥九歌则正在查看拍下的照片,“如果这照片传出去的话……”
矢崎晴树侧身瞄了一眼高桥拍下的照片——没有错。“它”有着描述不出的古怪模样,一切似乎都暗示着这不可能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产物,令人脊背发凉。
矢崎突然想到他们钻进来的铁丝网的洞——铁丝网向内弯曲,怎么看都是在他们之前有人来过这里。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打开铁丝网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现在在哪里?
之前游览车上的抓痕又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是“它”,还是另外的东西?如果不是“它”,这个地方到底还有多少个“这种东西”?
这个岛上处处透露着古怪,看似普通的缆车站里有塞满尸体的房间,看似普通的动物园却有这种令人恐惧的陌生物种。其实最初矢崎与其他人一起在海岸边醒来时,他虽然并不乐观,但也不算慌张——没有人失踪,并且岛上看起来也能找到能吃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活下去等待救援罢了。
但现在看来,这个岛有些过于危险了。
今天相苏町没有和矢崎同行,在出发之前矢崎听说相苏一行人要去公寓调查。
公寓那种地方应该不会有这种危险吧,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矢崎想。
2.
下午一行人继续去岛上的动物园调查。说来有些可笑,在经历了上午那样危险的状况后,他们竟然还会愿意回到那个地方。
今泉慎司不再和他们一起探索,取而代之的是桃泽诗织的弟弟桃泽领。矢崎在很久以前就见过领了——那是上船的第一天中午,那时候桃泽诗织不舒服在屋子里休息,领一个人出来买了两人的午饭。
而这次似乎是矢崎第一次和桃泽姐弟两个人同时一起接触。
矢崎以前也见过双胞胎姐弟,他们是矢崎高二时的同班同学。那两个人虽说是双胞胎姐弟,长相却不那么相似,每天像哥们儿一样吵架和好再吵架再和好,弄得整个班里鸡犬不宁。但桃泽诗织和桃泽领这对双胞胎的关系却好得过分了,这让独生子矢崎有些羡慕。
在探索鹿区时,桃泽诗织似乎被纪念品商店的曲奇饼干勾起了兴致。她拿起一罐饼干来回看,饼干罐上是小鹿抱着胡萝卜的图案,十分可爱。
鹿吃胡萝卜吗?
诗织打开了罐子,里面飘出来了很香的气味。
矢崎看着盯着曲奇出神的诗织:“诗织小姐很喜欢鹿吗?”
诗织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她的领:“比起喜欢鹿……弟弟喜欢的东西我都会喜欢吧?”
这时风城七海也走了过来,开口问:“所以是领君喜欢鹿吗?”
如果是弟弟喜欢鹿的话,姐姐想买给他也是正常的吧。矢崎晴树看着桃泽领,但领突然看了诗织一眼,说出了让矢崎十分惊讶的话。
“领也一样!姐姐喜欢的东西领都会喜欢的!”
诗织满足地眯起眼睛笑了。
“乖孩子——”她摸了摸领的头,领也抬起头看着姐姐心满意足地微笑。
这是让矢崎晴树羡慕的其中一件事。
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在爬行动物的区域搜索时,领在进入鳄鱼展馆的一瞬间眼睛突然亮了。他对着玻璃柜笑了笑,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那时的矢崎正回头看同行的人,他在一瞬间捕捉到了领的表情,顺着视线看过去,发现领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的是玻璃柜里展出的小鳄鱼标本。
果然还是小孩子嘛。矢崎想。但当他扭头再看向领时,领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面无表情了。
那种喜欢和憧憬的表情只停留了一瞬间。
为什么?
矢崎晴树有些疑惑地看着领,而诗织这时候笑着开口了:“看来领确实是太累了。”
“领,要休息一会儿吗?”
矢崎弯下腰凑近桃泽领。而领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不用了,一起继续吧。”
矢崎晴树皱了皱眉头——领似乎看起来真的有些疲倦。“如果累了,”他说,“要说出来哦。”
桃泽领这次没有再犹豫。
他说:“并没有啦,走吧。”
但是他的视线并没有投向矢崎晴树。他侧过头看着桃泽诗织,而此时的桃泽诗织满意地笑了。
“是个乖孩子呢。”
当他们走到爬行动物区的纪念品商店时,矢崎再次看到了与展馆里同样品种的小鳄鱼挂件。他从货架上拿了两个后,朝桃泽姐弟走了过去。
“走这么久辛苦了。”矢崎说,“看这个挂件很可爱,当做礼物送给你们吧?”
桃泽领看着挂件,又看了看诗织,没有说话。
“一人一个哦,辛苦了~”
诗织伸手拿走了两个挂件,然后递给了领一个。“谢谢。”
领拿着小鳄鱼,也跟着姐姐道谢。
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矢崎晴树想。
然而对于他们似乎不像普通姐弟关系的事情,矢崎晴树并没有注意到。
3.
一行人疯狂向前狂奔了很久,终于摆脱了追赶他们的怪物。
这是他们在动物园里见到的第二只活着的生物。比起上午遇到的“它”,现在这个追着他们跑了很久的凶猛生物长得正常多了——虽然只是对比之下。这只生物像是鳄鱼与狮子的杂交产物,有着两种动物的特征,长相怪异无比。
矢崎当然听说过动物杂交,但他也听说过生殖隔离。把鳄鱼和狮子杂交在一起,是现代科技可以实现的事吗?
桃泽姐弟看起来也有些累了。大家都累了。这天他们见到了太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活物,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上午的“它”和这个鳄狮杂交出来的生物虽然不同,但“它们”却都不像是自然产生的动物,似乎有人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
矢崎晴树离开动物园的时候往回看了一眼。动物园里依然萧瑟和平静,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像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真的能找到离开这个岛的办法吗?”
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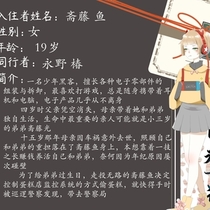
(字数:3153)
我钟爱被聚光灯照射的感觉。
不是通常释义中的那种笼罩舞台的光柱,而是更加宽泛灵活的,投诸我身上的人们的视线。
用阿夜的话来讲,大概我从出生起就已经是这种性格了。不被好好看着就没办法活下去,得不到足够关注就会深感寂寞,像是被目光所滋养的光合作物,自由自在地汲取附着皮肤的热量。即便身处全员都是陌生人的环境,也非得立刻干出点出挑的事情吸引注意力不可。
出生时据说是离奇地不哭不吵,使得产床前的医护人员大为紧张,连我的母亲都犹疑我是不是生而携带什么气短体虚的毛病,因此,当年尚无自觉的我,已然在人生的第一场亮相中攫取了胜利,不仅率先获准迎接光明,赢得贵重的兄长称号,未来的很长一段日子内也独享了特别的看护待遇。
家人总是忧虑于我其实毫无问题的心肺,生怕这个麻烦小鬼悄无声息倒在哪里停止呼吸。但等到我长大些许,几乎在学会说话的同时自学成才了如何歌唱,在勉强能摇摇晃晃行走不久就顿悟了该怎样跟随音乐摆动身体后,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关注顺其自然发酵成了别的果实——
卓有天赋的童星,活泼好动又表演欲旺盛的男孩,邻里同龄人公认的小首领。
在成年人眼中大抵是如此这般的印象吧。
演艺方面也许颇具灵性,但倒也远远不及真正的天才。唯一值得惊讶的,怕只有永远充沛过头的精力,活像一节空气充能的电池,白天黑夜轮轴转也不显乏。稍微疏忽就会立马消失在视线死角,但隔不多久又自己出现,主动制造惊天彻地的大动静——当然,是以孩子的评判标准,最严重也不过是在爸爸的鞋里丢了二踢脚——被抓住训斥却不懊恼,反而露出一副竟没被发现的遗憾表情。
那之后,岁月平稳流逝,我终于到了能独自观览文艺作品的年纪。周边的花鸟鱼虫亦终于免于遭殃。
吵闹的孩子会伴随成长而渐渐安静,而后在初中的某一天,蓦然醒悟自己的本性,因此而择取合适的人生道路,也是理所应当之事吧。
——请诸位将目光投向我吧。热切,冷漠或者憎恶,怎样的关注都好,务必要尽用力地看着我啊。
——但是,好像啊……光是被“看”着也还不够呢。
那是暑假百无聊赖的午后,齿间残余的布丁吮起来尚有牛奶的香甜。
我同天花板上缓慢旋转的电风扇,叶片吸附的苍蝇面面相觑,思考着它恶心的复眼映照出了我的多少面投影。
——只是被看着就可以吗?
伴随着耳畔轰鸣的摇滚,与夏日末尾粘腻地庸附肌肤的热浪,我呆呆地盯着唯一的观众胡思乱想。没有丝毫前兆的,骤然打了个冷战,浑身流过了前所未有的警醒与清凉。
——单单是映入瞳孔内侧,留下一瞬的影像,又有什么值得窃喜。连虫豸都能轻而易举做到这件事。
内心鼓噪的渴望自那经年累月凿破的小口喷涌而出。忽然,我意识到了,我无时无刻不在迫切妄想,想要收入怀中而又无法诉诸言语的东西,它的正体究竟是什么。
稍纵即逝的瞥视只会培酿愈渐激烈的怅然不满,若是屡屡重复被重视而后又被忽视的恶劣循环,我大约迟早会抓狂发疯。我需要的是舞台,是聚焦头顶的光线,是能够细致地刻画我的轮廓,而后竟然还能记忆它,理解它的目光的群落。
仅仅只抢占视线是不够的。我要尽可能的,在我能够拥有这些观众的短暂时间内,满满地占据他们的感官。用我的容貌,我的姿态,我的表演,我的声音,我所书写的文字和我创造的这一小段历史,填满他们所有的空缺。哪怕只是转瞬须臾也好,我希望他们能够只想到我,只拥有我——就像是在那段共处的时间之内只拥有他们的我自己一样。
我和我的观众,我们将对彼此誓约忠诚,签订矢志不渝脱手即焚的共存契约。
扮演其他角色,借助精心编造或加工的故事来获得情感回应,我姑且也曾尝试过,但很遗憾,因他人的经历而引发的共鸣,注定只归属角色本身,并不能让我产生任何成就感。演员这一大有前途的职业不幸PASS。
作家,就表达自我,寻求他人的理解而言是个不错的途径,年少轻狂的男孩自然也提笔试过。可每每落笔纸上,晕染墨迹的无暇苍白,连篇编织的蝇头文字,明明质地软韧,却能轻而易举予人刀尖般锋利危险的印象……那就像是手执尖刀,将自己慢而坚决地剖开示众,裸露出深红色的体腔,还要用漏气的喉管艰难叫卖,顾盼寻找愿意为听清这颗心脏的浊音而停留的看官。
我不禁质问自己,真的能忍受从此一生,都浸泡在漫长无期的自我凌迟之中么。
——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
我可是个毫无疑问的利己主义者。不如说,如果不是非得找寻到舒服的生存方式,令自己能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自在存活,我本来也没必要钻牛角尖到这种地步。
那么,书写自己,同时演出自己又如何呢?不必驭使作家那样冷酷直白的笔法,将自己货真价实切裂,五脏六腑示于人前,我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假装敷衍了事,把真正尖锐的尽皆藏在诙谐调侃的浮华下面,拿讽刺作外衣,玩笑当伪饰,凑一曲迷乱晦涩的爵士小调。
不愿了解的自会闭耳塞听,而甘愿随我往地狱一行的,便会敏锐觉察那弦外之音,破除迷雾,上前拉住我的手,与我携手坠落穹宇。
相当简单随性的,怀揣着中二离奇的憧憬,与超越年龄的成熟冷静,我作出了以我的整段人生为筹码的决定。
契机仅仅是一只偶然停驻眼前的黑色果蝇。
意识到自己的性向与众不同,和决定前进的道路,差不多是前后发生的事。嘛,考虑到再往外拓展就难以预估这场自我剖析的时间,此事就暂且略过不表。总而言之,初三那年我向家里正式出柜,并在隔日分文不取地离家出走。或许是出于自家儿子和不靠谱哥哥的了解,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弟弟,谁也没有试图寻找我,当然也没有报警。而我就恍如无事发生般照旧与家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甚至在找到打工后开始按时定量地邮寄生活费。
……
……据说人在濒死之际总不自觉地回忆往昔,眼前也会迷幻地流过人生五光十色的缩影。
万籁俱寂中独独染着鲜活色彩的我们,究竟是被侥幸漏过的幸运儿,还是不自知的受难者呢?
我眯着眼直面福音镇明灿的清晨,阳光笼盖的大地清幽沉静,气候既不过分炎热,又有些恰到好处的煦暖怡人,本应是郊游的绝好时机。然而,纵览四面八方,除去这间旅社,哪里都没有活物存在的迹象。
一夜间,我们这些本素不相识的旅客,被空落落地遗忘在了大地上。
——啊啊,多么旷大的舞台啊。我情不自禁心生感慨,难得担当观众,挑剔地检审着斧凿的痕迹,却不得不承认,这场浩大的失踪呈现的效果既突兀又自然。突兀当然是指时机,自然则是对遗留在面前的,仿佛只是戛然而止的日常生活般的布景的称赞。
创造出这一不可思议的布景的家伙,究竟是在期待怎样的演出。
简直像是提前于末日而降临的审判。无形的洪水淹没万物,空气的墙扉拔地而起。自以为安全的羔羊便在静默中迎接注定的消亡。
随口拼凑着消极的预言,顺便构思新作歌词,我站在门前考虑今日的行程。视野的角落,仍板正地穿着制服的森山雅人慢慢地走过,警帽硬挺的边缘切出了日光的金线,发色与眸色被动地呈现出有别于常态的柔和。或许是被这种晨时限定的亲切蛊惑,我思忖片刻,露出笑容跟了上去,同他打了招呼。
坦白讲,实在有些在意警察先生早先的某些说辞,若有机会,果然还是想与他同行,看看能不能试探出更详尽的线索……要么,单纯就聊聊天打发时间也不错。
这位先生温和而礼节周全地回应了邀请,惯常装饰在脸上的笑容可称滴水不漏。
聊了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夹杂插科打诨与顾左右而言他,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们对所谓超自然的事物绝不陌生,那件讳莫如深的案件也隐情复杂。不知道要混熟到什么程度,或者……事态危急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呢。
穷追猛打会引人厌恶,但要我就此放弃也不可能。揭开一角的潘多拉魔盒,可没有办法简简单单重新盖上。
集结探索队伍后,兴致勃勃又心怀忐忑的住客们踏上了第一回的短途冒险。
若是明日仍找不到穿过竹林的归途,要再羁旅一夜,就继续把我这延长的“走马灯”讲下去好了。反正,值得一说的人物还有很多不是吗。
自后方观望着这些陌生的背影,以及警察先生永远如松柏般挺拔的脊梁,我像是忽然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明明前途艰险却不由自主翘起嘴角。
盛大空旷的新舞台啊,得有多少演员才能组成一个首尾俱全的故事。
——————————
来不及写完了只让警察先生出现了一点点!冒犯了的话抱歉!
明天大概是鱼王传奇(xx



这是来自一位渺小的胆怯者,最初和最后的妄念。
明明有人在自己面前以如此凄惨的方式死去,梅宫赤绘更恐惧的依然是与人打交道这种好似稀松平常的事情。
真是奇怪,他能茫然地穿过满是血迹的可疑房间,却依然没有办法与他人正常的沟通,就算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勇气与某人搭话,也没有什么办法将这份勇气持续下去。
九天的福音镇被困事件给他留下的只有挥之不去的空虚,即使侥幸在事件中得以生还,那种因为和花海的交流而逐渐缓解的孤独感还是卷土重来般地囫囵攫住了他。
回到那个牢笼般的家里之后,总感觉有什么之前无法察觉到的事情改变了。
比如他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做的饭并不好吃。
第一次感觉到烧制瓷器也稍微有些无聊。
第一次感觉屏幕里的番剧也毫无吸引力。
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可悲。
曾经的好友花海也有更重要的事,也有更重要的人,虽然被告知可以随时去找他们玩,但是……
他没有办法踏出迈向那里的重要一步。
够了吧,已经够了吧,再盲目靠近的话,会被讨厌的。
不知分寸的家伙无论在哪种场合下都十分不讨人喜欢。
那说的正是自己。
他记得那个叫做三日月十六夜的孩子挺喜欢撞门,明明受了伤却还要坚持着不影响同伴的探索。之后他也撞了一次门,麻木的钝痛有种几乎令人着迷的危险魅力,使他这样的人也能产生一点点可悲的,被需要的错觉。
“哪怕有那么一刻,我有帮得上大家的忙就好了。”
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也是这么想的吗?
但是现在想起那些事情早已毫无意义,从福音镇逃出后,三日月十六夜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无论他如何寻找都不见一点踪迹。
应该是人格魅力几乎为零的自己再次被讨厌了的缘故吧,梅宫赤绘思索了半天,最后茫然之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以他还是不能再靠近任何人了,最后的最后,他大概都会是那个被抛下的存在。
因此,面对花海的邀请,他第一次选择了拒绝。
“我需要一点时间调养一下。”当时用的是这么一个蹩脚的理由。他的确也该调养一下,好好休整,仔细反思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人际关系的无常,即使是现在,他依然总也没办法窥见端倪。
但是,除了那刚刚有所起色就全部倒退回去的人际关系,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在等待着这个名为梅宫赤绘的青年。
虽然同他一起历经噩梦的人一个也看不到了,但是噩梦的碎片却紧紧依附在记忆里,散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
就像他拿起锅铲,眼前便会闪过那个哪里都找不到了的孩子对着他自己都不抱希望的料理给出好评的样子。
他打开厕所的门,伴着特殊气味的十六连打冲水键的响声就会立即充斥脑海。
拆开手臂上绷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看到那个与周围多数割伤不同的,撞门时留下的擦伤,就会想起为他温柔地包扎痛处的人已经成为一滩无法辨认的残破碎块,那个促使他产生撞门想法的人已消失无踪。
本以为已经麻木的心再度抽痛起来,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在以某种令人绝望的方式逼迫他回想起那个地狱般的九天。
虽然这种情况下找朋友倾诉是最好的缓解方法,但是这方法显然并不适用于身为话题杀手的社交恐惧青年。
于是赤绘侧着身子蜷在地上板强迫自己放空思想,既然无法将那段记忆选择性遗忘,那就干脆什么也不想了吧。
可是真的什么也不想又谈何容易,刚刚闭上眼睛,幕后黑手凄惨的死状和七彩的假发就成了新的噩梦。
这段浑浑噩噩时光的终结者是梅宫赤绘的妹妹依麻里。
在知晓自己的哥哥已经连续几天只靠冰箱里少得可怜的水果生活之后,依麻里毫不犹豫地翘了课,以一种侵略性十足的姿态把赤绘从地上拉起来按到餐桌边,气势汹汹地拿起勺子……
“你总是这样,依麻里可是很担心的!”
超市便当的味道立刻深入咽喉。
在咳嗽着吃完一份廉价便当并平静下来之后,赤绘开始磕磕绊绊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稍微……也交到了朋友,虽然后来找不到了。”
“我被困在那个地方……有人死掉,有人失踪……”
“那你找不到的那个家伙,说不定已经死了哦……”
依麻里没想到的是,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能激起赤绘如此大的反应。
“没有,我逃出来的时候,还能看见她……之后就找不到了。”
“没有。”
“她没有死。”
“只是因为我太讨厌,所以离开了。”
“……才不是……”
那张总是写满茫然的脸扭曲得不成样子,依麻里惊讶地看见那双本以为不会再流露出其他复杂神色的空洞眼睛里将要满溢而出的泪水。
“……我只是被讨厌了而已。”
承认自己是因为不讨喜而被讨厌,比承认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忽然死亡,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到简单的多。
依麻里忽然明白了什么。
“什么嘛,果然是你,到这种时候还要逃避……”
梅宫赤绘没有回答他的妹妹,自顾自地深呼吸着,等待情绪平复。
梅宫依麻里摇摇头,感叹了一声“又是这样”就出了门。
赤绘躺在地板上,绞尽脑汁思考了半天,才终于确认自己没有一个叫做依麻里的妹妹。
他叹了口气从地上爬起来,明天还要工作,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万幸发达的互联网能帮他像个普通人那样获取订单。
现在的他看不见任何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他们都是没必要接触的,都是不存在的。
已经不会再祈求获得到什么了,已经不会再希望拥有什么了,现在的梅宫赤绘不能回想过去,也无法承受现在,不敢得到也不想失去,只是个迷失在层层恐惧中的胆怯者而已。


1.
矢崎晴树自上船开始就十分兴奋。
他似乎是缺乏了晕船的那一条神经,从陆地到水面上后没有一丁点的不良反应。
然而同行的相苏町似乎就无法享受在船上的第一个清晨了——她感到有些头晕,短暂地在室外待了一会儿便又回房间了,留下矢崎一个人继续没什么意义地消耗着精力。
天气真的很好。
矢崎站在栏杆旁,面朝大海深吸了一口气。这里与城市很不同,能让总是静不下来的矢崎晴树放空大脑,什么都不做地发很久的呆。
这时矢崎听到背后传来小女孩的声音。
“……有没有……好像……眼熟?”
“……哪边?”
“……看错……”
矢崎在离得很远的甲板另一边,他转头看向声音来源,出乎他意料地——那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而她们正指着大海的远处低声聊天,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她们自顾自地说话,似乎并不想认识陌生人,也不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发现。其中一个女孩摇了摇头以后,她们便转身想要离开甲板。
这时广播响了。广播与矢崎上船前看的行程安排并无差异,但却引起了那对双胞胎姐妹的注意。矢崎晴树看她们似乎有些犹豫,便朝甲板的另一边走了过去。
“安乐岛……”
其中一个小女孩重复了一遍今天的目的地海域,欲言又止地看着她的双胞胎姐妹。
甲板上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对姐妹——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今日的风景和行程,而她们犹豫的态度在这艘游轮上过于格格不入。一位穿着有些正式的男性想了想,开口道:“安乐岛怎么了么?”
对安乐岛表达出了怪异的态度的小女孩摇了摇头,“不……只是觉得似乎在哪里听过。”
而另一个看起来稍微有些强势的女孩回应道:“叔叔是不认识的人所以不能告诉叔叔哦。”
矢崎晴树突然觉得强势的女孩反倒在隐瞒些什么了。安乐岛这个名字矢崎从制定旅游计划开始就听过无数遍,只知道是个风景不错的地方,也并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可在意的,但听这个女孩的话,她莫非是以前就了解这个地方?
于是矢崎蹲下,对强势的女孩说:“那告诉哥哥好不好呢?”
“可是哥哥我也不认识啊?”
矢崎愣了一下,然后尴尬的笑了。“那我们可以先交个朋友喔!”他揉了揉鼻子,“毕竟接下来大家都要一起玩的,我叫矢崎晴树,你呢?”
“那就是晴树哥哥了!”强势的女孩回答,“美琴就是美琴哦!”
而在此同时,和别人聊天的另一个小女孩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深泽实琴……”
深泽姐妹很快与大家热烈地聊了起来。矢崎有些意外——十分钟前矢崎还觉得她们没有与别人交流的意愿,甚至似乎虽然和大家在一艘船上,却不在同一个世界似的,现在却只是两个普通的小女孩。
“哈哈哈,我乱想什么呢。”矢崎摸了摸头,自言自语道。
那她们的父母又在哪呢?他突然想,她们的父母就放心让两个这么小的女孩子在船上到处跑吗?
这时候他看到了回到甲板的相苏町。相苏似乎还是有些没有精神,但比早上见面时好很多了。他问相苏:“休息好了吗?要跟大家一起吃饭吗?”
“头已经不痛了。”
他招了招手,示意对方来一起聊天。大约是因为感受到了两个女孩毫不胆怯的和大家对话的态度,矢崎又把心放了回去。
大概美琴和实琴的父母真的很放心吧。他想。
2.
矢崎晴树一个人百无聊赖到处晃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刚认识的十羽漪良纺。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他却十分想和十羽漪聊一聊。十羽漪虽然看长相大约是自己的同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带着一种矢崎在同龄人身上从未见过的特别的气质。
也许正是这种气质在吸引着矢崎。
他走到十羽漪的房间门口,敲了敲门。他敲完门才突然想起来十羽漪之前离开甲板的时候说要回去睡觉……矢崎立刻在房间门口不知所措了起来。
“是谁……啊,原来是你啊。”
对方衣服不太整齐,似乎是刚从床上起来。矢崎更加不好意思了,他有些面带愧疚地说:“如果你打算睡一会,我就不打扰……”
“没关系哦,如果因为无聊的睡觉错失了矢崎先生,我会很失落的。”
十羽漪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然后就自顾自地走回了房间里。矢崎晴树本想离开的脚步也停在原地,他有些慌慌张张地跟了进去。
真的很不一样。矢崎晴树想。又或者十羽漪先生只是长相年轻,年纪却不小了吗?
所以矢崎先问了对方的年龄。
十羽漪坐在床边,带着悠闲的笑容说:“不知道晴树今年多大了,我20岁哦。”
没想到比自己还小一岁。
矢崎晴树的心情莫名其妙的放松了下来。十羽漪良纺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得十足不羁,像是个看透一切的人,但矢崎晴树却觉得同一个年龄的人会有什么区别呢?
“那十羽漪还在读书吗?我现在还在上大学……”
“我早就不是学生了。”十羽漪耸耸肩,“上学那么无聊我待不住的。”
果然。
矢崎晴树很喜欢现在这种沉浸于学习的象牙塔生活,但这并不代表他很满足。他想要快点毕业,想要找一份工作,即使朋友都在说千篇一律的生活枯燥无比。
他脱口而出道:“我也好想毕业进入社会喔——”
十羽漪的表情有了一丝轻微的变化。他的表情看起来仍然悠闲,却又带了一丝细微的阴沉,“是啊,社会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啊……”
矢崎愣住了,看着十羽漪自顾自地说:“社会里面那些自以为带着面具握着权杖的人最终也只会沦为别人的工具……看他们一步步堕落真的很有意思。”
他朝矢崎晴树笑了笑,那是和矢崎进门时看到的不同的笑容。
“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懂你说的……”矢崎摸了摸头,“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开心一点喔,毕竟即使在社会里也会有很多不像你说的那种……大概吧。”
矢崎觉得坐在自己对面的人似乎和自己很不同,但似乎自己又能触碰到对方的想法。
“各位乘客你们好,”广播突兀地响了起来,“我们的派对即将开始,请大家……”
矢崎站了起来,“那,我就不打扰了……晚上见!”
“晚上见。”
矢崎晴树走出十羽漪的房间,到了甲板上的时候,天已经几乎全黑了。广播里放着有重低音和强鼓点的,能刺激人的精神的音乐。
人们聚集在泳池或吧台旁边,三三两两的聊着天。矢崎晴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朝人群跑了过去。
派对开始了。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