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龙息企划仅在终章进行一次结局选择的投票,一人一票制。
2.终章结束后,结算各阵营所有章节的投稿总数(以E站数量为准),投稿最多的阵营将影响后日谈结局的内容。
微博账号:龙息企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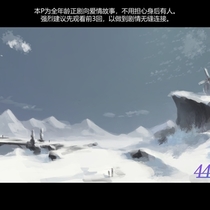
(擅自摸了互动,如果ooc那一定是我的机会,感谢茶8老师给我一个摸北欧老乡互动的机会!虽然aibo只出场了一句话但我要把她带上(?)
维德·β·萨缪尔是个怎么样的人?
诚然,钟塔人员构成如此庞大,无论是离经叛道的魔法师、颇具天赋的魔法师、还是违反戒律的背叛者,这一切都是如此稀松平常。名叫维德的魔法师,名叫维德的背叛者,他没有任何值得这里的人特意去记忆的地方。
瑚金也是在看到笔记本上那潦草的签名时,才恍然想起这里曾经有这样一个人。
瑚金与维德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哪怕她们出身于同一座城市。略比维德年长一些的瑚金是钟塔的老师,而彼时的维德只是数以百计的学徒中的一员罢了。或许曾经有些许瞬间,她们曾在某一节课堂上探讨过同一个问题,或者在走廊中侧身而过,仅此而已。
所以,当瑚金看到笔记本上的署名时,她的心情是有些许复杂的。研究炼金术的魔法师会被当成怪人,明目张胆试图将炼金术与魔法结合更是一种不敬,所以即使是钟塔浩瀚的藏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也寥寥无几。
但维德却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笔记放在了这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藏在了这里。他像是故意在挑战钟塔的容忍底线,并且等待一个同样在是与非的边缘试探的人。笔记的本体是魔法咏唱的原理,而他用手写批注在旁边记录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与研究结果。和他离经叛道的行为截然相反,他的文字很有条理,甚至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就像与先贤在进行一场不被允许公开的对谈。
瑚金感到一丝恼火,是的,一丝,一闪而过。比那桩婚约递到她手中时更微弱,比在应酬中敷衍那些学阀或是自诩聪明的资助人时更短暂。是因为自己的研究被一名学生抢先一步?不,学术从来与年龄无关,大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她的不悦自听说维德已不在钟塔时产生,自听说他离开钟塔的理由时戛然而止,前后仅仅间隔了半句话的功夫。
笔记的内容很详细,甚至可以说,一项可以打破魔法与炼金术两者壁垒的学说雏形已经产生,但这项研究却胎死腹中,又被它曾经的探究者弃若敝履。
维德·β·萨缪尔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瑚金再次在银顶城与维德相遇时,她们之间仍然未有更多的交集。曾经的少年已经成为了青年,面容倒是与他们在课堂视线交错时所差无几,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恰恰一切都和瑚金对他模糊不清的印象天差地别。
他热络地和她打招呼,说着空洞的奉承话,就像那些学术会上盛赞她的年轻与智慧的庸人。在瑚金的记忆里,也可能是臆想中,他应该是安静的、离群的、如同她们共同的故乡吹来的风一般干燥又冰冷。她问他为何将那本笔记留在钟塔,而他却漫不经心地答非所问:
“那种小事不值您挂心,但如果鄙人的胡言乱语能够为瑚金老师带来些许灵感,那简直是鄙人三生之幸。”
他的语气是带笑的,却不带一丝感情,像一丝讥讽,像一声叹息。他在说完这些话之后,便扭头用指节敲了一下身边辛苦算账的龙化病人的头,轻描淡写地帮她更正了预算的金额。原本该陪在他左右的魔纹骑士变成了风尘仆仆的佣兵,原本该是他归宿的书阁变成了嘈杂的市井,他对她抛出的话题不再有兴趣,哪怕那是他昔日的心血。
瑚金突然想起了有关维德为何被逐出钟塔的传言。
她不会主动挑拨,也不会主动刺伤别人,所以她只是摊摊手,用一句玩笑话表达些许遗憾:
“看来我错过了和你探讨的最佳时机。”
“不,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机。”维德回过头,平淡地答复她,“我只是换了个课题罢了。”
这大约是瑚金与维德为数不多的会面中,他唯一一次露出真正意义上的笑容。
又名《坑害喀纳安的n+1种方式》
在做了各种准备后,终于到了雪山之行这一天,进山之旅一切都显得是那样顺利,当然,这要忽略那个在山脚处遇到的女孩,以及变小的默利与自称是他骑士的魔法师亚兹拉尔。
喀纳安只觉心累,这支目前有7人的队伍中,似乎也只有与他一样同为骑士的埃默里赫比较靠谱,至少他有认真警戒周围,其他人……真的不是来郊游的吗?
总之,这趟旅程——姑且这么叫吧——在喀纳安眼中,从遇到阿尔伯特并接了他的委托开始,便注定了不会太平。就像开头,因为琉璃死缠烂打,不得不临时增加队员。就像途中,因为晕车吐了一地的亚兹拉尔。就像现在,初现征兆的暴风雪。
“寻找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暴风雪就要来了。”
作为这支队伍里唯一有着雪山生存经验的人,众人都听从了喀纳安的话,寻找着那个可能存在的休整点。
也许是厄运女神都觉得喀纳安悲惨,这次没有继续为难他,在法师魔法的辅助下,这支更像郊游的队伍总算是在暴风雪彻底掩埋掉他们之前找到了一处避风的山洞。
喀纳安在检查确认了洞窟的安全性后,便叫上埃默里赫,两人在洞口附近负责警戒。
埃默里赫很佩服他的这位室友,他似乎知道所有的有关野外生存的事情。
“很感谢你对我们的照顾。”喀纳安一路上对大家的照顾他是看在眼里的。
“希望接下来能顺利吧。”喀纳安表情略微无奈。洞穴内部隐约传来了欢笑声,联想起自己被某人忽悠来带领这支毫无经验的雪山小队,他不由说到:“阿尔伯特魔法师在社交上还真是有种特殊的天赋。”
对方突然提到自己兄长,埃默里赫有些好奇:
“喀纳安你,是怎么看待兄长的?”
听到埃默里赫的询问,喀纳安内心略过一串念头:‘阿尔伯特?那个骄纵的贵族子弟?目前队伍里最累赘的魔法师?’当然这些是不能对着埃默里赫说的。
“他是个好魔法师,只是这里的情况限制了他的发挥。”
喀纳安单纯是指阿尔伯特的攻击魔法不适合雪山,容易引起雪崩,一旁的埃默里赫却突然沉默,这让喀纳安觉得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
埃默里赫因为‘限制’两字,想到了一些事情。
阿尔伯特的一切,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羡慕渴求的存在。出身于鼎盛状态下的实权贵族家族,权利于金钱于他不是什么问题,还有着颇为出色的容貌与相当优秀的魔法天赋。很多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终点,放在阿尔伯特身上,便是与生俱来便拥有的事物,这也令他看上去没什么欲望——似乎那些被旁人称作欲望的事物,他都有。但是人在没有成为真正的圣人之前,又怎么会真的毫无欲望的活着。
埃默里赫知道,阿尔伯特是有欲望的。那是被他掩藏的很好的,对魔法,对知识过于疯狂的追求。他甚至,想要研究龙。那本放在他密室书桌上,源于已经被毁灭的约里德家族的龙化症研究笔记,那些被魔法师们列为禁忌,本应该被销毁或者封存的笔记,还有那些标本都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我还有理智,不会亲自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如果能通过别的途径得知这些知识,我也不会拒绝。’阿尔伯特那时的话语,略显疯狂的表情也很清晰的浮现于脑海中。
限制吗?如果哪一天,欲望冲破了理智,阿尔伯特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无论怎样,以哈里斯家的情况,以阿尔伯特的能力,事情只会比当初约里德家的更大。
“我只要,单纯做他的利剑就好了。”埃默里赫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句,也许只是他不愿深入去想一些事情,不愿辜负阿尔伯特对他的信任。
‘这跟利剑有什么关系?’喀纳安脑海中略过这样一个念头,他突然发现他看不懂哈里斯兄弟的脑回路。正当他思索着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里面传来了阿卡的大嗓门。
“你怎么缩小了?”
阿卡的声音惊动了正在守卫的两名骑士,两人急忙跑回去,却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到。
“这种时候,就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喀纳安蹙眉:“现在可不是在银顶城内。”
“这不是恶作剧。”阿尔伯特没有丝毫慌张的样子:“看来黄金之家提供的发热药水出了问题。”
“有没有办法变回来?”喀纳安眉头更深。默利就算了,他是直接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现的,至少有保暖衣物可以穿,而阿尔伯特这时候变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原本的衣物现在没有办法穿,而在雪山上,失温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阿尔伯特摊手:“我没有办法。”他看向琉璃:“你是炼金术师,有办法吗?”
“这就需要专业仪器,进行专业研究。”炼金术师也表示暂时无法解决:“而且明知道有问题还去喝那个药水,这是你的问题。”
喀纳安“……”好想把阿尔伯特打一顿丢出去怎么办?他叹了口气,压下心中的想法,认命的去翻找可以使用的物品,给这个小娃娃制作衣物。
虽然已经尽力,但在这个连针线都缺乏的环境下,喀纳安最终也只能将衣物过于长的地方斩断,并用绳子绑好袖口,将裤子与鞋子绑在一起——腰带能让裤子牢牢贴在他身上真是太好了!
默利沉默着看着喀纳安帮阿尔伯特整理衣物,阿尔伯特则一脸新奇,看起来对自己目前的形象颇为满意。他有些兴奋,在喀纳安整理好衣物后开始撒娇卖萌。虽然喀纳安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小阿尔伯特略带婴儿肥的脸蛋,笑起来弯弯的大眼睛,再加上撒娇卖萌,着实很难让人生出气来。
看着正玩得开心的阿尔伯特,喀纳安拉了拉有点呆愣的埃默里赫,任命继续去洞口进行防守。
——————————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会在毫无准备还没有任何生存经验的情况下来到雪山?
这是那名胳膊受伤的女孩闯进来时喀纳安的想法。
姑娘说她叫蕾嘉尔,是名流浪炼金术师,只是来雪山上参观,但是倒霉遇到狼群,伤到手臂,在逃避狼群追击时还迷了路,正在发愁要怎么办,就遇到了他们,还真是走运。
听闻有狼群,喀纳安更为警觉,不过许是暴风雪吹散了蕾嘉尔的味道,这一晚他们安然度过。嗯,这要排除中间的小插曲才行。
“啊~火堆真是太棒了!好温暖~”——蕾
“冷?这个是什么发热药水?给你。”——阿卡
“哈哈,太好了!谢谢你!”——蕾
“啊,那个……算了你已经喝了。”——阿尔
“什么?诶?我怎么变小了?”——蕾
“你们一个个的!还有完没完!!”——崩溃的喀纳安
“嘎嘎!好玩!好玩!”——翁鸦鸦
———————————
雪橇快速行驶在雪地上,奔向最近的一处休整点。
喀纳安很有些心慌,他感到四周有什么危险存在,但放眼望去只有白茫茫的雪地,植被稀疏,不像是可以躲藏什么人的样子。但是喀纳安相信他这种长期野外生存形成的第六感,全程不敢放松,而这种警觉性也令他在狼群袭来时第一时间发起反击。
糟透了!阿尔伯特心情很差,这些狼却能够免疫低阶的魔法,风刃打在他们身上甚至连狼毛都割不破,至于高阶的魔法,那会制造比之前暴风雪还要恐怖的风暴,万一引起雪崩,除了能够飞行的阿尔伯特自己,这只小队恐怕不会有谁幸存下来。
强压下心中的烦躁,阿尔伯特转而使用辅助类魔法,或为同伴施加屏障,或给狼群施加些许影响。这其中,阿卡得到的援助最多,这姑娘招式大开大合,威力巨大但对自身防护不足,这从她一刀劈砍下一颗狼头,但自己差点被咬到就能看出,万一她受伤,这场本就艰难的战斗会更糟。
小队且战且退,越过被冰冻的河流,纵然喀纳安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但在这种完全不利的环境下,小队还是发生了减员事件——琉璃不知道何时消失不见,默利跟亚兹拉尔也趁着众人没空搭理他们逃走了。
战斗最终在阿卡与喀纳安斩断冰面阻挡住狼群过河中落下帷幕,大代价是损失两条雪橇犬,丢失了部分物资,琉璃失踪,默利与亚兹拉尔逃跑,以及喀纳安摔下悬崖。
众人狼狈的很,蕾嘉尔原本被包扎好的伤口此刻再次崩裂开来,阿卡体力消耗也很大,正抱着肉干咀嚼着,埃默里赫忧心失踪的队友,显得坐立不安。
阿尔伯特终究是家主,此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分析局势。埃默里赫同他说过喀纳安魔纹的效果,在有着厚厚积雪的情况下,再加上魔纹的效果,摔下悬崖的喀纳安未必不能生还。默利……既然敢逃跑就跑吧,这种情况下他不在反到更好。而琉璃,这姑娘不像喀纳安,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只能祈祷她没出什么事。
“埃里。”阿尔伯特整理好思路:“我记得喀纳安教过你雪山生存要点。”
“是。”
“你带他们两个先找一处地方休整一下,做些食物补充体力,我去找喀纳安。”
“兄长,我……”埃默里赫想说我跟你一起去,但他也明白现在这种情况,阿尔伯特的安排属于最优解,最终,话语变成了:“我知道了,兄长你要小心。我会设置魔法道标让你能找到我们。”
——————————
可以飞行有时会变成敌人的活靶子,但有时,却会很方便。
阿尔伯特操控风之翼,向悬崖下方飞去。入眼只有白茫茫一片,想要寻找失踪者无异于海底捞针。阿尔伯特心情沉重,于公于私,他都不希望喀纳安出事。
冷风吹过,衣物不合体的弊端显现出来,阿尔伯特召唤出一个小火球,依靠火球的温度勉强保持住体温,思考怎么才能找到那个不知身处何处的人。
漫无目的的寻找,通过喀纳安掉下来的位置猜测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过了多久,阿尔伯特觉得自己已经冷到快要失去知觉时,终于看到一点黑色向他冲来。是那只一直跟着喀纳安的臭嘴乌鸦。
“这边!这边!”乌鸦大叫着,转身飞去。
阿尔伯特是将喀纳安从狼肚子里拉出来的。若不是狼尸上明显的刀口,他差点以为喀纳安是被这只狼给生吞了,虽然喀纳安现在浑身是血的样子,着实不怎么好看。
考虑到现在在雪山上,一个水球砸下去血水未必能洗掉,喀纳安肯定会变成冰人,阿尔伯特放弃掉现在就把这个血人洗干净的方法,转而思考要怎么把他带回营地——那座悬崖着实不算矮,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居然没受什么严重的伤,喀纳安命也真是硬。
“哈里斯家主居然冒着危险来找我,看来我还是有用处的。”喀纳安起初惊讶,以他对阿尔伯特的了解,这不像是他能做出的事情,不过旋即想起他找自己一同前往雪山的原因,便也释然。
似乎除了自己带着他飞上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快速回到营地,阿尔伯特皱眉,旋即脱掉身上外套扔给喀纳安。
“绳子跟部分行李被水冲走,所以你现在最好能用这个将自己固定在我身上,我带你飞上去。以我现在的状态可抱不动你。”
阿尔伯特的风之翼是能够带着人一起飞行的,前提是这个人不会掉下去。风之翼位于背后,为了不影响魔法,想带人只能抱着,或者用什么特殊的装备把人吊起来,出于这个原因,阿尔伯特并不乐意带人一同飞行——在这之前,他也只抱着他的未婚妻梅布尔飞过一次。
“我想我可以自己爬上去……”
“悬崖被坚冰覆盖,你自己攀爬既费时间也不安全。”阿尔伯特抱着双臂,没有外套,寒冷感更剧。这令他心情也降到冰点。
感受到阿尔伯特糟糕的心情,虽然没受什么大的伤害,但体力也所剩不多的喀纳安索性也豁出去,他用衣服将两人腰部绑在一起,确保就算他抓不住阿尔伯特也不会第一时间掉下去后,以一种熊抱的姿势将自己挂在了他身上,然后失重感,强风吹拂感,寒冷感一同袭来,让喀纳安险些松手。
抛开那些瞬间起飞以及雪山寒冷空气带来的不适,阿尔伯特这个魔法很适合赶路,速度相当快,在喀纳安被冻到松开手之前他们来到了埃默里赫他们搭建的临时营地中。
阿尔伯特被冻得厉害,喀纳安也没好到哪里——被狼血浸透的服装起不到什么保暖效果。此刻两人裹着刚刚翻找出来的衣服,坐着火堆旁取暖,试图排出身体里的寒气。
埃默里赫把阿尔伯特抱到怀里,试图让他暖和些,然后拿着汤勺喂他喝热汤。因为寒冷,阿尔伯特此刻手抖到甚至拿不住汤勺。一旁的喀纳安状态略好,能拿住汤勺,然后通过比食堂大妈还要抖的手把汤全部撒到外面,蕾嘉尔看不下去,主动来帮他。阿卡则叼着面包警戒四周。
——————————
许是之前过于倒霉用掉了所有霉运的缘故,这支悲惨的队伍终于是走运了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处温泉,还发现了逃掉的默利,不同的是之前跟在他身边的亚兹拉尔变成了温德米尔。默利的眼睛被头发挡住,却也可以隐约看到下面的纱布。
然而众人并没有心情去寒暄,从温泉位置开始,顺着墙壁一路延伸而下的那些记录才是吸引众人眼球之处。
“这些是,构成铭文的基本原理?”蕾嘉尔作为目前队伍中唯一的炼金术师,也是最兴奋的一个。
“咦?这里有点不一样。嗯,龙血,遗骸?龙,馈赠……不会吧……”蕾嘉尔一时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应对,她悄悄看了下队伍中的魔法师们,见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才稍作安心。
‘龙的遗骸?龙血?’阿尔伯特沉思着,他不是炼金师,对炼金术相关知识不如蕾嘉尔,但那处划痕所表达的信息他是看懂了的,如果没有搞错意思,龙的遗骸吗?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得到,龙的遗骸,相比能从中得到很庞大的信息吧。阿尔伯特压下心中所想,跟着队伍继续前行。
洞穴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墙壁上刻满了华美繁复的壁画,但不知道壁画顺序的众人也只能解读出些零零散散的信息。
阿尔伯特盯着一处图案,这个图案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似乎是炼金铭文,又似乎是魔纹……等等,魔纹?他的眼睛猛然睁大,想起了熟悉感的来源,那是无尽书库中记载的,第一位魔纹骑士的魔纹!
魔纹为什么会跟炼金知识一同出现?是炼金术师创造了第一位魔纹骑士?还是炼金术最先是由魔法师创造并记录于此?或者干脆,这些知识都是那传说中的龙留下的?种种想法不断闪现,令阿尔伯特的精神异常亢奋。
这只是第一处,那么龙,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你们还会留下什么信息呢?真是令人期待。
温泉小故事
“好幸福!”沉稳如喀纳安,在经历种种事故后,将自己泡在温泉里放松,也不由发出一声感叹。
三个喝了减龄药水的小孩子恢复了两个,唯一没有恢复的默利,也由温德米尔细心照料,不需要他操心,当前,喀纳安只想好好放松一下。可惜的是,这趟旅程似是想让喀纳安与它抗争到底。
“我有些头晕,先出去了。”阿尔伯特扶着额头,也没有泡多久,怎么会这么头晕?
“兄长,我也一……”埃默里赫想要起身,但没等他完全站起,就见阿尔伯特倒向了他的方向。池底的湿滑以及突然的受力,令他连带着阿尔伯特,一同砸向了毫无准备的喀纳安,三人就这样摔在了一起。
“你们突然干什么?”喀纳安挣扎坐起,不知道这个麻烦附体的法师又在整什么幺蛾子。
“好烫!”埃默里赫发现了不对,阿尔伯特脸透着不正常的红,意识也迷迷糊糊的样子。
“这是,之前着凉导致发烧。”喀纳安试了试阿尔伯特额头的温度,联想起他变小没有合身衣服穿的事情,很快得出结论。‘这还真是……连个温泉都泡不安生!’他只觉嘴里发苦,再次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接这个该死的任务。“搭把手,我们把他抬到火堆旁。”喀纳安架起阿尔伯特一边的胳膊。
“这边有敌袭吗?”阿卡听到这边乱糟糟的动静,扛着大刀就要过来——现在才到,是因为蕾嘉尔强行拉住她给她套了件衣服。
佣兵与骑士面面相觑。
喀纳安庆幸,顾及到是野外温泉,他们是穿着浴袍下来泡的,所以现在还不算是坦诚相见,不然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至于浴袍……阿尔伯特绝对是来旅游的!仗着有空间包,他拿了很多无关用品。
“没有敌袭,只是我们需要把阿尔伯特送到火堆旁……”阿卡的行动力超强,喀纳安甚至怀疑她做事前根本没动脑子。
“交给我吧!”阿卡放下大剑,把阿尔伯特以公主抱的形式抱了起来,往火堆旁赶去,留下两个石化骑士与一对看戏兄弟。
‘希望阿尔伯特醒过来不要再制造麻烦。’喀纳安祈祷一句:‘有点好奇他知道自己被一个姑娘公主抱了后的想法呢。’
沉稳如喀纳安,也会有自己的小坏心思呢。


(一)
「我想。温德米尔你,应该还记得认识兔子先生。」
默利晃了晃手里的粉色兔子玩偶。
「......」
「兔子先生说,今天有奶酪哦!只要你睁开眼睛。」
「......」
「行了温德米尔,快起来,睡这么久,脑袋瘪掉了。」
「......」
嗯,好像醒不过来了。
那么,兔子先生,在这里陪着他吧。
默利走在街上时,天已经黑了。
「如果我变得很胖很胖,兔子先生还会喜欢我吗」
「兔子先生说,他喜欢肉乎乎的感觉。所以,多吃点吧」
「那如果很久很久之后,我忘记兔子先生了呢?」
「…….请不要忘记,兔子先生,想活下去」
想到了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
会忘记吗……
(二)
风与月是两个遥远的精灵。
一个奔跑在地面,一个受禁于宇宙。
风是安抚稻草,摧毁房屋的存在。
而月只是月,挂在穹顶的公主。
山峦之外是山峦,云层之上是云层。
风一遍遍地仰望天空,脚步却丝毫不停。
追求着什么,又等待着什么。
风无从知晓。
他掀起一层层海浪,掀翻一座座塔楼。
(三)
默利来到了约里德的废弃宅邸。
残破的大门上挂着一面旗帜。
那是约里德家族的徽标,只不过被一个巨大的红叉压在身下。
或许是因为工程量巨大,或许是因为那些可怕的往事。
这间宅邸荒废数年却始终未被拆除。
如今这也只是一间大房子,一位落魄贵族的躯壳。
似乎仍有些声音在这里回响…..
「哥哥的房间就在你的左边」
「当然,温德米尔也可以搬过来和我一起睡」
默利抱起小温德米尔,轻轻丢在床上。
「谁是最重要的人?」
「哥哥!」
「要听谁的话?」
「哥哥!」
「在哥哥和爸爸妈妈姐姐里选一个呢?」
「哥哥!」
温德米尔对答如流,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
默利十分满意地揉了揉小家伙的头发,替他盖好了被子。
就像每一个甜美童话的结尾。
默利轻轻吻在温德米尔的额头,被窝里一大一小两只手紧紧相扣,似乎可以阻挡风暴,阻挡洪水。
咔擦…….
默利推了推宅邸的墙。
像被白蚁啃坏的树干,墙壁直直倒了下去。
说起来,自己认识温德米尔多久了?
再过两个月就是第九年了。
时间过的真慢啊。
默利在宅邸漫步许久,知道月亮高悬,才动身离开。
很大,即便只剩下残骸,宅邸依旧占据了很多土地。
家族并未给自己留下什么。
哦,有两具尸体,挂在旗杆上六七个月。
那是出牢笼的日子,再次见到父母时,他们早已无法说话,支配魔法也不行。
毕竟被挂在风口里数个月,温德米尔根本认不出来。
(四)
风来到一座火山。
愤怒的神明一遍又一遍的惩戒着大地。
「我在拯救他们。」
神明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是我的爱!这是我的爱…..」
「您怎么哭了。神明大人」
「那是热烈的结晶。」
熔岩被洒向高空,冷却成坚硬的岩石。
熔岩被灌入大地,沸腾成炽热的血水。
「您的信徒们都变成岩石了。」
「那是他们对我至死不渝的守护。」
「这真的是爱吗,神明大人,我看到的只有苦痛。」
火山停止了喷发。
整片大陆都安静下来。
她看了看脚下的世界,黑色的河流与灰烬森林,大地的脉流早已被熔岩斩断,凝固的人怀抱着寒冷的心。
「爱是改变,同化,爱是……」
火山嘶吼着,伸出浆红的触手,妄想抓住这个质疑她的精灵。
(五)
「默利。」
希德尔抱着一沓手稿走出书库,迎面撞上想要进去的默利。
「啊,希德尔,日安」
「……日安」
熟悉的面孔,却不熟悉的表情。
默利沉着脸,侧身进入书库。
还没走吗?
希德尔看了看窗外,欢笑声不绝于耳,又是一年枫华庆典,热闹的节日。
时间与记忆是死对头,禁魔仪式还是前天,现在就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吗。
明明是那样不明所以的愤怒。
麻木的人们。
「叩叩叩」
默利来到无尽书库的中央,敲响那个隐秘的门扉。
棕红的门在默利眼前出现。
轻扭把手,贤者的门便被推开。
「默利。」
「贤者大人。」
默利站在门口,脖子上缠着绷带,无神的双眼直视着屋子里的卡纳。
「进来吧。」
「…….」
卡纳站在书架前,拨弄着手里的西洋镜。
咔咔咔咔……
西洋镜转动的声音很像钟塔运行。
「要问点什么?」
卡纳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现在……依然可以使用魔法……为什么。」
「你觉得西洋镜是怎么转动的?」
「…….发条轴轮?」
「那这样呢?」
卡纳转动手指,一根细长的轮轴从西洋镜里飞出,这是齿轮机械的心脏,温德米尔曾对这些小玩意儿很感兴趣。
西洋镜依然转动着,只不过少了齿轮咬合的声音。
「……」
「魔法师拥有操纵这些的力量,即便你不相信龙,他的力量也依然赐福予你。」
「为什么没有把我禁魔。我杀了莉莉娅!蛋糕刀划开了她的脖子!」
「………」
卡纳并未回答默利的疑问,继续摆弄着手里的小玩意儿。
「卡纳大人。」
「重要吗?默利。」
「……..」
「不信仰龙与钟塔的你,我所做的处置便毫无意义」
「我想获得一个答案。您毁掉了我的家,绞死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和温德米尔,给予我还算正常的生活,如今……」
「你和他很像。」
卡纳打断默利。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默利,我只是规则处理,你姐姐莉莉娅的死…..」
「…….」
「这个送给你。去吧,去找你认为可以获得答案的人。」
默利接住那个桃红色的西洋镜。
没有轴心依然可以旋转。
没有信仰依然可以吟唱。
(六)
风的旅途没有终点。
这是风在见到珍珠时的自我介绍。
「留在这里吧,欣赏我美丽的光。」
珍珠从蚌壳中跃下,伸出一双纤细洁白的手,轻捧住风的脸颊。
「那些人,都是你的客人吗?」
风指了指蚌壳后,一小座堆起来的白骨。
「他们呀!都是我的追随者!」
珍珠穿着洁白的裙子,在风面前轻轻转着圈。
「这是,凝聚成钻石的爱呀!」
风牵起珍珠的手,感受着那其中的温度。
冰冷、僵硬和机械。
「可是却他们都死去了,人类无法在海底生存,他们的身体早就被鱼吃光了。」
「可是爱不会!」
珍珠的眼中积满泪水。
「凝聚、守护与洞察!这是爱的真谛!」
珍珠声嘶力竭。
风松开少女的手,转身去向更遥远的地方。
(七)
「特里维亚老师,好久不见。」
「…..默利。刚从卡纳那里出来吗?」
特里维亚放下手里的小刀,抬头看了看这个挡住自己光的人。
「您在……分尸小松鼠吗?」
特里维亚握着一把银色小刀,桌子上躺着一只棕色皮毛的松鼠,松鼠的四肢被细麻绳固定牢靠。
「看看它们的……内部构造。」
松鼠的腹腔被划开,粉嫩的皮下组织与筋膜暴露在外。
「有什么事情吗?」
阳光被结结实实挡住,特里维亚所幸将刀与松鼠搁在一旁。
「它…..不痛吗?」
「用了幻睡魔法,不痛,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在睡梦中死去。」
「…….老师,死亡的时候会感觉到疼痛吗?」
「嗯?」
似乎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特里维亚的嘴角勾起,隐没在黑暗里的眼中涌现出少许的光。
「如果是死亡的瞬间,会;但如果是死亡之后,收获的只有疲倦。」
莉莉娅…..一定很痛吧。
「谈谈吧,工具是什么。」
「一把蛋糕刀。」
「捅穿心脏?」
「划破了脖子。」
特里维亚拾起刀,将刀柄压在松鼠的颈脖上,不出一会儿,心脏便停止搏动。
「大脑一片空白,意识恢复时已经没了气息,惊恐慌乱,然后镇定下来……我说的没错吧。」
「…….」
默利轻轻点了点头。
「我想带走重伤的弟弟,她,发了疯,拿刀威胁我放手…….我不能让弟弟再流一滴血…….她朝我扑过来,我夺过刀……」
「哼哼。」
「我没有办法……就算我受伤也没事,但是温德米尔。」
特里维亚推开椅子来到默利面前,俯视着这个混乱的少年。
房间仿佛一个破洞的瓶子,任凭乌黑的海水涌入,直到沉底。
片刻后,黑暗占领了这里。
特里维亚捧着一柄白色的蜡烛,将它递给默利。
「还记得姐姐长什么样吗?」
「和我一样的黄色眼睛,棕褐色长发……」
「血泊里的姐姐也是那样吗?」
默利抬起头。
蜡烛微弱的光照在特里维亚的脸上,缠着绷带的脸颊与枯瘦的皮肤,白色的眼球嵌在没有一丝肌肉的眼眶里。
「记住她的样子。」
「……..」
「这是你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补偿与救赎。」
「即使你的目的是拯救他人,即使你可以顶着正义女神的胸章。」
(八)
风重新回到了自己诞生的村庄。
印象里,故乡的夏季总有一场流星雨。
记忆开始的地方藏着水晶。
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但村庄已然被海水淹没,大片的房屋只剩下几个露出海面的屋顶。
「你好,归乡的旅客。」
「是你淹没了我的故乡吗?」
「是我,我叫塞壬。」
「可以把村庄还给我吗?」
「可以。」
塞壬弹奏竖琴,美妙的歌喉伴着音乐。
海水在她的指挥下向日出的方向退去。
「那么,你要这些断壁残垣有什么用呢。在我到来的时候,你选择了离去,他们没了你的守护,都失去了生命。」
「我想看流星雨。我想坐在那个屋顶上。」
风指了指远处。
「流星雨早已消失。」
「你离去的太久了,群星被打乱重新拼凑,如今这里只剩下永悬的月亮。」
风顺着塞壬的目光抬头望去。
那是个金色长发的少女,精致的笑容犹如一颗皓石。
「带着这些重新上路吧。」
塞壬将三个瓶子塞进风的手中。
分别是,思念、陪伴与守望。
(九)
默利从钟塔走出,卡纳与特里维亚的话久久驻足在脑子里。
头好沉。
现在该去哪。
默利望向一个熟悉的方向,但自己手中没有万花筒。
「默利。」
是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你好。」
默利将手背在身后使劲拧了拧,朝阿尔伯特挤出一个微笑。
「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还给你。」
阿尔伯特递过来一个盒子。
「这是?」
默利揭开盖子。
「………」
粉色的雨衣,被叠理整齐,印有温德米尔涂鸦的那一面正巧于最上方。
「希德尔很感谢您的雨衣,虽然他并没有用到。」
「……..」
「祝您好运。」
默利抓着阿尔伯特的盒子,手背青筋凸起,盒子被捏得变形碎烂。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颤动。
心跳声盖过了所有声响,心脏每一次搏动都牵动着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
默利靠在一旁的树上。
窒息感,阵痛感,分配给每一个器官。
从未有过的感觉…….
种子要发芽了吗……
冬季精灵。
「温德米尔是我的底线。我会保护好他。」
「只能听我的话,这样温德米尔才不会受伤。」
「在家里要照顾好姐姐哦!姐姐生病了。」
「回家时,先拥抱。」
根茎撕破种皮,贪婪吸收着周围的养料。
像倒刺一样,在默利的心脏上扎根。
抽起的茎叶抵着心房的顶,似乎要将这里撑破。
默利从未遇想过种子发芽的情景。
就像孩子们把头放进被窝,夜晚的怪物便会离开一样。
靠着这个方法,默利躲避了一直以来的所有。
(十)
风终于找到了旅途的终点。
要到顶上去,去找月亮。
这是他对收藏家说的话。
「如果您下定决心,这趟旅途便不在话下。」
收藏家仔细擦拭着每一个展柜。
「这些,都是你的收藏品吗?」
「他们是我的爱人。」
风贴着透明展柜朝里看去,犹如小人国一般的景象。
「他们从出生就在里面了吗?」
「不,是我邀请他们进去的。」
收藏家晃了晃手里的笼子。
「可是,他们不会愿意的,他们没有自由。」
「自由?可笑,奢侈,愚昧。」
「........」
「只要我对藏品足够专注,他们对我足够畏惧,这就是至死不渝的爱。」
风在收藏家的目光下退向角落,轻轻搬下那里的拉杆。
「你!住手!」
收藏家拿去铁笼与镣铐,向风冲来。
但风只是风,收藏家撞在墙壁上,昏了过去。
「走吧!你们自由了。」
风对着那些小人欢呼道。
「别让他再抓住你们了!」
「嗯?你们怎么不逃跑.....」
「你们.......」
小人国的居民们看着这个庞然大物,短暂的震惊后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
(十一)
温德米尔全身上下缠满绷带,好像神话故事里的木乃伊。
默利瘫在床脚,手里举着名为「兔子先生」的玩偶。
温德米尔什么时候可以醒来?
默利捏了捏兔子先生。
兔子脑袋软趴趴地倾倒在一旁。
兔子先生也不知道。
真没用啊,明明是温德米尔除我之外唯一的伙伴了。
「还记得风精灵的故事吗?」
默利从床脚的缝隙里掏出一本童话。
「他从收藏家的城堡逃出来后.....」
「好吧,这个故事我也不太喜欢。」
默利将童话丢进垃圾桶。
「第二十七天了,温德米尔依然在沉睡之中。」
「这时,王子已经来到她的身边。」
「传说,真爱之吻可以唤醒被睡眠纺锤刺伤的公主。」
「那么......」
默利轻轻闭上眼睛,俯下身去。
迎接双唇的确是一层有一层冰冷的绷带。
公主没有苏醒。
(十二)
风精灵死在沙漠中。
一片可以将所有事物转化为沙砾的地方。
火山、珍珠、塞壬与收藏家成就了风所有的回忆。
月亮在哪里呢?
风在濒死之际仰望夜空。
「你好啊,风。」
「月。」
少女身上满是锁链与镣铐,行走时铃铃作响,像一只玻璃风铃。
「你终于找到我了,王子。」
月把风的脑袋轻轻放在自己的双腿上。「终于记起来了吗?」
「嗯.......」
「这里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啊。」
大片的星辰跟随着月离去,犹如新娘和她的裙摆。
风再也不用仰望天空,再也不用麻木的旅行。
所有赋予给月的,都是他所谓的爱。
风精灵最渴望、最畏惧的东西。
----------默利END------------
最近写文卡手所以我决定拆段发(土下座)
“埃里,你真的要上雪山了吗?”
酒馆里年轻的女孩子们在金发的龙化佣兵刚刚落座之际,就七嘴八舌地围了过来。埃里点了一杯酒,也替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孩子们点了她们爱吃的或者爱喝的,耐心地听着她们说的每一句话。
“听说雪山上魔物很多,你一定要小心啊!”
“如果有我弟弟的消息还请务必告诉我……”
“对了这是一些保暖的药水,小小心意,带上吧!”
他会温柔地对待每一位向他倾诉的女孩子,而她们也回报他以温柔。从她们的话里他可以直接或间接知道很多事,比如雪狼们不知为何成群结队地出现,比如先遣的骑士们似乎受到了龙化佣兵不分敌我的攻击。
“老板”为了寻找失踪的佣兵已经先一步上山了,这些消息很多是真是假已无从对证。埃里喝了一口酒,正在他思考这些情报时,他感觉自己的手肘被人碰了碰。他低下头,看到一位身材矮小的龙化佣兵冲他打了声招呼:
“呜说你正在母鸡抓龙的队友,就让我来找你了!”
外国话?埃里一瞬间有些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
面前的佣兵他是见过的,从好几年前她就总是出没在黑山羊酒馆,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过深入的交流。她看起来像是个小孩子,埃里心想,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小孩子站出来用与他年纪不符的成熟语调解释道:
“康佩阁下的意思是,我们受乌莉小姐指派,将要和您一起前往雪山探索。”
埃里看了看面前两个小孩子,露出了有些迟疑的神色。说话老成到有些古怪的小孩子叹了口气,似笑非笑地对他说:
“阁下人缘如此之好,不知最近是否听说过街边买的劣质药水?”
“我听说现在市面上买的保暖药水里好像混进了失败品。”基蓝摸着兔子的绒毛,随口同多伊说道,“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小孩子。”
“但是他们会卖给我们吗?”整理行李的多伊心不在焉地答道,语气中有一丝怨念,“这也算是炼金制品吧。”
“你还真是对炼金制品有相当强的执念呢……”基蓝有一丝无奈。多伊的思维在正常人眼里,或者说,循规蹈矩的人眼里总是非常不可思议,他对一切都看得很开,到了一种近乎悲观的程度。同时他总是很有……创造力,这种创造性的想法意味着他总是对一些在当下看来并不合法或者不合规矩的事充满了好奇。也正是这种好奇心和创造性,让他在小部分人眼里看来,除了“败犬”之外又多了“潜在恐怖分子”的标签。
而多伊对此的表示仅有不咸不淡的一句话:
“毕竟我们骑士和炼金制品也算是一种没有血缘的兄弟吧。”
——也许全银顶城只有他自己会认为自己的兄弟是一个可持续加热的水壶。
“你真的不考虑跟我组队吗?”在给行李系好最后一个绳结之后,多伊随手把它们背在肩上问身旁的基蓝。而基蓝则摇摇头,有些遗憾地说:
“总得有人留守银顶城啊,而且我的视力上雪山恐怕只会成为累赘。”
多伊不禁叹了口气,哪怕他其实早都预想过自己会被基蓝拒绝。探索雪山势在必行,早在四强角逐赛之际,就有很多人借着比赛的机会提前商量好了组队事宜。但是多伊既没有愿意主动邀请他的朋友,也几个没有熟络到他会主动邀请的同事。好在萨利亚出于同情,愿意帮他介绍一起探索雪山的队友。
他扭头看向那些向着巨龙结晶攀爬的藤蔓,摸了摸基蓝怀里的兔子,心说这次这些兔子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把它们吃完了。
手持长弓的龙化佣兵已经在约定地点等他了,只是他身旁还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很兴奋地指着他说:
“好大的罐头哇。”
然后被另一个不知为何看起来有点眼熟的孩子敲了头。
“您好,我是埃里。”佣兵同他自我介绍道,“这边的两位是……”
“福利院的小孩子吧,我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哪里。”多伊显然误以为维德和康佩是萨利亚那边救治的孩子。康佩听了一头雾水,而维德花了两秒钟才忍住没拿错版的药水泼他。
单纯的刀子剧情,不会存在于主线的剧情,里之人还是正经的he人
——————————————
雪山上的风景依旧绝美,雪花覆盖之处纯白的风景,仿若未受丝毫烟火的仙境。但一个人的到来却破坏了这份意境。
阿尔伯特双眸无神,就那样走在雪地之上,他怀中抱着一柄剑,原本干净的剑身如今遍布血污,有那位一直跟着他的小骑士的,也有他自己的。
“咳咳……”或许是雪山上的风太凉,或许是他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声一同出现的血点,宣告了阿尔伯特此行的终点。他倒在雪地中,血液染红了身下原本洁白的雪,开出妖艳美丽的花朵。
“抱歉,不能带你回家了,我这个哥哥还真是不合格,最后也只能让你同我一起长眠在这雪山之中。”这段话浮现于心中,他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视线渐渐模糊的同时,一幅幅鲜明的画面却也同时浮现出来。
成功通过钟塔测试与父母庆祝的画面,埃默里赫眼眸闪亮看着他的画面,管家先生拉着他去看埃默里赫练剑的画面,与希德尔一同庆祝通过了湖夫人课程的画面,枫华庆典众人齐聚的画面,烤肉party抢夺烤肉的画面,埃默里赫倒在他身前的画面,以及,希德尔满脸怒气将冰锥射向他的画面。
视线模糊。腹部被冰锥伤到的伤口依旧有血液不断渗出。
“对不起……”眼前为什么开始发黑?难道是特里维亚老师对他使用魔法了吗?
“我没想到会伤到他……”希德尔喜欢的人他真的没想要伤他的。
“我只是想控制住他,不是故意的……”被龙尾抽飞导致的伤痛与埃默里赫逝去对他的打击令他魔法失控,虽然竭力控制,但还是导致那位遍体鳞伤。
‘埃里,你来接我了吗?我怎么记得你被我收进了一个小袋子中?哈哈,这是错觉吧……’
‘兄长……’
‘都说了要叫哥哥,这样更亲近。咦?我为什么会看见我魔力耗尽,风之翼消散,倒在雪地中的画面?是谁对我用了幻觉魔法吗?’
‘兄长,回去!’
‘回去?银顶城吗?前面就是啊?’
“埃里。”小小的阿尔伯特牵起更加小的埃默里赫的手:“这是枫华庆典,我很喜欢呢!一起去玩吧!”
眼前的光芒彻底消散。
风带起漫天雪花,埋葬了倒下的生灵。重归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