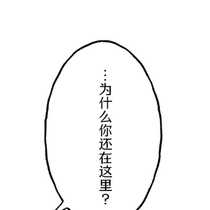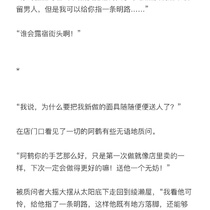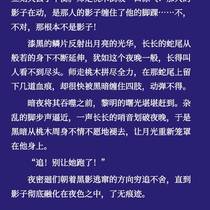祇園精舎の鐘の声
諸行無常の響きあり
娑羅双樹の花の色
盛者必衰の理を顕す
驕れる人も久しからず
唯春の夜の夢の如し
======
战国时代末,人类与鬼女爆发战争。人类巫女千鹤重创鬼女首领椛,使其逃往信州。鬼女偃旗息鼓沉寂养伤,人类迎来了百年安宁,而后世称这场大战为“红叶狩”。
明和九年春,水天宫大火,火势蔓延至大半江户城。人类与鬼女的命运就此逆转。
无论是苦苦支撑的巫女血脉,还是暗中蛰伏的鬼女一族,亦或者是江户城中普通的芸芸众生,若能预知这无法挽回的结局,是否还愿投入这长宵之中,犹如夜蛾扑火。
那么请看,明和八年的春樱,已然绽放……
柯诺卡带着三百三十三号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这里,却没有想到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这是位于米国新江户城——使用英语的话,也有纽埃多这样的叫法——的某片街区。
本来是个街区,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像不久前经历了一场极大规模的爆破或是火灾。到处都是焦黑的灼烧痕迹,有些房子甚至能通过墙面上的洞看到内里,地上散乱着破碎的岩石和泥灰,空气中还有粉尘和硝烟在飘散。路上空无一人,但也没看到尸体,不知道是不是撤离或躲起来了。
她找到一块比较完整且较高的承重墙,尝试爬上屋顶去远眺,但当整个人的重心都放上去时,那堵墙还是摇晃了一下,缝隙里掉出碎砂。三百三十三号在后面扶了她一把,让她没有摔下来。
“难道这就是教会预言里的那场大火?”她皱眉喃喃。
三百三十三号面色也很不好看,走过来的一路上,他都在试图寻找还能救的活人,或者哪怕能够安葬的尸体……或者尸块。
然而一无所获。
他神情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了。
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发现任何伤亡者——这可能比发现了尸块更加糟糕。
·
他们回到了车上,继续往北开了一段。但是前面的路毁坏比较严重,他们不得不再次下车。
“谁!?”三百三十三号警觉地偏头看向远处的路口,身形一闪,崎岖的地面对他好像无法造成影响,几个纵跃抓住了躲在墙后试图逃窜的黑影。
他速度极快,那个被抓住的黑影反应也很快,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啊啊啊啊啊求求你不要吃我!”
三百三十三号:“……”
柯诺卡从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追上来之后,看到的场景就是某个金发青年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趴在地上,抱着三百三十号的脚踝死活不肯起来的场景。
“补药吃我啊,求求你们,我从小就不锻炼,身上一点肌肉都没有。草鸡大家都知道要吃散养的不要圈养的,我就是圈养的那种!肉很柴的一点都不好吃!”
“……”他已经黑着脸解释了好几遍自己并不吃人,但金发青年好像完全没有听进去。
三百三十号不想动作太大让对方受伤,他已经看出这个青年像是饿了很久,状态并不好,但就偏偏凭着一口气——大概是求生欲吧?——硬是像块牛皮糖一样甩也甩不开。
难得看到他这种窘迫的样子,柯诺卡噗嗤笑出了声。三百三十三号抿了抿嘴唇,有点恼地看了过来,暗示她快帮忙。
柯诺卡一边笑一边蹲到了那个金发青年的脑袋边,伸手撸了撸那头金发,嗯,手感不太好,看起来确实风餐露宿好几天了,应该不是演的。
“可以停下了,先生。请放心,我们不吃你。”她凑到对方耳边放大声音,同时为了从对方的嚎哭中吸引对方注意,用两只手捏住对方的脸用力往两侧一拉,“您看看您,毛发干枯,肤色暗淡,形体不协调,骨头好似缺钙,身上也没有溯源码,谁知道您是吃什么长大的,饲料里有没有添加剂?说不定您是转基因产物呢?我们可不会随便吃路边不认识的地沟肉,万一吃完看到绿色小人在天上飞算谁的呢?”
青年哭得实在是太伤心了没法立即停下,但他听着这些话,眼睛越瞪越大,一边抽噎,一边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你……不是,这对吗?”他又大声抽了抽鼻子,“我也没那么差吧……?”
柯诺卡微笑:“对的对的,这对的。”
·
稍微花了点时间才让青年彻底冷静下来,再次向他强调自己这边真的不吃人。
青年怂怂地看了看三百三十号,依然不太相信的样子:“但是这位先生的身手,他不是人类吧?他真的不是吸血鬼什么的……?”其实不仅是身手啊!这位先生眼神真的好凶恶,感觉像是要吃小孩一样,他真的怀疑他会吃人!但他不敢当面说……
柯诺卡和三百三十三号对视一眼,两人都有点意外。
柯诺卡:“非人种族也有很多种类,而且世上还存在流着异族血液的特殊人类,大家食谱各不相同。请放心,我们的食物中确实不包括人类。”
一直讨论食物食物的,青年看起来越发饿得上气不接下气,三百三十三号索性从包里掏了些压缩饼干和水出来分给青年,顺便证明一下自己的食谱。
这个行为显然瞬间提高了信任度,青年道完谢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双方交谈许久却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很显然青年知道部分非人种族有利用名字施展法术的方法,尤其是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很容易引发麻烦——这一点他们平时其实也非常注意。不过这里的重点是青年似乎很熟悉神秘侧,说不定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等青年咕噜咕噜喝下水,喘着气稍作歇息的时候,她再次开口:“其实我倒想问,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吃人,这里之前发生的事情和食人种族有关吗?”
“不、不是!比那可怕多了!那场可怕的大火,那场火……嗯,嗯?等一下!”恐惧让青年语无伦次起来,但随后他意识到了更加震惊的事情,提高了声音,“你们该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这里来了吧?那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倒也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
柯诺卡往三百三十三号的方向看了一眼。
这趟旅途,原本想寻找的是终点。无论是玩弄命运的诅咒,还是布满人生的阴雨,都应当存在一个能够终结与安息的地方。
但这时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里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一切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
一发完,标题及梗完全来自企划的愚人节banner!
其实自己也没有多想设定,主要是想玩新江户=纽埃多和三百三十三号这两个梗,循环着《红日》和《最重要的事》随便写了点东西……
本来想多写到几个人的但是感觉时间不太够了啊啊啊所以就这样吧(扁扁地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