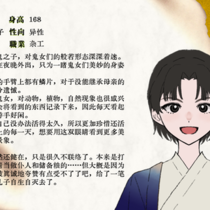*点击就看银杏智斗大反π
*没斗过
五声乌鸦叫过,侧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当值的小太监对银杏略一点头,示意她快些进去。
夜已深了,司徒京却尚未睡下。宫中起火,他自然不能安寝,见银杏风尘仆仆赶来,脸上尽是不悦。
“你究竟有何要事,非得在此时禀报不可?”
乌鸦叫是司徒京和她约定好的暗号,以五声最为紧急。银杏没有像往常那样跪下说话,而是站直了身体,强迫自己直视司徒京的眼睛:“在下有要事奏报,但还请大人将家父之事据实以告,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想必此事非同小可,竟然让你有胆子威胁我了,”司徒京冷哼一声,“究竟何事?”
“我必须要先听到家父之事。”
“跪下!”司徒京大喝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只是这宫里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站着和我谈条件?”
银杏不跪。她直视着他,强迫自己用最平静的口吻说道:“皇上死了,是我杀的。”
她期待着司徒京那张千年不变的面具轰然碎裂,她想看到他惊愕,迷茫,甚至恐惧的神情,但司徒京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冷笑了一声:“哦,如何杀的,说来听听?”
银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她可是杀了皇上!那是皇帝,天子,九五之尊,不是路边的野猫野狗,宫里的宫女太监,是皇上!
她咬紧嘴唇让自己冷静下来,再一次问道:“当年家父平白受冤,我一家蒙难,幕后究竟何人主使?”
司徒京沉默片刻,终于开口:
“你父亲林海舟,曾是前朝内阁大学士的幕僚。”
也许是因为自己所言之事关系重大,司徒京终于还是松了口,却只说了一句便停了下来。
“然后呢?”银杏急切地问道。她终于抓到一丝父亲蒙冤的线索,不能就这样错过!
“我已经给出了我的诚意,现在你该说说陛下是怎么死的了,”司徒京挥手指了指一旁的座椅,“坐。”
银杏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荒谬:仿佛她杀了皇帝,才有资格在司徒京面前坐着说话。
银杏从头讲述起这漫长的一夜。她跟随汝阳公主离开桃花宴,一路来到佛堂,面见了太后,公主又被皇上召见,不料那昏君竟想拿她作人牲!眼见姚小娥危在旦夕,银杏哪里顾得上那么多,抄起桃花枝捅进皇帝心口,那昏君当场就没了气息,可桃树却在他的尸身上生长起来,甚是可怖!
此后小娥托她传信之事,却不便与司徒京说,银杏便按下不表。好在她在混乱中寻到二皇子,将信交给了他,只是来不及把详情与他说明。
司徒京神色未变,淡然道:“这便是你和我谈判的筹码?我知道这些又有何用,应当把你这个弑君的刺客拉出去斩首才是。”
“宫中火起,太后生死未卜。然而我与公主面见太后时,她曾讲起一桩宫中秘事。”
这便是银杏最大的倚仗。此等机密之事,司徒京不可能不想知道。
司徒京却反问道:“我无意参与立储之事,也从未卷入朝堂斗争,宫中秘事与我何干?”
那你要我去做二皇子的眼线,难道真是让我去吃白饭的?银杏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道:“那就把我处死好了,反正我死了,秘密就和我一起被埋进土里了。”
司徒京冷笑:“据你所言,此事汝阳公主也知晓。皇帝一死,她也脱不了干系。等她和你一道关进天牢,我倒要看看她的嘴是不是比你的还要硬。”
……银杏真恨自己多嘴,为何要说汝阳公主也知晓此事?她本想以此事作为筹码,可司徒京终究还是技高一筹。罢了,即便被处死,死前杀了那昏君,也算是死而无憾!
门外突然有人禀报,司徒京示意银杏藏在屏风后面,走出门去,片刻后他关门落锁,皱眉对银杏道:“你父亲的事我所知不多,但我有所耳闻,新帝即位后,大学士一派便被清算,而幕后主使便是枢密使庆春泽。”
被突如其来的收获冲昏了头脑,银杏没去想为什么司徒京突然改了主意,急切地问道:“此事当真?”
司徒京点头,慢条斯理地说道:“现在,你可以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吧?”
这个漫长的夜晚仍未结束。司徒京说她不能再留在宫中,甚至不能再留在城内了。银杏乔装一番,趁桃花和大火带来的混乱还未平息溜出了宫,回望却见参天桃花,不禁一阵胆寒:自己将那桃树枝捅入皇帝胸口,是不是无意之间犯下大错?
“姑娘,快走吧。”一旁的侍卫低声催促道。
司徒京竟然大发善心,派人护送银杏出城。只要出了京城,便可去往江南避避风头。大概是皇帝已死的消息尚未从宫中传出,出城的路格外顺利,天光大亮之时,银杏便已与那侍卫一同策马奔驰,远远离开了桃花笼罩的京城。
行至一处荒地,银杏说想歇息一会儿,两人便下了马,找了处背阴的地方坐着。
“唉,城里怕是要出大乱子了……”
侍卫感叹道。
银杏沉默不语,突然提膝撞向侍卫腹部,趁侍卫吃痛倒地,拔出他腰间宝剑,飞身上马,扬长而去。
司徒京哪会发什么善心,他肯留她一命,必然是因为她还有用处!她再不想像枚棋子那样受他摆布,她要拿回自己的名字,拿回自己的剑!
银杏策马扬鞭,将层层叠叠的桃花甩在身后。
*点击就看小小剑客被搓扁揉圆
*就算只写了一根头发丝也要响应
“杏儿,杏儿……”
“醒醒,该起了。”
仿佛从水底艰难地浮上水面,银杏从梦中醒来了。方才梦中的所见所闻消散大半,只留下强烈的愤恨,大概是又梦到从前。
她艰难地坐起身子,眼前的女子对她温柔一笑:“总算醒了,快起来吧,可别误了时辰。”
银杏揉了揉眼睛,只觉得眼眶湿漉漉的,似乎有泪痕,暗道不妙。她试探着向女子发问:“小葵姐,我刚刚可曾说了什么?”
“没有,”小葵笑道,“就算你说了,也只是梦中胡言而已,当不得真。”
小葵姐一直对她多有照顾,料想就算自己真的说出什么,她也不会四处乱说。再说,梦里的话谁会当真?银杏放下心来,手脚麻利地梳洗打扮。自打做了掌设,活计也没比从前轻松许多,虽说不必像寻常宫女那样整日地清扫,却也要四处奔走,忙碌得很。
也许是这样的生活使她逐渐麻木,潜藏的愤怒才会在夜晚喷涌而出,提醒她去做那件必做之事。
我没忘,银杏想。有朝一日,她将化身利剑,刺穿那昏君的心脏,为父母,为家族报仇——然而她已许久没摸过剑了。
入宫数月,银杏这把剑早已不似先前那般锋利。
一开始,她舍弃了自己的名字。
听闻花鸟使将至,县丞家中小姐出逃,王家上下兵荒马乱,生怕落得抗旨不遵的罪名。赶来追回小姐的下人抓错了人,银杏就这么成了王杏儿,被县丞死马当活马医地带进了府。
若是能进宫做妃子,得手的机会要多少有多少!银杏成了替身,花鸟使来时,她竭力出演大家闺秀,实则琴棋书画样样稀松,只有竹笛勉强吹得像样。纯秋端坐屋内,仔细观瞧,面色不改,直到把钱袋拿在手里掂了掂,嘴角才上扬几分:宫里这样的姑娘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可有了银钱做砝码,天平的一头便沉沉地压了下来。
于是王杏儿入宫。
入宫前,她舍弃了自己的剑。削铁如泥的一把好剑,在当铺只不过值碎银几两。她打算用这银钱用来上下打点,好让她有机会面圣,可她姿色平平,又无过人才艺,这面见皇上的机会哪里轮得到她?她成了尚寝局的小小宫女,整日清扫宫中,没有一刻得闲。
若她真是王杏儿,此刻免不了怨声载道,但银杏是不叫苦,也不叫累的。她七岁习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并非什么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因此极快地在宫中安定下来。
唯有一件事让她不快:几位宫女见她干活麻利又不善言辞,总是将她的功劳揽去。起初她忍气吞声,后来便忍无可忍。她没了剑,却还有拳脚。脸上的巴掌火辣辣的疼,打她的人被她一脚踢翻在地,半天都没能爬起来。
这事原本交由掌设处理就好,谁料那日司徒京目睹这场争执,冷着脸将银杏带来问话。银杏忍不住叫屈:活都是我做的,可她们上下嘴皮一翻,就全成她们的了!
司徒京轻哼一声:既然是你做的,为何无一人替你作证?说罢便让银杏一干人等领罚,银杏罚得最重,挨了几下板子,好几天没能下床走动。
小葵姐一向关照她,特地来给她上药。她一边叹息一边说:过刚易折,过刚易折呀……咱们女人要像水一样,不管什么沟沟坎坎都能趟过去才好,你说对不对?
银杏赌气道:得罪了司徒公公,我看我也没几天好活了。
小葵姐笑道:我看未必。你卧床这几日,她们几个忙得焦头烂额,公公一向心细如发,该知道谁是实打实做事的那个。
银杏一想到那天司徒京的冷言冷语,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要是真那么心细如发,就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地罚我!
小葵姐苦口婆心道:司徒公公是在提点你呢!你这性子的确是该好好改改了。
改?如何改?银杏向来只知道怎样把剑磨得更锋利,却想不到有一日,她得把剑变钝才能过得下去。
忍气吞声只会让这些人更嚣张,一味讨好又像热脸贴冷屁股,银杏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她还在琢磨着如何去做,就又惹上了麻烦。宫里丢了几样摆设,宫女们众口一词,说是银杏拿的。司徒京不由分说,把银杏拉去打板子,要打到她开口为止。这次打得更重,但银杏愣是半句求饶也不说,硬生生地挺了过去。
司徒京冷笑:好一个硬骨头,你不怕死吗?
银杏咬紧牙关,狠狠地瞪着他:不是我做的,我死都不认。
好!司徒京拍起手来,吩咐手下将银杏带走看管起来。银杏以为自己要被下狱,却没想到司徒京派人为她治伤,一养便是半月。期间司徒京来过一次,说了些话,险些没把银杏气死:我早知此事不是你所为,那日罚你,一是为了服众,二是为了磨磨你的心性,要你日后做事圆滑些。过刚易折的道理你可懂得?我可是相当器重你啊。
银杏不懂,也不想懂。器重?又没给她银子,也没给她差事,板子倒是挨了两顿,若是宫中人都是这么器重人,她宁可受冷落。
她没想到,伤好之后银子和差事都来了。银杏和小葵一起成了掌设,八品的女官怎么也比宫女强上几分。那几个欺辱她的宫女已经不知去向,听说是偷了东西,与太监销赃时被逮个正着,如今尸体大概已经被丢在乱葬岗了。
银杏愣愣地摸着手中的银钱,心想司徒京倒是真没说谎,他的确是器重自己的。
成了掌设之后,倒是没怎么有人找她的麻烦。银杏卖力干活,只闲暇时琢磨屠龙大业:宫中守卫森严,偷溜进皇帝寝宫简直是天方夜谭。若是自己精通琴艺舞艺,就能趁着宫宴下手,早知如此,自己学什么剑,应该学舞,学唱曲才对!若是去求司徒京,让他给安排个皇帝跟前的差使,自己也好有机会下手,但司徒京又凭什么答应自己?
想来想去,都是些没用的办法。皇帝就在宫中,一想到他仍高坐龙椅之上,银杏的胸中就如同烈火焚烧:就是他害自己家破人亡,凭什么他还能活在世上?
也许是那火烧得太旺,终有被识破的一天。
你不是王杏儿。司徒京在她面前负手而立,平静地说出让她胆寒的话语。她此生从未感到如此恐惧,司徒京是如何看穿自己的?莫非是先前他问过几次家世,自己的回答出了破绽?可她早已与王家人串通妥当,想来不会有问题才对。她跪在地上冷汗直流,料想自己的死期就在今日。不对,这不对!她的剑呢?她就算是死,也应当死在杀敌的时候,与自己的剑死在一起。
她不该入宫,不该当掉自己的剑!
可司徒京却说:抬起头来。
他似是仔细端详了一番,点头道:你与你父亲有七八分像。
此话一出,银杏更是震惊。司徒京见过她的父亲?是了,算算年月,那时他应该也在宫中,见过父亲也不奇怪。那当年的事,司徒京也知道吗?
司徒京略一点头,缓缓开口:你父亲蒙受不白之冤,此事我也略有耳闻。可当年之事牵扯甚多,你想为父亲洗脱冤屈,怕是不能。
银杏默默听着,心里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她绝无可能撼动这颗大树,扳倒让父亲蒙冤之人。
可究竟是谁害父亲蒙冤,银杏直到现在仍然不知。
若你肯替我做事,我便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你不想知道是谁害你父亲蒙冤下狱,又是谁让你家破人亡,落到如今境地?司徒京眯起眼睛笑了,像是笃定银杏不会拒绝。
做……做什么?银杏不安地问。
司徒京笑容不变,吐出两个字:一切。
司徒京给她时间慢慢思考,银杏便权衡起来:若是给司徒京卖命,不知道要替他做多少肮脏事!可若是一直做小小女官,她何年何月才能复仇?带她出逃的嬷嬷从来只说父亲蒙冤,银杏再问详情,她却一概不知,想来对朝中之事知之甚少。司徒京却全都知道,只要她点头答应,就能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答案,这样的诱惑叫她怎么拒绝得了?
也许是思虑过重,一连想了数日,银杏生了场病。小葵姐来探望她,说最近天气转凉,宫里不少人都病倒了。她喂银杏喝药,又握着银杏的手让她安心,那副模样让银杏想起自己的妈妈。
妈妈,妈妈。银杏在心中呼唤,眼泪和着汤药一起咽进肚子。
银杏的病很快好了大半,小葵姐却病倒了。起先只是小病,咳了几天仍不见好,渐渐地身体也虚弱下去,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寻常的药不管用,银杏心中焦急,想去求位太医来诊治,可却碰了一鼻子灰。最近太医院正是忙碌的时候,哪有闲暇管一位小小宫女?
银杏急得落泪。她挨板子的时候都没掉一滴眼泪,此时的眼泪却掉个不停。小葵见她这样,伸手为她擦泪,声音却像是随时会断掉的蜘蛛丝一般,轻飘飘地挂在半空。
杏儿,杏儿,我对不住你。
有什么可对不住的?银杏只当她是病糊涂了。虽说这段日子掌设的活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可自己病着的时候,小葵姐不也一样?
小葵姐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下去,银杏已别无他法,只好跪在地上,求司徒京给小葵姐找位太医诊治。
司徒京饶有兴趣地看着银杏,良久他问:那你愿意用什么来换?
一切。银杏答道。
司徒京突然大笑起来:一切?你真要为了她押上自己的一切吗?
银杏再拜:小葵姐待我如姐如母,求大人救救她。
司徒京冷笑:那你可知,是谁将你的梦话告知于我,才让我戳破了你的身份?
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银杏想起那日小葵姐说,梦中的胡言是当不得真的。
银杏不可置信: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司徒京怜悯地看向银杏:无非是想谋个一官半职,换份更清闲的差事。如姐如母?这宫中无人不想向上爬,你的小葵姐也不例外。既知如此,你还想救她吗?
银杏吞了眼泪,咬紧牙关,再拜:要救的。
小葵姐死在初春,即便有了太医的诊治,她还是没能捱过去。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银杏已在二皇子府,只觉得春风也冰冷刺骨。她想起小葵姐的笑容和她粗糙的手,想起她说女人像水,无论什么样的沟沟坎坎都能趟过去。
可银杏成不了那样的水。她只是一片小小落叶,即便想要挣扎向上,却只能顺流而下,身不由己……
长叹一声,她将信纸与泪水一同扔进火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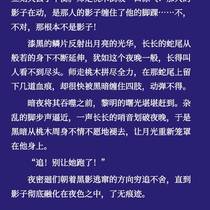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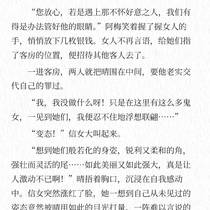
春樱落尽,转眼已是初夏。慈善院午饭时间还没结束,眼尖的小孩便叫起来:“老师,小夏又溜出去玩了!”
不等其他人发话,信女就放下筷子跳了起来:“我去找她!”她主动揽下这一差事,也只不过是想出去玩,要是能趁机躲过一两节课程就更好了。她这点小心思当然逃不过山女们的眼睛,但信女向来乖巧,就也默许了,放她出门。
信女步履轻松出了门,小夏会去哪里并不难猜,多半又是在河边玩水抓鱼。信女故意绕了个远,转到巷子里去,看墙根处开着的紫色小花。突然,她有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便默不作声地起身,向巷子口走去。
还没走出几步,她猛地回过头去,巷子那头飘飞的衣角被她的视线逮个正着。
“喂,我看见你了,出来!”信女一边大喊着为自己壮胆,一边回忆武术课上学到的技巧。若是那家伙敢现身,肯定讨不到便宜!
“是我啦,是我!”
一个少年从墙上探出头来,语气让信女差点以为他是自己的什么熟人,可仔细一瞧又完全不认识。她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凶狠:“你跟着我做什么?离我远点!”
“你别怕,我只是想看看你头上的花,”少年笑嘻嘻地说,“六片花瓣的樱花很少见呀,我想离近一点看看!”
“你是说这个?”信女摸了摸头顶的簪子,这是奶奶送给她的,自从收到之后她就总是戴在头上,“可这只是簪子上的装饰而已呀。”
“那是我搞错了,果然就该离近一点看。”少年跳下墙头,信女赶忙退后几步与他拉开距离。看她这样,少年也不再往前走了,而是站在原地说道:“我知道你,你是慈善院的信女对不对?我是晴!”
“所以可以让我过去了吗?我还有事要做。”信女冷淡地转身要走,却冷不丁地听到晴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你的角很漂亮哦。”
信女顿时寒毛直竖:这家伙,知道她鬼女的身份!他到底是什么人,是夜密廻的人吗?一瞬间,她甚至有种莫名的冲动,想狠狠地撕咬他的脖子,再将此人吞下。她猛然回过头去看晴,却没在他的脸上发现敌意,反而是称得上真诚的笑容,仿佛刚刚那句话只不过是普通的夸奖。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赶快回去告诉慈善院的老师们,让她们想想办法才行!
她用一秒钟做了逃跑的决定,转头却撞进一个有些熟悉的怀抱里。是奶奶来了!信女赶忙抱住了她,在她耳边小声说道:“他知道我是鬼女!”
奶奶却没像她想象中那般反应。她轻轻拍了拍信女的背,用仍然慈爱的声音说道:“没事,没事。小晴不是坏孩子,他吓到你了吗?喂,小晴!你是不是欺负她了?”
晴听到这话乖乖走过来,低头向信女道歉:“对不起,吓到你了。我只是想说你的角很好看。”
奶奶责怪地看了晴一眼:“你呀!这种话可不是随便就能说出口的!”
她牵着信女的手,一步一步把她带出了小巷,把晴远远甩在身后。
“奶奶,他是谁呀?”信女好奇地问道。她并没有变成般若之后的记忆,因此对那一夜发生的种种毫不知情。
奶奶柔声解释:“晴是鬼女的孩子,所以知道我们的事。他人不坏,只是个可怜人,不过要是他欺负了你,你就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主!”
“也……也不算吧。”信女小声嘀咕。那家伙除了吓了自己一跳,似乎也没做什么坏事。不过,晴的那句话却让信女产生了其他的问题。
“奶奶,我的角是什么样子?”
信女没有般若时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能变成什么模样。奶奶神秘地笑了笑,在嘴唇前竖起一根手指:“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要长大!”信女说着这样孩子气的话,抱着奶奶的胳膊撒娇。
在外人看来,她们只不过是一对最普通的祖孙而已。
小夏早已先两人一步溜回慈善院,正躺在地上打滚撒泼,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抄书的惩罚。管教小孩不是阿梅的专长,她总是乐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好在还有其他人在,不至于让孩子们娇纵过度。
慈善院的孩子们又多是懂事早慧的,她们早早吃过太多苦头,总要有人补上那一点甜。
“今天晚饭后有桃子吃哦。”阿梅提着水果穿过院子,女孩子们的欢笑声有了具体的颜色:粉红色的,鲜艳而甜美的桃子,切成小块摆在碗里,人人都能吃上一点儿。
如同往年一般的夏季就这样降临,但阿梅的身体却无任何异状。去年的芒会上她向山女们求教,有人说百岁前那年会格外渴望血肉,也有人渐渐长出鳞片和蛇目,却也有如同阿梅这般无事发生的山女,想来是人人不同。这样倒也无妨,她还能再多些时间守着慈善院的孩子们,只是这些孩子,真是让人忍不住地担心。
匆匆又是数月,盂兰盆节开设集市,阿梅便早早前去,打算买些新鲜瓜果给孩子们解馋。
她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刚刚把东西拿在手里,身旁就传来熟悉的声音。男孩轻轻叫了一声“奶奶”,便熟练地接过她手里的布口袋,步履轻快地扶着她走路。
“小晴,都说了你不必做这些事,我身体硬朗得很。”阿梅笑道。自从她把晴从信女的口中拖出来之后,这孩子每每见到她,都会跑来帮她提东西,有时还会送来野菜,蘑菇,竹笋一类的东西,全都进了慈善院儿童们的肚子。
“没关系,我乐意替奶奶拿着。”晴爽朗地笑着,用缠着绷带的手臂挠了挠头。
阿梅皱起眉头:“伤还没好吗?”按理说被信女咬伤已经一月有余,那伤总该痊愈了才对。
“哦,那个呀,早就好了,”晴满不在乎地笑道,“只是前几天不小心受了点伤啦。”
阿梅板起脸训斥他:“你肯定又去做危险的事了,年轻人总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嘿嘿,本来也没几年好活啦。”晴语气轻松,说出来的话语却很沉重。阿梅说不出话,拿出一个苹果硬塞进小孩手里。小晴这孩子也是苦命人,鬼之子少有得到母亲喜爱的,他也不例外,可这孩子又偏偏那么爱他的母亲,唉,光是想想就觉得心疼!
她看向晴那双明亮的眼睛,遥远的记忆宛如烛火,在脑海中轻轻摇曳。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有像晴那样的孩子挽着她的手臂,笑着呼唤她:
“妈妈!”
空气中弥漫着古怪的,腐烂瓜果的香气。
回过神来,阿梅发觉自己身在房间之中。她朝前走去,试图寻找出口,层层叠叠的房间无限延伸,仿佛没有尽头似的。
……这大概是幻境,或者别的什么。直觉告诉她这里并不安全,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但身后却传来低低的声音:
“娘……”
阿梅低下头,快步向前走。沉溺于过去绝非理智之举,只会平添烦恼。
那个声音却愈发急切,甚至带上几分哭腔。
“娘,我也是迫不得已,您原谅我,原谅我……”
母亲原谅孩子,是比想象中还要容易的事。但若说从此便不恨,恐怕也是谎言。怎能不恨?在她拖着沉重老迈的残躯,如同蛆虫一般爬过黑色的泥土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点恨意?那双她牵着走过回家路的小手,将她弃置于山林之中的时候,难道她没有用怨恨的目光看向他的背影吗?
“妈妈,原谅我……”
那声音苦苦哀求着,从低沉变为清脆,彼时他去店里学徒,偶有贪玩惫懒,见她生气,也是这样求饶。她硬起心肠训斥,第二天却仍旧做好饭菜。母亲原谅孩子就是如此容易!
“妈妈……妈妈。”
声音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婴儿的啼哭。阿梅浑身一颤,猛地回过头去,赤红的婴儿躺在地上,响亮地发出初生的啼哭。是他——不!是他!
因果报应,不外如此。是母亲先抛弃了孩子,所以孩子才会抛弃母亲。阿梅笑中含泪,伸手扼住婴儿脖颈:
即便再来一次,她也会这样做。
原谅我,孩子,妈妈也是迫不得已。
夏季的热烈阳光重新笼罩阿梅,周遭却不见了晴的身影。也许那孩子先回去了吧?阿梅这样想着,拾起地上的包裹。她还得给慈善院的孩子们做饭,可不能在这里耽搁时间!
障子之间中肤色青白的婴孩,就这样静悄悄地消失在阳光之下。

*有人直到主线发了才知道序章就是第一章
*有人第一次见老婆的时候差点被吃了
孩子们都睡下了。阿梅终于得来片刻清闲,独自端了茶具去后院赏月。月泉旁的百合花总是开得很好,花瓣如同月光般纯洁,不过在阿梅眼中,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色。
“阿梅,还不睡吗?”
身后传来女童般稚嫩的声音。阿梅并没回头,而是给来者倒了杯茶:“打算过一会儿再睡。”
春龙胆顺势坐了下来,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虽说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春龙胆在院里的年头却比大多数人都要长。她同阿梅一样照顾着孩子们,但阿梅总是将她也视为需要照顾的那方,即便春龙胆的外表十年如一日,从未变过。
两人静静地喝了一会儿茶,夜晚的微风吹过,廊下的风铃叮铃铃地响了几声。阿梅放下茶杯,慢慢开口说道:
“我的事,已经听小红说过了吗?”
“嗯。”
春龙胆轻轻点头,又问:“是什么时候?”
“大约就在年内,我也不知何时,”阿梅歉疚地笑了笑,“也许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会。你我本就该互相帮衬,何来麻烦一说呢?”
阿梅又笑了笑:“只怪我连自己的生辰也记不清。实在是……太久以前的事啦……”
然而这九十九年的漫长岁月,却也如同弹指一挥间,轻飘飘地过去了。
下个百年,她要化为人身蛇尾的妖怪,靠吸食人血延长生命。这没什么不好的,不属于人类的时间,便不能再用人类的活法,可她心里唯独放不下的,是慈善院的孩子们。
“……小菜惠,还有小夏,总是一个看不住就偷溜出去玩,虽说每次都好好地回来了,可还是让人操心。真理不肯好好穿鞋子的话,至少要把袜子穿上,她的脚已经磨破好几次了;要是秋夜吃不下蔬菜,就告诉她,吃了这些蔬菜,就能变得像小巽那么强;还有,蒲兰半夜会踢被子,夏天还好,冬天受凉了可就糟糕了……”
阿梅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才察觉到自己说得有些太多了。春龙胆点一点头,用不符合孩子外表的语气说道:“不必担心,阿梅。我们会照顾好她们。”
阿梅知道自己本不必这么担心。慈善院的教职工自然不必说,总是尽心尽力的,大孩子们也总会照顾更小的孩子。像是朱鹭这样离开慈善院的女孩,也会经常回来看看,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于是慈善院的女孩们得以顺顺利利地长大,成为“无论怎样都能活下去的女孩”。
春龙胆又抿了一口茶,问道:“您打算告诉孩子们吗?”
阿梅摇了摇头。她不想在孩子们的心中平添烦恼。
春龙胆又问:“那信女呢?您总得告诉她吧。”
唉,是啊!她是得告诉信女的,可要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阿梅却迟迟不能决定。若是拖到连她也忘记的生辰,那时就不得不说了,可是对于那孩子来说,会不会又太过突然了?
阿梅兀自烦恼着。春龙胆抬头看看月亮的高度,很快站起身来:“很晚了,您也早些睡吧。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忙呢。”
“是啊……明早就吃杂菜粥如何?”
慈善院的生活就是这样,没什么空闲烦恼自己的事,还有很多事要忙。阿梅与春龙胆道别,很快回去睡了。
几日过去,阿梅忙前忙后,无暇考虑如何向信女道别一事,或者说,是她自己每每想到,就要故意去找些活计来做。一想到快满百岁的人,还是烦恼多多,阿梅便觉得这人生有趣,怎么一刻也不得平静?
这日夜里,孩子们都睡下了,阿梅却没有睡。她仔细听长屋里的动静,果然不过多时,信女如同梦游般走出长屋——今日便是她外出“狩猎”的日子。
阿梅算过日子,知道就是这两天。虽说信女每次都平安归来,但她总是不怎么放心。她本想跟上去,却又想着:日后自己不能再这样跟着,那孩子也应当有力量自保……可想来想去,仍旧忍不住起身出门。孩子们就是这样,总是让人挂心!
仅仅借着月色,阿梅也足以看清道路。这是山之主的赐福,让她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年龄仍旧健步如飞。她一时找不到信女的踪迹,便凭着曾经的经验找寻。她走过几处街道,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巷子里找到了信女:
她的蛇尾牢牢缠住一人,似乎正要卷起对方,将其囫囵个吞入腹中。阿梅松了口气,却在看到那猎物时心头一震,连忙冲向信女:“等一下,小信,不可以——”
妈妈,我好像要死了。虽说有些不甘心,可被鬼女吃掉,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死法。她的眼睛真漂亮,像蛇一样,尾巴也强而有力,仔细一看,角是长在颈后的,与您的不同,却也很美。
好想摸一下她的角……在死之前,能摸到吗?
晴没感到恐惧,反而兴奋起来。鬼女张开嘴,露出尖利的牙齿,肆无忌惮地展示着食欲。他努力想将手从蛇尾的缠绕中挣脱,但反而被越缠越紧,正当他几乎想放弃的时候,救兵赶到了。
“好了……好了。”
老奶奶抚摸着鬼女的身体,让其安静下来。鬼女显然对突然中断的进食感到不满,尾巴躁动地拍打着地面。老奶奶见状,挽起袖口,将手臂递到鬼女眼前。
“还是我来吧。”
晴抢先一步上前,几乎将自己的手臂送到鬼女口中。鲜血让鬼女平静下来,晴却遭到老奶奶的怒目而视:“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晴用完好的那只手挠了挠头:“没事的,我在家经常做这种事。我是鬼女的孩子。”
“不是夜密廻的人?”老奶奶又问。显然鬼之子的身份让她更警觉了。
晴伸开双手以示清白:“不是,您看我连武器都没拿呢!”
老奶奶不再说话,把晴的手臂从鬼女口中扯了出来,那上面已经鲜血淋漓。看到伤口,她眉头的皱纹更加深了。
“我不管你这个古怪的小鬼到底是谁,如果被我逮到你伤害她,我绝对饶不了你,你赶快走吧!”说罢,老奶奶将安分下来的鬼女护在身后,挥手赶他离开。
“谢谢您今晚的恩情,我不会忘记的!”
晴知道自己不能再待在这里,朝着老奶奶鞠了一躬,跑开了。
将信女带回慈善院花了点时间,阿梅把她带进自己住的屋子,任凭信女缠上她的身体,以此安抚她的躁动。
阿梅回忆起刚刚的一切:自己向来不干预信女的“狩猎”,但今天实在奇怪。
她见过不少次信女的狩猎,可从未见过清醒着等待被吃下肚子的猎物!还有那双眼睛,那双流露出期待和兴奋的眼睛,甚至让人没来由地产生几分恐惧……以及怀念。
阿梅发现自己竟然没忘记那双眼睛。唉,那双明亮的眼睛是从何时开始,就不再注视着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