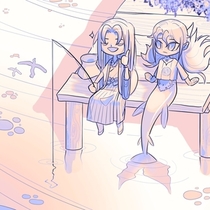Ma Jolie宋朝篇
欢迎来玩
对不起这次主线拖了很久,辛苦大家的耐心等待,下次一定写完再开!
后日谈预计将于3/5发布,计分统计将于清明节截止。




皓月当空,白岛一片静谧。皮良特地找了个人少的时间,借口自己睡不着,拉宋慧出来赏月。
虽不是满月,一弯银钩也别有一番意趣。两人在一处水潭边坐下,望着水里的月亮随意谈天。
说是随意,可皮良是存了一番心思的。他先是问了宋慧家住何方,父母如何,在心里暗自盘算说媒之事。自己要娶宋慧,家里应当不反对吧?若是反对,他软磨硬泡几日,这事也该成了,怕只怕宋家人不愿让女儿远嫁……咳,自己想这些做什么?最要紧的还是宋慧的态度,她要是不肯,自己盘算再多也没用呀!
“那,宋兄离开白岛之后,接下来要去哪里?”皮良又问。
“唔,离家久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那我能不能去你家提……”皮良话到嘴边,才察觉失言,慌忙改口,“我是说,去你家拜访!我接下来也要继续云游,若是去宋兄那里,想必方便很多。”
宋慧立刻答应:“好呀,正好让你尝尝我娘的手艺,我也好久没吃她做的饭了。”
皮良暗想,宋慧答应得倒是很快,只要自己真去了宋慧家中,她是女儿身一事可就再也瞒不住了,不知道宋慧想没想到这一层?这样也好,让宋慧坦白总好过被他拆穿,想到这里皮良不禁喜上眉梢。
“皮兄你笑什么?”宋慧好奇道。
“没什么,”皮良用手摸了摸洁白如玉的地面,刻意地转移了话题,“只是觉得这几日所见十分奇妙,处处像是仙境一般,能够来此一见,真是不虚此行了。”
宋慧也笑道:“是呀,这地方真让我大开眼界!皮兄是不是又能写个什么好故事了?”
“等从白岛离开,我肯定要将所见所闻全都记下。”
皮良一顿,又转头看向宋慧:“这几日我总在想,这世上有没有比白岛还奇妙的地方?若是有鱼仙儿,是不是也有个猫仙儿狗仙儿的,住在什么黑岛红岛,要坐上两个月的船才能到。等从白岛离开,我想去到处找找,到处看看。宋兄若是有空闲,能不能和我一起去?”
总算是说出口,皮良悬着的心放了一半,还剩另一半在空中吊着,就等宋慧开口说答案。
“好啊,要是真有什么猫仙狗仙,我也想见识见识呢!”宋慧一口答应,眼睛笑得弯弯的,像天上挂着的月亮。
宋慧走后,皮良才走到另一处水潭边,默默地坐了下来。
一阵水花打破了水面的平静,青黛探出头来,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可没故意要偷听。”
皮良的耳朵有点发烫,嘴上却说:“不打紧,又不是要紧事。”
“我若没看错,你可是喜欢那姑娘?”青黛问道。
“算是吧。”皮良偏过头去,整张脸都要烧起来。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算’是怎么回事儿?”青黛不依不饶地追问。
“没有算,我就是……喜欢……她。”皮良吞吞吐吐地说。
青黛从水潭里探出整个上半身,眼神中带着求知的欲望:“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喜欢,是什么?爱又是什么?”
皮良一时怔住,他好像还没想过这些,只好边想边说:
“喜欢,就是她高兴,我就高兴,她难过,我就难过。她在的时候,就觉得满足,不在的时候又会惦记,想一直和她一起,想多看她笑……爱,爱就是想为她付出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付出一切?包括你的生命吗?你会为了她死吗?”
“我……”皮良一时语塞,半晌才点了点头,“我会的。”
青黛看着皮良,微微摇了摇头:“这倒是奇也怪也,人都想活,爱却会让人甘愿赴死,我实在是搞不懂这其中缘由。”
“也许只是青黛姑娘还没遇到意中人吧。”说到意中人三个字,皮良想着宋慧的身影,不禁浅浅一笑。
“白岛之人来了又走,我还未曾寻得。在那之前,还是多给我些话本子瞧瞧吧。”
青黛鱼尾一甩,潜入水中,皮良以为她这就要走,没想到她再次探出头来:“说来,过几日有一场喜宴,你可曾听说?”
“倒是听说一点儿,只不过,像我这种寻常人能前去吗?”
“你若是想去,我寻张喜帖给你就是。”
“那,可不可以……”
“两张是吧?”青黛了然,又一甩鱼尾,这次是真的离去了。
青黛姑娘还真是体贴。不过眼看她将自己想法全部看透,皮良又忍不住觉得耳朵发烧了。
婚宴前夜,皮良又与青黛月下相聚。
“请帖我已备好,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青黛道,“你来这里所为何事?”
“我……就是听说这里有座白岛,白岛上有好多仙人,想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想亲自见识一番。还有那传说中起死回生的仙药,我也想看上一看,尝上一尝,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听着皮良缓缓道来,青黛的表情严肃了几分。
“你记好:若你还想坚守本心,便不要吃喜宴上的东西。将来若是出了什么岔子,莫怪我今日没提醒过你。”
“坚守……本心?”皮良重复了一遍她的话,“我不太明白……”
“我言尽于此,剩下的,就看你的造化了!”青黛说罢,留下请帖便离开了此地。皮良想不明白青黛的用意,不过在喜宴上不吃东西,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一晚,皮良睡得不大安稳。他梦见自己乘着一艘小船,在漆黑的海上摇摇欲坠。风浪将船抛起,片刻后又重重落下,一盏孤灯随着他风雨飘摇,他只能死死抓着船板,不让自己掉到海里去。
风声灌满他的耳朵,听得久了,竟然渐渐浮现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起波浪……”
“遇水起波浪……遇水起波浪呵!”
“不祥……不祥……遇水……起波浪……”
“不祥……”
奇怪的声音逐渐被一阵敲击声取代,皮良睁开眼睛,才发现门外咚咚咚的敲门声已经响了半天。他昏昏沉沉前去开门,宋慧见他这样,一脸担忧:“皮兄还好吗?”
“没事,没事,就是没睡好。”
“哦!那就行!我看时辰快到了,想叫你一道去喜宴呢!”
皮良低头看看自己穿着,摇头道:“你先去,我收拾收拾一会儿就来,对了,这个给你……”
他把喜帖递到宋慧手里,感觉还是昏昏沉沉不太清醒,原本想叮嘱宋慧的事也忘了个干净。宋慧接过喜帖,喜笑颜开地出了门,皮良也慢吞吞地穿好衣服,打着哈欠往门外走。
鱼仙儿结亲,自是在水下。宾客挤挤挨挨,皮良没寻到宋慧,只好独自得了避水鳞,跟着众人往水下去。未曾想,白岛之上层楼叠榭,水下仍然别有洞天。原来鱼仙也像人一样,住在屋舍之中,皮良啧啧称奇,将眼见景象牢牢记住,只等回去写在纸上。
等进了屋门,到了礼堂,皮良又觉得怪。这仙儿住的地方,倒不如白岛上整洁漂亮。屋瓦破旧,门上牌匾也摇摇欲坠,不像是神仙住的地方。许是好久无人修缮……是鱼仙儿自己不愿修缮吗?未曾细想,宾客落座,鱼仙儿簇拥着新人上前来。
鱼仙儿成亲,大体也与人相似,虽然那新郎人身鱼尾,可看得久了,也不觉得有多奇怪。众人目送新人拜过堂入了洞房,又被鱼仙儿簇拥着浮上水面,说是已备好了席面。
是了,在水下总是不便饮食,难怪刚刚桌上无水无酒呢!皮良了然,又看向莲叶上精致汤盏,甜香扑鼻,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他立刻感到腹中空空,想来今天自己一起床就来了这儿,正好该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可耳边突然又浮现青黛昨晚的叮嘱:
“若你还想坚守本心,便不要吃喜宴上的东西。”
身旁的鱼仙儿见皮良手里空空,将一盏小钵塞到他手中,喜笑颜开地看着他。宾客们的闲言碎语又飘进皮良耳朵里:
“这东西闻之如蜜,不会是仙药吧!”
“哎哟!我认得它,这可是好东西,你们不吃,我可吃了!”
仙药?皮良死死盯着碗里的东西,不敢相信仙药就这么到了他的手里。原来这是仙药吗?传说中,能够让人死而复生,长生不老的仙药?妇人吃下它,生下的孩子飞到了月亮上去,病人吃下它,一夜便康复如初了,它到底是什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亲口尝一尝,才能知道……
皮良端起小钵,耳畔突然响起昨夜梦中那个苍老的声音:
“……起波浪……”
“遇水,起波浪呵……”
宋慧再见到皮良时,只觉得他与往常不同了。也许是因为刚刚打湿了头发,少年的一头长发披散下来,发梢还不住地滴着水,配合上他苍白的脸色,整个人仿佛刚刚从水中爬出来的水鬼。
“皮,皮兄……”宋慧的声音颤抖着,“你……没事吧?”
“我……究竟是有事,还是没事呢?”
皮良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惨白的笑。
仙药,状似人心,色白如玉,味甘如蜜。因其美味,食之令人念念不忘。
——《乘风笔谈·白岛篇·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