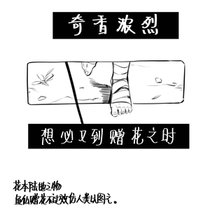Ma Jolie宋朝篇
欢迎来玩
对不起这次主线拖了很久,辛苦大家的耐心等待,下次一定写完再开!
后日谈预计将于3/5发布,计分统计将于清明节截止。
做人
崇宁年间吾在国子监求学,得数位同窗好友,其中有一陈姓书生,与吾等谈过一件奇事。
言其家中建有豪奢园囿,但仅得一鹿居,家里人称这只鹿为老祖,鹿在府邸内通行无阻,子弟见了均要行大礼,他年少时还曾因忘记施礼而被训斥。
后知其缘故,系晋朝时陈家有一子弟,单名白字,此人深有佛缘,但性格乖戾,有高僧几次至陈家欲渡他修佛,皆拒之。高僧劝道,人生苦短,施主若为佛弟子,来生可为人也。
然陈白狂妄道,你自去修你的来世,我来世就做个浮蝶儿花贼又如何呢。遂着人将其撵走。
陈白身故,至亲与他沐浴更衣,停灵于室,定于次日出殡。然次日陈白尸身踪迹皆无,只得一只浮蝶儿扑于榻上,奇大无比。众皆认为是陈白,不愿其离去,但也不敢与其接触,恐其飞走遂闭门锁窗,日间着清水、净花入内供其取食。
过了一旬,那浮蝶儿不再动弹,似是故去。家中欲以其代陈白葬之,但升棺之时,闻听棺内有扣扣扣异响,只得再次打开,视之有一虫叩首,一指来长,浑身莹白透亮,质若白玉,好食晨露。至入秋,虫亡矣,现一狸奴,雪里拖枪,硕鼠避之不及。因此事奇异,遍传乡野,远近有好事人来家中打探。而至亲本就不舍陈白离去,其又数次死而复生,且转生之物命数皆短,不若人之长寿,盼望终有一日陈白能得人身与之团聚,于是将陈白化物养于家中。
后来晋灭,南北并立,又至隋唐亦亡,世事变迁,陈白与家人仍共度春秋,但原先的至亲早已仙去,后代均称之为老祖。
到陈生这代,老祖已化鹿多年,日渐衰竭。
吾等均认为此乃陈生戏言,但数日后,不见陈生,问其师才知陈生乃请假奔丧,待其回转后与吾等见面,陈生叹道,老祖去矣。
方又解释,此次老祖竟化为异仙,人首鱼身,貌若青年,体态健硕,尾有一丈,能通人言,是族谱从未记载过的情形,遂焚香祭祖,禀告陈白归来,前人夙愿已了。
后陈白着人送其入海,陈家子弟数次询问是否伺候不周,才要离开。
陈白答道,非也,我活了五百多岁,转世不知凡几,这才知晓,做人有做人的情趣,可是不做人也有不做人的快乐,和人住在一起已经不符合我的本性了,只是我此前没有机会告诉你们,但这次我终于可以去做鱼了哩,我很欢喜。
于是陈家自泉州送陈白入海,此后也没有人再见过他了。
————————————————————
造梦
有一生名为皮良,肚中有文章千余,一日夜间听到有人在窗外细声细气道,先生,我白日里听书,甚为好奇,可否到你处一观。
皮良不及拒绝,遂感到有人穿堂入室,携手而游。初始如入混沌境,除身边伴游外空无一物,后过崎岖山路,唯头顶有光,然一过狭口,星河山川撞入眼前,万物奇诡壮丽,与常世无一相同。尚未待他细看,蓦然间日月同天,龙凤齐鸣,飞虹落霞转瞬即逝,又现城郭楼宇,熙熙攘攘,朝代更迭,时空流转,一夕之间窥见千年。
皮良乃是凡人,如何能抵挡此等洪流,只觉得头晕眼花险些闭过气去。游伴牵引其游玩一夜,赞不绝口,归家后仍是在窗外道谢,今次对不住先生哩。但先生肚中景色确实宏伟,见地非凡,凡人无缘得见甚是可惜,不如我赠一日,先生可给世人观之。
次日皮良洗漱完毕,遇好友至,遂将夜游一事告知。
述至一半,只听外间惊呼不已,人声鼎沸不绝于耳,与友人外出,只见街头巷尾人潮涌动,对着空中指指点点,抬头一看,只见半空云雾之中异像频频闪现,有亭台楼阁才子佳人私会述情,又有千军万马两军对峙取敌寇首级,还有那神鬼妖狐精怪伴着天庭众仙巡游,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令人目不暇接,全是皮良所讲过的传奇异闻。
友人细看之下,发现在如此热闹的碧空边缘,云层之后有一鱼仙左顾右盼牵着一摇摇欲坠的人影走过,那人看来就和他身旁的皮良长得一模一样。



*一些关于挽妹土哥的过去补充
(一)
一夜之间,兄长突然从濒死的状态恢复过来,健康得和常人无异,而整日沉默着、以泪洗面的母亲因为得而复失终于在这一刻放声大哭,被压抑了数日的悲恸震耳欲聋,在门口的唐挽看着母亲,最后还是没有走上前。
病榻上,穿着单薄、只一件单衣的少年面色虽仍旧苍白不见血色,却没有病人应有的隐忍痛苦的神色,唐竹看见她,露出一丝微笑,唤道:“阿挽。”
自己和兄长的关系并不差,今日之前,她也同母亲一样,因为大夫定言的不治之症而落泪,按理说此刻应该喜极而泣,扑过去和儿时那样亲密地说上几句话,可偏偏在看见少年朝自己自己招手的时候,唐挽迈出的第一步悬在空中,犹如被仙法固定石化,怎么也落不下去。
哪里不一样了。
可到底是哪里?除去不再孱弱的身体,眼前的人分明和兄长没有半分不同,就连唇角微笑的弧度也如此流畅,没能让她寻到丁点的破绽。
是错觉吗?是因为不敢相信吗?她本已经做好和兄长诀别的准备,事情却突然有了不可思议的转机,这是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情,她应当高兴,应当庆祝,可为什么她却觉得有东西在悄无声息间带走了真正的唐竹,留下一个待填补的虚无的壳子,用他们的回忆作二次填充,再构筑出这样精心的、飘忽不定的幻想。
“哥哥。”
她走过去,握住兄长冰冷的手,试图从往昔的回忆里捕捉他的漏洞,她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妄想找到躲闪和思考的痕迹,可少年只是用那双温和的、平静的眸子静静地回望,对一切问题对答如流。
完美的,和记忆里没有任何区别的兄长,唐挽同他告别,回到自己的房间,夜深露重,她看着窗外垂下皎洁光芒的月亮,反复告诉自己只是想多了,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二)
父亲和母亲带着贵重的礼物,带她和兄长去了隔了几条巷子的杨府。
大人们在交谈,唐挽实在不喜欢那样的氛围,盯着面前还冒着热气的茶盏。茶香氤氲着,缭绕着,她想到那些自己陪母亲前去拜访的寺庙里久久未能散去的白烟,好像也是这样,带着诉求和代价来,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还愿——她听见母亲颤抖的声音和反复的感谢。
在她出神怔愣的时候,父亲叫了她的名字。她抬起头,不知何时,厅堂里多出了一个人:在她面前的少年约莫与她同岁,穿着精致而繁琐的衣物,他站得端正,皎如玉树,惊才风逸,行礼问好时亦雍容不迫。
父亲夸赞的声音响起:“令郎可真是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少年露出恰到好处的腼腆,作出回应,表示惶恐,从他们的对话和表情中不难看出,父亲很欣赏他。
笑声过后,她看见少年父亲抬起手:“承圭,带唐小姐出去逛逛吧。”
于是那少年走过来,在这之前他们分明素不相识,他看起来早就认识了她,态度熟稔,像她真正的兄长那样——他甚至知道她的名字,叫得亲昵,好像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
“唐挽妹妹。”他边笑着,朝她伸出手,“我带你去看看池塘的鲤鱼吧。”
彼时唐挽尚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明了他那颗乍看鲜活的心里面都是各种漆黑粘稠的东西,她只是下意识厌恶每一个试图套近乎的人,她躲开他的手。
可杨承圭并不尴尬,只是慢慢收回手,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声音依旧温柔得如化雨的春风:“还未自我介绍,我姓杨,杨承圭,与你兄长同岁,你亦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兄长。”
他们离开厅堂,来到杨府的花园,假山旁的池塘里,鲜艳的鲤鱼游动着,唐挽看着他,一字一顿、极其认真地纠正他:“你不是我兄长,我只有一个兄长。”
杨承圭如无暇白玉般天衣无缝的笑容终于在此刻有了些许的松动,可唐挽只看见那裂缝一瞬,很快被填补,崭新如初。他笑着,摇了摇头:“没关系。”
没关系,他接着又小声道,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这便是她与杨承圭的初遇,她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在所有人夸奖他的时候不屑一顾,可杨承圭无动于衷,只是看着她,那目光里有她看不懂的艳羡。
(三)
那之后,不知道大人们达成了何种协议,两家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一开始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导致对方屡次出现在唐府,再后来,杨承圭住了进来。
起初他也试图邀约唐挽一起看书、逛灯会,偶有出门,更是会给她带上一些小物件回来,但她通通拒绝,毫不留情,就连母亲的指责也没能劝动她。
或许是因为处在同一屋檐之下,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渐渐缓和,若是没有刀术课程和其他要紧事,唐挽会同意他的邀约,也开始接受他送给自己的礼物,并且思考该以什么回礼。她送过不少墨宝,除此之外未曾想到有什么合适,偶有一次提起,杨承圭只道,不必费心去思考,哪怕是同类的礼物,只要是阿挽送的,我都很开心。
唐挽只觉得他奇怪,干脆要他自己挑选想要的礼物,可杨承圭却固执地重复着她以前送过的那些物件,且累教不改,于是她只能作罢。
后来唐挽发现,他和兄长的关系不错,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一同出门。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同一类人,她从下人那里无意间听见过相似的评价,内容有些无聊,多是些讨论外貌和性格的话语。但是,“杨小少爷真是个好人”,这句话的出现频率太高了。
不可否认,杨承圭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具体体现他会帮助每一个向他寻求帮助的人,再麻烦的事情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的称赞。
在不知道多少次目睹他为了答成别人的请求累苦累活忙得焦头烂额,唐挽拦住他:“你就不知道拒绝吗?”
杨承圭听见她的话,抬起头,重复着她的话:“‘拒绝’?”他笑着反问,那笑容竟然透露出几分诡异来,“是啊,我怎么不拒绝呢?”
唐挽跟了他一路,看着他从邻家的小女孩帮到集市的摊贩,她终于确定一件事,杨承圭是个不知疲倦地帮助人的疯子。
“你当真是疯了。”她道,“如果你不愿意拒绝,你可以让我帮你拒绝。”
杨承圭先是一愣,随后笑道:“没关系的,阿挽,你对我真好。”
(四)
发现杨承圭不对劲的那天,他也是这么笑着,用这样温柔的语气对她说,阿挽,你对我真好。
彼时杨承圭刚同意了他人堪称无理的请求,随后他回了房间,唐挽在那一刻终于确定,他或许不是一定要帮助别人,而是因为他无法拒绝。他病态地完成着所有人的委托,不管合理与否,不管会对自己造成如何影响,仅仅是因为他无法开口说“不”,而那曾几何时无意间泄露出的她无法理解的神情,那是来自于杨承圭对她的羡慕,羡慕她有说“不”的能力。
要他帮忙的人似乎是拿准了杨承圭无法拒绝,要求被同意后露出小人得志般的狡猾笑容,唐挽忍无可忍,走上去拽着对方的领子质问对方为何如此厚颜无耻,却得到一句“可是他同意了,除非你让他亲口拒绝”的回答。
她松开对方的衣领,转而怒火朝天地往杨承圭的房间走去。
透过门缝,隐约能瞧见里面人的背影,唐挽实在过于生气,以至于忘记了所有的礼节,未曾敲门,就这样猛地推开门,冷声命令道:“你现在就跟我出去,把那人赶走,再也不准——”
这命令的声音戛然而止,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失去了声音,愣在原地,睁大了眼睛,接着就要尖叫起来:“杨——”
“嘘。”
冰冷的食指贴上她的嘴唇,杨承圭跌跌撞撞起身,脸上难得露出慌乱的神色,此刻二人凑得太近,放大了数倍,因此格外清晰,就连眼角眉梢都有藏不住的情急。
嘀嗒——唐挽低下头,发觉红色的液体落在自己的衣摆,于瞬间绽开成一朵花的形状,还有几滴落在她的脚边,轻易将地毯染上了颜色。她死死地盯着他的另一只手,浑身都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能用眼神询问。
在她推门而入的瞬间,杨承圭正拿着一把匕首,对准自己左手的手腕,面无表情、毫不犹豫地切了下去,就像是在处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他的声音里带着几近祈求的语气:“阿挽,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等、等等。”唐挽慌乱地撕下自己的裙摆,想要去为他包扎,又怕动着他的伤口,“我……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杨承圭轻轻地“啊”了一声,他就像没有痛觉、没有感知那样后知后觉地抬起手臂,任由她处理。
在小心翼翼包扎伤口的时候,唐挽注意到,他的小臂上林林总总留下了不少的伤口,她沉默着、一言不发地处理完毕,再抬头看他,意识到他已然是惯犯。
“不痛吗?”她问。
“其实还好。”杨承圭低着头。
“杨承圭,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他的声音轻得快要散在风里,“是啊,为什么呢?”
唐挽道:“迟早有一天你会死的。”
“他们都不是真心喜欢我的,只是因为我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父亲也好、家中的弟弟妹妹们也好、还是这座城镇里的其他人,大家都是因为有利可图才态度亲切。”杨承圭却答非所问,“阿挽,我来到你家这么久,只有你不需要我,只有你讨厌我,只有你关心我……只有你是真心的。”
他的胸前还留着大片大片被染透的红,杨承圭微笑着抬起头,认真而固执地看着她,唐挽在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瞧见了一个心慌意乱的自己。
“阿挽,你对我真好。”他的声音如同蛊惑人心的魔咒,引诱着她坠入深渊,“这么多人里只有你是真心在意我的,只有你。”

封爵
商溪,开封人士,今少府监丞也。
传其夜梦使者扣门,恭敬有礼地问道,郎君起了吗。
商溪出言相询,门外答道,吾乃祖龙使者,王军已至闽越,奈何敌众,苦战良久。今闻郎君奇技,请君相助。
不待其回答,强请三声,请也。请也。请也。旋即人即已至沙场,始觉胯下骑名驹,手中持长刃,身后阵列万人,虽因逆光故众兵丁面目无法检视,但气势雄浑,默然待其指令,属实为精兵也。又见对阵有一奇伟将军,顶盔掼甲、罩袍束带,日照下银鳞甲胄光彩夺目,身后亦兵多将广,人强马壮。
两军对峙间,使者于场中提声叫道,若成,君可得三公之位矣。
其声高亢,宛如雷霆,亦不知是向哪方言语。此言毕,忽闻杀声震天,人头攒动,瞬息敌将已奔至近前,以长枪与商溪你来我往战过数十回合,而两军将士更是冲入敌对阵中,搏命厮杀。如此交战一夜,众皆感到筋疲力尽,待敌寇尽除,五更鸡鸣,商溪方才从战中脱身,这时手腕抖如筛糠,甚至无力取杯饮茶了。
此后一月中,其夜夜为此东奔西走,征战四方,逐一平定南粤、西瓯,无一晚闲暇,但战斗愈久愈是娴熟,已没有当初的惶恐了。
是夜使者至,激动道,今日终局也,已替郎君请丞相位。郎君请上阵。
商溪淡然起身,逐一净手、洁面、更衣才与使者共赴疆场恶战,并以霹雳手段于阵前斩下首领头颅,遂登殿,提敌首献君受封,闻得头顶有男子之声乐道,吾胜之!
这男音浑厚,震耳欲聋,使商溪陡然梦醒,此时他手中还抓着半粒珍珠棋子,浑圆洁白,自中对半剖开。
后此事传开,世人皆说,是神仙对弈,抽世人神魂做棋,那枚珍珠白棋就是敌方首领。而商溪有功得神仙赏赐才能步步高升呢。
————————————————————————
做官
开封商溪,少府监丞,对奇珍异宝颇有见地,好茶。
有一日冲泡龙园胜雪,汤出白玉壶,八分满,置于茶盏中待凉。饮时,见茶汤中有仙,人首鱼身,银发青尾,大小只一寸有余,将一细物托举出水。
商溪顺意取走托举之物,那物入手后见风即长,是一卷文书。
又见鱼仙搅动鱼尾,掀起细密泡沫,沫上浮现图纹。盏中显一近海溶洞,礁石林立,有一砗磲,壳内满载珍珠,仙卧其上,那些微末珠子惟妙惟肖,又有一人影自壳中搂取珍珠,人影随茶汤晃动,窃珠举动亦栩栩如生。
茶沫消散后鱼仙亦不得见。文书展之,为某地房屋地契。
商溪遂至某地,询之,地契失而复得屋主却并不据实相告。商溪予以百金买其屋,被拒。再加价一倍,仍被拒之门外。后以权谋之,夜居其屋,商溪梦一斗,斗大若室,内中圆珠手插不进,数次取之,缺口仍顷刻补满。
梦醒后,床榻之上满是珠子晃动,莹白圆润,流光溢彩,盈千累万。
甚喜,又于沿海搜寻溶洞,数月后寻至一洞,外观相仿,入内见水中庞大砗磲盛有上等海珠,虽是梦中取走之数甚巨,但仍在壳中余下小半。
洞外又有数条破损海船堆叠,有大有小,乃是近年走失商船,内有残损货物。
商溪凭海珠升官发财,以为奇,与友谈之,友笑道,鱼居于海,卧于贝,珍珠若其丝衾,人至贝中取珠,谓之盗。开封包公断案素有威名,虽包公已逝,但它又能从何处得知呢?你与包公相邻,此鱼状告盗匪至你处,是它误入歧途了。但你将寻得之物据为己有,已开罪于它,依我愚见,余生你切莫近水为好。
——————————————————
来放个之前的链接:
《夜行舟》《石羊》《还债》: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168/
《复生》: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199/
《做人》《造梦》:http://elfartworld.com/works/9377233/


*虽然很少但是有寄生虫的描写,在最后面
1110字
“真要坐这儿吗?”
“就坐这儿吧,不是想看真亮一点吗。”
“我怕血崩我一身。”
“别废话了快看吧待会儿结束了。”
不知道还以为菜市场有人问斩呢,其实是圆子和侍应(他自称)出来透透凉气。
避开人多的地方,再吃点,呃,凉的东西。
岸上再怎么热,也影响不到水里,甜瓜放井水里镇一镇又解渴又美味。再就是地窖里存的酒,应付亲朋好友来玩耍游戏,就是容易喝太多。
可惜现在身在他乡,这两样都没有,圆子想去周边找找能拿得动的带回去,难得出来一次总不能空着手啊。
所以他现在得坐在最前面看人切鱼了。
客栈里一点也不凉快,甚至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有人说拿刀的师傅师从某个酒楼名厨,被他取卵的乌鱼扔回水里还能游动如常;有人说他那把细长尖刀是用极北之地的罕见金属打造,一出鞘便带着丝丝寒气,鱼生怕热,什么不怕热啊,反正新片下来的鱼肉放进嘴里鲜活得好像能在嘴里活过来一样。讲乌鱼的那个八成是烦了,一巴掌把正说话的这个手里攥的小报打掉,让他别照着念了。圆子听得刚有点意思,只能把目光聚焦在砧板上,刀他不认识,鱼就更不用说了,只记得鲤鱼比鲫鱼大一圈,草鱼和鲤鱼站在他面前,他能直接拉着它俩结拜兄弟。
眼前这条鱼还算仁慈,给他看见白的那面,白的那面是肚子,黑的是后脊梁。刀顺着鱼头“哧溜”钻进鱼皮和鱼肉的缝隙中间,没见一滴血。
“哎你看,没崩我身上。”他冲侍应努努嘴,侍应回给他一个绝望的表情。
他没看见盛着鱼血的盆子就在鱼头边上,在旁边俩人吹牛的时候悄悄把岗占了。
这个眼神确实不能再搁开封写邸报,漏点啥内容臭骂一顿都是小的。好在鱼血腥,圆子闻见后有点不好意思地闭上嘴,继续看杀鱼。前一条鱼的脊梁骨囫囵个地从鱼嘴里掏了出来,方才还热衷于分享小道消息的看客顿时觉得小报索然无味,眼珠子恨不得贴砧板上,好窥得其中奥妙。下一条皮肉分离,肥肥的肚肉如纸薄——圆子说的绝不是邸报的纸,那纸放在鱼肉前还要自愧不如。一条又一条的鱼经过砧板,圆子也渐渐瞅得有点乏了,他想,切鱼的人天天切,是不是也乏了呢。
临走前他让侍应帮他买那条细长如裤带的鱼,“剁成段放点油炸一炸就很好吃了,刺在脊梁和两侧一共三条。”杀鱼的驾轻就熟地说,指着另一个黝黑的人:“钱给他。”说完又包了点鱼生问他吃不吃。
圆子毕竟也生在有水的地方,觉得鱼生没什么味,只拿着带鱼走了,用油炸过果真鲜美,不配小菜都吃了好几碗饭。不久后他听说有人吃了有虫的鱼生,肚子里翻江倒海痛得要死,大夫从嗓子里钳出几条棉线似的虫子依旧上吐下泻,听得他一阵后怕。
“那这人之后怎么样了?”
“似乎是吃了白岛来的仙药,啪地一下就能下地蹦跶了。小伙子有兴趣不,再给十文就接着讲哦。”
老头把手伸到圆子面前。
圆子没少听噱头全压在前面的故事,觉得十文钱也买不到什么压箱底的东西,摆手说不了不了,遂从顺水客栈出去。